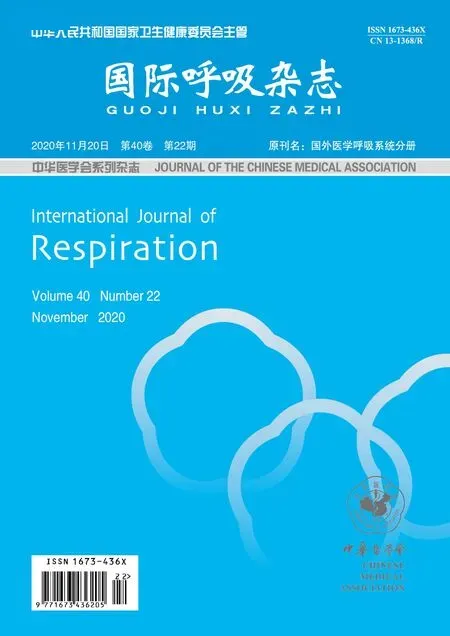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李芯雨 陈中琦 吉宁飞 张明顺
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 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211166;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210029
截至2020年9月13日20时,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 me coronavirus 2,SARS-Co 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已造成188个国家或地区超过2 878万人感染,92 万人死亡(数据来自John Hopkins CSSE,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 ml)。ARDS 是一种以急性起病的严重呼吸困难、顽固性低氧血症、弥漫性肺泡损伤并进展为急性呼吸衰竭为特点的临床综合征,具有起病急、发展快、预后差、病死率高等特点,是COVID-19重症患者的常见致死原因之一[1]。本文将从COVID-19合并ARDS角度综述最新的临床和研究进展。
1 流行病学
目前的临床资料显示,ARDS是COVID-19的常见致命性并发症之一,COVID-19 的病死率有近50%归因于ARDS[2]。在疫情较重的武汉市,一定点医院收治的41例患者中,12例 (29%)合并ARDS,从出现症状到发展为ARDS时间的M(QR)为9 (6)d,从出现症状到需要使用机械通气时间的M(QR)为10.5 (7)d,进入ICU 时间的M(QR)为10.5 (9)d[3]。有时病情进展非常迅速,COVID-19可在2 d内发展为ARDS[4-5]。武汉金银潭医院99例住院患者中17 例 (17%)患者出现ARDS,其中11例 (11%)病情迅速恶化,最终发展为多器官衰竭而导致死亡[1]。纽约市首批收治进入ICU 的300例患者中275例(91.7%)符合ARDS 标准,该组患者30 d 存活率为43.6%[6]。韩国永安大学医学中心一项回顾性研究的98例确诊患者中,13例符合ARDS且全部接受ICU 治疗[7]。一项纳入6个研究、50 466例患者的荟萃分析得出因COVID-19住院的患者ARDS发生率为14.8%[8]。
2 临床症状与危险因素
识别COVID-19合并ARDS的临床特征有利于尽早治疗,最常见的初始症状依次为发热、干咳、鼻塞。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一项纳入84例COVID-19合并ARDS患者的队列研究中,ARDS患者与无ARDS患者相比呼吸困难的发生率更高[5]。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入院时有乏力症状的患者更易出现ARDS[9]。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入院时出现呼吸急促及呼吸困难的患者更易发展为重症及出现ARDS[10]。在广东省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中,45例重症患者中37 例 (82.2%)出现了ARDS[11]。相对于轻症患者,重症患者发生ARDS的比例更高。武汉中南医院221例住院患者中无非重症患者出现ARDS,而87.3%重症患者出现ARDS[12]。高龄 (>65 岁)、发热(≥39 ℃)、高血压、糖尿病、嗜中性粒细胞增多、淋巴细胞瘤 (以及较低的CD3+和CD4+T 细胞计数)、器官功能障碍、炎症相关指数升高 (高敏感度C-反应蛋白和血清铁蛋白)及凝血异常 (凝血酶原时间和D-二聚体升高)都与ARDS发生的较高风险显著相关[5]。针对COVID-19 重症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男性、高龄 (>65岁)[13]、既往有糖尿病、脑血管病和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9]更容易出现ARDS。此外,在COVID-19 中ARDS 的严重程度与APACHE Ⅱ、SOFA、CURB评分正相关[9]。何为群等[14]分析了25例SARS合并ARDS患者病例后指出,高龄、缺氧持续的时间长、血小板减少、高血钠、血肌酐升高为SARS合并ARDS 患者死亡高危因素。COVID-19 合并ARDS发生的高危因素及其发生机制尚有待进一步阐述。
3 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尤其是血气分析对于COVID-19 和ARDS的诊断、分级和病情转归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成年患者符合下列任何一条即为重型COVID-19:出现气促,呼吸频率≥30 次/min;静息状态下,指血氧饱和度≤93%;氧合指数≤300 mm Hg(1 mmHg=0.133 k Pa)高海拔地区 (海拔超过1 000 m)地区需要根据以下公式对氧合指数进行校正:氧合指数×[760/大气压 (mm Hg)];临床症状进行性加重,肺部影像学显示24~48 h内病灶明显进展>50%者[15]。而对于ARDS的诊断,柏林定义依氧合指数将ARDS 分为轻度(200~300 mm Hg)、中度 (100~200 mmHg)、重度 (≤100 mm Hg)3 个等级,合并ARDS 患者均属于重型COVID-19。浙江省的一项多中心91例患者的病例报道中,18例表现出Pa O2下降[16]。中南医院ICU 44 例重症患者Pa O2的M (QR)为66 (34)mm Hg[1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住 院 患 者 死 亡 前 24 h Pa O2的M(QR) 为47 (21)mm Hg[17]。合并ARDS的患者相比于无ARDS患者,氧合指数下降明显 (145 mm Hg比475 mm Hg)[9]。此外,合并ARDS的COVID-19患者相比无ARDS患者,外周血淋巴计数下降,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尿素氮、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升高,且与其ARDS 严重程度相关[9]。Gibson等[4]提出血液中的白细胞数、外周血淋巴数、C-反应蛋白水平对于提示COVID-19合并ARDS有重要意义。
4 影像表现
影像学检查对于识别和管理ARDS具有一定意义。尽管病因不同,ARDS的影像表现存在一些共同点:发病12~24 h内,常表现为间质性肺水肿,双肺弥漫性密度升高,透亮度下降,可有小片状模糊阴影;发病1~3 d后,双肺呈现出肺泡性肺水肿改变,先表现为斑片状,随后融合为大片模糊阴影[18];当肺脏出现实变时,双肺野普遍变白,常称 “白肺”,心影轮廓消失,仅肋膈角处残留少量透亮影像;发病7 d后,肺部阴影逐渐消失,部分患者肺部残留纤维化。COVID-19患者的胸部CT 影像普遍异常,60%以上呈现双肺磨玻璃影和实变,实变病灶在重症患者中更常见。重症患者的胸部CT 影像常出现双肺弥漫性病变,以实变影为主合并磨玻璃影,部分重症患者出现 “白肺”,转归期病变吸收、消失,有残留纤维索条影[19]。1 例重症COVID-19合并ARDS、败血性休克、MODS的患者的CT影像显示炎性病变、肺周磨玻璃影和kerley线,提示患者存在ARDS相关的肺水肿和肺纤维化[20-21]。2例意大利的输入性病例后续进展为ARDS,X 线和CT 扫描结果显示,患者肺部除了多处斑块状玻璃混和铺路石征外,还发现肺血管管径扩大而内径缩小的非典型病变,原文作者认为是肺部恶化的早期放射学体征[22]。
5 病理特征
1例尸检报告发现COVID-19患者存在双侧弥漫性肺泡损伤伴细胞纤维黏液样渗出,右肺有明显的肺泡上皮细胞脱落和透明膜形成,左肺显示肺水肿与透明膜,提示ARDS[23]。一项回顾性研究在COVID-19 重症患者发病早期阶段的肺组织标本中,发现了弥漫性的肺泡损伤 (包括肺泡水肿与富含蛋白质的渗出液)、血管堵塞、局灶性纤维蛋白簇和炎细胞浸润,以及肺泡上皮细胞增生和间质增厚[24]。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点均与ARDS产生的病理生理有关。
6 治疗
6.1 呼吸支持
6.1.1 氧疗 ARDS患者表现为顽固性低氧血症,而氧疗是缓解低氧血症的基本手段。氧疗可以通过增加肺泡气氧分压,从而提高Pa O2,纠正低氧血症,缓解因缺氧导致的呼吸肌疲劳,降低心脏代偿性做功。应当根据患者的呼吸困难程度与治疗反应选择合适的氧疗方案。临床常用的氧疗方法包括:经鼻高流量氧疗、面罩吸氧法、气道压力释放通气等。其中经鼻高流量湿化吸氧常用于治疗轻症ARDS,常用通气流量是40~60 L/min,并根据患者的氧饱和度情况,选择合适的吸入氧浓度,保证患者的Sa O2不低于95%,呼吸频率在25~30次/min。
6.1.2 机械通气
6.1.2.1 无创机械通气 常规氧疗主要用于轻症ARDS,多数患者一旦诊断为ARDS,应尽早进行机械通气。COVID-19一线治疗人员提出,COVID-19 合并轻、中度ARDS的患者在无明显禁忌证时可以采取无创正压通气,但如果患者呼吸状况2 h未得到改善,呼吸频率>35次/min,潮气量>9 ml/kg,或氧合指数<150 mm Hg,无论氧饱和度多少,应当立即进行有创机械通气。此外,还需观察患者对无创正压通气的耐受性,若患者出现焦虑、失眠、甚至意识障碍时,应考虑有创机械通气[25]。
6.1.2.2 有创机械通气 尽早主动进行气管插管并使用肌肉松弛药物可以使重症ARDS患者的肺部尽早得到休息,降低炎症反应[26],减少肺应力损伤。ARDS治疗指南推荐采用肺保护性通气策略,主要内容包括小潮气量通气、控制气道平台压不超过30~35 c mH2O (1 c mH2O=0.098 k Pa)、肺复张、采用合适水平的呼气末正压和保留患者的自主呼吸[27]。患者病情稳定后则及时撤机,常用撤机指征主要有:(1)诱发呼吸衰竭的原发病得到控制。(2)氧合状况稳定。氧合指数≥200 mm Hg、最大吸气压<-25 mm Hg、呼吸指数<80,提示易于撤机;呼吸指数>105,提示难于撤机。(3)循环状况稳定。(4)无明显的呼吸性酸中毒。
6.1.2.3 机械通气后续护理 气管插管后应及时进行气道管理,及时清理口腔与气道分泌物,警惕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推荐密闭式吸痰管,避免中断呼气末正压造成肺不张[28]。ARDS患者机械通气时常使用镇痛镇静药物,以保证人机协调,避免呼吸机造成的肺损伤,但过度镇静可能会导致患者失去自主呼吸能力,不利于COVID-19患者的预后,WHO 不推荐氧合指数<150 mm Hg 的COVID-19患者使用神经肌肉阻滞药物[29]。无禁忌证的情况下,患者可采用30°~45°半卧位,避免胃肠内容物反流入下呼吸道,引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此外,既往研究表明在机械通气时采用俯卧位可以提高接受保护性肺通气的ARDS患者的生存率[30-32],WHO 也强烈推荐重症COVID-19 合并ARDS患者保持12 h/d俯卧位通气[29]。
6.1.3 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ECMO 是一种体外心肺替代技术,CESAR、EOLIA 及后续研究揭示V-V ECMO 是严重ARDS患者的挽救性治疗措施。魏翔等[33]提出在本次COVID-19 中,ECMO 撤机的成功率较低,应当在病情恶化迹象出现早期使用ECMO,而不是将ECMO 作为补救措施,提升ECMO 救治的成功率。包含10个国家,54个合作中心的欧洲ICU 注册系统收集的398例危重患者在进入ICU 的前7 d 中,293 例患者诊断为ARDS,11 例患者使用了ECMO,7 例患者幸存[3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9 例行ECMO 辅助治疗的患者均有效改善低氧血症[35]。针对合并ARDS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提出,应该尽早为出现严重呼吸衰竭的患者提供ECMO[36]。
我国的一项COVID-19救治专家共识提出,经过标准的ARDS机械通气治疗后仍然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若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考虑启用ECMO:(1)氧合指数<100 mmHg;(2)气道平台压>35 c mH2O;(3)PaCO2>50 mm Hg 且p H <7.25[28]。此 外,有COVID-19医护人员提出可以放宽ECMO 的上机指征,在积极救治的情况下,若患者的病情仍然持续进展,氧合指数<150 mm Hg,预计还将恶化时即可上机,改善机体的缺氧状况[25]。在COVID-19中,ECMO 术后的个体化护理监测对救治的稳定性和成功率至关重要。监护的主要内容包括实时监测ECMO 管路通畅、设备运转正常,患者出血及凝血情况、呼吸功能状况、血流动力情况、尿量,对患者进行镇静护理,控制感染,预防压疮,自身防护交叉感染等[37]。
6.2 抗病毒药物 目前尚无有效的抗SARS-Co V-2 的药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提出可以试用的抗病毒药物包括:α-干扰素、利巴韦林(建议与干扰素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应用)、磷酸氯喹、阿比多尔以及多种中药[15]。具备抗2019-n Co V 潜能、临床易获取且性价比高的药物主要包括干扰素、阿比多尔和磷酸氯喹,但确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还需进一步观察。6.3 抗菌药物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指出需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但对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必要时可以给予抗菌药物治疗继发感染[15]。武汉一项221例COVID-19患者的数据分析指出,接受侵入性导管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发生二次感染,包括院内多重耐药病原体,如鲍曼不动杆菌、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肠球菌[12]。一项荟萃分析指出ICU 患者有更高的细菌共同感染率[38]。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根据病原学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对于气道开放的危重型患者,在积极寻找病原的同时,应尽快给予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具体用药方案可以参考 《中国成人医院获得性肺炎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8年版)》[39]。
6.4 免疫治疗 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重症患者相比于轻中度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CD8+T 淋巴细胞比例、IL-6、IL-10、IL-2和γ-干扰素水平升高[40]。对COVID-19 合并ARDS的患者外周血流式细胞检测发现,CD4+T 细胞和CD8+T 细胞显著减少,CD4+T 细胞中促炎性CCR6+Th17的浓度增加,CD8+T 细胞毒性增强[23],提示异常的免疫功能是COVID-19合并ARDS发生的危险因素。相关回顾性分析指出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可明显提高危重患者生存率[41]。靶向免疫细胞的免疫治疗也是可能的方法之一。
6.4.1 免疫调节剂 α-干扰素和胸腺肽α1 是COVID-19治疗中常用的2种免疫调节剂。α-干扰素可按照成人每次500万U 或者相应剂量,加入灭菌注射用水2 ml,2次/d雾化吸入使用[15]。胸腺肽α1 是一种双向免疫调节剂,有学者提出对淋巴细胞计数降低、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可考虑使用胸腺肽α1[28]。
6.4.2 免疫球蛋白 对双肺广泛性病变、实验室检测IL-6升高的重症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托珠单抗治疗[15]。北京协和医院提出重症患者可酌情早期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0.25~0.50 g/ (kg·d),疗程3~5 d[42]。
6.5 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 康复者恢复期血浆中存在中和抗体。既往研究发现,针对HIV-1的中和抗体参与游离病毒清除和阻断新感染,并且加速感染细胞清除[43-44]。此外,恢复期血浆治疗可降低甲型H1 N1流感及SARS-Co V感染患者病死率[44]。 《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临床治疗方案 (试行第二版)》明确提出,针对病情进展较快、重症、危重症的COVID-19患者,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康复者恢复期血浆进行治疗[45]。首期恢复期血浆治疗结果显示,患者接受治疗12~24 h后,血氧饱和度提高,病毒载量下降,主要炎症指标明显下降,淋巴细胞比例上升,患者的临床体征明显好转[46]。筛选出中和抗体滴度高的恢复期血浆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新手段,同时也应当警惕血浆质量不稳定、病原体血液传播、过敏反应等风险。
6.6 皮质类固醇治疗 回顾性多中心研究分析武汉市150例患者资料后发现,导致COVID-19高病死率的因素可能是病毒激活的炎症因子风暴或心肌炎[47]。欧洲ICU 注册系统的入院和治疗数据表明,危重患者的特点是细胞因子和细胞驱动的炎症和凝血激活、严重缺氧,约24%的病例进展为多器官衰竭和死亡[34]。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ARDS与炎症因子风暴密切相关,糖皮质激素可能通过激活ACE2受体和降低IL-6 水平发挥作用[48],减轻全身炎症反应状态,改善肺渗出、损伤[49]。适当使用糖皮质激素还可以减少患者使用机械通气的机率[50]。对武汉市中心医院连续收治的30例危重症患者和同时间段随机纳入的30例非危重症患者的对比分析中,90%危重型患者和50%非危重型患者使用了糖皮质激素,以期降低过激炎症反应的损害[51]。
关于糖皮质激素在COVID-19中的使用存在争议。有文献提出早期使用皮质类固醇会提高血浆病毒载量[52],也有病例报道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以改善血氧饱和度、影像学表现[5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指出,对于氧合指标进行性恶化、影像学进展迅速、机体炎症反应过度激活状态的患者,可以短期内(3~5 d,不超过10 d)酌情使用糖皮质激素,建议剂量相当于甲泼尼龙0.5~1 mg/ (kg·d),同时警惕较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免疫抑制作用[15]。
So等[2]报道的7 例接受机械通气的COVID-19 合并ARDS患者均进行了高剂量短期糖皮质激素治疗,糖皮质激素使用中位时间为13 d,7例患者的发热和缺氧均得到改善,C-反应蛋白水平显著降低;不良反应包括5例患者出现高血糖,2例患者出现妄想。一项纳入200例COVID-19患者的开放标签试验发现,短期高剂量使用地塞米松能够降低机械通气治疗 (包括ECMO)患者的28天死亡率[54]。
7 预后
COVID-19 合并ARDS 患者的病死率极高,且随着ARDS的严重程度升高而升高[13]。通过对武汉710例确诊患者病例分析发现,35 例患者出现ARDS,病死率达74.3%,提示预后不良[13]。相关研究整合了7 036份英国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在线调查的数据,患者反映受到与日俱增的焦虑和压力的折磨,疫情已经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消极影响[55]。由于COVID-19为新发疾病,目前尚无法获得COVID-19合并ARDS幸存者中长期恢复状况的资料。鉴于COVID-19的感染方式、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特征与SARS的相似性,可以参考SARS患者的康复状况。根据对46例SARS幸存者的肺功能和运动能力评估,23 例 (50%)幸存者存在轻度肺功能障碍,41%的患者存在非通气受限的运动能力低下[56]。一项为期2年、纳入123 例SARS幸存者,针对其肺功能、运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的前瞻性研究显示,52%的幸存者肺泡内弥散通气受损,且CT 结果提示肺纤维化,运动能力和健康状况显著低于普通人群;仅78%的幸存者恢复正常工作[57]。一项关于ARDS幸存者 (包含SARS合并ARDS幸存者)长期影响的研究表明,ARDS的长期后遗症包括长期认知障碍、心理疾病、肺功能障碍 (3/4以上幸存者CT显示存在肺纤维化)、神经肌肉紧张和长期护理导致的精神、经济负担[58]。
综上所述,COVID-19 患者一旦诊断为ARDS,病情往往进展迅速,干预措施有限,故早期识别十分关键。临床上应随时注意患者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氧合指数及肺部影像学的改变。采用LIPS评分、早期急性肺损伤相关评分及时识别和评估ARDS的发生风险。一旦确诊,需及时予以适合的吸氧方式,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应用机械通气及非机械通气,注意机械通气后续护理及药物使用。必要时即时采用ECMO。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