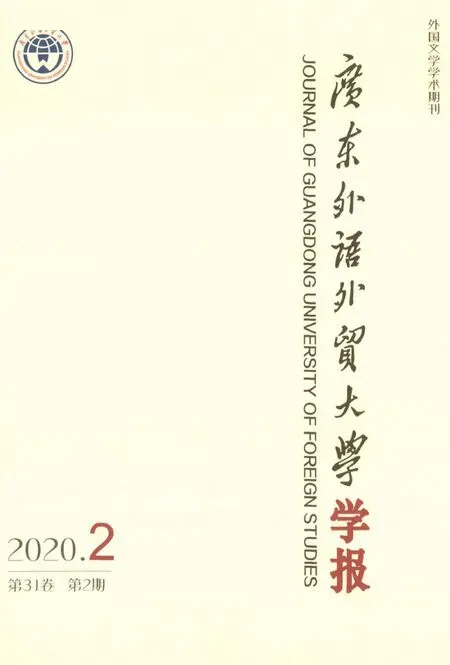《达·芬奇密码》:符码艺术背后的文化真相
唐 毅 牛晓帆
引言
关于“文化”的定义,人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在世界不同文化形态间畅行无阻的准确说法。正如地球上有奔腾的黄河、恒河与尼罗河,有雄伟的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和科迪勒拉山,人类文化也因其所跨越的浩瀚历史和地理空间而具有纷繁复杂的多样属性。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同文化的分布从点到线、从线到面逐步走向通和,在全球化的今天业已形成多元一体的崭新格局。然而,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并非只有机遇、融合与发展,在科技、消费和后工业的困境中还展示出焦虑、空虚与精神危机。对于这种矛盾的境况,英国作家查尔斯·帕希·斯诺(C. P. Snow,1905—1980)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人类智慧的整体文化,不应该割裂成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割裂后的两种文化,就难免互相隔离,互相误解,这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很不利的”(陈佛松,2002:1)。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严重分离导致当代社会生活日益物质化、庸俗化,科学原本为人的物质生活服务,却大有宰制人的精神生活的可能。
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是一味指责科学的负面效应还是只想返回原始的自然状态,都不是最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只有打破物质技术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才能使文化从分裂走向融合,从机械对接走向温润相通。文学能够肩负起这项划时代的重大使命,作家也是值得信赖的思想文化先锋。西方文学以《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为肇始,作家对人类科技与精神文化间相互关系的关注就已投射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在当代文坛,科幻题材的作品以其巨大的市场份额占据着不容小觑的文学地位,丹·布朗(Dan Brown,1964—)等人在科学、工业、医学与政治、宗教、艺术之间穿巡摸索,为现代技术与人的精神生活的结合探寻道路,在消解信仰中重构信仰,在摧毁信心后重获信心。以丹·布朗为代表的作家群体表现出“对当下世界人们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怀、对人类生存现状和未来命运的隐忧”(朱振武,2014),体现了科技时代文学的必然走向以及作家群体置身于后工业语境的总体反思。
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作家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或身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他们的文学作品也经常反映出精神迥异的文化属性。美国作家丹·布朗从小生长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早年赴欧洲学习艺术,最终形成他“对西方经典文化了然于胸,对世俗社会又洞察入微”(朱振武,2005)的创作特点。从《数字城堡》(DigitalFortress,1996)、《天使与魔鬼》(Angels&Demons,2001)到《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 2003)、《失落的秘符》(TheLostSymbol,2009)以及《地狱》(Inferno,2013),丹·布朗的作品始终能够“在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中表现出对文化问题的深层认识,探讨着当下社会中的诸多疑团,关心着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现状,字里行间流露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朱振武,2010)。面对现代科技的强大冲力,他选择以思考和关怀的姿态去解构历史、宗教、艺术和现实,其成名小说《达·芬奇密码》成功地运用符号和密码构成的叙事艺术手法,巧妙地结合现代科技与宗教、艺术等元素,凸显出作家对西方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体反思。具体到这部小说里,主要表现为丹·布朗对其扩张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等特征的有力揭示和深入思考。
西方传统文化的扩张性
《达·芬奇密码》涉及宗教、科学、伦理、艺术、数学等多个领域,由谋杀、密码、符号牵引出错综复杂的推理过程,最终回归于圣杯故事。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大众对文学的消费需求,还通过对西方宗教和科学艺术的深刻认知让我们看到丹·布朗在文化全球化时代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超越文本表层审美范畴的内在意蕴也许正是其小说在中国大陆畅销不衰的原因所在。当下,《达·芬奇密码》更多地被称作文化悬疑小说,或许也是因为丹·布朗不仅擅于设计扣人心弦的悬疑推理,还表现出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终极关怀。
这部作品为西方文化圈之外的读者提供了了解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丰富素材,凸显出西方文化与全球其他类型文化间的诸多差异。有学者曾将中国与西方文化做过形象的对比,认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是太极图,而西方文化的象征是十字架。经过千百年历史的积淀,崇尚浑圆的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向心力、包容力和平衡性,欣赏线性的西方文化具有向外延展的扩张性、侵略性和冲击力。与中国文化自古重视人伦思想不同,自古希腊罗马文化以降的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人力量、宗教信仰、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等理念,古希腊神话对神人同体的建构便是西方崇尚武力、英雄和个体力量之滥觞。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个人的压制引起了航海时代到来后的个人主义的强力反弹。十七世纪至今,西方经历了诸多的思想运动、殖民开拓甚至军事冲突,传统的西方文化逐渐演变为当今具有主导性的全球文化,既具有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也保存着西方文化的某些内在的深层要素。
文化通过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创造活动来呈现自我的特征,图形符号、语言文字、行为活动等元素编织起人类文化的巨大罗网。“从最远古时代起,象征符号的概念就已经出现在各种文化、社会结构和宗教体系之中,促进每一种世界观的形成,帮助人类了解宇宙以及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马克·奥康奈尔、拉杰·艾瑞,2014:1)。《达·芬奇密码》就是一部关于符号和密码的作品。主人公兰登博士是一位“终生都在探索孤立的象征符号或概念之间隐含的关联性的人”(丹·布朗,2009:12),在他的研究领域和生活的周遭,符号的意义无所不在,正是符码串联起小说故事的总体脉络。五芒星和六角星形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对故事情节起着穿针引线和前后呼应的作用,它们既是推理符号也是文化象征。“索尼埃食指也有血迹,……用自己的血作墨,以赤裸的腹部作画布,索尼埃画了非常简单的符号——五条直线相交而成的五角星”(丹·布朗,2009:31),在索尼埃被杀现场尸体摆放呈五芒星形,索菲童年玩的塔罗牌背面有五芒星,在罗斯琳教堂的大殿地面有巨大的六角星形痕迹。与这些符号相伴而生的往往是杀戮、阴谋和欺骗,是正统与异教的殊死搏斗。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符号总是跟它背后的有意识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它的含义总是比它代表的概念窄”(马克·奥康奈尔、拉杰·艾瑞,2014:43)。在索尼埃遇害现场发现五芒星符号后,兰登向法希解释了这一图形符号在不同文化时期的涵义,他指出,“尽管如你在电影中所见,五芒星被解读为恶魔,但从史学的角度讲,这并不准确。它起初的女性含义是正确的。但一千年来,五芒星的象征意义被歪曲了”;同时他坚信“五芒星真正的起源是神圣的”(丹·布朗,2009:33)。在《达·芬奇密码》的图形符号里,既潜藏着小说故事有待发现的真相,又在客观上表现出作品整体呈现的文化属性,即作家在创作时赋予或带给作品的文化特质。
在西方的符号文化里,水平直线和垂直线分别是阴阳两性的象征,它们组合而成的十字架图形便是西方宗教文化的核心符号。无论是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黑暗时代,还是十字军东征引发的历史浩劫,这种线性符号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和扩张性,同时也体现出宗教在那个时代拥有蓬勃的生命力。丹·布朗在小说里运用线条烘托出特定的环境效果,玫瑰线、卢浮宫博物馆的长廊、巴黎瑞士银行金属建筑的线条和传送带,都利用了视觉审美的张力来表现情节发展的延续性和紧迫性。小说对卢浮宫博物馆前的玻璃金字塔格外关照,描述了法国人对这一建筑的矛盾心态:“这座由生于中国的美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引起诸多争议的全新现代玻璃金字塔,现在仍受到传统派的嘲讽。……批评贝聿铭的人把这金字塔描述为光洁黑板上的指甲划痕。然而激进的崇拜者们认为贝聿铭这座七十一英尺高的透明金字塔将古老的结构和现代技法结合起来,艳丽多姿,二者相得益彰”(丹·布朗,2009:15)。如“指甲划痕”一般的线性效果,使玻璃金字塔显露出西方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歧,既迎合了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立性和排他性,也引发了对此褒贬不一的评判。值得一提的是,雨果小说里的郇山隐修会成员对巴黎圣母院有着“木刻镶板的双尖拱”(雨果,1982:5)的刻画,在《悲惨世界》里将巴黎地下水道的分布描写得难辨真伪,这些都展示出西方文化对线性审美的特殊需求。
文学作品中的符号折射出作家的文化心理,在特定时代的文学洪流中将被归为特定的文化属性。从五芒星到玻璃金字塔,这些线性的图案或建筑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西方文化的排他性和扩张性,满足作品情节构造的同时也满足了西方文化以自我和个体为中心的精神追求。丹·布朗作品的主要译者朱振武(2014)曾指出,《达·芬奇密码》和其他作品“在故事层面上书写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冲突”,可见个人始终在布朗系列小说里占据显著的书写位置,个人的独立性与排他性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多元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当代世界的主流,但不意味着民族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就没有隔阂。古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对欧洲文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自中世纪以来,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一支,“基督教吸收犹太教及东方各民族宗教的学说并加以具体化、通俗化”(陈佛松,2002:133),从源头上显露出西方文化的多元特征。受历史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西方社会发展至今已紧密地融为一体,但彼此间在思想文化上的冲突与对立或多或少始终存在。“符号学家常说,法国,这个以其阳刚之气、沉溺于女色以及像拿破仑和矮子丕平这样矮小而无安全感的领袖著称的国家,选择一个一千英尺高的男性生殖器作为国家的象征再合适不过了”(丹·布朗,2009:13)。兰登对巴黎建筑的冷嘲热讽,称埃菲尔铁塔是矮个子法国人立起的巨大的男性生殖器,这一情节在侦破案件的路途上看似漫不经心甚至显得突兀,实际上却是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对立性的生动体现。此外,《达·芬奇密码》中多处提及五芒星和神秘符号在民间的误读,西方宗教对神圣女性形象的扭曲,艺术家达·芬奇冒犯上帝和触怒基督教信仰,窃听等高科技设备对社会伦理的破坏等等,无不表明丹·布朗在当代全球文化发展问题上精于反思的担当精神。
丹·布朗在这部小说里表达了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古今文化之间关系的关切和反思,牵引出一系列质疑:基督教不同教派间的斗争源于信仰真伪还是宗教欺骗?绘画艺术传递的仅仅是肖像或风景的美学意蕴?一个词语表达的古今含义为何相去甚远?在超越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丹·布朗进一步察觉到仍然存在于多元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误读。如何澄清宗教间的文化公案,如何窥见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灵魂,如何发掘历史未述之真相,作家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展示信仰的力量和影响,展示艺术对大众和学者的魅力和失魅。总之,通过对宗教、历史与艺术的解构,《达·芬奇密码》“消解了人性与神性、善与恶、科学与宗教等这些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处于二元对立的中心概念”(耿秀萍,2011)。丹·布朗试图以艺术为人类文化的横截面,在艺术的涂层上描绘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所能具有的共通特点。“达·芬奇……斐波那契数列……五芒星……所有这些都通过一个艺术史上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丹·布朗,2009:84),符码在这种文字语言难以融通的情境下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媒介作用,艺术则先天性地满足符码及其附属意象的价值需求,由此,丹·布朗在小说里力图艺术化地回答这些看似棘手的问题。
《达·芬奇密码》是一部艺术文化与宗教文化合璧的文学作品。欧洲传统的绘画、文字和建筑等艺术元素,基督教和异教间的信仰冲突等形成这部小说的表层意蕴和审美趣味。作家利用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蒙娜丽莎》等画作巧设索尼埃遇害的场景,艺术化地开启整个破解悬案与发现真相的进程。在传统侦探小说的影响下,丹·布朗“一方面大胆吸取通俗小说的精华,一方面又大胆借鉴影视手法,通过多种新奇的尝试,形成了独特而又别致的创作范式”(付慧,2005)。他对艺术的亲近使其文学创作焕发出超越文字意义的特殊气质,在多元文化传递与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此外,宗教也是小说的重要主题。丹·布朗及其作品都出自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宗教上的皈依与反驳也是在这种前提下进行。基督教学说以“上帝-基督说”为核心内容,这种学说“直接导致了天堂和地狱、上帝的城和地上的城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刘建军,2005:5)。在现代文学以前,多数西方文学作品都依赖基督教文化而存在,然而,在丹·布朗所处的当代社会,漫长的宗教历史似乎最终被归为虚无:“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的”“历史的本质就是一家之言”(丹·布朗,2009:239),历史的真相似已无足轻重,宗教的重要性似乎只在于信仰本身。他在小说的结尾处指出,“为我们灵魂服务的不在于圣杯本身,而是它身上藏着的谜,以及令人惊叹的东西。圣杯美就美在它虚无缥缈的本质”(丹·布朗,2009:429)。这种本体论的审美阐释既指明了宗教信仰的当下意义,也为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达·芬奇密码》中,由多元文化引出的谜团和悬案,只有在多元文化之间实现互认与融通才能最终得以破解。从文本内涵到文化主题,丹·布朗书写着文明历史上的对立、误解、冲突以及聚散分合,表现出对当下西方信仰危机的深切忧虑和对西方重塑文化内核的殷切期盼。
多元价值与多重道路
一种恒定的社会文化通常表现为特定的价值观念,西方社会经历了两希文化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洗礼,在近现代世界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伴随着西方先进科技、工业的扩展以及殖民开拓,西方文化价值观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并催生出纷繁复杂的新文化形态。美国学者约翰·W.奥马利(John W. O’Malley,2012:275)认为,西方文化“如此复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错综复杂,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使其他的文化适应于自身的价值体系,甚至在真正地以伙伴的关系相互联系时也是如此”。当代西方文化固然呈现出难以梳理的复杂矛盾和多元特征,但是文化自身的价值伦理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因此,当下文学研究领域的伦理关怀显得愈发重要。朱振武(2014:37)指出,“丹·布朗的小说创作是对后工业化语境下人类遭遇的生存危机、信仰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的揭示和诠释,是对现实社会中生态伦理、科技伦理、宗教伦理和行为伦理等当下热点问题的有力揭橥”。《达·芬奇密码》和丹·布朗的其他小说一样,在故事情节、人物设置和思想内涵等方面竭力以社会普遍价值为指向,顺应读者大众的伦理关怀,为这种悬疑惊悚题材提升了文化品格,因而获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达·芬奇密码》围绕谋杀案和圣杯故事两条线索展开叙事,符号和密码是串联这些线索的核心要素。“密码……罗斯琳教堂拥有众多神秘的东西……每一块石头上都雕刻了符号,表面上看来漫不经心,然而由这些符号设置的密码却深不可测。……它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圣杯故事……罗斯琳监管会还许诺给任何能够解释其内在涵义的人以丰厚的奖赏,但这个密码,至今仍然是个谜”(丹·布朗,2009:421)。正如图形、符号、数字和密码传递的开放含义一样,小说试图突破那种固定的故事结局走向一种多元开放的思索。具体来看,小说人物可分为两种类型:以兰登和索菲为代表的正义一方,以塞拉斯和提彬为代表的邪恶一方。小说从整体上透露出多元文化共融的开放姿态和包容属性,但在具体情节中仍能捕捉到正邪、善恶、方圆、急慢、轻重的对立关系。无论是宗教的代言人,国家机器的代表,还是文化艺术学者,塞拉斯、阿林加洛沙、法希、索菲、提彬、兰登等人都被一连串的数字、符号、密码或猜想卷入整个事件,在冲突和矛盾中一步步逼近故事的真相。众多小说人物的情感和行动维系于或实或虚的裸体画、黄金分割率和符码环环相扣的暗示之中。在这些符码构成的“谜”途上,正反两派人物最终各自归位,索菲与家人团聚,警方成功破案,提彬罪有应得,塞拉斯在信仰中自我救赎,兰登教授收获爱与安宁。在符码象征和大团圆的结局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丹·布朗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关怀。小说讲述的善恶之路是人类文化走向的两条主干道,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善恶似乎难以准确地衡量人与事物的是非真伪。兰登从被动应付到主动求索,从深陷泥沼到赢得转机,展现了人类斗争、挣扎和自救的历程。索菲对祖父的情感从爱到恨,从谅解到自省,展示出西方文化的思辨特质。提彬和主教出于功利铤而走险最终落寞退场,说明这是人类邪念的不归路。丹·布朗从符号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的精神出路,在小说中“消解了善与恶之间往往被认为是很清晰的那条界线,将人的两面性同时呈现出来,从而回避了一种建立在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原则上的伦理体系”(朱振武,2014:43)。
丹·布朗的作品具有一种既延续又断裂的双重特性。在西方文化研究中,“连续和断裂是困扰着所有历史学家的根本问题”,文化的演进构成历史发展的重要侧面,“我们的生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标明断裂,告诉人们事物是如何变化的”(约翰·W.奥马利,2012:276)。《达·芬奇密码》维护了泾渭分明的善恶终局,表明作家对传统价值的服从,同时却在西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发生裂变,否定非黑即白的对立原则,重塑现实世界和人类心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后现代世界里,当一切宏大叙事都遭到解构之时,一种不确定状况就成为人们生活的恒定状态。随着善与恶确定性的消解,人们在面临极大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被抛进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之中”(朱振武,2013)。丹·布朗深刻洞悉当下人的精神变量,在作品中将其展示为多元的价值追求和多样的生活道路,以求满足当代读者在文学中猎奇的同时重觅心灵的伊甸园。
符码艺术传递的包容性
《达·芬奇密码》的艺术魅力来源于符码及其象征意义,整部小说蕴藏着一个或明或暗的符码体系,在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体系可看作是西方传统的“英雄的原型旅程”,在其中“象征符号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为了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人生的目标、意义而奋斗。英雄的历程可用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描述:接受历险的召唤、入门、归来”(马克·奥康奈尔、拉杰·艾瑞,2014:48)。小说主人公兰登的发现之旅和心路历程与这种原型文化相吻合,重释了接受挑战——困境中逆袭——英雄归来的叙事模式。在小说的众多符码中,除线性视觉象征的扩张性外,丹·布朗还关注西方文化里与之对立的包容性。毋庸置疑,这样一位支持多元价值的作家必定在文学创作中传递开放包容的信息。“索尼埃离群索居,但他对艺术的那份奉献精神却使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丹·布朗,2009:12);兰登则让艺术服务于他的案件推理,根据符号和密码的暗示功能“把这个世界视为一张由历史和事件相互交织而成的深不可测的大网”(丹·布朗,2009:12)。在索尼埃被杀现场的五芒星外围有一道圆圈,被认为是女性保护的符号,也是男女和谐的象征。而“这个五芒星代表万物中阴性的那一半——一个宗教史学家称为‘神圣女性’或‘神圣女神’的概念”(丹·布朗,2009:32)。在东西方文明史上,奉阴为上是最初的共同观念,如小说里郇山隐修会对神圣女性抹大拉·玛利亚的崇拜。女性是生命的孕育者和创造者,女性与男性在早期崇拜里是平等相倚的关系,阴性符号所代表的“和”文化更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没有误解的远古时代,符号揭示着文化最本原、最开放、最包容的涵义。
随着农业文明、宗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变迁,漫长的历史表明人类在竞争和生存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西方当代文化具有比较前沿的批判性,《达·芬奇密码》蕴含着超越通俗文学范畴的严肃主题,它被认为“是消除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对立的典范”(朱振武,2005)。达·芬奇不只是刻画美的艺术家,还是宏大叙事中的某个细节点,他的作品成为改写历史的重要工具。丹·布朗颠覆了某些固化在读者心里的传统概念,比如五芒星,它代表维纳斯,也代表平衡美;又如牛顿墓碑上的圆球和砸落在他头上的苹果,“那个本来应该放在牛顿墓上的圆球竟然是从天而降,砸在牛顿头上并给他终生事业带来灵感的红艳艳的苹果”,而这个苹果被联想成“神圣女性堕落的象征”(丹·布朗,2009:409)。小说艺术化地展现了对女性崇拜的追本溯源。作家试图“重建一种以女神崇拜为本源特色的基督教神话的同时也向统治人们精神信仰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提出了挑战”(耿秀萍,2011)。在小说结尾处,索菲的祖母对兰登表示“人们正通过艺术、音乐以及著书立说的形式”(丹·布朗,2009:429)传承着圣杯的故事,其实也是作家对艺术传承文明的一份期待:当代艺术应是圆形的,是具有包容力的。
《达·芬奇密码》还可被视为一场图形符号和数字密码组成的推理游戏。符码的特征和游戏的规则隐秘相通,使小说获得了悬疑特征之外的生动性。朱光潜(2005:83)认为“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小说的符码艺术也是关于符码的游戏。从古至今,人类的游戏行为大致都代表着一种创造、理解和认知。游戏往往促成人际和睦,活跃群体气氛,还能带来新的发现。游戏与艺术一样,“把死板的宇宙看成活跃的生灵”(朱光潜,2005:87)。艺术的活跃性和丰富性给丹·布朗带来强大的创作动力,《达·芬奇密码》展示出他在符码艺术上精雕细琢的巨大成功。概而言之,小说“对‘上帝已死’的信仰危机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可能是打扰了人们多年来理性的沉寂,也可能是搅乱了很多人单一童稚的心灵”(朱振武,2010)。小说通过庞大的符码知识体系艺术化地传递着人类文化始终具备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结论
《达·芬奇密码》是一部重释文化的杰作。符码是艺术文化的重要元素,是不同人群的联结纽带,是多种道路的构成要件,也是历史真相的终极引线。丹·布朗通过符码艺术向世人昭示西方文化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化史,西方文化的扩张性与包容性因此而得以鲜活地呈现。在他的作品中,符码主导着神秘莫测的悬疑推理;在其作品外,符码则象征着智慧、艺术和爱。在当代科技主导的西方后工业社会,《达·芬奇密码》试图在历史的解构中重塑历史,在符码艺术的象征意义背后发掘精神文化的多样价值,“警示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现代人必须对自己的思想信仰重新审视和思考”(耿秀萍,2011),并借助文学艺术的路径引导人的心灵世界踏入新的信仰天地。
——以2018、2019年批评奖作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