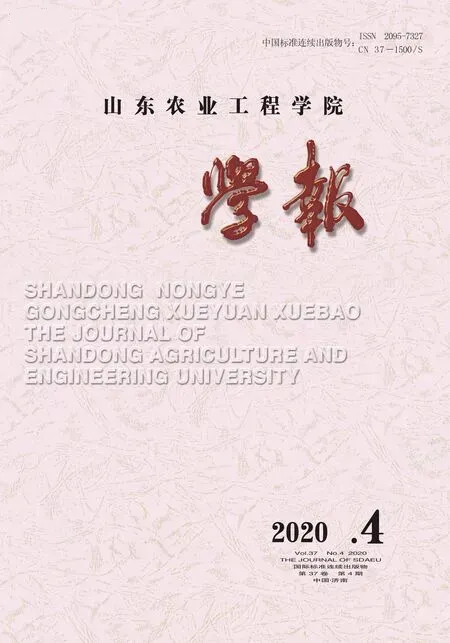基于审美视角的严歌苓小说《芳华》解析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1)
0.引言
《芳华》这部小说,通过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对70年代的青春时代进行了描述,其中既没有对青春芳华的怀旧之意,也没有对70年代的青春的憧憬和向往之情。作者严歌苓仅仅是单纯的叙述了那个时代的故事。简而言之,主要运用回忆的叙述方式描绘了那个时代的青春芳华,吸引了许多读者对70年代已经逝去的青春芳华重新产生了浓烈的记忆。
1.作者简介
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人,21世纪的著名中英文作家,同时也是好莱坞著名编剧。她曾出版很多部文学作品,较为代表性的有《金陵十三钗》、《心弦》、《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严歌苓由于居住在国外,因此较为擅长进行双语创作,这和她的学习背景以及环境有很大关系。严歌苓发表的小说多数为揭示人性关系以及历史评价为主体的文章,作品内容内掺杂着浓烈的批判意味,伴随历史的沉淀,严歌苓的小说内容逐渐引人思考。严歌苓作为著名作家获奖无数,这不仅仅代表着优秀的作品,同时诠释了她多年来在文学创作上付出的努力以及获取的造诣。
严歌苓擅长于极简的创作风格,文章语言精练亦刚亦柔的手法相结合,在此过程中不断变换写作时间,所阐述的作品极具艺术性,值得后来的阅读者深入探究和学习。她通过文学作品打开了读者的审美视角,与此同时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审美视角将作品内容的文学内涵发挥的淋漓尽致,进一步剖析了人物关系,是作品内容更加清晰化,将哲学理论解析的极其透彻,为整篇文章铺垫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作品内容的深度总结可以发现,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特点较为相似,女性的社会地位均处于较低的位置,并且女性缺少完善健全的思想,从另外的视角作为描写点,通过作品描述了人性以及现实社会。
2.《芳华》小说介绍
《芳华》是一部具有时代性的作品,作品将文工团作为作品的切入点进行阐述,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描写了美妙的青春年华,并对失去的青春芳华有了反思。因此,这部作品仿佛是现代的严歌苓与青春时期的她一种对话模式。文章中的文工团为充分响应毛泽东思想号召,所有的表演者们不断地进行排练多样化的节目,处于青年时期的男男女女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生了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同时人性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转变,在时代的不断沉淀中阐述自己的情感和情义。小说中的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刘峰,他不仅是文工团中的热心肠,同时也是一个好帮手,帮助了文工团中每个表演者解决了繁琐的小事,这个人物贯穿了整个小说,将小说内容更加生动和形象。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何小曼,何小曼的一生经历了各种起伏经历。整个小说中的感情叙述十分真挚,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看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从内心深处产生情感共鸣,能够体会到透过文章背后的人性关系,使读者回忆道自己的经历和回忆,具有强烈的认同感。
整部小说运用了一定的技巧进行叙述,小说的叙事技巧也较强,将小说的整体价值提升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文章的整体结构感较为紧凑,因此,这部小说的叙述形式区别于其他小说,给人以强力的情感共鸣,能够使阅读者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小说增强了吸引力,并未当今时代的小说叙述形式给予了一定的引导作用,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芳华》这部小说的整体叙述手法十分成功,通过感情线将整体小说结构和中心主旨梳理的极其清晰化,通过文工团中的成长故事叙述,深入阐述了青春芳华中逝去的时间。除此之外,小说本身的文学色彩也较为丰富,使得《芳华》这本小说能够在发表的短时间内吸引到大量的读者,并对小说的评价均具有强烈的感情意味,整体而言这部小说对情感的叙述是从内心出发,通过自述的方式将小说呈现的更立体化。
3.审美视角下的严歌苓小说《芳华》解析
3.1 复调性审美效果
《芳华》在叙述过程中,采用了视角不断转化的效果,营造了一视角转化,通过第一人称的内视角以及第一人称的外视角进行了叙述,不断地转化形式形成了两种小说效果。首先,是通过回顾时空中的我阐述进而为下文保留了一定的悬念。一般小说中通过第一视角对事件进行预判时,通常会留下未知的悬念,但是在《芳华》中,严歌苓巧妙地运用了两个时空视角的结合,为下文留下了悬念。小说的开始是这样描写“我”和刘峰的,中年时期我们巧遇,然而刘峰却刻意没有与“我”相见。之后小说的描写重回三十年前,从青年时期的“我”角度,将刘峰描绘成一个“英雄”般的形象,小说开篇这种两种时空角度的叙述,非常成功的为接下来的情节留下了悬念和铺垫。青年时期的“英雄”怎会到中年时期会变得如此“落魄”,刘峰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整部小说围绕此悬念进行叙述,作者通过悬念引导读者对青年时期发生的故事进行了深入反思。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通过总悬念的引导,通过有限的视角进行事件叙述,在事件爆发后才能得知前因后果,因此,在“触摸事件”发生后,原本的好人刘峰好像一下子颠覆了原本的形象,这样的手法所叙述出刘峰的遭遇,带给读者心里的震撼是“惊奇”并不是“悬念”。然而在《芳华》中,严歌苓整体叙事过程并未仅仅通过少年时期“我”的视角,而是在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时,转换了中年时期“我”的视角进行时间的回顾,给予读者了一些可循的蛛丝马迹。
刘峰的形象在整部小说中始终好的“没人性”,甚至带给当时作者的感受是,想看他犯错看他的另一面。甚至无法想象刘峰的坏人设形象。然而就在“触摸事件”爆发之后,原本的好人形象瞬间变成了反派,被林丁丁痛哭着控诉,那其中较为清晰地一句话,则是林丁丁的室友问她为什么不能是刘峰?林丁丁哭着向室友说:“就是不行,反正就是不能是刘峰”作者原本以为那是恋爱的萌芽期,直至事件暴露后才知道自己原来的判断时错误的。严歌苓在运用回顾时空的“我”在叙述中讲到,大概刘峰对林丁丁的追求,早到也许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通过作者分别利用不同的文笔讲述“触摸事件”后,在讲述之前作者就已经进行了不断的暗示,从而是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阅读兴趣,并未小说增加了一定的戏剧性。通过回顾时空中的“我”,运用已知的角度对整件事进行了回顾,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刘峰的命运被这一件事彻底改变的荒谬性,进而使引起了读者的反思。
其次,通过回顾时空的“我”与叙述时空的“我”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反思主体。通过两种时空叙述之间的转化和相互干预效果,呈现了不同时空的我对事件的认识角度。《芳华》中的整体叙述角度转化均相对较为复杂,主要通过年少时期的“我”作为第一叙述主体,然而处于那个时期的作者无法跳出环境的制约对事件有整体角度的思考。于是,严歌苓便通过中年时期的“我”对少年时期的“我”所阐述的事件进行思考,通过叙述时空“我”对事件的整体评价产生了一定的干预效果。整部小说中这样的手法几乎贯穿全文,叙述中的两个“我”构成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关系,在叙述70年代懵懂的青春芳华时,也更多的对自我和人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增加了小说整体的反复性和审美效果。《芳华》与严歌苓的其他小说一样,叙述的意图不在于对历史的描绘,而是着重思考了时代和历史的因素,通过叙述时空的“我”进行故事中人与事的叙述,通过回顾时空的“我”对事件进行批判和反思,体现了70年代人们对自己命运无力把控的同时,将个人、历史、时代之间的繁琐联系充分体现了出来。
3.2 陌生化审美效果
“陌生化”通常也被称之为“反常化”,陌生化的概念由俄国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通常而言,与已知视角相比,第一人称有限的叙述视角相对来说更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已知的视角在进行叙述时通常较为全面,然而这种视角的弊端则是使读者的主动性丧失掉。由于叙事的过程过于全面,对情感的抒发和把控上相对有所制约,导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失去了探究问题前因后果的乐趣,缺少阅读的悬念。反之,若运用有限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叙述时,作者往往对人物与事件的评价来源于自己的主观感受,读者在阅读时会与自身经验进行对比,往往与之不同则会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种效果似乎远远超出了读者所预知的审美感受,进而更加有效地激发了读者的自主思考能力以及不断延伸了读者审美感受。
《芳华》的叙事过程中,严歌苓在创设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时,往往通过年少时期的“我”有限的视角进行的叙事。例如,严歌苓在描写小说中刘峰的追悼会时,通常小说在进行描写追悼会时,通常会采用已知的叙事手法能够呈现出一种庄严和神圣,并且通过场面情境效果的渲染感染到读者,使读者随之悲痛并获得一定的宣泄。然而严歌苓仍然运用了年少时期“我”的视角进行描写,将追悼会的悲痛与庄严化解了。《芳华》中刘峰的追悼会,严歌苓并没有对追悼会现场的氛围进行情感渲染。而是因为刘峰侄子的迟到,导致追悼会并未如期进行,灵堂又租给了下个时间段的人家使用,被人逼着拆掉灵堂草草结束了追悼会,连何小曼的追悼词都没有机会念。
“突然从门口进来三个眼睛红肿的中年男女,长得极相像。他们大声质问我们,怎么还不拆灵堂,腾地方,他们要挂老母亲的遗像。小曼更慌了,说她不知道这间灵堂还租给了下家。刘倩迎上去,说她父亲的追悼会还没开呢,怎么能腾地方给他们?!”这一段的叙事过程将灵堂描绘成了只是按时出租的商业用地,参与追悼的亲友似乎像是你追我赶的剧场表演者,超出了时间则不肯善罢甘休。然而本该庄严神圣的追悼会成了一场闹剧。严歌苓对这场追悼会的叙述显然突破了读者原本对于追悼会的概念,通过“我”的角度来看,原本悲伤的情境因突发的状况成了一场闹剧,没有运用常规的追悼会叙述,使读者没有与悲伤情境共情的机会。这样陌生化的追悼会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为读者展缓了审美感受。
追悼会的情景至此已经结束,然而带个读者的感受,则是一个一辈子做善事的“好人”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甚至连一个完整的追悼会都没有,因无力改变他人的看法,因无力改变命运的轨道。通过此场景中读者认为的荒谬,体现出了现实社会的人性,通过追悼会场景的叙述不断地深化了刘峰的坎坷命运,同时也暗示了造成这种悲凉场景的现实荒谬。
3.3 互文性审美效果
《芳华》中所叙述的70年代文工团故事,其实与严歌苓现实的经历是完全相似的。小说始终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角度进行叙述,并且小说中“我”的作家身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强烈的认为这是严歌苓的一部自传小说,描述的是严歌苓在70年代所经历的一切。与此同时,严歌苓在叙述过程中又不断向读者说明着“我”的身份,仿佛以作家的身份一切都有合理的理由进行想象和虚构,打破“我”的视角进入已知的视角中继续进行事件阐述。读者在整部小说的阅读中均在反复思考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小说复杂的互文性,进一步给了读者审美效果。
通过这种互文性的叙述效果,给予了读者对真实性的进一步思考空间。由于大部分读者将《芳华》看作为严歌苓的自传,因此,在阅读时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则变成了读者正常的心理预期。严歌苓在叙事的过程中,始终借用“我”的角度进行文章的合理想象和虚构,尤其是在叙述人物何小曼的身世时,那段叙述几乎成为全文中最为感人的一部分。然而很明显,无论是作者还是小说中的“我”,均无法了解到何小曼没来到文工团之前所发生的故事,并且在叙述中那样细致入微的描写。严歌苓运用了虚构的手法,将小说中的想象部分的叙述更加合理化,给读者一种虚构和现实无法分清的模糊感。若严歌苓在叙述过程中,过于关乎真实性,那么所有的读者则会将这份身世背景带来的情感体验,全部集中于人物的本身。严歌苓在叙述过程中不断暗示读者这是一种作家的虚构和想象,是读者在阅读时,更加关注的点则是:这一切是否真实发生的?是作者的想象或是来源于作者本身?
严歌苓在小说中反复强调着这一切均是她一个人构想中的画面和情境,进而促使读者带着理性去阅读文章。读者阅读过程中的一系列想象,以及对问题的思考,若从浅层次而言是小说的虚拟与现实问题,实则超出了这范围与其他事情相互联系。对70年代事物的认知以及事件的思考深度、对作者严歌苓创作风格的了解以及个人的价值观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芳华》中叙述的虚拟性和现实性判断产生影响,进而不断深化了小说中互文性带给读者的审美效果。然而关于《芳华》中故事的真实性,严歌苓曾在书中给出了答案:“过去那些人和事,重复地谈,重复地笑,谈多了,故事都走了样。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面,跟着一块活,一块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摸样了。可是谁又能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几句话既是对自己写作风格的进一步解读,同时像是送给读者的一段话。由此可见,通过叙述角度的不断转化,使读者始终处于迷茫的、无法辨别真实和虚拟的情境中,《芳华》这本小说通过作者、读者、文本之间三者复杂的历史互文性,为读者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审美体验。
4.结语
综上所述,严歌苓正式运用了这种叙述角度的不断转换,将《芳华》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小说构架,带给读者更好的审美效果。同时在文章中不断为读者构建和消除着现实与虚拟之间的想象,使读者无法分清小说中现实与虚拟的真实概念。文工团的“芳华”早已逝去,那些青春的点点滴滴也随着时代逐渐消散,但人性反而逐渐清晰化。在《芳华》中严歌苓并未运用常规的叙述方法,而是通过不断地视角转化呈现了小说不一样的结构,给读者已更为多彩的审美效果,也将《芳华》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与审美价值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