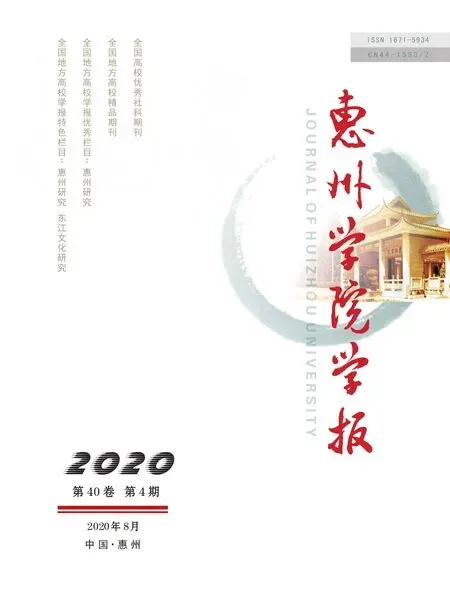由绚烂归于平淡1
——《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风格演变的影响
冯爱琳,谭伟燕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作为古典小说艺术的典范,《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审美价值影响着一代代作家。被称为“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的张爱玲7岁仿写《摩登红楼梦》,晚年更是耗费十年的时间和心血完成《红楼梦魇》一书。可见,《红楼梦》对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容小觑,尤其在张爱玲小说风格的演变上更是举足轻重。
文章以1952 年张爱玲离开大陆为界线将其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将它们与《红楼梦》作比较,探讨《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风格演变的影响,深入品味张爱玲小说独特的美学品格和艺术成就。
一、绚烂中呈现“红楼烙印”
每位谙熟《红楼梦》的读者在阅读张爱玲的小说后,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张爱玲将自己从《红楼梦》中汲取的养料浇注在小说创作中,使作品散发出浓郁的“红楼风”。前期作品主要收集在小说集《传奇》中,带有明显的“红楼烙印”。《传奇》阶段的张爱玲渴望凭借小说一举成名:“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135,初登文坛的她明确表示自己为上海人而写,“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1]81,刻意迎合读者对于传奇的欣赏欲望。因此,其早期创作刻意营造“传奇”式的绚烂之风。绚烂之风不仅表现在讥诮、凌厉,且带有几分泼辣的语言上,更引人注目的是情节之奇。在小说集《传奇》初版的扉页上,张爱玲以两行题签表明了她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传奇》的用意所在:“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传奇》初版)此处的传奇意指摒弃纯粹写实手法、在庸常的现实生活中提炼惊异、重视读者审美体验的故事形态。如果将《传奇》中的故事稍加提炼,读者自会发现这些故事都有抓人眼球的情节模式:比如女学生堕落的故事、变态母亲的故事、异域青年被舆论诽谤身败名裂羞愤自尽的故事、落难女子邂逅奇情修得正果的故事以及父女畸情的故事、姐姐构陷妹妹的故事等等。此外,绚烂之风也呈现在故事时间的设定上。张爱玲喜欢拉开与现实时间的距离,将故事时间设定在20 世纪10 或20 年代,用《金锁记》里的话就是“三十年前的月亮”。这被刻意拉远的距离感必然产生一种传奇的效果,油然而生的是一种隔着历史云烟氤氲而生的神秘感。这种对绚烂之风的追求使张爱玲在创作之初就以烂熟于心、且一贯被目为传奇的《红楼梦》为蓝本,《红楼梦》成为张爱玲不竭的创作资源。其早期作品在语言表达和人物塑造上有明显的模仿《红楼梦》的痕迹,“始终不能自拔于《红楼梦》型窠臼之中”(吴小如语)[2]58,打上了深深的“红楼烙印”。
(一)语言表达上的“红楼”印迹
读张爱玲的早期小说,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说在遣词造句方面与《红楼梦》的高度契合。其早期创作重在化用《红楼梦》的俗语和句式,连骂人的话都直接从《红楼梦》中挪用,比如骂年轻女子的俚语“蹄子”“小蹄子”“浪蹄子”等;此外,诸如“仔细……”“偏生……”“猪油蒙了心”“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赔了夫人又折兵”“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等《红楼梦》惯用的句式也常被张爱玲搬用在小说中,浓浓的“红味”语言充斥其中。
当然,张爱玲对《红楼梦》的借鉴不仅仅限于对遣词造句的简单模仿,“而是从笔端自然流泻出来的,随同人物的口吻、声气、心态、神韵一齐呈现出来的活的语言,这是张爱玲自己的,又的的确确是从《红楼梦》化出的”[3]50-67。其语言从人物心里流淌而出,与人物性格高度契合,虽不乏模仿的痕迹,却是十分地妥帖。《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奉迎梁太太的“姑妈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虽能在《红楼梦》里李纨奉承凤姐的“水晶心肝玻璃人儿”中找到源头,其表达的人物内心情感自与为哄凤姐开心的李纨不同,若细细品味则能感受寄人篱下的薇龙此刻内心的孤独、无助和苦涩。《金锁记》中曹七巧冲哥嫂的一通发泄与《红楼梦》中鸳鸯怒斥嫂子的一番讥诮、凌厉,且带着几分泼辣的语言有几分相似,但七巧因得不到情爱的压抑以及因压抑而导致的疯狂与鸳鸯的不愿屈服于命运的自我抗争自然不是一回事。
张爱玲对《红楼梦》的色彩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其小说中的房屋居室、陈列摆设、服饰装束等无不着颜染色。由于自小对颜色的敏感,张爱玲对《红楼梦》中的色彩语言有着近乎痴迷的偏爱,各类颜色词都能信手拈来。大量的颜色词相互映衬冲击,给读者带来丰富的视觉想象和视觉冲击。《茉莉香片》中描述婚姻囚笼中的冯碧落:“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4]54。紫色与白色相映衬散发着悲哀幽怨的死亡气息,映衬出抑郁的气质,被赋予新的内涵。《倾城之恋》“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只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5]53,此处用参差犯冲的颜色渲染营造出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自杀前的场景:“煤气的火光,像一朵硕大的黑心的蓝菊花,细长的花瓣向里拳曲着。他把火渐渐关小了,花瓣子渐渐的短了,短了,快没有了,只剩下一圈齐整的小蓝牙齿……”[4]45,蓝色的火光散发出诡异的气息。这些绚烂华丽的颜色词源于对《红楼梦》的借鉴和学习,给读者留下绚烂多姿的视觉印象。
(二)人物塑造中的“红楼”印迹
张爱玲前期小说繁多的人物形象都有红楼人物的印迹,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刻画手法上与《红楼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最为典型。曹七巧活脱脱是王熙凤的化身,身上由表及里都散发着《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内在特质。曹七巧的泼辣性情与凤姐的“辣”味神似,就连小说中描写她登场的方式也是“凤姐”式的:“(七巧)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5]89,曹七巧尖酸泼辣的腔调给人以“来者不善”之感,这与王熙凤登场时林黛玉觉得她“放诞无礼”如出一辙。张爱玲小说中还有一位王熙凤式的人物是《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她的口角犀利、生活骄奢也与凤姐颇为相似。葛薇龙第一次见梁太太时,梁太太就单刀直入地说,“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倒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5]6这样的刻薄与尖酸同凤姐的泼辣张狂的性格颇为相像。此外,还有白流苏与林黛玉的敏感自尊和对年华易逝的焦虑,范柳原与贾宝玉的离经叛道及内心对自由和真善美的向往,薇龙进梁府与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忐忑心理都有高度契合之处。细细读来,张爱玲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着挥之不去的熟悉感,氤氲着红楼人物的韵味。
与张爱玲本人早期喜爱奇装异服相对应的是,张爱玲小说注重以繁复醒目的服饰描写表现鲜活的人物形象。恐怕还没有一部书像《红楼梦》般将人物的服饰描写得如此精细,深受《红楼梦》影响的张爱玲在人物服饰上也着墨甚多。《金锁记》中曹七巧每次出场的服饰都不尽相同,其服饰变化是根据人物的性情、地位和心理的变化而变化的。初次出场的七巧“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5]89,此时的她心里充满着对季泽的爱恋,银红衫子象征着七巧内心那团熊熊燃烧的爱欲之火;第二次出场的七巧正处于热孝期,“穿着白香云纱衫,黑裙子,然而她脸上像抹了胭脂似的,从那揉红了的眼圈儿到烧热的颧骨”“脸上烫,身子却冷得打颤”“一颗心便在热茶里扑通扑通跳”[5]99,此时的她关注分家后财产的分配,担心孤儿寡母被欺负了,白衫黑裙的着装与内心的忐忑和焦灼形成强烈的对比;第三次出场的七巧穿着“佛青实地纱袄子,特地系上一条玄色铁线纱裙”[5]101,此时的七巧满怀对季泽图财的狐疑,青色和玄色的服饰暗含着对季泽的戒备和抗拒。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中年后的七巧,她冷静编造女儿吸鸦片的谎言,残忍地掐断了女儿心底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一丝爱欲。小说以童世舫的视线看去,一个面目模糊的小身材老太太,“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5]122,大红热水袋与湖绿地衣形成巨大的色彩反差,昏黄的日色促成了构图上的阴影,高大的女仆与矮身材的老太太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莫名地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感,世舫直觉地感到她是一个疯子——此时的七巧已经由人蜕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魔鬼了。此外,《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写王娇蕊穿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露出里面深粉色的衬裙,表现她的随性、神秘感以及诱惑性,隐喻她与振保之间的暧昧情感;写佟振保望见浴室中的孟烟鹂“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的,一半压在颔下,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5]160,凸显烟鹂的随意邋遢以及女性美感的荡然无存,暗示佟振保对她的厌弃和漠视。《封锁》里描写的吕宗祯“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和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惟恐唤起公众的注意”[4]98-99,一个生活在牢笼中的无趣男人和一个严肃而寡淡的女人呼之欲出。张爱玲作品中精细的服饰描写、精致的服饰搭配,且富有变化的服饰叙事都绚烂多姿,与《红楼梦》的经典服饰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彰显出深深的“红楼烙印”。这些有迹可循的烙印免不了给读者一种华丽绚烂的文风的印象。
二、平淡中凸显的“红楼神韵”
张爱玲前期的小说风格可以说是“有迹可寻”,而后期小说似乎难见红楼痕迹。张爱玲后期创作将《红楼梦》隐藏在深处,变得“不落痕迹”,追求更高的“红楼神韵”,因此小说风格发生明显的转变。张爱玲后期的小说风格呈现出一种“神似”《红楼梦》的美学风貌——“平淡而近自然”。
“平淡而近自然”是张爱玲后期一直推崇的美学风格。苏轼曾言,“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6]710(《与二郎侄》)。可见,平淡其实是比绚烂更高的美学境界。曹雪芹便成功地营造了真正的“平淡而近自然”,胭脂斋多次批道:“淡淡写来”“淡淡抹去”“随笔写来”“随笔带出”等等。胡适认为“《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①。俞平伯也说,《红楼梦》“初看时觉似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7]105。后期的张爱玲深谙此意。随着张爱玲人生阅历的增加及对《红楼梦》的深度感悟,其作品从前期以辞藻之华丽、情节之曲折激荡而刻意营造的“传奇”式的绚烂之风逐渐转向后期“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学风格。
(一)情节的淡化
张爱玲一改前期作品的戏剧性和传奇性,后期创作出现情节淡化的趋势。作品用平稳的叙事语调,娓娓道来,刻意淡化情节,注重营造“平淡而近自然”的艺术之境。其后期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小团圆》等都不以故事见长,情节上都是平淡自然的。只有一篇短篇小说《色戒》有着明显的冲突,情节上更曲折有致。然而《色戒》的曲折并不是张爱玲刻意为之。相反,她有意弱化这个间谍故事本应有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将王佳芝刺杀行动的失败归因于女性在情感面前刹那间的恍惚和动摇。这样,一个本是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的间谍故事,在张爱玲不经意的、近乎漠然的叙事口吻中落下帷幕,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却有“淡极始知花更艳”之妙。情节的淡化在《小团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全篇几乎都是女主人公盛九莉成长生活片段的随意连接,淡淡地述说自己真实的人生历程,从头至尾都没有戏剧化的故事情节,“貌似平淡,而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8]91。在张爱玲创作后期,她多次改写作品,淡化情节,让平淡自然流露。比如改写自《金锁记》的《怨女》,将《金锁记》的一大高潮——母亲怨毒狠辣地毁灭女儿爱情这一情节去除,不用高潮迭起与氛围渲染的炫奇手法以增加情节的曲折性,改换成一种平淡又自然的手法去塑造更贴近现实人生、更具真实感的人物形象。柴银娣的形象不渲染、不过分,因而更具有人间性,也更富有人生的启发性,更让人体悟到人生华美背后的“苍凉”。在《国语本〈海上花列传〉译后记》中,她这样阐述对《红楼梦》的“平淡而近自然”之风的认识:
原著八十回中没有一件大事,除了晴雯之死。……大事都在后四十回内。原著可以说没有轮廓,即有也是隐隐的,经过近代的考据才明确起来。一向读者看来,是后四十回予以轮廓,前八十回只提供了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8]244
张爱玲曾在《红楼梦魇》中说,世上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她明确表示自己对《红楼梦》的痴迷只限于前八十回。前八十回让她痴迷的正是波澜不惊的叙事节奏和“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这正契合于苏轼说的“不是平淡”而是“绚烂之极”,也正是张爱玲想从《红楼梦》中极力捕捉的神韵。
(二)语言的朴素含蓄
张爱玲后期小说语言的朴素化是“平淡而近自然”的又一表现。与前期作品相比,后期作品语言不再辞藻华丽、意象繁多、色彩绚烂,而换以平淡朴素含蓄之韵致。后期作品的多次改写,体现出张爱玲对《红楼梦》“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学风貌的自觉追求。《金锁记》被改写后,不仅在情节上作了淡化处理,而且整体语言风格也逐渐朴素化,平淡中见自然。比如开头部分的处理,《怨女》将《金锁记》开篇戏剧化的月亮意象换成对景物平淡无奇的自然描绘,摒弃对意象的反复渲染,转变为对朴素自然的环境平实的描写,深具《红楼梦》的内质精髓。还有改写自《十八春》的《半生缘》,开篇用朴素自然的语言,以平和亲切的口吻向读者开始讲述“半生”的爱情故事,使读者在朴素的语言中感受岁月变迁与男女主人公情感的发展。《半生缘》以世钧曼桢重逢时的一句话“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为结尾,其中传达出的惆怅无奈的悲凉感与《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的人生况味和艺术境界颇为贴切。为此,陈子善在《<半生缘>浅见》中指出:“《半生缘》比《十八春》更接近《红楼梦》的境界”[9]2。这就是“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学价值与艺术魅力。张爱玲感悟了《红楼梦》的简约与蕴藉,从主题内容到人物塑造再到情节设置,都是含蓄简约,平淡自然的。她在《谈看书》也曾说“有时候有意无意轻描淡写两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异代的读者感到震动”[8]105。可见,张爱玲自觉追求“平淡而近自然”的审美蕴藉,是契合于《红楼梦》“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学境界的。
为达到“平淡而近自然”的语言效果,张爱玲后期创作大量采用了不事雕琢的白描手法。白描是用最朴素简洁的描写叙述最为本真的情态面貌,不加以修饰和渲染,即用最为平淡的笔触去展现事物面貌或者叙述事情的发展。她在《表姨细姨及其他》中明确表达了对传统白描手法的向往,并努力在创作中实践。比如《相见欢》中尝试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运用白描的手法,把人物的个性和意向的表达直接呈现于对白动作与意见中[8]203。张爱玲后期小说推崇“意在言外”的含蓄传统,即由读者自己去下结论,作评判,作“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作品在大段的人物对话之间隐去了一些叙述性的文字,致使读者在阅读时不得不跟随人物的意识流动前奔后突。这一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的阻碍,以至于张爱玲为回应林佩芬女士的一篇关于《相见欢》的书评,竟写了一篇长长的注,这就是上面提到的《表姨细姨及其他》。尽管张爱玲未能达到《红楼梦》白描手法的精深之处,但是她视白描为古典小说的精髓并持续在此用力的方向是大致不错的。
前期张爱玲的作品擅用故事性去刻意渲染,鲜以白描铺陈故事。后期张爱玲对这种朴素简洁的“平淡而近自然”的手法格外推崇,尤其是对《红楼梦》中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极为赞赏。白描追求朴实无华的“平淡而近自然”的韵致,与绚烂的技巧相比,白描手法没有刻意为之的修饰,不做作,不买弄,更能传达人物的真情实感,也更贴近生活,使作品产生与人共鸣的艺术效果。《红楼梦》中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望见贾府“桌上碗盘森列”,都是“满满的鱼肉”,而“不过略动了几样”[10]173。曹雪芹在淡淡的几句笔墨里道出农家妇人眼中的贵族生活的奢靡。《红楼梦》中的白描手法几乎处处都是,谙熟《红楼梦》的张爱玲受此启发,深谙其中白描手法中的“平淡而近自然”之道。张爱玲后期小说的景物描写不再走《金锁记》式的华丽造景之路,而是尽量随着人物的活动、心理自然流出,呈现的是“平淡而近自然”的韵致:
……一出上海就乘货车,大家坐在行李上,没有车门,门口敞着,一路上朔风呜呜吹进来,把头发吹成一块灰饼,她用手梳爬着,涩得手都插不进去。但是天气实在好,江南的田野还是美:冬天萧疏的树,也还有些碧绿的菜畦,夹着一湾亮蓝水塘。车声隆隆,在那长方形的缺口里景色迅速变换,像个山水画摺子豁辣豁辣扯开来。(《小团圆》)[11]232
《小团圆》一改张爱玲早期写景的浓墨重彩、极尽雕饰,它以细腻的工笔白描手法,朴素简略、不事雕琢地摹刻出生命中的鲜活感受,在景物中铺陈那余韵不尽的情感,让读者感受那百转千回的矛盾挣扎。这洗尽铅华的白描手法,正是她领悟到深隐精微的“红楼”意旨后所做出的自觉选择。难怪陈子善断言,《小团圆》和《红楼梦》有着跨越时空的对接。
可见,张爱玲后期风格的转变经由“绚烂”到“平淡”的发展过程,这一由“形似”到“神似”的演进是作者对《红楼梦》艺术审美价值的发掘以及对《红楼梦》精神内涵的承传。张爱玲将其“平淡近自然”的美学风貌融入自己的小说,形成其后期小说风格的一大亮点。
三、前后期贯穿的“红楼气息”
张爱玲作品中弥散的无所不在的“红楼气息”就是日常生活的书写艺术和苍凉悲哀的美学品格。这是《红楼梦》的深层艺术境界,也是张爱玲创作一贯的坚守。张爱玲保留着这股深邃的“红楼气息”,将其赋予在作品的精神内涵里,并结合自身独特的人生体悟浇灌在作品中,形成独特的艺术境界。
(一)日常生活的书写艺术
日常生活的书写艺术首先表现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红楼梦》一样,张爱玲一贯执着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她偏嗜于实事中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8]140。这样富含人生味的生活实事才能鲜活地展示时代的真相及深藏于其中的人性。张爱玲出生于衰朽的旧式家庭,且处在复杂敏感巨变的大时代,她能清楚地看到时代的动荡和沧桑,出于她自身对时代的疏离感与失落感,她感到“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虽然“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以致“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但是在她看来,人生安稳的一面有着永恒的意味。她刻意回避战争这样“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宏大命题,着意表现人生的琐屑与安稳,所以她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和“男女间的生活小事”[1]172-174,即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性格背景各异,是旧社会百姓中最普通的一类人。她们所处的那种习以平常、琐碎单调的日常生活场景,如请安、打牌、闲聊、聚餐跳舞、约会调情、嫁娶酒宴等,是当时社会最为普泛的生活状态。这些信手拈来的日常生活内容反复出现在张爱玲小说中,呈现出五味杂陈的生活底蕴。她以叙述生活的琐屑来反映时代的普遍现实,浓缩了二十世纪上海真实的物质环境,虽不刻意呈现时代变迁带给人们的恐惧与无奈,却更显无奈与苍凉。
其次,日常生活的书写艺术表现在对细节的精细摹刻。与《红楼梦》中宴饮、洗漱、睡觉等日常生活细节以及对服饰、摆设、用具、环境等日常器具进行大量的细致描写一样,张爱玲也同样着墨于生活细节上,从不吝啬笔墨描写由普通人日复一日地行坐起卧、衣食住行及箱包家具等构成的日常生活空间。《金锁记》中对芝寿卧房的描写便可见一斑:“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5]113。这里以喜写哀,则倍现其哀,繁复的、充满喜气的陈设中却充斥着死亡的气息,不厌其烦地静态描述中蕴藉着难以言说的沉痛和悲哀。
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是对一个时代历史的真实反映,更是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的展现。日常生活的书写艺术代表着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真实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浸淫于日常生活中的小市民的真实人性。简言之,就是张爱玲借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叙述来呈现时代的真实肌理。其实,这也是作家对时代变迁的苍凉感悟。
(二)末世苍凉的美学品格
《红楼梦》有着末世悲凉情结,整个基调是苍凉中的浮华,而“苍凉”或者“荒凉”更是张爱玲最为倾心的字眼,是弥散在她整个创作生涯中的悲剧底色。受到《红楼梦》浸染以及孤独凄凉身世影响的张爱玲,将苍凉的韵致赋予作品之中,挥之不去的时间感和宿命感催生了张爱玲作品苍凉的气韵。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明确表示,“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173。她用悲观意识写出乱世中的人生百态,苍凉中难掩无奈的宿命感。《红楼梦》的贾宝玉与《倾城之恋》的范柳原都有着对命运无常的感慨,都是悲凉人生况味的感悟者。范柳原这一形象是张爱玲对宿命感的具象表达,小说多处提及范柳原感叹人生无奈和对命运的无力感。他说:“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5]71。“生与死”的命运的难以捉摸与我们偏说“在一起”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深深困扰着范柳原。作品透过无奈的宿命感散发着难以言说的悲凉。
长篇小说《小团圆》展示的是一幅完整残破的画面:支离的家庭、破碎的爱情、卑微的人物。它的开篇就渲染着苍凉的时代氛围:“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心上”[11]15。如此凄凉寂寞的月色笼罩的是挥之不去的苍凉感。小说没有宏大的主题,只有人物的生活场景的连接,喧嚣嘈杂的环境和人来人往的流动更对照出主人公的孤独与凄怆,极具画面感的描写笼罩着苍凉的气氛,回旋着悲凉的基调。这是张爱玲在《红楼梦》悲剧美的启示下的苍凉书写,没有“悲凉”“苍凉”的字眼,却在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喟叹中表达了难以诉说的苍凉之感。张爱玲小说还有许多标志性的关键词:月亮、凄怆、生命、阴暗、恐怖、乱世……这些词散见于小说中,用此借以烘托出小说独有的悲凉氛围,写尽普通人的苍凉人生。不难看出,张爱玲作品中苍凉的美学品格实际上是张爱玲对人生深刻的感悟,“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宿命感是她对生命的无奈和对生存意义及价值的思考。“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5]84看似团圆却到底“还是有点怅惘”,本该欢喜却到底还是“苍凉”。置身于“乱世”的张爱玲以《红楼梦》式的忧患意识引发对生命和人性一次次的反思和拷问,催生了作品无尽的苍凉意蕴。
注释:
①如甲戍侧批“淡淡写来,方是二人自幼气味相投”“文章只是随笔写来,便有流离生动之妙”;庚辰眉批“淡描轻写,全无痕迹”;庚辰侧批“淡淡一句,勾出贾珍多少文字来”;庚辰夹批“淡淡抹去,妙”等等。参见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