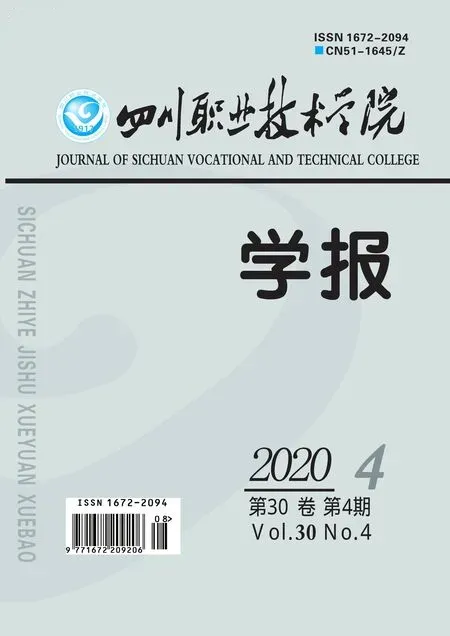从空间视域看《苦行记》中的种族观
李向云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225)
马克·吐温作为一个文学巨匠,为美国文学留下宝贵财富。马克·吐温因其游记而著名,从而引起人们对于美国西部的关注。在他的所有游记作品中,《苦行记》和《傻子出国记》因揭露了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而广受关注,其中,包括种族问题。在《苦行记》中,个人和国家的种族观不言而喻。《苦行记》记录了作者在西部游历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对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问题的反思。除了描述自己的旅程、淘金热和西部人们投机行为外,他还把注意力放在了美国印第安人和中国人身上,展示了他对种族主义的态度。
游记文学以空间运动为基础,以地点和行程变化为特点进行创作。作者通过描述出现在某一固定地点的人来展示一个地方的特征,从而将空间赋予寓意。在《苦行记》中,作者拜访过许多地方,这些地方都代表着当地的风俗习惯、社会背景以及经济发展情况。而在这些地点中,印地安人的荒原和中国移民的“中国区”广受关注。两个空间代表着两个种族群体和两种伦理,一种被美国主流社会(即白人群体)排斥的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对小说主题的影响极大,空间的构造和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者早期的种族观。例如,在《苦行记》中,沙漠象征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特征。有沙漠的地方,就有美国印第安人,他们杀戮、入侵和抢劫;而在“中国区”,这条街见证了混乱、鸦片和肮脏的中餐。所以当再提到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指生存的物质空间或场所,而是一种带有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物。因此,本文将空间意象与空间理论结合,解读马克·吐温早期生涯中对种族主义的态度。
一、理论基础
“空间转向”自提出以来经历了三个时期: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和索亚。基于前人的理论,索亚首次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本文将主要从索亚的理论出发,分析《苦行记》中的空间转换,进而揭示马克·吐温对种族主义的态度。根据索亚的观点,空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
“第一空间”是指“一种物质化的空间”[1]74,这种空间有其客观性与真实性。它可以被观察,描绘与测量。因此,第一空间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被研究,比如某些事物的地点、位置和情境。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实体。我们可以在“家庭、建筑、社区、村庄、城市、地区、国家、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缘政治”等领域开展社会实践[1]75。而第二空间是一种理想状态:“第二空间是一个概念化的,符码化的,构想的精神空间,属于艺术家,文学家,符号学家,政治家创造的空间。”这里空间更加类似于人们想要创建的乌托邦世界。在这里,充满着权力和意识形态。而通过这种权力构想出的乌托邦世界去揭发世界的“真实”。这个更像我们所存在的世界。这样的空间与第一空间完全相反。一个是物质的实体,另一个是理想的描述。两者走向了两个极端。因此,第三空间的出现是合理且必要的。
“第三空间”是索亚首次提出的,它不是“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简单的否定,他强调第三空间的开放性和广博性。索亚在他的书中写道:“这是一个一切都在其中的空间,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每一个事物都清清楚楚;但它又是一个秘密的猜想的事物,充满幻想与暗示,对于它,我们家喻户晓,但是从来没有彻底地看清它,理解它。”[1]10因此在索亚的第三个空间中,它尽可能的包括性别、种族、阶级等,在这样广泛的概念之下,读者可以了解不断变化位移中的社会背景。这也是为什么笔者选择以“第三空间”来分析种族主义。它可以包含和传达出更多的社会意义。因此,本文旨在分析《苦行记》中的空间转换所传递出的种族观。
二、荒漠中的印第安人
(一)第一空间视域下的荒漠
荒漠作为现实存在的地理环境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其痕迹。欧洲移民者发现新大陆后,美洲印第安人便开始了他们的噩梦。他们失去了家园,被迫向西迁移,因为移民者需要这片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的“应许之地”来发展自己。因此,这些可怜的美国印第安人不得不迁移到密西西比以西的沙漠地区。西部荒漠就是他们的生活场所,在那里他们遭受着恶劣天气和生活条件的折磨。更糟糕的是,自从淘金热开始,他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他们的保留地变得有限,因此不得不进一步向西迁移,并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现存的黄石国家公园留下了例证。黄石国家公园是19世纪初印第安人居住的荒野,是美国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由于受到迫害和生活条件的压力,他们在悬崖上修建住所,成为当今的景观遗产。除此之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与那些野生动物搏斗,去获取食物和居住空间。所以从马克·吐温笔下,读者们可以知道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荒漠是一个在自然不过的生存环境。
(二)荒漠中印第安人的活动
在《苦行记》中,美洲印第安人出现在马克·吐温西部之旅的伊始。据笔者统计,从第一章到第三十章共有14处关于印第安人的描写。在这些章节中,第19章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美洲印第安人。在这14处描述中,10处描述是关于印第安人“抢劫”的活动;2处是关于他们的饮食习惯和居住环境的描写;一处是描写印第安人的迷信;唯一一处比较正面的描写是关于他们为白人工作。因此在阅读了《苦行记》之后,印第安人的负面形象留在了读者脑海中,诸如暴力抢劫活动,与动物争夺食物,与旅途中的旅行者搏斗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记录。胡妮在《托尼·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中提示到,一个人拥有的生存空间越小,就越重要[2]36,这意味着人们空间的活动越细化,他们拥有的权力和特权就越多。如果个人能够在一个更狭小、更明确的空间内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他或她就能在这个国家享有更多的权利和特权。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沙漠中的印第安人时,看到的仅有他们与白人的争斗。而他们的住宅只是无限的荒漠,这里没有家庭的概念,也没有社区的概念,而家庭和社区是文明的标志。
作为一个被驱逐的部落,在新环境中,印第安人必会学习耕作和播种,狩猎和生存,但所有这些可能的活动都是缺席的。因此,很明显,印第安人被白人边缘化了。事实上,从白人的角度来看,美洲印第安人只是一种令人畏惧的动物。他们“不生产,没有村子,没有结构严密的村社——他们唯一栖身之处不过是挂在灌木上用以遮挡风雪的破布片,而且,他们的栖身之地是我国或是其他国家最陡峭,最寒冷,没人愿意涉足的不毛之地。”[3]124他们在生物链中的位置仅位于蠕虫和苍蝇之上。在白人眼中,他们的地位甚至不如猫。“他们饥饿,永远饥饿,猪吃得下去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拒绝,猪通常都会拒绝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挑剔;他们也打猎,但奢望不过是,猎食大耳野兔,蟋蟀和蝗虫,从秃鹰和郊狼那里盗猎腐肉。”[2]124从第19章的描述中,作者清楚地呈现出一个懒惰、低劣的种族,表现出马克·吐温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厌恶和不屑的情绪和态度。任何对印第安人否定性的描述都是对白人种族的一种赞美与肯定。
(三)第三空间视域下的荒漠
荒漠既是一个生存的场所,也可以在“第三空间”理论的指导下具有其空间意义。荒漠不仅是美国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白人社会中的一个象征符号。查日新教授在其《空间转向:文化协商与身份重构》一文指出:“每一个人类空间的场域——‘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都可以被看作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既是物质的,也是形而上的。”[4]我们之所以能够用辩证的思想去解读空间,是因为空间涵盖了社会意义,传达了文化意义和思想态度。在《苦行记》中,“荒漠”作为一个居住的地方,也不例外。“荒漠”的形象与美国印第安人这个被边缘化群体的身份和命运息息相关。
当我们提到荒漠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贫瘠的沙漠,食物匮乏和荒芜,文明永远不会在这里驻足,事实也的确如此。欧洲人带着传统的荒野观念来到了新大陆,这种荒野观源于《圣经》中伊甸园文化的传统。天堂对立面的任何地方都是荒野。因此,来自欧洲的移民者自然而然地把新世界看作是一个荒芜的地方,“荒野是非常真实和非常可怕的。”[5]101因此,荒野中的居民在道德和身体上都是不文明的。在现实条件下,物质的缺失导致了文明和经济的落后。因此,这样的形象传达出印第安人的落后与愚昧,对整个美国社会毫无用处。在白人思维中,印第安人是野蛮和不文明的,他们应该生活在荒漠中,因为荒漠往往是黑暗和邪恶的象征[5]24。只要移民者提到印第安人,贫瘠的荒漠就不断地与野蛮的印第安人结合在一起。因此,印第安人在生物链中落后于其他动物的想法不足为奇。通过荒漠意象,马克·吐温对于印第安人的态度不言而喻:厌恶、不屑和轻蔑。
三、“中国区”的中国移民
马克·吐温是一位为数不多的关注中国移民作家。不仅《苦行记》中描述了一群中国人,其它作品如《歌德斯密斯的朋友再度出洋》、《阿辛》、《黄祸的寓言》、《中国人约翰》等作品中也详细记录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这些作品呈现出不同的中国性格与特征:有的是中华美德的体现,有的则讽刺中国人的缺陷。然而,无论怎样塑造这些人物,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被称作“中国佬”的移民都与白人居住的主要社区隔离开来。每当马克·吐温提及他们,就会有一个明显的“空间”转移,从美国社会转移到“中国区”。虽然这看起来是自然的空间定位,但“空间”的变化暗含着马克·吐温对中国人的态度与情感:轻蔑与讽刺。
(一)第一空间视域下的“中国区”
在《苦行记》第54章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国区”。马克·吐温在本章开头写道:“中国人居住在‘中国区’”[2]293,并以此为空间活动的背景,展开对中国移民的描写。实际上,这也是后期唐人街发展的一个雏形。自从第一批中国移民来到美国,这种专为中国人准备的区域、街道或任何类似地方的概念和实体一直都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区域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由于习俗的原因,中国移民从不犹豫地选择聚集在一起,这样,他们可以共享他们的食物、语言、风俗习惯,为他们在外国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除此之外,文化传统为这种聚集做了很多贡献。正如费孝通在他的著作《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6]因此,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由于植根于一代又一代的“乡土情结”,他们会选择住在一起。其次,“中国人区”的形成是由于白人的偏见和迫害。由于最初的风俗习惯不同,白人认为中国人是“异教徒”。在白人眼里,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种族。当然,“信仰”在这里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仅局限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中国人的信仰是具有神秘气息的。他们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信仰与祭拜他们的祖先。马克·吐温在《苦行记》中代表他的同胞们,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人信仰的看法:
中国人极为崇敬他们的死者——事实上,他们崇拜他们已故的祖先。因此,在中国,不论是在一个人的前院、后院或是他家住地的其他地方都是他的家族宗茔地,他就能每时每刻光临那个坟墓了。因此,这个巨大的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公墓[3]358。
中国人尊重死者,这是事实。而马克·吐温文中对中国人崇敬死者的描述却违背了事实。在这里,来自于白种人的偏见和嘲笑显而易见。这种误解导致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中国人区”或是“唐人街”的形成。然后,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来自白人的迫害。美国社会对中国移民充满了暴力和杀戮,尤其是中央铁路的修建过程。因此,为了保护自己,中国人更喜欢住在一起,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争端。《苦行记》中的一段描述揭露了白人社会对于中国移民的敌对态度和暴力活动。马克·吐温说:“几个小伙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石头把一个中国人活活砸死,尽管一大群人目睹这一可耻的暴行,居然没有人站出来干涉。”[3]357用石头打死人是如此残忍以至于读者们无法想象,但这只是美国数千起华人暴力案件中的一例。特别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后,中国人受到了空前的敌意,殴打致死、杀戮或任何导致死亡的暴力活动经常出现。因为这些中国工人“耐心、勤劳、安静、平和、和蔼可亲,他们威胁着那些懒惰、混乱、甚至抱怨的本地工人”,所以他们被白人排斥在外。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个社区来生活,保护自己,并尽可能提供一个合适的住所。
(二)华人在“中国区”的活动
与荒漠中的印第安人相比,“中国区”的华人活动会更加丰富与文明。《苦行记》第54章记载了华人在“中国区”从事的五种主要活动或工作:厨师、洗衣工、杂货店和食品店老板、彩票业投机者和白人家庭佣人。不难发现,中国人负责的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收到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往往不成比例。由于工资较低,这些工作被当地白种人拒绝了。例如,“他们洗衣服的价格是每打2.5美元——这对当时白人所能支付的洗衣费用来说,相当低廉了。”[3]294在白人主流社会和文化中,中国人被称为“中国佬”或“苦力”,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蔑称。白人只把华人当作仆人,为他们提供基础的需求和必要的劳务。
尽管华人为谋生和服务白人社会而努力奋斗,但他们仍然受到整个社会的不尊重和鄙视。白人对待他们犹如对待狗一般;华人利用基督徒视为垃圾的材料;马克·吐温他自己也拒绝了阿辛的邀请,因为他认为香肠里有老鼠的尸体;而华人的彩票生意在马克·吐温看来是一种投机生意。纵观全文,马克·吐温似乎是代表中国移民者来述说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但是马克·吐温采用的是美国的立场和标准。尽管他承认中国人参与了美国历史的建设,但他将中国人排除在文明大门之外。马克·吐温所描写的每一项活动都缺乏他的肯定和钦佩,因为很明显,他认为华人和白人不是同一种族,更不会放置到平等的地位来讨论。
(三)第三空间视域下的“中国区”
“中国区”一方面为移民提供了居住的场所,另一方面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了一个文化社区,也就是现在的“唐人街”。每次说到“中国区”,我们都会想到中国餐馆和食品、移民以及“他者”身份。因此,“中国区”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是一个文化空间。刘进在《论空间批评》里指出,空间是一个充满政治和经济冲突和争议的地方,而不是一面镜子,以一种片面的方式直接反映社会[7]。在马克·吐温看来,“中国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中国区”的描述,马克·吐温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意识形态中传递和巩固了中国的形象。
首先,像“远东”地区一样,这里乱七八糟,人满为患,贫困落后。马克·吐温从未访问过中国,因此他是根据美国盛行的传闻来描述中国的。他听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帝国。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挤满了穷人,就像“中国区”一样,建筑密集在一起,由于道路太窄,马车无法通过。此外在《苦行记》中,“帝国”一词不止一次被提及:“因此,这个巨大的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墓地”;“在帝国的任何地方,修路都不得不冒犯他们的祖先或亲友的坟墓”[3]359。在这样的“帝国”里,除了皇帝和官员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奴隶,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将自己的王权隐居起来,不能被普通的人类接近。当然,马克·吐温在这里暗示,中国是一个充满压迫和奴隶的国家,与“机遇之地”和“勇敢之地”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样的一个帝国里,人们生活在巨大的苦难中,他们就像流浪汉一样,四处漂泊,呈现着病态的神情,颓靡的黄色,拖着长尾,寄生在这样的一个“帝国”里。
其次,这是一个鸦片肆虐的国家。在《苦行记》中,对于中国移民们结束一天劳作后吸食鸦片的场景作者作了细致的描写。他写道:约翰,连抽二十多口,然后翻身去梦里告别了他的洗衣活计,到天堂享受老鼠和燕窝去了[3]361。这里不仅只有一个“约翰”,而是每一个人都是“约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染上了毒瘾。即使他们是穷苦的“流浪汉”,他们也会为毒品买单,这暗示着来自“帝国”的人们都有不良的习惯,这与新教徒的节俭和务实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完全是另一个国度的“异教徒”。
第三,这是一个异教国家。他们不信仰上帝,而是他们的祖先。在中国,不论是在一个人的前院、后院或是他家住地的其它地方都是他的家族茔地,他就能每时每刻光临那个坟墓[2]358。在“中国区”内,由于空间有限,马克·吐温把这种对“信仰”的描写转向室内。他写道,他在中国餐馆吃饭,然后从店老板那里得到保佑平安的灵光,并向一两尊异教神合十行礼[2]363。在这里,揭示了在西方国家,基督教信仰是对身份的唯一认同,上帝是白人唯一可以祈祷的人。人可以信仰和祈祷,否则,他们则是异教徒。因此,当马克·吐温描述“中国区”时,他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将其与主要社会区分开来:“他们的居住区和该城市其它部分稍微隔开点。”[3]357,表现出与白人不同的身份。
四、空间视域下的种族观
根据福柯提出的权力空间理论,空间本身是一个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它是在社会发展和人类干预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此外,空间是知识和权力得以运作的地方,在这样的空间里,一切都是为了表达国家的哲学和意志而设计和表演的,每一个人都为国家精神服务。因此,空间代表力量与权力,换言之,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被权力监督的社会。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哪种文学体裁中,空间可以代表国家和国家的意志。马克·吐温把美国印地安人和中国人放在不同的空间,这不仅是出于游记小说体裁的要求,也是出于对“权力空间”的考虑。印第安人和中国人与白人有着不同的伦理道德,因此,他们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而主流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文明和先进的社会。因此,无论是印第安人居住的荒漠,还是中国人居住的“中国区”,这两个地方都被标记为贫穷、原始、凌乱,甚至是野蛮的地方——位于社会的边缘。从索亚的“第三空间”来看,它更像是一个“他者”的空间,主流社会永远不会接受它。事实上,马克·吐温通过空间的转换,将这两个种族异化为“他者”。
对美国印第安人来说,这是一个存在于荒漠中的种族。有印第安人的地方,就有杀戮、抢劫和各野蛮袭击。从第一章到第三十章共有14篇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描写。13个描述是关于白人的抢劫和杀戮活动以及他们野蛮的饮食习惯,这是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通过这些在荒漠中的活动和描写,读者们读到的只是一群野蛮人,一个残忍的种族,没有同情和人类的情感。他们生活在野蛮的环境中,因此他们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然而,马克·吐温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什么印第安人要与白人为敌,甚至与邮递员作战,以及白人对“野蛮人”的屠杀。然而在整本书中,除了所谓的“合法”防御之外,很难找到任何关于白人对印第安人屠杀。因此,马克·吐温对于这个野蛮种族的蔑视和歧视不言而喻。对马克·吐温本人甚至他的国家来说,把美国人和印第安人放在一起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生物链中。因此,远西的“荒漠”是他们的家园和“游乐场”,这个地方需要文明社会的熏陶和感染。
而对中国移民来说,马克·吐温将这一种族置于一个比印第安人更高的生物链中,至少他们处在充满中国文化的中国区。而在这个街区,中国人尽职尽责,尽最大努力在异国他乡谋生。毫无疑问,马克·吐温在这里凸显了中国人的优点:勤奋、耐心、节俭、随和与不酗酒。所有这些优点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缺位的。每次他提到中国人的优点,他都会提到白人所有的缺点。然而,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优点都可以轻而易举被学习。同时,马克·吐温通过他的笔尖传达了一种警告,即他们的新生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的一些同胞们如此懒惰和傲慢,以至于远东民族可能会超越他们。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要向那些中国人学习他们的优点,否则他们将被毁灭。但当提到中国人的缺点时,显示出一种致命性和种族的劣根性。每一次提到中国的缺点都是对美国优点的肯定。美国没有鸦片、奴隶和皇帝,是一个民主和机遇的圣地。通过对这些弊端的深入分析,笔者发现,这些弊端都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根源,即使他们生活在美国,也永远无法消除他人眼中的这种致命的缺陷。以“自由”为例,马克·吐温一直强调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所以人们生来就是奴隶。奴性根植于他们的血液。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都是奴隶,机械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即使他们是男性。在国内,他们是为皇帝服务的;在国外,他们是为白人家庭服务的“优秀家仆”。除此之外,他们卑躬屈膝,永远不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在第54章的开头,马克·吐温写道:“他们是个无害的民族,即使白人不理睬他们,或者像狗一样对待他们。”[2]356。在这里,马克似乎在谈论中国人的善良,而事实上,“狗”一词会让读者意识到,这个种族是没有发言权、辩护权,更没有指证白人的权力。
所以通过对“中国区”的描写,马克·吐温实际上是在丑化中国这个贫穷、负担过重、封建迷信、缺乏自由意志和精神的国家的形象。更有趣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谈到中国移民时,马克更喜欢使用Chinaman这个词,而Chinaman在西方意识形态中指“中国佬”。在第54章中,马克·吐温共使用24个“中国佬”来指华人。因此,从这些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马克·吐温并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而“中国区”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第三空间”,他们永远不会被白人社会接受和同化。它也像是一座无形的“监狱”,在那里,围墙是按照地理意义建造的,用来将其他人与主要社区隔离开来,作为惩罚的一种方式。行政权力至少是无形的或不可见的,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感受到它的监督和压力。正如福柯在《惩戒与惩罚》一书中所提到的:“惩罚权力不再公开显示自己,而是默默组建一个客体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惩罚将作为治疗而公开运作。”[8]很明显,这里的“中国区”扮演着监狱的角色,显示出美国的意志和准则,或者至少是美国的标准。因此,马克·吐温对中国人的态度仍然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白人的傲慢和对落后民族的偏见。
所以不管是“荒漠”还是“中国区”,它们都扮演了第三空间的角色——一种边缘化的地区。这些地区在整个社会内部,但在主体社会之外。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人可以进入主要社会,但他们不能住在这里。他们可以在这里工作,但工作之后,他们必须回去。这就是第三空间”的存在意义,它时刻提醒人们不属于主体社会。在这里,第三空间展示了主体社会分裂的意愿和不妥协的意志。马克·吐温作为主体社区的发言人,很难向这样的第三空间妥协。因此,通过第三个空间,我们可以了解马克对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态度。除此之外,在马克·吐温种族优越性的背后,是“美国的伟大”,种族等级制度,显示出一种殖民主义的观点
五、结语
空间与场所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下的种族观,空间的切换是作者主观种族态度的转变。第三空间下的“荒漠”和“中国区”为我们了解这两个种族的新视角,这些区域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印第安人和中国移民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马克·吐温区别于白人种族的一种空间构造,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为除白人以外的其他族裔划分的“第三空间”,是为“他者”打造的边缘化空间。以此传达了作者主观意识中对于种族的偏见。作为早期游记中的种族观,也与后期马克·吐温的对于种族的新认识形成了对比,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马克·吐温的种族观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