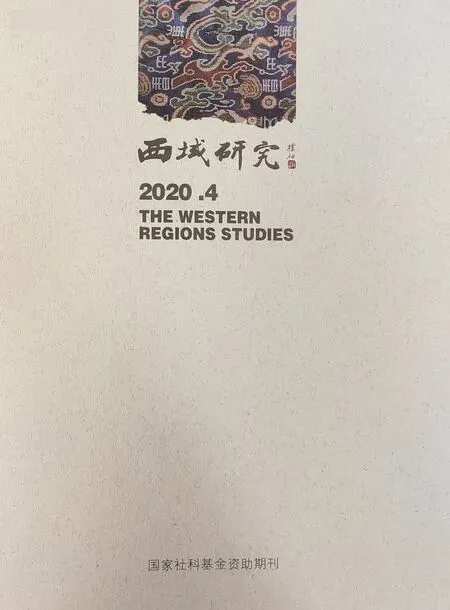张骞的“不得要领”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孟宪实
内容提要:张骞西使,所有使命都未达成,西汉寄以厚望的大月氏、乌孙都缺乏对汉朝的了解,这是张骞使命不达的关键,这便是史书所谓的“不得要领”。但张骞出使西域仍然是人类历史大事件。欧亚大陆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开始走向最初的“一体化”,各个文明区和国家之间,政治联系由此启动。如果说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的第二期,那么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则是全球化第一期的起步。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激发下,丝绸之路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很多问题值得深入追究。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贯通,因此具有了世界史意义。但是,张骞出使的直接目的,是联络月氏和乌孙,建立共抗匈奴的联盟。就此而言,张骞出使并没有达到目的,史称“不得要领”。但是,“不得要领”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后来的研究更强调丝绸之路的主体方向,这个最初的问题,常被忽略。略加考辨,就正方家。
一 出使大月氏“不得要领”
张骞出使西域共有两次,一次出使月氏,一次出使乌孙,但具体出使目标,两次皆未达成,这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没有达成?最初的解释见于《史记》。《史记·大宛列传》披露张骞事迹,内容如下:
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1)《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修订本,2013年,第3805~3808页。
《史记》的这段记载,是我们回顾这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始记录,这里引用全文,因为信息有限,无不重要。与本文关系最重要的两个内容需要重点提示,一是张骞出使大月氏的目的;二是大月氏对汉朝建议的反应。正是因为大月氏的反应,《史记》称张骞“不得要领”,这是史书的评述,相当于总结张骞出使失败之因由。
《汉书·张骞传》这段记载,尽数来自《史记》,其文如下:“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2)《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88页。《史记》《汉书》文字相同,所谓“不得要领”,是张骞不得大月氏要领。“不得要领”当如何解释呢?《史记》的诸家解释重点在语词。《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要领,要契。”《索引》李奇云“要领,要契也”;小颜以为衣有要领;刘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颇是其意,于文字为疏者。(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注释,第3807页。
对此,《册府元龟》也有类似的解释,其原文与史汉相同,括号部分是注释:
康居传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以大夏为臣,为之作君也),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下远音于万切)。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要,一遥切,衣要也。领,衣领也。凡持衣者则执要与领。言骞不能得月氏意趣,无以持归于汉,故以要领为喻)。(4)《册府元龟》卷六五二《奉使部·达王命》,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517页。《册府》文字都来自《汉书》等旧注,证明这类说法获得后代的认同。
有关要领的解释,用衣领来比喻,要领即要害。《册府》的解释有所扩展,认为不得要领是“不能得月氏意趣”。这个解释,也被胡三省移用在《资治通鉴》注释中。(5)《资治通鉴》卷一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611页。以“意趣”比喻要领,从外在的关键进入内在的需求,有深入解释的方面。而张骞虽然在大月氏滞留一年多,依然不能把握大月氏的“意趣”。所谓“意趣”即内在需求,因为不能掌握,自然无法说服,张骞只能无功而返。
张骞出使西域,主要的战略任务并没有完成,通常研究者比较赞同或满足于传统史书的解释,进一步讨论的并不多。陶喻之先生著《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新解》一文认为,是大月氏信仰了佛教,从而不愿意听从张骞的主张:“显而易见,张赛出使大月氏时外交上失利的原因,是双方没有一致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主张。”(6)陶喻之:《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新解》,《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第37~40页。究竟如何理解张骞的“不得要领”,需从多个视角观察。
张骞的历史功绩是开辟了丝绸之路,但这并不是汉武帝朝廷交办的使命。他的使命是寻找大月氏,并与之实现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匈奴。这个使命的前半部分是寻找大月氏,张骞完成了,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要达成战略联盟,却没有成功。张骞没有说服大月氏,结盟的战略只好放弃,而史书的解释便是“不得要领”。应该承认,《史记》所记内容肯定来自张骞,所以“不得要领”,完全可以看作是张骞自己的解释。
在今天能够阅读的历史文献中,汉朝的这个联盟月氏战略并不是表达得很完整,文献记载又很有限,所以我们今天的研讨,不得不有所推测。最早涉及张骞出使的《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的使命表达得就不完整:“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够读出联合月氏共击匈奴的战略,但是到底怎样实施这个战略,语焉不详。《汉书·张骞传》的文字完全来自《史记》,几乎没有增加新的信息。(7)《汉书·张骞传》:“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见《汉书》第2687页。
有关张骞出使的记载,《资治通鉴》晚出,但比较完整。其言为: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馀,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8)《资治通鉴》卷一八,第610~611页。
汉朝要联合月氏,有两个背景最为重要,一是月氏原来的居所,“故居敦煌、祁连间。”其二,月氏与匈奴有仇,但苦于力量不足,即“无与共击之”。《通鉴》介绍月氏的“故居”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汉朝联合月氏的重要依据之一,那就是邀请月氏返回故地,与汉朝联合攻打匈奴,这样既可以解决月氏“无与共击之”的难题,又可以解决汉朝的匈奴之患。《通鉴》引入的新资料,是《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传》未曾措意的,但这资料来自《汉书·西域传》,并非《通鉴》发明。《汉书·西域传》有大月氏条: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9)《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大月氏国条,第3890~3891页。
有关大月氏的原来居住地,从《史记·匈奴列传》中也能略有感觉,但不如《汉书·西域传》说得明确。在匈奴崛起之前,月氏很强大,匈奴的冒顿单于曾经作为人质居住在月氏。打败月氏和东胡,是匈奴崛起的标志。匈奴打击月氏,按照西汉的理解是过于残暴,所以大月氏才有报仇之心,可惜无报仇之力。这是西汉月氏战略的出发点,认为对方有结盟的可能性。《资治通鉴》在书写张骞出使西域背景时,对于月氏的介绍更全面了,但也忘记了《史记》和《汉书》都强调的西汉背景,即“汉方欲事灭胡”。正是因为汉武帝的朝廷决定与匈奴开战,才有张骞出使西域,希望建立联盟,消灭共同的敌人匈奴。(10)张骞出使西域的背景,决定了张骞出使的具体时间。传世文献,特别是《资治通鉴》的考证,有忽略背景的嫌疑,参见拙文:《张骞初使西域时间新论》,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
张骞没有说服大月氏,《大宛列传》中其实已经有交待:“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大月氏的现状是土地肥沃、社会安定,局势良好且十分满意。如果同意汉朝的建议,他们需要放弃眼前的安定生活,长途跋涉,再回东方与匈奴作战。因为生活安定,距离遥远,报仇之心已经消失。对于大月氏而言,张骞的建议是国家重大战略变化,是否能完成报仇目标,事实上也不清楚。这就意味着,接受张骞的建议,具有风险性。对比风险与收获,即使能够打败匈奴,敦煌祁连之间河西走廊的自然条件,也不能与大夏相提并论。张骞如何能说服大月氏人放弃手中的西瓜去抢夺遥远的芝麻?所以,“不得要领”是正常结局。(11)从大月氏的视角理解张骞“不得要领”,是《史记》以来就是主要思路,这也是今天研究者的基本观点。参见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3年第1期,第40~46页。
二 出使乌孙未达成结盟
张骞两次出使,第一次因为不得月氏要领而失败。第二次,张骞出使乌孙还是没有成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重点是说服乌孙返回原来居住地,情况与大月氏相似。而所有乌孙的情况,都是张骞介绍给汉武帝的。当时,张骞因为战场失期,被免为庶人,他渴望重新工作的心理很清晰。张骞说服汉武帝,在战略上联合乌孙抗击匈奴是可行的。《汉书·张骞传》有如下完整的记录: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语在《西域传》。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12)《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691~2692页。
这次结果是“未能得其决”。而《史记》对此的描写还是“骞不得其要领”(1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18页。。对此,《汉书·西域传》的记录更详细。其文为:
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14)《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条,第3902页。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在乌孙再次遭遇失败。《汉书》这里所谓“未能得其决”与《史记·大宛列传》中“不得其要领”含义一样,即未能说服乌孙响应汉朝的战略建议。
张骞出使乌孙时,与第一次出使环境已经完全不同。第一次出使对于汉武帝的朝廷而言,完全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找到大月氏,是否能够结盟,全然未知,试探的成分居多。事实上,张骞还在途中,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已经正式开场。到张骞出使归来,汉朝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在北方取得重大胜利。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击陇西,大破匈奴西方浑邪、休屠二王。这导致匈奴内部矛盾爆发,单于要诛杀战败的二王,催发二王向汉投降。后来,虽然浑邪王杀休屠王,只有四万人投降,但是通往西方的道路却畅通了。对于此事,《汉书·张骞传》说法更明确:“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15)《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691页。转年,匈奴在正面发动反攻,代郡、雁门和右北平都发生战斗,汉朝损失几千人,博望侯张骞等人误军期,赎为庶人。此时,汉朝连续大胜,匈奴虽然坚持不称臣,但汉朝全面掌控了战场局面。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再次出击,胜利成果扩大,迫使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一段关于张骞的文字,如同张骞简历,其文曰: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16)《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3539页。
由此看张骞的经历,简洁明了。第一阶段是通使大夏;第二阶段归来后为校尉;第三阶段从大将军有功,封博望侯;第四阶段,因罪赎为庶人;第五阶段,再使乌孙,归国不久去世。可惜具体时间未详,需要其他资料补充论证。
张骞封侯时间是准确的。《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记载,元朔“六年三月甲辰,侯张骞元年。以校尉从大将军六年击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绝域大夏功侯。”张骞封侯,不仅是因为立有军功,也包括此前的出使绝域。此事,《汉书》也如此记载,三月甲辰,一字不差。(17)《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第646页。元朔六年,是公元前123年。至于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一事,时间也是清楚的,《史记》记为“后三岁”。《汉书·功臣表》明确写作“元狩二年”,《通鉴》写作“夏”。(18)《资治通鉴》卷一九,第630页。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汉朝取得巨大胜利,直接导致秋天浑邪王率众降汉,河西走廊无人居住。上文引《汉书·张骞传》“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正是指这件事。
这就成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背景。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间依然模糊不清,《资治通鉴》置于元鼎二年(前115)叙述:“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19)《资治通鉴》卷二〇,中华书局,1956年,第657页。因为张骞要劝说乌孙回到河西走廊,出发的时间最晚也是公元前121年之后。
张骞第二次出使失败,史书记载远比第一次清楚,因此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次的问题所在。首先,西汉对乌孙的要求是清楚的,乌孙回到原来住地,双方通婚结为兄弟,共同抗拒匈奴。西汉要与乌孙建立平等的联盟,所谓“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就是兄弟之国。乌孙的情形与月氏相似,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对于大月氏的建议也应该相似,邀请大月氏东归,双方建立平等的联盟,共抗匈奴。
乌孙对张骞的回答,内容清晰。乌孙是匈奴的手下败将,长期折服于匈奴,深知匈奴强大。但是,乌孙与汉朝的关系却是“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乌孙亲眼见到了张骞庞大的使者团:“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但是,乌孙事实上对于汉朝的大小、强弱却并不了解。即是说,虽然张骞率领一个庞大、富有的使团,依然不能证明汉朝的强大与否。在这种前提下,乌孙如果投身与汉朝的联盟,如果汉朝没有使者说的那么强大,还要公然与匈奴为敌,后果恐怕是灾难性的。这是根本性的战略,乌孙不敢贸然行事,找了一系列借口,如乌孙王没有实权,不能独立做主等等。最后,乌孙很礼貌地赠送汉朝几十匹骏马,还派使者亲自来汉朝致谢,而真正的意图是侦察汉朝的实际情况。
乌孙所在地是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比较大月氏所在,距离汉朝要近得多。由乌孙的情况来分析大月氏,张骞不得月氏要领,理由变得更容易理解。大月氏对汉朝的了解一定少于乌孙,乌孙尚且需要对汉朝摸底侦察,距离汉朝更遥远的大月氏具有类似想法,当然不奇怪。张骞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到达乌孙,而张骞到达大月氏的时候,除了手中的使节有一定的证明力以外,匈奴夫人和孩子,另外就是堂邑氏奴甘父。原本,张骞出使大月氏的时候,也有一个一百多人的使团,但最后到达大月氏的只有两人。从乌孙三百人使团都不足以证明汉朝之强大的事实看,即使一百多人的全部使团成员都能到达大月氏,也未见得能够取信大月氏,何况事实上只有两人!仅凭张骞两人,要说服大月氏改变国家战略,放弃现有的和平富足生活投入与匈奴的全面战争,说服力过于弱小是显而易见的。
张骞西使路上,主要是通过言辞说服沿途各国。从匈奴逃出,张骞首先到达大宛,然后是康居,最后是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的记录如下:
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20)《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06~3807页。
大宛对于汉朝的富裕是有所耳闻的,因为没有交通,只能是半信半疑。现在见到张骞,认为是获得了良好机会。于是帮助张骞,把他送达康居,康居再把张骞送达大月氏。此后,所有汉朝的情况,都出自张骞之口。凭此,就让大月氏举国东迁与匈奴开战,无论谁作为大月氏的领袖,都是难以同意的。后来,汉朝与西北各国有了外交往来,汉朝的情况也被各国了解,证明张骞所言不虚,“(张)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21)《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693页。但这是后话,就张骞出使之初而言,张骞不得月氏要领,具有必然性。
大宛对于汉朝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最主要的就是“饶财”,即富饶。大宛在乌孙之西,对于汉朝的了解不该比乌孙更多,为什么看上去大宛更加积极主动呢?这需要给予区别对待。汉朝对于大月氏和乌孙的需要是顶级战略,举国合作抗击匈奴,同时伴随大迁徙。而大宛对于汉朝的需要很有限,仅仅是通商而已。互通有无,在商品上获得交换价值,通商就值得,所以这对于大宛而言,需求是比较单一,风险较小。但是,大月氏和乌孙,汉朝希望与他们进行战略合作,对手是强大的匈奴,所以风险很大,表现出谨慎很正常。
三 来自“西南夷”的佐证
张骞两次出使,对于西域的总体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各国的空间位置也清楚起来。基本情况是乌孙最近,然后是大宛等国。《史记》所记第二次出使乌孙,派遣副使前往各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2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19页。对此,《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所记为“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第2692页)比《史记》记载要少。至于空间位置,史书也有记载,大宛“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2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08页。。而大月氏的位置是:“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24)《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10页。在这些西域各国中,张骞的时代,只有大宛对汉朝有所耳闻。但是,从后来贰师城发生的冲突看,大宛对于与汉朝通商积极性有限,了解也有限,至少把遥远距离当作难以克服的障碍。(25)余太山先生的《张骞西使新考》一文中,曾经引用董仲舒和司马相如说法中有“康居”等西域诸国信息,认为张骞出使之前这些信息西汉已经了解,本文宁愿相信这是后来文字修饰的结果。判断当时的交通状况与彼此的了解程度,基本公式是距离越远越缺乏了解。
张骞主要的使命无一达成,究其原因,从大月氏到乌孙,对于汉朝战略结盟的拒绝,都因为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对汉朝的不了解。此事史书表达为张骞对大月氏、乌孙的“不得要领”,事实上,大月氏、乌孙对汉朝同样是“不得要领”。战略盟友的大小强弱都无从得知是无法合作的,古今中外,此题都无解。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大月氏的自身状况,忽略了因为交通不畅,彼此缺乏了解这个基本命题。连基本情况都不了解,如何进行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不仅如此,所谓合作是联合起来与强敌作战,而这种合作背景下的战争,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如此,张骞才不得要领,没能达成使命。
秦汉中国,一个巨大的历史运动正在展开。重新统一的中国,发展动力强劲,对周边世界的影响也如期而至。随着张骞出使西域的影响日益深化,西向发展已然成为当时中国日益稳定的方向。但是,当这一系列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各地的准备都不足,到处显现出茫然不定的状态。乌孙、大月氏这些地区对于汉朝茫然无知,充分证明此前的联络缺乏,更突显张骞出使的历史意义。周边世界对汉朝的无知,不是偶然表现,同样的故事在当时中国的西南方也在上演。
云南、贵州地区,西汉时称作“西南夷”。关于西南夷的经营,以张骞出使归来为界,可分作前后两个阶段。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系统记载,所谓西南夷,“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地形复杂,居民散漫存在,或有君长,大约有上百个区域,其中夜郎和滇两个小王国势力最大。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攻打东越,乘机派番阳令唐蒙前往南越,施加政治影响。唐蒙在南越发现了一款食物,就是南越王吃的“枸酱”,而这种酱只有蜀地生产。这证明南越与蜀地是有交通的。唐蒙是有心人,回长安后专门找蜀地商人征询,商人的回答是蜀地的枸酱通过夜郎进入南越,夜郎虽然不是南越的臣属,但南越对夜郎影响巨大。于是唐蒙向朝廷建议,通过巴蜀经营夜郎,进而影响南越。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拜唐蒙为中郎将,率领军队从巴蜀进入夜郎,在南夷之地建立了犍为郡。(26)《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3604页。唐蒙的成功激励了蜀人司马相如,他的建议也获得支持,他受命前往西夷,说服当地居民,为蜀郡增添了“一都尉,十余县”(27)《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3604页;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第3668页。。此后,西南夷几次叛乱,朝廷又要经营北方,在公孙弘的建议下,汉朝停止了经营西南夷。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这是元朔三年(前126)年初的事。(28)《资治通鉴》卷一八,第610页。
经营西南夷第二阶段,是张骞出使归来之后。《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29)《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3604页。此处所记元狩元年博望侯归来,《通鉴考异》已经辨其非是,见“按《年表》,骞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归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骞通身毒国”,《资治通鉴》卷一八,第611页。
这也是由一件商品引发的道路探索活动,因为搜索范围太大,可惜最后没有成功。此事史书记载时间不详,《通鉴》叙述于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邛竹杖,明确是蜀地产物,是从身毒(印度)转手贸易而来,那么蜀地与身毒有道路相通的推论自然是成立的。从方位上推导,继续向滇(云南)方向探索也是正确的。但跟唐蒙的顺利相比,这次探索没有成功。对于汉朝的这个探索,西南夷方面支持不力,这也是半途而废的部分原因,而最终西南夷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南越亡国之后,即元鼎六年(前111)。
西南夷不配合西汉的道路探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也不了解汉朝。《史记·西南夷列传》留下一个著名故事,充分反映问题的本质: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30)《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3606页。
在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不能简单地看作无知。《史记》已经进行了自然而然的解释,因为道路不通,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十年之后,西南夷之地都成为汉朝的郡县。夜郎,位于贵州六盘水市东南、安顺市西南。滇即昆明湖,今云南大理。西南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内部,对比张骞在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应该理解那个时代的基本情形:缺乏交通,缺乏了解。面对中国的崛起和积极探索,周遭的反映是茫然无知。张骞的遭遇很正常,也正因为如此,才彰显出张骞出使的重要性。
四 结论
如今我们研究丝绸之路,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并重。考古资料能够补充很多新的信息,如甘肃出土的汉简等。(31)参见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26~35页。考古资料证实,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是广泛存在的。(32)林梅村:《张骞通西域以前的丝绸之路》,《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第166~176页。王炳华先生指出:“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自陕西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已经实际存在。只不过主要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在官府文档中少见反映。”(33)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收获》,《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收入作者《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因为联系的主体不是政府,所以没有纳入国家的记录体系,不能广为人知。既然有联系,就应该有交通道路,有学者指出:“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雄辩地证明,远在凿空前的若干世纪,西域就同内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4)参见朱振杰:《“凿空”前西域与内地的联系》,《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71~79页。但就当时的基本情况而言,隔绝性毕竟是主要的,张骞出使之后,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才进入新的时代。
张骞出使之前,中原与西域的贸易联系广泛存在,但这丝毫不能降低张骞出使的意义。贸易关系以商品为主轴,丝绸之路上主要是转手贸易。一件具体商品只要有价值就会不停地进行转手交易,商品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不停地转手之后只能不断地消耗甚至消失。以来自中原丝绸的贸易而言,西方有关丝绸的信息长期处于混沌状态。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样长期模糊不清,这与转手贸易的方式关系重大。当然,进步是存在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罗马时代就比古希腊时代进步很多。(35)参见郭小红:《古罗马向东方的探索与丝绸之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增刊(世界历史研究),第74~79页。
更重要的是,商人与使者所注意的问题焦点不同。商人更关心的是商品和贸易问题,而使者却关心国家层面的问题。中原获知的西域各国信息,几乎都来自张骞的报告,从中不难看出张骞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安息为例,了解张骞的观察。其文曰: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3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11页。
先是国家的方位,然后是各国的空间关系,再次是物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情况,商业、货币和文字,都在张骞的视野之内。这些,通常都不是商贾之人所注意的。不仅是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张骞还有超越国家的抽象总结,最著名的就是“土著”与“行国”国家类型说。日知先生高度评价张骞的这个类型说,认为是两千年前提出的重要政治学概念。(37)日知:《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第25~32页。
根据《大宛列传》的记载,土著之国有大宛、安息、条枝、大夏,行国有乌孙、大月氏、康居、奄蔡。这个观察和结论很重要,改变了中国对西域的基本认识。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前178),匈奴单于来信相吿,匈奴打败月氏,控制西域,其文为: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38)《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3479页。
这是西汉获得西域信息很重要的一封信,其中也不乏误导,即西域各国都是“引弓之民”。文化类型异同,自然影响国家政策。按照过去的印象,西域都是引弓之国,西汉政府自然兴趣索然。现在张骞报告,西域不仅有引弓之国即“行国”,也有冠带之邦即“土著”或城郭之国。张骞于是建议“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39)《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18页。。这激发起汉武帝的帝王雄心是一个方面,当时中国对城郭之国的文化亲近感才是西汉经营西域的政策得以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深层原因。
张骞出使西域,战略目标是匈奴,即使是匈奴人,也对丝绸之路多有贡献。(40)参见王子今:《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0~16页。然而,这些事实都无损于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意义,因为张骞之前毕竟以封闭阻塞为主,所以张骞出使才被称作“凿空”。张骞出使西域,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与西域(西方)世界正式接触、相互往来的开端。欧亚大陆作为当时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正式互通消息,开启了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门。彼此隔绝的时代结束,世界一体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