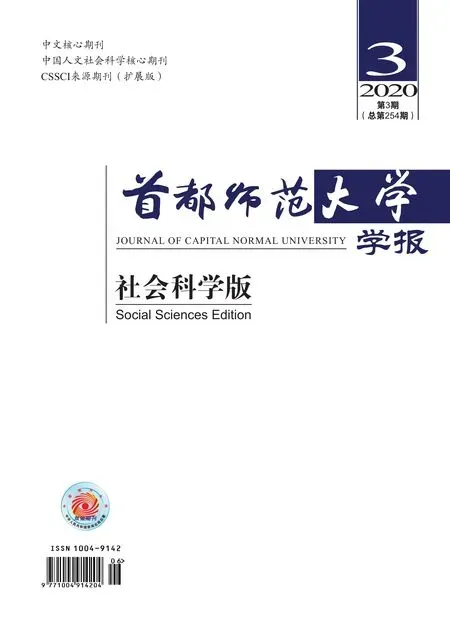全球史研究中的“他者叙事”
刘文明
全球史不同于以往民族国家史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关注那些超越国家界限并具有大范围意义的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往往也表现出跨文化性,会涉及多种文化和力量之间的互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要根据研究对象设定一个跨国家、跨文化的广阔空间,然后从宏观视角来考察发生在这个社会空间中的具体历史现象,即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笔,从网络和互动视角来审视具有区域性甚至全球性意义的个案。这种研究路径,正是当下越来越多的全球史学者倡导的微观全球史研究。在这种研究中,跨文化互动和全球性公共空间是两个重要概念。在跨文化互动中,相互认知是互动的重要基础,而由相互认知形成的“他者叙事”,自然成了全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与此同时,区域性或全球性公共空间也是全球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研究者将研究个案置于一个广阔的公共空间来思考,考察这个空间中与其研究对象发生关联的各种因素。当然,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就某时某地发生的事件而言,有直接的当事者,有间接的利益相关者,还有置身事外的看客。在历史研究中,通过当事者的叙事来重构和再现过去,一直是传统民族国家“信史”书写的重要基础。然而,当我们将某个历史事件置于一个广阔的公共空间来思考时,对方和局外人的叙事,亦即“他者叙事”恰好为研究者提供了考察问题的多维向度,并且构成了研究者理解事件发生的跨国公共空间、探究各种因素的关联性、建构事件区域性意义的重要基础,这也正是全球史不同于民族国家史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因此,如何利用跨文化互动和跨国公共空间中的“他者叙事”,是微观全球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本文便试图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跨文化互动中的“他者叙事”
20世纪下半叶,文化研究中的“他者”概念逐渐从人类学运用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也伴随着文化转向而开始使用这一概念,至今它已成为文化史和全球史研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当然,不同学者在使用“他者”来描述某个社会文化群体时,其含义可能因情境而不同,但一般来说是指基于文化差异而区别于本社群成员的外人,包括与“我们”相对的“你们”和在“我们”之外的“他们”。这也就意味着它包含了两个范畴:作为对立面的“他者”和作为旁观者的“他者”。由此,“他者叙事”也因这两种情况而存在差异,即对立叙事和旁观叙事。但由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是文化的,因此任何一种他者叙事都是跨文化叙事。
“他者”作为“自我”的对立面,是一个群体(“我们”)带着文化偏见,强调并建构其与另一个(或一些)群体(“你们/他们”)之间的差异(包括事实的和想象的差异)而形成的一系列话语实践的结果。①Rob Kitchin,Nigel Thrift (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vol.8,Oxford:Elsevier Ltd.,2009,p.43.因此“他者”是基于真实的文化差异而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其重要功能便是以“他者”来强化对“自我”的认同。这种“他者”观念及其相关叙事自古有之。从西方文明来看,古典时代的希腊就形成了“他者”意识。当时希腊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众多大小不一的城邦构成,但希腊人却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意识,他们自称为“希腊人”(Hellenes),而将外族称为“蛮族”(barbaros)。这种“他者”观的形成,是由于产生了一种觉得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都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并由此赋予了“蛮族”一种文化的含义。虽然此时“蛮族”还没有现代词汇贬称“野蛮人”那样的意思,但它的使用,已初步具备了近现代欧洲人用来指称非欧洲人(“他者”)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评判。基托说:“要是我们问一个希腊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不同于蛮族,……他可能会说,而且事实上的确也这样说了:‘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②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这种蛮族受到“奴役”而希腊人享有“自由”的观念,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就描写了大量希腊人为捍卫“自由”而抵抗波斯人的故事。例如,当一个波斯人规劝两位斯巴达人臣服波斯国王时,他们回答说:“对于作一名奴隶,那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但是你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③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16页。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并非现代语义的“自由”,但无论这种“自由”是什么,在希腊人的价值判断中无疑是东方“蛮族”没有体验过的好东西,表现出一种拥有“自由”的文化优越感。事实上,“自我”和“他者”是一对相互建构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范畴,在此,希腊人作为波斯人的对立面,也就是波斯人的“他者”,希罗多德关于“波斯人没有自由”的叙事,对于波斯人来说就是一种对立叙事,这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一种西方人关于东方社会的元叙事。
在中世纪,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欧洲人面对伊斯兰世界的他者对立叙事。例如,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为发动十字军而作的演讲就是一种对立叙事,它在促成拉丁欧洲的“基督教世界”观念转化为现实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乌尔班二世说道:“甚至世界属于我们的这小小一部分,也受到了突厥人和萨拉森人的压制。因此,300年来他们征服了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而且这些懦弱的人还热切希望占有其余的领土;他们没有勇气短兵相接,而是喜欢用飞箭的方式作战。突厥人从来不敢近身战斗,但是,他们从驻地出发,远处拉弓,相信凭借风力造成杀伤;当他们给箭头涂毒,是毒液而不是勇敢造成了攻击带来的伤亡。因此,无论结果如何,我将之归因于运气而非勇气,因为他们靠飞箭和毒药来作战。显然,那个地区的每个种族,由于受到炎热太阳的烤灼,擅长反省而气血不足;因此他们避免短兵相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气血太少。相反,那些生活在极地严寒中的人,远离太阳的炎热,的确缺乏谨慎,但他们气血旺盛,作战时极为敏捷。你们是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气候较为温和地区的民族,既气血旺盛而不惧伤亡,又不缺乏谨慎。同样,你们在军营中能够行为端正,在战斗中能够考虑周全。这样,你们带着杀敌技能和勇气去从事一场值得纪念的远征。”①J.A.Giles (ed.),William of Malmesbury’s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London,1847,pp.360-361.乌尔班二世的演讲,一方面对于唤醒西欧基督徒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集体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在演讲中所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上帝的敌人”形象,凭借其演讲的影响力而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加强了西欧基督教徒的“基督教世界”观念和身份认同。
当“他者”作为旁观者出现时,“他者叙事”只是一种观察记录,虽然也或多或少表现出记录者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但不会像对立叙事那样敌视对方并将其污名化。这种旁观叙事,在西方历史文献中也俯拾皆是。例如,在近代西方扩张的过程中,西方人作为殖民地世界的“他者”,传教士、航海家、殖民者、旅行者等都留下了大量关于东方社会和殖民地人民的旁观叙事。西班牙天主教神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us de Vitoria)在其《论印第安人》(1532年)中描述了这样一幅印第安人社会图景:“他们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官,甚至不能掌控他们的家庭事务;他们没有任何文学或艺术,既没有文科,也没有工艺;他们没有精细农业和工匠,缺乏人类生活的许多其他便利设施和必需品。因此为了他们的利益,应该坚持由西班牙君主来承担他们国家的管理,为他们的城镇提供行政长官和管理者,甚至应该派给他们新的领主。”②Franciscus de Vitoria,De Indis et de Ivre Belli Relectiones,Ernest Nys(ed.),John Pawley Bate(trans.),http://www.constitution.org/victoria/victoria_4.html,2012年9月9日。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目睹了康熙帝前往天坛祭天的盛况,对康熙帝作了仔细描述。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作了这样的转述:“中国的王者从来没有在他接见外国使节时表现得那么神圣,那么至高无上。这支人数可观的军队,此时则全副武装;这群难以数计的官员,身着礼服,依等级爵位分开,依次就位,井然有序,肃穆无声,神态庄重,表现得如同在他们的神庙中似的。各部大臣,各主权国君王、贝勒、额驸、王位继承人在皇帝的面前都无比谦恭,而当他们高居于百姓之上时则非如此。皇帝本人,高踞宝座之上,面对跪伏脚下的这群崇拜者;这是惟有中国人才有的至高无上的、伟大的气魄,而基督的谦卑甚至不允许欧洲最辉煌的朝廷的国王追求它。”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郭强、龙云、李伟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当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于1770年到达澳大利亚时,他眼中是这样一群原住民:“他们不仅根本不懂我们欧洲人所追求的那种物质丰裕,就连我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之所以快乐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些。他们生活在一种静止的状态中,这种相差悬殊的境况对他们没有影响。土地和海洋自觉自愿地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的一切。”④詹姆斯·库克:《库克船长日记——“努力”号于1768—1771年的航行》,比格尔霍尔编,刘秉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20页。
从维多利亚、安文思、库克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作为异文化的“他者”,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观察者,都是从自身文化出发来思考和描写他们的叙述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一种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审视和评判。因此,这种观察叙事虽然比对立叙事具有较为客观的一面,但也毕竟是一种跨文化的理解,主观臆断和想象自然不可避免。但是,无论对立叙事还是观察叙事,无论直接在场还是间接转述,这些叙事作为他者视角的史料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往往可以弥补当事者所没有的观察事物的维度。
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受制于交通手段和传播媒介的不发达,即时性和共时性的叙事只能局限于能够实现直接互动的小范围。因为,无论他者的对立叙事还是观察叙事,制作成文本并流传开来需要一段时间,有的长达数十年,因此被叙述的对象往往要事后一段时间才能知晓关于其自身的“他者叙事”,有的甚至始终不知道。例如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叙事,一些文献在一两百年之后才为中国人所知晓和阅读。因此,全球史学者所考察的19世纪之前的“他者叙事”,从相互认知和建构的角度来说,因涉及空间范围较广而往往缺乏即时性和共时性的效果,成了一种滞后的话语,叙述者的言说相对于被叙述者来说也就成了一种不在场的话语,因而这种“他者叙事”是一种无声叙事。然而,这种无声叙事为研究者观察和理解叙述对象提供了他者视角,同时也倒映出了叙述者的思想世界,并且有助于建构大范围的历史关联。
“他者叙事”相对于被叙述者而言的历时性和不在场性,在19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19世纪下半叶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以及报刊媒体的发展,更是为全球性公共空间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使“他者叙事”作为一种共时性话语在大范围内流动成为可能,“他者叙事”在此基础上也日益演变成了一种在场的有声叙事。
二、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他者叙事”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探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提出了公共领域形成的三个要素,即公众、公众舆论和公共场所(媒介)。公共领域就是由公众自由参与而理性地讨论事务的公共空间。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沙龙和咖啡馆里的讨论,可以看作是最早形成的公共领域,而之后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和杂志,进一步促进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①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只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他在2001年仍然这样认为:“到目前为止,促使各种公共舆论广泛产生的必要基础(infrastructure)只存在于各民族国家范围内。”②Jürgen Habermas,“Why Europe Needs A Constitution,”New Left Review 11,September/October,2001,p.18.这种看法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有关。他把公共领域只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强调在公众参与和民主协商面前存在一个公共权力部门,而这一条件在跨国情境下很难得到满足。但是,如果我们将公共领域看作一种公共舆论的话语空间,只是各种参与者围绕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展开讨论而形成的舆论场域,那么,跨国性公共领域从19世纪就开始出现了。为了区别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笔者更倾向于将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这种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称为“公共空间”,即跨国公共空间或全球性公共空间。
“他者叙事”作为一种共时性有声叙事的出现,以跨国的全球性公共空间的形成为条件,而这一条件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化环境中初步具备。
首先,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交通技术革新(轮船和火车的使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形成,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这正如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所指出:“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是60年,这段时间是空前的网络形成时期。……若把覆盖整个世界的网络的形成称作‘全球化’的话,那么1860—1914年则是全球化被显著推进的时期。”③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1页。在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一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地方性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或因其由域外因素所引发,或因其具有世界性的后果和影响。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完全有可能围绕一个事件而形成一种国际舆论的全球性公共空间。
其次,19世纪中叶以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全球性公共空间中话语的即时性和共时性成为可能。1844年在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电报线路,1851年在英国多佛和法国加莱之间铺设了第一条跨海国际电报线路。从此,英、法、德、美等国纷纷成立电报公司,电报业迅速发展起来。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成功铺设,意味着大西洋两岸实现了信息的迅速传播。到19世纪80年代,由电缆联结而成的世界网络基本成型,信息传播进入了电报时代。此时的欧洲和北美,甚至每个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电报局。当时的中国也成了这个网络中的一部分。1880至1894年间,在李鸿章的推动下,清政府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了电报局,基本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电报网络,并且还铺设了通往朝鲜、越南和俄国的电报线路。正是在这种信息即时传递的基础上,有关甲午战争的消息能迅速传遍世界,并形成一个全球性舆论场域,英美报刊的“他者叙事”也成为一种有声叙事。
再次,19世纪下半叶报刊杂志和通讯社的发展,为全球性公共空间的形成提供了其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公众舆论和公共场所(媒介)。报纸在欧洲出现于17世纪,并且于1702年在伦敦出现了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报》,此后报纸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媒介在欧美发展起来。到19世纪下半叶,以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为代表的“新式新闻事业”发展起来。一些具有新理念的报纸突出新闻传播的职能,保持社论的独立性,迎合读者的阅读旨趣并将内容通俗化,以大字标题和插图来改革排版等,结果使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在美国,英文日报从1880年的850家增加到1900年的1967家,报纸订户从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0%上升到26%。①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第九版),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与此同时,欧美人士在非英语国家开办的英文报纸也发展起来。例如,19世纪40年代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外文报刊多达120种以上,主要有在香港的《孖剌报》、《德臣报》和《南华早报》,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海航运日报》和《大美晚报》,在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等。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非西方国家开办的英文报刊与欧美报刊构成了一个国际舆论圈。另一方面,国际通讯社在20世纪下半叶也依托电报技术而发展起来。较早建立并随后具有国际影响的通讯社,主要有法国的哈瓦斯社(后来的法新社)(1835年)、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1849年)、英国的路透社(1851年)。在美国,1848年几家报社联合成立了港口新闻联合社,后来几经变化于1892年成立了联合通讯社(美联社)。这些通讯社到19世纪末都发展成为国际通讯社,向各国报刊提供即时新闻。
因此,到19世纪下半叶,由于全球性公共空间的出现,全球史学者所考察的公共空间中的“他者叙事”,无论对立叙事还是观察叙事,都已具有了共时性话语的特征,是一种被叙述者能够即时感知到的有声叙事。
全球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运用跨国公共空间中的“他者叙事”?笔者在此以中日甲午战争的英美报刊舆论为例做一简要阐述。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第一场普遍使用电报用于传递信息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中已有使用但不普遍),因为在战争期间,电报除了用于军事之外,在新闻媒体中也开始被广泛运用。这使得甲午战争成了一场具有即时国际舆论的战争。那么,在这个国际舆论构成的全球性公共空间中,“他者叙事”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这场战争有何史学价值?
首先,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他者叙事”由于其在场性,也就使得其话语具有了实践性,从而有可能对叙事对象产生影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报刊舆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在甲午战争中,当托马斯·科文、詹姆斯·克里尔曼等西方记者在美英报刊上揭露旅顺大屠杀真相时,日本政府急忙进行辩护,外务次官林董在给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Trench)的备忘录中声称:“很可能超过了必要的流血,但由外国记者特别是《世界报》记者发往国外的报道希望产生轰动效应,不仅大肆渲染,而且严重夸大。”③“Substance of a Memorandum communicated to Her Majesty’s Minister by Mr.Hayashi,December 19,1894,”i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34.同时日本政府还将辩解写成书面材料转给《泰晤士报》和《世界报》刊出,声称日军所杀的是士兵而非平民,因为清兵在战斗中改装成了平民继续抵抗;而且,日本士兵见到被杀害的日军俘虏后极为愤慨,忍无可忍才对清军进行了报复。④“The War In The East,”The Times (London),December 15,1894,p.5; “Japan Confesses,”The World(New York),December 17,1894,p.1.由于克里尔曼在纽约《世界报》上的报道被英美许多报刊转载,旅顺大屠杀一下子成了世界舆论的焦点。日本政府在这种局面下进一步狡辩,再次发表了一份老调重弹的声明,仍然强调被杀者是换装的清军士兵、日军在目睹其战俘被害后群情激愤等等。但为了达到更广泛的宣传效果,译成了英文、法文和德文三个版本。①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9页。这一史实表明,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他者叙事已然是一种共时性的有声叙事,引起了被叙述者的即时回应,即日本政府的反应。
其次,甲午战争虽发生于中日之间,但此时的东亚已非半个世纪前清朝主导的东亚,而是一个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和彼此角逐的东亚,通过对英美报刊舆论的考察,既可以使我们从当时的国际舆论来观察这场战争,也可以使我们从“他者叙事”来了解“他者”。例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美国纽约《晚邮报》的一篇文章把中日之间的战争看作是对现代军队和“文明国家”制造的装备的检验:“还能找到比半文明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更好的试验品吗?实际上,在竞争对手都只是半文明国家的情况下,对于旁观者来说还有一种额外的利益。他们一直在玩文明生活的游戏,到现在有好些年了,但是西方国家对此一直都是一种半娱乐的心态,觉得这完全是一场有趣的闹剧。虚饰的文明怎能经得起战争的折腾?”②“Outside Interest in the War,”The Evening Post,New York.from The Literary Digest,Vol.IX,No.16,New York,August 18,1894,pp.451-452.这种看法反映了当时一部分西方人对清朝和日本学习西方采取怀疑和看热闹的态度,把它当作一场“闹剧”,认为其表面的“文明”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又如,《纽约先驱报》鼓吹支持日本打败中国,然后西方乘机改变中国:“日本将有权对快要接受条件投降的大清帝国进行改革或重建。她要把西方文明标准通过朝鲜推进到中国,就欧洲列强而言,在不妨害其利益的情况下,世界上这些伟大文明应该以其建议和赞同,允许日本激励其愚昧的邻居进入现代生活领域。日本的文明化使命应该进行到底。然后,为了中国未来问题的最终解决,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就可以在东京举行一次会议。”③“Europe’s Quadruple Alliance in View of China’s Overthrow,”New York Herald,October 11,1894,p.8.这反映了西方国家打着“文明”的旗号,企图利用日本侵略来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
再次,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些英美记者的新闻报道,可以弥补当事者记述的不足,为研究这场战争提供珍贵史料。例如,克里尔曼在亲身经历旅顺大屠杀后给纽约《世界报》写的新闻报道,成为记载日军暴行的珍贵史料。关于旅顺屠杀事件,中文史料极少,日文史料也只有间接反映,只有克里尔曼的记录最为详细。其中,1894年12月20日克里尔曼发表于《世界报》的长篇通讯《旅顺大屠杀》,占据了当天《世界报》头版和第二版整整两个版面。当时编辑还将一些关键句当作小标题:“日军屠杀了至少2000名无助民众”,“杀戮三天”,“大山大将及其军官没有试图阻止暴行”,“城市各处遭到劫掠”,“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残缺不全的尸体堵塞了街道而士兵却大笑”,“店主们被枪杀和砍杀”。④James Creelman,“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The World(New York),December 20,1894,p.1.这样,这篇报道以一个个具体的事件详细记载了日军屠杀无辜民众的过程,并且在英语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让世界知道了真相,至今成为控诉日军暴行的铁证。1895年中国人编写的《中倭战守始末记》中“倭寇残杀记”部分,主要译自克里尔曼这篇报道。
第四,甲午战争中英美报刊的“他者叙事”,为我们理解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些军事之外的新维度,或者从一个新的维度来理解战争中相关的人和事。例如,英国《泰晤士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对“高升号”事件的讨论,主要围绕国际法这一主题展开。日军击沉“高升号”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西方舆论对战端的看法。在这场讨论中,1894年8月3日《泰晤士报》刊登约翰·韦斯特累克(John Westlake)的《高升号的沉没》一文,因其剑桥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身份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日舰击沉高升号的行为是合法的,英国政府不应对这一事件进行干预。⑤John Westlake,“The Sinking Of the Kowshing,”The Times (London),Aug.03,1894,p.10.随后在8月6日,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霍兰德(Thomas Holland)也在《泰晤士报》刊文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些看法应该对英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又如,英美战地记者对清军的报道,有助于我们从他者视角来理解清军的行为及其观念。随日军采访的克里尔曼曾这样描述他在平壤战役中所见的清军阵地:“宽阔的城墙上遍插红色、黄色的军旗,有数百面之多。6个清军将领,每个人都高高挂起自己的大旗,旗面的尺寸说明了其主人的军阶。清军主帅叶将军的大旗据测长达30英尺,旗面上绣着一个汉字,代表他的名字。……透过望远镜,看到一连串的堡垒上有大量军旗迎风招展,形成一条绵延数英里的军旗线。清军将领们大摇大摆地在城墙上走来走去,各自的军旗高高举起在前开道,同时以击鼓声和号角声进行挑衅。”①James Creelman,On the Great Highway:The Wanderings and Adventures of A Special Correspondent,Boston:Lothrop Publishing Company,1901,pp.35-36.“天空阴沉,下起了雨。令日军惊讶的是清军竟然在其堡垒墙壁上插上了巨大的油纸伞,以使自己在战斗时免遭淋湿。四面八方都能看到清军的油纸大伞,它们就像这些防御工事的外壳,在雨水中幽幽发光。”②James Creelman,On the Great Highway:The Wanderings and Adventures of A Special Correspondent,pp.45-46.这种观察,从他者视角解释了清军在平壤战役中失败的原因。
三、结语
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历史学者与史料不断对话的过程,而文本一直是历史学者赖以建构历史的重要史料。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当事者(我)的记录、对方(你)和旁观者(他)的记录。当事者的记录是一种主位视角的叙事,而对方和旁观者的记录是一种客位视角的叙事。民族国家史注重当事者记录,认为这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历史学者可以用移情的方法加以理解并用于历史个案的细致描述。然而,当全球史学者考察大范围的历史现象,要从更广阔的互动情境来思考问题时,发现仅用当事者记录来做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借助于对方和旁观者的“他者叙事”来理解和考察历史,以便建立大范围的历史关联。因此,“他者叙事”便成为全球史学者不可或缺的史料。
全球史学者考察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现象,具有跨文化互动或全球性意义的历史事件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因此全球史研究中所用的“他者叙事”是一种跨文化叙事。然而,由于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全球化程度不同,“他者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在19世纪以前,人类各群体之间的互动还不密切,信息传播媒介也不发达,来自异域文化的“他者叙事”对当事者来说缺乏即时性和共时性效果,是一种相对滞后的他者话语,因此是一种不在场的无声叙事,但它为全球史研究者提供了理解大范围历史关联所需要的视角和史料。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交通和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报刊杂志等媒体的发展,世界成了一个互动密切的整体,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空间由此形成。在这种空间中,当事者和观察者具有同时在场性,“他者叙事”也因其即时性和共时性而成为一种有声叙事,并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将中日甲午战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公共舆论空间,借助于“他者叙事”来审视这场战争,可以为我们理解这场战争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新维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他者”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处于强势地位时,“他者叙事”就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并进而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支配性影响。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全球性公共空间中,西方列强相对于广大非西方世界而言正是扮演了这种强势他者的角色,它们对东方社会的想象和建构,是一种西方霸权下的帝国主义“他者叙事”。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出:“在东方的知识这一总标题下,在18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庇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的基础上。”③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页。因此,当西方作为他者,在近现代全球史研究中运用这种“他者叙事”时,全球史学者应该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