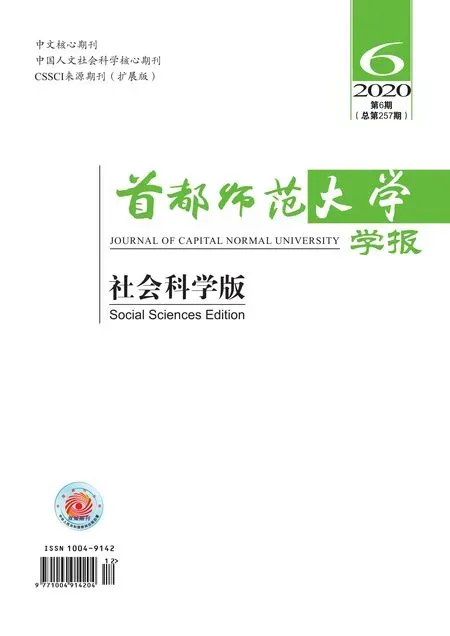象征性教育政策执行的案例研究
——基于学校文化建设政策的探讨
徐志勇 赵志红
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通过构建优质文化引领学校内涵发展,已经成为学校管理的重要方式。学校开展文化建设的动因与实践行动,在本质上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对国家提出的推动学校文化发展系列政策的落实,是一种政策执行行为。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由于政策本身不涉及资源的直接分配,亦不是国家强制性执行,不同学校的行动选择千差万别,效果更是参差不齐。那么,一所学校的校长如何能将这样一项非强制性的政策深入落实到位,是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的问题。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方法
政策执行是将政策规定的内容转化为现实的过程。①Deleon,P.,“What Ever Happened to Policy Implementation?An Alternative Approach,”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12,no.4,2002,pp.467-492.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伟大社会”改革的措施,当时制定的很多政策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政策实施结果令人非常失望。由于政策执行过程复杂,政策本身的可行性及对资源的依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效果,自此,政策研究者开始反思政策执行如何获得成功。②Pressman,J.L.,Implementation:How Great Expectations in Washington Are Dashed in Oakland,Berkeley C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执行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是第一代政策执行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分析政策执行失败的原因,认为政策执行失败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本身存在问题,且执行机构的不服从。80年代是第二代政策执行研究,重点在于提出政策执行的模型,包括政策执行的促进和阻碍因素等。③Fowler,F.,Policy Studie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An Introduction,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Inc.,2004,pp.271-277.90年代初开始进入第三代政策执行研究,强调用科学方法、定量分析等来构建理论、验证假设。④丁煌、定明捷:《国外政策执行理论前沿评述》,《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1期。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领域逐渐出现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意义建构视角。意义建构视角引领下的政策执行研究,关注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认知链”(cognitive chains),把政策与执行间的关系转化为执行者的“思考”(thought),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就是影响执行者“思考”的因素。⑤李玲、陈宣霖:《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比较》,《外国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随着意义建构视角研究的深入,象征性政策的执行问题开始为研究者所关注。象征性政策是相对于实质性政策而言的分类。实质性政策提供的是具体的、有形的资源或实质的权力,涉及公共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而象征性政策则不具体提供资源条件、利益分配或要求强制性实施,它更多的是通过价值引导、政策宣称或确立愿景等来描述政策方向,或对实践进行理念引领。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M.G.Roskin)认为,象征性公共政策是指“那些创造情感忠诚的政府行为(爱国主义、忠诚、顺从或民族自豪感)或把社会地位赋予社会上的关键人物”的政策。⑥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林震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在象征性政策的功能与效果方面,安德森(J.E.Anderson)指出“符号性的政策分配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很少对人们产生实际的效果,它们并不交付表面上许诺的东西”。⑦詹姆斯·安德森:《公共政策》,李玲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象征性教育政策的目标兼有解决问题和倡导理想两个方面,其制定和实施过程充分体现了决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精英、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机构共同发挥作用。⑧魏峰:《我国“教师节”的设立——在象征性政策与实质性政策之间》,《教师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种象征性政策。学校文化是在特定内外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代表学校师生员工特征的价值观、信仰体系和准则规范,以及师生员工教与学、管理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总和。国家建设学校文化的政策体现在一系列政策文本中,既有教育部出台的学校文化专门性政策,如2006年发布的《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也有作为教育政策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对“营造健康向上的学校文化”进行了专章规定。学校文化建设系列政策出台的目的在于倡导学校培育良性文化来潜移默化地规范师生行为,形成学校文化自觉,以观念引领和柔性管理措施来引领学校发展。学校文化政策与一般的实质性政策不同,其更关注对学校进行办学方向引导及教育价值观澄清,在政策的目标、执行、效果、评价等方面不涉及实质性的资源分配或明确的权力清单。作为一种象征性政策,学校文化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学校文化的政策目标多是倡导性的,对于政策目标不进行具体规定;第二,在政策实施方面,不注重对教育资源及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更多的是靠学校管理者的自主实践及探索;第三,在政策效果方面,由于目标具体性、资源条件及强制性行政措施等方面的限制,政策总体效果容易表面化、流于形式;①褚宏启:《警惕教育中的“伪创新”与“真折腾”》,《中小学管理》2017年第3期。第四,在政策评价方面,一般不涉及强制性的惩罚措施,难以根据政策执行效果进行有约束力的奖惩。②黄忠敬:《教育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
本研究采用格尔茨提出的深描方法。格尔茨指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于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究意义的解释科学。”③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在格尔茨看来,在文化研究中,深描是“记载特殊的社会行为在这些行为的发出者眼中的意义,与尽可能清楚地表述如此获得的知识关于(在其中发现了它的)社会揭示了什么,以及关于社会生活本身揭示了什么之间的差异”④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本研究尝试从北京的一所学校的案例出发,采用人类学“深描”的方法,深入剖析学校政策执行的背景、行动选择与背后的行为机理,以期为今后象征性政策执行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角度。
在过去三年中,研究者与案例学校逐年签订了文化合作研究协议,在协议的约束下开展专家引领下的学校文化改进研究。在每一年度之初,都会制定该年度合作研究的具体实施方案,平均每月至少开展两次进校研究,并安排专人做好文字、音频、图片及视频记录,按研究要求有目的地收集学校内部与课题相关的教育教学及管理资料,并按照人类学田野观察要求整理好记录文本,定期做出学校文化合作研究简报。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上述民族志记录文本,并根据研究要求进行了选择性呈现。
二、政策执行背景:案例学校构建学校文化所面临的情境
每一项政策的执行都是在真实的情境中展开,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政策能否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是由多种复杂的因素共同决定的。
(一)政策执行的区域性推动:学校文化示范校评选
为了落实国家对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教育部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其后在教育部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中,都对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进行了专章规定,如在2013年发布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2017年发布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中,都把学校文化建设作为对学校及校长的重要考评维度。北京市教委也制定了《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建设与评估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公布了学校文化评估指标体系。该方案提出:“形成中小学办学特色。开展育人模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改革试验,为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深化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变革,进一步激发学校自主发展活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评选500所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示范校。”为落实这项政策,2013—2016年,北京市教委先后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学校文化研究中心、北京教育学院等专业教育研究机构进行学校文化示范校的评选工作,并于2016年底完成了全市500所学校的评选。
三年的文化示范校评选工作,其可视化的显性成果是为北京市500所中小学挂牌“学校文化示范校”,这标志着从政府层面对这些学校的文化建设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表彰。此外,此次评选工作对学校的文化创建与变革产生了以下的影响:第一,评选过程中形成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44个三级指标在内的《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文化示范校建设与评估指标体系(试行)》,⑤张东娇、张凤华:《学校文化示范校建设指标体系学理解读与评估应用》,《教育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并据此对全市申报文化示范校的学校进行评估。第二,通过集中的理论宣讲、学校自我评估与总结中的尝试性应用、项目组实地调研中的实践培训等方式,学校成员逐步形成对学校文化示范校评价标准的理解,并尝试性地据此评估和构建学校文化。第三,学校成员在不断深化对标准的理解和落实中,形成关于学校文化意义、概念、构成元素、实践方式等的自我理解与认知,更新了学校成员尤其是校长对于学校文化的认知图式,引领其学校文化的实践行动。
(二)政策执行的组织背景:学校有“文化”但不够明确且难以落地
在北京市500所学校文化示范校评选中,本文所涉及的案例学校作为其所在区的重点小学,于2013年接受了第一批验收并取得了相应的认定。案例学校形成了“微笑教育”的办学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悦然·致尚”的办学目标、“培养健康、快乐、致尚的‘悦’少年”的育人目标、“让微笑伴我成长”的校训,以此构成学校办学理念体系。实践方面,提出建设“心悦诚服”的制度文化、“和悦入心”的学生文化、“和颜悦色”的教师文化、“心悦神怡”的课程文化和“赏心悦目”的环境文化等。
本案例中关注的F校长,就是在案例校完成学校文化示范校评估之后接任校长并着手开展文化建设与变革的。F校长之所以想要进一步变革学校的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学校目前的办学理念体系不够明确,表达不精准且缺乏阐释;第二,实践体系中各个元素的提法不够贴切,操作性不强。这在F校长某次的访谈中有所体现:
办学理念文字的表述我们还是达成了一致共识,(我)比较欣赏这个,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追求。那么围绕这个核心理念,现在我们梳理出来的育人目标、办学目标、校训,下一步需要再梳理。我们的校歌、校花、校树,包括每一种理念的确定,包括内涵的表述,这些可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的。现在基本上缺什么呢?缺对每个表述的内涵界定,这个基本都没有。
在理念体系之下,我们从几个重点的,比如说管理,教师、学生、环境就是学校管理的几个不同的维度提出来一个大致的(表述)。(目前文本中)这个是原来提的,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为了凑原来的“悦”,但我觉得真正是否合适,怎么解读,特别精准的、贴切的都没有。所以在实践层面我们的方向实际上是不明确的。
对案例学校当时的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学校在“学校文化”这一政策的执行中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积极回应”政策,按照要求和评价标准对学校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建构”;第二,“微笑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文化品牌,只是一个“象征”,未能得到学校教师与学生的理解、认同与行为践行。基于此,校长认识到,若要政策真正落地发挥实效,必须深入开展文化建设,对当时的学校文化做出系统变革。
(三)政策执行的校长认知基础:校长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且能引领实践
从意义建构视角来看,教育政策执行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充满了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意义建构。基于以上的理论视角对F校长的政策执行过程进行观照,我们发现,校长对“学校文化”这项政策本身的意义理解与建构,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效果。F校长在一次集体研讨时曾谈道:
我们的需求就是,要建立一个核心理念引领下的、能够适合学校的、体现核心精神和价值观的整个精神文化体系。这也是我作为校长需要的,我对外得有一套说法,有话语系统。但话语系统不能是空中楼阁,这套话语系统要真正转化为我们的实践。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在F校长看来学校精神文化体系构成了校长的话语系统和理论体系,并且应转化为学校的实践。在“学校文化”这一概念刚刚进入教育实践领域时,很多校长将其定位在文本的表达或校长提出的口号,相对于这样的认识而言,F校长对于“学校文化”的理解显然更契合“文化”本源的意义。这也直接引领F校长坚定地对学校现有文化进行变革,促使学校文化政策发挥实效。
三、政策执行过程:引入专业力量,通过项目推动,系统变革学校文化
政策执行的过程,需要执行者精准定位政策目标,选择恰当的政策行动并有效地落实。本案例中,通过校长的表达,我们将其政策执行目标确定为:在学校“微笑教育”核心理念引领下,形成契合学校需求的办学理念体系,并将其转化为学校的实践,使之在全校师生的行为中得以彰显。据此,校长选择了自己的政策行动:引入专业力量,通过项目推动,系统变革学校文化。
(一)专业引领:引入专业力量,构建核心研究团队
如前文所述,学校文化政策在案例学校的落实,并非F校长的首创,此次的文化建设与变革,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提升和深化。原来的政策执行情况之所以不够理想,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比如学校成员对学校文化的理解不到位,他们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文本的呈现,在提炼概念与撰写文本时主要是学校领导在操作,教师的参与度很低。再如,学校相关人员承担学校多项工作,事务繁忙,很难抽出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思考与研究,导致学校文化建设水平多年在一种低水平上重复。
基于以上情况,校长认识到,若想在学校文化构建与研究方面真正有所深化与提升,使文化切实发挥引领学校内涵发展的作用,必须有专业力量的加入。因此,校长经过调研与考察引入某高校专家团队,对学校的文化建设做出专业指导,协助学校开展相关工作。在专家团队的选择中,学校考虑到诸多因素:第一,专家团队负责人多年参与U-S合作的学校文化创建项目,有丰富的经验且在全国各地多所学校达成很好的效果;第二,双方对学校文化本身以及学校文化建设的项目理念与实践研究达成了高度共识。以下是专家团队的项目理念表达:
1.基于学校真实场景
学校文化建设项目实施的总体策略是:为了学校,基于场景,系统思考,实现提升。研究者需要进入学校真实的工作场景,观察学校工作,倾听师生心声,全面收集学校文化建设相关资料,形成对学校文化发展状况的深入理解,系统思考与策划学校文化发展方向与策略,实现学校文化总体提升。
2.建立伙伴协作共同体
研究者与学校建立起协作共生的伙伴关系,明确学校是项目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学校全体成员必须发挥主动精神开展各项工作;大学研究者是学校文化发展的协作伙伴,为学校文化建设提供专业的指导。双方的职责是共同梳理、总结、提炼、培育、提升学校文化。要秉持“互爱、互敬、互助”的原则,在平静和谐的氛围中实现协作共生。
3.专业化开展项目研究
系统梳理学校发展历史,全面收集学校文化建设资料,深入实际观察学校各方面日常行为以及事关学校发展的关键事件处理,形成对学校文化发展现状的全面理解。运用适切的学校文化理论与分析工具,协助学校培育学校文化及特色,提升学校文化内涵。通过建设学校文化体系,为提高学校办学品质和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发挥学校在区域的引领作用。
4.提高学校内生性文化发展能力
在与学校一起进行文化分析评估的基础上,研究者指导与帮助学校形成系统、科学的文化发展方案,对在管理、德育、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生发展等方面的文化实施进行针对性指导,帮助学校领导干部与教师形成自觉观察文化、思考文化、培育文化和实施文化的思维方式,提升学校内生性的文化发展能力。
达成基本共识之后,为了避免以往文化建设中“工作过多、精力分散、难以集中精力开展研究工作”的困境再次出现,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文化研究小组,研究小组的人员构成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小组由校长牵头,校长需要全程参与。因为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关涉学校方方面面各项事务的系统性工作,校长必须要承担把握方向、调动人员等责任,同时要与项目组深度交流和碰撞,将校长的思想全面渗透到学校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中。
第二,研究能力较强的青年教师,他们学历高、研究能力强、具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和较强的行动力,在团队中承担较多的研究任务,参与学校办学理念体系的研讨并贡献智慧。
第三,中层领导、教研组长、骨干教师,他们专业能力强,在自己的学科或班主任管理等领域是实践专家,在学校有一定的话语权,在团队中承担着专业方向把舵、号召老师参与等职责。
研究团队形成后,学校即着手开展“学校文化理念与实践体系”项目研究,研究初步拟定持续三年,以形塑高水平学校文化体系为目标,分层推进、步步深入,逐步形成学校办学理念体系并探索在实践中的转化行动。
(二)理念提炼:提炼办学理念,形成共同愿景,凝聚全员合力
办学理念体系包括办学理念、核心价值观、育人目标、办学目标、校训、校歌等内容,这些共同构成了学校全体成员的共享价值,因此办学理念体系的构建本质上即“构建组织成员的共享价值”。
在实地调研和分析学校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深入探寻学校的文化基因,全面了解学校领导与教师对学校教育使命的深刻反思,同时系统梳理教育学与心理学相关理论,对“微笑教育”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系统阐释:“坚持教育的儿童立场,注重创设轻松快乐的学校氛围,通过趣味生成的教育教学过程,发展学生智能,培养良好品格,使学生具有优雅的举止、丰盈的内心与和悦的生活状态。”“微笑教育”体现为四个方面:快乐氛围(悦动)、趣味生成(悦成)、和悦生活(悦意)和笑对人生(悦心)。
基于“微笑教育”的核心价值观阐释,确定学校“古雅新韵、城纳众山”的校训与“培养优雅自信、乐学善思、大气包容的‘和悦少年’”的育人目标,并将学校办学目标确定为“建设有影响力的‘古城·微笑’文化名校”。最后,项目组专家用一首小诗来总括学校的文化理念体系:古雅新韵微妙现,城纳众山笑盈园,二仪和谐教诲谆,小微精进育英才。
“微笑教育”引领下的办学理念体系,既承袭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又契合学生的发展需求与学校未来的教育理想。通过实施微笑教育,建设微笑文化,把学校办成学生微笑成长的童趣乐园、智慧学园。就学校发展状态而言,学校是一所区域内领先发展的学校,目前在北京市已经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未来需要进一步将文化建设做深、做实,提高学校在全国更大范围的文化知名度,形成更有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古城微笑文化品牌。
学校办学理念体系的提炼,在学校全体成员中初步形成共同愿景,全校师生的行为选择遵循“微笑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大家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开始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学校的办学目标与育人目标,有利于全校形成合力。
(三)实践转化:科学化行动策略引领实践的系统变革
为将前期所提炼出的共享价值转化为实践,融入学校成员的一言一行,渗透到学校的一草一木,校长采取了科学化的行动策略,引领学校的系统变革。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分领域策划,重点突出,层层推进
学校文化理念体系落实到学校实践中,可分为管理文化、课程文化、教学文化、学生文化、教师文化和环境文化六大领域。这六大领域在实践中并非平行关系,学校领导依据本校具体情况与六大实践文化的性质,认为在实践文化研究中,应该将重点放在学生文化、教学文化、课程文化和教师文化四大领域,并遵循以上顺序。
之所以做出以上的行动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学生文化是对学生的行为做出规约,而学校的首要目标就是育人,结合育人目标提炼出学生文化,会使学校的育人方向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因此应将其放在首要位置去解决,这样教师在实践中才会更有主心骨。
第二,课堂是学校教育活动开展的主战场,学生生命底色在课堂中得以孕育。在育人方向得到清晰后,打造彰显学校特色的文化课堂是实践的第一步,因此,教学文化需要在学生文化研究完成后开展。
第三,当在课堂上明确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教与学的互动应该如何实践才能达成文化课堂后,需要将视野进一步拓展,从学校整体课程文化的构建出发,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一个科学、系统、内容丰富、可供选择的课程体系,引领教师与学生的行为,深化理念的落实。
第四,聚焦于学生发展方向,从课堂教学实践和课程的构建实施等不同的角度观察与构建教师的行为后,势必需要从理念层面引领教师文化,提出能概括和引领教师发展的核心理念,打造独具“微笑教育”特色的教师文化。
学生文化、教学文化、课程文化和教师文化四个领域的策划相互分离又互相影响,环环相扣并层层推进,形成了学校独有的实践文化建设策略。2.
集体宣讲提高认同,有的放矢高效参与在实践文化研究层层推进的过程中,教师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和中坚力量,专家团队的理论指导与校长的理念、想法,只有通过教师的行为转化,才能真正落实到学校的育人活动与学生的行为表现上。因此,在政策执行的环节,必须提高教师对文化体系的认知、认同并引导他们参与项目研究,自觉将理念转化到自己的日常教育教学行为中。
为了提高全体教师对学校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学校在项目研究的各个阶段都会采取文化核心小组定期研讨的方式与干部及骨干教师开展研讨活动,达成共识。同时采取“专家讲座”的方式将阶段性研究成果向全体教师集体宣讲,让全校所有老师都能了解学校文化建设的进度,并随之思考其与自身本职工作的关系。之所以采用“专家讲座”而非校长个人宣讲的方式,是因为专家本身具有“专业化”的象征身份,有更高的认可度。基于这样的宣讲行为,教师对学校文化产生了基本的认知、一定程度的认同,并开始思考如何将之在自身的行为中进行转化。
此外,“有的放矢”也是校长引导教师参与项目研究、践行学校文化的重要行动策略。在研究开展的整个过程中,难免有教师认为“这个研究跟我的教学关系不大”而不愿意参与研究,而且,这样的消极情绪可能在同组、同年级的“小范围”内传播,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参与研究。为避免这样的情况蔓延从而导致教师的参与率低,校长在每个研究阶段开始前的计划制定时,均会结合相应阶段的研究目标,有目的地选择更适合且研究效率更高的人员参与研究。例如,理念提炼阶段更重视研究能力较强的青年教师参与,课例研究阶段更重视学科教学能力更强的教研组长或骨干教师参与,以达到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四、政策执行效果:学校文化对内引领行为转变,对外产生品牌辐射效应
经过三年研究,项目开始之初所设定的政策执行目标,逐渐在学校得以实现,学校文化政策在案例学校的落实逐渐产生了一系列实效。
(一)系统优化,学校核心价值引领学校文化特色发展
回应起初提出的政策目标,案例学校经过三年研究,已经形成了基于“微笑教育”核心价值观的办学理念体系,其中对“微笑教育”的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明确提出“微笑教育”所应表现出的实践特性,对育人目标等文化理念体系的相关元素进行了提炼与详细阐释。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生机盎然”的学生文化、“好伙伴课堂”教学文化、“体验未来”课程文化,以及“专业共生”的教师文化。在逻辑及实践上,学校文化的理念体系与实践体系得到优化,并得到师生的广泛认可。
有了这样的文化体系,校长在接手学校之初所面临的“概念满天飞”却无法真正落地的文化困境得以初步化解,学校形成了立足国家政策导向与学校历史传统、符合学校全体成员教育期待且契合学生发展需求的全新文化体系,学校的文化体系得以优化,品牌特色建设取得实质进展。
(二)课题引领,教师有意识地在教学实践中渗透学校文化
教师对学校文化的践行,首先体现在课堂教学中。经过三年的研究,研究者对学校教师的课堂进行观察,整体来看,教师能有意识地结合学生的学习起点,设计适切的教学目标,并据此设计课堂上的主干问题,供学生自学或以小组合作等方式进行自主探究,学生在课堂上有很高的参与度,其中学生的思维参与水平较之前有明显提升;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时,能比较具体地给出有效指导,在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也能较好地观察学生的情况,以便给予及时的指导或是在集体交流时选择合适的同学进行交流和展示。这些课堂教学行为较好地回应了学校“好伙伴课堂”教学文化所提出的高品质思维参与、构建学习共同体、学生拥有心理安全感和学生真正的实际获得四大关键指标。
学校教师也有意识地通过课题研究的方式将学校文化理念与日常教育教学行动相融合。例如,由校长主持、骨干教师为核心成员的市级课题“学生核心素养培育背景下‘好伙伴课堂’构建的行动研究”,课题组核心成员主持的市级课题“基于‘好伙伴课堂’构建的小学生课堂倾听能力培养策略研究”和“小学中高年级阅读思维可视化策略研究”等,都是通过行动研究的方式探索“好伙伴课堂”的教学文化在课堂中的实践转化。以课题为抓手,带动教师们制度化、规范化地开展教学文化研究,教学改革不断深入。
(三)学生文化生机盎然,获得家长广泛认可
只有当学生的整体风貌逐渐凸显出学校理想中学生文化“应有的样子”,学校文化的构建才开始真正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育人目标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通过三年的项目研究与实践,学生“生机盎然”的整体风貌日渐凸显,从学生身上可以看到学校学生文化中倡导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自主自律的行为习惯”与“合作共生的人际关系”等理念。
通过对学校文化建设的系统思考,学校举办了戏剧节、科技节、徒步远走、足球嘉年华等系列特色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学生是活动设计者及真正的参与主体,发展的自主性得到充分体现。学校丰富多元的课程、全员参与的大型学生活动等办学成就得到家长的高度认可和赞誉。在学校组织的特色活动中,家长们踊跃报名参加活动,给学校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四)品牌建设成效突出,产生一定辐射效应
除上文所论的内部变化之外,政府、家长、兄弟学校、前来参观学习的同行对学校“微笑教育”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知,学校文化开始产生对外辐射效应。
首先,通过督导、检查、教育教学展示等多种活动,学校多角度立体化地向各级各类行政管理部门展示了学校文化建设成果,如北京市政府督导室下校督导过程中,学校获得专家一致好评,学校还获得市优秀课程建设成果一等奖、区教育教学展示活动的“五星奖”等荣誉。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学校文化建设的成效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
其次,学校作为区域内办学成绩突出的优质小学,一直是“国培”等各类教育培训、教育扶贫等项目中其他学校领导与教师“跟岗学习”的重点对象。学习过程中,参训人员对案例学校的文化特色有高度的认同,如京津冀一体化的“手拉手”学校项目中,来自雄安新区的学校高度认同该学校的文化体系,在后续工作中积极派员来校“取经”,希望学校能在该领域对其进行系统引领。
五、政策执行机制:宏观政策在学校得以有效执行的行动逻辑
案例学校采取项目研究的方式,层层推进学校文化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案例学校的象征性政策执行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源于其特有的行为机制。概而述之,校长的政策执行发生在全社会重视文化建设、学校具有初步的文化概念但缺乏系统性与实践力等现实情境中,其对学校教育、学校文化建设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但在追求过程中也遭遇到教师热情不高、时间矛盾难以调和等现实困难,挣扎在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校长用自己的行动智慧,推动了理想的一步步实现。
(一)校长对政策的清晰认知与合理定位
前文曾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意义建构视角的政策执行研究,强调政策执行者并非被动地执行,而是基于自己的原有认知、具体的政策情境等对政策作出自己的意义赋予,从而选择相应的行为来确保政策在实践中落实。具体到本案例中,校长对政策性质的基本认知和定位,直接影响其政策执行行为的选择。
象征是人们理解政治生活以及政策过程的重要工具。鲍曼(L.G.Bolman)和迪尔(T.E.Deal)提出“象征视角”来理解组织的意义和行为,“象征符号包含着强烈的智慧和情感取向,表达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象征性关注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它有什么意义。①李·鲍曼、特伦斯·迪尔:《组织重构:艺术、选择与领导》,桑强、高杰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案例校的政策执行中,校长充分认识到学校文化的象征性意义,意识到在学校构建自己的意义体系、形成全体成员的共享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在将象征性政策落地的过程中,校长表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抓住学校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采取项目制运作的方式,集中大学专家、学校优秀教师等多方力量,使其共同参与到政策执行过程中,为学校打造既传承历史又服务未来的文化体系。
(二)校长基于对教育本质的把握而萌发的教育理想
政策要得到有效执行,执行主体需要使政策的新要求与自己已有的政策认知、组织机构的已有实践基础实现对接。②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学校文化建设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学校构建一种理想并在校长的带领下将这种理想逐渐转化为实践。校长作为一所学校的“掌舵者”,其教育理想会直接对学校理想的构建产生影响。案例中的F校长,在进行学校文化变革之前,对于学校的发展有自己清晰的想法。
我现在朴素的想法就是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让老师有一些发展,让孩子在我们这一任领导下确实能够比较快乐,能够有所获得。对于我们想做的事情,必须要坚定地、倾注全力去做。比如我们想把阅读这件事做好,让学校中每个孩子都能享受阅读,喜爱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再比如,我们数学学科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大家就觉得要让孩子除了爱阅读以外,还能够觉得生活很有智趣,把学习当作很有意义的事情,喜爱学习。实际上我们学校,从整体上,书香和智趣是我们希望能够突出的两点。同时,健康也很重要,我们的体育也有优势。因此,从我心里,坚持的就是“健康+阅读+智趣”。
可以看出F校长对学校教育的基本假设是:学校教育要让孩子能够快乐并且能有所获得,而该目标得以实现需要关注健康、阅读和智趣三个点。学校的“微笑教育”以及“微笑教育”引领下的办学理念和实践体系,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而提出的。
(三)智慧化解理想实现过程中的现实困境
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森强调了政策执行的重要性,“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到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③兰秉洁、刁田丁:《政策学》,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然而,在当前复杂的教育改革环境中,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均得到成功执行。④Meredith,I.,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Confronting Complexit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p.2.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是一个涉及政策目标、方案、执行结构和人员、外部环境等众多要素的复杂过程,由于许多教育政策涉及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教育教学活动,需要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学校文化和师生特点,细化分析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
学校文化政策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政策,不直接涉及实质性利益的分配,而是倡导一种政策理想的提出和实现。这一政策在学校中落实,遇到了不少现实的困难,校长引领学校成员采取主动措施,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确保学校文化建设取得实际效果。
1.多种途径引导政策认知,应对利益相关者的掣肘
政策执行过程中,校长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利益相关群体缺乏长远眼光,难以认识到重塑学校价值理念、构建全新学校文化体系对于学校、教师乃至学生成长的重要意义,因此,对校长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持不理解或者不支持的态度。例如,一些教师认为参与学校文化建设项目研究会影响自己“做更重要的事情”,从而不愿花精力参与相关研究;有家长认为学校提一些“华而不实”的口号对孩子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学校不应该把过多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对这些情况,校长一方面采取集中宣讲的方式向学生、教师和家长宣传学校的文化体系,促进相关群体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在活动设计过程中,融入学校的文化符号,让象征意义转化为一种实际意义。
2.寻求专业资源支持,解决学校内部成员主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局限
在本案例中,学校管理者主导的文化建设难以实现高水准的文化重塑。在此次通过项目研究的方式深入推动文化建设之前,学校文化建设一直是学校少部分中层领导带领极少数教师来操作。由于学校成员对学校文化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学校成员研究能力的限制、局内人身份的限制等等,导致学校文化建设一直处于一种“低水平徘徊”状态,难以实现高水平文化重塑。面对这样的困境,校长引入了专业的研究团队提供支持,并从校内选择“精兵强将”构建研究团队保障项目研究的高效开展。
3.将外部要求内化为学校价值体系,消解外部力量的消极影响
各级各类的督导、评价、指定性改革项目等在学校的落地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学校开展内部工作的精力。校长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是“为我所用”,将督导、检查、评价等都融入学校的价值体系中,不需要另起炉灶,最大程度地减少外来力量对学校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
六、反思与讨论
面对“学校文化”这样的象征性政策,虽然国家和政府主管部门并未通过强制力来约束学校执行相关政策,但校长充分认识到这项政策对学校发展的象征性意义,并采取行政性项目推动的方式在学校落实。虽然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但校长都能通过智慧的方式化解并确保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本研究从“微观”的视角,深入剖析一项象征性政策在学校的执行情境、执行过程及有效执行的行为机制,以期为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一)象征性政策的落实,执行者对政策的深度理解尤为关键
学校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性政策,在获得执行的过程中,其直接的动力并不来源于政府的强制力,只有得到执行者的价值认同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因而其更加依赖于执行主体的认知与意义构建。校长作为执行主体的核心,对学校文化政策的深度理解是政策得以落实的关键。
基于以上观点,对于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而言,在象征性政策的制定中,要关注执行者如何能更好地理解政策本身,理解其对教育发展的意义之所在,这构成了此类政策得以执行的基础。对政策执行者而言,面对此类政策,需要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学习政策精神,深入理解政策之本意及其价值之所在,以确保政策执行的方向不会发生偏差。对教育政策研究者而言,当研究对象为象征性政策时,需要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认知。
(二)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知,需要理论研究者的高位引领
对于政策执行者而言,由于“身在此山中”的缘故,他们很难跳出具体的情境对所需执行的政策的背景、意义等形成理性和高位的认知,此时专业理论研究者作为在本领域占有最先进知识、把握本领域研究与实践前沿的专业人士,可以为政策执行者做出关于政策的权威解读,因此,理论研究者对政策执行者的引导就变得尤为关键。
本研究中的案例学校在执行学校文化政策的过程中,教育政策与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者通过理论指导、专题性讲座、座谈交流、头脑风暴等方式,为政策执行者系统解决了学校文化对于学校发展的意义及从学理层面上如何构建优质的学校文化的问题,引领执行者的政策认知,使政策执行者对于政策的认知愈来愈趋于科学与合理。在此过程中,理论研究者的指导不可或缺。
(三)将非强制性政策转化为规定性工作任务,是执行政策的有效手段
象征性政策的非强制性特征,导致此类政策的执行缺乏一种强制约束的力量。面对此类政策,即使执行者充分认识到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强烈的意愿去行动,但由于约束力的缺乏,导致此类事务在与其他强制性事务发生冲突时,会首当其冲地被舍弃。因此,若要缺乏强制力量约束的象征性政策得以顺利执行,需要采取适宜的方式,将非强制性政策转化为规定性的学校日常工作任务。
本研究中的案例学校,以项目引领的方式促使政策落地,便是以一种规定性的日常工作制度措施将理论研究者与优秀实践者汇合在同一时空下,在共同研究的过程中充分汇集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确保政策目标的达成,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