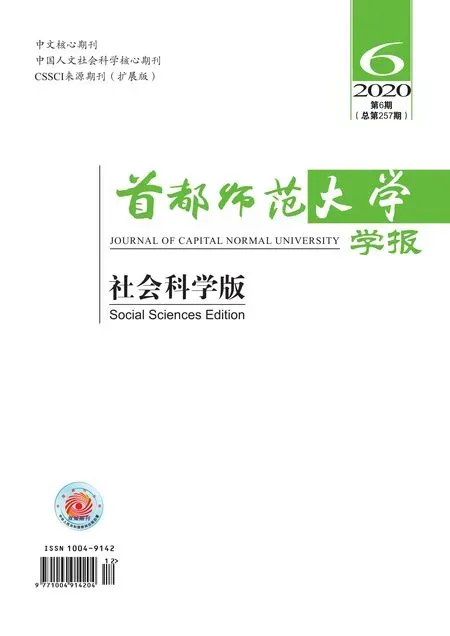《四世同堂》:一部现代中国的“战争与和平”
——兼论中国抗战文学中的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问题
邵宁宁
有关《四世同堂》在民族国家问题上认识的复杂性,前人已颇有论说。十数年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就其所表现之战时生活经验和现代国民意识凝成之关系做过一些简要的分析,但当时的认识尚未能越出民族国家的视野,而对作品中另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暴力与人道、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等等——做出必要的讨论。众所周知,《四世同堂》是老舍最长的一部创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抗战小说中思想分量最重的一部。就如有学者已指出的:“以小说的主题与结构来看,老舍必然有心写作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向欧洲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如《战争与和平》等看齐。”①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不过,对于他的这一追求是否得到实现,所论多有怀疑。譬如还在1981年,赵园就在整体考察老舍的创作时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产生如《战争与和平》那样足称一时代纪念碑式的艺术巨构。”②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虽然直接针对的并非《四世同堂》,但也包括《四世同堂》应是无疑义的。同期的吴小美和其后的王德威论及这一小说,同样不少遗憾之辞。①详参吴小美:《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4、5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不过,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更像是主要从艺术表现的完美度出发所做出的判断,而很少涉及该作中具体与之有关的思想。赵园所说:“长于写实”的老舍,在《四世同堂》等作“却弃长就短,发了过多的关于‘文化’的议论。这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被当作了作者的话筒。人物有时不是在演他们自己,而是在代作者立言。他们的议论,又往往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以至成为老舍小说中最沉闷累赘的部分”。②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确是很能激发人们的同感的论断。但若换一个角度看,是否“最沉闷累赘的部分”,出于不同的阅读目的人,则或亦会有不同的感受。一部小说本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读法。对一部小说之作为反映/表现之作或思辨思考之作,研究者或许也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倘若允许我们将小说也当作一种精神文本,则这样一种“同义反复”,同样可以看作一种精神“症候”,其中所反映的作者思想在某一问题上的纠结缠绕,也同样具有值得认真分析的价值。
一、和平与抵抗——作为和平之都的北平及其精神反思
《四世同堂》是一部以北平沦陷期的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全景式地反映北平市民的抵抗意识的萌生和发展,自然是全书最明确的主题。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老舍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又的确是始终在一种和平主义的文化心理背景中进行的。众所周知,“北平”之称,源于战国时燕国所置之右北平郡,其后历代沿革,屡为首都,屡经废置,命名中也总都含有一种祝愿和平之意。明朝建立,易元大都名为北平府;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市,无不如此。而在老舍笔下,和平同样可以作为北平的灵魂来看待。就如前人所发现的,在《四世同堂》里,有一个“老舍寄予最多私人感情的……隐形角色,就是北平。……他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重庆或遥远异乡的美国写部小说,但是他热衷描述的却是各个季节北平的不同景象。……因为战争,北平在老舍的想象中显得生疏了,反而被赋予了一种比往昔都更加美好的文学意象”③王德威:《写实主义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215页。。而其中最为美好的,无疑是那由宜人的天气、丰盈的物产以及种种充满人情和礼仪风俗所构成的文明气度。
《惶惑》第十四节有一段有关北平秋天的描写,堪称小说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匀。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挟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
老舍爱北平。在北平的四季,他最爱的是秋天。其关键所在,正在这样一种和平气象。连大自然都是这样地温和无害,遑论人情有多么淳美——就像中秋时看到兔儿爷的摊子与许多水果摊儿立在一处:“人们的心中就又立刻勾出一幅美丽的,和平的,欢喜的,拜月图来。”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小说一开始,即为日本人的入侵所打破。书中写到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市民听到日本坦克车在北平街头的声音,紧接着出现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
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说不清这是瑞宣还是作者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反应。无可疑的只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抵抗,争斗”开始正式成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四世同堂》是一部国民觉醒之书、抵抗之书,也是一部精神自新之书。像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次次发生过的那样,每到中华民族的现实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们在奋起抗争的同时,也都会将对问题的反思指向自己的文化,指向自己国民人格的构成。《四世同堂》同样如此。面对异民族的“强奸”,首先是中国人的善良、平和,一下地变成了这个文化的弱点。早在《四世同堂》之前,老舍写到中国人的爱和平,已然情绪并不单一。《猫城记》中讽刺猫人“被兵们当作鼓打,还是笑嘻嘻的;天一黑便去睡觉,连半点声音也没有”,称“假如有好的领袖,他们必定是最和平,最守法的公民”,便有明显的批判意味。但即便如此,《四世同堂》中写到北平人的和平品性,仍然心绪繁复。在瑞宣和他人的记忆中,“祖父的教训永远是和平,忍气,吃亏,而没有勇敢,大胆,与冒险”,“祁天佑——自幼儿就腼腆,一辈子没有作过错事,永远和平,老实,要强,稳重”,瑞宣“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爱和平,喜自由,有理想,和审美的心;不野调无腔,不迷信,不自私”,李四爷“永远吃苦,有时候也作奴隶。忍耐是他最高的智慧,和平是他最有用的武器”。就连住在城郊的常二爷,“不认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也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至于老诗人钱默吟,更是寄寓了作者无限的诗意文化想象:他的“屋里,除了鲜花,便是旧书与破字画。他的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当他读陶诗,或自己想写一首诗的时节,他就常常的感到妻室儿女与破坛子烂罐子都是些障碍,累赘,而诗是在清风明月与高山大川之间的。一想诗,他的心灵便化在一种什么抽象的宇宙里;在那里,连最美的山川花月也不过是暂时的,粗糙的,足以限制住思想的东西”。数不清书中还有多少这样的形容与描写,小说对北平人和平心性的描写,真可谓不厌其烦。
然而,这一切毕竟还是为正在到来的战争所打破。北平沦陷后,瑞宣清楚地意识到,北平的“老百姓是不甘心受日本人奴役的,他们要反抗。可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和平、守法思想,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力不从心”。看到从敌伪组织的游行中回来的人们,他感到难过——“那么多的学生和教师,就楞会没有一个敢干一下子的!”他想:“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战争爆发不久,“和平”的谣言就很多,“北平的报纸一致的鼓吹和平,……连富善先生也以为和平就在不远。他不喜欢日本人,可是他以为他所喜爱的中国人能少流点血”,但瑞宣明白这“和平”,其实别有所指,“这次若是和了,不久日本就会发动第二次的侵略!”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支配下,他进一步想:“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身”,“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
战争重塑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自我期待,战争所带来的民族自新,不但是要葬埋(如老舍另一本写抗战题材的小说《火葬》的标题所示)如冠晓荷、大赤包、瑞丰、蓝东阳一类的败类和污泥浊水,而且也要对民族成员中最优秀的那些人的心性做出重塑。瑞宣想:“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的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它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一度渴望着“把自己融化在什么山川的精灵里,使自己得到最高的和平与安恬”的钱默吟,开始希望“把自己化入一股刚强之气,去抵抗那恶的力量”。就连一向胆小的祁老人,也敢于“露出胸膛教他们放枪”。一边满怀感情地渲染、珍惜着这座城市的和平文化,一边不断对这种文化精神做出反思和批判,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感情,始终构成着这部作品最重要的思想张力。
二、暴力与人道——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托尔斯泰主义及其他
丰子恺在1938年《战地》第4期的《谈抗战歌曲》中说:“此次抗战,我们的任务不但是杀敌却暴,以力服人而已。我们还须向全世界宣扬正义,唤起全世界爱好和平、拥护人道的国民的响应,合力铲除世界上残暴的非人道的魔鬼,为世界人类建立永远的和平幸福的基础。”①丰子恺:《关于抗战歌曲》,《丰子恺全集·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11,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同样的思想,也回荡在《四世同堂》这样的小说里。
自进入氏族部落社会以来,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久已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不时成为各国文学表现的重大主题。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考虑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思想主流,以及秦统一后大部分时期的历史实际,这样的说法,决非虚言。与许多崇拜武力的民族不同,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思想的主流,除从“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认识出发,主张“积务于兵”的法家之外,无论是孔墨老庄,还是后来传入的佛教,对战争都从根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到孟子的“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从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道德经》)到墨子的“非攻”(《墨子》)、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以至佛教的护生戒杀,都以消弭战祸或将战争的破坏限制到最小范围为目标。即使在中国国力最为强大的汉唐,对穷兵黩武的批判,也始终是中国社会话语的主流。正如杜甫诗所言:“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这种和平主义的理想,的确构造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种文明。直到时间进入近代,才为巨大的外部压力所催生的深刻疑虑所打破。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面对着外来入侵的战争威胁,富国强兵渐成近代思潮的突出特征,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日益迫切的瓜分豆剖、亡国灭种危机,重整武备、重扬尚武精神,也渐成新的社会共识。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有人主张它应该始终坚持自己的和平主义正道。譬如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际,托尔斯泰在英国《泰晤士报》公开发表反战文章,其后又与中国学者辜鸿铭通信,再次申述自己对欧洲——尤其是俄国——暴行的谴责态度,以及自己对当时中国的自强运动可能重蹈欧洲文明“以暴易暴”的覆辙的忧虑。这一切,在当时的中国及世界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一度写过《斯巴达之魂》的鲁迅,到1908年写《破恶声论》时,也明确表达了对当时流行的“崇侵略”的兽性爱国主义的反对。
不过,迫于时势,当时更多人还是不全能够理解他这种“不以暴力抗恶”的良心善意。譬如早在1907年,在《大阪每日新闻》刊出托氏《致支那人书》后,宋教仁即想将之译载于《民报》,但最终并未实行。有学者推测,其原因即与革命派不赞成这种“不抵抗”的主张有关。②范国富:《鲁迅留日时期思想建构中的列夫·托尔斯泰》,《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0期。而鲁迅在《破恶声论》中,也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指出“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戾初志远矣”。在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一边肯定“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边毫不容情地否定其为“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③倪蕊琴:《托尔斯泰主义纵横谈》,刘耘华主编:《孙景尧先生周年祭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而其思想传到中国,又引起了如冯乃超对鲁迅的攻击、阿英与巴金的争论等新文学内部的论争。④参见张华:《关于“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0期;阿英:《力的文艺·自序附记》,《阿英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从辛亥到五四,托氏作品大量译入中国,作为“俄国新圣”的托尔斯泰思想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⑤参见陈建华编:《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后记》,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五四时期的作家,如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蒋梦麟、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等,都以不同形式介绍或论述过托氏观点。巴金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家》,写到觉新思想,就明言“他很赞成刘半农底作揖哲学,他又喜欢托尔斯泰底无抵抗主义”。几乎所有读过《四世同堂》的人,都可以察觉到它与《家》在主题和结构上的某种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瑞宣的性格及其所面对的问题,亦可谓觉新的性格及其所面对的问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某种再现。而在面对托尔斯泰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上,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老舍比之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其所持的态度也更为积极。瑞宣说:“觉得自己绝不是犯了神经病,由喜爱和平改为崇拜战争,绝不是。他读过托尔司泰、罗素、罗曼罗兰的非战的文字,……人不应当互相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后一句话,不但堪称老舍理想中最具人性光辉的内容,而且也要算鲁迅《破恶声论》后中国文学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又一次最正面的回应。
不过,《四世同堂》全书所写,又的确首先是对这种历史传承下来的和平精神的反思和批判。前面说到,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痛感自己文化的过度“文弱”,并进行过不少的反省与批判。但事实的情况是,截至抗战爆发,一切似乎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有什么改变。日本的侵入,让北平人首先感到惊讶的就是:“咱们的那么多的兵呢?都哪儿去啦?”而历史学家雷海宗,更是在稍后径直将两千多年中国的文化概括为“无兵的文化”①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自打北平沦陷起,祁瑞宣就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自责之中:“以为自己是最没有用处的废物: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去作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也没有!”而钱默吟则更明言:“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的我们遇见了野兽。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这位陶渊明式的诗人,毫不掩饰自己对“体力”的崇拜,在他看来,“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有咱们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四世同堂》再一次将对一种尚武精神的崇拜推到了人们意识的中心。1933年的鲁迅,曾借爱罗先珂的话不无所指地反对将孩子变成“打仗的机器”②鲁迅:《新秋杂识》,《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287页。,但到此刻的钱默吟,心心念念的,却正是儿媳能“生个会打仗的孩子”。
《四世同堂》相当集中地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和平文化的反思与批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作者就完全放弃了他对暴力的批判和对人道的期待。即便明确意识到“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安门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瑞宣还是觉得,“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不可忽视的还有钱先生说“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时用的“暂时”一语。像托尔斯泰所期望的那样,中国文化传统与老舍的确都有着根深蒂固的非暴力倾向。就像钱诗人最终还是将孙子的名字从“钱仇”改成了“钱善”,老舍最终也没有放弃他对人性善良与世界和平的追求。即便支持反抗,支持战争,一种朴素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还是如一股暖流贯穿全书。这一切,或许的确表达了人类一种最健全的希望,然而在现代世界,似乎仍然难以得到实现。
三、民族国家与世界——现代身份认同中的“国民”与“世界公民”问题
《四世同堂》是一部爱国主义主题的小说,然而写作《四世同堂》的老舍,始终是在一种现代世界视野里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的。③对于老舍小说的世界性视野,前人亦已有所发现,譬如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在《老舍小说新论》中说:“老舍小说观是世界的。他在1949年之前一再宣称他到英国后才走上创作之路,那是表示他的作品的世界观是超越狭窄的爱国主义。”俄国学者B.谢曼诺夫也认为老舍“最能显示出民族与国际同时也是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龙敏君:《老舍研究在国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认真地读《四世同堂》,不能不注意其在民族国家追求与世界主义间所具有的这一种张力。读《四世同堂》,不可忽视的还有其中写到的几个外国人。如英国人富善,如瑞宣所在学校的日本教官山木,如小羊圈胡同的那个日本老太婆。富善是现代作家笔下少有的对中国抱有同情热爱的外国人形象,对于他的理解,或许值得另撰专文讨论,这里暂不展开,我们只将注意力投向书中另两位日本人。
早有学者注意到,中国抗战文学有关日本人形象的刻画,多有将其作妖魔化处理的趋向,直到今天的抗日神剧仍然如此。然而,这一认识却并不能简单地推及当代之前。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虽然不像西方文学描写敌国人物那样深入生动,但也并非都只有简单化的处理。《四世同堂》中的山木是个动物学家,平时除了教日语,就是“在屋里读书或制标本,几乎不过问校务。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可是学生骂他,他只装作没有听见”,以致一度使瑞宣误以为他是一个“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学者”,直到有一天传来他的儿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阵亡的消息。他郑重地用中国话向同事、学生报告他“最大的,最大的,光荣”。针对他“中国,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要救中国。中国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见识,有勇气,敢为救中国而牺牲性命”的认识,瑞宣很想独自去找他谈一谈,告诉他:“你的儿子根本不是为救中国而牺牲了的,你的儿子和几十万军队是来灭中国的!”他同时还想对他说清:“没想到你,一个学者,也和别的日本人一样的胡涂!你们的胡涂使你们疯狂,你们只知道你们是最优秀的,理当作主人的民族,而不晓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甘心作你们的奴隶。中国的抗战就是要打明白了你们,教你们明白你们并不是主人的民族,而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着民族的平等与自由的!”这一切,显然也是深埋老舍心中,而想讲给世界的话。
小羊圈胡同1号院的日本老太婆,是《四世同堂》中另一个寄寓了作者理想的人物。“老太婆跟祁老人一样,也爱好和平,她在战争中失去了年轻一辈的亲人。……然而这场侵略战争使黩武分子趾高气扬,却使有良心的人惭愧内疚。甭管怎么说,她到底是日本人。她觉得自己对小妞子的死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祁老人面前,她觉得自己有罪”。描写日本人而使其具有这种负罪感,在中国抗战文学的表现中,是罕见的,它不仅没有将敌国人民全部妖魔化,而且明确地将战争责任问题从一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上升到了更高的人类文明反思水平:
所有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在日本老太婆身上。她不再是往日那个爱好和平的老太婆,而是个集武力,侵略,屠杀的化身。饱含仇恨怒火的眼光射穿了她的身体,她可怎么办呢?
她无法为自己申辩。到了算账的日子,几句话是无济于事的。
她纵然知道自己无罪,可又说不出来。她认为自己应当分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虽说她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然而她毕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因此她也必须承担罪责。
看着面前这些人,她忽然觉着自己并不了解他们。他们不再是她的街坊邻居,而是仇恨她,甚至想杀她的人。她知道,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好对付,可是谁敢担保,他们今天不会发狂,在她身上宣泄仇恨?
日本老太婆与瑞宣的对话里说:“什么时候咱们才会由一半走兽,一半人,变成完全是人,不再打仗了呢?”瑞宣惨笑着说:“你我也许已经没有了兽性……可是你拦不住你家的男人去杀中国人,我也没因爱和平而挡住你们来杀我们!在我的心中,我真觉得自古以来所有的战争都不值得流一滴血,可是从今天的局势来看,我又觉得把所有的血都流净也比被征服强!”读《四世同堂》,不可不注意这里的“惨笑”,它和当时更为广泛地存在的“惨胜”感一样,构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意识中最为复杂的内容。
《四世同堂》是一部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国民意识凝成的复杂性的作品。《四世同堂》写到的瑞全,一向都被当作“中国青年的代表——象征着勇敢,强有力的新中国”。《惶惑》第5节的这段话,堪称表达出了作者对年轻一代最热诚的希望:
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铐镣,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他们没法有滋味的活下去,除非他们能创造出新的中国史。他们的心声就是反抗。……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身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
打破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与束缚,做个自由的人,是五四以来知识青年的共同追求;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铐镣,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瑞全是被瑞宣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实现者看待的。看到他的“一刹时”,他甚至能“几乎把妞子的死都忘了”。对于瑞全形象的真实性,当然也可以有种种的批评。但在我看来,像钱先生一样,他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可当作老舍的社会人生之思的一种体现来看待的。
但对这后一步,就像对这段话中说到的“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铐镣”一语一样,我们一向还是缺少充分的注意与理解。但这里实在蕴藏着理解老舍思想中颇为超前的一种意识内容。不仅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国民,而且要做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这种“世界公民”意识,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发展之一。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欧洲启蒙运动的最大和最富有成果的争议都与世界主义有关。”他转引19世纪中叶海因利希·劳伯的话说:“爱国主义是单方面的、狭隘的,但它又是实用的、有益的、令人幸福的、使人安宁的;而世界主义是亮丽的、伟大的,但对于一个个人而言,它却显得过于伟大,这种思想是美妙的,但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却是内心的矛盾分裂……”①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杨祖群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前面说到,老舍始终是在一种世界视野中写这部小说的。小说两次提到世界将分成两大阵营。前一次是写瑞宣“推测到慢慢的全世界会分为两大营阵,中国就有了助援与胜利的希望”;后一次写瑞全想到随着“战争变成全世界的”,他与钱先生“同样的变为与世界发生了关系的人”,而在“全世界分成两大营阵”之后,“公理必定战胜强权”,世界上吃过战争的苦的人“必会永远恨恶战争,从而建设起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种有关两个阵营的想象当然还都是针对当时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同盟的。瑞宣在教室里向学生倾诉自己,批评“人类成了武器的奴隶,没有出息”,寄望“人类也会冷静下来,结束战争,缔结和议。要是大家都裁减军备,不再当武器的奴隶,和平就有指望了”。只是他未曾想到,战后的“两个阵营”,又将演化出怎样的新的对垒。更不知道人类要实现康德式的“永久和平”,要走的还有多么漫长的路程。
1981年,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的《邓小平文集》所作序言中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②阎晓宏等主编:《邓小平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这或许是中国在经历几十年的封闭之后,又一次以一种至为庄重的方式,宣告了它融入世界的理想。历史选择这样一位人物来做这样的宣告,自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但无论如何,对于《四世同堂》来说,的确需要这样一种“世界公民”意识的复归,才能为我们更准确、完整地理解其意义提供某种可能。
四、“残璧”与“完璧”——出版延宕中的意识困扰
要完整地认识《四世同堂》,还不能不考虑它复杂、曲折的成书过程。众所周知,《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分别创作、发表于1944—1946年之间。第三部《饥荒》创作于作者受邀赴美讲学、居留的1946—1949年。根据老舍1949年致楼适夷的信中的话看,1949年12月老舍归国之际,全书其实已经完成,并已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国出版。从1950年5月起,其中的一部分(前20段)也开始在上海《小说》杂志上连载,不过到1951年1月即停止,从此未见下文。据1951年10月老舍致日译者铃木择郎和桑岛一信,可知他还曾明确说过:“需要对《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发表”,同时还说“何时着手修改还不知道。现在工作繁忙,无闲暇顾及。这实在对不起各位,但也无奈”。③赵武平:《〈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饥荒〉的回译》,赵武平补译:《四世同堂》,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
“文革”中,《饥荒》手稿丢失。1983年,又有马小弥根据美国哈考特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浦爱德的英文节译本《黄色风暴》(TheYellowStorm)回译出该书最后13段作为《四世同堂补篇》出版。不过,据浦爱德自己的说法,英文节译本出版时对原书已有不少删节④参魏韶华、刘洪涛:《埃达·浦爱德与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本》,《东方论坛》2008年第3期。,而马小弥在回译时也根据当时观念对其中一些细节做出了一些改动。全书显见得已成“残璧”,然而不料到2014年,又有赵武平先生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发现的英文全译本及有关资料披露。此后,东方出版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推出赵武平补译本、毕冰宾补译本,至此,《四世同堂》似乎又终成“完璧”。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1951年正在连载中的《饥荒》为什么会忽然中断连载呢?读者从此中又能看出些什么?
作者的家人曾说:“这是个很难解答清楚的问题,因为作者本人生前并没留下任何解释。它可能永远都是个谜。人们可以做一些推测,但也仅仅是推测而已。”这样的推测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理解老舍及其该时期的思想却不无意义。譬如比照老舍1950年对《骆驼祥子》的修改,他们推测《四世同堂》的结尾虽然写到了中国的胜利,但“气氛与其说是欢呼,不如说是悲壮”,“这幅模样和‘胜利者’似乎太不相衬”。①胡絜青、舒乙:《破镜重圆——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吴怀斌、曾广灿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93-694页。这样的说法,颇让人想起《寒夜》出版后因其结尾巴金遭受的那些批评,其可信度当然是不低的。再如,针对马小弥翻译部分对原作的一些删改,有学者推测其处理方式可能也与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文革’。可能受此前的思想影响,觉得这些心理活动的存在,会削弱瑞全作为抗日斗士的形象,让他显得优柔寡断,不符合当时所倡导的典型形象”有关②周绚隆:《关于〈四世同堂〉的英译与回译》,《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3日。,无疑也有其道理。
无可怀疑的是,在《四世同堂》的成书过程中,的确始终有一只看不见的时代之手在不断拨正着它的方向,决定着它的取舍。或许不应忘记的还有:老舍写作《饥荒》之际,正当战后世界和平运动蓬勃展开之时,而当其连载之际,已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西方对抗再趋紧张之时。从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仍然只能是“斗争”而非“和解”,是民族国家的稳固而非“走向世界”。了解这种更大尺度上的时代背景,或许也是理解1951年之后《饥荒》“不宜”连载,并需“全部加以修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翻阅回译补足的《四世同堂》,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曾被浦爱德节译本整篇删除过的那篇钱默吟先生的《悔过书》,这也是全书的最后一节,从内容和结构看,都大有对全书做最后总结的味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与其说是一篇“悔过书”,不如说是一篇“反战檄文”。对于《黄色风暴》为什么会删除它,曾有学者从人物的“学养与做派”及原文所可能使用的文体(或为文言)等方面做过一些推测。但问题可能比这更复杂。这一点,只要看看《悔过书》中诸如“任何想用战争方式解决人类问题的都是思想上的落伍者。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野蛮原始的做法”“人类穿上军服后会因为某些原因变成禽兽”一类谴责战争与暴力的文字,或许就会略有理解。这或许是一篇更直接体现了王德威所谓作品中的“说教”的文字,但也是理解《四世同堂》以及老舍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思想倾向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像是预感到了它可能遭受的批评,就在它本身,作者已预先声辩:“不要以为我是在向你们布道。我不懂布道,并且厌恶布道。我从不愿以一己浅薄之见去说服别人,因我认为只有人们都认为正确的方为真理。真理即众人之共识,一旦我们停止独立思考,我们不仅会被别人欺骗,还会被自己的圣人欺骗。”
《四世同堂》不是一部艺术上的完美之作,但它确实集中展现了老舍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诸多问题的思考,寄托了他对中国文化最深厚、最复杂的感情,其在许多认识上的超前性,至今还值得从新的角度做出分析和思考。就如现代文学留给我们的许多欣慰与遗憾,小说本身及其发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陷或遗憾,我们已无法改变,但尽力尝试以一种更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探询其中所包含的一切,仍然是一项很值得尝试的工作。海因利希·劳伯说:“世界主义这种思想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事物,但对全体人类而言,它过于伟大,因此只能停留在思想阶段。如果这种思想不能具备具体的个性与形态,那么它的存在仍将被视若无物。”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具体的个性与形态”呢?阅读《四世同堂》,反思老舍寓于其中的所思所虑,或许仍不难寻得一些积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