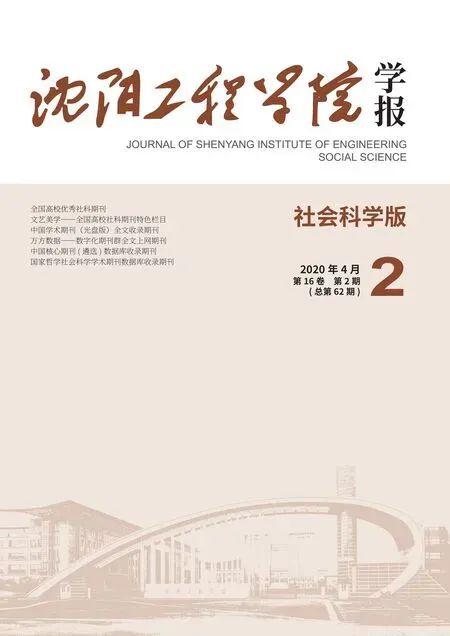福克纳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现状综述
王美萱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美国南方作家艾伦·塔特(Allen Tate)指出,福克纳的“创造性和力量是他的同时代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所无法匹敌的”[1]。福克纳能够蜚声文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小说中集中展示了美国南方的伦理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兴起,采用文学伦理学方法重新阐释福克纳小说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众多学者深入挖掘福克纳小说的伦理道德意义,进一步揭示福克纳小说超越美国南方地域性、超越时代的普适性价值。基于此,本文从国外研究现状和国内研究现状两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整理,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经验和不足,并预测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向。
一、福克纳文学伦理学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福克纳研究中涉及文学伦理学的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对福克纳小说家庭伦理的关注,二是对福克纳小说种族伦理的关注,三是对福克纳小说生态伦理的关注。
首先,就福克纳小说的家庭伦理来看,这类研究深切关注了福克纳家庭小说中的“善与恶”“乱伦与复仇”等主题,集中体现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两部作品中。美国早期的福克纳研究学者,如柯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艾伦·塔特等,大都关注过福克纳主要的家庭小说。美国学者艾文(J. T. Irwin)在1975 年出版的专著《成双与乱伦/重复与复仇:福克纳的沉思性阅读》一书中,从伦理学角度阐释了福克纳小说的乱伦和复仇的主题,涉及文学伦理学中的“人性因子”等问题。
评论家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在《无可匹敌的时间:威廉·福克纳传》中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与《我弥留之际》进行对比,细致分析了家庭伦理问题。在帕里尼看来,“家庭成员之间隐蔽的恶意,是福克纳小说中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主题。”[2]帕里尼还在著作的第五章“约克纳帕塔法县”中,从家庭伦理研究入手,将《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在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形象等各个方面进行对比。帕里尼还深切关注了福克纳小说中家庭伦理崩坏的问题,细致剖析了乱伦主题。帕里尼的分析揭示了福克纳小说中固有的伦理禁忌观念,为研究福克纳小说的伦理道德问题提供了基本路径。
与杰伊·帕里尼相似,弗莱德里克·R.卡尔(Frederick R.Karl)在其著作《福克纳传》中也提及了福克纳小说中的家庭伦理问题,在谈及《喧哗与骚动》时他指出:“福克纳对手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这些修改改变了《喧哗与骚动》的某些意义,表明在个人意愿与命运的殊死搏斗中,家庭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种家庭关系的模式,大体是以败落、无能、父母对子女的忽视、冷漠,以及生活在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中的父母等为基础的。”[3]卡尔将《喧哗与骚动》归结为家庭小说,强调家庭关系对人物性格养成和命运发展的巨大作用,揭示出伦理关系失衡是导致人物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
其次,就福克纳小说的种族伦理来看,这类研究集中探讨了福克纳小说中美国南方种族身份、情感归属、心理认知和道德伦理等主题。1981 年评论家詹金斯(L.Jenkins)出版的《福克纳与黑人—白人关系:一种心理学方法的阐释》和1983 年桑德奎斯特(E.Sundquist)出版的《福克纳:破裂之屋》对福克纳小说种族伦理的阐释最具代表性。桑德奎斯特在《福克纳:破裂之屋》的序言中指出:“我的书名《福克纳:破裂之屋》涉及与蓄奴制有关的、后来演变为内战的地区冲突,界定出福克纳关于种族冲突的多部小说的意义层面。”[4]桑德奎斯特从种族伦理角度切入,解读了福克纳的六部小说,揭示了美国南方社会特有的种族隔离制度,展现了当时社会激烈的种族冲突,描绘了在此种社会道德约束下黑人现实和精神的伦理困境。此外,弗莱德里克·R.卡尔在《福克纳传》中对福克纳小说中的种族伦理也有涉猎。卡尔评述道:“通常被认为福克纳的三部主要作品的《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都含有强烈的种族暗示,后两部尤其如此。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昆丁在讲述中时常涉及从战前至1909 年的各种种族问题——这样就与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联系起来了。小说的核心问题是种族态度。”[3]601卡尔将《押沙龙!押沙龙》的悲剧划归到种族伦理层面,将主人公萨德本的悲剧看作种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社会等级关系认知错误的伦理悲剧。
最后,就福克纳小说的生态伦理来看,这类研究将福克纳小说的生态观念置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之下,集中阐释了美国南方生态系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呼唤。国外学者大多强调工业化对田园传统的破坏,关注人类精神家园的堕落,揭示出一个处在转折时期的美国南方所面对的生态伦理困境。美国评论家约瑟夫·R.沃尔克(Jo‐seph R. Urgo)和安·J. 阿巴迪(Ann J. Abadie)在2003 年主编并出版的论文集《福克纳与南方生态》中对福克纳小说的生态伦理进行了集中阐释。该论文集认为福克纳最关心的是社会生态,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迫切问题。该论文集的相关论述打破了单纯地关注自然生态的孤立局面,将生态伦理与社会伦理相结合,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对当时的美国南方现状加以思考,呼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伦理关系建构。此外,美国作家利奥·马克斯(Leo Marx)的《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科技与田园理想》也关注了福克纳小说的生态伦理问题。利奥·马克斯在该书第五章“两个力的王国”开篇援引了福克纳小说《去吧,摩西》中的原文,认为一切美德源于自然,对自然与人浑融关系充满了美好的期盼。利奥·马克斯还认为,在花园里现身的机器,引起了新旧文化的冲突,自然破坏已经上升到生态伦理层面,美国南方田园经济在工业文明铁蹄下顷刻覆灭,引起了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焦虑,使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遭受毁灭性打击。
二、国内福克纳小说文学伦理学研究现状
随着以聂珍钊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创新性方法,国内明确运用文学伦理学方法研究福克纳小说日益呈现出更为集中、更有针对性的趋势。
国内集中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福克纳小说进行阐释的是武月明的专著《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一书。该书共分六章,结合了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等作品,从福克纳小说的生态伦理、种族伦理、家庭伦理、女性伦理、成长伦理的角度入手,“以管窥被福克纳记录在文本时间中的20 世纪美国南方社会有别于北方的伦理现象与伦理关系。”[5]武月明既肯定了大自然所承载的文明价值,关注了自然生态与工业化文明之间的伦理冲突,又揭示了人类社会变革中“存在与占有”、“和谐与对峙”的伦理秩序的演变。武月明指出:“福克纳的终极伦理诉求是人类、特别是南方人的救赎只有在自然中才能完成。”[5]83她还认为:“种族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反人性’,违背了最基本的人伦。”[5]104武月明在此将福克纳小说中的种族问题看作是道德问题,更多地关注种族伦理层面,而非血统问题。虽然武月明的《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一书较为系统地展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在福克纳小说中的运用,梳理归类较为全面,但在篇目选取上杂糅了福克纳各个创作时期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体裁分类指向不够统一,且该书在章节目录的建构方面也趋向于简单化倾向,深层次阐释略显不足。
蔡勇庆在《生态神学视野下的福克纳研究》一书中则采用“环境建构与生态意识”的角度集中关注了福克纳小说中的“文化身份与受造身份”,阐释了“世俗时间与神圣时间”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圣灵寓居的共同体”等概念,倡导“对生态共同体的期盼”。蔡勇庆在福克纳小说研究中引入生态神学理论,将自然的破坏和人类社会道德的堕落紧密联系在一起,细致阐述了美国南方社会存在的神性、人性和生态之间的现实冲突和伦理困境。蔡勇庆认为:“美国思想传统中的荒野形象建构和种族主义观念,即典型地体现了人类从上帝那里汲取的权力,将之用于对世界实行宰治统治。”[6]这深刻揭示了美国南方固有的、被遮蔽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存在的浑融一体的关系。蔡勇庆还阐释了“二元思维”和“宰治理性”概念:“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文化身份大都是以二元对立的模式呈现出来……前者处于统治地位,后者处于劣势的被压迫地位,这个分离的系统不但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对立,也使处于中间地带的人成为无家可归的边缘人和流浪者。”[6]82“二元思维”和“宰治理性”的关系问题,从伦理学角度揭示了美国南方精神困境产生的原因。不仅如此,蔡勇庆还运用生态神学观点将许多问题整合统一起来,为福克纳小说的生态伦理研究拓宽了视野。但他过度强调了整体性的观念,对生态伦理细节的阐释不够详尽。
王钢在《文化诗学视阈下的福克纳小说人学观》一书中也针对福克纳小说的家庭伦理和生态伦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该书第一章“堕落的人的发现与‘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集中关注了福克纳家庭小说中的乱伦主题。王钢认为,福克纳利用乱伦主题,“透过表象,揭示出乱伦的内在深度模式,将现世之恶的展示与美国南方传统价值的崩溃、南方家庭解体和‘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所体现的衰落丧失感完满地呈现出来”。[7]在具体文本分析上,王钢结合了福克纳小说文本,展示了道德秩序失衡下美国南方家庭内部血缘关系的倒错,呈现了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伤害的伦理困境。王钢还认为,福克纳小说集中关照了家庭内部各个成员在伦理秩序失衡的处境下的性格扭曲,进而展现了美国南方特有的、弥散在家庭内部的对往昔美德的追忆和对伦理困境的束手无策。在该书第三章“人的本质的外在重建与生态神学观念”中,王钢又结合福克纳经典小说《去吧,摩西》,运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指出,福克纳特有的具有基督教神性色彩的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有助于人本质的救赎和重建。王钢的研究和结论将自然生态纳入神学范畴,从宗教文化视域分析阐释福克纳小说,为福克纳小说研究开拓了新的园地。王钢的这本专著广泛涉猎了生态神学等相关理论,将自然的破坏和人类社会道德的堕落紧密联系在一起,细致地探讨了福克纳小说中人性、神性、自然生态之间浑融一体的关系,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福克纳作品中深刻的伦理意识。可以说,专著立足学术前沿,结合基督教美学和神学理论,为研究福克纳小说的家庭伦理和生态伦理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范例。
除了上述主要的专著,集中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对福克纳小说进行研究的还有刘桃冶的博士论文《福克纳文学作品伦理取向研究——以三部作品为例》和刘国枝的博士论文《威廉·福克纳荒野旅行小说的原型模式》。前者的研究以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三部小说为例,集中阐释福克纳小说作品伦理取向的生成、表现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后者从论文标题上来看虽然与文学伦理学研究没有直接联系,但作者在探讨福克纳小说的荒野模式时,广泛涉及了福克纳作品中的生态伦理和种族伦理问题。
而就报章杂志文章来看,论及福克纳小说文学伦理学的数量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刘睿姝发表在《光明日报》2017 年5 月10 日第13 版上的文章《福克纳小说的生态批判意蕴》、张慧荣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11 年第3 期的论文《从〈熊〉看原生生命链毁坏对殖民进程的推动》、张立新发表在《国外文学》2010 年第2 期的论文《禁忌、放纵与毁灭——福克纳小说中的“乱伦”母题及其意义》以及郭棲庆、潘志明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 期的论文《再析〈我弥留之际〉中的本德仑一家》等。
刘睿姝在文章中强调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和谐统一。她明确指出,在福克纳的笔下人与自然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和谐秩序。人类因为无度的贪欲,运用人造环境蚕食了自然的祥和宁静,疯狂榨取森林资源戕害动物,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当生命共同体的法则被打破,大自然的惩罚就降临到了人类社会中。这种惩罚带来的现实困境迅速蔓延到人类的精神层面。在深重的精神危机背后,是重建人与自然浑融一体关系的强烈诉求。张慧荣的文章以福克福克纳小说即是从生态伦理角度对上述这一问题的艺术化展现与揭示。张慧荣的文章以福克纳的中篇小说《熊》为分析文本,探讨了殖民主义进程中印第安人、黑人等伦理身份的丧失问题,展现了美国南方特殊历史时期黑人所处的伦理困境。张立新则认为:“乱伦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最重要的母题之一。”[8]通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张立新试图论证乱伦是美国南方走向没落的根源之一。郭棲庆、潘志明的文章则探讨了福克纳小说《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仑一家矛盾复杂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成员间错乱的伦理关系,有助于理解美国南方固有的家庭伦理和道德秩序。
三、结 论
综合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运用文学伦理学方法对福克纳小说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出福克纳作品中未敞开的、被遮蔽的伦理内涵,有利于彰显福克纳作品内部蕴含的文化诗学本体论意义,有利于理解福克纳作品中普世的命运共同体理想和丰沛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