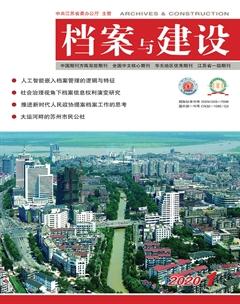我的新四军女兵母亲徐增
仲卫功
关于母亲徐增的人生经历,我知晓得并不多,关于她的一点一滴都让我无比珍惜。她的音容笑貌,她善良柔和、宽厚真诚、勤俭朴实的品格,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母亲是江苏省常熟县吴市人,原名马锦明。马氏家族是由南京移居到吴市镇东北街。清代光绪年间,马氏等三家合资经营“木行浜”,后来马氏又独家经营,主要用来停放木排料,被木行老板视为贮存木材的水上仓库。马氏主要是经营布店,于清代光绪年间开设了“马泰和京广店”,至清末民初,店名改为“马泰和绸布号”。其棉织品大多从上海的大商号批来,丝织品都到丝绸产地苏州、盛泽一带去采购。品种齐全,花色新颖,行时衣料进货较多,由此赢得顾客的青睐。经三代人掌柜,营业地域甚广,在当地享有盛名。
我母亲有一个哥哥马邦铧和一个弟弟马邦鋐,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儿,聪明伶俐,善良美丽,倍受宠爱。我外公去世较早,主要靠外婆持家。我外婆觉得,男孩子读了书要学做生意,将来将祖业传承弘扬。女孩子读书是为了有教养,女孩子要知书达理,要过平和恬淡的生活。若是能学点医学知识,那就能更好地照顾好自己。我母亲很孝顺,依着家里的希望读书、学医。她酷爱医学,真心愿意当个医生,果然,如愿成为了中医妇科医生。
1945年10月,22岁的马锦明为了广大劳苦大众,为了新中国,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医生工作,放弃了原本舒适安逸的生活,瞒着母亲和兄弟,从家中偷跑出来,与宋焕英、屈桂芬两闺蜜以及仲国球在约定的地方见面,四个人一起跑出吴市镇,到了另一小镇北新闸。因担心家里发现后派人出来追回,故白天就躲在农民家里,直到晚上才来到江边,坐上摆渡船,在黑夜中渡过长江,直奔那向往已久的光明之处,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新四军。待他们到达苏北时才发现,从吴市镇出来的还有马仁德、华晨、薛尚年。这一天,同乡七位年轻人一起参加了新四军,都被分配到新四军北撤一大队,大队长是仲国鋆。
我外婆发现女儿不见了,到处找不到时,估计到有可能投奔共产党去了。然后,派出马泰和绸布店的马家堂房大侄儿马仁德及店员华晨一起去周边寻找,再三叮嘱务必将马锦明带回去。谁知,他俩不仅未将马锦明带回家,也追随着一起参加了新四军。
我外婆见不到心爱的女儿,常独坐在女儿房间,面对着两书橱的医药书发呆。她不思茶饭,连续失眠,头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原本女儿用中草药为她专门配制的头痛粉疗效很好,头疼时服一小包即可缓解。这次不同于以往,头痛粉也失灵了,头疼欲裂,不能见光亮、不能听嘈杂声。那几天又遇下大雨,雨落在房顶上的声音犹如鞭子抽打在她的头顶、脑门、脑勺,头部血管随着心脏猛烈搏动并撕拉,似乎颅内脑压骤升,颅骨将炸裂,恶心呕吐,痛苦不堪无法忍受。无奈之下,房间窗户用窗帘挡实以遮光线,用旧棉花毯子铺在屋顶瓦上和屋檐上来缓冲雨落声,以减少神经刺激。由女儿的出走而诱发的这场心因性头痛病,几乎要了我外婆的命。
我母亲等初到苏北,正逢入冬,新四军的吃穿住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常常食不果腹。他们刚刚参加新四军,还不适应部队严格纪律,做了件不符合规矩的事情。我母亲很慷慨地拿出一枚金戒指,放在烧饼店里,随时可去取燒饼。当有机会时,她与几位新战友一起偷偷跑去烧饼店,老板会让他们进入里屋,拿出热乎乎、香喷喷的烧饼,他们美美地吞咽。这是他们几个新兵的秘密,也算是私下开小灶了。
不久,我母亲被分配进入新四军苏中公学分校学习,那时,她改名为徐增。她聪慧好学,很快就成了所在班级(一班)的班长。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接受财经等专业培训。
我母亲在家是大小姐,从小过惯了较为舒适的、衣食无忧的生活,突然变换到落差较大的艰苦环境中,她一时有点不适应。但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她参加革命的决心。她取出从家里带出来的,父母为她定制并刻着“锦明”字样的数枚金戒指、一对金手镯,还有她心爱的派克金笔,这笔是她当妇科医生的第一天我外婆送她的礼物,还取下佩戴在手腕上的翡翠玉镯,倾囊而出,全部捐给了组织,为共同度过艰难岁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从此,她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党指向哪就战斗到哪,愿意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她从江南去了苏北,从江苏到了山东。曾在中共领导的华中行政办事处、山东省政府实业厅担任会计等工作。
1949年4月上海解放之时,我母亲26岁,随解放军华东南下纵队到上海,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农林处任总会计。
我外婆得知女儿的消息,即派出年轻帅气的小儿子马邦鋐去上海,寻找擅自离家参加革命、多年未能见面的女儿。几经周折,姐弟俩在上海市军管会见面了。姐姐成熟了,弟弟长大了,两人兴奋不已,关上门,席地而坐,问这问那,时而流泪,时而欢笑,聊个没完。
姐弟俩正聊得热烈,被一阵急促敲门声打断。来人不由分说,将两人分别带到两个房间,同时盘问许多与家庭有关的同样问题,如:你俩多久未见,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分开的,父母的名字生日,家里人口、住址、房子状况,等等。然后将记录一一比对,结果完全一致,来人这才友好地祝贺姐弟俩重逢。
那时上海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各色特务无孔不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随时可能发生。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又是要害部门,突然冒出一个老家弟弟来访,说话还要关着门,似乎行为有点诡异,当然会引起组织的注意与怀疑了。况且,这楼里有重要的领导人,还有临时金库,戒备森严。那谨慎、盘问、对质都是必需的程序。
1949年9月,我母亲从上海调到常熟工作,担任常熟市人民政府统计科长,常熟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二副主任。1955年,我母亲调至苏州市,担任苏州专员公署税务局副局长、计划委员会物价组负责人,苏州师范附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苏州市第十一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她长期从事金融及教育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地为党工作。
解放初期,我父母经苏州地委批准,于1949年12月结婚。结婚时,父亲就风趣地宣布说,要生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名字都起好了,叫“为人民立功勋”。惹得大家捧腹不已,笑开了颜!这个玩笑掷地有声,一诺千金。1951年初长子出生,取名“仲力为”,小名“布布”,即布尔什维克的意思。随后数年,果然如父亲预言的那样,又得了五个子女,正好三男三女,我们兄妹六人的名字各自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为人民立功勋”。
这是父母的心愿,也是对子女的要求。正如他们愿意为抵抗日本侵略、为解放全中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私奉献。他们热爱共产党,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他们早已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共产党。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任苏州市某中学的书记兼校长,是时常要被批斗的“走资派”,受尽了折磨和摧残,蒙受不白之冤。1968年7月1日,我们突然接到造反派的通知说“徐增死了”,说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简直是天塌地崩了!我们不信,母亲怎么可能舍得丢下我们三双儿女?那年,我们兄妹最大的17岁,最小的8岁,我12岁。我们大哭着,撕心裂肺,可造反派只是冷冷地说:“有什么好哭的,不就是死了个走资派吗。你们要划清界线。”我们坚信,母亲是清白的!1978年5月,在我母亲含冤辞世十年后,迟了太久太久的讣告终于发出,组织上给予我母亲平反昭雪,为被迫害致死的党的好干部徐增召开了追悼会,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数千名亲朋好友聚集苏州,沉痛悼念我母亲,场面十分隆重、感人。
我的新四军女兵母亲已离开我们51年了。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悲惨的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想起仍然心痛不已,泪流满面。每当我思念父母亲时,都会拿出我最喜爱的景德镇瓷杯,放入苏州东山明前碧螺春,用摄氏90度的水温,泡上新茶,敬请父母品味。感谢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感谢父母养育了我们。借此淡淡的春芽清香,表达浓浓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