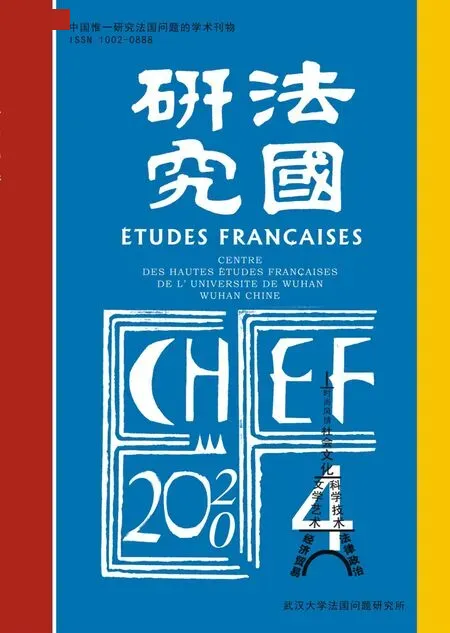从“无器官身体”看《沼泽》中的“无动机行为”
范玉洁
从“无器官身体”看《沼泽》中的“无动机行为”
范玉洁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欧洲学院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提出“无器官身体”的概念,描述了表达身体欲望强弱的三条线——克分子线、分子线与逃逸线,分别对应人们在欲望面前被动、犹豫、主动的不同生存状态。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最早在《沼泽》这部“傻剧”中表达了“无动机行为”理念,作品人物在死水般的生活中或麻木不知,或彷徨犹豫,或奋起反抗。本文试图用“无器官身体”理论解读《沼泽》中呈现的不同人物,总结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逃逸路线,探究纪德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新的责任担当。
《沼泽》 “无器官身体” “无动机行为” 精神逃逸
《沼泽》是纪德1896年出版的作品,这部作品标志着纪德的创作开始走向成熟。“它所展示的文学观念是全新的和极为奇特的。这种全新的文学观念比雅克·里维埃提出的‘文学观念的危机’早了三十年,比‘新小说派’提出的‘反小说’的认识提前了四十年”[1],足见其作品的前瞻性和现代性。但因其独特的拼凑式叙述特点,并未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直到后来新小说派因其荒诞的叙事风格、较少的情节安排和出色的人物心理描写,将之视为开山鼻祖,《沼泽》才又进入批评家的视野。许多研究围绕其写作风格和人物心理分析进行,详细论证了其简单而松散凌乱的情节和毫无个性的人物。朱静在其《纪德研究》一书中,将《沼泽》的主题定为“写作和写作的不可能性以及交往与交往的无法实现”[2],纪德自己也认为这是一部关于“放弃写作”的作品。 然而,作为一部极具现代性的作品,对它的解读应是多样的、开放的。“无动机行为”贯穿纪德“傻剧”系列作品,从首次提出到成熟展现,体现着纪德的写作思想演变和审美追求。无动机并不是没有动机,也不是鼓励犯罪,而是当传统道德、世俗规范扼杀人性、麻木人性时,纪德提出的新的责任担当。纪德承认“《沼泽》讲的正是一种生存状态,”[3]这与“无器官身体”追求的描述人类生存状态不谋而合。本文从小说首次提出的“无动机行为”入手,利用“无器官身体”理论论证无动机并不是无作为,探究纪德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自由的追求。首先,笔者将简略详实地介绍“无器官身体”和“无动机行为”的概念内涵;接着,从文本入手分析《沼泽》中“无器官身体”的表现方式和人物的“无动机行为”和精神逃逸路线;最后,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作者如此构思的深意及对当今社会的借鉴价值。
一.“无器官身体”和“无动机行为”
(一) “无器官身体”
“无器官身体”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加塔里独创的哲学术语,最早可追溯于德勒兹《意义的逻辑》一书。“无器官身体”不是真的指器官的缺失,而是身体不受具体器官的束缚,摆脱传统观念的制约。在德勒兹与加塔里合作的两本哲学著作《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无器官身体”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在德勒兹看来,无器官身体就是欲望。[4]德勒兹认为,无器官身体是经由欲望机器的不断生产与综合而最终成型的,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欲望为无器官身体的形成提供了养料。“无器官身体总是一个强度的容贯的平面,就此来说,无论是多功能的、不确定的器官还是临时的、过渡性的器官,它们都处在强度的连续体之中,并具有内在性平面之固有的容贯性。”[5]无器官身体就是一个感觉的平面,就是感觉的整个领域,因为感觉是有强度性的,根据强弱程度,身体可以分为三条线:克分子线、分子线与逃逸线。这里的线不是指实在的、看得见的线,“线是指一种生成状态,是用来形容人的生存方式或社会制度形态的,”[6]克分子线是传统社会模式,消极地接受社会既定的规章制度。这个阶段的身体是封闭的,没有任何自由,严格按照规定行事。分子线上的人随时做好逃逸的准备,在“循规蹈矩”和“随心所欲”之间徘徊。他们已经意识到所处环境的消极乏味,想要改变现状却无能为力,干脆逆来顺受或熟视无睹。逃逸线是德勒兹重点论证的生存状态,他通向无身体器官,朝着绝对的自由、未知的方向前进。这条线上的人不甘于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主动打破束缚,发出向自由进军的呐喊。
(二) “无动机行为”
《沼泽》与《锁不住的普罗米修斯》、《梵蒂冈的地窖》统一归为纪德的“傻剧”作品,“无动机行为”是纪德在《沼泽》中首次提出、并贯穿“傻剧”系列作品的概念。在《沼泽》中,纪德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内涵:“像样负责的行为,是自由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不再是自由的了,我不是要促使产生行为,而是要解救出自由……”[7]《锁不住的普罗米修斯》中纪德进一步指出了“无动机行为”的荒诞性,强调了个体的自由性,“一种无动机行为?如何来理解呢?要知道,不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不带任何后果的行为,……不,而是没有动机:一种不以任何结果为目的的行为。你懂吗?利益、热情,什么都不是。无利害的行为;从自我中生发;也没有目标;因而没有指引;自由的行为;自发的行为。”(朱静:199)《梵蒂冈的地窖》中“无动机行为”更多了点叛逆色彩,“人们老在想象‘如果怎样,就会怎样’,其实总会有一个小小缝隙,从中会冒出意外来的。没有什么事会完全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发生……而正是这一点在促使我有所动作”(安德烈·纪德,2016:232)无动机行为看似荒诞,自身裹挟着漫无目的、不思进取的被动性和随心所欲、不服管教的叛逆性的二元论张力,实际是纪德对束缚人性的传统道德中探索的一条出路。如同《背德者》中米歇尔的非道德主义是为了建立新的自我道德,冲破传统束缚,无动机行为是为了建立新的自我担当,探寻人在麻木冷漠的世界中如何打破藩篱。
朱静在《纪德研究》中认为,纪德在《梵蒂冈的地窖》一书中才将“无动机行为”从理论付诸实践,笔者认为,《沼泽》表面上描写的是生活在死水一潭的环境中,单调乏味、循规蹈矩的克分子线状态和贪图安逸、犹豫不决的分子线状态,实际上也通过作家“我”,毫无目的的出行这一逃逸线状态,用实际行动实践了“无动机行为”。对“无动机行为”的理解,要经过从表面到本质的认识过程。一方面,它借指那些生活无目标,终日碌碌无为的麻木行为;另一方面,它也是像《沼泽》的主人公“我”一样,寻求偶然性和意外,打破计划规定、不按世俗规则行事的群体。自由,是纪德不懈创作、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对于纪德来说,‘无动机行为’就是一项自由的行动。”[8]“无动机行为”是纪德摆脱现实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逃逸。
二.《沼泽》中“无器官身体”和“无动机行为”的表现
“无动机行为”理论就是纪德对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本质的理论创新。“无器官身体”将人们对自由与欲望的追求强度分成三种——克分子线、分子线、逃逸线。在传统对《沼泽》叙事风格和“傻剧”理念的分析之外,利用“无器官身体”理论,对纪德的“无动机行为”有更进一步的解读。
(一) 克分子线——消极接受、安常处顺
纪德认为日常的行为规范让人负起琐碎微小的责任,让人们肩负重担却不能逾规越矩。人们在这一阶段的“无动机行为”表现为消极接受、安常处顺。日复一日地重复如温水煮青蛙,让人们习惯了安逸,却束缚了人的自由。正如作品名字所象征的,乏味的生活如一潭沼泽,表面平静,一片祥和,殊不知,踏入其中的人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直到被它吞噬、窒息。作家“我”在构思一部作品的主人公蒂提尔时,以他现实中的好友理查德为原型,却刻意省去了理查德的家人和朋友,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没有全部罗列的必要。可见作家“我”所处的生活是多么单调乏味,“生活使我产生的情绪,我要说的是这种情绪:烦闷、虚荣、单调……我们每日所见,还要暗淡而乏味得多。”(安德烈·纪德,2016:21)而维持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是盲目无知、毫无目标的人们唯一能做的事。作家“我”唯一在做的事情便是创作《沼泽》,结尾时他又放弃了未完成的《沼泽》,开始构思《湿地》。这一讽刺性的安排,开头与结尾的同构性暗示了生活本身的循环性, “有些事人们每天周而复始地做,只因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毫无进展,甚至连维持都谈不上……然而人又不能什么也不干……困兽在空间中的运动,或潮汐在海滩上的运动都是在时间之中。”(安德烈·纪德,2016:23)纪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略带讽刺地描写了克分子线上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是无事可做,而做机械重复的圆周运动。然而这样的生活就像温水煮青蛙,消磨了人的意志,纪德借作家“我”之口,表达了对克分子线状态的不满,“我抱怨的恰恰是谁也不抱怨!接受害处便助长害处……久而久之,人们就乐在其中了。我抱怨什么,先生……正是谁也不反抗。”(安德烈·纪德,2016:50)安常处顺是行动无动机在克分子线上的常态。
(二)分子线——徘徊犹豫、视若无睹
然而,“无动机行为”并不单单指那些生活毫无目的,消极盲目的人,分子线上的人虽然看得到生活的单调,却徘徊犹豫、视若无睹。书中的作家“我”,一开始徘徊于安于现状和主动反抗之间,既有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一面,又有不满足于被安排好的既定生活,寻求意外的倾向。“我”习惯于在记事本上给自己列个计划,“弄个记事本,写下一周每天我应当干什么,这才算聪明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我从记事本中汲取责任感。”(安德烈•纪德,2016:22)然而,更好地计划也是为了更好地打破它,体验未知的意外,“我提前一周就写出来,以便有足够的时间置于脑后,为自己制造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这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不可或缺的。这样,我每天晚上睡觉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且又已经由我安排好了的明天。”(安德烈·纪德,2016:22)纪德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赋予人物更多的个性张力,作家“我”制定计划与背离计划同时存在,反映出打破传统规范的不容易。同时,用打翻制定的计划这一行为来寻求意外,本身就是一种向前迈进的尝试性反抗,彰显着行动的伟大。
作家“我”有一件贯穿全书的主要行动,就是写作。《沼泽》采用纪德著名的“回”型嵌套结构,即“故事套故事”的手法,叙述作家“我”正在构思一本名为《沼泽》的小说。“我”要写作《沼泽》这本书的初衷,本就是源自对周遭环境毫无动机地观赏,“我就专注地注视着游虫;甚至可以说,多少是这景象使我萌生写《沼泽》的念头:一种徒劳无益的观赏之感。”(安德烈·纪德,2016:29)并把这样的观赏赋予了他笔下的主人公蒂提尔。作家“我”时而认为他笔下的主人公生活在沼泽的高地上,徒劳的观赏会使他幸福,时而又向周围的朋友提出这种毫无动机的生活让人麻木无知。通过否定自己的前后主张所呈现的情节矛盾,更体现出主人公的徘徊犹豫。
如果作家“我”面对温水煮青蛙的生活,还有是否需要奋力改变的犹豫,那他周围的朋友,则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生活的欺骗。当作家“我”竭力想让安日尔看清生活的循环往复不过单调乏味时,遭到了于贝尔的劝阻,“如果她这样挺幸福,你干吗去搅扰她……你要让她睁开眼睛,你不遗余力做的结果,不就是让她感到不幸吗?”害怕丧失既得的幸福而不去改变,看到真相却犹豫不前。做沉默的大多数,是当时人们的普遍选择。纪德的目的是唤醒沉睡在死水般生活的人们,重新给予人们追求自由的意识。于是,“无动机行为”在另一个意义上,并不是没有动机,而是更深层次的反抗。
(三)逃逸线——主动反抗、拯救自由
德勒兹和加塔利都用强度表示无器官身体对欲望的需求程度,最佳强度是0,“‘无器官身体’将首要空间留给强度,使事物从强度0开始生产。”[9]逃逸线就是“无器官身体”的最佳强度,是0。“逃逸线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力量,它在僵化的社会机制和扭曲的权力建构中具有冲破藩篱的势头。”[10]逃逸并不是躲避,而是创造与生成,是对既存制度的背离和反抗。纪德在《沼泽》中借哲学家之口道出了“无动机行为”的本质,“先生,您所说的自由行为,照您的意思,我看就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行为。”(安德烈·纪德,2016:42)无动机行为并不是真的没有动机,通过毫无目的的行为,纪德追求的是不受限制的欲望。纪德在一封回信中曾写道:“任何事物都有动机,我描写的是一种表面上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这种行为受到一股莫名的鼓动,这样的人倾向于反抗和背离。”[11]所以,《沼泽》中作家“我”想去旅行,去哪却没做计划,“动身就是动身,单纯得很:出乎意料本身就是我的目的。”(安德烈·纪德,2016:36)看似没有动机的旅行,本身就是对传统旅行意义的打破和对自由的追求,是作家“我”打破束缚的精神逃逸。
《沼泽》的情节高潮在安日尔举行文学集会的晚上,狭窄的房子里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作家“我”在向朋友介绍自己的书时,将自己的书比作一颗蛋,“一本书,于贝尔,像一只蛋那样,封闭、充实而光滑……蛋不是装满的,生下来就是满的。”(安德烈·纪德,2016:38)这与“无器官身体”不谋而合。德勒兹将“无器官身体”用“卵”来表示,“无器官身体”就是卵,是纯粹强度之地。“无器官身体像蛋那样,并不前于有机体而存在,而是与有机体毗连,并且持续地处于建构自身的过程中[12]”卵就是一个光滑的蛋,摆脱了与外界所有的有机联系,自给自足。就如同人的欲望,由内向外的扩展,不断生成。无动机行为致力于打破外界(蛋壳以外的压力)的束缚,不因阻力而消散。只有逃逸线上的人才具备这样的原生力量,不受世俗规则的束缚并竭力冲破藩篱。文学集会结束后的晚上,“我”做了很奇怪的梦,梦到了睡莲、丝绒。他还梦见自己在一个满是走廊和关闭的门的大房子里,一群文学家追在自己身后。“我觉得他鼓动起安日尔的所有客人来追我。这么多呀!这么多呀!文学家……啪!又是一道关着的门。啪!噢!难道我们永远也走不出去吗,出不了这走廊!”(安德烈·纪德,2016:55)弗洛伊德认为,梦应当被解释为一种愿望的达成,睡莲是美女的象征,丝绒则是欲望的典型代表,作家“我”的梦象征着作家潜意识中对欲望的追求。“我”将作品比作一个光滑的蛋,也是纪德“全欲”生活在作品中的表现。(安德烈·纪德,2016:12)而一道道关闭的门,走不完的狭长走廊和让人窒息的房间,都是现实中规则的束缚以及文人之间的虚假吹捧和追名逐利。梦醒之后的“我”甩掉束缚在身上的被子(被子在这也是束缚人的本性与自由的象征),感觉清凉舒爽,“我猛一用劲儿,将被子掀起来,接着一下子全蹬掉了。房间的空气围住我:均匀呼吸……凉爽……”(安德烈·纪德,2016:55)此时的作家“我”经过自我怀疑和周围朋友的反向刺激,跨过了徘徊犹豫的阶段,站在了争取自由的逃逸线上,实现了自己的精神逃逸之旅。
三.“无动机行为”中的微型社会与“无器官身体”的诉求
一如其他作品中那样,纪德在《沼泽》一书中加入了很多现实元素。虚构的文学作品在纪德这犹如一面面镜子,折射着真实生活中五光十色的场景。“无动机行为”中的微型社会也是纪德所处环境的真实写照。纪德借作家“我”道出了自己的艺术观,“艺术就是相当有力地描绘一个特殊的题材,以便让人从中理解它所从属的普遍……想一想眼睛靠近门锁孔所看到的广阔景物……某个人看这仅仅是个门锁孔,但是他只要肯俯下身去,就能从孔中望见整个世界。”(安德烈·纪德,2016:46)纪德认为,艺术就是通过特殊表现一般,关注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他曾在日记中透露自己要举办文学集会的梦想,“一个精致的客厅,由小玛德莱娜和我主持。所有艺术家都来做客。”(安德烈·纪德,2002:65)这个梦想就以无情嘲讽的形式,在《沼泽》的高潮部分得到了再现——现实中的文人只会装模作样地谈论无关痛痒的话题。纪德也借《沼泽》一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步入高速发展时期,人们不断为责任所累,被世俗琐事绑架、失去自由的现象,“凡是经过我们手做的事,仿佛都得由我们维护延续:从而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怕事情做多了负担太重,因为,每个举动一旦完成,非但没有变成我们的一个启动器,反而变成凹陷的床,邀我们又倒下去——又倒下去。”(安德烈·纪德,2016:49)在《沼泽》中,作家“我”称人们的这种行为叫“回顾病”,现实中也是如此。人没有一刻是为当下而活,既要维持昨日的成果,就得了患得患失的病,必须花费今天去检查,重复地做同一件事。更不必谈有多余的精力去反抗、改变。“整个外界,法律、习俗、人行道,似乎决定我们的重复动作,规定我们的单调行为,而其实,这一切又多么投合我们喜爱重复的心理”(安德烈·纪德,2016:50)于是安常处顺,便是贪图安逸的人们最好的选择。“无动机行为”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们毫无动机的生活的戏仿,来反抗消极接受的生活状态。纪德从无动机入手,强调了人的自由本质,“无动机行为”其实就是极端的自由,是纪德的“全欲”生活。
“欲望在法文中写作désir,它来自法语动词désirer。而désirer于11世纪末源出拉丁文desirare,其原本意义为‘对缺乏者的抱憾’。”[13]德勒兹认为欲望不是欠缺,而是从内到外的生成。德勒兹认为“无器官身体”的身体是积极的欲望,是从内到外的不断生产,身体为欲望提供了发生的平面。在平面(如原野、沙漠)中,一望无际,没有方向,欲望可以自由奔驰。《沼泽》中有很多视野开阔的平野,如“我穿越了大片荒原,辽阔的平野,无边无际,”(安德烈·纪德,2016:34)也可以理解为主人公身处无边欲望的诉求。在欲望中穿梭的逃逸线通过对身体的不断解码,不断生成差异化、新奇的身体。作家“我”笔下的主人公蒂提尔,是维吉尔诗中的人物,他也是“我”的朋友理查德,甚至是“我”自己,“蒂提尔,是我,又不是我;蒂提尔,是那个傻瓜,那是我,是你……是我们大家……”(安德烈·纪德,2016:42)纪德打破蒂提尔原来的身体界限,让他成为任何一个可能,赋予蒂提尔巨大的张力潜能,成为欲望的代言人、“无动机行为”的实践者。
结语
“无动机行为”一方面通过模仿现实生活中人们机械性地重复,毫无动机的生存状态,用讽刺地手法表达了毫无动机行为的荒诞性。另一方面通过打破对世俗规则的习惯顺从,突破凡事都要有动机、有计划的僵死状态,寻求意料之外的偶然性。“无器官身体”通过克分子线、分子线、逃逸线概括出人们在欲望面前的生存状态,其中逃逸线最终通往“无器官身体”,同样注重对偶然性的追求。“逃逸线的构想,或者说无器官身体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个不断创造和流变的多样化身体,这样的身体,不是站在制度的对立面,而是摒除了不合理的现状,使社会涌现多元。”(石燕:213-218)《沼泽》中人们对待死水般生活的消极态度,正是需要“无器官身体”去打破重建的。通过“无器官身体”分析《沼泽》中人物的“无动机行为”,进而分析主人公“我”的精神逃逸路线,是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对纪德作品的全新解读和哲学理论应用于文学分析的全新尝试。当然,笔者哲学背景还比较薄弱,分析中还需加强去伪存真的能力,力争理论与文本做到水乳交融。
[1]葛雷:《意味无穷的“沼泽”——读纪德的小说“沼泽”》,《国外文学》,1989(02):174-178。
[2]朱静等:《纪德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184页。
[3][法]安德烈·纪德:《纪德文集·日记卷》,李玉民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482页。
[4]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0, p. 191. 笔者译。
[5]胡新宇:《德勒兹差异哲学与美学研究》[D],复旦大学,2012年。
[6]李震,钟芝红:《无器官身体:论德勒兹身体美学的生成》,载于《文艺争鸣》,2019(04):98-109。
[7][法]安德烈·纪德:《世界文学名著名译文库纪德集:梵蒂冈的地窖》,陈筱卿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47页。
[8] Léon Pierre and Quint,. Paris, Stock, 1932, p. 161.
[9]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 326-327. 笔者译
[10]石燕:《身体的“逃逸线”之旅:论《西游记》的群魔变形故事》,载于《浙江学刊》,2019(01):213-218。
[11] Jean Maisonneuve,. ERES, 2009/2 n° 92, p. 193-199.
[12] Adrian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2-34.
[13]于奇智:《欲望机器》,载于《外国文学》,2004(06):60-65。
西安外国语大学2019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安德烈·瓦尔特笔记》的互文性解读,项目编号:SSYB2019102。
(责任编辑: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