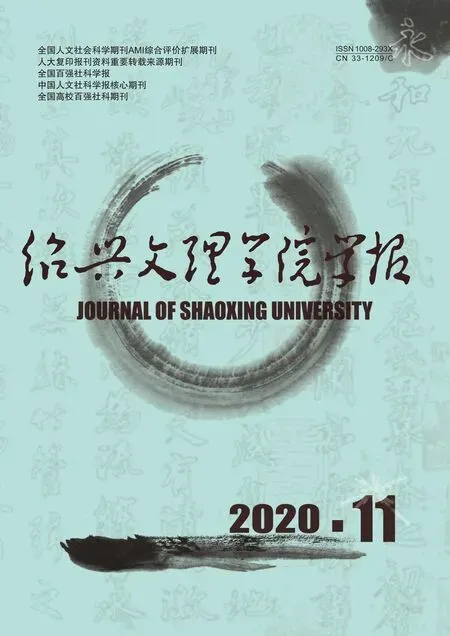论陆游乡居诗与宋代戏剧
——以浙东运河、鉴湖流域为中心
赵豫云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大运河研究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浙东运河位于中国大运河南端,自杭州南延伸至浙东的绍兴和宁波,是一条“穿越宁绍平原全境的濒临后海杭州湾的通江达海运河”[1]183。按历史时期,自西向东分别由西兴运河(西晋始凿,西兴至绍兴城)、“山阴故水道”(出自《越绝书》,春秋越国始创,东汉起纳入鉴湖而成鉴湖航道,绍兴城至曹娥江)以及曹娥江至入海口招宝山的渠化水道(始建于南朝宋以前的梁湖埭渠化工程和天然河流姚江、甬江)三部分组成。南宋“以南方都会为全国交通中心”[2],鉴湖、浙东运河成为“国家级主航道”[1]9,是浙东运河的最辉煌期。
陆游生于淮上,长于水乡,归老鉴湖,终生与水、船有莫大的因缘。浙东运河特别是鉴湖流域也是其诗充分展现的重点(1)陆游鉴湖诗部分笔者主要选取其地理空间紧邻浙东运河航道者。鉴湖并非完全的天然湖泊而是一项人工水利工程。浙东运河的前身是凿于公元前5世纪的山阴故水道,于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被纳入鉴湖之中。宋代鉴湖分为西湖航道和东湖航道。在南宋绍熙五年(1194)鉴湖衰落,鉴湖运河航道演变成漕河、会稽段运河。陆游故乡“三山”(韩家山、石堰山、行宫山)等地大多紧邻鉴湖、浙东运河航道。。陆游乡居期间,时常行旅于浙东运河沿线,以及因追忆故园,写有大量反映绍兴一带戏剧演出等文娱活动的诗篇。陆游乡居诗是研究绍兴地域文化的宝库,但因数量庞大,学界在深度整理研究上尚显欠缺。因此,有必要从浙东运河、鉴湖角度,对其从戏剧史上进行一番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一、浙东运河沿线的民间歌舞、民俗演出和民间说唱
绍兴一带在东汉后持续的水利建设和改造,得以形成六朝后的物质富裕、文化昌盛局面,其与北方中原文化不断融合。建炎南渡后,绍兴更成为南宋京畿之地,浙东运河成为可以直接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级航道。参与过《嘉泰会稽志》修订工作的陆游有云:“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莫敢望也!”(2)见陆游:《嘉泰会稽志》“序”,出自施宿撰《嘉泰会稽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丰厚的经济实力和便利的中外交通使绍兴可以成为宋代戏剧传播和戏曲形成的“桥头堡”、引擎城市。
陆游所处的南宋初、中期正是宋杂剧、诸宫调等演出伎艺南传和南戏的形成、发展时期。绍兴等江南地区民间艺术也在进步,民俗表演等文化娱乐活动盛行。陆游乡居诗中就有不少关于浙东运河和鉴湖沿线草市镇及农村文娱演出的生动描摹,充满了市井气息和农村风味。陆游在中国古代大诗人中乡居时间最长,且勤于出游观察,是比较罕见的长寿者。因此,长时间跨度的、大量的陆游诗歌,能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浙东运河沿线的商业和文娱活动,具有诗史意义。
(一)与戏剧有血缘关系的民间歌舞、民俗演出等文娱活动,如渔歌、赛神、傩戏等
1.渔歌、菱唱等民间自娱性歌舞活动
南宋时的绍兴农村有老少男女都喜歌、舞的习俗,特别在丰收或春社等节日、喜庆时刻,类似今日的少数民族地区或日本乡村。陆游亦有诗“十里烟波明月夜,万人歌吹早莺天”(3)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27页。本文所引陆游诗,均出自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简称《诗稿》),下文所引陆诗仅随文标明所属卷数及诗题,不再赘列版本信息。。(《诗稿》卷二十一《故山》四首其二)平日里则有渔歌、菱唱等活动。
渔歌是船郎、舟子行舟时的唱橹之歌,菱歌多为渔家女采菱时所唱,渔歌、菱唱应与唐代流行的“踏歌”(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类似今天的秧歌曲)一样,都是渊源于古代劳动人民的“劳者歌其事”。宋代绍兴府尤其是浙东运河沿线地区,渔歌在民间非常盛行。陆游《新秋往来湖山间》(四首其四)云:“渔歌相和苇间起,菱船远入烟中去。”(《诗稿》卷七十二)是白日发生的可以对唱的渔歌。《夜泛蜻蜓浦》亦有:“烟浦渔歌断,芦洲鬼火明。”(《诗稿》卷十七)则是在夜半三更听到的渔歌,可见在绍兴水乡渔歌几乎随处、随时都可演唱。
鉴湖烟雨中的菱唱更显悠长缥缈、韵味隽永,陆游对此赞誉有加,“烟艇满目菱歌长”(《诗稿》卷十八《丙午五月大雨五日不止镜湖渺然想见湖未废时有感而赋》),“菱歌缥缈泛烟津”(《诗稿》卷二十八《镜湖女》)等。有时“菱歌”在陆游诗中类似一种背景乐,如他写于鉴湖堤岸、运河江畔的《湖塘晚眺》(二首其二)曰:“烟中卖鱼市,月下采莲舟。帆鼓娥江晚,菱歌姥庙秋。”(《诗稿》卷四十六)
陆游甚至自己也亲自创作“渔歌菱唱”,如淳熙十六年(1189),陆游在为他的词集自序时说:“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3]可见南宋时流行于民间的“渔歌菱唱”同宋词一样,也是一种音乐文学,也可由文人参与创作。
渔歌菱唱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型船上自娱性歌舞。陆游自己也时常以歌舞自娱。他在淳熙十二年(1185)于山阴奉祠(领半薪)时所作词:“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叶船。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4](《渔父·灯下读玄真子渔歌因怀山阴故隐追拟》五首其三)镜湖湖面碧波如镜,如同玻璃万顷,陆游不禁欣然起舞。
中国戏曲相较西洋而言是独特的歌舞剧,它在以歌舞戏、滑稽戏为主体的基础上综合吸收了各色艺术,包括舞蹈、美术、诗、词、歌、赋,甚至音乐、杂技、武术等,在北宋晚期得以初具雏形并渐趋成熟。南宋绍兴自汉、六朝以后开始盛行的渔歌、菱唱等民间音乐、歌舞也是戏曲形成、发展时期的重要汲取对象。
2.赛神、傩鼓、竞渡等祭祀、节日类民俗表演
陆游所在的绍兴,逢节庆、丰收时日,农村会自发地举行各种文娱活动,如赛神、傩舞、龙舟竞渡等,这也是浙东民间固有的、广受欢迎的祭祀、民俗活动表演。
首先,“赛神”实为祭神,亦称赛社。社日多是在农闲时以酒食祭祀土地神,并“集中在土谷庙议事,举行庆祝、演剧活动”[5]。汉代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始有秋社。宋代起,社日一般在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间或有四时致祭者。从《剑南诗稿》中的赛神诗可知社日一般在社庙等地举行,除祭祀外还常伴有笙、箫、鼓等集体性的歌舞活动,其费用即“社钱”一般是村中长者或祭祀祠庙的工作人员通过村民集资的方式收取。因此,南宋时的“社”是一个村庄集神、人活动于一体的祭祀(祭土地神)兼娱乐(如喝社酒、分社肉等)活动。
陆游作于乾道三年(1167)的《游山西村》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诗稿》卷一)山西村在鉴湖三山、运河航道附近。此诗不仅叙写了风光旖旎的江南山村,还使读者感受到绍兴春社来临前文化氛围(包括音乐以及其他仪式等)的浓厚,以及古朴的乡村民俗。也有夜晚演出即“夜场”的春社,如写于庆元四年(1198)冬的:“比邻毕出观夜场,老稚相呼作春社。”(《诗稿》卷三十八《三山卜居今三十有三年矣屋陋甚而地有余数世之后当自成一村今日病少间作诗以示后人》二首其一)
作于嘉泰二年(1202)的《夏初湖村杂题》(八首其四):“听残赛庙咚咚鼓,数尽归村只只船。”(《诗稿》卷五十一)是夏季的赛社活动。又有《镜湖女》:“日暮归来月色新,菱歌缥缈泛烟津。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湖桥看赛神。”(《诗稿》卷二十八)应也是在夏季于跨湖桥举行的社日活动。
秋社在陆游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社日是为祭祀,首先是巫的活动,巫是神意志的替身、传达者。陆游淳熙十一年(1184)秋作于山阴的《赛神曲》诗云:
丛祠千岁临江渚,拜赐今年那可数,须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辄许。嘉禾九穗持上府,庙前女巫递歌舞。呜呜歌讴坎坎鼓,香烟成云神降语。大饼如槃牲腯肥,再拜献神神不违。晚来人醉相扶归,蝉声满庙锁斜晖。(《诗稿》卷十六)
诗中作祭的土谷祠(社庙)“临江渚”,濒临浙东运河、鉴湖,即明清后的“行宫庙”(4)绍兴“行宫庙”同陆游故乡三山之一的“行宫山”,其得名已不能确考,或曰与建炎南渡中宋高宗沿浙东运河南逃有关,或曰因清乾隆帝沿运河下江南设行宫于此而得名。,近柳姑祠。女巫击鼓又载歌载舞,持代表丰收的九穗嘉禾上祭礼,缭绕成云的香烟中替神“降语”。又有嘉泰元年(1201)所作《秋社》诗:“雨余残日照庭槐,社鼓咚咚赛庙回。又见神盘分肉至,不堪沙雁带寒来。”(《诗稿》卷四十七)是鉴湖在秋社日举行的民俗演出。《霜降前四日颇寒》:“儿童锄麦罢,邻里赛神回。”(《诗稿》卷六十八)则似是深秋时节的秋赛活动。
冬季是一年之末,冬社场面也十分庄重、热闹,陆游在绍熙四年(1193)冬所作《赛神曲》:“老巫前致词,小姑抱酒壶: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神归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诗稿》卷二十九)是鉴湖一带农村在夜间冬社的祭祀盛况。祭祀结束后还有众人的歌舞演出,“夜深歌舞官道隅”,证明这是场祭祀和娱乐结合的娱神娱人的民俗活动。
其次,村巫之外,还有乡傩。“傩”是古时民间驱鬼逐疫的一种仪式,傩舞是祭祀仪式中的一种舞蹈。傩戏是在傩舞的基础上吸取民间歌舞、戏剧而发展成的一种戏剧形式。傩戏滥觞于商周时的方相氏驱傩活动,汉以后,渐发展成具浓厚娱人色彩和戏乐成分的礼仪祀典。于宋代前后,受到民间歌舞、戏剧的影响,傩仪开始衍变为旨在酬神还愿的傩戏。傩戏是民俗、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陆游乡居期间出现“傩鼓”的词有1首,即《朝中措》:“咚咚傩鼓饯流年。烛焰动金船。彩燕难寻前梦,酥花空点春妍。”是于岁腊前一日举行的击鼓驱疫活动。诗则有6首,如《舍北晚步》:“漠漠炊烟村远近,咚咚傩鼓埭西东。”(《诗稿》卷三十八)是运河水上建筑——“埭”附近开阔地带的“傩鼓”表演。乡傩除了傩鼓,还应伴随简单的歌舞等戏剧表演。陆游作于庆元元年(1195)的《岁暮》诗就说道:“太息儿童痴过我,乡傩虽陋亦争看。”(《诗稿》卷三十四)
再者,江南绍兴一带的龙舟竞渡,其文化渊源和南方一些省份如湖南的祭祀屈原不同(也有学者认为龙舟竞渡习俗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乃是纪念大禹的生日,如“二月镜湖水拍天,禹王庙下斗龙船”[6]。(《吴娃曲》四首其三)所写的就是在传说中的大禹生日(农历三月初五)举行竞渡龙舟的节日场景。
此外,“下湖(乘舟入湖),也指越地的一种祭祀风俗”[7]。大禹生日,乡民需备酒食、乘画舫,设歌舞去拜祭禹庙,名为“下湖(鉴湖)”。陆游诗《阿姥》:“城南倒社下湖忙,阿姥龙钟七十强。犹有尘埃嫁时镜,东涂西抹不成妆。”(《诗稿》卷四十三)这类节日祭祀,娱人也娱神,民众可以亲身参与。《上巳书事》诗亦有“单衣初著下湖天,飞盖相随出郭船”句。(《诗稿》卷三十二)“下湖”虽是为了祭祀大禹,但显然也带有市民狂欢的娱乐性质,甚或有戏剧的成分。
(二)商业性质的、有组织的堂会歌舞演出和民间说唱,如堂会伶人的画船宴会演出、诸宫调、陶真等
绍兴以船为家,因此北方在茶楼和私宅举行的商业性的堂会歌舞演出,绍兴则时常在楼船、游船上举办。《湖上今岁游人颇盛戏作》(四首其二):“画船鼓吹载凉州,不到三更枉出游。忽有歌声出霄汉,谁家开宴五云楼。”(《诗稿》卷三十五)是鉴湖楼船上的宴会演出。
南宋浙东一带,草市镇密集分布。陆游《野步至近村》(《诗稿》卷五十七)云:“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平民的文化娱乐日趋丰富,乃至乡村的草市镇也遍布娱乐场所,艺人聚集。体育活动蹴鞠在农村青少年中也较流行,如《残春》(二首其一):“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诗稿》卷六十一)另如《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首其四)诗: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诗稿》卷三十三)
“赵家庄”即“赵家畈”,在山阴道上,距陆游故居“三山”约二十里,也是水乡。此诗是描写流动说书艺人傍晚在村头古柳下负鼓表演,离奇的故事吸引了众村民围观的景象。盲翁所说“蔡中郎”为文学作品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主人公蔡邕(蔡伯喈),此故事讲述蔡伯喈及第后抛弃妻室、父母,入赘牛相府的负心事(与蔡邕的史传不符,故陆游说已属是非惹身)。南宋时流行于南北,除南戏外,还有院本、盲词等,文俱已不传。
“负鼓盲翁正作场”是由主唱者自己击鼓并伴奏、定拍,且一人说唱到底,所上演的应是诸宫调等说唱表演艺术(5)龙建国:《诸宫调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考证后认为这一说唱伎艺为诸宫调。笔者亦认为当属诸宫调、陶真等说唱演出,而不是一些论者所说的事实上明代才有的鼓词,也非流行于北宋文人士大夫宴会之中而南宋业已衰落的鼓子词。。此诗作于南宋中期光宗庆元元年(1195),诸宫调则是诞生于北宋中期汴京的北方民间说唱伎艺,随着高宗南渡和北人南迁早已南传至浙东一带,前一年的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也正处于南戏兴起的阶段。诸宫调对南戏形成、兴起的直接影响,学界早有论证。陆游所在的运河城市绍兴在诸宫调的传播和南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于此也是一例明证。
二、浙东运河沿线专业和商业化的戏剧、戏曲演出
除了前述的民间歌舞、民俗演出和民间说唱之外,陆游乡居诗中的浙东运河、鉴湖沿线,还存在较专业化和商业化的戏剧、戏曲演出,如参军戏和民间村伶、老伶的“夜场”等演出以及较商业化的“优场”“戏场”,证明在南宋绍兴一带,专业化和商业化的戏剧演出业已较流行和普遍,也说明戏曲之乡的绍兴有悠久的传承历史。
(一)参军戏
浙东运河、鉴湖一带自古多丰年,是富庶之乡。建炎南渡后,宋王朝宗室、显贵多有在绍兴购置田产。北方人口大量迁入,人口更为密集。加之距离行在临安较近、交通方便,戏剧演出也得以迅速传播。陆游有《春社》(四首其四)诗:
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诗稿》卷二十七)
可见绍兴一带戏剧氛围之浓厚,在山阴农村热闹的春社日,还有参军戏的上演。参军戏是一种以滑稽问答、讽谏为主的戏剧形式,盛行于唐,“至宋代还盛演不衰”,但“在杂剧已经兴起的宋代,参军戏已经开始融入杂剧”[8]。主角(参军)和配角(苍鹘)的逗笑、滑稽演出,时常使儿童们欢喜异常。绍兴府地区“处处是优场”的艺术土壤和戏剧文化氛围,也为南戏兴起、传播创造了条件。诗中的“京都新禁舞斋郎”之《舞斋郎》应是指根据北宋开始流行的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南戏,主人公“舞斋郎”(6)“斋郎”,本为官名,是掌祭祀的小吏,亦为宋代舞队名。宋人将役使虫蚁(虫和小的鸟雀)戴着面具跳舞者曰“舞斋郎”。是宋真宗时期保州(今保定)的一个“弄虫蚁”(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的杂耍艺人,名唤赵二十七郎,后从军。此戏意在褒扬爱国抗辽、恢复故土。《舞斋郎》南戏当时盛行于杭州,但大约是与当时主政者的主和政策相悖,故遭到了禁演。
徐渭《南词叙录》言:“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甚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9]宋光宗朝也即绍熙年间(1190—1194),是陆游的66岁至70岁,此时他寸步未离故乡。陆游《春社》诗中“参军”所讽的“京都新禁舞斋郎”戏文,即是“宋光宗朝被禁演的‘戏文’,是南戏正式形成的标志”[10]。宋光宗朝,南戏由民间传入杭州、绍兴等运河城市,特别是在杭州等地盛行后出现了专业编演团体,已从话本和诸宫调等说唱伎艺中吸收充足养分,发展成大戏而盛行,甚至遭到了禁戏。这是被称作“戏文”的南戏的定型阶段。绍兴府与杭州仅一钱塘江之隔,两地戏剧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甚至京都新禁戏文的事也很快传到绍兴。
(二)村伶夜场、优场、戏场演出
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的发展,特别是浙东运河沿线草市镇的勃兴,绍兴的一些城镇甚至包括陆游所在的近郊农村,市民意识和通俗文化兴起并传播,农村市场的农民也对文化消费有了一定的需求,开始出现一些较为商业性的村伶“夜场”“优场”和更为专业的“戏场”。
第一,陆游乡居诗中,寺庙里做夜场的“村伶”应为“堕民”,“优场”表演者应为“堕民”或路歧艺人。
村巫、乡傩的演出活动与戏剧、戏曲有“重则血缘,轻则边缘”[5]的关系,但因其本质上从属于或派生于祭祀,故仍依托于绍兴农业的丰歉和习俗。陆游所处时代绍兴府地区较接近戏剧或者说与戏曲血缘较近的演出,除村巫、乡傩、诸宫调等说唱艺术、参军戏之外,还有村伶、堕民的演出活动。
陆游诗中多次提到的“村伶”这一演出群体,其演出项目甚至演出形式由于叙述较略,已无从详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其演出为“戏剧”的可能性无疑很大,比巫、傩更接近戏剧、戏曲。如陆游作于庆元四年(1198)秋的《书喜》(三首其二):
今年端的是丰穰,十里家家喜欲狂。俗美农夫知让畔,化行蚕妇不争桑。酒坊饮客朝成市,佛庙村伶夜作场。身是闲人新病愈,剩移霜菊待重阳。(《诗稿》卷三十七)
以及间隔6年后,作于嘉泰四年(1204)春的《出行湖山间杂赋》(四首其二):
新酿学鹅黄,幽花作蜜香。客邀闲即去,病起醉何伤。野寺无晨粥,村伶有夜场。吾心静如水,随事答年光。(《诗稿》卷五十七)
两诗中“村伶”上演的皆为夜场,演出场地都在寺庙。表演的时间点似乎仍与农业的丰歉或者祭祀有一定关联。中国戏曲与神庙的祭祀活动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祭祀仪式中的表演活动是戏曲演出吸收的重要对象。那么绍兴“村伶”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在陆游诗中“村伶”的活动均与寺、庙(祭祀)相关,这自然令人联想到和尚班与道士班群体的道场、坐唱,而“村伶”的字意是乡村艺人,职业的和尚和道士通常不被称为“伶”。结合绍兴一带在南宋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陆游诗中的“村伶”应该就是在绍兴被称为“堕民”“丐户”“乐户”的群体。
可确定的是,“村伶”不是城市里的伶人,而是本村或附近村的乡土艺人。《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丐户以立夏日出鲜衣鼓笛相娱,非此类则以为耻。”“丐户就是越地的堕民,明清以后,堕民有以演戏为生者,称为绍兴乱弹,后来形成绍剧,其起源当是立夏鼓笛相娱的风俗。”[11]宋至明清的浙江方志如《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万历绍兴府志》等,以及鲁迅《我谈“堕民”》(《鲁迅全集·准风月谈》)一文对“堕民”均有记录,堕民遍及绍兴府治下八县,其在浙东运河沿线城乡皆有分布。所谓“堕民”,“谓之丐户,……男子则捕蛙、卖饧、拗竹灯檠……;正旦元宵执响器以闹人堂,立春、端午持土牛芒神以闯人室;九月社伙会参神送圣,迎灯走马;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脸,钟鼓剧戏,种种沿门需索……”(《乾隆鄞县志·风俗》)在节日鼓吹、演戏,平日做各种营生。陆游作于开禧三年(1207)春的“陌上吹箫正卖饧”(《诗稿》卷七十《春感》)和作于嘉定元年(1208)春的“陌上吹箫已卖饧”(《诗稿》卷七十五《春晴》二首其一),所写就是堕民。可见,“堕民”是兼做各种杂事、不入官的“乐户”。
至于陆游乡居诗中关于“优场”的描写则有四处较为典型。
其一是作于淳熙四年(1177)的《夜登小南门城上》:
野艇鱼罾举,优场炬火明。湖塘正如此,回首忆柴荆。(《诗稿》卷八)
诗后自注:“予故山在镜湖之南。”是于成都回忆绍兴鉴湖乡居生活的故园诗,“优场”的演出地在运河、鉴湖的湖塘一带。演出人员应是村伶(堕民),演出项目应是社火、百戏类。
其二是距上诗过后16年,作于绍熙四年(1193)的《春社》(四首其四):
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诗稿》卷二十七)
“太平处处是优场”是因光宗朝的绍熙年间,宋金休战已30年,政局也已稳定近60年,鉴湖一带水利和交通条件良好,经济恢复并发展,一片盛平景象。也表明在春社日,戏剧氛围非常浓厚。演出地在陆游故乡山阴的鉴湖农村,演出项目可能较多,有社戏、诸宫调等,演出人员应有村伶,以及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表演诸宫调等说唱伎艺的路歧艺人等。
其三是距上诗过后13年,作于开禧二年(1206)冬的《夜投山家》(四首其二):
夜行山步鼓咚咚,小市优场炬火红。唤起少年巴蜀梦,宕渠山寺看蚕丛。(《诗稿》卷六十九)
此诗既然题名为《夜投山家》,需投宿,证明离陆游此时住处三山等地较远,加之三山为较小的土丘,不足以称“山家”,因此演出场地应在距三山30里左右的兰亭、漓渚附近。“山步”为山脚、水滨的草市,因寻求商业市场的关系,绍兴乡村的戏剧演出常在浙东运河及其流域沿线的草市镇举行。诗中演出人员为村伶或“路歧”等流动人员,演出内容应为百戏等。
其四是在陆游去世前两年,即嘉定元年(1208)秋写于山阴的《野意》:
小雨荷锄分药品,乍凉扶杖看优场。此身已作农夫死,却愧时贤独未忘。(《诗稿》卷七十八)
是无意中提及了“优场”,从诗中语境可判断出“优场”演出并非一定在农闲时刻,从侧面也反映出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南宋近郊乡村,“优场”演出逐渐摆脱祭祀和民俗活动而具有一定的商业性。
上述陆诗,第一首至第三首,从诗人53岁到82岁,时间跨度近30年。似可证明这样相对简单的“优场戏”(应以百戏杂耍为主)上演频率不高,应已不太受看客欢迎了。综上可见,绍兴镜湖流域的“优场”表演者应为“堕民”或路歧艺人。前文有论的陆游诗中的诸宫调和参军戏,其演出人员的身份也应是宋代绍兴的“堕民”或路歧艺人群体。
第二,陆游诗中“戏场”里的演出极有可能是宋杂剧或南戏。
《剑南诗稿》里的陆游归居诗中出现“戏场”的共有7首,相对较多,且高频率地出现在其晚年,即70岁以后,这说明陆游诗中“戏场”的演出项目极有可能是宋杂剧或南戏。现将较具代表性的几首试做分析。
其一,陆游在庆元元年(1195)三月所作《初夏》(十首其二):
剪韭腌齑粟作浆,新炊麦饭满村香。先生醉后骑黄犊,北陌东阡看戏场。(《诗稿》卷三十二)
演出时间在初夏时节,演出地点在农村的开阔场地,演出项目应是百戏、杂剧等。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所列“百戏”项目有:“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又载:“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12]“村落百戏之人”应是宋代的乡村“路歧艺人”,其表演技艺水平要比城市的勾栏瓦市次一些,是流动戏班。“构成中国戏剧的三大要素——歌舞、百戏、故事是南戏诞生的远源。”[13]南宋浙东运河、鉴湖一带演出百戏等项目的“戏场”也为南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二,陆游在嘉泰四年(1204)秋所作《村居遣兴》(三首其一):
追数交朋略散亡,臂孱足蹇固其常。一年又见秋风至,孤梦潜随夜漏长。不办诵书如倚相,颇能啖饭胜张苍。回看薄宦成何味,只借朝衫作戏场。(《诗稿》卷五十八)
诗中“只借朝衫作戏场”非实指,而是借“戏场”为素材别有寄托。但能有如此表达,显然也是因为当时“戏场”演出已在浙东一带较常见,因而有这样的类比。
其三,陆游在开禧元年(1205)冬作有《稽山行》:
禹庙争奉牲,兰亭共流觞。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诗稿》卷六十五)
“社”是居民组织,《周礼》以二十五家为一社。“倒社观戏场”意为几乎全村的人都去了“戏场”看戏。其演出场地应在村庄的空旷处,演出规模大,演出项目应也较繁多,可能有杂剧等。陆游所处时代的镜湖农村文娱项目多与节日、祭祀、竞渡等集体活动紧密结合,也说明戏曲与神庙祭祀的渊源。
其四,陆游在开禧二年(1206)夏写有《初夏闲居》(八首其三):
高城薄暮闻吹角,小市丰年有戏场。白首史官闲尽岁,只将搜句答流光。(《诗稿》卷六十六)
演出地点为某“小市”。镜湖和浙东运河沿线“小市”密布,通常为村店、山店等,规模有限、营业时间较短,只售卖一些简单的农副产品,与商品丰富、规模较大、营业时间长且多位于交通枢纽的大市差别很大。演出规模和项目应比较小和少。
开禧二年(1206)秋又有《行饭至湖上》诗:
行饭消摇日有常,青蛙又到古祠旁。残芜满路无多绿,落叶投空不待黄。只道诗书能发冢,岂知博簺亦亡羊。此身只合都无事,时向湖桥看戏场。(《诗稿》卷六十八)
诗中“湖桥”指今东跨湖桥(7)指偏门即常禧门外之跨湖桥。偏门即陆游诗中的扁门,扁通“偏”,为僻远之意。除陆游诗外宋代无方志意义上的“东跨湖桥”。邹志方《陆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亦言:“陆游所写(跨湖桥和湖桥)大多为(今)东跨湖桥。”因参照系(以别业或府城)不同,陆游诗中常见的“东跨湖桥”实为《嘉泰会稽志》中的“西跨湖桥”,位于府城偏门(常禧门)外、镜湖南塘,距陆游三山仅数里,古桥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今已不存,现为钢结构混凝土面跨湖桥梁,并非清康熙十年(1671)的《山阴县志》始有载录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距陆游三山二十几里的柯桥湖塘跨湖桥。现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绍兴古桥群中的“西跨湖桥”,是清代方志中所称的“湖塘跨湖桥”,非宋代古桥、偏门外的西跨湖桥。,属南宋时镜湖流域较大的市镇(另如柯桥、漓渚等)之一。“古祠”即“马太守庙”,在鉴湖之滨、跨湖桥以南,通往“山阴道”官道,是为纪念创立鉴湖水利工程而冤死的东汉会稽太守马臻而建的祠庙。“时向湖桥看戏场”中“时向”二字,说明“东跨湖桥”这样的“戏场”演出是常态化的,也较那些村伶演出的“优场”更加商业化、专业化,演出项目应有杂剧甚至南戏等。东跨湖桥距离陆游三山别业仅数里路程,因此可以频繁来这里看戏。
浙东运河上的、绍兴“偏门”外的东跨湖桥(按:在陆游诗中有时亦称“长桥”)在南宋时经常有各种演出活动,如“到处更约西邻女,明日湖桥看赛神”(《诗稿》卷二十八《镜湖女》)的夏日赛社表演,以及“云烟古寺闻僧梵,灯火长桥见戏场”(《诗稿》卷五十九《出游》五首其四)的秋日戏场表演等。
其五,陆游在嘉定元年(1208)冬所作《幽居岁暮》(五首其三):
巷北观神社,村东看戏场。谁知屏居意,不独为耕桑。(《诗稿》卷八十)
演出场地是在“村东”的开阔处,与“神社”并列,可见诗中“戏场”的演出项目应不属祭祀表演,但这种娱乐项目又与“神社”的祭祀活动在时间点上相一致或相衔接。演出人员可能是堕民或路歧艺人,演出项目可能有杂剧等。
比较上述诸多诗作可发现,陆游“戏场”诗的写作集中在陆游的晚年(从71岁到84岁)且诗中戏场演出频率越来越高即相隔年数越来越短,从1195年到1204年的相隔9年,从1205年至1206年的相隔1年,甚至1206年的一年两次。演出场地不在“社庙”(按:“优场”则多有在“社庙”举行的),而在乡村的开阔场地,如“北陌东阡”“村东”或市镇、区域的交通枢纽(东跨湖桥)等。而陆游70岁以前的诗没有一首涉及“戏场”,这应不属巧合,陆游的诗歌有诗史和方志性质,陆游对新生事物极其敏感并会及时反映到诗歌里。
整体而论,“戏场”的演出项目和演出艺术形态要比“优场”更为高级且常态化,演出宋杂剧和南戏的可能性很大。从戏曲史上看,绍兴人徐渭说:“南戏始于光宗朝”,是他认为的最迟时间,应有依据。宋光宗朝时南戏已经兴起、定型并已由温州传至杭州、绍兴等地,而陆游故乡在浙东运河沿线并不闭塞。陆游关涉“戏场”的诗作也全部作于宋光宗朝后,只是其中对戏剧的描写太过概略,是否为南戏还有待找到具有说服力的明证。
三、结语
从交通和地域来看,浙东运河沟通了钱塘江、钱清江、鉴湖、平水江(若耶溪)、曹娥江(剡溪)、姚江、甬江等,沿途城市绍兴、明州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更便于吸收外地甚至国外的戏剧文化,如南戏就有受印度梵剧影响说。
陆游之前,包括“浙东唐诗之路”留下的那些唐人诗篇,极少涉及绍兴一带的民俗和戏剧等文艺活动,即使是大多宋代浙东籍诗人也较少对之用心体察,只有长年乡居、大量记录的陆游,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可供研究的作品。陆游存诗近万首,据笔者初步统计,其7500余首乡居诗中,可明确判断出以浙东运河、鉴湖航道附近地理空间为创作背景的在300首以上,其中大部分又与他的故乡鉴湖有关。陆游在他34岁入仕前和65岁退隐后的大部分时间居住、活动在其家乡绍兴府境内,再加其仕途蹭蹬,多次被免官也间有归居乡里,过着一段较为漫长的农村田园生活,可说是中国古代大诗人中乡居时间(约占其生命的三分之二)最长的。因而,陆游乡居诗中反映的戏剧等文娱活动,涉及南宋前、中期极其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值得关注。
陆游乡居诗中留下的南宋浙东运河和鉴湖沿线草市镇和农村的戏剧、文娱演出的宝贵资料,可使我们沿着他留下的一些履迹,探究在绍兴府市镇和农村地区民间戏剧表演的场地和分布范围,为研究宋代戏剧、戏曲的传播、发展提供一些史料之外的辅助资料,既有利于了解南宋浙东地区的水利、地理、民俗、文化,也有利于深入开掘陆游乡居诗对戏剧史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