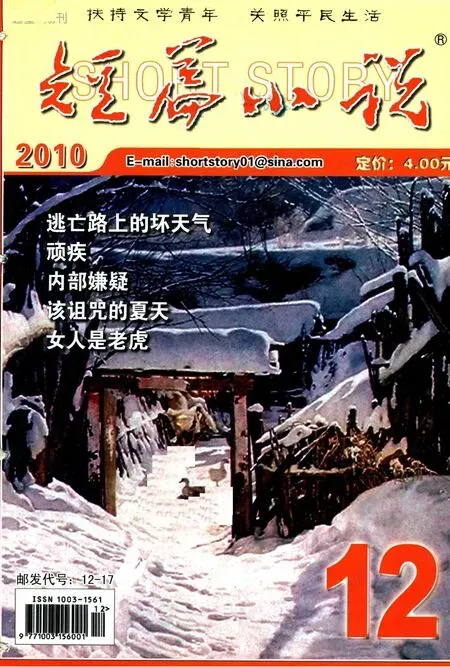惊悚之恋
◎陶诗秀

01
周一的时候,和国钊约好周五见。
已经三年了,没有见过他。自从他去美国之后,我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他要留美的消息很突然,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他突然宣布下个月就要去美国。而我,跟他交往了三年,居然是在这样的场合,和大家一起知道这个消息。
我当然不平衡,但我没有质问。因为这三年,我们的关系早已从如火如荼进入了平稳期,继而有些不咸不淡。关系还维持着,似乎谁也不愿意捅破那层纸,但我们都心照不宣:分手,似乎只是早晚的事。
但我仍然有些不平衡!好歹也是有过亲密关系的,三年,不是短时间啊!三年里,我们有过甜言蜜语,有过一起流眼泪、一起欢笑的镜头。我们是真心爱过的,甚至还讨论过今后的婚姻和孩子……但这一切最后也都成了过往烟云。
三年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爱情是永恒的,但爱的对象不是。这和一日三餐一样,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实,可往往大家都视而不见,仍然前仆后继地飞蛾扑火,以身试法。
记得他走的前一天,我和他最后一次约会。他把他单身宿舍里的一些零碎物件给了我,其中包括一个握力器、几张电影光盘。有几张是我们一起看过的,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除了这些,还有几支半旧的画笔。
国钊喜欢画素描,就像《铁达尼号》里的杰克一样,可是他却一张也没给我画过。我曾笑着对他说,我可以像电影里的萝丝一样,一丝不挂地给他画。他却不像杰克那么勇敢,他说他画不出我的特点,即便是我们赤裸裸地面对,他也说像隔着层纱。
最开始交往的时候,他还写过一两首诗。但我总忍不住用职业的眼光审视,总是给他挑毛病,笑话他用词土。结果弄得他再也不写了。
那天我们没怎么说话就上床了,也许是遗憾或失去或什么的混合情感吧!我又感到刚认识他那时候的冲动,又有了当时的欲望。他似乎也是。于是我们疯狂做爱,我大叫,拚命抓他、咬他,他也竭尽全力服侍我。最后我们都达到了高潮,汗水淋漓地瘫倒在床上。半晌,谁也没说话,他似乎要睡着了。
我捅捅他:“你说,这次去美,跟我有关吗?”
他没说话。我翻过身,把上半身压在他宽阔的肩上,盯着他的眼睛,又问了一句:“说啊,我是不是你考虑的一个原因?”
他看着我的眼睛,停顿了几秒钟,然后把眼睛转开说:“嗯,是的。”
我看到他眼睛里带着一点躲闪。我明白他在撒谎,却还不死心。
“那你说说,为了我什么,你要去美国呢?比如,可以给我找到一些机会?”
“是的,没错。”他的脸上发出些光,“也许我可以认识一些留美文化人,帮你的书在国外打开市场。也许碰上几个好莱坞的导演、制片人,你的书可以拍电影,也说不定啊!”
我看着他犹豫的眼神笑了,很满足地趴在了他的肩上,闭上了眼睛。
反正现在,他是属于我的。
临走的时候,我从包里掏出一个钥匙链,上面是一只红色的小无尾熊。“这个送给你。”
“多大了,玩这个?”国钊很惊讶地看着我,似乎不想要。
“爱要不要!”我随手把小熊扔到他的床上。
“要,当然!”他却没有去拿,而是走过来想抱我。
我推开他:“你自己,好自为之吧!那边的人际关系,可没这里这么简单。”
国钊微笑了一下,还是给了我一个熊抱:“瞧你说的,好像我去敌营似的。我倒是不放心你……”他欲言又止。
不放心你还去?我在心里问,但没有再说什么。
02
国钊去了两年回来了。两年里我们很少通信,但每年生日的时候,他都会用微信发来几支花和蛋糕,我也就简单回复个 “谢谢”罢了。
我换了工作,新工作年薪高些,但有时候要出差采访。我疲于奔命,根本无暇写什么真正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东西。心里像有一个洞,到了晚上,空空的,无法填补。
偶尔会想起国钊,想着他在纽约到底混得如何。也许他已经真的彻底海化了,不然怎么也没什么消息?嗨,祝福他吧!否则又能怎么样呢?
两年后,又是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我:国钊回来了,在山城一家证券公司上班。
国钊为什么又回来?他在那边都干了什么?去过哪里?这些问题虽然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却从来没有问过。
现在很多人留洋西方,结果水土不服又回国;不然就是沦陷于温柔之乡的,有的是。我猜想他是混得不好,这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有些打击,因为他一向不服输,他是个心气儿很高的家伙。
自然,他从没再跟我提过什么出版社或者导演。现在想来,当时在那个场合,他能这么机智地回答,又安抚了我的虚荣心,也是相当体贴,煞费苦心了。
回来后我们一直没有再见面,他搬去了渝中,而我仍住在南岸的郊区。他回来的一年里,我们通过几次短信。他很礼貌地说:“什么时候来渝中玩,来找我哦!”
我也礼貌地回答:“好的,一定!”
这“一定”就是一年。
03
周四的时候我在网上查了天气预报,说周五可能会下暴雨。三月份,重庆的天气有时候会抽个羊角疯。去年就是这样,三月底了还一会儿寒冷,一会儿又下暴雨。据说三月生日的人也是如此,我觉得百分之五十吧!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脾气,但是我也绝不承认自己会无缘无故地犯神经。
我是比春风还温柔些的,我不想国钊风尘仆仆地赶过来,就为了见我一面庆生。于是给他发了微信:“听说周五可能有暴雨呢!如果那样的话,你还是不要开车来了,安全要紧。要不下周五再见吧!”
那天上午,果然开始下暴雨了。暴雨倾盆而下,水流成河。
然而到了下午,太阳出来,天上飘着几缕白云,晴朗得一塌糊涂。地上的雨水早已不见,连湿漉漉的地面也几乎干了。我不禁想:嗨,今天也许不该取消约会吧!原来是个好天气呢!
我给国钊发微信,说天气很好。他回说:是你取消的啊!天意吧!后面还放了个鬼脸。心情似乎不错,这是他回来以后很少的语气。
我不禁有些纳闷:他是高兴没来呢,还是故意撒娇?
04
到了下周二,我收到了他的短信:“周五出差去台湾高雄,不能去了,改日吧!总有机会。”
字很多,但每句都很简短。字里行间的意思不明朗。不知是否有遗憾,还是逃过一劫?
是的,总有机会,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确定的事情。我给自己吃了颗宽心丸:Life is always uncertain.也正因如此,才让人觉得生活中有些未知的浪漫,就像这三月天,谁知道明天是晴、是雨,还是雪呢!
周五已经请假了,既然约会取消,我不想回去上班,睡了个懒觉,起来以后开始打扫房间。这地方我住了五年了,五年来总共加起来打扫房间的次数有限。
以前国钊在的时候,我们倒是时不时地清洁一下。自从他走后,我懒得再收拾,经常是扒个窝儿就凑合了——反正没人看到,穿着光鲜亮丽的上班族不都是这样?
收拾到我的小书架时,就看到几张电影光盘。我拿着抹布的手停下来。好吧,反正没事,看看电影打发时间倒是不错。我随手翻弄,就看到国钊留下的几张:《铁达尼号》,美国人真是能瞎编,一个历史悲剧的铁达尼号,硬被拍成一场爱情大戏。这种舞台化的激情看一遍也就够了。
我拿起另一张《广岛之恋》,耳畔不禁想起女主角最后的话:“我一定会把你忘记的!看我怎样忘记你!”
当时和国钊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俩都哭了,还说了很多胡话。不,这个电影我不会再看了!
我放下《广岛之恋》,拿起史蒂芬·金的《宠物坟场》,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外面下着雨,我吓得直往他怀里钻。此时看着,心里不禁有种赌气的想法:好吧,就看这个!现在青天白日的,我就不信我自己一个人不敢看!
05
又过了一周,周四国钊本该回来重庆。我还在琢磨,是否该发个信去问问,又想:干吗老是我主动?这不是很掉价!我决定等。
到了早上,果然我收到他的微信,但却是个失望的消息:明天的飞机取消了。
是吗?我回了两个字,心里却不大相信,以为又是他扯谎。
是,有龙卷风。我们还进行了演习,所有人都躲到地下一层,他回答。
哦!那多加小心吧!
他回了一个笑脸。牛郎织女,不容易啊!
什么意思?……他的心情似乎不错,扯出这么个典故,是说我和他?显然是,可是,牛郎和织女,好歹人家也是两口子了,古往今来,世人皆知他们的关系。我们算什么呢?
我没问。也许该追问一句,可是骄傲让我就此打住。
谁会知道,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对话!
06
第三天上班午休时间,我在厨房一边吃着我的三明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新闻。电视上一男一女正用职业无感情的声音说着,画面缤纷交错。其中一个镜头画面是一辆翻倒的巴士。
“据驻台湾记者阿珍报导,一辆从高雄开往台北的长途巴士在一号高速路出了车祸。车上有三十四人,伤亡二十五人,包括司机。事故起因还在调查中,目前伤者均送到附近台北医院……”
“又是个事故。”一旁吃饭的娱乐版主编老乔说。
“唔,那个地方真是祸事多啊!”我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咬了一口花生火腿的面包。
07
周末,我还赖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突然电话铃响了。一看表,还不到十点。我很讨厌周末这么早打电话的人,翻个身没理。
电话响了四声后有人留言,我也没听清楚,又稀里糊涂地睡着了。
等我十一点爬起来,吃完我的早中午混合餐,才拿起电话查留言。看看来电显示,是本地的号码,我并不熟悉。
“这里是渝中X殡仪馆。国钊的追悼会订于X日X时在殡仪馆举行,特此通知。”
什么?我把留言重复放了三遍,都是这么一句话。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眼前发黑,险些摔倒。他不是飞机取消了?我又听了一遍。没错!是国钊的名字。
我感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涌到嗓子眼,想吐,然后我的腿开始哆嗦,站不住了。
我扶着桌子弯下腰,眼前模糊成一片:这个笨蛋,难道他去坐了巴士?那可是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不可能!他是公差,何必受这种罪?不可能!
我摇摇晃晃地扑向计算机桌,碰翻了一把椅子,脚趾头生疼。我顾不得看脚是不是破了,一头扑过去,打开计算机网页搜索新闻。
新闻页上只有简单报导,没有姓名,附着两张翻车的照片。可我还是拚命放大照片,拚命寻找每一个角落,我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不怀希望却仍然幻想。
最后在一片汽车碎玻璃的旁边,我看到了一个红色圆圆的东西……那是一只无尾熊。虽然不是很清楚,我知道没错,那就是我在国钊临走时给他的无尾熊!
你干吗要那么做啊!世界缺了你就不转了吗?傻瓜!我对着计算机号啕大哭。
我的头仍是晕乎乎的,像喝醉了一样。我走到书架前,一眼看到上面放的几样东西。那是国钊临走时留下的握力器、光盘和几支笔。我哆哆嗦嗦地拿起它们,它们却从我手中滑落,掉在地上。
《广岛之恋》的盒子开了,光盘散在边上,露出下面一张小纸片,上面有一首诗和一小段话。
小沐:
对不起我这次走,没事先告诉你。我是觉得,我们之间该做个决定了。我知道你心高气傲,不会先提出来,但我已经在你对我的态度上感到了一切。所以我想,我这样走,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记住我的好吧!原谅我不辞而别。祝你幸福!我会一直默默注视你,为你祝福。这是我的最后一首诗,以后再也不会写了……
那个还寒的三月呵
总期待着渐近的脚步
一条马路的对面
陌生如一次突然遭遇
你提前站在午后阳光里
用影子丈量着心灵距离
一张餐桌的两端
两杯茶水呷在心底
目光游离思想,你知道么
咫尺天涯的爱,只因有你
如果沿着这条熟悉的路,我还能再找到那个浑身都写满文字的小沐吗?
国钊,2013.3.15
08
我没有去参加国钊的追悼会,因为我无法去面对一个再无法给我任何解释的国钊。
过了好久,我才想起一个问题:那个殡仪馆是如何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难道国钊会提前把所有人的名单都准备好?这不是太荒诞吗?然而既然没去,我也无从知道了。
这和国钊在高雄都干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坐巴士回台北,还有,他生命最后一刻都想了什么……这些对我都成为永远的谜。
一年后的三月,又到了我生日这天,我打开手机,看到妈妈的短信祝福。我给妈妈通了个视频,告诉她自己一切都好,不要担心。然后开始吃早饭。
如今生日对我已经是个很敏感又孤单的日子,就像一朵花开在没有阳光的阴影里,透着单薄清冷,却又期待着一阵风吹过,使它能婀娜舞动。
我决定今天一定把自己忙个昏天黑地,反正也没人等着我吃蛋糕。
果然,一到报社,就接到个很急的采访任务。一上午忙得水都没喝一口,到了中午,才稍微喘口气。
进了厨房,我把昨晚的剩饭放进微波炉,按了一分钟键。听到“嘟嘟”声,机器开始转了,我抱着双臂,等在一米以外的地方——那是国钊告诉我的。第一次和他在我的公寓里热饭,刚把汤放进微波炉,按了按钮之后,他一把把我拽到一旁。
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玩什么浪漫。结果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得距离微波炉远点,不然微波那东西对人身体不好。
哦?怎么不好法?生不了孩子咋的?我不以为然。
差不多吧!对女人尤其不好。反正差不多……他一脸认真。
我想笑,可没笑出来。
从此以后,我每次把食物放进微波炉,都会退后一步。想起他当时的样子就莞尔一笑。
这时,我又听到一声“嘟嘟”,却不是微波炉发出的,是手机微信。
我打开手机,里面冒出一句: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洒下一片玫瑰花。
我吓呆了,差点把手机扔出去。因为这个微信是国钊发来的!
难道他没死?不可能!殡仪馆不可能出错啊!是谁在恶作剧?可这明明是他的微信账号!被人盗用?可盗用的人怎么知道我的生日?他们都是为了骗钱的,谁还会有闲情搭理这无聊的生日祝福?
也许是他提前设定好的?老乔曾告诉过我,有的手机有这功能。如果是那样,我的心里倒是可以有很大的安慰。
这样想着,我摸摸胸口,想让心跳慢下来。可是立刻,另一个疑问陡然钻进我的脑海:国钊的手机此刻会在谁的手里?谁在用?一直在用?
我的手开始发抖,敲回去几个字:请问,您是国钊的朋友吗?
然后屏住呼吸,紧盯着机屏。
那边停顿了一下,那一秒似乎比一年都长。终于发过来一个笑脸,似乎在等待什么。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国钊的前妻,你好!
我倒退了几步,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再也无法控制。在泪眼模糊中,我发过去一个谢谢的手势,又发过去一个握手。然后,我哆嗦着摁住国钊的电话号,直到跳出“删除”两个字。
删了他,就意味着我生命从此断掉三年;如果不删,也许就成为这辈子永远翻不过去的一页,我会永远生活在阴影里。
我的手停在了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