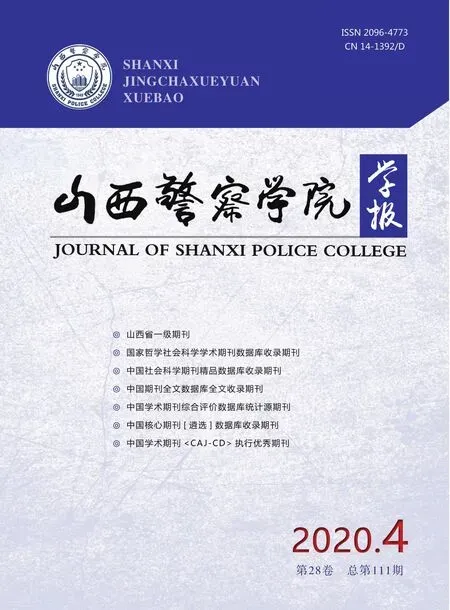“新常态”视阙下警察执法境遇分析与对策探究
□侯延昶
(中国刑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854)
近年来,警察的执法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警察执法进入“新常态”,这也意味着警察执法要摆脱“旧常态”的束缚。所谓警察执法旧常态,是指警察原有的执法环境下执法的随意性、非程序执法以及原有粗放式执法模式,这样的执法生态下产生的是警察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旧常态下执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增加以及警民关系不和谐的严峻挑战,也是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这些都是新常态的环境下所要摒弃并加以改良的弊病。可以说,新常态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新的秩序和新的境遇,以及在此新的执法环境下警察执法应当采取的新策略。
一、“新常态”视阙下公安民警执法境遇分析
(一)犯罪高峰期持续,民警压力较大,职业风险大。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相关数据表明:“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判处罪犯118.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7.2%和2.2%”(指2014年度)。2016年度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9.9万件,判处罪犯123.2万人,同比分别上升7.5%和4%。
再来看警察受伤牺牲的统计,据人民网报道,2015年全国有438名公安民警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同比增长11.5%,牺牲民警平均年龄46.3岁。其中,71名公安民警在抢险救灾中牺牲,205名民警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去世。2014年全国有393名民警牺牲、5624名民警负伤。仅春节期间,就有9名民警牺牲在节日安保岗位上。另据公安部某负责人透露,2014年牺牲民警年龄集中在30岁至49岁之间,平均年龄45.3岁。其中,284名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占牺牲总数的72%。从牺牲的原因来看,猝死所占比例最大,有201名民警猝死,占牺牲总数的51%。从负伤的情况来看,有2417名民警在与犯罪分子搏斗时受伤,比2013年增加469人,上升24%。毫无疑问,人民警察成为和平年代伤亡率最高的职业。十八大以来,民警共牺牲2106人,负伤22977人。执行勤务牺牲651人,占30.9%;抢险救灾牺牲139人,占6.6%;同违法犯罪分子搏斗牺牲122人,占比5.8%;其中58人遭遇暴力袭警,占比47.5%。受伤的民警中,执行勤务受伤12706人,占5.5%;暴力袭警受伤的7087人,占比31.4%;同犯罪分子搏斗受伤2191人,占比9.5%。其中在暴力袭警的受伤人员中,执行勤务中遇袭6180人,遭受报复伤害91人,围攻殴打致伤816人。
(二)新型警情和非警务活动占比较大
以往警察处理的绝大多数是传统警情,也就是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办理,但自从“漳州110模式”被认可后,我们提倡“有警必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这使得大量非刑事、治安警情涌现,警力奔赴在救助、化解纠纷、社会服务以及其他机关处置困难的政务行为上,这些警情有一些属于警察管理范围,有些不属警察职责范围但是由于缺少相关职能部门介入,公安机关被赋予相应职责。因此,相对以往传统治安、刑事警情相比较,日常生活救助以及日常纠纷等新型警情所占比例大幅加剧,再加之维稳、控访以及民警参与的其他非警务活动占比较大。
(三)职业归属感、职业荣誉感降低
2006年,福州市公安局对该局20个警种部门的1200名民警的工作压力以及职业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人深省,有46.51%的民警重压下想调离岗位,20.87%的民警想辞职。调查显示,警察职业的吸引力和职业荣誉感正呈现下降趋势。有76.76%的民警在调查中认为警察荣誉感正在下降,69.11%的民警认为警察职业与其他政府部门相比较差。[1]无独有偶,2008年,广州市公安局团委在全市公安系统各级团组织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一次青年民警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调研活动,据统计,有超过75%的青年民警认为当前工作任务过重,压力过大,有57.2%的青年民警认为“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最大苦恼是工作压力”。将近60%的青年民警认为过多的指标和繁重的工作影响了自己的业余生活和“充电”提高。其他地方公安机关的统计也有类似情况。[2]通过以上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当代警察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荣誉感降低。
(四)警察执法公信力降低,民众与警察敌对情绪加重
从“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案件”、广西警察枪杀孕妇、“人大硕士遭遇执法死亡”等案件,可以看出公众对于警察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质疑之声屡见不鲜。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实行已久,依法治警,从严治警的理念也广为人知,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警察队伍的数量、层次、素质参差不齐,各地执法环境以及法制环境的差异,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等行为屡见报端,加之以往警察管理的触角覆盖过大导致警察权力滥用,警察压力较大导致的执法过失和不当行为等都严重拷问着警察执法的公信力。
警察在公众心目中形象普遍较差,执法中警察与执法对象对立现象也较严重。管中窥豹,一叶知秋。2010年上海杨佳袭警案,致使七名警察牺牲,而网上对于杨佳的袭警赞扬和对于警察牺牲的冷漠可谓令人心寒。2015年洛阳交警被当街捅死,网民也是对警察被杀这一明显事实褒贬不一。2017年警察曲玉权被杀,最终杀害警察的暴徒在被法院量刑问题上,公众、警察以及法院等群体存在较大争议,也可看出警察在普通百姓以及更上层精英群体心中的认知程度。我们可以看到,但凡涉及警察出现的公众事件,不论警察是非对错,民众似乎必然先对警察发难,这是单纯少数人的观点么?我们再来看近几年阻碍警察执法,对抗执法的事件所反映出的执法现状,百度下“警察执法”,有成千上万条阻碍抗拒执法的行为方式,“跪地式”“脱衣式”谩骂殴打式、“我爸是领导”式,“你能把我怎样”式等。当然这些现象有的是违法嫌疑人有意阻碍执法,有的则是“仇警”心理作祟。此类现象对公众心理有反向示范作用,严重危害警察执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对警察职业有较大冲击。
二、“新常态”视阙下警察执法境遇之背景分析
(一)旧的执法环境与新的执法环境之剧烈反差
从时间跨度来看,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节点,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这可以归为公安工作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社会基本呈两元化格局,社会阶层明显而矛盾单一,此时公安机关作为带有暴力性质的专政工具和拥有极大权威和极少制约的权力机关,警察也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和自由裁量余地。当今,改革进入深水期,前期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我国两元化格局迅速瓦解,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犯罪的高发和社会极端心理人群的产生;经济发展带来公民社会的雏形的同时,也带来了民众维权意识提升和社会管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式思想方式和社会生活与传统模式激烈碰撞,这些阵痛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对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的刺激作用明显,影响巨大。
在此社会背景下,我国公安机关的职能经历了从专政工具到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利剑,如今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执法服务并举的转化,实际是公安机关责任变大了,权力相对限缩,法治社会对公安机关要求却越来越高。
(二)新旧制度、体制机制的猛烈碰撞带来的新要求和转型滞后性的弊端
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立法趋势对公安民警执法办案提出更高要求,而对警察执法办案的保障和权利赋予没有及时跟进。众所周知,我们的刑事法修订频繁,主要的立法动向还是在扩大刑事处罚范围,使法律管理范围内的空白领域,比如网络空间、食品药品监管等问题纳入到法律中来。治安管控方面也是如此,流动人口、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地方政府的维稳需求等也无疑增大了警察执法管理的内容,给公安机关带来巨大挑战。此外,由于立法技术的局限,许多粗线条的立法大量存在,比如“口袋罪”式的法条以及模棱两可的立法表述都是对于法治社会所倡导的程序执法、依法行政的挑战,给警察执法留下巨大的潜在隐患。
当然,公权力的限制和私权利的扩张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果警察相关保障和权利在立法层面存在缺失,就会使得警察自身保障缺失,执法风险增加。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作为警察权力运用的依据之一,在刑法和刑诉法已经多次修订的背景下多年未变,而警察屡屡受伤、牺牲的执法形势下,警察使用致命性武器的依据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警械与武器使用条例》,其立法之粗糙,层级之低令人无奈。另外,公安权力运行的边界还有模糊地带存在,非公安业务没有法律依据支持之处常有。
其次,从公安管理体制机制来看,公安管理体制在新形势下未完全转型。公安机关的管理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模式,所以各地公安机关在部门设置和职能分工上不尽相同,体制机制完善探索仍未成型。以巡警部门和派出所为例,有的地区称特巡警,有的称交巡警,有的称交巡特;派出所也是,有的地方派出所分为治安所和户籍所,有的有刑侦业务、有的没有;有的民警只管社区,有的社区民警办案和社区管理集于一身等,比如重庆市取消派出所一级,河南也曾试水,将分局一级撤销,其终极目的为的是解决警力倒挂问题,但是这样的尝试并未达到目的。类似问题还有公安业务考核制度,许多地区考核体系落后而繁杂,在一线部门和基层干警眼中被视为造假大比武,例如考核中一些没有科学依据,或者早已落伍的考核指标长期存在,使得民警苦不堪言。
再者,警察执法、保障、晋升、工资待遇的相关法律也没有完全保障到位。警察集社会面管理和刑事侦查等职能为一身,工作特殊性并未得到重视,警察职业不同于一般公务员,这个领域有太多业务不同于一般执法者,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都有其特殊性,其所辖部门和人员数量也是相当庞大,其经费的来源和去向有的较为特殊,应当在其职业保障和相关制度上予以体现。
总之,以上弊病都可归为“旧瓶装新酒”之痛。旧的体制机制是建立在公权力强势基础上,民警依附于强大的公安权力之上,权力制约缺失和绝对权力较大使得警察个体也较为强势。而如今,随着执法环境的改变,管理层和民众对于警察权力的新要求下,公安权力的绝对强势不复存在,而公权力相对弱化使得个体警察权利和保障相对缩减,落后的体制、机制下对民警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保障不利,警察权的限缩使警察之执法权益受挫。
(三)新旧理念交锋之痛楚
改革开放之前,公安机关是暴力机器,对于阶级敌人也就是违法犯罪分子就要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因此,刑讯逼供,既严又厉的刑事政策应运而生。警察拥有绝对权威,在理念上秉持保护革命成果,镇压各类反革命分子和罪犯,因此,警察职业作为革命的保护者,自然是神圣之极。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违法犯罪也随之增多,保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成为首要任务,于是“严打”刑事政策应运而生,巡防队员、联防甚至各厂保卫部门也加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打击犯罪、保卫经济成果的战斗中,“严打”讲的是从重从快打击处理刑事犯罪,大量刑事犯罪分子、违法人员在巨大压力下被绳之于法,在“从重从快”的理念下,警察权威被放大,警察权力也愈加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稳步推进。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市民社会逐步成型,也使得权力制约和公民权利意识深入人心。从公安自身管理“五条禁令、三项纪律”到国家层面“程序执法”,“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举,“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提出等等。从前模式下一些隐藏在背后的冤假错案、权力滥用、管理错位的问题也逐步得以纠正。当代法治背景下,警察权力既要被约束,又要在转型期的复杂社会形势下履行职责,以满足政府和社会对于法治的渴求和打击犯罪的需求。
(四)“相对弱势群体”之对比落差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上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对较低、话语权较弱的群体,比较公认的弱势群体,例如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但近来,我们发现,一些公务员、医生和教师等机关事业单位和白领行业也称自己为弱势群体,甚至警察也称自己为弱势群体。究竟是否弱势呢?我们认为此现象可以用社会学中“相对剥夺感”和“从林法则” 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简单而言,相对剥夺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是有权享有但并不拥有。具体而言,警察职业群体在行使公权力面对私权利时是强势群体,但是在警察个体手持警棍面对持枪的穷凶极恶的暴徒,在面对群体事件成百上千的群情激奋的人群时是弱势,为了执行任务遭受谩骂殴打而不能有所为时是弱势,在待遇、保障和付出相对于其他公务员群体不对等时是弱势。这就是“相对弱势”的现象。而“丛林法则”可以阐释为何警察群体认为自己为弱势。因为在法治和规则不被普遍遵守的社会里,任何强势群体在面对更强大的,更不遵守规则的群体时都可能为弱势,强势群体只是暂时和相对的,丛林法则下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谁也不是赢家。因此,只有实现规则之治,在依法治国状态下才会使得所有人的权利都得以保护,平等对待。
三、“新常态”形势下公安机关执法对策分析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尔夫·达伦道夫曾指出,“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时代警察队伍建设和发展一定会面临新的问题,警察执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安机关必须具备高度的凝聚力和执法威严,如果警察执法长期存在被动、不利、受阻的局面,将不利于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因此,国家相关部门以及公安机关自身必须行动起来,切实保障警察执法,加强对警察职业的保护,出台相应措施。
(一)完善相关立法,明确警察执法尺度、程序和标准并使之公开化。警察执法依据是法律法规,因此代表法律权威和尊严,其公信力和执法行为不容挑衅和质疑,针对警察执法的过失、错误和瑕疵,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投诉。因此,公安机关应当从程序执法入手,完善警察程序执法细则和规定,使得警察按照既定规则和细则执法,并接受公众监督。另一方面,明确执法对象相应义务和责任,要求执法对象必须在执法现场配合警察执法,按照既定规则接受警察指令和从事相关行为,如果执法相对方对执法行为和处罚有异议或者对于警察执法程序不满,可以按照法律和法规以及既定规则投诉甚至起诉,但是如果现场阻碍警察执法,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也就是树立警察执法优先,执法对象存疑置后的规则。这也需要加大警察培训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规范化和标准化训练,并对警察执法正面和反面案例予以剖析、研判和大量宣讲。学者马蒂指出:“冲突作为社会互动的其中一种重要的任务不是歧视和完全消除冲突,而是要发现冲突背后存在的利益争端,创造和保持一种能使冲突变得对社会有益的机制。[4]
(二)建立执法责任豁免机制,加强警察工会维权机构和警察维权组织维权职能。一方面,应当在执法规范化和标准化流程基础上,遵循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作为衡量标准。严格责任追究,构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的执法责任体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同时也要健全执法过错容错机制,在完成规定的执法行为和程序前提下予以免责。另一方面,我国公务员相关权利保障的规定多集中于《公务员法》内,但是相关警察维权的维权主体和方式方法规定还不详尽,因此,警察工会和警察维权组织应当充当此类角色。
(三)完善后勤保障制度。完善警察加班、考核、绩效等内部制度,分流非警务工作警情,增加警察执法效益,保障警察工作无后顾之忧。警务工作要善于做“加法和减法”,该给予警察的利益要予以保障,该予以减负的应当予以削减,切实维护好警察群体的职业积极性主动性。
(四)对于公众要加大宣传力度,增进警民沟通。警察与公众有效互动,使公众对警察执法的程序、监督、执法责任加深理解,同时对于公众不配合执法、消极甚至阻碍执法的后果和危害予以阐述,使得公众对于警察执法在方法、程序、以及救济和不利后果等问题上都有明确认知,警察与民众认知尽量达成共识,以保障正确的执法行为,监督、制约不当执法行为,消除妨碍执法的不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