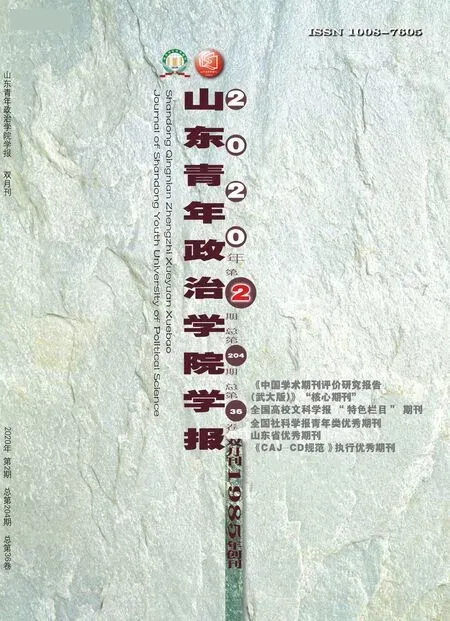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背景、现状与问题
刘卫东 ,范天玉
(1.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成都 611756 ;2. 乔治华盛顿大学 东亚语言文学研究系,华盛顿 20052)
19世纪末以来,创意写作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从教育系统、文化产业和社会领域吸收不同层次的资源,不断调整自身的学科结构和实践方式,前后经历了多次的复杂演进,其社会化实践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包括20世纪20年代侧重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的创意写作理念[1],二战后面向社会领域注重“公共社群发展”(public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写作的社会层面的探索,[2]近年来出现的面向文化产业的实践,以及寻求构建自身独立学术地位的“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academic discipline)的趋向。[3]其中,基于创意写作在教学、创作等方面不断的数字化现象,学者亚当·科勒(Adam Koehler)提出了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creative writing’s digital turn)问题。[4]综合创意写作近20年的实践与研究状况,它主要是指创意写作的教学与创作方法、实践路径的数字化趋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创意作家的培养、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课程、学位的涌现等。
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一方面是社会发展中
数字化技术不断与创意写作融合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创意写作在数字化时代不断调整自身,寻求新的转型与扩张的结果。作为创意写作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它的基本内涵尚需要进一步勘察。按照英国国家作家教育协会(the U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riters in education)对德蒙福特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介绍,其写作除了诗歌、小说和戏剧之外,还包括了“脚本和非脚本的表演,口头和录制的创作以及电子,数字和其他新媒体中可能的各种形式”。[5]后者正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不断发展而出现的,它直接扩展了创意写作的课程类型,使得创意写作的工坊类型也日趋多元化、数字化、虚拟化。如果按照卡洛林·米勒(Carolyn Handler Miller)的观点,创意写作视域中的新媒体写作“还包括更多深奥的平台,例如虚拟现实,沉浸式环境,智能玩具,交互式电影院和交互式电视。”[6]随着创意写作数字转向进一步发展,更多的文本类型、创作方式与新的问题涌现,对创意写作的教学与理论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综合审视英语国家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可以看到以新型数字、媒介技术为基础的创意写作的快速发展,直接拓展了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的内涵,它使得创意写作的教学与实践都呈现出空前的多元化、复杂化,为创意写作跨学科发展带来了契机,同时也对既有的创意写作教学模式与理念以及创意写作研究都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对英语国家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背景、突出的现象与存在问题进行综合观察,探寻其中蕴含的发展契机与潜在的问题,可为中国创意写作当前兴起的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课程、学位的建设提供相应的参考,也是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继续深入的必要工作。
一、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多重背景
以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史的研究为例,综合保罗·道森(Paul Drawson)、格雷姆·哈珀(Gaeme Harper)、科勒尔的观点,特别是迈尔斯(D.G.Myers)的论点,创意写作在百余年的发展中随着历史语境的不断演变,自身的学科理念和课程结构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和转变。[7]当前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是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前沿问题之一,也是随着时代语境不断变迁而逐步演进的结果。与之前的创意写作每一次学科演进类似,这次的数字转向同样有其特定的背景,即社会层面数字技术的日益发展、教育层面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以及写作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的不断渗透,三者共同构成了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重要背景。
(一)社会领域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构成了当代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技术基础。如果说20世纪早期以默恩斯(Hugues Mearns)为代表的创意写作教学者对自我表达的推崇受到了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在二战后面向不同社群的作家工坊发展受到了社会民主化运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影响,那么当前的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明显地受到了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驱动。正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创意写作教育拥有了新的可利用的教学工具、新的方法,它在无形中改变着创意写作课堂教学的模式。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创意写作教育的影响如今已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它已经渗透到创意写作教育的课堂。正如学者布朗温·威廉姆斯(Bronwyn T.Willianms)在《数字技术与创意写作教育》(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Pedagogy)中所指出,“认为是我们选择把数字媒体带到创意写作课堂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个世界大多数学生都有强大的手提电脑,数字技术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字都进入了我们的课堂。”[8]数字技术并非作为一种数字工具(digital tools)被简单地运用到创意写作教育中去,它与创意写作高度融合,为创意写作提供新的写作方式、发展动力,其中突出的现象就是“创意写作与新媒体”(creative writing and new media)课程与学位的涌现。[9]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新的创意写作课程与学位得以成型,这表明它不但直接影响着创意写作课堂教学方式,还对创意写作的学科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社会领域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对创意写作的影响还体现在它拓展并促生了新的创意写作研究领域,即科勒所说的创意写作研究的数字分支(a digital arm of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10]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对当代创意写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意味着创意写作拥有了新一轮学科拓展、教学革新的新空间的同时,也使得创意写作的社会化实践、理论研究拥有更多可能的路径。
(二)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遍应用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和改进的同时,教育领域也在积极引进并设计数字化的课程,教学与实践等环节都呈现出数字化的趋势,这为创意写作的数字化转向营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氛围。从创意写作的课堂教学乃至社会领域的实践,都在这个趋势下迅速得以推进。美国国家写作项目(National Writing Project)已经有针对新媒体写作的相关研究和活动,旨在帮助人们通过新媒体完成写作表达与各种叙事。[11]创意写作研究学者Stephanie Vanderslice在评论国家写作项目时也指出,“几年前的国家写作项目,多年来一直在敦促创意写作教学法来拥抱数字技术”[12]。
应该指出的是,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遍应用,不仅在技术上为创意写作引入数字技术作为教学工具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也在观念上为创意写作的数字化发展奠定了合理性基础,使得创意写作可以借助这一契机设计自己以实践为导向(practice-led)的课程。如学者戴安娜·唐纳利(Dianna Donnelly)所说,“在这个交汇处之外,我们见证了创意写作研究的向前发展,因为创意写作老师拥抱并将更多的技术素养技能(文学超文本,数字叙事,播客等)纳入他们的课程设计。”[13]得益于这一背景,创意写作的诸多教学环节可以引入各种数字化媒体,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课程,以更好地突出自身的学科特点。
显然,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并非是孤立进行的,它与整个教育领域在教育技术、教育理念对数字技术的接纳密切相关。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遍应用不仅赋予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新的动力,也无形中为创意写作以数字技术为媒介进行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三)数字化叙事为创意写作注入新力量
20世纪70年代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写作领域的显著影响就是在计算机辅助下数字化叙事(digital narrative)的涌现。[14]数字化叙事是基于计算机技术进行的各种数字故事讲述(digital storytelling),能够调动各种图片、音频与程序形成不同于传统文本的超文本,它不仅扩展了写作的概念(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writing),[15]还提供了新的书写技术,实现了书写方式便捷化、语法检查自动化以及文本处理批量化,这种高度技术化的写作让语法修辞训练更多地作为基础训练而存在,尤其是对已经具有基本读写能力的作者来说,其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掌握新的书写技术、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意,通过数字叙事实现自己的核心创意。
1987年,D.J.Bolte与M.Joyce在《超文本与创意写作》(Hypertext and creative writing)中就已经指出,“实际上,超文本可能适用于整个人类读写能力,包括小说的写作和阅读。”[16]数字化叙事不仅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路径,它还为创意写作课堂、社会范围的各类人员提供了创造性的表达自己思想的新的工具。尤其是创意写作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写作工坊(the digital writing workshop)的出现,数字故事讲述成为该类型工坊的突出现象,以工坊为基础实践(workshop-based practice)的数字故事讲述不断发展,[17]都与数字化叙事长期以来的发展并向教育领域的渗透密不可分。
最后,数字化叙事发展中发展出的以“故事讲述”为基础的“自定义叙事”(emergency narrative)对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这种叙事可以弥补“创意写作与技术使用之间确切存在的空缺”[18],这种数字叙事发展出来的“自定义叙事是一种以小说的方式表现创意的可行方法。”[19]这些有数字化叙事实践发展出来的对创意的重视,与创意写作的创意本位理念可谓相互呼应。[20]而近年来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又恰好为此打下了基础。
二、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现状
随着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的不断演进,在新的数字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创意写作的具体创作、教育和研究都开始大量运用新的数字技术,新的数字叙事技术、数字传播媒介成为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的重要驱动力量。其中,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创意写作教学与创作模式变化、创意写作实践路径拓展、新型“创意作家”(creative writer)的培养以及创意写作与新媒体方面课程、学位的涌现四个方面。
(一)创意写作的教学与创作模式变化
创意写作数字转向最为直观的表现在于其教学与创作模式层面出现的数字化,教学层面对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创作的重视,创作层面对各种新型的数字叙事平台、工具的运用,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创意写作教学中,所涉及的文本类型、形态与传统印刷媒体时代相比,具有高度的虚拟化、数字化和抽象化特点。相应地,创意写作课堂上学生们的创作模式也更多地受到数字故事讲述等新兴的数字叙事影响。[21]
就创意写作的教学而言,其变化表现在注重传统的文学类型训练与文学理论教学的同时,需要把新的叙事模式、叙事工具引入课堂,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指导,这又意味着创意写作教师也需要随之做出改变,具有丰富创意经验的艺术家、新媒体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得以更多地进入课堂。学者哈珀直接把传统的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模式称之为线性的创意写作教育(linear creative writing pedagogics),认为基于新媒体的写作创造了一种非线性的空间,这使得写作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并指出“线性创意写作教学的主要成果是完成后的作品,而非线性的创意写作数学的成果则是基于对学科的理解认识产生的更广泛多样的产物。”[22]
而就创作模式而言,基础数字化技术出现的跨媒介、跨专业、跨产业链的协同写作(collaborative writing)[23]等在创作的方法层面也与传统的平面媒体时代的写作具有较大的差异。另外,数字化转向使得创意写作所涉及的多种文本类型的创作方式具有了跨媒介、跨平台和跨产业空间,以及在文本形态层面的非线性、开放性和交互式等多种特点,这些都需要新的数字化的创意写作教学法来解决。例如,就数字故事与视频、游戏等媒体写作而言,写作所涉及的教学内容显然超出了平面媒体时代创意写作教育的知识领域,在类似视频写作与新媒体(Video Composing in the New Media Age)这样的内容方面,[24]原有的人物心理描写、人物性格表现等显然很难与当前的创作对应起来。
(二)创意写作的实践路径拓展
在创意写作的数字化转向背景下,创意写作作为一种创意实践(using digital tools as creative practice)[25],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个专业领域内,数字化的实践使得它具备了面向文化产业、数字经济等更多领域的可能性。这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或更早时期的创意写作不同之处,也是演进中变化较大的地方。
创意写作作为一种创意实践,其最突出的现象在于数字化、多类型的写作工坊的出现,这类工坊对学员的文学素养、媒介素养以及数字技术素养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费吉尼亚理工创意写作方向注重对“新媒体创意写作方面作文创新技巧”(innovative techniques of composition in new media writing)的拓展,还开设有“创意写作和数字媒体夏令营”(creative writing and digital media summer camp)的活动。[26]数字化的工坊实践可以面向城市范围内的居民,这使得它可以进一步走出校园,在更大的空间内发挥自身的作用。
这些实践表明创意写作的数字化实践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社会介入性。这意味着新媒体带给创意写作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和空间,创意写作给予新媒体更多的跨学科写作的机遇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创意写作以工坊为核心的社会实践路径依旧有效,但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显然已经不再局限于课堂内部,而是具备了以数字化的工坊为形式,介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基础。
(三)新型“创意作家”的系统培养
数字化转向带来的创意写作实践具有突出的跨媒介、跨产业、跨学科的特点,这使得创意写作培养的作家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的作者培养,而是走出了文学院系,更进一步面向整个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的创意作家,[27]与其他艺术领域的跨专业写作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创意社群(creative community),其作品被视为创意作品(creative work),共同构成以写作为纽带的创意实践(creative practice),[28]而其共同的面向则是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
以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塔大学(Athabasca University)写作和新媒体(Master of Arts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riting and New Media)[29]学位为例,其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以新媒体方向的写作为主,培养目标已经不是传统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家、诗人。而在新加坡理工学院(Singapore Polytechnic)也设有面向电视与新媒体的创意写作(Diploma in Creative Writing for TV & New Media)文凭课程,主要是针对电视与新媒体产业培养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30]
此外,还有更为多元的表现,在社区学院汤普金科兰德社区学院(Tompkins Cortland Community College)创意写作课程通过提供鼓励写作能力,创造性表达,和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创意写作课程通过提供鼓励写作能力、创造性表达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使得学生可以为以后艺术和娱乐行业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31]班戈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尤是如此,不仅包括媒体文化(Media Culture)、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创意写作:散文(Creative Writing:Prose)、创意写作:诗歌(Creative Writing:Poetry)、媒体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 of the Media),还有跨媒体故事讲述(Transmedia Storytelling)。[32]其中,第三年的课程中的出版写作(Writing for Publishing)和表演艺术写作(Writing for Performance),都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的课程训练,旨在培养适应新的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意作家。
(四)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课程、学位的涌现
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课程、学位的出现是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中的突出现象,它是创意写作的数字化、数字化的创意写作实践的交互产物,是创意写作数字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新的表现。比如美国的Navajo Technical University,开设的有创意写作与新媒体学士学位(The Bachelor of Fine Arts degree program in Creative Writing and New Media),本土的文化可以通过新媒体叙事得以新的传播和保护。[33]多数开设该学位的院校,其课程设置相当多元,既有舞台与银幕写作,其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教育多开设的既有舞台与银幕写作(Begin Writing for Stage and Screen),也有跨媒体的虚构写作(Intermediate Fiction Writing),[34]其共通点在于它们都是基于数字技术生成的新型媒体扩展出的新的创意写作课程、学位。
在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课程、学位涌现的情况下,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创意写作产生了面向出版、新闻与表演艺术领域的写作课程,这些新的课程与学位增设,表明创意写作进一步具备了跨学科的能力,跨课程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across curriculum)成为突出现象。[35]创意写作研究学者叶炜对这种跨学科的实践,特别是其中跨艺术课程的创意写作的发展有着明确的观点,“今后创意写作教学方式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它不能停留于文学课的表面,而是要走向艺术课的深层,或者至少它要兼顾文学和艺术的两面。”[36]
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课程、学位的涌现,为创意写作带来了跨学科发展的新的驱动力,特别是可视化技术对都市景观和文学场景的构建会更为直观,文学场景的构建与其他艺术学科的高度融合已经具备了技术基础,创意写作跨课程的探索借助数字化转向的力量,已经打破了各种课程之间泾渭分明的区隔。尤其是在数字出版(digital publishing)、3D打印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研究的视域中,多媒体出版作品已经难以简单地界定为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了,这其中既蕴含了创意写作发展的契机,也潜在地对当前的创意写作教育与研究都提出了挑战。如Hazel Smith在谈论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时候曾指出,“最重要的是,新媒体写作是算法的(algorithmic)写作方法发展:即它们将一组规则应用于特定的写作任务。”[37]如何基于数字化的创意写作特点设计相应的课程,推进相应的创意写作教育,这是当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契机与问题
创意写作的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创意写作的教学、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与传统的写作教育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创意写作研究学者Jeri Kroll指出,“网络空间的发展通过提出有关形式和风格的新问题迅速改变了教育规则,更不用说美学质量、道德以及写作了。”[38]数字技术对创意写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Kroll已经对此也有了明确论述,她指出“为作家们塑造了全球语境的科技、电子、政治以及经济发展影响了作家看待自己,通过学习新模式来创作新颖的作品,以及吸引和维持读者并教育下一代创作者的方式。”[39]创意写作的数字化转向给创意写作研究、教学以及创意写作的社会化实践都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其中既有发展契机也包含了潜在的问题。
(一)创意写作数字转向蕴含的契机
首先,最值得注意的是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过程中,蕴含了创意写作跨艺术、跨产业、跨媒介实践的可能性,使得创意写作具备了与艺术、音乐等其他专业融合发展的契机。如创意写作研究学者唐纳利认为,“媒体设计,美术和创意产业领域中的创意写作研究还有更多的合作可能性”。[40]叶炜也认为,“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创意写作将跳出单纯依靠文学院系发展的窠臼,汲取艺术院系的营养,不断走向艺术实践,以进一步提升创意写作的实践品格和艺术品质。由此,创意写作将在文学院系和艺术院系的和谐共生中不断成长,在学科和艺术之间取得更好的良性互动。”[41]以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为契机,其相应的课程教育与社会实践拓展具备了新的基础,这是中国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当前发展中不可忽略的事实。
其次,随着创意写作数字化的进一步展开,创意写作与多种艺术类型之间开始越来越多地共享数字技术、媒介等要素。其蕴含的深层问题是创意写作通过跨课程、跨学科的实践,与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类型写作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创意实践,其主体是创意作家,其媒介是创意写作,其面向是创意城市,他们是新的基于数字技术与城市数字化发展而涌现的创意社群。某种意义上以创意写作为纽带的创意社群又可以视为创意共同体,是基于社会生产劳动中创意实践而聚集生成的,这正是创意写作视域中创意本体论提出的客观基础。[42]
在创意写作新一轮的数字转向过程中,文学写作、应用型写作与面向文化产业的各种文本以及新媒体写作催生的新型类型,彼此之间的文本界限变得模糊乃至被拆解,使得多种在传统写作理论看来截然不同的文本背后共同的因素浮现出来,这构成了从创意本位出发[43],重新定义文学本质的学说提出的客观基础。如唐纳利曾指出,“随着创意写作跨越高校系统内部的边界,我们看到了重新定义文学的新方法与新的学科合作关系的更大潜力。”[44]也正如此,在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观察创意写作创意本体论提出的基础和依据,以及对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观察。创意本体论并不是为了构建某种话语体系而提出的,而是从认识论的高度重新审视文学的本质,它的出发点在于从“新文科”发展的视域展开,[45]探求创意写作中国化的原创理论,数字转向提供了新的观察条件和可能,创意写作跨学科实践、社会路径的多元化正是其基础。
(二)创意写作数字转向潜在的问题
学者乔西·巴纳德(Josie Barnard)在论述数字化技术带给创意写作的多模态的跨文本和类型的问题时曾指出,“创意写作已经陷入困境,而对手正是它自己。一方面,人们担心多模态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有必要立即全力地迎接多模态。”[46]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对既有课程结构与教学理念提出的挑战,并不是简单地引入或设计数字课程那么简单,这需要创意写作研究者、教育者立足于创意写作长时间的发展历程观察,从新的高度看待当前正在发生的这些现象。
首先,创意写作数字转向尚处于早期,如何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现象加以把握和研究尚待展开。如学者R. Lyle Skains认为“重要的不仅是教育者和教师开发这些新媒体教学工具和方法来解决交流,而且我们也明白书面写作与数字媒体写作之间的根本性认知差异。”[47]这意味着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并非简单地运用数字技术设计不同的课程,同时也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对这一现象进行勘察,单纯的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写作课程开发并不等于数字转向的主要内容。
其次,创意写作的数字化使得创意写作的学科得以进一步拓展,这一方面使得它具有空前的活力,一方面又给如何界定它的学科边界,重新审视创意写作与既有学科之间的关系,定义创意写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培养创意作家首先要熟悉这种跨越文本类型与媒介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across genres and media),[48]这除了需要在推进数字化的创意写作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展开理论研究,还要探究文学素养与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等能力的衔接与培养问题。
再次,随着WEB2.0技术的不断发展,个体在传播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传统的点对面传播被新媒体的点对点传播所取代。包括彭兰、宋全成在内的诸多传播学学者都曾表述传统的“把关人”理论已渐失效,或转变为新的形式。彭兰表示,群众的投票取代了传统的“把关人”实行了过滤信息的作用,而对创意写作来说,这恰恰是需要警惕的。[49]当“把关人”缺席,权威审核被流量榜单所取代,与产业高度挂钩的创意写作要如何避免被市场左右而转化为生产高度的同质化“文化罐头”的文字工厂,值得每一个实践者深思。
四、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应对之策
在描述过往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关键节点时,许多学者都偏好使用“十字路口”这一隐喻,将学科面临重大抉择的状况形象化,[50]学者科勒所提出的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则更为明确地为创意写作的当前态势直接命名。创意写作的数字化转向迄今为止尚未为学界重视,其研究也处于初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创意写作可以主动选择进入该研究领域,依托中国飞速发展的数字媒体技术与文化产业,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推进中国创意写作下一个十年的快速发展。
(一)借鉴国外创意写作培养模式
随着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不断发展,新媒体技术不断被运用到课堂教学,面向文化产业的创意写作越来越多地关涉到数字化写作,即使是以培养传统作家为主要目标的创意写作教育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数字化写作的问题。中国创意写作可以借鉴英语国家注重学生文学素养、媒介素养与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综合培养的模式,引导学生学习文化产业知识,培养具有文学创意能力且能运用数字化工具写作的创意作家。[51]另外,从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角度观察,[52]在不涉及对学科架构进行大调整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在创意写作课程中增加数字叙事、新媒体方面的教学内容,逐步探索有效的教学模式。
(二)推进中国创意写作研究深入
中国创意写作研究学者在早期就提出了“创意写作学科是研究创意写作本身的活动规律、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规律、创意产业管理和运作规律的学科……”,[53]借助当前中国创意写作研究兴起的趋势,加强创意写作与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以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史为视点,纵向梳理其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的动力、方向与问题,开展一批个案研究,并对当前态势进行评估,这是中国创意写作研究潜在的可行方向。认识到它对当前创意写作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可能的影响,对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进行研究,不仅关系到中国创意写作教育下一步的发展路径探索,也与推进创意写作中国化发展深入密切相关。
(三)加强创意写作的国际化交流
在翻译与引进英语国家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相关论著的同时,积极参与并加强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是实现中国创意写作教学理念与研究视域与国际保持同步的有效方式。目前,中国创意写作从创生至今已有十余年,借助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刚刚开启的时间窗口,加强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稳步推进中国创意写作在数字化转向方面的研究,这是中国创意写作下一个十年重要的发展契机。
1880年以来创意写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次转向,每次都给创意写作的教学、研究与社会实践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与挑战,正是在这些转向中,创意写作不断地走出校园,面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面对当前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如何对这一概念进行确认,对相应的现象加以梳理,对其中的学理进行阐述,发掘其中潜在的规律,则成为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领域都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中国,2017年上海大学与阅文集团开始了共建“网络文学方向创意写作硕士联合培养点”,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增设了媒体与创意写作方向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类似《数字化时代的创意写作》等著作也已经被引进到国内出版,创意写作数字化日渐成为研究人员关注的对象。基于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的趋势,立足于中国当前文化产业、公共文化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实,依靠当地发达的数字技术与媒体产业,构建具有自身特点的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体系,这将使得创意写作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路径更为多元化。
最后,在数字技术与创意写作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与英语国家在创意写作的数字化发展方面,具备了类似的客观条件,双方第一次同时置于新的发展契机与挑战之中,具有了高度的同步性。在创意写作数字转向的趋势下,中国在借鉴与吸收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发展经验之时,借助创意写作数字转向为契机,充分对潜在的挑战加以回应,以本土新闻、出版、戏剧、影视与艺术学等专业的课程改革为切入点,推进本土创意写作的跨学科发展,实现在方法与理论层面与国际保持同步,这无疑是中国创意写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