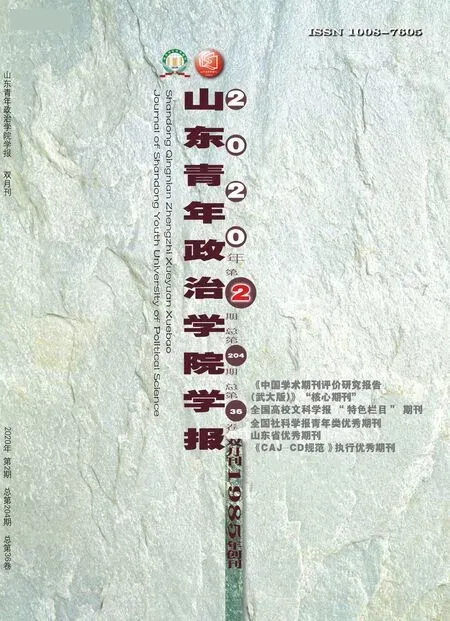从“转发锦鲤”看青少年网络俗信:表征、本质与引导
岳 彩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闵行 200241)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9年8月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以中青年群体为主,截至2019年6月,10-39岁网民群体占网民整体的65.1%,其中20-29岁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24.6%。[1]青少年网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网络社会的整体风貌。大量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锦鲤”以祈求好运,作为一种特殊的用户信息行为,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与社交网络的助力下,成为一种独特的网络文化景观。以“转发锦鲤”为窗口,分析青少年网络俗信的外在表征与内在逻辑,对于了解青少年心理特征与现实诉求,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进而对青少年进行更具针对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占领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网络阵地,具有重要意义。
一、“锦鲤”、“转发锦鲤”及其新表征
(一)符码统治下的意义赋予:从锦鲤到“锦鲤”
锦鲤作为一种被赋予意义的传统文化图腾由来已久。道教将鲤鱼视为圣物,骑坐鲤鱼被认为是得道成仙的标志,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对俗》中说:“夫得道者,……琴高乘朱鲤于深渊,斯其验也。”[2]然而,现代“锦鲤”的形象显然已经溢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圣物及传统吉祥图腾的含义。在语言的隐喻机制与类机制作用下,“锦鲤”与“幸运”之间产生关联,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与出场语境的多样,类推产生的“锦鲤”发生了意义的泛化。网络颠覆了锦鲤的原本意义,重新构建一套新的符号意义,将“锦鲤”原本固定的能指和所指强行撕裂,然后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构建新的能指与所指关系。锦鲤成为媒体塑造、众多网民参与的即兴改编的文化过程,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和文化背景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在现代媒体的塑造和网络传播的加持下,锦鲤成为好运的象征,随着热度的增长,锦鲤开始泛指在小概率事件中运气极佳的人,锦鲤的走红过程也是锦鲤意义的泛化过程。
早期,作为网络幸运吉祥物的锦鲤,是以完整的动物形态出现的,典型代表是名为“锦鲤大王”的微博“大V”,每日分享一张锦鲤的图片,附上文字“你只管努力,其它交给锦鲤”。后来,随着锦鲤形象在微博等自媒体的高频出现,锦鲤的象征意义开始凸显,只要是代表幸运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为“锦鲤”。而锦鲤意义泛化的高潮出现于一档选秀节目中,实力备受争议的杨超越成为比赛的第三名,锦鲤的形象与人的形象开始同质化,此后支付宝中奖的幸运儿微博用户——“信小呆”更将“锦鲤”泛化推至网络空间的风口浪尖,人们开始将各种网络热点事件中出现的带有“类幸运”特征的人称为“锦鲤”。互联网与新媒体内在的免费共享、迅速扩散的特质,为网络俗信提供了生成渠道和传播路径,使之成为了风格鲜明的网络文化景观。
(二)主体缺场造就“乌合之众”:从“锦鲤”到“转发锦鲤”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出,一群人的聚合,在形成“心理群体”时,会表现出迥异于个体的特征,并总是受到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他将这种群体称为“乌合之众”(The Crowd)。[3]当“锦鲤”从抽象的网络亚文化领域溢出到真实的生活场景,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几乎所有转发锦鲤的人都希望自己具有“锦鲤体质”,凭借天赐的好运实现人生的“逆风翻盘”。 关于锦鲤的语言系统也相应地扩大,“锦鲤体质”、“锦鲤本鲤”、“人型锦鲤”、“锦鲤属性”、“吸欧气”等等,大众在随意转发、不经考证,麻木从众的过程中,表现出集体非理性与无意识的状态,网络参与热情高涨,跟风转发锦鲤成为一种时尚。在转发的过程中,众多参与者并不在意转发是否真的会收获好运,崇尚“简单的快乐”,参与转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网络狂欢,具有消遣性、娱乐性的特点,是青少年寻求娱乐化情感支持与归因的途径。“转发”这一行为暗含着认同的态度,除对内容的认同外,很多时候也包含着对转发这种形式的支持与赞同。
传统的祈福流程固定、形式复杂,需要耗费一定人力、物力、财力,但是“转发锦鲤”只需要在网络上轻轻一点,成本趋近于无。微信平台上甚至有“转发锦鲤”的小程序,不需要费心去找“锦鲤”的图片,只需要指尖轻轻一点,就可以实现“好运”的“一步到位”。网络亚文化造就了转发锦鲤的“乌合之众”,产生羊群效应,大众纷纷“转发锦鲤”,使这种带有传统好运色彩的鱼类在网络上掀起一股不容忽视的“锦鲤效应”。“转发这条锦鲤,就会……”的语式在各类自媒体语境中十分常见,标准的“转发锦鲤”流程是转发包含“锦鲤”含义的图片,配上相应的祈愿文字,如“考试通过”、“面试好运”等,如果愿望得以实现,许多人还选择再次转发之前的祈愿微博,作为“还愿”。 媒体经常充当“转发锦鲤”这一羊群效应的煽动者,大肆报道许多电视节目或社会事件中幸运的人物,例如“转发这个杨超越,不用努力也能得第三”。青少年通过这种盲目的转发行为,将日常的愿望诉诸于虚拟的网络表达之中。锦鲤从古代的以自然为主导的图腾崇拜对象,逐渐演变成以社会为主导,以象征、叙事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社会崇拜对象。
(三)资本逻辑与娱乐泛化的耦合:从转发锦鲤到锦鲤营销
资本凭借对偶像生成与崇拜的熟练操作,将“锦鲤抽奖”作为吸引用户的一种手段,卷入商业运作。以ID名为“锦鲤大王”的用户为例,该博主此前一直在微博发布锦鲤的图片,并通过持续转发网友的“还愿”微博,积累了两千多万粉丝,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多个粉丝群。同时,凭借在网络中的超高人气,接到了诸多广告,在淘宝开起了同名店铺,售卖“配套法器”,成功地将“锦鲤”纳入经济生活的领域,使其成为可供消费,亦可带来巨大收益的概念。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娱乐超出自身的边界,溢出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发锦鲤”这场网络游戏突破其存在的场域,其形式和意义都溢出自身,渗入到人们真实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
转发锦鲤衍生出一系列的“锦鲤效应”,众多商家开始借助“锦鲤”的概念进行宣传和销售,“高校锦鲤”、“品牌锦鲤”、“美妆锦鲤”、“商场锦鲤”、“七夕锦鲤”等现象层出不穷。商家对这种程序简单、收效明显的营销手段爱不释手,消费者也对这种看起来毫不费力,指尖一点就能成为“天选之子”的机会趋之若鹜。人们自然能够意识到这种天降的好运是极小概率的事件,但是转发行为本身表示自己融入在这场大众参与的游戏中,由此也能获得片刻的愉悦,锦鲤营销的主导者和受众都乐在其中。然而,锦鲤营销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商家利用人们对锦鲤的狂热,发布锦鲤营销广告,提供虚假奖品或暗箱操作,只为通过大众无意识的转发提高自身产品的知名度。更有甚者,以此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电信诈骗,这些现象显然已经与锦鲤祈愿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二、“转发锦鲤”的本质与青少年网络俗信的内在逻辑
(一)内群体的符号交往方式:仪式的消解催生同质化人格
迷信常常带有某些特定的仪式,而以转发锦鲤为代表的青少年网络俗信则实现了仪式的消解,迷信的严肃感和程序化被随意改写了,其形式更接近于一种网络游戏,弱化了“迷信”,只剩下符号的狂欢。“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4]随着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青少年在网络上通过一系列的在线行为建构了一个虚拟但稳定的交往空间。“锦鲤”的泛化,是青少年在网络亚文化的影响下,对“物”的兴趣丧失,转而对“符号”、“形式”感兴趣的表现。网络俗信作为青少年线上表达的一部分,其意义偏重于展示而非告诉,通过“转发锦鲤”时附上的文字来展示自己的近况,属于戈夫曼所说的“塑造自我形象的表演行为”,是青少年表达情感诉求、寻求身份认同的手段。青少年在现实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异化感和孤独感,借助转发锦鲤的方式,得到排遣和发泄。这一行为背后的运作逻辑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网络共同体,以“转发锦鲤”为代表的在线祈愿活动使网络俗信成为网络趣缘群体建立的途径。由于网络世界的虚拟性,青少年在网络世界的交往实践是一种主体间的符号互动,网络俗信也是个体化社会的符号互动的一种方式。[5]
青少年网络俗信现象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景观,早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在诸如QQ等平台上就有“转发这一消息就能收获好运”等相关信息传播,网络为各种信息传播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自然为社会俗信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渠道,使它的影响较以往的口耳相传更加深远,对人们价值观的塑造也更加明显。随着堪舆文化在网络的传播,在民间“说凶即凶,说祸即祸”的畏惧心理影响下,为求心安而跟风参与的网络俗信就类似于一种语言禁忌,是原始图腾崇拜的现实承接与降维,表现出符号崇拜与媒介崇拜的统一。霍克海默认为现代沟通媒介可以产生隔离的效果“在他们越来越被隔离起来的同时,他们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了。正是因为沟通把人们隔离了起来,所以才确立了人们之间的相似性。”[6]网络营造的虚拟环境,塑造了青少年假象的自由意识,而在自以为独立自由的虚假幻象中,许多青少年往往选择进行惰性模仿,盲目跟风转发锦鲤就是其突出表现。
(二)网络亚文化的短暂狂欢:真实的压力与虚拟的释放
按照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网络俗信是青少年表演的前台,呈现出的是“我正在努力”、“我快要转运了”等较为乐观的形象,而在后台,隐藏的是他们真实生活中的压力和焦虑。科层制的社会结构与极富流变性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压力源,身处其中的青少年会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对其身体、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考试、就业、买房,科层制下狭窄的上升通道,家庭代际沟通的矛盾等都是青少年转型期的“特色压力”。这种多方面的困惑与不确定性的压力是伴随其整个生活的状态的,不能避免,也无法逃避,显然也不存在某种捷径或手段可以将人从这种选择中彻底解放出来。网络俗信自然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现实生活对于未知的不安与焦虑,但短暂性的“无意识”一定意义上成为排解压力、消除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建立在对两种生活的划分,一种是官方、严肃的现实生活,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网络以其虚拟性与交互性为青少年提供了网络俗信的狂欢广场,“转发锦鲤”就是典型的狂欢语言,是制造狂欢气氛和狂欢感受的关键。这种狂欢带来了一种对真实好运的替代性快感,但这种快感通常是短暂又自欺欺人的,而明知其自欺欺人,却义无反顾投身其中,是因为在这场大众的狂欢中,“转发锦鲤”无需支付任何成本,也不会遭到任何指责。现实的巨大压力与真实情感寄托不能满足应对压力需要的矛盾,使青少年将这种不能满足又期望满足的情绪寄托于虚拟的网络俗信表达上。短暂的狂欢成为网络社会中青少年参与的主要诉求,网络亚文化的自我表达和解嘲使青少年能够实现当前情境中的脱嵌。自我评价和情感体验在狂欢状态下瞬间实现华丽转身,生活的重压在虚拟的网络事件中,借助“锦鲤”的符号实现了短暂的释放。
(三)后现代式的荒诞:自我表达与解嘲
现实社会的流变性与真实生活的压力,使青少年产生对未来生活的迷茫感,进而期待有某种介质来对人的性格和命运进行归纳和预测。明知转发锦鲤的线上行为与线下的真实事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受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影响,加上“转发锦鲤”与其他祈愿活动相比零成本的特点,众多青少年还是在清醒的状态下选择加入这场网络狂欢。知其不可信而行之,是对于戏剧性一夜暴富与不劳而获的一种调侃,包含了荒诞的黑色幽默感,是网络“丧文化”、“佛系文化”等亚文化的衍生,也是后现代式荒诞的一种体现。
同时,青少年网络俗信中充满了戏谑、自嘲的底层叙事,以反讽式的话语对抗来实现生活重压下的自我慰藉。青少年是乐于表达的群体,其表达方式同时兼具明显性和隐蔽性,一方面要求个性的展示,追求与众不同,一方面又敏感多思,渴望获得认同。弗洛姆认为“唯有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时,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力才有意义;唯有当内心的心理状况能使我们确立自己的个体行时,摆脱外在权威性控制的自由才能成为一项永恒的收获。”[7]青少年在这种复杂心理的影响下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状态,但其心理状况并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行为,期待摆脱外在的权威,可又总是受到权威的束缚,于是在这种尴尬、艰难的境地中将转发锦鲤这种荒诞的网络行为作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抗。
三、对青少年“转发锦鲤”网络俗信的引导
(一)培养媒介素养,减少“我向幻觉行为”
“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造”,[8]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与自媒体的繁荣,网上冲浪成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自我表达都变得“手机化”了,部分青少年将“转发锦鲤”以及类似的网络俗信行为作为自我降格来寻求现实调和的可能,作为一种自我激励与认同的方式,期待通过转发的行为,积极的心理暗示,兑换“自我实现的预言”。很多青少年即使在网上“转发锦鲤”,在现实生活中也依然积极向上,看似“无为”,实际对充满希望的转机无比期待。对这部分青年应当引导其网络俗信行为反向赋能的实现,创造可引导的空间,理解、包容,不过分夸大、过度解读,不表现出侵犯性,避免产生偏颇的情绪和偏激的思想。而对于一味沉溺于网络俗信,“万事靠锦鲤”的青少年,则更需要科学研判、理性应对、正面疏导,在网络传播中进行主流价值嵌入,线上线下及时把握青少年的社会心态动向,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引导青少年摆脱“屏社交依赖”,养成使用网络技术的价值理性。
当青少年转发锦鲤时,会自然的产生与行为不一致的想法,怀疑转发就能收获好运的可行性,短暂地受到认知与行为不一致的困扰,这一不愉快的情绪状态会促使其努力恢复一致性。根据里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青少年会试图通过改变认知来使其更符合行为。[9]即通过将生活中发生的幸运归因于“转发锦鲤”,或者向周围人诉说自己从转发中获得了“简单的快乐”,从而为转发的行为寻找理由,这种沉浸于虚拟实在的“我向幻觉行为”具有显见的沉浸倾向。[10]使青少年沉溺在虚幻的情境与社会关系中,表现出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价值选择与虚无化和去意义化的价值取向,进而导致理性思维的退化。这种不加审视的投入网络狂欢中是对规训的反抗,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规训。文本失去意义,图像只是情绪表达的载体,各种亚文化与社会思潮趁虚而入,对事物发展的规律缺乏本质性、规律性探讨的青少年容易陷入媒体与商业合谋的娱乐狂欢中。使青少年摆脱屏社交依赖,回归真实的社会交往,就要提高其媒介素养,警惕不良商家在锦鲤营销中进行虚假宣传,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引导青少年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积极进行自我评价与反思,培育理性思维,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志向,呼唤信息时代人文精神的复归。
(二)合理疏通压力,消除祈愿幻觉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11]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体拥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但并非知道如何选择,必须作出选择并承担选择的后果使风险社会下的个体倍感压力。“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同时也是对运气要求强烈的时刻。青少年在与时代的接洽过程中,个体焦虑的韧性与传统力量的式微相互较量,而网络俗信为这种矛盾的心理提供了一个出口,青少年通过参与这场网络亚文化的狂欢,宣泄现实生活中的“习得性无助”,将自己暂时从压力和孤独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虚拟的快感。但是盲目的跟风和无意义的参与仍然无法获得内心深处真正的解放,无法满足压力的完全排解。对于这种压力应对方式的异化,需要关注青年网络俗信映照的现实诉求,关切青少年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提供青少年以个体情绪的合理排解出口,引导青少年健康处理情绪,加强理论教育,注重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培育。
吉登斯认为,“焦虑必须放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不是仅仅被看成与特定风险或危险相联结的独特性现象”。[12]网络俗信作为具有明显青少年群体特征的行为,通过心理暗示,为青年人搭建了一种暂时的可控感,短暂地形成青少年对社会矛盾的幻想式解决。祈求一种单纯的赌博式的好运,以拜物的形式将无法预测和掌握的命运戏谑化、抽象化、神秘化,通过网络的扁平化特征压缩“神”与人之间的距离。[13]青少年参与网络俗信的过程中,将“神”的宗教色彩和神圣意义解构,表现出随意粘贴涂改的破坏性表意与改写,“锦鲤转发”、“锦鲤祈愿”、“锦鲤还愿”,成为“包治百病”的社会庸医,潜移默化地对无神论造成了冲击。因此,要警惕网络世界中迷信思想的沉渣泛起,避免产生青少年信仰危机,引导青少年对社会现实与情境保持理性的判断,消除祈愿幻觉,端正价值观,形成理性平和、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
(三)树立正确自我认同,培育奋斗精神
当线上祈愿与愿望成真发生偶然联系,青少年容易产生错误的归因,虚拟活动与真实事件成为因果关系。在强化理论的作用下,青少年容易在遇到人生的挑战时,选择再次在虚拟网络中祈愿,而不是面对现实,努力奋斗。将取得的成就与历经的坎坷全部归因于网络俗信行为,表现出明显的遁世主义与犬儒主义倾向,内隐着错误归因下青年的自我认同危机。同时,在现代性的环境下,传统的命运观依然存在,即认为事物的进程早已以某种方式被预先注定了。在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下,青少年容易认为个人所作出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的,因此放弃通过努力把握风险中蕴含的机遇,期待通过网络祈愿的形式获得好运的加成,祈祷“注定的结局”是偏向于自己的意愿。这种无意义的网络行为消解了主流文化倡导的胸怀理想、奋斗拼搏精神,其中潜藏的价值虚无主义,容易消解青少年对生活的热情,不利于青少年独立人格的建立,不利于培养青少年奋发精神,青年如果一味将对现实生活的期望寄托于网络俗信,无疑会失去奋斗动力,导致行动瘫痪。这种“我向幻觉行为”同时具有潜在的唯我主义倾向,由于网络虚拟世界的仿真效果,会形成明显的移情效应,通过转发锦鲤等一系列网络俗信行为,传递告诉自己的状态,获得别人的关注,习惯了这种行为方式的青少年,在真实社会生活中也会要求一切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这种行为与心理特征显然不利于现代利益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整合,也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自我认同。
在盲目转发参与这场网络俗信的狂欢时,青少年逐渐减少了对语言形式和表征的反思,通过形象取代概念与意义,网络语言表达从实际包含着的意义的承载物变成了没有内容的符号。以“锦鲤大王”的微博为例,众多参与转发者转发时语言极其单调,大多数转发者备注的文字为网络用语,如“少壮不努力,长大怪水逆。生活不如意,开始拜锦鲤”、“吸欧气”、“日常唯心”等等。当青少年频繁地把大众传媒与群众文化生产出来的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时,青少年的经验就日益变得贫乏,自我就萎缩了,[14]逐渐成为资本与媒体塑造的对象。因此,需要对网络俗信的价值误区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青年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针对网络俗信的后现代特征,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合理地嵌入主流价值倾向,为青少年提供健康良好、充满正能量的网络环境,引导其减少网络俗信行为,以努力奋斗成就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