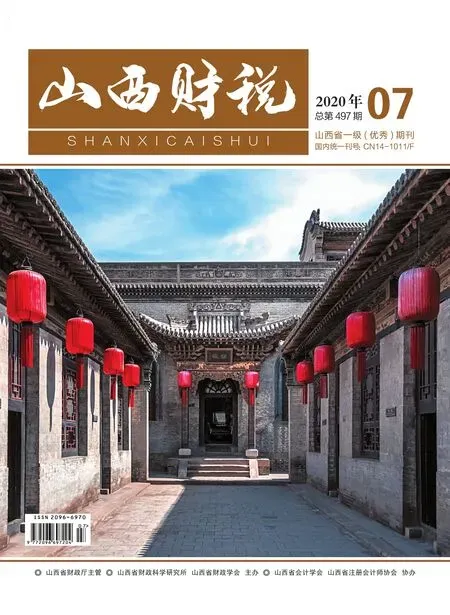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山西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
改革开放以来,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满足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对劳动资源的需求,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改变了城乡间的资源配置,也改变了农村农业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新时代,山西省“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即将终结、“第二代”农民工成为流动的主体,导致山西农业“老龄化”、“化学化”,增加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难度,制约了山西乡村的绿色发展。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流出、留住、吸引、培育有机结合的劳动力流动机制,促进山西乡村绿色发展。
一、山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
(一)“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即将终结
2016年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801.2万人,占2016年乡村常住人口的49.7%。2018年山西省农民工总量526.0万人,比2017年末增加8.3万人,占2018年乡村常住人口的34%,其中外出农民工259.2万人,可见“剩余”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正不断减少。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无限供给、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将逐渐成为历史。从民工潮至民工荒,从“有工就打,给钱就干”到对就业环境、工资待遇等的选择,都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只为谋生的“无限供给”的时代即将终结,农村劳动力的“有限供给”、“相对稀缺”将成为全国乃至我省的常态。
(二)“第二代”农民工成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主体
至 2020年 1950—1979年出生的“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年龄段为41岁—70岁,这一代农村劳动力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技术技能缺乏、外出务工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了“离土不离乡”、务工兼顾务农的特点。但是由于常年体力和精力的透支,导致40岁农民工被迫离城返乡,出现了农民工“40岁”现象。因此,“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生涯已经终结。
据山西调查总队调查,早在2013年全省农民工中1980年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40%。2017年全省农民工总量达517.67万人,比2016年增长了3.16%;平均年龄为39.4岁,其中“第二代”农民工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17%,比2016年增长了1.8%;男性占比高达72.38%,已婚占比高达75.4%。可见,“第二代”农民工已成为了我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体。这一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水平较高、对就业的环境与工资待遇期望值高、倾向于居家搬迁留城、渴望市民化。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受“跳出农门”思想的影响,虽从农村流出,但并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进入城市第二、三产业就业。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制约山西乡村绿色发展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农业“老龄化”
山西省的地貌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山区面积占总面积高达80%,耕地多崎岖不平,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农业生产如耕地、播种、除草、追肥、收割、晾晒等一系列繁琐的生产环节,都耗时、耗力,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以青壮年为主的“第二代”农民工的流出,使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多以50岁以上留守农村的劳动力为主。2016年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55岁以上人员占比19.9%,农业呈现出了“老龄化”特点。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匮乏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2019年山西省农作物种植面积3524.5千公顷,比2018年减少30.8千公顷,其中粮食种植面积、油料种植面的都有所减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这部分年长劳动者文化水平有限、体力精力有限,面对繁琐的、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只能选择适合机械化种植、适合大块土地种植、简便易收的高产量的农作物。农村小块土地撂荒、抛荒严重,农业“老龄化”使农业“薄种薄收”成为山西乡村的普遍耕种状态。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农业“化学化”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农业生产中所需的大量劳动力逐渐被大量农业生产资料所替代。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三大生产资料的投入,替代了人畜粪便、绿色沤肥等绿色有机肥料的还田,三大生产资料的使用却使传统绿色农业走上了“化学农业”之路。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2018年山西省农用化肥施用量逐年下降,但年均折纯量仍为116.31万吨,其中氮肥年均折纯量为32.15万吨,磷肥年均折纯量为15.28万吨,钾肥年均折纯量为9.89万吨。2018年山西省农作物种植面积3555.3千公顷即5332.95万亩,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为109.61万吨,计算可得,农作物亩均化肥使用量为20.5公斤,远高于世界每亩8公斤的平均水平;2013年—2018年山西省农药年均使用量为2.97万吨;农用塑料薄膜年均使用量为48438.38吨,2017年甚至高达5万吨。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的大规模、大范围的使用,造成土壤结构变差、微生物含量下降,导致土地质量退化、肥力下降,使农业生产陷入土地肥力下降——增加施肥——土地质量恶化的恶性循环。
山西农村农作物种植普遍存在重化肥、轻有机肥,蔬菜、果园等经济园艺作物也存在施肥过量的现象。化肥和农药的施用方式仍以人工施肥为主,地表施肥和喷洒的化肥农药对土壤、地下水资源、空气等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犹如“饮鸩止渴”,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农业面源污染竟成为农村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此外,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经营,大型连锁超市、农产品批发商等商业资本,将大量生产、集中销售的模式带入到了农产品流通领域,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生产和销售模式也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使用转基因种子、温室大棚技术、缩短农作物成熟的生长激素等,向市场供给大量的“人造”农产品。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陷入困境
山西素有煤炭大省之称,但多年来大规模、高强的煤炭开采,造成了地表塌陷、山体滑坡、地下水下降甚至枯竭,再加之干旱少雨的气候,使环境治理刻不容缓。除了农业面源污染外,农村生产、生活污染也严重破坏了山西农村生态环境。截止2016年,山西仅有63.9%的农村实现了生活垃圾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8.5%的农村实现了生活污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27%的农村完成或部分完成厕所的改造。由于山西水资源匮乏、农村多处于山区,现代的污水处理系统并不适合山西省。处理农村生产生活的垃圾、污水最好的途径就是修建沼气池,沼气池的综合利用既能为农村居民生活提供清洁的燃料、改善居住环境,也能为农业生产提供绿色农家肥料,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但是青壮劳动力的流出,家庭成员的减少,饲养牲畜量的减少,排泄物及生活垃圾也随之减少,沼气原料的匮乏使“猪—沼—果”、“猪—沼—菜”等绿色生产模式难以推广实现,增加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难度。
三、构建驱动山西乡村绿色发展的劳动力流动机制
(一)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农村流出人口市民化
农村劳动力向就业机会多、务工收入高的城镇流动,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因此,要逐步推进户籍制度的顶层设计,彻底解除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城乡二元户籍“枷锁”,尊重“第二代”农民工留城安家的意愿,让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民工有序落户城镇。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是居无定所、无归属感。因此,政府应合理出台农民工购房补贴政策,鼓励农民工进城安家,保障落户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推动农村流出人口市民化。如2017年山西省忻州市、吕梁市、临汾市、运城市等地相继出台了每平方米100—400元购房补助金和奖励金,鼓励农民工和农民进城购买商品房。
(二)以生态农业为核心进行三产融合,留住农村劳动力
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三产融合,是留住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发展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三产融合。一是构建以种植、养殖为核心,集加工、运输、储存、销售为一体的纵向融合产业链。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都要实现科技化、标准化、规模化,在农产品生产环节,杜绝使用化学种子,减少化学用品的使用量,实现生产源头零污染的绿色生产;加工环节使用清洁生产设备,减少化学添加剂的使用,保障农产品的安全;运输、储存环节要使用可降解的绿色包装、绿色清洁燃料等,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绿色供应。二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集养老、观光、休闲、养生为一体的横向融合产业链。天然、优美的自然环境是乡村最大的财富,基于特色农产品、自然风景、民俗文化等,打造多功能的生态园区,促进三产融合,为农民创收。如依托平遥古城的文化景观,打造集农产品制作体验、销售、观光为一体的生态园区。
(三)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吸引劳动力返乡
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合理引入社会资本重点解决山西农村的饮水安全、农户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等问题,探索以政府补贴和农户自付的方式普及自来水引入、清洁燃料的推广、生活垃圾的处理等,满足农村居民对干净、卫生的生活设施的需求。同时,加强农村网络、物流配送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便利的生活环境。增加农村养老、医疗服务的供给,加大对农村养老院、乡镇卫生院的投入和建设,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减轻青壮劳动力的养老负担,提高农村居民的抗风险能力。以生态宜居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吸引农村劳动力返乡工作和生活。
(四)振兴乡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农业人才
乡村绿色发展,关键在人才。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三产融合需要大量的田间种植能手、农业科技人才、电商人才和营销人才等新型农业人才。2018年山西中等职业院校毕业学生为111831人,其中农林牧渔专业的毕业生为5076人,仅占总毕业人数的4.54%,可见山西农业人才严重匮乏。而新型农业人才不可能通过短时间内的培训、学习就可获得。因此,要更新乡村职业教育的教育理念,立足于本地的农业生产、农村发展需要,改革乡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与农业高等院校联合培养新型农业人才,让绿色的农业生产理念、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产品营销模式等,真正应用到三产融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