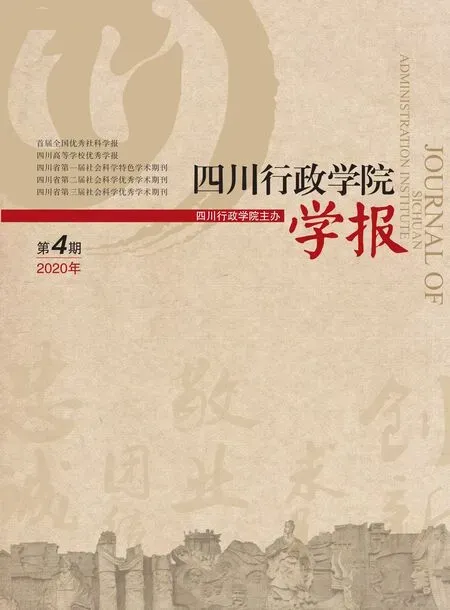城市贫困治理的时空正义性: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2)
内容提要:全面小康时代,反贫困的重点和领域发生了改变,解决相对贫困成为主题。城市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城市贫困治理在当前具有时空正义性和紧迫性。从时间正义性看,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扶贫关注领域的转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经济安全的脆弱性、老龄化社会的加剧等让城市贫困治理成为一种至善至道的治理重点取向;从空间正义性看,城市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城市的共富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空间领域,城市贫困治理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城市空间表达。这种正义性认知的构建,促进了城市贫困治理的时期转型,要求全面梳理城市贫困的类型和人群特征,采取内源性突破和外源性完善的行动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贫困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贫困治理需要在历史进程中根据现实逻辑解决。2020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扶贫之路开启了新的征程。全面小康时代,反贫困的重点和领域发生了改变,解决相对贫困成为主题。城市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之一,城市贫困治理在当前时期特征下具有时空正义性。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企业改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老龄社会的加剧等时期问题的深化而凸显。“贫困突然变得像流行病一样在城市里暴发”[1],张立宏发出了呼喊:“城市贫困层,不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2],于是城市贫困成为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陈相成,1997),从而进入了规模化研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着重呼唤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将研究视线放在了城市贫困的成因、特征、规模的测度等方面,认为社会转轨带来城市贫困问题(杨娅,1997),体制贫困是城市贫困的根源(权衡,1998)。进入21世纪,学者们在对城市贫困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更注重对城市致贫因素进行分析(杨钢,2001;林毅夫,2002;高云虹,2006);对城市反贫困的政策框架、制度建设、治理举措等进行设计(李军,2000;庄慧玲,2001;钱凯,2002;王卓,2004;李叶叶,姚雪萍,2007);而不同城市贫困群体比如城市农民工贫困群体、城市老年人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儿童等的帮扶体系构建等也成为研究的重点(李金滟,2004;李裕玲,2007;冯晓杭,2008)。
2010年后,学者们将城市贫困问题外拓,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多学科领域的融合上进行研究,涉及城市贫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 (王蓓蕾,2011),城市贫困的空间问题 (徐祥运,2011),可持续视角下的城市贫困治理问题(刘璐琳,2012),城市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李长健,2017),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问题(李梦娜,2019),城市贫困发生机制不同视角的解读(姚毅,2012),转型期新型贫困空间问题研究(吴克领,2013),城市贫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杨丽雪,2014,等等)。
2015年后,城市贫困的治理成为研究的重点,学者们普遍探讨了城市贫困治理面临的困境和路径问题,指出城市贫困治理需要构建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在逻辑上要进行从“救济”到“包容”,从“政府主导”到“多元主体共治”的转变[3](贺庆生,2015)。城市贫困的治理之道在于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以解决就业为导向激发城市新贫困群体个体潜能[4](范逢春,2016)。进入“十三五”时期后,学界开始关注2020年后我国的相对贫困问题,研究了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战略转型重点(谷树忠,2016;张琦,2016;左停,2016;李小云,2018;魏后凯,2018;谭诗斌,2018;凌经球,2018;孙久文等,2019;向德平等,2019;白永秀等,2019),2020年后相对贫困的主要特点(关信平,2018;唐任伍,2019;凌经球,2019),相对贫困的治理政策(汪三贵等,2018;桂华,2019;高强等,2019;叶兴庆等,2019),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模式(左停,2016;唐任伍,2019;黄征学等,2019)以及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机制(黄承伟,2016;关信平,2018;李小云,2019)。
总而言之,对城市贫困的关注在2015年我国全面展开脱贫攻坚战后稍有消减。2015年的脱贫攻坚战要求“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5],这让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注点都更多地放在了乡村的脱贫攻坚上。笔者以“脱贫攻坚”为主题在知网上进行检索,发现2015-2020年,共有15289篇论文研究该主题;而以“城市贫困”为主题在知网上检索,只有相关论文1408篇。后者不及前者的1/10。当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即将达成,新型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现代化征程徐徐展开,城市反贫困治理应该有新的效能。效能提升源于认知准确。基于此,全面认知当前城市贫困状况和治理正义性,为城市反贫困奠定理论基础就具有切实意义。
二、城市贫困规模与群体认知下的治理正义性
正义就是指人们适应时空发展环境转换和条件要求,实施自己应该做的行为,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本文中的正义,是以“正义”的哲学语境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当前进行城市贫困治理在时期上和空间上的 “适然性”和“应然性”。城市贫困治理“应然性”,建立在对当前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和群体状况认知的基础上。
(一)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认知
关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认知,实践层和学术界存在分歧。实践层从便于统计的角度,将低收入人群视为贫困人口。2018年我国民政部统计城市低保人口数为1008.03万人,较2010年的2310.5万人下降了1302.47万人,减贫成效显著。但2018年全国城市特困人员27.7万人,比2017年增加了9.1%[6]。城市低收入的认定标准,各省各市由于收入水平存在不同而标准不一样,但共同点是根据当地平均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而定。
学术界认为,城市贫困人群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纯以收入来界定,没有考虑到城市贫困的特征,没有考虑到新贫困人口。但究竟该如何界定,学界也尚未达成统一认知。在具体规模认知上,夏庆杰等(2017)指出“中国城市贫困状况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7]。范逢春(2016)认为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在8%,按照2014年城镇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总和计算,城市新贫困人口规模超过8000万人[8]。陈润卿(2017)提出,截至2016年年末,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已达到6000万人。谭诗斌(2018)利用自然贫困线分析法,测算出城市贫困率为 5%[9];而根据易迎霞(2018)[10]的研究,城市贫困在两大社会背景下会更加凸显:一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贫困更加凸显;二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流动人口规模增加引致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将会明显增加[11]。王锴(2019)认为应该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理解城市贫困规模,他通过CFPS得出中国1989-2016年城市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指数,数据显示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率多年来无明显改善,远高于城市绝对贫困率[12]。
基于此,城市贫困人口具体规模并没有权威性的数据。但在不讨论城市贫困人口内涵界定的前提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城市贫困人口规模不容忽视和小觑。在农村贫困人口减至四百多万人的对比下,城市贫困人群规模相对凸显,亟需应对治理。二是城市贫困人口的产生同社会机制体制改革有莫大的关联。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城市新型贫困人口有增加趋势。三是城市贫困人口涉及群体类型多,面积广,特征复杂,是一种相对贫困,在规模统计上和治理难度上较之绝对贫困更难以识别,更复杂,更困难。
(二)城市贫困人口群体表征与类型认知
1.城市贫困人口表征认知。城市贫困人群复杂,其表征具有多样性,因此在表征认知上要把握几个方面:一是城市贫困人口内涵界定复杂。经济物质标准是基本的标准,而能否满足基本商品消费和劳务支出,或者是否还有必要考虑能否满足教育、医疗等需求支出,甚或要不要考虑各类生存性机会的缺失等观点都存在。二是城市贫困人群识别困难。城市贫困具有“隐蔽性、离散性”特征。贫困不是光彩的事,城市人通常羞于将家庭贫困示于人前;同时城市贫困不是区域性、集聚性贫困,通常以离散形式存在,给识别带来了困难;此外,城市是“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很难了解彼此情况,传统的邻里识别方式很难发生作用。三是城市贫困具有动态性特征,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进程推进、社会结构转型等宏观环境的变化,出现了城市新型贫困问题,但这部分人群当前未被纳入城市贫困人口政策体系。
2.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类型认知。治理城市贫困,需要对群体进行梳理和分类,为分类施策奠定基础。在具体分类前,有必要从总体上认知城市贫困人群。民政部指出城市贫困群体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三无”人员、经济困难居民(如残疾人、孤寡老人)、贫困大学生等组成[13];朱火云(2019)提出,民政部门是按户籍人口进行统计的。城市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是不在统计范围内的,因此,城市新贫困人口应该包括城市贫困失业人员、贫困就业人员、经济困难居民、贫困大学生群体及贫困农民工群体[14]。这些是对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类型的总体认知,是一种官方实践认知和学界的修订认知。在这个总体认知下,我们可以对城市贫困人群按照不同标准进行群体分类和特征画像。
一是按照年龄来分,学界研究的主体范畴是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和未成年贫困人口。在学者们看来,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中的特殊弱势群体,贫困发生率比较高。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老年人相对于青年人而言更易陷入贫困,且与残疾人、儿童等相类似,一旦陷入贫困,很难依靠自身力量走出来,只能借助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力量,才有可能摆脱贫困”[15]。城市贫困青少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受教育机会不足引发贫困代际传递,同时存在就业缺乏规划的合理性问题。
二是按照有无城市户籍划分为城市贫困市民、城市流动性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市民是具有城市户口,纳入城市低保范畴的人口,他们具有贫困人口的普遍特征。尤为需要关注的是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城市流动性贫困人口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产生。在这些流动人口中,一些受教育层次低、技能水平弱的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着低收入工作,处于打短工和零工状态,工作稳定性和持续性弱,也无固定住所、无固定经济来源,被称为“新三无”贫困人群[16],极易因为失业或半失业而陷入贫困。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比率达到15.2%,比常住人口的平均贫困率要高出50%[17],显著高于城市人口。这部分人群既被排除在农村精准扶贫之外,又因为不是城市户口而不能纳入到城市扶贫的范畴,城镇户籍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也将他们排斥在外,处于城乡贫困救助的“真空地带”[18],反贫困工作非常复杂,给我国贫困政策体系带来巨大挑战[19]。
三是按照贫困持续状况划分,可以分为持续性贫困人口和结构性贫困人口。持续性贫困人口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甚至可能发生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类贫困人口应该是城市扶贫关注的重点,应更多从改善教育、健康、生产性支出等方面关注他们的扶贫问题。结构性贫困人口是由于暂时性失业、疾病、家庭特殊变故等原因而引致的贫困。这类贫困问题,“仅仅属于暂时的经济现象,因为外在因素是致贫的根源,而一切外在的、强加于人的因素相对于内在的根植性的因素来说,更容易被人为地改变和克服”[20]。
四是按照贫困形态划分为隐形贫困人口和现实性贫困人口。隐形贫困人口是近年来兴起的热词,是指“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但实际上经济非常脆弱的人”,主要是城市青年阶层内部的亚阶层(敖成兵,2019),他们因为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存在问题而具有经济脆弱性,极易陷入贫困。这种贫困已经在城市里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也存在一定的阶层认同和精神意指,表达着一种人生状态。对这类城市贫困人口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文化意象。现实性贫困人口是相对于“隐形贫困人口”的称谓,主要是指显然性地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生活困顿人群。他们的贫困能够被看见被感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经济力弱化,基本的温饱都难以满足,或者说“在满足温饱方面的支出要低于社会平均水平”[21]。现实性贫困人口不仅收入低下,个人能力也存在被剥夺情况[22]。这类人群是城市贫困治理的主要对象。
五是按照贫困内容分,可以分为经济性贫困人口、文化意蕴性贫困人口。经济性贫困,表现为生产、生活资料缺乏,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是一种绝对性贫困。文化意蕴性贫困,是由经济性贫困衍生或者说派生,两者基本上同时并存。经济贫困一般会导致消费贫困、权利贫困和文化贫困。城市贫困群体,一方面生活条件低下,另一方面,各种权能都受到限制,比如就业权、子女教育权、医疗权、居住权等相对缺乏,无法得到完全的保障和公平的对待。而这些权能的不足或者缺乏又导致贫困人口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更无法应对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变迁,逐步陷入贫困境地,形成恶性循环。这要求城市贫困治理不仅关注生存权,还要关注发展权。
六是按照贫困程度划分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人们由于各种因素难以获得保障基本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生存受到挑战,生活难以为继。陷入绝对贫困下的群体,缺衣少食,生活困顿,精神文化享受更难以企及。在我国,绝对贫困基本已经消除。相对贫困是比较标准下的贫困,其贫困程度取决于跟某种标准生活的距离。城市贫困主要是一种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难度更大,相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来说,意义也更大。
三、全面小康时代背景下的城市贫困治理正义性
在全面小康时代,致力于城市贫困治理,具有必要性和公道性。
(一)城市贫困治理是全面小康时代的重点任务
在我国,党和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理念,响应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呼声,始终将消除贫困作为执政的一大目标,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部署致力于消除贫困,尤其是消除农村贫困问题。2013年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思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精准脱贫战略。2020年成为消除农村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到2020年底,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将成为历史,战胜绝对贫困的经验将成为历史的胜绩。但这并不意味着全民脱贫,也不是我国反贫困行动的终结,而是新的、更加长期和复杂的反相对贫困行动的开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长效机制”的新课题,需要在新的历史阶段认真研究和解决。而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样本更多落在了城市,要致力于解决城市相对贫困问题,这也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相对贫困是表现之一。城市贫困问题,大体上是一种“相对贫困”,是一种 “富裕中的贫困”(冯丹萌,2019),“后减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重心要逐步转向相对贫困”(向德平,2020)。这将城市贫困治理纳入了视线,将改变“我国政府尚未将城市贫困人口列入反贫困计划中”(朱火云,2019)的现状,开启相对贫困治理征程。城市相对贫困治理也就成为了后扶贫时期的重点任务和难题,关系到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
(二)城市贫困治理是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内涵
重视城市贫困治理,在现代化体系建设中,具有必然性和应然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施了有序的发展规划,确立了明确的阶段性建设任务,让经济社会沿着阶段性目标稳步前进。就脱贫攻坚来说,党和政府一届接着一届抓,一年接着一年干,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取得了巨大成效,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贡献。到2020年底全面小康社会建成,贫困县将全体摘帽,党带领人民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征程。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达成,城市是重点,是关键。城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治理创新基本上都在城市领域发生。2019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有8.4亿多人口生活在城市。如果没有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就不存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城市贫困治理绝对是城市治理的内涵之一,蕴含着城市贫困的消减,蕴含着贫困治理举措的有效性,通过反贫困措施,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建设和谐美好的城市社会。
我国城市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城市治理的一大要求。城市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群是城市主体的短板和短腿,这部分人群的生活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和谐稳定和现代化质量。研究显示,如果城市贫困人群关于高标准生活和丰富多样机会的理想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是产生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原动力,会给城市社会带来不稳定性。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城市领域,必然表现为城市贫困治理的成效。实际上,就深度来说,城市贫困更甚于乡村,城市贫困治理挑战性更大。
(三)城市贫困治理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逻辑要义
当前,我国城市化采取了新型城镇化路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具有可持续性的城镇化,其内涵是人口的城镇化 (郭险峰,2015),致力于提升生活、居住于城市的人的福祉是新型城镇化的逻辑要义。城市贫困人群也是城市人的一部分,提升他们的福祉,削减他们的贫困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任务。新型城镇化和城市贫困治理的逻辑联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扩大了城市贫困人口规模。正如前文所说,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一些缺乏技能,文化水平低的农民工很可能因为跟不上城市产业化发展的要求,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失业,陷入到贫困,成为城市新贫困人口。这部分人群的反贫困工作因为成因复杂,且具有流动性,而增添了城市贫困治理的难度。二是城市贫困治理是新型城镇化和谐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城镇化过程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既内含着城市市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要求社会和谐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阐述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时,将社会和谐作为城镇化的“必然要求”。这表明,社会和谐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但城市贫困人口通常是利益和权力诉求的非满足者,在社会利益格局调整中处于弱势地位,还可能面临社会歧视、教育被排斥等难题,极易产生心理失衡和不满情绪,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由此,城市贫困治理就意义重大。三是城市贫困治理是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必然要求。城市贫困人群之所以贫困,就是难以参与到城市生产体系中去,因为失业而造成贫困。这表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能作用于生产,缺乏有效产出,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城市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群消费能力有限,甚至缺乏消费,不利于城市生产的拉动。因此,从生产和消费角度看,城市贫困治理将有效提升贫困人群生产效能和消费需求,为乡村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乡村产品的消费等提供基础。
四、空间逻辑下城市贫困治理的正义性
(一)城市贫困治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城市空间表达
城乡融合进程中,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空间领域不断延展,乡村趋于产业化、核心化。这个过程伴随着城中村的出现,伴随着流动人口的贫困化,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流动劳动力推升了城市贫困人群数量,中国城市出现社会极化的趋势。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因素也正逐步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主要因子,城市贫困人口的区位化现象也因而迅速凸显出来。国际国内城市社会的发展已经印证了这一点。Rana(2011)对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很快,对农村减贫效应很明显,但农村贫困发生了区位转移,转移到了城市,比如孟加拉国农村贫困问题转移到了达卡。在发展中国家,有近1/3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23]。张新红等(2019)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兰州市贫困居住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城市贫困人口聚居于被称为兰州的“城市伤疤”的城乡接合部,城中村与棚户区相间分布。也就是说,中国城市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特征和地域聚集性,城中村、棚户区等成为容纳城市贫困的空间载体。哪怕政府通过拆改着力于整治城中村问题,但只是使贫困农民工被推向城市的边缘地带,大城市的城中村再开发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
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逆的,乡村振兴的推进也是必须的,城乡融合是必然的路径。贺雪峰(2020)提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只有绝大多数农民进城了,农村剩下有限农民,农户才会有相对较多的农村获利机会,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也才能具备可能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必须同时推进城市贫困治理,关注进城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区域空间分布,关注城市化进程下社会空间重构和居住空间分异产生的城中村城市贫困特殊空间,推进制度安排同城市空间分异的契合性,城市化进程才是有效能的,乡村振兴才是值得期待的。
(二)城市贫困治理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城市呈现
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4]这蕴含了城市贫困治理的价值目标。追求“共富”的价值取向,意味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是对应于全体人民的,城市贫困人口在富裕路上不能、不会被抛弃。当前1000多万的城市低保人口,6000多万的城市新贫困人口是 “实现共同富裕”短腿短板的城市区域表现。实际上,由于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是经济增长的极点,对要素具有虹吸效应,因此“两极分化”在城市更为凸显,相对贫困程度也就更深。而且由于城市贫困具有“结构性陷阱”的特质,因此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对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并没有显示出理论上的结果,反而因为整体的水涨船高而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阻碍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尽早实现。基于此,重视城市贫困的治理,通过各项举措保证城市贫困群体能够生存,尽可能促进他们的发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缩小他们同先富群体的差距,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
五、时空正义下城市贫困治理实践行动
城市贫困治理基于贫困人群的复杂性而推进困难,单一的政策体系或应对举措难以适应巨大的贫困规模和复杂的人群特征,多元共治是基本的价值取向,分类施策是基本的行动方向,对此学者们已多有述及。中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完善,力图从低保制度、保险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构建一系列制度体系安排。但很显然,现行制度体系的安排仍存在“救助多于发展促进、贫困类型难以全面覆盖、政策存在交叉重叠”等问题,反贫困行动体系仍需优化。本文从反贫困的内外因作用方法出发,认为城市贫困治理的实践行动可以从内源性突破和外源性完善两个方面构建一个内外围合体系。
(一)内源性突破:贫困人群自我发展内生机制构建
发展权是当前学术界探讨和使用得比较多的视角,从长远计,从可持续计,城市贫困治理需要重视激发贫困人群自我发展内生机制的构建,通过自我力量获得发展的权能。当前贫困人口“被覆盖”的现状,不利于其主体性的发挥。一是积极树立脱贫主体意识,不悲观不沉沦,由被动到主动,由外推力转向内生力。在自我脱贫意识的建立和引导下,想方设法寻找脱贫路径,提升脱贫能力。当然,意识的树立是长期的过程,是外在环境变化的内生反应,需要各方面条件,特别是宣传和教育合力而为。二是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贫困人群之所以贫困,除开身体因素制约导致的能力缺失外,缺乏发展能力,包括缺乏参与就业创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方法和能力是主要原因。基于此,贫困人群要在自我发展意识的引导下,通过参与教育、培训,自我学习等方式方法,寻找到就业机会,提高参与市场竞争和就业博弈的能力,融入城市就业体系,拓宽收入途径,获得收入的持续源泉。
(二)外源性突破:发展型救济体系的完善
城市贫困是相对贫困,生存型贫困救济体系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从长远来看,基于贫困人口发展权构建的发展型救济才是政府着力的重点,特别是对失业造成的结构性贫困,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贫困人口来说尤为重要。政府要从三方面着手,构建一个完善的贫困治理体系。一是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型救助金低线,应对城市物价和通胀带来的生活水平挤压问题;完善城市医疗保障体系,规避低收入人群因病致贫难题;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准确对接反贫困政策体系。二是构建教育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政策体系。参与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政府一方面要关注贫困人群的自我教育问题,通过发放教育补贴、提供教育培训机会等手段,提升低收入贫困人群就业技能,使其获得就业机会,或者自我创业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贫困人群子女均等地参与教育的机会,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获得教育的机会,落实好教育部门 《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乃至通过救助形式不让贫困人群子女因贫辍学,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构建全方位社会动员机制,建设多元共治体系。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救济。积极应对当前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救济存在的非透明性和公正性缺失的质疑,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开放性、透明性建设,重塑信任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救助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