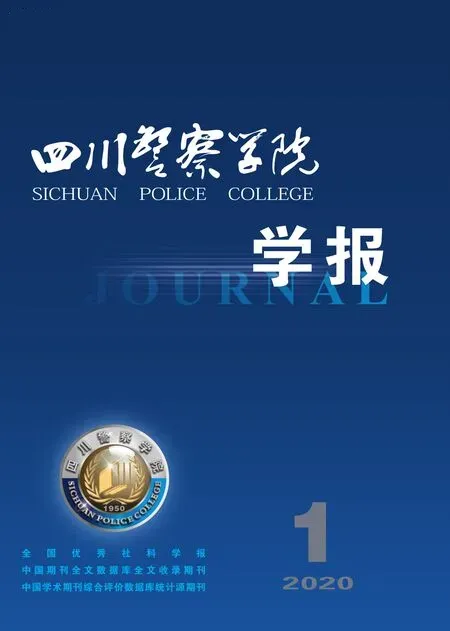甘孜藏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
——以公安工作为视角
陈安强,周天柱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泸州 64600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提出了新要求。这是从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从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甘孜藏区是全国第二大藏区四川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川、滇、藏、青四省区结合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长期以来,达赖集团图谋“西藏独立”的政治野心从未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遏制和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从未改变。甘孜藏区已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实施战略分化的“重点区”,达赖集团实施“藏独”分裂图谋的“轴心区”和“示范区”。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其信奉所谓的“丛林法则”。藏区的群体性事件,往往被西方反华势力冠以“人权”问题而大肆炒作,并借此诋毁我国的治藏方针和政策。藏区有别于内地的特殊历史性在于社会制度的跨越式过渡,即从农奴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在短期内难以快速跟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大对藏区经济的投入,使甘孜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各地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由于经济利益差别的扩大,藏区广大农牧民群众对待涉及经济的纠纷表现出非常激烈的状态。近年来,在甘孜州因草场纠纷、移民搬迁、下岗就业等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较多,聚集规模较大,对利益诉求的方式也较为激烈,这成为影响甘孜藏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近40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特别重视藏区政治安全问题的研究,而涉及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欠缺国家能力视角的系统研究。如何从政策和法律的角度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定性、分类并加以规范,快速有效、稳妥合法地处置好各种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对甘孜州造成的现实危害和不良影响,维护甘孜藏区的和谐与稳定,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甘孜藏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现状及原因
甘孜藏族自治州始建于1950年11月,是我国第一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总面积15.3万平方公里,辖18个县(市)、325个乡镇、2785个村,辖18个县市325个乡镇2679个行政村,幅员面积15.3万平方公里,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近300公里。平均海拔3500米,年平均气温7.8℃,极端最低气温-46℃,平均含氧量仅为内地的1/3,高海拔地区(石渠、理塘、色达等)更是七月飞雪、八月冰冻,条件极其艰苦。甘孜藏区生活着藏、汉、彝、羌等25个民族110万人民,藏族占总人口的81.5%[1],是四川省藏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为全国第二大藏区。甘孜州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其中黄河水系支流和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等长江水系河干支流的水能蕴藏量就达3731万千瓦,居全省市地州之首。全州林地面积6219万亩,水果、干果及其他经济林木资源分布广泛,是我国第二大林区西南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州天然草地1410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2%,多为优质低产草地。虫草、贝母等中藏药资源1137种,松茸、木耳等食用菌种达300余种,具有显著经济效益。金、铜、铁、铅、锌、云母等可利用储量的矿种36种118处。海螺沟、跑马山、稻城亚丁、丹巴甲居藏寨是川西旅游环线的重要景点。但是由于经济、地理等条件的限制,甘孜州的各类资源分布不均,且人均实际可利用资源较少,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地处高原上的广大农牧民对物质和精神需求不断增长,因经济利益需求而产生的矛盾越发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2019年甘孜藏区共发生63起群体性事件,参加人数较多、参与者的诉求多样。根据近五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原因分析,甘孜藏区群体性事件主要集中于四类:一是因资源权属的争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二是因草场地界争夺以及草场边界划分分歧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三是藏民采挖虫草、松茸等季节性资源因采挖地争夺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四是因矿产开采权、开采地的争夺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中,因草场、边界和虫草采挖问题产生纠纷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占比最大(约80%)且发生频率最高,也是甘孜州群体性突发事件最难调处的类型,即便当时调处平息,但是以后的复发率高。如乡城与云南香格里拉市的“5·29”枪击事件。除此之外,近年来甘孜藏区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因环境污染问题引起周边居民的不满,如2016年康定县“5·3”死鱼事件;二是因移民搬迁引发的纠纷,主要表现在近年来甘孜州较大的水利工程建设的增多,出现因移民搬迁产生的民意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并且此类事件苗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如因2015年康定姑咱镇浸水村村民对《四川省大渡河黄金坪水电站下游局部区域房屋门窗震动影响初步分析》报告的鉴定结果有异议,于9月15日引发的浸水村100余名村民聚集到黄金坪水电站大坝进行阻工的群体性事件;三是因刑事案件引起的争端。新旧因素的交织导致甘孜州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更为复杂、多样,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宗教因素的影响
民族与宗教关系密切,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互相缠绕。藏传佛教从公元八世纪中后期传入藏区后,经过1000多年发展演变,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形成了政教合一体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解放前的甘孜藏区,神权代表着政权,绝大多数农牧民信奉藏传佛教,佛教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精神支柱和对来世的追求目标。甘孜州寺庙多(512座,占全国藏区23%)、僧人多(5.7万,占全州总人口5%)、教派多(5大教派齐全)居全国藏区之首[2]。正因为如此,部分农牧民党员甚至少数干部存在着“双重信仰”,部分寺庙仍在追求政教合一,千方百计干预司法、干预教育、干预社会生活,甚至干预基层政权建设,一些群众“信寺庙不信政府”,而寺庙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衡量,在诸多矛盾纠纷中更倾向于对自身利益相关的一方,致使矛盾双方在调处过程中出现不公正现象,反而导致矛盾激化。这些都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彻底调处构成了障碍。
(二)跨越式的社会制度的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解放前,甘孜藏区封建制、农奴制、部落制三种社会形态共存,大多数藏族聚居区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在九龙彝族聚居区保持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在特别偏远的牧区如石渠、色达等地区则沿袭着部落制。解放初,全州农业生产水平低,1949年粮食亩产量100斤左右(约为种子的5倍),工业落后,城乡仅有极少数零星的、设备简陋的小手工业,国民教育程度低下,一些县甚至谈不上教育,如石渠、色达等县直到1958年才开办教育。解放后,甘孜藏区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社会发育程度低,生产力落后,部落和宗族势力残存延续,尤其在牧区群众对土司、部落头人后裔依然敬畏。这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产生着深刻影响。收入来源单薄必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强烈,这也是“三山一界”(草山、药山、矿山、边界)纠纷突出的重要原因。
(三)法制意识的欠缺
在甘孜藏区,由于种种历史地理原因,当地农牧民群众法律意识不强、法制机构建设不健全、法律执行较为困难,这些原因就造成当地农牧民群众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愿意以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由于缺乏一部完善的关于处理民族地区重大突发事件的法律制度体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无法可依[3]。同时,一些部门工作方式、方法简单落后,还有个别单位(主要集中在基层组织)行政不作为、滥作为,使群众对政府部门产生不信赖感,于是寻找法律以外的途径解决矛盾纠纷。
二、当前甘孜藏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
(一)聚众性高
在甘孜藏区以三人以上形成聚众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比较多,大多数是出于涉及到各方自身利益的纠纷,如草场纠纷。纠纷涉及范围无论是在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各方利益主体所在地的群众都会自发组成对抗队,人数少则十余人,多则上百人、上千人聚集在一起,甚至老弱妇孺都赤膊上阵,以人多势众来壮声威、造声势,借此达到震慑对方的目的。
(二)组织性强
一般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突发的、松散的,具有强烈的民意目的性。近年来在甘孜藏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出现了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动机制。首先,在群体性事件的事前,参与者之间进行了有计划、有预谋的准备,包括行动方案的制定、目标任务的确定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的确定等。其次,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参与者之间以组织领导者为主进行有分工的行动,或煽动围观群众参与,或组织人员打砸,或阻拦调解人员发言等。最后,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参与者根据达成目标的不同出现事后的角色转,化如有的集资上访,有的聘请律师,有的以受难者的角色寻求媒体支持,以扩大事态的影响,等等。在整个群体性事件的聚散进退中,事件的指挥者或骨干成员又根据群体性事件发展情况,对参与的成员在幕前幕后进行角色转换。在指挥者的游说怂恿下,部分农牧民群众原有的轻微不满情绪容易被放大,从而产生过激言行。这使事件加速恶性演化。。
(三)阶段性明显
许多群体性事件都发生在甘孜藏区所称的虫草季节、松茸季节。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甘孜藏区中存在着很多边界争议性地带,处于争议地带的农牧民对政府部门勘界成果认同度不高,特别是随着虫草、松茸等资源价格上涨,个别地方的个别边界地区群众出现了“寸土不让、寸草必争”的现象,从而导致了大量的冲突和纠纷事件发生。如2016年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东旺乡村与甘孜州乡城县白依乡因日努共草场采挖虫草,引发的枪击事件。
(四)暴力性突出
当发生群体性纠纷时,大多数农牧民群众将“法不责众”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参与者个体存在差异性。这些不同年龄、性别、性格、职业和利益诉求的复杂人群在组织人员的互动下,极易引发导火索爆发冲突,冲突各方各自聚集人员,有枪的扛枪、有刀的拿刀,没有刀枪的持棍棒、捡石块,“十八般武艺”通通献出,互相拼狠斗勇,不计后果,往往酿成恶性流血事件。
(五)反复性多
反复性是指因同一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次反复出现。在藏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反复性具有其特殊性,藏区群体性事件的反复发生的原因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每个时期随着各种资源的价值变化,争议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如在藏区畜牧业经济市场好转时,对牧场的纠纷就会在旧的协议上产生分歧。而在虫草和松茸价格上涨时,又会因草山地界问题产生分歧。二是每一代人对资源利益追求的不同,产生的纠纷存在差异性,导致纠纷具有长期性、反复性。例如云南香格里拉市和乡城白依乡草场纠纷经历几代人,每次通过不同方式达成的协议都不能长久稳控。三是群体性事件主体抱有错误的认识观。藏区农牧民法律意识普遍不高,许多人把相关政府部门的调处当成“闹”的结果,错误地认为“只有闹起来,政府才会管起来”。如此一来群体性事件往往反复发生。
(六)破坏性大
群体性事件常常对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安宁,扰乱社会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4]。在甘孜藏区,当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双方无论男女老少都会丢下手中事一齐上阵既误了发展生产、抓收入的良好季节,又造成人心惶惶,影响了社会稳定。此外藏区家族与家族、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一旦爆发群体性事件,容易引发“新仇旧恨”,而藏区特殊的宗教信仰、人文环境使得藏区群众难以接受公安机关的调解,这也给公安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三、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
处理甘孜藏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处理反“藏独”分裂活动的敌我矛盾二者存在着根本区别。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以物质利益冲突为主的具有一定程度对抗性的矛盾,但受特殊因素影响其在一定条件、一定场合下可能对抗性表现得也很明显。对于这些对抗性增强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仍然不能以处理“藏独”分裂这类敌我矛盾的强制方法和手段来处理。在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应将其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事前、事中、事后,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动态处置的思维模式,即既要注重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前因事件,也要注重因群体性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的结果事件。要认真分析甘孜藏区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及时发现矛盾苗头,及时进行化解,防止矛盾沉淀积累,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群体事件发生过程中,要保障使其向非暴力对抗的方向转化,直至矛盾解决。在群体事件处理解决后,应注意吸取“前车之鉴”,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将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大力营造藏区社会主义法治环境。
(一)做好事前矛盾化解工作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开展一切藏区工作的基本遵循。坚持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以最恰当的方式处理甘孜藏区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才能做到在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保障藏区民众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要根据藏区群众的不同民意需求,创建民众进行情感沟通、冤屈表达、夙愿陈述的事前矛盾沟通、化解机制,让藏区民众在发生矛盾纠纷时候,可以适时地寻求相关的地方协调机关或者协调人员,陈述自己的要求愿望,发泄压抑已久的情绪和不满,从而舒缓他们的心理负担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重视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且牵涉面广、反映强烈的群众合法利益问题,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首先,公安机关要建立健全矛盾日常调处机制,加强对群体性事件苗头的研判,掌握规律特点,确保各类群体性事件苗头得到疏导化解。其次,要拓展信访、投诉、沟通渠道,使各种矛盾纠纷得以及时掌握。最后,对掌握的问题应坚持主动提前介入,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重点群体的矛盾分析研判,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超前落实对应工作措施,先期缓解矛盾,防止因矛盾累积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健全情报预警机制
群体性事件有突发性和潜伏性两种,但无论是突发性还是潜伏性,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任何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把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是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最有效的方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实践证明,群体性事件只有发现得早,才可能控制得住,处置得好。因此,应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的工作理念,把事前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充分发挥群众力量以更快、更准、更深、更广的方式获取情报信息,建立积极主动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事前预警机制。一是要强化情报信息收集意识,将获取情报信息纳入预警范围,将情报收集工作贯穿于基层工作之中。二是要构建藏区情报信息网络一体化结构,以基层组织为主体,建立横向覆盖藏区各个区域的情报信息网,纵向贯穿于各级基层组织部门的情报分析研判一体化架构体系。三是要建立对不稳定因素的排查机制,对藏区的重点地域、重点人员、重点行业等进行排查,及时发现可能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安定的因素,了解问题的苗头和态势,及时进行分析汇总,形成系统完整的情报分析报告。
(三)完善公平正当的执法程序
1.在参与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公安干警应明确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劝阻、疏导工作,防止事态扩大。因此,公安干警一定要遵守“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原则制定处置方案,切忌随意抓人、随便动用警械,激化矛盾。同时,在事发现场又要审时度势,抓住时机,维护法律尊严,依法果断处置。对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事件,要注意深挖藏在幕后的策划主谋,在证据充分和力量充足的情况下,要派便衣参与到闹事群众中发现主要骨干和犯罪分子,机会成熟时,可当众揭露其阴谋并对主要参与者依法果断处置,实施现场抓捕,强制将其带离,以免造成更大损失。
2.严格法律界限,坚持宽严相济的处理原则。在处置过程中,应针对不同的参与者,坚持依法妥善处理。对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对其进行认真教育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放宽,既往不咎。对唆使煽动、挑起矛盾、制造事端的一般组织策划者,要认真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宽严相济,适当从宽”“惩办与教育相结合,重在教育”的原则,适时进行处理。对极少数人别有用心蓄意滋事,乘群体上访之机搞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依法严厉打击,决不心慈手软。
3.做好群众工作,及时收集证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现场的不确定性,加之群众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意出来作证,该类事件的查证、取证工作往往难以开展。因此,公安机关一方面联合基层组织或者地方维稳部门做好群众沟通协调工作,结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认真进行劝导,以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另一方面,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展情况,抓紧抓实现场调查取证工作,及时固定证据。通过积极走访调查及时了解事态发生的起因,以及引发事件的主要成员,采取果断措施对其进行及时控制。通过录音、录像等设备及时固定现场煽动闹事、指使他人进行破坏活动者的违法犯罪证据,为事件后续的处理提供可靠依据。
4.准确定性,依法处置。由于藏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大多带有一定的民意诉求和民族宗教色彩,一旦对事件主要人员的处置不恰当,就有可能进一步引发民众的不满,损害法律的威严,同时,也可能成为境外分裂势力进行反宣舆论造势的把柄。因此,在处置事件过程中,应当注重对参与人员的准确定性,适用正确的法律条款进行处罚。(1)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即是属于轻微违法行为,还是明显违法甚至构成犯罪的行为。(2)准确界定行为性质,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其甘孜州相关规定准确界定其行为性质,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准确界定其所犯罪名,必要时可以要求检察院或者法院参与调查工作中,提供法律指导。(3)对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地方公安机关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治安违法人员时,处罚的幅度一定要注意与被处罚人的主客观因素以及社会综合因素相结合。同时,在处置过程中,有关地方领导出于藏区维稳局势的控制,对公安机关的处置要求过于强硬,追求迅速处置、迅速结案,避免事态的扩大化影响。这容易忽略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的准确界定,反而会为藏区社会治安的稳定埋下隐患。因此,处理藏区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件,一定要坚持法律原则,严格依据法律程序办理,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进行定罪量刑,确保处罚的合法性和准确性。
(四)构建长效性综合应对机制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突出特点是情绪过激、行为过激,加之藏区彪悍的民族性格,如果以硬碰硬,势必碰出“火”来,扩大事态,激化矛盾。因此,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因情施策,灵活运用战略性处置策略,妥善处置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一般不宜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强行阻止,对群众的合理要求,能够解决的要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要拿出解决计划。确实无法解决或要求不合理的要向群众讲清情况,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要坚持依靠法律和政策办事,不能为了平息事态而做出违背法律和政策的承诺,不订“城下之盟”[5]。对煽动闹事的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要加强证据收集,对冲击党政要害机关、阻断交通特别是交通大动脉的或趁机进行打、砸、抢、烧的要旗帜鲜明、果断快速地予以惩治。对混入其间的民族分裂分子、非法宗教邪教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要高度关注,适时打击,避免非政治性问题演变为政治性问题。
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预防为主、力争主动、关心群众利益、教育疏导和民主法制原则”,坚持“可疏不可堵、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逆”的原则和“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6],各级党委、政府是处置工作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政法机关和各职能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开展现场处置工作。同时,如若事件一旦发生,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的指挥者应本着“战略上积极防范、战术上果断处置”的原则[7],寻找战机、控制局势,掌控事态主动权,因情施策,灵活运用战略手段进行妥善处置。具体来说:一是反应要迅速。在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要在第一时间组织警力赶赴现场,稳控事态,展开调查,固定证据,查清原因、经过、诉求等情况,对参与人员做好情绪疏导、思想教育等工作。同时要在第一时间向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汇报情况。二是部门要密切协作。处置群体性事件时间紧、任务重,往往涉及公安、信访、维稳、司法、安监、卫生等多个部门,单靠公安机关一家难以及时高效处置。因此,必须要坚持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处置,形成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合力。要明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各自职责,杜绝出现相互推诿、办事拖拉等现象。三是稳控要有力。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对参与人员开展情绪疏导、政策宣传、法制教育等工作,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解决问题,督促双方协商解决问题。对情绪过激、扬言上访滋事的重点人员,要落实措施,加强管控,确保事态不扩大,人员不失控。四是处置要灵活。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既要对参与人的合法诉求予以肯定,对其困难表示理解,又要严厉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敦促其依法表达诉求。
(五)加强事后稳控体系建设
群体性事件平息后,如果不及时跟进后续管理,很容易出现反弹或者反复,尤其是事件中的个别人利益受到损害或者解决中谈好的条件不能及时兑现的情况下,就很可能会使前期的工作“付诸东流”,甚至会出现报复性反弹,导致比前期更为严重、影响面更大的事件。因此,群体性事件的后期阶段,公安机关也一定要抓好善后处置工作,确保处置彻底到位。要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后续工作,加强对涉事人员责任追究和法制教育,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互通讯息、形成合力,解决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平息群体性事件后,要对承诺解决的问题,逐一落实兑现,对可能导致反复的不安定因素,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及时化解。要通过开展善后回访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提升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水平。要强化责任,严肃追究。对发生的每起群体性事件,要定性定量分析,了解深层次、内幕性情况,按照责任追究规定,对因部门负责人未依法履行职责,致使能够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排查调处矛盾不力导致矛盾激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以及贻误战机、处置失当、造成事态扩大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工作沟通,及时交流,敦促相关单位履行法定职责,进一步做好社会矛盾的化解工作,以消除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环境和条件。
四、结语
甘孜藏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大、发生面广量大、影响因素复杂,处置难度高。公安机关应提高重视度,去除见惯不惊的心理,同时也不能惊慌失措,应抱定良好的态度积极应对。要深刻领会党的藏区发展政策,提高站位,加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机制与系统的构建,并在运行中不断予以完善。要发挥防控机制、矛盾释放机制、信息处理机制等多层次多维度机制对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作用,通过有机整合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达到预防机制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为甘孜藏区的发展创造一个成熟健康、法治进步、高效有序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