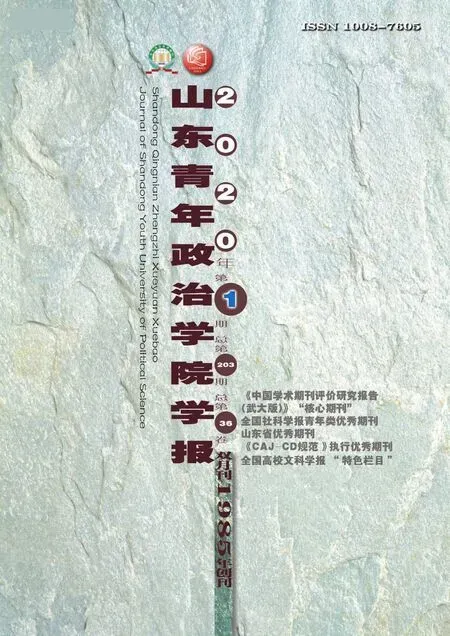狂欢话语中的当代青年成长与文化认同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叙事解读
姜吉林,逯 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济南 250103)
2019年下半年,仿佛是一夕之间,中国电影,确切来说,应该是中国动画电影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作为标志,豪取商业票房与艺术口碑的双重丰收。像极了片名“魔童降世”,它的出现,好似中国电影艺术美学探索集中爆发的某种隐喻,截止到10月7日,其实时票房已高达49.7亿[1],距突破50亿仅有一步之遥,仅次于中国影史上《战狼2》的56.8亿元,豆瓣评分基本在8.7与8.8分之间。围绕此片的高票房与主题,网友们展开了各种热烈讨论,从而使该片的播映成为热点的公众事件。不可否认,作为一部剑走偏锋的动画电影,它成功地搅动了中国电影市场,成为了某种“现象级”的影片,但同时它的成功,又表征着特殊的时代情境与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为什么是动画电影?为什么是中国古典文化叙事题材?检视《魔童》的叙事主题与结构、当代青年群体文化心理多元复杂的时代脉动,以及大众流行文化及话语方式在当前青年群体的符号化传播途径,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动画电影探寻民族性艺术精神与青年群体在当下历史时空中复杂多变的身份认证的契合可为实现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当代青年生命成长路径提供一种合理的参考,大众流行话语与传统美学的互相融入是当代青年在艺术上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探索方式。
一、当代青年成长与身份认同
很明显,《魔童》其叙事内容包含着一个成长题材的主题内核与框架,作为以青少年群体为主体受众、导演亦主要是青年群体的当下中国动画电影,成长主题备受关注。在影片故事中,哪吒的成长历程颇具象征意味:由于怀胎三年,与魔丸伴生,哪吒甫一出生,便受到了某种隐喻性“正统主流”文化的规训。作为大众麻烦的制造者,公众良俗秩序的颠覆者,哪吒从小的成长之路虽无主观恶意,但由于天生神力或是魔力,他经常给百姓带来灾难,在众人眼中,他就是带来不祥与厄运的“魔童”,是“妖”,而影片的叙事也确实是在祛“妖”的身份认同整体框架中实现的。在西方亚文化研究视域中,青少年族群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叛逆性的群体身份特征,需要主流社会的规训与压制,因为“对立价值观表达了对社会中主导的合法控制结构的不满或干预”[2],于是在影片叙事中,从小哪吒就被规束在李府大院,陪同他玩耍的只有家丁随从以及父母亲;但即使如此,他的魔性或是叛逆性仍然使他能够偷偷潜入公众社会,造成轩然大波,后来,太乙真人又成功地把他束缚于“山河社稷图”的独异空间中,这实际上是喻示了当下青年群体对于主流社会的抵抗颠覆与正统社会的话语系统对其反复的规训其对抗关系的一种象征性话语,从而确立了非常明显的一对二元范畴。
但是青年群体的成长需要中国当下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与洗礼,正是在此点上,影片的思考与艺术处理让我们眼前一亮,也使西方青年亚文化研究其二元对立式的研究方法失去了话语解释权。在此,我们以同样优秀的国产动画电影,1979年的《哪吒闹海》作为我们探讨《魔童》的互文性参照,《哪吒闹海》中的哪吒由于路见不平,杀死了龙太子,触怒了主流社会秩序,原来的李靖父亲形象成为了压制叛逆性的传统父权形象,于是二元对立的结果是反抗与颠覆,最终哪吒剔骨还肉,切断了与父系的联系。不得不说,在1979年那个时代,这种处理方式带有很强烈的时代特征,哪吒形象成为象征性地反抗那个时代被意识形态化并加以批判的传统“孝道”的特殊符号。时至今日,中国当下社会其文化心理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3],“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4],叙事的讲述同样呈现当下的历史性,《魔童》对父亲母亲形象其叙述进行了颇有意味的转换:面对哪吒招惹的无尽是非与麻烦,《魔童》中的父母,总是以爱之名,对哪吒施以巨大的宽恕、包容与教化,甚至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成为哪吒最终转换为英雄的至为重要的力量,尤其是父亲形象,一改《哪吒闹海》中的粗暴与威严,其“慈父”特质使他为救儿子前往寻找元始天尊,而且愿意以血亲换咒符与哪吒共同承担天劫,从而颠覆了旧版中“严父”的刻板形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成为了某种“超理性”的存在,因为他始终确信在他的努力下,三年之内可以将哪吒导向正道;甚至在哪吒三岁生日当天,当哪吒已经知晓自己的“魔丸”身份时,也是父亲告诉哪吒“别人的说法都不算数,你自己说了才算!”,这在哪吒最终实现身份认同,回归传统正义中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母亲则扮演了颇富当代女性气质的“慈母”,她也始终相信哪吒,相信哪吒哪怕是魔丸再生,仍然可以弃恶从善,获得拯救,只不过这个在旧版本中温良贤淑的传统母亲形象,经过导演饺子的一番当代性转换,变成了颇富当下大众文化气质女性特征的“慈母”形象:是她,在太乙真人要除掉祸患、杀死魔丸的时候,抵命相救,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她,“不爱红装爱武装”,在电影中被设置成一位花木兰式英雄形象,与夫君李靖共同戍边抗妖;同样是她以颇富当代教育理念的母亲形象,鼓励哪吒,敢冒受伤风险陪哪吒踢毽子(因为哪吒天生神力),甚至欺骗哪吒是“灵珠转世”,使哪吒的身份认同趋向正义,努力将哪吒的魔性转化成救民危难的英雄主义行为,实现主流认同。影片叙事中,电影分明是将哪吒母亲的形象塑造成了一位在孩子青春期成长中实施了成功教育理念、“妇女能顶半边天”,富有某种“女汉子”气质的当代中国女性,实现了与当代大众文化的接壤,这是影片获得受众认可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由于电影中父母形象这一根本性的设定,使得在青春成长的道路上,哪吒一直处于一种父母关爱下寻求社会认同的身份确证中,这种身份确证被规范在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为特征的社会集群性文化中,是个体对于群体价值的主动回归与认同。在叙事中,影片极力渲染父爱母爱的当下性,以及叛逆之子对于亲孝关系的反思和对父母之爱的反哺,这显然是对传统孝慈家庭伦德的当代复归,是以饺子导演为代表的当代青年群体对于中国式家庭亲族关系甚至家庭教育的某种思考的投射,与西方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规训与反抗、惩戒与颠覆、被动性收编的社群文化特征的二元论主题存在根本性差异。
二、古典叙事题材与国族性传统文化思维认同
《魔童》借用了古典叙事题材,但在影片中,哪吒的成长之路不单纯是祛除亚文化属性的青年叛逆、回归正统、建功立业,最终达致主流认同的传统路数,在青年成长的叙事主体框架中,另外一个颇具中国文化特质认知模式的“善恶二元关系”的命运式主题构造成为表达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叙事源动力。也就是说,在青年成长,回归社会集群,实现当代中国青年身份认同的框架之外,更有一个涵纳一切的命运主题,而这个主题其内在的思考,更具有中国文化气质。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展开的起点可以说是对于生命的思考,阴阳之道、天人关系等这些根本性的中华文化命题极具人类文化普适性,《魔童》正是由于在整体叙事框架中引入了这样一些终极式的命题思考,使得它的内涵更为丰富。
哪吒本应该是灵珠转世,阴差阳错之间,最后成为了魔丸转世,而灵珠却成为了龙子敖丙转世。但在影片叙事最开始的时候,灵珠与魔丸却是共生于一体,脱胎于混元珠,而混元珠的形态在影片构图中也是以鱼的形态呈现,其形象设置画面美学系统实际上是借用了太极阴阳鱼的形态(虽然是一个样子邪恶的鱼形象),“它贪婪地吸收日月精华”,阴阳两者其关系随着叙事的展开,也逐步被置换成善与恶之间的复杂关系。西方文化研究的认知模式是善恶二元对立,它会摄取其中一极,在艺术表达上,要么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英雄主义主题,要么就是正义善良被遮蔽、好人受难的悲剧,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中,阴与阳、善与恶的关系远为复杂。仅从太极阴阳鱼的关系构图来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二者相伴相生,却又互为转化,这实际上是《易经》式思维。世间的事情并没有绝对的二元分别,都是共生共长,互为转化。善恶也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善可以转化为恶,恶也可能趋向善。而且在中国文化思维的最高层面,是摒弃善恶对立的二元思维的,其关系呈现为即善即恶,非善非恶,善即是恶。这种复杂的中国文化认知,被影片叙事置换成关涉个人成长终极思考的命运主题,并最终被具化为哪吒与敖丙之间复杂多元却又共生的关系。
在二者之间原初关系设定中,有一个身份认证从而确定的善恶选择问题,即妖代表恶,人代表善(影片中哪吒对别人将他视为“妖怪”的身份认知深恶痛绝),申公豹和他的弟子敖丙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是民众眼中的“善恶”,确切来说,这是成见或是偏见。哪吒是人,本应是灵珠转世,因为“李靖是天命之人”,那么他的儿子哪吒也应是行匡扶正义之责,铲除奸魔的大运大善之人,但最终他魔丸入胎,成为众人眼中的“妖怪”,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是源于一椿恶的机缘:申公豹出于嫉妒,破坏了元始天尊的计划。而敖丙本是龙族太子,是“妖”,但却由于申公豹的报复计划,与龙族达成交易,成为了灵珠转世的胎体。二者的成长过程其两相对比也架构了影片叙事的重要内核,即善恶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从外貌来看,哪吒充满魔性,形象符号也采用了烟熏妆(这一点亦成为影迷热议的话题),从行事风格而言,他从小就是个“混世魔王”,打架斗殴,给地方百姓带来重重灾难与烦恼,成为众人眼中的“妖”,这个形象身上布满了“恶”的因素。但是在影片叙事中的成长主题表达中,我们也注意到,此“恶”或许也是由于民众从小赋予的“恶”的偏见,将一个原本天真善良的哪吒逼成了众人眼中的“妖怪”,所谓民众之“善”与哪吒之“恶”,其实很难泾渭分明予以决断,因为正是由于对“善”的执著追求,使得哪吒始终保持清醒自知,没有泯灭自己的良知,最终成就了自我;敖丙,作为龙族太子,本应该也具有无上地位——龙族当年是天庭镇压妖族的借力,但是由于他们的“妖族”身份,在民众眼里,他们显然属于恶的化身,也不为天庭所信任。但是由于灵珠入体,敖丙却成了“善”的化身,他的长相帅气,行事善良道义,曾帮助哪吒惩治妖怪,挽救小妹,也曾反驳师父申公豹为哪吒辩护:“若不取掉乾坤圈,哪吒也并非十恶不赦”,但他虽是灵珠本体、“善”的本性,却由于他的妖族身份,即使是为善,帮助民众,也突破不了民众对他们认知的偏见,因此他只能遮掩着自己的妖族特性与印记(头上的龙角),当被民众发现其龙族身份后,即使他拯救了民众,但仍被李靖为代表的他们斥骂为“是狗改不了吃屎”。而且由于怕龙族秘密泄露,善良如他,也不得不从妖族群体利益出发,试图毁灭陈塘关,他开始从“善”转化成了事实上的“恶”。无论是哪吒还是敖丙,都面临着一个有关自我身份确认的二难选择:他们二人皆有着追求善与正义的本性,但俗世中的人们却有将他们认定为“恶”的偏见和成见。在影片叙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们的命运,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思维中关于善恶认知的复杂多元性,如何处理这种身份认知的复杂性,也成为考验影片叙事逻辑的重要一环,答案还得从中国传统性文化思维中寻找。
最终在成长过程的身份认同与艰难抉择中,“我命由我不由天”,“若命运不公,就和它斗到底”,哪吒这最终的觉悟成为了整部影片的核心主题,同时这也是一个颇具存在主义色彩的现实选择,但这其实源自古老的中华文化智慧,是破解影片叙事主题的关键。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尤其是《周易》前两卦乾卦和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易经,这两卦包含着中华文化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创造,并非宿命,即“命自我立,福自我求”[5],后世无论儒家、道家亦或是佛家,在文化观上都秉持这种命运观。对哪吒而言,实际上就是“我命由我主宰”,他同时将这一觉悟传达给了敖丙。当敖丙败于哪吒枪下,怯怯地说:“我是妖族,出生那一刻命就定了”时,是哪吒给他以振聋发聩般的启示:“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这种主题设定实际上是对于传统文化关于生命命运等形而上宏大命题的认同与回归。
在叙事及画面美学方面,影片进一步在细节上与传统价值体系施行了认同。中国传统思想中,“道”为一切的根源,宇宙中所有事物,包括命运所展开的区间,都是在道的统摄中展衍的,这个“道”的布设,影片通过一个有意味的隐笔实现,那就是“乾坤圈”,在《易经》思维中,乾是天道,坤是地道,乾坤卦是最圆满的卦象。哪吒只有在乾坤圈的规束下才是清醒自知的,当哪吒没有乾坤圈加体,他就是混乱无序、失却自我意识、给天地苍生带来灾难的魔丸,是焚毁一切的灭世火童,是“恶”。这意指着只有在“道”的规范内,哪吒对命运的抗争与主宰才具有合法性;与此同时,哪吒与敖丙既有相对的敌对关系,又充满人情的朋友之义,他们这种对立共生的关系,在画面美学上最终成为动态的阴阳鱼。哪吒是火童,敖丙是水龙,当两人携手共同抵抗天劫时,影片出现了水火既济的动态阴阳鱼图案,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而水火既济卦在易经体系中,正是经历了重重磨难,获取圆满成功的第63卦[6],影片用一个富有诗意的场景结束了此叙事段,天上落下了滴滴甘霖,陈塘关的百姓们也经历了劫后重生及对哪吒与敖丙英雄正义巨大付出的感动,他们都双膝跪下,所谓的善与恶在此达到了最终的和解。
正是这种对于阴阳善恶、天道命运的终极思考奠定了影片叙事的最终框架,也使影片的叙事表达充满了深刻的“中国性”特征,回归了国族文化传统,从而使影片的整个叙事表达带有形而上的意蕴,这一点或许也增加了西方受众在理解上的难度。
三、大众狂欢话语、传统绘画美学与当代文化认同
《魔童》以成长题材作为叙事架构,叙事主题亦呈现了传统文化思维,同时为贴近当代话语语境,实现文化信息传递与对话,在艺术话语呈现方式上也借用了大众流行文化,借境了中国传统绘画美学。
从叙事风格而言,以青少年群体作为主要受众,导演是新锐青年导演的动画电影《魔童》其叙事话语体系主要采用了“狂欢化”的表现形式。“狂欢话语”是前苏联艺术理论家巴赫金在总结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巨著《巨人传》时所采用的说法。所谓“狂欢”,其精神实质是民主化自由气质,取消官方与平民社会的阶级差别,代表着平民娱乐精神,民间审美文化旨趣,正像巴赫金所探讨的那样,这种话语表达形式来自于西方社会民间的“狂欢节”[7]。
《哪吒》中的“狂欢化话语”采用诸多形式:首先是地方方言运用,打破正统形象,主要以太乙真人为代表。不得不说这个形象是《哪吒》幽默戏谑话语形式的笑点承担,一口川普配上他那土肥圆的身形,直接摧毁了原初神话包括79版《哪吒闹海》中太乙真人其仙风道骨的“官方形象”,但其好酒误事、粗俗甚至下流的“小丑”形象在影片审美呈现中却出现了相反效果。从受众审美心理来看,或许在观影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种对于官方正统、一本正经的艺术形象的一种反向贬损而造成戏谑效果的热衷,因为根据巴赫金的观点,这是真正的“狂欢节”娱乐性。方言话语形式,来自于民间,现在一般出现在某些剧情故事片中,在动漫电影中出现,这或许是第一次,其主要也是为了配合《哪吒》其幽默戏谑的美学效果。还有申公豹的“结巴”形象,哪吒母亲的“女汉子”形象,长生云“小云云”饶舌啰嗉、粗犷大汉“娘娘腔”其实都具有反向颠覆的艺术效果。
其次,是“物质——肉体下部以及降格、颠倒、滑稽改编的全部体系”[8]。巴赫金在此,主要指粗俗甚至下流,涉及肢体及生理排泄的话语形式。在《哪吒》中,影片会经常以一种粗俗下流、甚至令人感官不适的方式表达某些情节,而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是以揭露隐私的方式,弥合了层级差别,在影院这样一个平民空间内,实现了娱乐狂欢,体现了某种狂欢精神的空间性效果。比如,当地民众孩童不胜其扰,计划向哪吒复仇,结果被哪吒以恶作剧的方式作弄,里面就涉及了小便排泄等手段;哪吒被海妖毒化,从海妖那里寻取解药,结果画面呈现为海妖排泄鼻涕液体,而哪吒要吞下此“解药”,并且还得涂抹敖丙全身,善良的敖丙恢复后,还探鼻闻闻,结果发现有大蒜味;在山河社稷图空间中夺取指点江山笔一幕太乙真人“放屁”与申公豹吸气“我的储备还有一些”等等,这些细节的呈现非常富有现场性,一定会获致观影受众“接地气”的评价。
“狂欢化”话语形式在艺术表达的当代,其实是大众流行文化主要的借力,因为大众流行文化体现的就是当代艺术的平民性、自由化、娱乐化特征,如果说传统的《哪吒》题材以反抗颠覆权威的方式实现平民性与主流正统的对立的话,那么当下《魔童》就是以极端娱乐化的话语形式表达了大众自由精神,而这也是当前青年流行文化的主要表达方式。
《魔童》在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大众流行文化话语形式,甚至某些叙事桥段都借用了当代仙侠小说、玄幻网络文学题材,比如“山河社稷图”中的特异空间,“妖族”的设定,天降雷劫,“结界”、符箓、道家仙术等诸多概念现在都是仙侠小说、玄幻文学流行的话语表达形式,作为以青少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的网文群体和动漫群体而言,这是再熟悉不过的话语符号。同时网络仙侠既传统又现代的话语方式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与动漫绘画颇具传统美学色彩的呈现方式完美的结合,又拓展了当下中国电影艺术表达的话语空间,为未来中国电影艺术走向(包括剧情故事片)提供了合理的思考。这种贴近当代青年文化心理的艺术表达形式毫无疑问是实现青年文化认同的重要话语方式。
动画电影,其画面语言的基石是绘画艺术,在《哪吒》动漫绘画的物象符号中,我们能看到许多传统器物,其细节呈现,也使《哪吒》的工笔织缝让人叹为观止,这里面有代表史前陶器的太乙真人喝酒用的涡轮陶罐,结界兽所体现的“三星堆”文化,生日宴席的陶觚酒器,以及体现古典建筑美学精神的李府大院,山河社稷图中美仑美奂的仙宫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物象符号并不产生于同一个时代,若是在剧情片时代片中,这样运用一定不妥,但是在动画电影中,它们并不违和地被集到一处,其实摄取的是它们的象征意义与所代表的古典情怀。
当代动漫电影的发展主体方向是3D,但不可否认,传统绘画艺术仍是它的根底,尤其是自成体系,以写意留白、山水点染、皴笔泼墨等为主体技法的中国传统绘画,这是中国当代动画电影必须依赖的艺术“重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该片导演饺子(本名杨宇)也有个平实却非常深刻的感悟,那就是动画电影可能是当前传统艺术呈现、实现文化传递最好的选择。在《魔童》降世中,其绘画艺术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其后台远景布景充分运用了国画山水的意境,大开大阖之间,无限拓展了影片受众高远的审美想象空间和审美意蕴,前台近景人物造型又充分发挥了当下3D技术带来的写实精神,虚实之间,使整个动画电影话面语言合理得当,再配合上场面调度中摄影机适当的推、拉、摇、移,特效、慢镜、快进、定格等运动方式,使得本片的画面语言不输于剧情故事片却又超越了故事片,这可谓是充分发挥了传统艺术“虚实相生”的境界。
实际上,中国传统动画曾经有过辉煌,以建国初期的《大闹天宫》为代表,我们曾获世界大奖无数,也曾根据传统艺术特征,发展了多种类型,比如水墨动画、剪纸动画,木偶戏等。《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阿凡提》《九色鹿》《哪吒闹海》等等都曾经在世界艺术画廊中如雷贯耳,用一句俗话来说,我们能打的手段太多了!关键是要找回我们的民族身份,以及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强大民族自信力!依托于丰富的历史文化思想资源宝库,中国电影艺术在未来相当可期。
于我们而言,做为以青少年群体为主要目标受众的中国当代动画电影其大众流行文化的外在形式与传统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青年人实现社会认同、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艺术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审美呈现,它向来寄寓着凝聚社会共识,传达国族文化并实现整个社会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导向与价值追求,当然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也是实现社会教育的重要媒介。
201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我们经历了建国七十周年的洗礼。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文化以西方文化作为巨大的参照系,经历历史文化与思想体系巨大的波折与重重调适,改弦更张,断裂重组,最后终于涅槃重生,重新确立了我们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自信。我们也最终总结出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如果说落后就要挨打,那么落后也一定没有话语权,包括艺术话语权;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古典文化叙事题材是当代中国文化呈现取之不竭的艺术宝库。借助于青少年受众为主体的文化群体,以大众流行文化表达他们的身份认同从而将古典进行现代性审美转换,并架构具有永恒超越性的中华文化主体思维,“我命由我不由天”,相信中华文化的高光时刻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