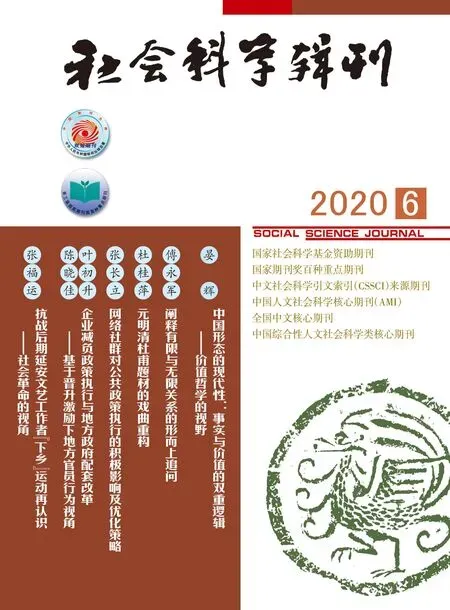统一战线与青年运动:一二·九运动前后中共在北平私立中国学院的发展
严海建
私立中国学院最初校名为“国民大学”,由孙中山和马邻翼倡议创立于1912年,1913年正式开学,1917年更名为“中国大学”,1931年,私立中国大学因不符合国民政府的大学立案标准,改名“中国学院”①关于中国学院校史的研究,可参见陈瑜:《中国大学研究(1912—1949)》,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3年。。私立中国学院在一二·九运动前后表现突出,是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既往关于一二·九运动及中共高校党建的研究中,大多偏重于整体叙述,或以北大、清华、燕京为论述中心,从而遮蔽了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及中共高校党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相关研究可参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一二九运动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周良书:《1927年—1937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北京党史》2006年第3期,等等。实际上,在历次的爱国救亡运动中,不同学校的表现会有差异,正如有论者所言,不同学校有着特色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生运动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亚文化的多元决定了学运的起落与内涵的差异。〔1〕本文尝试通过北平私立中国学院这一个案,探讨中共在高校“运动”学生的内外条件及机制,以期对一二·九运动及中共高校党建史有更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一、一二·九运动前后中共在中国学院的组织与活动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大学学生宋介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中国大学的进步学生还创办《曙光》杂志宣传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中共很早就在中国大学建立了党支部,黄龙、曾晓渊、钟伯卿等人先后担任支部书记,领导中国大学师生参与革命斗争。中大师生在三一八惨案、九一八事变后的抗议运动中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敌视。1933年,国民党在平津对中共及其外围组织进行大搜捕,使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下,1933—1935年上半年,中共的地下组织和外围群众团体很难开展活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虽然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国学院的党支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但党员的活动没有停止。一批党员师生坚持传播革命思想,团结进步青年,为一二·九运动创造了条件,一二·九运动后中共也在中国学院获得极大发展。
一二·九运动前后,中共在中国学院有一批教师党员,对传播中共革命思想、吸引进步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学院的政治经济系先后由马哲民、李达、黄松龄等进步教授担任系主任,聘请鲁明、吕振羽、施复亮、温建公、刘侃元、杜叔林和杨秀峰等左派教师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和列宁论帝国主义。国学系主任吴承仕采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国学,齐燕铭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中国通史,陈伯达、曹靖华、孙席珍和张致祥等在讲授先秦诸子思想、苏俄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时也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中国学院的进步师生出版了很多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由齐燕铭、张致祥主编的《文化动向》除了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外,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文化动向》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吴承仕、齐燕铭、张致祥和孙席珍又将之改换为《文史》重新复刊。《文史》被查封停刊后,张致祥又主持出版《盍旦》半月刊。这些刊物发表的文章针砭时弊、激扬民气、宣传救国,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①关于中国学院进步刊物的情况,参见孙席珍:《回忆我在北平的日子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页。
1936年初,中共北方局在中国学院成立了一个党的特别小组,负责领导北平的文化运动。据张楠回忆:
从“一二九”到七七事变,曹靖华参加一个由中国大学国学系几位老师组成的时事座谈会。参加的人不知道这个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批准的,由北方局负责文化工作的陈伯达领导的党的特别小组。在这之前,中大国学系主任吴承仕和齐燕铭、管彤(即张致祥)主编的《文史》杂志上,发表了陈伯达的《从名实问题看中国古代哲学基本分野》和关于先秦诸子的文章。吴承仕很赏识这些文章,聘请陈伯达到国学系讲授先秦诸子。化名陈志梅的陈伯达和吴承仕他们相处了一段时日,向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提出,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建议“把吴承仕几位进步文化人吸收到党内。但这些人不可能同一般的人一样过党的组织生活和建立组织关系”。这建议得到北方局领导批准,成立了党的特别小组,由陈伯达直接与北方局联系。特别小组成员5人,吴承仕、齐燕铭、管彤(组长)、曹靖华、孙席珍。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学委委员高承志常列席。这个党的特别小组是北方局领导北平文化运动的一条重要渠道。〔2〕
国学系主任吴承仕是中国学院教师党员的核心人物,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都是吴承仕的学生或助手。李达、吕振羽、范文澜、曹靖华、杨秀峰和张友渔等中共党员或进步教授在中国学院兼课,同样也对青年学生有很大影响。曾担任中国学院党支部书记的任仲夷曾特别提到进步教授对学生的影响:“这些教授不仅在课堂上授课时对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并对中大和全市的学生运动进行帮助和指导,乃至亲自参加学生们的各项活动。”〔3〕
在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中国学院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社会科学、革命文艺、马列主义的革命书刊,讨论现实问题。政治经济系的程国奇、石惠轩、孔洁光、王大同、陈国新、高钦和甘一飞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土地问题研究会。这些读书会还吸引了北大、师大、宏达中学和志成中学的同学参加。这些活动传播了进步思想,提高了同学们的思想认识,为此后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二·九运动前,中国学院学生会派出董毓华等为代表,参加中共领导的北平各界黄河救灾委员会的工作。根据委员会的号召,中国学院师生在校内外开展募捐救灾活动。各系各班推选代表约30余人,会同各校同学,携救灾衣物和现金,分头到受灾严重和灾民集中地进行慰问。后来根据北平地下党的指示,把救灾组织改为北平各校联合的组织,于是救灾委员会就成了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前身。
1935年,日本加紧了侵华步伐,公然宣扬“华北特殊化”,欲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华北,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致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此国家危亡的关头,北平学联决定发起一场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12月8日,中国学院派出董毓华、甘全礼、孔震萍和王大同等作为代表参加了学联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于12月9日各校联合进行请愿。中国学院学生救国会对学生进行了广泛动员,组织学生参加了12月9日和12月16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运动。
中共在中国学院学生中有秘密的党支部,是中共领导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核心组织。1935年12月—1936年2月,中国学院党支部先后由甘一飞、孔震萍担任书记,1936年2月,冀察当局实行大逮捕后,党支部遭到破坏。1936年四五月间重建,陈德满任支部书记,任仲夷任组织委员,吴承华任宣传委员。1936年6月到1937年6月,改由任仲夷任书记,委员是吴承华、刘烈人。中共组织的大发展主要是在一二·九运动以后。据任仲夷回忆,中国学院党支部重建之初,只有党员10余人,支部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前后入党的。随着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国学院的党组织也很快发展起来。从1936年5月至1937年5月的一年时间内,中国学院党支部的党员增加了2—3倍,由开始时的十几个人增加到40多人。如果把组织关系在校外的党员都计算在内,全校共产党员约有六七十人。这对在校学生总数约千人的学校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比重。〔4〕
1936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破坏学生运动,令学校提前放假,并要求各大学派代表到南京听训。学联为抵制这一命令,决定利用寒假组织南下宣传团到农村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联合广大农民共赴国难。南下宣传团返回北平后,中共决定,以南下宣传团为基础,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称“民先队”),将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吸收进民先队,形成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使其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坚,从而让学生运动坚持下去,发展起来。民先队是一个具有严格纪律的、带有半军事性的组织,同时又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群众组织。1936年2月,中国学院建立了民先大队部,在组织上受北平民先总部和西城区队部领导,吴承华、杨易辰先后担任大队长。在中国学院民先队员中,共产党员约占1/3。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凡参加民先队的党员,一般都不发生横向联系,而是按照党的组织系统,分别编成党员小组。在民先队之中,党的组织是不公开的,但中国学院民先队实际上已成为向党输送新党员的基本队伍。〔5〕中国学院民先队组织发展很快,建队以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队员就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
除了民先队以外,中国学院校内的学生会和班级组织也基本由中共党员或接受中共领导的进步学生主导,从而可以在校内合法地开展工作。据中国学院学生胡述文回忆:“中国学院不设班长,每班设服务生2人,连选得连任,余修连任服务生4年。服务生经选举产生后,由校方认可,有合法身份。余修即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召集各班服务生开联席会开展活动。”〔6〕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就是在学生会的组织下进行的,当时的学生会主席董毓华是学生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及学联代表。
一二·九运动前后中共组织在中国学院的发展呈现出若干特点。与国立大学不同,私立中国学院的教师中有相当部分活跃的中共党员。如果说在一二·九运动中,很多学校的教授扮演的角色是“急切的劝阻者”或“同情的旁观者”,那么中国学院的教授则扮演的是“热情的鼓动者”①关于教授与学运的关系可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因为中国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已经是同路人了,教师党员往往能在学生与校方对立的情况下,增强进步学生的力量。此外,中国学院学生中有不少党员骨干,但这些党员在发挥作用时往往采取秘密的方式,并不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在具体领导学生爱国救亡运动时,往往利用民先队和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一方面通过隐蔽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动员了广大学生。上述特征也是中国学院特有的学生亚文化的表现,这种亚文化对于校内风潮的发起与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驱祁迎何”运动与中共对统一战线的运用
1936年3、4月间,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开始寻求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北方局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改变之前白区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学运问题上开始调整工作方式,将冀察政务委员会列为统战对象,争取其团结抗日。为此,北平学联决定把“取消政委会”“打倒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开始改变对学运的敌视态度,1936年5月,冀察当局开始释放之前抓捕的学运积极分子。〔7〕北平学联还提出“师生团结抗日”的口号,要求进步学生争取学校当局的支持。中国学院的进步学生尝试了各种方式争取学校当局的支持,但校方顽固不化,坚持破坏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立场。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权力大多系于办学经费的出资人或实际校产的拥有者,故而校长大多出自校董中最有权势且对学校争取资源贡献最大的人。私立中国大学在1921年王正廷出任校长并长期执掌校政后,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王正廷任内为学校争取到很多资源,尤其是购得郑王府作为校址后,大大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王正廷掌校时,并不实际在校,而是由其任命的总务长祁大鹏总管校务。祁大鹏早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在校期间也曾参加学生爱国运动②祁大鹏在中国大学读书时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还与中共党员宋介同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期刊《曙光》的发起人,到1921年,因宋介赴美留学,《曙光》社务由祁大鹏负责。参见《曙光杂志社启事》(1921年9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9页。,毕业后曾在王正廷任外交部部长期间担任亚洲司司长和外交部驻北平档案保管处处长等职,深得王正廷的信任。自1932年秋开始,祁大鹏担任中国学院总务长,作为校长代理人,实际负责校务管理。祁大鹏任总务长之初,一度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但随着学潮的频发,祁大鹏开始与南京政府接近,对学运的态度也由消极默许到积极打压。
1936年2月,国民政府中央与平津当局决定取缔学联并镇压学潮。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对记者谈话表示:“国府颁布的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刻已转饬公安局严厉遵行,嗣后凡有鼓动学潮及扰乱社会秩序者,决严予严办。”当时报载:“中央与地方当局,既对学潮一致持严峻态度,平学生运动暂形平息,学联已无形解散,激烈派续有人被检举,各著名大学,皆有探警站岗。至被捕学生,以中国学院之十八名为最多。”〔8〕这次抓捕被中共学生称为“二月雪天”,当时中国学院正在召开慰劳南下宣传团大会,冀察当局派军警进校抓捕学运骨干。因此次大逮捕,中国学院的党组织和学生会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学生会组织停顿。中共党组织在1936年4月重建,但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公开组织学生进行爱国救亡运动,故而需要重建学生会。1936年4、5月间,在中共校内组织的领导下,学生会重新举行选举,选出执行委员15人,执委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史立德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因选举未得到校方同意,校方对此异常不满,总务长祁大鹏责令新学生会停止活动,并以缺课太多为由勒令开除学生会负责人,由此导致中共地下组织与校方的矛盾日趋尖锐。〔9〕
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学院校方加强对学生的控制。祁大鹏请南京方面任命的张天爵为教育长,加强对学生的训导。张天爵在学校处处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并发表拥护南京当局的言论。此外,校方还与警察局合作,增加门卫,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看管,限制学生出校和集体活动。进步师生在多方争取祁大鹏无果后,决定发起驱逐祁大鹏的运动。
驱逐祁大鹏的运动是由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以校内党员师生为骨干、发动广大学生参与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中共北平市委及学联、中共在中国学院的支部、民先队、学生会和左派教授吴承仕、黄松龄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张致祥回忆决定发动驱祁运动的过程:“中大学生会请示党组后,由史立德同检斋先生和黄松龄商量,请吴、黄以系主任身份和学生会配合进行这一斗争。当时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还专门为此拜访了检斋先生。”〔10〕
中共北平市委之所以同意发起驱逐祁大鹏的运动,是因为中国学院的党组织比较健全,工作得力,如果能够排除校方的干涉,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据张致祥回忆:“当时民先、学联经常在清华和燕京大学活动,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工作条件,在市内再选择几所院校为活动中心。……东北大学和中国大学地处城内,党的组织比较坚强,群众基础较好,学生抗日救国会及各种学生组织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的,正气压着邪气。”〔11〕中共北平市委同意中国学院党组织驱祁,因为这不仅关系一个学校前途的问题,还关系着北平学运的整体。
自1936年7月起,以打倒祁大鹏为主体的学潮即开始酝酿,但仍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①早在1935年暑期,中国学院校内就曾发生驱逐祁大鹏的风潮,但因王正廷的力挺,最后未能成功。参见《中国学院学生酝酿驱逐祁大鹏校方昨开会拟定驱祁计划宋介谈学生举动难成事实》,《益世报》1935年7月18日,第2张第8版;《中国学院驱祁风潮已渐次扩大》,《益世报》1935年8月21日,第2张第8版。1936年8月,中国学院校长王正廷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给了学生驱逐祁大鹏的机会。王正廷任驻美大使的消息公布后,吴承仕就提出:“王要出国,必然来中大交代工作,乘他此来的机会,以学生会名义向他提出撤换祁大鹏的强烈要求。王的代理人倒台了,王本人出国在即,势必不能再来中大,这样我们的文章就好作了。”〔12〕史立德把吴的意见报告中国学院党支部,最终北平市委同意,黄敬亲自到吴家中进行磋商,最终决定借此机会倒祁。
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国学院党组织对驱逐祁大鹏运动进行严密部署。②据史立德回忆:“中大党组织和革命教授为便于指挥这场革命学潮,由吴承仕教授在东交民巷德国饭店租了一间房,由张致祥常住那里。”参见史立德:《一二九运动前后的中国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18,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58页。1936年11月21日,上午九时王正廷到校召集学生训话,王讲完后,学生拟呈递意见书,遭祁大鹏阻止,学生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祁大鹏。与此同时,中国学院附中学生也都赶到,但被校警阻于门外,校内学生要求放行,在场全体学生对王正廷下跪,当学生代表宣读呈文时,竟有愤而大哭者。学生会组织学生齐集西花厅前,学生代表高元贵、陆钦鑫当众宣读祁大鹏的种种劣迹,其中就有“摧残合理爱国运动,陷害爱国同学。学生运动时,祁氏竟将爱国同学像片,亲交军警,按像逮捕学生,因而被捕者达七十余人之多”〔13〕。上午十时校董会开会,对于王正廷提请辞职案,决定“准王正廷请假,暂由吕复代理校长”。吕复时任天津法商学院院长,同时又是中国学院的校董。会后“吕复决于日内赴津,办理天津法商学院院务交代事宜”〔14〕。下午二时许,中国学院董事会结束后,校长王正廷及各董事要离校,学生则坚决不放行,要求撤换祁大鹏。在学生的围困下,王正廷起初仅表示“撤换祁总务长,须经详细考虑后,始能实行”。学生不满,坚持不去。最后校董会董事长马邻翼、董事何其巩出面,确定最后两个条件:一、祁大鹏由董事会担保,自动辞职;二、各同学安全由王校长之人格担保无虞。至午后三时许,学生始满意离去。〔15〕
11月21日,中国学院学生提出整顿学校意见书,跪哭请愿并包围董事会诸人,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步骤。从结果来看,董事会最终同意撤换祁大鹏,但并不能算是完全胜利。王正廷提请辞职案未通过,校董会只是准其请假,所以王还是正式校长,而且新任代理校长吕复也不是校内进步力量中意的人选。①王正廷来平之前即已商定吕复出任代理校长。参见《法商学院院长吕复辞职就任中大院长继任人选未定》,《益世报》1936年10月30日,第2张第6版。祁大鹏被打倒,代之以吕复,王正廷仍是校长,等于是换汤不换药,所以倒祁之后还要拒吕。据史立德回忆,身为校董会董事的吴承仕并不满意校董会的这个决议。当晚,他召集黄敬、黄松龄、齐燕铭、张致祥、黄诚和史立德等人来家商议。吴承仕认为,吕复此人在镇压学运方面比祁大鹏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手段阴险,而多数同学对此并不了解,所以“倒祁容易,拒吕则难”。于是,中国学院党组织把事态的发展变化报告给中共北平市委,并立即派代表到天津,与河北法商学院共同商量斗争的办法。北平市委同意中国学院党组织提出的方案,立即给天津市委写了介绍信。〔16〕
11月22日,中国学院学生会派邹育才、史立德二人,带着组织的介绍信去天津与法商学院学生会取得联系。由于吕复在法商学院也不得人心,所以为支援中国学院的斗争,法商学院掀起了一场“倒吕”的学潮,并把大幅“吕复止步”的标语悬挂在校门。中国学院董事会21日决议吕复担任代理校长,吕复随即返津,23日法商学院即突起风波。〔17〕法商学院风潮是由中共组织策动的,时间上如此密集且及时的安排,意在使吕复陷于风潮中而不能赴北平接任。同时,中国学院学生会把拒绝吕复代理校政的决议,分别送交至董事会长马邻翼和常务董事何其巩,并提出八项苛刻的要求,要求吕复到任前承诺办到,以期吕复能知难而退。
王正廷离平经停天津,敦促吕复到校负责,但“吕复表示在法商学潮未解决前,拟不他往,亦暂不拟就任中国学院代理院长之职”〔18〕。吕复于11月27日复函中国学院学生会,“表示本人是否就任,正在考虑中,对八事要求不便置答”〔19〕。至此,中国学院代理院长的人选成为悬案,王正廷对记者表示中国学院院长人选候返京后再行决定。
倒祁运动并非单纯的校内风潮,中共试图驱逐压制左派学生的祁大鹏,国民党背景的学生则拥护祁大鹏,无奈在校内势单力孤,最终图谋失败。据当事学生回忆:“中国大学的复兴社的曹景襄等和诚社的杜玄德等破坏该校学生会领导的倒祁(驱逐总务长祁大鹏)运动。祁大鹏被驱逐出校之后,他们又收买流氓保护祁大鹏回校。”〔20〕在新校长未定的间隙,祁大鹏于12月1日清晨6时许,在警察的护卫下突然闯进中国学院,当时学生还在熟睡,所以没人察觉,他便带人将校内所有“倒祁”标语尽皆撕去,并占据校长室,企图复辟。祁还张贴通告,开除史立德、黄诚等7名学生代表。同学闻讯后极为愤慨,一致出动,越聚越多,喊打声四起,至正午时分,祁被迫离校。学校政务暂时由教务长方宗鳌代理。〔21〕
经过“倒祁”“拒吕”一系列运动后,校长人选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按照私立大学惯例,校长须由校董会选举产生。1936年12月3日,中国学院学生自治会代表史立德又谒董事长马邻翼及常董何其巩,表示同学等反对吕复,欢迎马董事长及何董事。马邻翼答复:“本人年及耄耋,不能理事,代理院长一席,各董事之意,如吕董事坚辞不就,拟请何董事勉为其难。”〔22〕董事会去电王正廷,表示同意何其巩代理校长,王正廷被迫接受。12月4日,该任命正式提交董事会通过。中国学院学生自治会对此表示欢迎,提出“将前对吕复要求之各点,改书面为口头,以婉约词句,请何允准”〔23〕。以示区别于拒绝吕复的态度,让学生会和新校长都有台阶下。
何其巩出任中国学院代理校长,表面上看是校董会推选的结果,实际上是中共与何其巩私下早已进行沟通并达成的共识。中共之所以选择何其巩,主要是看重其西北军的背景,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运用的结果。
何其巩早年投身军旅,任西北军冯玉祥部文书,渐为冯所器重。1926年9月,何其巩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其后随冯参与北伐,与国民党政要多有交集。1928年6月,何其巩由冯玉祥推荐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1933年5月,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5年12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24〕何其巩是西北军旧部,长期在华北任职和活动,与华北地方当局尤其是西北军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驱祁”“拒吕”“迎何”一系列运动中,何其巩得到了中共和左派师生的支持。据史立德回忆,驱祁运动成功后,左派学生曾想请德高望重的吴承仕、黄松龄等出面组成校委会,以掌握校政,但吴承仕坚决反对。吴认为,要避免国民政府的干涉,还是要在董事会里做文章,而校董会会长马邻翼年事已高,常务董事何其巩遂成为最合适的人选。〔25〕中共与何其巩之所以能合作,一方面是因为“何其巩同西北军有旧,宋哲元、秦德纯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而何其巩又不甘寂寞想借中大为阶梯重新上台”。另一方面中共与何其巩达成共识,“希望他长校之后,应看到国难深重,保护学生救亡运动”,何亦表示同意。〔26〕总之,何其巩出任中国学院校长符合中共团结西北军的政策要求,以及避免走到前台直接对抗的考虑,同时对于赋闲的何其巩来说,出任中国学院校长也有助于其提高声望。①据李泰棻回忆:“曾经担任过北平市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何其巩彼时正赋闲在家,见此情形,便联络校内部分师生和中国大学在平董事,将马逼走,聘他为代理校长。”参见李泰棻:《何其巩在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三、中国学院校内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
何其巩任校长后,中国学院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据中国学院学生会主席史立德回忆,何其巩任校长后,“中大救国会不但可以公开活动,而且学校当局专门拨出五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每月还能从学校领取一定数量的油墨纸张之类。我们还让出两间房子专供北平学联使用”〔27〕。中国学院党支部书记任仲夷称,何其巩任校长后,“全校的政治局面打开了,学生爱国运动和党的工作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平学联决定在中大设立一个固定的办事机构,以便于同各校联系。许多被反动势力统治着的学校的进步学生,经常到中大来进行活动。有些学校的党的活动,也到中大来进行。中大就像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一样,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活动中心”〔28〕。
何其巩1936年接任中国学院校长的重要背景是原西北军旧部开始执掌平津。1935年8月,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2月又被指定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12月,何其巩接任中国学院校长,宋哲元等冀察政要莅临祝贺,以示支持。据史立德回忆,何其巩到校不久,即邀请冀察当局的要人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到校发表讲话,同时还邀请了宪兵司令邵文凯、北平公安局局长陈继淹到中国学院。吴承仕认为,何其巩此举,“既为他装了门面,又取得了合法地位”,是为了做给校内师生看,表明“可请他们赞助学校”〔29〕。事实上,何其巩确实多次利用其个人的政治关系为校内进步学生提供保护。
中国学院的爱国救亡运动在校内外公开进行,引起南京国民政府和北平当局的忌恨和压制。1937年1月18日夜,中国学院学生会的黄诚、吴承华、史立德、陆钦鑫和吉慧贞等五名主要负责人被捕,1月19日晨,学生阎佐臣也被逮捕。〔30〕对此,何其巩在接见学生时表示:“本人决以私人资格向各关系当局疏解六学生事件,当不致有何困难。”〔31〕随后,何其巩亲自与宋哲元、秦德纯沟通,反复交涉,最终由宋下手谕,释放被捕学生。〔32〕
北平特务组织把何其巩支持进步学生的情况反映到南京,称“何其巩让共产党牵着鼻子走”。朱家骅给北平市长秦德纯写信,要秦注意何的动向。秦德纯到何家后,把朱家骅的原信给何看,提醒何有人告状。随后,何其巩到学校找来党员教授吴承仕,说:“对此我一笑置之。”但吴承仕还是向中共北平市委做了反映,市委认为,要保护何其巩,各种进步活动要适当疏散隐蔽。〔33〕
在驱祁迎何的运动中,何其巩与中共是胜利的一方,对于王正廷和国民党则相反,故而事后王正廷与国民党合流,处心积虑想要打倒何其巩。对于已经形成统一战线的何其巩与中共来说,则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抵制王正廷和国民党的反击。
中国学院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1937年春,国民党派与何其巩有同乡之谊的中宣部副部长方治到北平与何面谈,提出解聘进步教授和开除爱国学生的要求,被何拒绝,于是CC系决定打倒何其巩。〔34〕国民党先是找到即将出国的王正廷,要他以原任校长资格出面,让董事会改选中国学院毕业生、CC系骨干陈希豪为代理校长。
1937年5月,CC系与原校长王正廷合谋,试图打倒何其巩。王正廷是不想丢掉地盘,CC系则是希望打击中国学院的左派力量,双方一拍即合。据当时报载:“北平中国大学校长王儒堂业经出国,校董会委陈希豪代理。”〔35〕实际上校董会并未开会,中国学院学生以南京政府无权以行政命令擅自决定校长人选为由,严辞拒绝陈希豪入校。何其巩公开表态,虽然他本人“决不留恋校长位置”,但也“无权将校长职务交出”,并坚决表示跟同学站在一起,“共同奋斗”〔36〕。之后,何其巩拒不交卸校长职务,最终陈希豪未能进校,何其巩由代理校长变成正式校长,在校内的地位也更形稳固。
据何其巩的秘书崔曕回忆,在CC系图谋倒何之时,何让崔曕放心,称“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并出示了一份6月22日宋哲元给蒋介石的电报抄件,内容是宋向蒋力保何继续担任中国学院校长。〔37〕6月26日,蒋介石致电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宋哲元所请。〔38〕由此可见,何其巩在华北地方的权势网络发挥了作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顾忌华北的地方势力,故不能从外部强行改造中国学院,只能选择迁就华北地方势力。
统一战线的逻辑在于,一方面要符合双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国民党一方存在“裂缝”,中共才有争取的可能。有论者指出,1936年4月,随着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中共改变了以往对冀察政委会的敌视,转而走上拥护冀察政委会抗日的道路。在北方局统战工作影响下,冀察政委会与学生救亡力量的关系也经历了由敌视对立到汇流的转变。〔3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北军背景的何其巩才能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之间存在的裂隙稳固自己的地位,同样通过统一战线,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获得了更多群众的支持和舆论的同情。
结语
经过驱逐祁大鹏的运动后,同情与支持中共的何其巩担任校长,中共在私立中国学院获得了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党组织对私立中国学院的校政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而使中国学院成为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一个“根据地”,这在中共高校党建史上是非常特殊的个案,值得深入探讨。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从外部环境而言,主要是因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运用,从内部环境来看,私立中国学院特有的亚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春提出的政策原则,在其所涉及的个案中能否运用及运用到何种程度,主要取决于个案的内部环境及其特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共大多是在边缘地带坚持与发展,国民党统治存在的各种裂缝为中共生存发展提供了可能。〔40〕民国时代的若干私立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北平私立中国学院以文法科为主,教师中左派进步力量较大,学生因出路问题及校内氛围的熏染易被中共吸引而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私立学校校董会作为校内最高权力的法理结构,使得政府不能直接介入私立学校的校内治理,而在学校权力重心不稳的情况下,部分校董与师生联合就可以实现校政的更新。冯友兰回忆蒋梦麟“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41〕在驱逐祁大鹏的风潮中,进步力量之所以易于着手,就是因为进步教授与学生的联合,使得祁大鹏在校内陷于孤立,国民党纵然有意介入,但格于私立大学校长产生需校董会选举的成例而无法着手,相反中共正是利用了既有的合法程序进行斗争从而取得胜利。
中共对统一战线的灵活运用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之一。驱逐祁大鹏的目的达到后,中共并未让党员直接接管学校,而是考虑到现实环境,为避免学校被解散从而丧失阵地,选择有西北军背景又对中共表示同情的何其巩出任校长。中共与何其巩形成的统一战线,实现了表里的双赢,中共利用何其巩西北军旧部的身份与冀察当局形成缓冲,从而拓展了校内学生运动的空间,同时也保护了校内的进步师生。何其巩也利用校内师生的支持,抵制国民党势力的介入,稳固自身地位。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了最大多数的同盟,既使自身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同时又促进了北方青年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