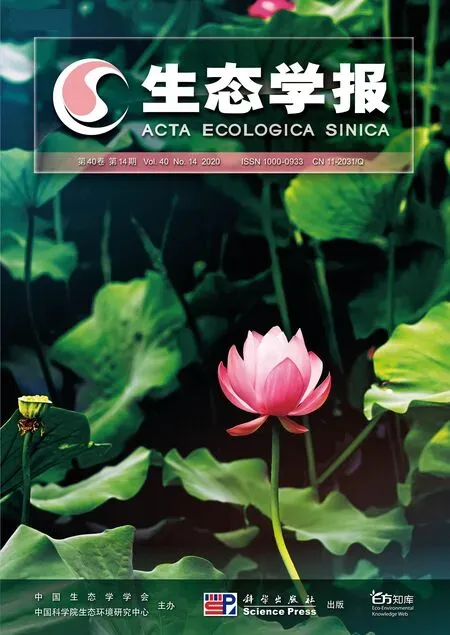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分布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综述
徐雨晴,肖风劲,於 琍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北京 100081
森林生态系统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很高的生物生产力、生物量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碳储量占整个陆地植被碳储量的80%以上,每年碳固定量约占整个陆地生物碳固定量的2/3[1],因此它对于维护全球碳平衡具有重大作用。森林与气候之间关系密切,大气中CO2平均每7年通过光合作用与陆地生物圈交换一次,其中70%是由森林进行的[2]。气候变化特别是降水和温度的变化,对森林植被的生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而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森林分布、林地土壤呼吸和生产力诸方面的变化反过来也可对地球气候产生重大的反馈作用。
森林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通过植被光合作用在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所产生的有机物质总量与自养呼吸之差。NPP作为表征植被活力的关键变量,能直接反映出植物群落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生产能力[3],也是衡量植被固碳能力的最主要指标,关系到生态系统对CO2引起的温室效应缓解作用的强弱[4]。森林生态系统NPP的微小变化都会引起大气中CO2浓度较大幅度的改变,从而导致气候的变化[5],因而它也是地表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判定碳汇/源和调节生态过程的主要因子[6]。另一方面,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发生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这对陆地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植被生产力的变化[7],且陆地植被生产力对气候的变化十分敏感。
鉴于自然环境下的森林植被生产力能够反映陆地生态系统的质量状态、对碳平衡和全球气候变化均具有一定的反馈作用,因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开展森林生态系统NPP的评估,直接关系到地球的承载能力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助于认识气候变化与森林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于深刻理解和研究陆地碳循环和全球变化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区域地表植被估产、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也都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综合国内外目前的NPP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在时间序列上的波动情况;2)空间分布特征,包括经纬向变化规律,区域之间以及气候带之间的变化与差异;3)驱动因子;4)估算方法。由于森林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野外测定困难,同时也受人类活动影响等原因,目前国际上对森林生态系统NPP的时空格局分异及生物地理学机制的认识还不能达到精确评估的需要。
中国不仅具有从温带到热带、从湿润到干旱的不同气候带,也具有从北方针叶林带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热带雨林的多样性自然植被[8]。我国已有大量针对近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来以来国家和区域尺度上植被NPP时空分布的研究,其中专门针对森林生态系统NPP的研究也有不少。研究尺度多为全国范围或者片段式区域,以行政区或流域尺度最为多见。然而,这些研究总体比较分散,其中部分研究的结果、结论并不一致,甚至相悖,尚缺乏异同性分析与比较,也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这并不利于全面掌握我国相关研究的整体情况、了解清晰明确的研究结论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规律及原因探究,也非常影响对森林NPP的精确评估及机理认识,因而,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合和总结非常有必要。鉴于此,本文收集了近几十年我国植被NPP研究的主要相关文献,依据其研究结果,系统地综述了全国及区域尺度森林生态系统NPP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未来可能变化趋势,揭示出NPP与气候因子的关系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情况,并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起到一定的索引和参考作用。
1 NPP估算方法
全球不同尺度下NPP估算大致经历了站点实测和模型估算两个阶段。1960—1970年代,国际生物圈计划对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展开了大量的野外调查,第一次对生物圈尺度的生物量和生产力进行了分析。野外调查获得的实测数据比较可靠,但很难进行大范围比较均匀的实地调查取样,因而难以进行大区域乃至全球尺度NPP估算,更无法就NPP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做出机理性预测。模型估算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而成为研究大尺度空间范围NPP分布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由于实测方法测定结果的准确性是模型估算方法无法企及的,因而很多模型估算结果往往需要利用实测结果进行验证和订正。目前,国内外关于估算NPP的模型有20多种,大体可分为统计模型、过程模型和参数模型三类,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气候生产力模型。包括统计模型和半经验半理论模型两大类,它是利用年均温度和年降水量等气候因子与实际测量NPP之间的统计关系而建立的回归模型,其优点是模型简单、应用方便,缺点是不同的研究区域误差可能较大。统计模型是较早期出现的经验模型,半经验半理论模型是统计模型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引进了植被净辐射和辐射干燥度等因子,增强了模型的机理性。但是,由于半经验半理论模型是在土壤水分供给充分、植物生长茂盛条件下的蒸发量来计算植物NPP的,对于世界大多数地区该条件并不满足,因而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区应用时估算值偏高[9]。气候生产力模型主要有Miami模型、Thornthwaite Memorial模型、Chikugo模型、朱志辉模型和周广胜模型。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又称机理模型或生理生态过程模型)。是通过对植物的光合作用、有机物分解及营养元素的循环等生理过程的模拟而得到的,可以与大气环流模式耦合,因此可以用这类模型进行NPP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响应和反馈研究。由于其较强的机理性和系统性,所以该类模型的可靠性比较高,在不同条件下均可以详细地描述生物学过程[9]。该类模型主要包括BEPS模型、Century模型、Biome-BGC模型、CEVSA模型等。
光能利用率模型(遥感数据驱动模型)。是基于资源平衡观点以植物光合作用过程和Monteith提出的以光能利用率为基础建立的[9],模型简单,可直接利用遥感数据。1990年代出现了估算NPP的遥感模型,近年来随着遥感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以遥感数据驱动的植被NPP估算得到迅速发展和应用,成为一个主要发展方向。光能利用率模型使区域及全球尺度的NPP估算成为可能,但其生态学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国际上最流行的NPP遥感估算模型包括CASA和GLO-PEM。CASA模型是光能利用率模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遥感的技术方法,以NDVI为驱动,借助于主要的驱动因子(气温、降水量、太阳辐射量等)计算植被NPP值。
生态遥感耦合模型是综合了生理生态过程模型和光能利用率模型的优点,通过叶面积指数将二者整合起来,可以反映区域及全球尺度的NPP空间分布及动态,增强了陆地NPP估算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除此之外,近年国内外不断出现基于森林清查数据进行的NPP估算研究。我国森林资源清查体系已有4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森林资源清查样本数据,尤其是以省为单位的数据,这使得用清查数据估算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成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方法,并成为生态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王玉辉等[10]曾成功探讨利用森林资源清查资料的方法估算落叶松人工林和天然林生物量和生产力,并发展了估算公式。还有研究认为,基于树轮资料重建区域植被的NPP是可行和有效的,然而,此方法有可能导致对陆地生态系统生物量的低估现象出现,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11]。
2 全球森林NPP总体分布
从对全球森林生态系统NPP的研究来看,其领域主要涉及全球纬度格局、不同区域及不同气候类型区间的差异等几个方面:纬度梯度控制着气候的空间变异规律,直接影响着温度和降水格局,这一方面影响植被的光合、呼吸等生理过程,另一方面影响土壤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从而对森林NPP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其中,就纬向分布而言,全球森林生态系统NPP在赤道附近最大,随纬度升高而显著降低,纬度每升高1°NPP约减少11.05 gC m-2a-1,北半球及其区域NPP的这种纬向变化规律更明显[12]。例如,北半球地区纬度每升高1°NPP约减少11.71 gC m-2a-1,而南半球地区NPP未呈现出显著的纬向变化规律;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区域,纬度每升高1°NPP分别约减少17.10、23.689 gC m-2a-1和9.639 gC m-2a-1,而在南美洲区域NPP却未呈现出纬向变化规律[12]。就区域差异而言,全球各大洲之间森林生态系统NPP整体上差异不显著,只有南美洲显著高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12]。就不同气候类型区而言,森林生态系统NPP分布差异性很大,然而,相关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结论相悖。例如:有研究[13]表明,全球森林生态系统NPP呈现出从寒冷性气候区域向温暖性气候区域逐渐增大的趋势,热带区域显著高于温带区域;但也有研究[14]指出,热带区域森林生态系统地上部分的NPP与其他气候区域没有显著差异,甚至低于温带区域。
3 中国森林NPP分布格局及其变化
3.1 近几十年中国及其区域森林NPP分布
我国森林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南交通不便的深山区和边疆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地,而广大的西北地区森林资源贫乏。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地区。东北林区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林区,横跨温带和寒温带两个气候带,属于针阔混交林与北方针叶林的过渡区域,形成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针阔混交林和寒温带针叶林3个基本林区。西南地区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川西、滇西北、藏东南的高山峡谷地区,主要林区处在横断山脉,西南林区是我国第二大天然林区。南方地区森林资源分布比较均匀,人工林占很高比重。武夷山系和南岭山系较为集中,有林地面积占南方地区总面积的45%。
中国植被NPP年均值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的研究结果总体差异不大,其中最为具体和定量化的结果如下:沿经度方向,水分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潜在自然植被NPP与水分的分配格局总体保持一致,且NPP随着经度的增加而增大,具体为NPP在经度73°—98°之间较小(小于200.0 gC m-2a-1),随后随经度的增加而增大,到128°时最大(498.1 gC m-2a-1);沿纬度方向,NPP与热量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分配格局大体保持一致,总体呈现出“U”型递减模式,具体为NPP在18°时最大(722.8 gC m-2a-1),随后递增至39°时最低(为79.8 gC m-2a-1),递增至51°时又达到高值(499.5 gC m-2a-1)[15]。关于近几十年来中国植被NPP年际变化趋势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15]认为,中国潜在自然植被NPP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也有研究[16]表明,中国植被的NPP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期后陷入停滞。
中国不同气候带森林NPP变化范围为261.9—724.959 gC m-2a-1[17],这一范围值后来已得到绝大部分实测和模拟结果的验证。例如:利用遥感估算模型得到中国典型落叶针叶林NPP实测平均值为490 gC m-2a-1[18]及477.74 gC m-2a-1[19]。区域上,采用集成生物圈模型模拟大小兴安岭森林植被NPP年均值为494.79 gC m-2a-1[20],采用CASA 模型得出1992—2012年东北落叶针叶林NPP年均值为358.7 gC m-2a-1、落叶阔叶林NPP年均值为424.99 gC m-2a-1[21]。运用Biome-BGC模型模拟的1980—2013年长白落叶松林NPP变化范围为286.60—566.27 gC m-2a-1,均值为477.74 gC m-2a-1[19];模拟的1960—2011年长白山阔叶红松林NPP变化范围为473.28—703.44 gC m-2a-1,均值为611.71 gC m-2a-1,近似于基于样地实测的NPP均值594.66 gC m-2a-1[22];模拟的长白落叶松人工林NPP变化范围为272.79—844.80 gC m-2a-1,与基于样地实测的NPP具有很好的一致性[23];模拟的北京山区华北落叶松林NPP为225.49—519.38 gC m-2a-1[24]。然而,也有少数模型模拟的长白山阔叶红松林NPP值接近或超过了这一范围上限,且不同模型的模拟结果差异较大,例如,通过EPPML过程模型的模拟值为1084 gC m-2a-1[25],通过回归模型的模拟值为769.3 gC m-2a-1[26],通过GLOPEM-CEVSA模型的模拟值为722 gC m-2a-1[27]。
中国森林NPP年总量的估算值差别较大,有的研究[28]中为400×1012—640×1012gC/a(0.4—0.64 PgC/a)。也有研究表明[29],当气温平均升高1.5 ℃、降水平均增加5%时,中国植被NPP年总量由2.645×1015gC/a增加到2.80910×15gC/a,平均增加6.2%。
从研究的空间尺度来看,已有研究[30]表明,国内的NPP研究集中在全国以及东北、华北等区域。从本文的文献搜集情况来看,目前对我国森林NPP时空演变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中,以东北、东南林区较为多见,以西南林区最为少见。
3.1.1东北林区
从地形分布看,东北林区山地植被NPP最高,平原植被区次之,高原区最低[31]。分析东北不同森林地区的NPP发现,贡献率最大的是落叶阔叶林,以温带软阔叶林最大,NPP平均水平为577.2 gC m-2a-1;温带针阔混交林NPP年总量最高(17.001×1012gC/a),占NPP总量的27.16%[32]。完达山系和长白山脉地区主要以落叶阔叶林和温带常绿针叶林植被为主,受海洋气候影响,水热条件充分,植被NPP值相对较高,在700 gC m-2a-1以上;大兴安岭东麓、小兴安岭地区植被主要以温带针阔混交林和落叶针叶林为主,受温度条件限制,NPP值在600—800 gC m-2a-1[31]。1992—2012年落叶针叶林及落叶阔叶林NPP整体上均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增趋势,分别集中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山区,以及长白山地区与辽东半岛;NPP值变化范围大致相同,分别为235.51—439.11和237.94—435.38 gC m-2a-1[21]。
从时间动态来看,植被NPP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季节和年际变化两方面。对于年际变化,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东北地区森林生态系统NPP在不同气候情景下的模拟结果基本一致,且模拟结果一般高于或近似于NPP实测值,均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东北地区植被NPP的这种提高,很可能是受气候变化的系列影响,如:地区气温升高、多年冻土退化、冻土冻融时间缩短,植被发芽期提前、落叶期推后导致植被生长期延长[33]。
3.1.2东南林区
中国东南部植被年均NPP总体上呈现出从南到北、由东至西逐渐减少的态势,不同植被类型间差异明显,以常绿阔叶林最高,落叶针叶林最低[34]。从变化趋势来看,近10年(2001—2010年)来我国东南植被NPP整体上略有减少,其中南部地区明显减少,北部地区明显增加[34]。关于东南林区NPP的研究相对有限,目前主要是以省市为单位或更小空间范围的零散报道。例如,采用Biome-BGC生态过程模型模拟结果[35]表明,1991—2005年福建省森林NPP总量年均值为2.04×108gC/a,单位面积NPP年均值为759.63 gC m-2a-1,从区域分布来看,NPP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闽中、闽西两大山带海拔高受人类活动影响小的森林分布区;另有研究[36]指出,福建省常绿阔叶林的NPP为1800 gC m-2a-1。采用周广胜模型模拟出1954—2009年浙江天童地区常绿阔叶林NPP升高趋势极为显著(50—60年代呈下降趋势,60年代之后呈振荡上升趋势),年均值为1219.6 gC m-2a-1[37];天童地区木荷米槠林NPP年均值为2116—2555 gC m-2a-1[38]。江苏省南京市森林NPP由北向南呈现逐渐增加的特征,最南部地区NPP大于1300 gC m-2a-1[39]。
3.1.3西南林区
对我国西南林区NPP的研究更为有限,相关报道也更为少见且比较零散,基本上是以地区植被NPP的研究为主。例如,对西南地区的研究表明,2001—2011年西南地区植被NPP均值为540.33 gC m-2a-1[40];横断山区 2004—2014 年植被 NPP 在整体上呈波动增加趋势,全区NPP年总量变化范围为183.768×1012—223.239×1012gC/a,多年均值为208.498×1012gC/a;NPP年均值变化范围为408—496 gC m-2a-1,多年均值为463 gC m-2a-1[41]。
3.2 未来中国森林NPP分布
目前,对未来我国植被NPP的预估研究也还非常有限,已有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气候情景各异,结论也千差万别。对于未来我国植被NPP的变化而言,有研究[42]表明,33°N以南NPP将显著增加;33°N以北,NPP增加较少,局部地区生产力甚至下降。这与区域研究中气候变化将导致未来我国北方地区森林NPP明显增加的结论不一致:在未来温度增加2.5℃、降水增加12%、CO2浓度加倍的情景下,长白山阔叶树和红松林的NPP增幅分别为27.87%和23.96%[22];未来气候变化将导致我国东北地区森林NPP明显增加[43-44];未来气候情景下中国新疆天山云杉NPP也将会增加26.4%—37.2%[45]。也有研究模拟出未来气候变化引起的森林NPP在不同空间上的增加,如:到2030年我国森林NPP将由东南向西北递增1%—10%不等的幅度[46]。还有模拟预估结果表明,21世纪末(2090—2099年)A2、A1B、B1情景下我国植被NPP平均值依次由高降到低。其中,3情景下NPP最低值均在本溪,分别为895、953、886 gC m-2a-1;最高值在A1B、A2情景下均在琼海,B1情景下在桂平,分别为2927、2719、2826 gC m-2a-1[47],也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增加。
未来植被NPP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情况比较复杂,不同森林植被类型间差异性很大。一般而言,NPP对降水变化将为正响应;对温度变化正负响应均有,但对温度的响应强于对降水的响应;对CO2浓度变化为正响应或无响应。例如:有研究表明,在未来A2和B2情景下植被NPP与降水量增加呈正相关,与温度升高呈负相关,其中温度升高对NPP的负效应要大于降水量增加对NPP的正效应[19]。在未来CO2浓度、温度及降水同时增加的情景下,长白落叶松林NPP明显增加;单独增加温度会减小长白落叶松林的NPP,而降水及CO2浓度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NPP的增加,但降水增加的正效应明显弱于温度升高的负效应[23]。也有研究表明,未来单独升高温度或增加降水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阔叶红松林NPP的增加,但降水明显弱于温度的作用;CO2浓度加倍与温度、降水同时增加的情景下阔叶红松林NPP也将明显增加,然而,单独升高CO2浓度对阔叶红松林NPP没有明显的影响,但能促进长白落叶松林和华北地区典型油松林生态系统NPP的增加[15]。
综上,由于生态系统本身及外界环境影响的复杂性、测定标志不统一、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等各种原因,导致目前的研究中对NPP的定量描述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NPP长期动态变化特征也可能存在差异。然而,NPP的这种整合研究能够有助于全面掌握全国大范围以及特定区域特定生态环境条件下NPP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动态变化规律,充分反映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对NPP研究数据的积累和有效整合,对于大数据时代基础数据库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评估以及自然植被资源适度利用和科学管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4 气候因素对中国森林NPP的影响
植被与气候因子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耦合关系。气候通过改变环境条件在植被的生理结构、过程等方面控制植被NPP的形成,因而NPP的变化能直接反映植被生态系统对环境气候条件的响应。在千年尺度上,气候变化是区域植被变化的主要原因,而非气候因子仅处于次要地位。近几十年气候因子的变化已经引起森林生态系统植被分布和生产力等多方面的变化[48]。其中,温度、降水、大气CO2浓度、太阳辐射和地表蒸散的空间格局是影响植被NPP分布和碳收支的重要控制因素。目前大量研究分析了植被NPP与这些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尤其以前三个因子的研究居多。
4.1 单因子的影响
4.1.1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森林NPP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研究区域、时段差异以及与其他因素的协同作用其结论不尽相同。升温同时控制着植被光合和呼吸两个过程,对这两个过程的影响决定着生态系统NPP的升高或降低[49],即存在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一方面,单独温度升高对森林生态系统NPP产生抑制作用,因为升温可增大植被呼吸速率,加速植被的干物质消耗,不利于森林植被对营养物质的累积。同时,升温会加剧土壤水分蒸发,导致森林植被水分胁迫增强,植物为了避免体内水分的大量流失,气孔关闭,降低光合作用速率,从而限制植被生长。目前的研究中,升温对NPP抑制作用的研究结果相对较少,主要有对长白落叶松林[19]、北京主要森林[24]等的研究。
另一方面,升温也可以加快森林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进程,加快植被光合作用速率,延长植被生长季,从而提高植被的NPP[50]。升温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加速土壤凋落物的分解,促进土壤养分的矿化,加快养分的释放以及增加养分对植物生长的有效性[51]。许多中高纬度森林的生长均在一定程度上受氮素供给的限制,而升温能导致土壤氮素有效性的升高也可能间接地促进森林植被生产力的增加[52]。升温对NPP促进作用的研究结果比较多见,例如:中国东北地区气温较往年偏高1—2 ℃时,落叶针叶林年均NPP大幅增加[27];温度上升2 ℃时,兴安落叶松林的生物量和生产力均增加[53]。
升温对NPP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升温阈值。模拟结果表明,温度升高1.5℃和2℃时,东北大部分绿色植被(常绿针叶林和杂木林除外)NPP增加,增幅为0.58%—10.34%,均以针阔混交林波动最大;但温度升高超过3℃时,所有植被类型的NPP均降低,降幅最高达10.48%,以常绿针叶林降幅最大[49];江西省在气温低于17 ℃的区域,温度越高 NPP 也较高,而在温度高于17 ℃的区域,NPP则随温度增加而降低[54]。
温度对NPP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例如,有研究[19]表明,1980—2013年长白落叶松林NPP与年均温度无明显相关关系,而与上年11月至当年4月份温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秦岭火地塘林区油松林乔木层NPP与上年及当年7月份温度均正相关,其动态变化主要受1—7月份平均温度影响,华山松林乔木层NPP只与上年7月温度显著正相关,其动态变化主要受 5—7月份平均温度影响[55]。
4.1.2降水的影响
中国森林生产力的分布格局主要取决于气候环境中的水热条件,而其中的水分条件在决定中国大部分地区森林生产力水平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6]。水分需求、水分平衡影响着植物光合作用,从而对NPP产生影响。水分胁迫能导致气孔导度降低甚至关闭,植物蒸腾和光合作用都显著下降,植物在防止叶子失水的同时也减少了干物质的积累。
降水量对NPP的影响与植被所处的干湿环境息息相关,总体来说,降水量增加对NPP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尤其在较干旱地区,降水量增加能够缓解水分胁迫,增加土壤湿度,利于植被干物质的积累。然而,这种促进作用也存在一定的阈值,并不是降水量越高NPP就越大。例如,江西省在降水低于1900 mm的地区,随降水量增加NPP略有增加,但幅度较小且波动较为剧烈;在降水量为1900—1950 mm的地区,降水越多NPP也越高,且增加显著;但在降水量高于1950 mm的地区,NPP则随着降水的增加而降低[54]。此外,不同植被类型对降水量变化的敏感程度也不同,且相比降水量增加和减少的情况,NPP对降水量减少更为敏感,尤其对降雨量减少5%反应最为敏感,以针阔混交林最甚[49]。
一般而言,任何两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总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在现实情况下植被NPP变化通常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降水量的变化通常与温度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能还存在相互作用,故单独分析降水量单因子变化对森林NPP影响的意义并不大,因而相关研究也并不多见。
4.1.3CO2的影响
CO2作为原料参与光合作用,同时还通过对温度、植物水分及营养物质需求等作用来影响NPP。一般而言,当CO2浓度升高时,植物能通过降低自身的气孔导度来降低冠层蒸散,从而提高土壤水分的利用效率,同时还能够提高土壤氮的利用率,进而提高森林植被的光合作用效率,促进干物质的累积[56]。然而,关于CO2浓度升高对森林NPP的影响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
绝大部分研究认为,CO2浓度升高对森林NPP增加具有促进作用。例如,CO2浓度升高促进长白落叶松林NPP的积累,CO2浓度每升高1 mg/L, NPP增加2.6—3.5 gC m-2a-1,且CO2浓度越高,NPP增加的幅度越大[23],其他一些研究[19,57-59]也得出了相一致的结果。关于大气CO2的施肥效应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多数研究认为,CO2浓度升高有利于促进植物个体生长发育,加速生物量积累,即CO2具有施肥效应。对热带地区150多个地块的本底调查表明,近几十年来一些原始热带森林的生物量和生长速度均有所增加[60],这在55个温带森林地区也得到了证实,CO2施肥效应被认为是最为可能的贡献[61]。然而,由于生物群区、光合作用方式和生长形式的不同,不同植物对CO2浓度增加的反应差异很大。一般而言,生长速率快的物种比生长速率慢的物种(例如,落叶树比常绿树)对CO2浓度升高的响应更敏感[62]。对树木进行高浓度CO2熏蒸,一般也具有施肥效应,其短期直接效应表现为光合速率增强、光呼吸和暗呼吸均有所减弱、气孔导度降低、水分利用效率提高,生产力提高,从而促进树木的生长。但长期处于高CO2浓度下,树木对CO2浓度升高适应后,光合速率可能会逐渐恢复到原有水平,CO2的施肥效应会消失[63]。
然而,有部分研究[64]表明,即使在高水平营养供给下,也还有一些物种对CO2浓度的升高并没有反应。例如,单独增加温度(2℃)或单独增加降水(12%)都能促进阔叶红松林NPP增加,而单独CO2浓度倍增对阔叶红松林的NPP没有明显的影响[22];单独增加大气CO2浓度对新疆雪岭云杉NPP没起明显作用[45];单独CO2浓度变化对栓皮栎林NPP影响较小[24]。也有模拟研究[65]发现,CO2浓度增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远小于对小单木生长的影响,在竞争环境中生长的树木常常表现出比单个生长的树木的反应要小,在特定情况下对生态系统没有任何影响或影响很小。例如,Melillo等[66]通过TEM模型模拟发现,仅大气CO2浓度倍增并没有改变北方森林的NPP。甚至有基于树木年轮的研究[67]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的树木生长并没有随着气候和CO2的变化而增加。
目前,只有极少数研究认为,在CO2浓度加倍、气候不变的情况下,NPP降低,但降低幅度很小,例如,对北京山区栓皮栎林的研究[24]。
据分析,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可能与植物、环境条件以及CO2作用时间长短等均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虽然很多FACE试验表明在CO2浓度加倍的情况下植物NPP显著增加[68],但野外森林生长观测研究发现CO2的施肥效应很弱[68-69]。究其原因,一方面,目前多数FACE试验研究是短期的,而且试验中CO2浓度是突然增加的,然而在自然界中CO2浓度的增加是一种缓慢长期的过程。另一个方面,森林生产力对CO2的响应还受其他环境条件的限制,如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由于低温及其导致的可利用氮的限制,树木难以利用升高的CO2浓度提高生产力[66,69]。
4.2 多因子的协同作用
4.2.1降水与温度的协同作用
一般而言,单独降水增加有利于森林NPP积累,升温对森林NPP的影响可正可负,升温和降水的协同作用主要取决于这种正、负面影响的相互抵消或叠加结果。例如,单独温度升高2.6℃刺槐林NPP降低了14.58%,单独降水增加10%刺槐林NPP增加8.82%,当温度升高2.6℃同时降水增加10%时,NPP降低了7.48%[70]。相同升温情况下,降水量的变化情况对于NPP的变化具有决定作用,如对浙江天童地区常绿阔叶林预估研究[37]表明,同在温度升高2℃时,降水量增加20%时NPP将升高15.9%,降水量减少20%时NPP将降低4.9%。而且,温度升高比温度不变时,降水增减对NPP的影响更明显,而温度不变、降水增减对NPP影响均相对很小。例如,关于东北森林生态系统NPP的研究中,气温升高3℃、降雨量不变时NPP年总量增加0.032×1015gC/a,增加了9.37%;气温升高3℃同时降雨量增加20%时,年NPP增加0.037×1015gC/a,增加了10.99%;而当气温不变、降雨增加20%或减少20%时,年NPP总量也相应增加或降低,但幅度都很小,只有5.72%和3.14%[71]。
就全国范围而言,温度和降水变化对NPP影响的重要性因不同的环境条件,其结论不一。有研究[16]认为,中国大部分地区植被NPP的变化主要受气温变化的影响,而干旱半干旱区域植被NPP主要受到降水的影响。也有研究[64]认为,中国温度变化对NPP的影响总体低于降水变化的影响,植被NPP的响应情况更接近于单独降水变化时对植被NPP产生的影响。就区域分析发现,规律性也并不明显。一种研究结果表明,有些区域温度比降水对植被NPP的影响更显著,如:东北森林NPP对温度比对降雨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温度升高和降雨增减的情况下NPP变化的幅度较大,而温度不变、降水增减的情况下NPP变化均很小[71]。另一种研究结果表明,有些区域的森林NPP受降水比受温度的影响更显著,如:华北落叶松林(相关系数0.75)[72]、北京山区刺槐林(相关系数0.83)[73]、北京山区栓皮栎林(相关系数0.89)[24],它们的NPP年际变化与年降水量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温度的相关性不显著。还有一种研究结果则表明,温度、降水均能对NPP产生极显著的影响,如:长白山阔叶树NPP与温度、降水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2]。
然而,自然界中气温与降水变化对森林NPP的影响非常复杂,可能具有交互性或消长性,例如,生长季前的升温能导致红松林NPP增加,但这种增加也可能被夏季降水减少所抵消[74]。这种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例如,在中国东南部的北部地区植被NPP与降水关系密切,而在南部地区由于气温较高而且降水充沛植被NPP随温度和降水的变化没有北方明显[34]。此外,不同森林类型对温度和降水的响应也差异显著,例如,即使同在三峡库区,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及针阔混交林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表现出正响应:在温度增加2℃、降水增加20%的情况下,其生产力均增加,增幅分别达到24.34%、22.50%和15.98%;而常绿针叶林却相反,在相同的温度与降水变化条件下,生产力降低,减幅达5.55%[75]。
4.2.2CO2浓度与温度、降水的协同作用
CO2对森林生态系统NPP的影响与温度和降水的协同作用息息相关,但其作用效果不尽相同,依不同森林类型而异,结论甚至相反。
一方面,CO2浓度升高与降水量增加,两者协同作用对森林NPP具有正效应,但温度升高却表现出负效应。其中,有一类研究认为,CO2与降水量的协同正效应大于温度的负效应,但单独降水量的正效应不敌温度的负效应,如对长白落叶松人工林及北京山区刺槐林的研究[23, 73]。然而,也有研究表明,CO2与降水量的协同正效应却小于温度升高的负效应,例如,对SRES A2和B2排放情景下长白落叶松林的研究[19]。此外,还有研究表明,CO2浓度加倍、降水增加和温度增加协同作用降低了NPP,各因子之间表现出较强的交互作用,例如,对油松林的研究[76]。
另一方面,CO2浓度升高与降水、温度增加均有利于NPP积累,且协同增加作用比单个因子对NPP的积累作用更明显。例如,有研究认为,在未来CO2浓度加倍及温度、降水同时增加时,长白山阔叶红松林NPP将显著增加[22];CO2浓度加倍,气候不变或变化的情景下刺槐林NPP均增加,且气候因子间均为正交互作用[70]。
4.3 气候因子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气候因子是植被NPP分布的重要控制因素,但不同环境下不同气候因子的相对重要性明显不同。
针对全球较湿润的森林生态系统,年均温(r2约为0.50)较年降水(r2约为0.40)与NPP具有更强的相关性[12]。但也有研究[13]表明,年降水较年均温与NPP的相关性更强。对于干旱的陆地生态系统,在旱季,NPP对干旱强度尤其敏感,降水量及水资源利用率的变化对植被NPP影响显著;而在雨季,降水量的变化则对NPP的影响较小[77]。
就中国而言,绝大部分研究认为,不同森林生态系统NPP不同程度地受到气候因子的影响,总体而言,各气候因子对NPP的影响程度由区域植被生长的首要限制因素决定,如在高寒地区,低温是制约植物生长的主要因素,因此温度与NPP表现为较高的正相关;而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降水是影响植物生长的首要因素,所以降水量与NPP的正相关表现的更为突出,相反,温度升高可能会导致蒸发加剧,从而加重干旱的程度,因而有时与NPP呈现负相关[78]。例如:青藏高原西北部降水量小于400 mm的区域内植被 NPP 的主导因子是降水,东南部降水量大于 400 mm的区域内植被 NPP的主导因子是温度。而且,对NPP的首要控制因素因局地环境差异性大而差别很大,例如:同样在东北地区,大小兴安岭森林植被NPP整体呈现出了上升趋势,据原因分析,植被生长所需水分(降水、积雪融水、冻土融水、蒸散等)和热量条件均朝着更加适宜植被生长的方向发展,且该区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小[31]。同时,东北也有部分地区森林植被NPP主要与地表蒸散呈显著负相关,部分地区主要与温度和太阳辐射呈正相关[31,79]。在我国三北防护林项目区,降雨供应对NPP变率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干旱对NPP变化的贡献约高达74%[80]。
然而,也有少数研究[81]认为,我国大部分森林生态系统NPP不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其中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NPP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很低,特别是常绿阔叶林的高大乔木受降雨和温度变化影响小,抗旱抗涝,自我修复能力强,但亚热带常绿阔叶林NPP的脆弱性在增加。然而,除了气候因素,非气候因素对NPP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非气候因素中,植被类型、植被的环境条件包括地形、地貌等,以及人类活动均能对植被NPP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NPP时空格局与土地利用类型密切相关,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了植被类型变化进而影响植被NPP[82-83]。一般而言,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林NPP最高,落叶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次之。森林物种组成的长期变化也能间接地影响森林生产力[84]。植被的环境条件,包括地形条件如海拔、坡度和坡向,以及石漠化等,均能影响自然植被NPP。已有研究[85]表明,NPP在我国喀斯特地区比在非喀斯特区域反应敏感度高,离散程度大;NPP随石漠化等级的递增而减小,重度石漠化地区NPP明显小于其他地区,且石漠化等级越高NPP波动越剧烈。此外,其他一些自然因素包括自然灾害事件(如飓风[86]、火灾[79])、营养元素(如氮[87]、磷[88])也都会对NPP产生一定影响。而且,人类生产、生活或其他改造活动也能对森林NPP时空分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如:城市化[89]、森林滥砍乱伐、退耕还林等[90]。总而言之,NPP的变化是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以及其中耦合的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气候变化对森林生产力的影响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综上可见,目前的研究已充分展示了植被NPP对气候因素及其变化的响应特征,其中尤其是定量响应研究能为植被监测、资源利用和生态保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然而,这些研究中尚少涉及气候因素所引起的NPP变化过程中一系列植被生理反应,而这对深入理解气候变化与植被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机制至关重要,这还有待于在日后研究中进一步考虑。
5 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对中国森林生态系统NPP的研究取得了颇丰的成果,然而所开展的相关研究工作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5.1 重复性工作及研究结果差异性大
从目前已发表的NPP相关文献来看,我国对某些地区的研究重复性工作较多,特别是对重要林区如东北林区的研究尤其明显,这与学者之间研究信息交流和数据共享缺乏无不相关。同时,相关评估结果相差甚远,数据系统性差,导致即使是对相同区域的NPP估算值之间有的都无法进行比较。
无论是通过站点实测还是模型模拟,NPP估算值差异性来源都非常广泛。对于实测结果而言,即使同样都来自于野外站点调查,但结果仍然可能差异较大,可能的原因有:NPP包括地上、地下部分,有的研究只测定了地上部分,而有的研究则包括地上、地下两部分,即使均测定了地上、地下部分,对地下部分NPP的测定误差较大;野外调查经常面临很多困难,空间分布不均,样方选取的主观性强使得测定结果差异大;当将野外调查得的点尺度的NPP推算到更大空间尺度时,很可能会带来误差。对于模型模拟而言,由于不同模型的机理、运算方法和数据源等存在差异,导致对同一区域的NPP模拟值也很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即使使用同一个模型,参数设置、数据源不同也可能造成模拟结果的差异性。其中,所使用的气象数据一般都是用气候学方法计算并插值得到的,在这个由点到面以及不同分辨率之间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起误差,从而影响NPP估算结果。
5.2 现有结论的不确定性
模型为NPP估算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模型模拟能力、对相关参数获取限制以及参数化方法的误差等诸多方面,均会给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NPP的估算精度上。对于生态系统模型而言,模型模拟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基础上,对生态系统复杂机理进行一些简化处理,忽略掉一些非决定性或者无法进行评估的细节过程,这必将增加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例如,极端气候事件会对森林的分布、结构产生极大影响(如飓风和热带风暴对于热带雨林的破坏力巨大,对生态系统结构的改变往往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对气候变化背景下NPP的变化模拟过程中却很难对这些极端事件作出评估,从而未加以考虑,这也会对NPP模拟结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以Biome-BGC模型模拟为例,由于试验条件限制,一些研究只能针对部分敏感参数进行实地测量,其他很多参数都是参照相关文献以及模型本身自带的参数,也忽略了一些系数(如水分胁迫系数),这对模拟结果均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5.3 研究的局限性
目前对NPP的估算存在诸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基础数据不足、建模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和模型验证困难3个方面:对于模型估算,由于受一些基础数据及模型参数获取限制,建模工作往往受限。而且,由于受试验条件、野外工作环境所限,观测数据相对较少且较难获得,故而影响模拟结果与实测数据的全面拟合与校验,使得模型准确性验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研究区范围较小,地形(海拔、坡向、坡度)、土壤等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对NPP有较大的影响[91],而模型模拟时输入的参数无法细致地反映出这些细微变化,使得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存在偏差。
6 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1)模型精度和适用性提高仍是重点。模型是NPP估算不可或缺的手段。模型参数和数据来源是决定模型精度最重要的因素。国内对NPP 的模拟多是对国外有关模型的改进。模型运行所需的很多参数在国内尚未研究,因而参考前人的成果。因此,以后的研究中应考虑根据中国实际特别是根据区域及研究数据的特点将参数更合理和实践化,以确定适用性更强的参数。此外,由于国内还存在观测不太完善的问题,如测定标准不统一、观测指标连续性不够等,造成很多数据的可用性较差,因而建立长期定位观测网络体系、强调观测资料的标准化和可比性,也将有助于模型参数的校正和改进,从而提高模型精度。
(2)建立精度高综合性强的耦合模型是重点也是难点。虽然已有模型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它们也均有各自的优点,应该发挥各自优势。基于多种算法的集合模拟通常产生显著优于单个算法的模拟结果[92]。各模型的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将是准确预测研究的发展趋势[93]。因而扬长避短、融合各模型的优点,建立精度高、综合性强的耦合模型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今后NPP评估的一个必然发展方向。
(3)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目前植被NPP的影响研究中,所采用的气候指标基本上是年平均的变化,很少或没有考虑其季节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而在气候变暖大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趋多趋强,气候的季节波动将更为明显,这对很多物种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不容忽视。此外,如前文所述,林地生长环境(如海拔、地形、地貌等)、自然灾害(如风害、病虫害、火灾等)、营养元素(如氮、磷等)限制、人类活动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NPP,但由于数据收集困难、人为因素难以定量化等各种原因,NPP的评估过程中很少对这些因素进行全面考虑。故此,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加注重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发展更加完善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4)进一步加强机理性研究。目前陆地生态系统与关键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其耦合关系仍缺乏机理性分析,以后的研究中应予以加强。一般认为,温室效应和气候因子通过影响植物生长发育过程和水分循环过程,对植被生产力的形成产生影响[4,71]。然而,各因子随植物生长的变化情况以及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往往并没有太多考虑。此外,陆地生态系统与气候变化之间相互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清晰化,可能尚需从植物生理学角度去加以解释[15]。
(5)针对性选择合适的研究尺度。NPP评估的不确定性很大,且在不同地域尺度上差异明显,因而针对性选择合适的研究尺度非常重要。全球变化加剧了气候在地域间的不平衡性,使得NPP在区域尺度上的响应更加明显。就模型模拟而言,大尺度模型无法考虑地面栅格单元内植被、地形以及气候条件等的异质性,而区域尺度上的主导控制因素比较明确,空间异质性相对较低,因此也更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94],因而目前以及未来的研究更多地还是集中在区域尺度上。对于我国而言,模拟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北部生产力比南部具有较大的变化和不确定范围,因此,从最大程度减少和降低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的不确定程度出发,我国未来NPP研究的重点区域很可能在北方[42]。
(6)加强研究信息交流和建设网络化数据共享平台。由于研究信息交流仍较缺乏,不同学者采集的样地不同,利用不同的估算方法、不同的参数得到不同的估算结果,从而使得数据系统性较差、评估结果相差甚远,也容易出现重复性工作的情况。因而,在加强研究信息交流的基础上,采用先进的研究技术手段,围绕森林资源和环境保护等热点问题研究森林生产力,同时实现数据共享和网络化是生产力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95]。
综上,在选定合适的研究区域基础上,建立精度高、综合性强的耦合模型,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同时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同时在加强研究信息交流的基础上,建设网络化数据共享平台,有效减少重复性工作以及降低评估结果的差异性,这些都是未来NPP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