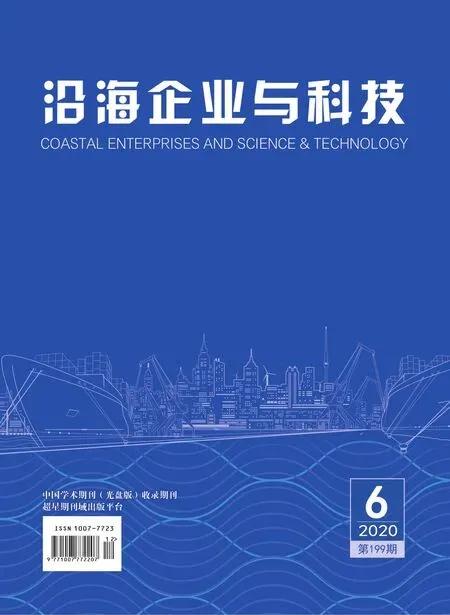壮族传统制陶工艺的发展历史与现代传承
——基于靖西市凌准村的田野考察
凌春辉
靖西市禄峒镇凌准村的古龙窑建于清朝乾隆四年(1739 年),至今已有近300 年的历史。数百年来窑火不熄,是迄今为止桂西地区现存的、唯一还在活态传承的古龙窑。凌准村生产的壮族土陶是纯手工制作,质地细腻、厚薄均匀,造型大胆,独具壮族乡村风格。凌准村壮族土陶制作和烧制技艺独特,其历史悠久、富有生活实用性,具有生活使用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学术研究价值等;然而,在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下,和诸多民族传统手工艺一样,正面临着市场萎缩、后继乏人的严峻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 年10 月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指出:“承认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进程在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与不容忍现象一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在缺乏保护资源的情况下,这种威胁尤为严重。”[1]然而,对于不得不接受全球化和市场化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来说,如何保护并发展传统的民族手工艺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壮族传统制陶手工艺承载着壮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生存智慧,是壮族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靖西凌准村的壮族传统制陶工艺曾作为当地壮族村民的主要谋生手段,与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水乳交融。而今,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冲击下,这门技艺的传承人队伍日渐萎缩,传统的土陶技艺逐步衰退,原始的夹沙陶技术也濒临消失。为此,本文以靖西市禄峒镇凌准村为调研点,对广西壮族传统制陶手工艺的兴衰发展历程进行田野考察,在此基础上,就壮族传统手工艺的现代传承与发展问题作一探究。
一、调查点概况
靖西市地处中越边境,边境线长152.5 公里,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平省茶岭县、重庆县山水相连,西与那坡县毗邻,北与百色市区和云南省富宁县交界,东与天等县、大新县接壤,东北紧靠德保县。总面积约3322 平方公里,辖11 个镇、8 个乡,全市99%以上人口是壮族,是全国典型的壮族人口聚居地。位于禄峒镇的凌准村原属荣劳乡,荣劳乡位于靖西市区西部33 公里。明、清时为荣劳峒,光绪年间为荣劳团。民国21 年为荣劳乡,属西区。1950 年初设荣劳区,后改为第六区,区驻荣劳,1951 年迁禄峒,改为第七区,1958 年后属禄峒公社。1984 年10 月,单独划出设置为乡,乡驻荣劳区,下辖12 个村(街)公所,85 个村民委员会,有荣劳、凌准两个圩场。该乡大部分地区为岩溶峰丛山区,谷地以荣劳、大史、四院三处较广,余为狭窄的洼地、槽谷,西部怀隆、伏龙一带有少数沙页岩土山。农业方面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红薯,兼种黄豆。经济作物有田七、油菜、甘蔗、八角等。凌准村是个典型的壮族村落,下辖龙球、峒邦、旧窑、新窑、新街、旧街、念者、弄怀等八个自然屯[2],2005 年荣劳乡并归禄峒镇。凌准村是靖西市主要的制陶手工业区,被称为“土陶工艺村”。该村周围树木丰茂、碧潭幽深、风景宜人,因村民擅长手工制陶而远近闻名。
二、靖西壮族传统制陶工艺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
据《靖西县志》记载:“凌准村的陶瓷制品,始于清代,主要产品有瓦缸、瓦钵、花盆、瓦瓮和酿酒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还生产陶碗花盘等,合作化时期纳入集体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后则以私人副业的形式进行生产。”当地村民口碑流传:凌准村从清代乾隆年间就开始制陶,这里的制陶技术是明清时期由湖南籍陶工所传授,旧窑屯、新窑屯的很多村民都是传承了六七代、甚至十代的制陶世家。该村的梁才耀师傅一家保存有“关于陶瓷师傅台建立”的资料,该资料记载:“自乾隆二年,梁、唐二姓携手由永淳西迁至此,开始发现此地土质适宜开发陶瓷,且地理龙脉极佳,环境优越,遂由梁正伟、唐绥和、唐协和、梁汝梅、梁汝昂等5 人共同首创就地破土建窑。一边开发种植,一边从事陶业,实行工农并举。随业定村名为窑庄。世代延习祖业,自此事业兴旺发达,生活安定。后人为纪念5 人事迹,尊其为陶瓷先师,并筑台立碑于窑旁,每日烧香供奉,并定于每年农历九九重阳节为敬奉造窑先师纪念日”。就这样,凌准村的制陶手工艺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制陶手工艺在凌准村得以代代相传并非偶然,与凌准村特有的土地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该村既拥有得天独厚的制陶所需要的粘土和沙土,还具备历史悠久的制陶工艺传统,因此土陶器的制作在凌准村曾经拥有辉煌的兴盛期。据村里一些老人的回忆,20 世纪50 年代以前,凌准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制作土陶器,除了念者屯和弄怀屯制作夹砂陶、峒邦屯不制作陶器之外,各家各户都以家族作坊为形式制陶。20 世纪60 至70 年代后,集体化的生产则取代了家族作坊式的加工,这一时期村里设置有专职的销售员和保管员,产品销售面有所拓宽,除了销往靖西县城和毗邻靖西的那坡县及云南部分县市外,还有部分产品销往了越南。20 世纪80 年代后,凌准村又恢复了家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这一时期的土陶器生产以旧窑屯、新窑屯为代表,几乎每家每户都以制陶为生。80 年代中后期的土陶生意最为火爆。据村里老人回忆,80 年代他每年烧窑的收入有1万多元,在那个年代这个收入可以说非常可观了。当时,因为产品供不应求,所以各家各户加班加点生产土陶的情景很是常见。在寒冷的冬天,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人们甚至通过烧热水来制作土陶。1986 年至1988 年这三年间,每天村里都会进出许多拉土陶器的车辆,其中很多都是拉往越南的。一些村民干脆就买来了手扶拖拉机,专门干起了土陶器成品的运输生意,收入也相当不错。90 年代后,凌准村的陶器生意由乡镇企业局统一收货和统一销售。1996 年至1998 年间,村民们主要根据当地企业局的订单进行生产。90 年代中期以后,土陶产品的市场日渐萎缩,需求量减少,其价格也越来越低。致使土陶产品收不完、卖不掉的趋势日趋加剧,很多村民只好另谋出路,停止了土陶生产。以新窑屯、旧窑屯、念者屯为例。过去新窑屯家家户户都生产土陶,但1998 年之后村民们都停止了土陶生意。新窑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塑料以及金属制品逐渐取代了陶制品,土陶市场的衰败使大部分村民不得不放弃土陶生意;二是受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过去新窑屯制作土陶所需沙土都是由旧窑屯提供,因为新窑屯本身缺乏制陶用的沙土,仅有的一座窑也是由旧窑屯帮垒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窑屯再也没有村民从事传统土陶器的生产。而旧窑屯作为土陶工艺发源地和主要传承地,90 年代中期后,其土陶制品种类和生产数量也逐渐减少,当地老一辈的制陶艺人开始闲置制陶手艺,而年轻一代更是缺少传承这门手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壮族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开发与经济互动》一文介绍到“旧窑屯制陶由过去的90 多户以生产土陶为主,发展到20 多户人家在生产土陶,当时生产土陶的人大部分在40 岁以上,30 岁左右的制陶艺人只有4~5 个,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一又苦又累且收入微薄的工作[3]”。因此,旧窑屯的土陶生产及其技艺传承也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困境,濒临后继乏人的危机。而今,旧窑屯坚持做土陶的只有4~5 家,制陶艺人的年龄都在40 岁以上。20 世纪90 年代,念者屯有8 户人家仍在坚持制作夹砂陶[4]。现在近三十年过去,念者屯已经没有人制作夹砂陶了。唯一掌握夹砂陶这门技艺的是凌准街的梁才耀。梁师傅平时利用农闲时节制作夹砂陶,他制作的夹砂陶造型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比如南瓜茶壶,竹报平安茶壶等,有些也融入壮族的文化元素,例如壮族英雄侬智高像、绣球等。如今,凌准村坚持经营制陶这门传统手工艺的已不足10 户,制陶艺人也逐年减少。当前陶器的生产方式也比较分散,制陶人根据客户的订单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器坯都统一在村子西边的窑里烧制。
三、靖西壮族传统制陶工艺的制作流程与革新现状
凌准村的陶土有红土、黄土、黑土等几种,其中以红、黄颜色的土为佳,黑土次之。据有经验的制陶人介绍,用红、黄土来烧制而成的陶器,声音显得清脆,敲击时会有金属声;而用黑土烧制的陶器,声音沉闷,没有金属声。因此,对于陶土的选择尤为重要。凌准村所采陶土的地点均在村子周围,方圆约两平方公里。凡发现有好泥土的地方,全村的陶工都能去采用,不准个人霸占,体现了原始的公有制度。靖西市传统制陶工艺品主要分为两种:夹砂陶和土陶。据了解,夹砂陶的制作主要是在念者屯和弄怀屯。靖西市制陶传统中,一个夹砂陶陶器的生产大概要经历“采泥—采石—舂石—抟泥—制坯—阴干—入窑—烘窑”等工艺流程。
采泥:陶泥的采集非常关键,要求泥土黏性强、杂质少且细腻柔滑。采回来的新鲜泥土要“养”,即放在大缸里用水浸泡,制坯时再从大缸里捞出。这是制陶的第一步。
采石:制作夹砂陶用的砂粒是从山上采的加工过的方解石。方解石呈晶体状,经大火煅烧后,容易松散软化,趁热用铁锤敲击,用竹筐或泥箕挑回来加工粉碎,就成为制作夹砂陶的重要原料。
舂石:采回来的方解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舂击至均匀的小颗粒状。用竹筛筛过一遍,就能倒入陶土内拌合制作器坯,这样,陶器就能耐火烧而不裂。
抟泥:陶工按照多年的经验将方解石与泥土的比例搭配好,然后在一块石板上抟泥,大约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坯泥显得光滑细腻。
制坯:当地采用轮制法制陶坯。这个方法很考验陶工的反应力和手脚的协调能力。陶工们脚踏转盘让其快速转动,同时双手在转盘上拉塑陶泥制成器坯。其流程大致如下:先在转盘上撒上一层草木灰,使其泥坯不与转盘粘连。在草木灰之上按压约2 厘米厚的陶土,作为器坯的底部,然后在上面用泥盘筑法作坯身及口沿。拉坯时使用“眉刮”,即用两块铁木做成的刮板。刮板厚0.3—0.4 厘米,宽7 厘米,高8.5 厘米,两端略呈锋刃,中间对称刻出一道凹齿形,以便握挟。操作时,一手挟持一块刮板在外坯,另一手挟持一块刮板在内坯,对称夹着坯壁,靠转盘的速度,不断地往上提拉。将器坯均匀提拉到一定的高度后,开始制作器坯的口沿。口沿不用刮板制作,而是用一块厚布缠在手指上,陶工们凭手感和几十年的制陶经验将口沿制成敞口、敛口或子母口等不同样式。
阴干:制成的器坯,需要在阴凉处放置3 至4天。由于靖西市的壮族居民居住的都是干栏式建筑,通风条件特别好,所以制成的器坯可以直接放于屋内阴干。但是,也有碰到客户急需取货的情况,陶工们就直接把器坯放在阳光下晒干。等器坯阴干至稍微坚硬时,陶工用专门的铁刀来修整底部,然后就可烘烧了。
入窑:靖西市传统制陶的窑室是一种半穴式露天窑。凌准村的陶窑就建在村头一个比较平缓的坡地上,向地下挖掘一个长宽约为1.6 米,窑深约30厘米,坑的南面有一个宽30 厘米的火口。在窑内,首先放上刚从山上砍伐的生木,以用来叠放器坯。装器坯时,大件的放在底部,小件的垒在上部。每次可以容纳40—50 件器坯,垒起来的器坯高出地表约1米,器坯上部分裸露,没有任何遮盖物。
烧制:烧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阴火和阳火阶段。阴火也就是慢火,将草慢慢放进坑里烘烧,火势不能太大,过旺的火容易将陶器烧裂。因此,每烧完一把草都要停一会。阴火烘烧大概需4 小时,期间还要进行3 次排气。每间隔一小时就用草在器坯表面明烧2 分钟,这就是排气。实际上,这也是补加火候的方法,使器坯全面受火,烧制均匀。阳火则与阴火不同,当阴火完成后,将草覆盖在器坯上,点火直接明烧,然后不断往火添草,一直烧40 分钟,陶器就烧成了。因陶器不施釉,陶工们可以根据火候来控制颜色,烧制的时间短,其陶器表面就呈铁红色,时间长了则呈灰白色。如果要使陶器变成黑色,就以生草或生树叶烧出浓黑烟将陶器烧黑。
凌准村除了擅长制作夹砂陶外,还擅长制作土陶。土陶主要制作生活用品,可以做成缸、坛、盆、罐、壶、蒸饭器、熬酒器、熬油器、烟囱、碗、香炉、金坛等器具。其中,缸分为大缸、小缸,坛分为大坛、小坛,盆分为花盆、洗脚盆、火龙盆,罐分为油罐、盐罐、酒罐、长罐,壶分为酒壶、茶壶。蒸饭器也叫“甑”,一般用于蒸糯米饭。
21 世纪后,以陶瓷先师后人梁才耀人为首的制陶艺人开始了对制陶技艺的革新,他的彩釉金坛让传统制陶工艺呈现出一缕新的生机与活力。梁师傅制作的彩釉金坛与原先的土陶相比,在金坛制作过程中分别增加了雕花、上釉等工序。其制作要经历“采泥—陶泥—揉泥—制坯—雕花—上釉—装窑”工序,具体如下:
采泥:采集黏土和沙土各一半。
陶泥:将采集回来的泥土搅拌均匀。将搅拌均匀的泥土放置在水中浸泡约5 天,然后用泥网过滤后晒干。
揉泥:和泥、闷泥先后反复进行,直至将泥揉得光滑细腻。
制坯:脚踏轮盘快速旋转坯盘,内为木制、外抹水和泥并用手工提塑,直至提拉成器坯。
雕花:将各种植物、动物等图案,采用泥条盘筑法装饰在器坯上,接着用木制雕花工具将各种图案雕刻成型。制作龙凤图饰耗时最长,大概需要20 分钟;制作麒麟图饰大概需要15 分钟;制作福、寿图饰大概需要10 分钟。这样下来,一个大金坛耗时一个半小时,小金坛则需要一个小时。
上釉:阴干后的器坯,陶艺人根据颜色深浅的需要将釉均匀地涂抹在器坯上。一般需要上釉3 次,或者直接用红泥制坯拌入草木灰烧成绿色陶器。
装窑:器坯按照大小顺序装窑,一般一窑可以容纳6 个口,一门40 个,最多可容纳400 多件小陶器、200 多件大陶器。
凌准村的传统土陶发展到现在,据梁才耀老人介绍,上釉的土陶只有金坛(即是葬具)这一品种,陶器上的图饰一般有龙、凤、麒麟这几种。这些都是很讲究的,福字位于中间,两条龙装饰两边的金坛为男性专用;寿字位于中间,两边分别装饰有两只凤的金坛为女性专用;还有一些比较讲究的,则用一大套一小使用的金坛。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1975 年,梁才耀师傅曾做过两套上釉金坛,但因与其他金坛相比价钱太贵并没能顺利卖掉,后来就不再制作上釉金坛了。直至2002 年由于传统土陶制品的滞销,梁师傅又开始尝试对金坛装饰的创新。他采用新的雕刻方法,即泥条盘筑法,很显然的创新使土陶有了活力,再次打开土陶的销路。当时,一个上釉的小金坛售价60 元,大金坛售价120 元,一整套的售价高达220 元。因为这种颇具特色的上釉金坛,当地有个老板就把梁才耀生产的金坛作为特色产品来买。现在的金坛市场已经不仅局限在靖西市区,邻近的广西德保、那坡等县和云南文山、富宁等县,以及境外的越南、泰国等国家都来订货,其中以成套的金坛最受商人欢迎。因为壮族大部分地区实行二次葬习俗,这也就为金坛的销售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市场空间。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梁才耀掌握了彩釉金坛这门技术,因此他的收入比其他从事传统土陶生产的人要高出一倍多。
目前,在凌准村掌握制作彩釉金坛这门手艺的只有梁才耀老人和他的小儿子。然而,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进行彩釉金坛的生产。他的三个儿子只有一个愿意学习这门手艺,但是掌握了制陶手艺的小儿子并不愿意在家里从事陶器的生产。现在他的大儿子是司机,专门在靖西市区开车;其他两个儿子都外出务工。除梁才耀老人外,凌准村其他的制陶艺人也是利用农作的闲暇时间来制作土陶,他们的土陶以素色为主,陶器主要印有简单的印纹陶纹和绳纹陶纹等装饰。
四、靖西传统制陶工艺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一)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
一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除了民间艺人自发的保护与传承之外;另外还需要政府发挥其行政职能,使公共资源有效地为公众服务。关于传统制陶手工艺的保护,靖西市已经把夹砂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靖西夹砂陶是广西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之一。然而目前凌准村掌握夹砂陶工艺的师傅绝大多数为年长的男性,年轻的男性大多都选择外出务工。传承人队伍青黄不接,传统的制作技术濒临失传。因此,传统夹砂陶的制作技艺有待于我们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政府部门的工作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实践,政府部门的参与将体现传统工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是传统工艺保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工艺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应遵循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的原则,纵使是进行开发,也应采取“保护性开发”的形式[5]。近年来,为做好凌准龙窑的传承和保护,禄峒镇党委、政府将土陶的传承生产与扶贫攻坚结合起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2016 年3 月镇党委、政府出台禄峒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凌准陶瓷保护工作方案,制定了可行性保护措施。2017 年3 月,禄峒镇镇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凌准街新窑屯龙窑维修工作的建议,该建议得到镇政府的高度重视,会后决定由镇文广站联合挂村干部及村委,对龙窑修缮工作进行细致调研,形成可行性报告。禄峒镇通过班子会讨论研究,决定将新龙窑修缮作为重要议事来抓,2017 年12 月下拨经费77138 元支持新龙窑修缮。在镇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新龙窑于2018 年8 月正式竣工,除开群众自发投工投劳外,总投资共计85256 元。另外,禄峒镇党委书记亲自挂片联系凌准街,对接上级部门加大力度对龙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安排具有产业发展特长的副职领导挂点联系该村,安排责任心强的镇干部负责挂点联系村具体工作,并派出镇级精干力量作为凌准街挂村第一书记。这些举措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脱贫攻坚有机融合,对该村的扶贫攻坚和土陶文化的保护传承,意义重大。
(二)传统手工技艺的继承与创新
传统手工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缺少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载体,主要以技艺或技能的形式存在于传统工艺持有者的头脑中。“只有掌握这些技艺的匠人、艺人或是普通百姓在以不同方式将它们复述、表演或是制作出来时,人们才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6]。一项传统工艺要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兴衰变迁而能无限延续下来,最根本的条件是精通该项技艺的艺人存在并且历经朝代变迁而能传承下来。技术人才是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发展的主体,他们精通技术,敢于创新,是工艺技术的活态载体。他们对本身所从事的工艺事业具有无限的热情,能自觉地把自己最大的勤劳与智慧投入其中,甘愿守候一生。他们是一项传统工艺的灵魂,是工艺血脉的延续。靳之林先生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问题,应首先着眼于人的抢救保护,而不只是让它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保护典籍和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物质的保护,作为精神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人的传承,是活态文化的传承。在这里,‘保护’二字的内涵就是传承,不能传承何谈保护?”[6]因此,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就应该从传承开始,只有传承下来,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一个传统要想延续下去,就离不开后代有意识地占有[7]。”很显然,一种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需要继承人有意识地去接受以及创新。目前,凌准村的传统土陶手工艺已经陷入了困境,不仅制陶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且缺乏年轻一辈传承人的参与生产。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不仅要求保护它的原真性,更要赋予它新的生命活力。
靖西壮族制陶传统的发展之所以面临困境,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背景下,传统陶制品市场无法满足制陶者的经济诉求,市场的不景气使众多制陶者放弃了祖辈传承下来的祖业。传统陶制品市场走向低迷,更多是与传统陶制品缺乏创新,品种单一、功能单一所导致。数百年来,凌准村所生产的陶器墨守成规,鲜有变化和发展。除了金坛,绝大多数的陶器一直局限于朴实无华、缺少装饰的生活用品。唯一出新的金坛,掌握其制作技艺的人也很少。这些无疑是凌准村传统制陶手工艺传承与发展的最大瓶颈。而要想解除这个困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革新。通过技艺创新,丰富陶制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使“传统”与“现代”成功对接,使陶制品既有历史气息又带时代风采,从而为传统制陶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因此,必须启动陶艺创新人才的培养。
作为靖西制陶手工艺的传承人,梁才耀师傅身上背负着把这一项民族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的使命。那坡县的符米铁就是跟随梁师傅学习制陶技术,如今已经能自己制作出一系列关于那坡黑衣壮记忆的泥塑作品。其代表作有《黑衣壮的酒》《母子粽》《有朋自远方来》等。此外,凌准村还成为了百色市高校的实践教学基地。百色学院艺术系艺术设计专业主修民族工艺设计方向的学生在学院老师的带领下,到靖西市凌准村进行实践教学活动。该教学活动在凌准村的梁才耀师傅家进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教学首先从最基本的成型技法学起。经过数天的学习,学生们基本上掌握了练泥、找中心、压底、拉高等拉坯的动作要领,继而学习雕刻加工成茶壶等造型和绘画、涂釉等各环节。这一系列的制陶过程学习使学生们对传统陶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期间,学生们完成了陶艺坯体作品共86 件,大部分是雕塑、壶型与瓶型的设计,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点。从陶艺专业角度来讲,学生们能够有实践的基地,进行类似的采风活动是学习陶艺最好的提升方法。通过向经验丰富的制陶艺人学习与交流,不但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传承和保护民间濒临失传的夹砂陶制作工艺的作用。
(三)制陶生态环境的优化与维护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凌准村为了能保持山清水秀的村落环境和陶制品的正常生产,在村民之间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制约机制。过去,村民们规定每次烧制陶器,均要留下一定数量的陶器成品作为修窑的基本费用。现在村民每次烧窑都要向村里提交使用费86 元。每次修窑,村里会公布修窑费用的收支细目。为保护好当地的土地资源环境,自建窑以来,凌准村有着明确的规定,陶工们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内取土。20 世纪60 年代后,村里更是制定了禁止伐树烧窑的规定,明确提出只能种树不准砍树,对违背祖训、民规者要严厉处罚。因此,纵使是在陶制品市场最为兴盛的时期,烧窑所需的木柴都是从附近的村子或市场上购买的。每次烧窑之前人们还要进行祭祀,每年的农历九九重阳节都要祭拜造窑先祖。可以说,尊师重训传统在凌准村蔚然成风。直至城镇化、工业化步伐加速发展的今天,走进凌准村,仍然能够看到一个绿水青山、神清气爽、风景秀丽的村庄景象。不得不说,一个有着悠久制陶工艺传统的村庄却能够保持得如此清静优美,良好的公序良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 语
“文化史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演变发展的,‘传统’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其本身就是一个继续创造的过程,所以,变化、发展是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的基因和动力。”[8]就传统手工艺而言,经过了历代艺人的实践,技术不断发展,而技术的发展则为传统工艺增添了生命活力。靖西的传统制陶技术,由原本的空缺装点到现在的彩釉装饰。在这些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发展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是对传统的创新式保护。因此,在继承传统之精华的同时,做出新的发展,是传统工艺保护与传承以及发展应该遵循的科学模式。要想把传统手工艺传承下去,就要实践好“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理念,要切实以政府为主导,要整合专家学者的智慧,更需要激活当地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主实践,唯有这样,才能使濒临困境的壮族传统制陶手工艺再现生机,才能实现技艺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