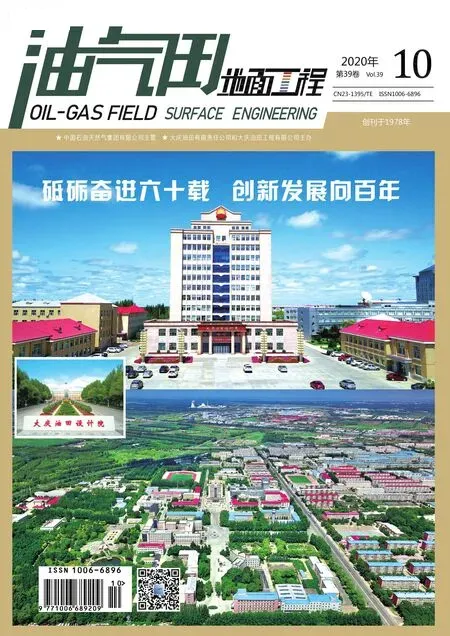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测量与估算研究现状*
孙永彪 张春香 解东来 那媛媛 张鑫
1河北师范大学中燃工学院
2美国环保协会
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是实现从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转变的重要手段。天然气的应用对缓解全球温室效应具有积极的作用[1],甲烷作为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比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具有更高的碳效率,释放单位热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标准煤少一半;而甲烷是比二氧化碳更强的温室气体,在100年时间框架内甲烷的增温潜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是二氧化碳的28~34倍,将时间框架缩短为20年则为二氧化碳的84倍,若甲烷排放到大气中将会降低天然气应用在温室效应方面的积极作用[2]。201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EPA)估算天然气系统的甲烷排放量约占人为甲烷排放总量的25%[3]。在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时,甲烷排放率需低于3.2%才能产生直接气候效益[4]。可见,天然气系统的甲烷排放率是评价天然气应用是否合理的关键指标。
影响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测量与估算的因素众多,致使甲烷排放率估算的准确性备受质疑,主要原因有5个:①天然气从气田引出要经过生产、处理、运输、存储和分配等环节到达终端用户,系统结构复杂、设备繁多、管线长且分布广;②甲烷排放伴随系统运行的整个过程,其中逃逸排放(Fugitive Emission)是指系统运行过程中由阀门、连接、压缩机和天然气发动机、汽轮机未燃烧的尾气及输配管线的泄漏所引起的排放,而放散排放是由管线、气井及设备的例行维护、系统扰动(如超压事故、泄压系统)造成的[3];③天然气系统处于开放的环境中,受其他排放源的干扰及气象条件的影响较大;④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测量技术有待提高,而且采用不同测量方法测量同一排放源所得结果存在差异;⑤甲烷排放自底向上(Bottom-up)估算法与自顶向下(Top-down)估算法存在系统性差异而且原因尚不明确。因此,有必要对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的测量与估算进行研究。
本文着重梳理了美国天然气输送存储系统、分配系统的甲烷排放测量与估算的研究,对比各种甲烷测量技术的应用情况和自底向上估算法及自顶向下估算法,探讨了测量与估算方法的特点并分析了造成估算结果系统差异性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甲烷排放的研究现状以期针对我国天然气系统的研究提出参考建议,加快我国在天然气甲烷排放方面的研究。在天然气生产甲烷排放方面,薛明等已对甲烷排放的测量估算及相关政策法规进行了着重的介绍[5],本文只做相关补充,不再详细展开。
1 美国甲烷排放量的估算
甲烷排放的估算方法分为自底向上法和自顶向下法。两种估算方法存在系统差异[6-7],对同一地区天然气系统进行估算时,自顶向下估算量一般大于自底向上,甲烷排放估算存在机理性和测量方面的难题。
1.1 自底向上估算法
20世纪90年代,为了对甲烷排放进行估算,美国气体研究院(Gas Research Institute,GRI)与环境保护署共同做了一项研究,后称GRI/EPA研究[8]。该项研究首先确定甲烷排放源,即将天然气系统的组件或环节进行分类,经试验测定排放源的甲烷排放因子[8](Emission Factor,EF);然后通过统计法对每类排放源整体进行估计,即得到排放源的活动因子(Activity Factor,AF);最后以二者的乘积EF×AF表示每类排放源全年甲烷排放量,不同类排放源的排放量累加得到年度天然气甲烷排放量[3]。甲烷排放自底向上估算法就是确定排放源的排放因子和活动因子,然后采用插值计算法对设施级、地区级甚至国家级的甲烷排放量进行估算。基于GRI/EPA研究的排放因子,EPA统计各排放源的活动因子,采用自底向上法估算甲烷排放量,两年发布一次温室气体清单(Greenhouse Gas Inventory,GHGI),该清单为现今最全的甲烷排放自底向上法的估算结果。
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天然气系统产生了很多变化,例如分配系统大量设备更新换代,管道材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9];气田生产大多数采用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等先进技术[10]。这些改变都会对排放因子产生较大影响,导致GHGI的准确性受到挑战。为了更好地了解天然气系统的现状,2011年EPA实施了温室气体报告强制规定(Greenhouse Gas Report Program,GHGRP),要求相关企业采用测量与排放因子相结合的方法估算设施级甲烷排放量,并上报年排放量在25 000 t以上的设施。GHGRP虽然为排放估算提供了大量的现场数据,但由于忽略设备、工艺环节的差异性,采用过时的平均排放因子其完整性受到很大的质疑。可见,排放因子直接影响着自底向上法甲烷排放量估算的准确性。
现在普遍采用现场直接测量法,利用声发射探测技术与高速流抽样技术[11]直接测量更新的新型组件或先进工艺环节的排放因子,然后采用插值法对甲烷排放量进行自底向上的估算,不仅可以提高估算的准确性,而且还可以通过与GHGI、GHGRP的上报量[9-10,12-15]进行比较,确定甲烷减排的有效措施。
生产环节采用新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都会对天然气生产的甲烷排放产生影响。ALLEN等采用现场直接测量和自底向上估算法,重点研究了完井返排、液体卸载、修井作业等生产环节,发现甲烷排放估算量低于GHGI[10];而进一步研究发现气井类型影响液体卸载的甲烷排放,其中带塞举升气井为主要排放源,其估算量与GHGI及GHGRP的上报量基本一致[12]。在设备更新方面,ALLEN等对气动装置(泵、阀门)进行研究,发现排放因子不低于GHGI,而气动阀门平均排放估算量比GHGI高17%且受到应用场合的影响,例如分离器、压缩机的气动阀门排放率高于其他设备;而且单位气井阀门数量为2.7个高于GHGI的1个[13]。液体卸载[12]和气动阀门[13]的排放分布为偏态分布,存在超级排放源,对自底向上法估算甲烷排放造成较大影响。在生产的其他方面,薛明[5]等对现有文献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可见,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有利于甲烷减排,而应用场合对设备的甲烷逃逸排放有一定的影响。
天然气长距离输送系统的主要排放源为压缩机及其附属设备、压气站和高压管线。在天然气长距离输送方面,ZIMMERLE等在扩大样本数量的情况下,使用2 292个现场测量数据、677个设施的额外排放数据和922个设施的活动数据,采用自底向上法对输送-存储系统进行了甲烷排放估算,发现压缩机相关设备为最大排放源,并发现超级排放源,甲烷排放估算量与GHGI置信区间重叠,比GHGRP的上报量高1.6倍[14]。SUBRAMINIAN等采用现场直接测量法和示踪剂释放技术测量了全美45个压气站(其中25个在GHGRP范围以内),利用逃逸、放散排放源的测量数据结合其排放因子,对压气站的排放量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①设备甲烷排放分布呈偏态,并发现了2个超级排放源;②在考虑超级排放源的情况下,平均排放因子大于GHGI,如不考虑则小于GHGI;③GHGRP的上报量受设施位置、运行状态的影响,因此在利用上报数据更新排放因子时需修正[15]。ZIMMERLE等采用现场测量法首次对96 km集输管线、56个清管器及39个截止阀进行了测量,发现近期更新的排放因子仍然低估了集输管线的甲烷排放[16]。可见,甲烷排放分布,超级排放源的存在和样本容量及其代表性对设施级、设备级自底向上法甲烷排放估算影响较大,而长距离管线输送天然气造成的甲烷排放需要进一步探索。
天然气分配系统的主要排放源为调节计量装置和管线。LAMB等人采用分层抽样法对230处埋地管线泄漏点、229个调节计量装置进行了现场测量并更新了排放因子,分配系统甲烷排放估算量比GHGI小36%~70%[9]。可见,设备管线更新有利于甲烷减排。但是目前为止,采用自底向上法估算分配系统甲烷排放量的研究相对较少,现场测量及统计数据的匮乏限制了设备管线更新、地理位置及季节对甲烷排放影响的研究。
采用自底向上法估算甲烷排放量可以对特定排放源的排放因子进行研究,但其估算的准确性严重依赖于测量样本的容量和排放源的排放分布。天然气系统设备多、覆盖范围广,很难对全部排放源进行识别和测量[17]。如果排放分布为正态分布,那么很容易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然而许多排放源的排放呈偏态分布[9,12,13,15]并且还存在超级排放源[12-14],这严重影响了自底向上甲烷排放估算的准确性。如果再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对多个地区同一时刻进行全天候测量,自底向上法的局限性将更大。
1.2 自顶向下估算法
甲烷排放自顶向下估算法是通过测量有界区域的甲烷浓度来量化该区域的甲烷排放量,按原理可分为质量平衡和传感器测量两种:质量平衡是利用飞行器测量某有界区域上、下风向断面的甲烷浓度来估算该区域的排放量;传感器测量通常采用气象传输模拟与固定传感器网络相结合或对流扩散模型与逆模型耦合来估算区域的甲烷排放量[11]。而根据测量区域的不同又可分为设施级、地区(盆地)级、大陆级和全球级的甲烷排放量估算,不同级别的测量与估算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1.2.1 设施级甲烷排放的测量与估算
设施级甲烷排放量自底向上法估算常采用现场直接测量法,而自顶向下法估算通常采用OTM33A测量方法(The EPA's Other Test Method 33A)和示踪剂释放技术。采用三种测量方法对同一设施的甲烷排放量进行估算,结果表明OTM33A测量法的精确度不如现场直接测量和示踪剂释放技术[17]。OTM33A测量法为一种反高斯方法,即在甲烷排放源下风侧20~200 m范围测量甲烷浓度和风况,依据经验确定高斯羽流扩散参数进而得到甲烷质量通量[18]。OTM33A应用的局限性为测量地必须有足够的顺风条件。而使用示踪剂释放技术进行测量时,需在设施内的1个(2个)地方以特定的速率释放1种(2种)示踪气体,用顺风羽流中目标分析物(甲烷)的混合比与示踪气体的混合比来估算甲烷排放量[17]。示踪剂释放法假设目标分析物(甲烷)与示踪气体共同分散到大气中,为使二者扩散均匀对测量时间要求较高,其应用局限性不仅要求测量地有足够的顺风条件以便取样,而且需要得到释放示踪气体的许可。
这两种方法多用于气井、矿井集输系统及处理厂等设施级甲烷排放的测量,在长距离输送系统[15]及分配系统中的应用较少。ROBERTSON等采用OTM33A法对气井甲烷排放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湿气盆地气井的甲烷排放量与产量呈负相关,而且高于干气盆地气井[19]。YACOVITCH等采用双示踪剂释放技术测量了2个天然气生产地区气井的小时排放量[20]。MITCHELL等采用双示踪剂释放技术对矿井集输设施和处理厂的甲烷排放量进行了测量估算,结果显示集气设施排放分布呈较为明显的偏态分布,液态储罐放散排放占整个集输设施的20%[21]。随后,MARCHESE等利用以上测量数据[21]结合设施数量,通过蒙特-卡罗模拟对全美天然气矿井集输系统和处理厂的甲烷排放量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矿井集输系统和处理厂以放散排放为主[22]。
1.2.2 地区级甲烷排放的测量与估算
地区级甲烷排放自顶向下法估算,针对不同的目标可采用机载测量、车载测量和地面固定监测网测量。
天然气生产地区甲烷排放自顶向下估算一般采用飞行器测量有界区域的顺、逆侧甲烷浓度,计算浓度差后乘以空气流动速率,得到区域甲烷排放总量。确定甲烷排放源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为遵循质量守恒,用总量减去GHGI非天然气系统排放源的排放量;另一种为应用碳同位素标记法或逆算模型确定天然气系统排放占比,进而估算地区天然气系统的甲烷排放量[23]。天然气生产地区甲烷排放的测量估算,已从对单一地区的研究转变为对不同地区[24]、不同季节[25]的研究,在排放偏态分布[26]及超级排放源[27]等问题上也做了相应研究,并与GHGI和GHGRP的上报量进行比较[28],发现化石源为天然气生产地区主要甲烷排放源[29-30],天然气系统的逃逸排放造成了自顶向下法估算与GHGI之间的差异[31]。
在城区甲烷排放测量估算方面,可搭建地面固定监测网进行连续测量,然而测量数据的解读高度依赖于大气模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11]。MCKAIN等使用全面的大气测量和建模框架,测量了波士顿地区平均甲烷排放通量,结合乙烷-甲烷比确定了天然气甲烷排放的占比,对波士顿城区的天然气年甲烷排放量进行了估算[32]。
而在分配系统方面,多采用移动车辆对管线进行大气测量。车载测量可以测出行车轨迹上的甲烷浓度,通过碳同位素标记法以区分生物甲烷源(如垃圾填埋场、湿地、下水道)和热甲烷源(如天然气),并确定甲烷排放源的占比,然后估算出分配系统的甲烷排放。在波士顿,PHILLIPS等采用车载测量法绘制了785 mile街道中心管线的甲烷排放地图,观察到街道水平甲烷浓度较高,并将其归因于3 000多处陈旧的天然气管线泄漏,通过碳同位素标记法确定天然气排放源的占比,对分配系统管线甲烷排放进行了估算[33]。在华盛顿,JACKSON等人同样采用车载测量法绘制了1 500 mile街道中心管线和5 893个泄漏点的地图,区分了甲烷排放源,最后估算出管道的甲烷排放量,并测定出潜在爆炸性浓度[34]。管线更新及修复有利于甲烷减排,美国三个城市开展了铸铁管线的更换项目但进度不同,GALLAPHER等人采用车载测量法绘制了三个城市街道的甲烷排放图,发现管线的泄漏与更换项目的进程有关,在已完成更换项目城市的单位长度管线甲烷排放量比没有完成的城市少90%[35]。
1.2.3 大陆级及全球级甲烷排放的测量与估算
大陆级及全球级甲烷排放自顶向下法估算常采用卫星观测法测量大范围空间的甲烷浓度,比地面监测网络测量范围更广,而且突破了飞行器测量的时间限制。虽然卫星观测能进行持续观测,但数据精度较低。大气中的甲烷能够被短波红外(Shortwave Infrared,SWIR)太阳后散射仪和热红外(Thermal Infrared,TIR)地球辐射热发射仪检测到;用于大气制图的扫描成像吸收光谱仪(Scanning Imaging Absorption Spectrometer for Atmospheric Chartography,SCIAMACHY)和温室气体观测卫星(Greenhouse Gases Observing Satellite,GOSAT)可以提供SWIR反演数据;而TIR反演数据可以从大气红外测深仪、对流层发射光谱仪及大气红外测深干涉仪得到[36]。一般来说,SWIR能提供大气柱的总甲烷浓度;而TIR能提供垂直剖面的甲烷浓度,但由于缺少热对比,TIR对对流层底层的灵敏度较低,这限制了其对区域源的探测应用价值[36]。
在卫星灵敏度足够高、覆盖范围足够广的条件下,空间分辨率的提高是大陆级及全球级甲烷排放测量估算的关键。WECHT等利用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化学输运模型(Goddard Earth Observing System Chemistry (GEOS-Chem)chemical transport model)及其伴随物,通过反演SCIAMACHY观测数据,对北美地区甲烷排放进行了估算[37],并结合机载测量将该地区甲烷排放的水平分辨率优化到1/2°×2/3°[36]。TURNER等利用2009—2011年GOSAT观测数据,基于同样的原理对全球和北美的甲烷排放进行了估算,空间分辨率分别可以达到4°×5°和50 km×50 km[38]。JACOB等结合表面观测、机载观测数据,通过全球级到点源级的逆算分析,将卫星观测成功应用到超级排放源的探测上[39]。
机载测量法多用于油气生产地区,发展较快且技术较为成熟[5];对城区内天然气分配系统、城区内各场站等的研究多采用车载测量,但相对较少;长距离输送系统具有管线距离长分布广、设施间距较大等特点,利用地面监测网络进行研究难度较大;卫星观测法虽然能解决空间和时间上的难题,但空间分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可见,不同甲烷排放自顶向下测量方法存在不同的问题,表明对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的理解和估算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3 甲烷排放估算结果差异性分析
在确定天然气甲烷排放源的占比条件下,通过自顶向下法估算与自底向上法估算的对比,可以确定温室气体清单中缺少的排放源,提高GHGI的排放源的完整性和估算的准确性。而大量基于自顶向下法的甲烷排放研究均显示,温室气体清单估算一直低估了天然气系统的甲烷排放量[6-7]。两种方法系统的差异性大大困扰着天然气应用过程中对气候影响的正确评估和能源政策的决策。
造成这种系统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抽样样本容量及代表性、组件环节排放的偏态分布[9,12,13,15]、超级排放源[12-14,27,39]的存在都会对自底向上法估算产生较大影响,导致系统差异性较大。ALLEN分析了造成系统差异性的原因并建议对超级排放源[40]进行检测;ZAVALA-ARAIZA等分析出异常工况可能导致超级排放源的产生[41];SCHWIETZKE等采用机载测量法对页岩气生产地区的甲烷排放进行空间解析,发现间歇性排放源影响较大[42];VAUGHN等对某天然气生产地进行了多尺度测量并获得详细活动数据,通过自顶向下法估算与自底向上法估算的时空对比,发现人工液体卸载的间歇性排放是造成排放时间差异的原因[43];ZAVALA-ARAIZA等采用重复测量的方法以提高自顶向下法估算的确定性,并整合完备的设施数目进行自底向上法估算,通过比较发现巴奈特地区甲烷排放估算量大约是GHGI的2倍[44]。
在设施级的甲烷排放估算中,测量方法也会对甲烷排放的估算结果造成影响。BELL等人测量了某地区268处设施,其中261处采用现场测量法,17处采用双示踪剂通量比法,50处采用OTM33A测量法。比较甲烷排放估算结果,发现基于现场测量的估算结果最低,且与基于现场测量的估算法和基于示踪剂释放技术的估算法相比,基于OTM33A测量的估算法精度较低[17]。而VAUGHN等对一天然气集输补给站进行了测量,对现场直接测量法、双示踪剂释放技术和机载测量法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基于现场直接测量法的估算值高于双示踪剂释放技术且低于机载测量法[45]。
2 国内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估算
中国天然气应用起步较晚,但产量增速很快。2018年,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2 803×108m3,同比增长17.5%,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达7.8%,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日最高用气量达10.37×108m3,同比增长20%[46]。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甲烷排放量随着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耗占比的增高而越来越高,但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测量估算还不成熟。现在我国采用《199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一、三层结合法,对天然气甲烷逃逸排放进行估算,但甲烷排放因子基本已经过时。随着新技术(如水力压裂、水平钻井)的成熟和应用,设备的更新换代、管线巡检修复的提升,都会对排放因子带来影响[5]。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的排放因子需要不断更新,以正确反映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的实际状况。
美国在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方面研究较多,但天然气系统之间的差异使中国难以直接借鉴引用美国环境保护署的GHGI。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我国天然气事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每年新增居民、工商业用户超过1 000万户。系统存在大量的调试操作(如天然气置换点火操作),火炬系统不稳定,而美国天然气系统处于平衡发展阶段,新增用户较少,甲烷排放量相对稳定。
(2)中国LNG设施较多且为较大甲烷排放源。我国天然气系统存在大量的LNG汽车加气站、LNG卫星站及LNG调峰储气站等设施,而美国LNG使用较少。目前LNG储罐储存超过4天就会产生BOG(蒸发气体),通过调查10座LNG汽车加气站发现,每座LNG加气站平均日甲烷放散量约为96.2 m3。
(3)中国甲烷减排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甲烷减排监管体系,在联邦层面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告制度(GHGRP),制定重点排放源目录和排放标准,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在州层面加强污染物减排立法[47]。在体系监管下,油气企业需要通过技术或设备升级、改善技术规范及优化操作程序等手段来有效控制甲烷排放。而目前我国对控制甲烷排放的重视不足,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大部分油气企业还未将甲烷减排作为运行目标之一。
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方面,对我国天然气系统甲烷排放的研究很少。薛明等回顾了国内油气生产过程的甲烷逃逸排放的测量研究[5],发现我国对该方面的研究较少,且大多数研究局限于单个组件或环节,如井口套管[48]、采出水[49]、煤层气井口[50]等,对整个系统的全面研究很少[5]。而对于输配系统,甲烷排放检测技术[51]、排放因子更新和自顶向下法估算等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目前我国很有必要开展对本国油气系统甲烷排放的研究。
3 结论
我国天然气的应用起步较晚,其甲烷排放的研究也大都借鉴他国经验[5],在原始测量研究方面成果颇少,但为了解决雾霾等环境问题,近年来天然气作为一次能源在我国能源占比正逐年增高,天然气系统的甲烷排放及造成的温室效应问题亟待解决。结合我国天然气行业现状和国内需求,给出以下建议:
(1)我国是天然气进口大国而非出口大国,建议先采用自底向上法对天然气场站、输送存储系统、分配系统等进行甲烷排放估算并完善温室气体清单。
(2)参考国外排放偏态分布和超级排放源的研究,结合本国天然气系统的实际状况,确定主要排放源。
(3)在排放源详细分类的基础上,采用现场直接测量技术对各类排放源尤其主要排放源的排放因子进行更新,完善温室气体清单。
(4)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开展机载测量和卫星观测,以实现对天然气系统多维度、全方位的甲烷排放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