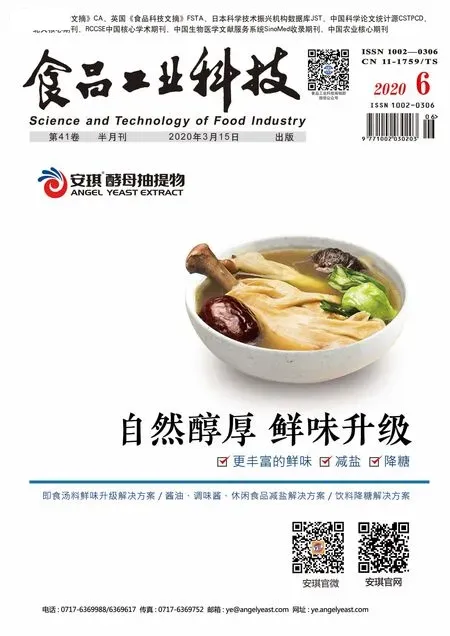微生物代谢产物影响肠道微生态系统的研究进展
,*
(1.辽宁晟启昊天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辽宁沈阳 110000;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亚健康干预技术实验室,湖南长沙 410128;3.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广州东莞 523808;4.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辽宁大连 116000)
人体肠道内动态定植了机体最庞大的微生态系统,肠道微生物菌群与人体健康关系的研究被2013年的“Science”杂志列入十大科学进展,“人类—微生物代谢轴”与机体健康的相关性为人们普遍认同。2007年底美国发起人类微生物组计划(HMP),继而欧盟及中国学者开展人体肠道宏基因组计划(MetaHIT),肠道微生物的相关研究持续增长。
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现今人们通常会服用活体益生菌、益生元等微生态制剂来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1-2],目前国内市场共有31个国产和进口活菌药品,如培菲康、促菌生、丽珠肠乐、妈咪爱等,共涉及枯草杆菌、双歧杆菌、酪酸梭菌等16个菌种。但目前益生菌的安全性及功能性评价体系有待完善,且受宿主肠道菌群定植抗力等因素影响,口服活菌的生物利用度、效果稳定性不容乐观,并有传递耐药基因的风险[3]。相较而言,非活菌体的菌群代谢产物能够耐受胃、小肠环境,直接进入大肠被肠道益生菌利用,具有化学结构明确、剂量参数安全、吸收性分布性良好、易于储藏等优点[4]。有学者提出后生素(postbiotic)概念,将代谢产物用于纠正肠道菌群紊乱[5]。本文将对微生物代谢产物及其与机体的共代谢产物对肠道微生态平衡的影响进行综述。
1 肠道微生态概述
人体与外界相通的腔道内及体表,分布有大量微生物,形成胃肠道、口腔、泌尿和皮肤等微生态系统,其中肠道内约有100 万亿细菌,占机体微生物总量78%,是机体最主要的微生态系统[6]。肠道微生态系统由肠道中的微生物及宿主微环境如组织、细胞、代谢产物等组成。
广义的肠道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与病毒,而通常所指的肠道微生物专指细菌,归属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变形菌门、疣微菌门、梭杆菌门、蓝细菌门以及螺旋体门、VadinBE97菌门[7]。其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属优势菌门,占肠道微生物菌群的98%以上,而变形菌门、放线菌门、梭杆菌门和疣微菌门数量及种类较为弱势。肠道微生物菌群根据其在肠道中的层次可分为腔菌群和膜菌群(或被称作浮游菌群和生物膜菌群);根据其生理功能及与宿主的关系,可分为共生菌、条件致病菌和病原菌;根据其生长环境及对氧的耐受程度,可分为专性厌氧菌、兼性厌氧菌和需氧菌。其中共生菌多为专性厌氧菌,占比99%以上[8]。
肠道微生物菌群与宿主在长期的协同进化下相互适用,达到动态平衡,作为一个独特的微生物器官参与调节宿主的消化吸收、能量代谢、免疫反应等[9]。若在外环境影响下,肠道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肠道菌群结构由生理性组合转变为病理性组合,将使肠道抵御病原体的能力下降,进而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反应、肥胖、糖尿病、炎症性肠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等疾病的发生[10]。
2 肠道微生物代谢活动及代谢产物
肠道菌群可以利用上消化道不被消化吸收的食物残渣、消化道细胞分泌物及死亡脱落的上皮细胞等作为代谢底物,进行代谢及生物合成[11]。肠道菌群代谢活动能够影响宿主的整体生理代谢特性,菌群与宿主之间存在活跃的代谢交换及“共代谢”过程[12]。遗传背景、年龄、饮食结构、底物滞留时间等能够影响肠道菌群代谢活动,通过不同的代谢途径产生不同的微生物代谢产物[13]。其中,遗传因素对宿主的饮食偏好、肠道结构功能起决定作用,而饮食结构能够快速改变肠道菌群结构组成及肠道代谢活动,从而影响代谢产物的产生。例如地中海饮食模式低脂肪、高膳食纤维,则其模式人群肠道菌群丰度高、SCFAs含量高;典型西方饮食模式高脂肪、高糖低纤维,则其模式人群肠道中拟杆菌门、双歧杆菌数量少,厚壁菌门数量增多,梭杆菌等潜在致病菌数量增多,SCFAs含量减少[14-15]。
2.1 碳水化合物代谢产物
碳水化合物发酵是肠道微生物的核心代谢活动,能够促使结肠能量及碳源再利用,发酵底物主要为低聚果糖、木糖醇、膳食纤维等复杂难消化的膳食糖类。经微生物水解,形成单糖、寡糖、乳酸、乙醇、有机酸等中间代谢产物,并最终形成代谢终产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16]。SCFA是由1~6个碳原子构成的有机羧酸,包括甲酸、乙酸、丙酸、丁酸、异丁酸、戊酸、异戊酸、己酸及异己酸等,其中,乙酸、丙酸、丁酸占肠道总SCFAs 95%以上,浓度比例3∶1∶1。健康人体每日可产生约50~100 mmol SCFAs[17]。
2.2 蛋白质、肽、氨基酸的代谢产物
结肠中的糖类发酵大多发生在结肠近端,随食糜移动至结肠末端时糖类耗尽,肠道微生物酵解蛋白质、氨基酸等底物代谢获得SCFAs[18];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等支链氨基酸脱氨基生成异丁酸、异戊酸、2-甲基丁酸等支链脂肪酸及氨;苯丙氨酸、酪氨酸、色氨酸等芳香族氨基酸代谢产生酚类、吲哚类化合物;蛋氨酸、胱氨酸等含硫氨基酸在硫酸盐还原菌作用下生成硫化氢[19];肽和氨基酸在拟杆菌属、梭菌属、双歧杆菌属、肠杆菌属、乳酸杆菌属和链球菌属细菌的作用下脱羧基生成组胺、酪胺、色胺、尸胺、腐胺、亚精胺、精胺等生物胺类物质[20];另外,在蛋白质不足的情况下,肠道菌群还可以利用氮源合成5-羟色胺及赖氨酸、苯丙氨酸、酪氨酸、色氨酸等人体必需氨基酸并补偿机体需求。
2.3 膳食脂肪代谢产物
肠道菌群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机体能量及脂肪代谢。膳食脂肪的来源有动物脂肪、植物脂肪、微生物脂肪及结构脂质,不同的膳食脂肪结构组成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及数量,产生不同的代谢产物,进而影响宿主的代谢及健康。部分膳食脂肪的代谢终产物为SCFAs;卵磷脂、膳食肉碱、磷脂酰胆碱等经肠道菌群酶解产生高水平三甲胺,经肝肠循环后氧化生成三甲胺-N-氧化物[21];胆固醇在肠道微生物的氧化作用下生成胆固烯酮,进而降解为类固醇及胆固烷醇;在胆汁酸的肝肠循环中,肠道厌氧微生物能够通过解偶联、脱氢、差向异构化、脱羟基反应将少量初级游离型胆汁酸分解代谢为次级胆汁酸[22],胆汁酸的微生物转化是宿主-菌群互相作用及共代谢的典型代表。
2.4 维生素及微量元素
人体肠道微生物能够合成维生素C、K、生物素、烟酸、叶酸及B族维生素等多种维生素,补充机体维生素、维持机体维生素稳定。双歧杆菌属及乳酸杆菌属能够利用人肠道提供的 6-羟甲基-7,8-蝶呤焦磷酸(DHPPP)和对氨基苯甲酸(PABA)底物合成叶酸[23];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和沙门菌等可以合成维生素B2[24];某些肠道专性厌氧菌如拟杆菌属、真细菌属、丙酸菌属和蛛网菌属是合成维生素 K2的主要菌群[25]。另外,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生的有机酸能够络合钙、铁、镁等微量元素,部分代谢产物对微量元素的代谢路径具有调控作用,进而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率[26]。
2.5 药物分子转化代谢产物
肠道微生物对药物分子的转化代谢能够影响药物的毒性、有效性、生物利用率。首先,肠道微生物能够直接参与口服药物分子的水解及氧化还原,转化为相应的药理或毒理成分而发挥作用,研究表明,京尼平苷必须经肠内菌群分泌的β-葡萄糖苷酶水解成京尼平才能被吸收,从而发挥促进胆汁分泌的药效[27],雌马酚作为大豆异黄酮的次级代谢产物,其生物学活性较其原型大豆异黄酮普遍提升;其次,肠道菌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调节宿主的代谢酶和转运体的表达,从而导致代谢和转运药物的能力发生变化,间接影响药物代谢[28];再次,肠道菌群代谢物如丁酸、胆汁酸可以作为核受体配体,介导药物代谢[29]。
2.6 其他代谢产物
微生物在生长代谢过程中能够分泌胞外多糖(EPS),保护肠道益生菌抵御营养缺乏、脱水、噬菌体、有毒物质、渗透压和拮抗物等不利条件,在其黏附定植、阳离子封存、生物膜形成、细胞识别等方面起重要作用。EPS是一种高分子量长链多糖聚合物,由醛糖或酮糖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依据其与菌体的依附关系,可分为粘液多糖和荚膜多糖[30]。目前国内外产EPS的乳酸菌主要集中在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属、球菌属、链球菌属及明串珠菌属[31]。
细菌核糖体能够合成一类对同种及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具有抑制活性的活性多肽或前体多肽,称作细菌抗菌肽或细菌素,它具有选择性毒性,产生菌对细菌素具有自身免疫性[32]。目前已发现的细菌素被归为四类:羊毛硫胺类细菌素,通常具有耐热特性,如nisin;非羊毛硫胺类细菌素,通常对李斯特菌具有特异抗性,热稳定性良好,如戊糖片球菌素;热稳定性较差的细菌素,分子量>30 kDa,如乳酸菌细菌素lactacin B;由磷脂、脂肪酸链等特定基团与蛋白基团共同构成的细菌素,如肠膜明串珠菌产细菌素leuconocin S[33-35]。
肠道微生物还能够产生许多免疫原性内毒素,如脂多糖,能够诱发宿主的炎症反应。脂多糖是革兰氏阴性菌外膜的主要脂质成分,由Lipid A、核心寡糖、O抗原链构成,具有构成细菌阻渗层、药物耐受性及作为免疫信号因子的作用,在细胞壁裂解后作为内毒素释放出来,在炎症反应中起激活剂作用[36]。
3 微生物代谢产物对肠道微生态平衡的调节作用
肠道菌群能够通过其自身代谢产物的分泌产生,影响肠道菌群结构及肠道内环境,从而影响肠道的微生态平衡。
3.1 短链脂肪酸(SCFAs)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
SCFAs是肠道微生物代谢的主要产物之一,能够参与多组代谢反应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及机体健康,其作用机制如下:
a.供能,尤其是丁酸能够直接为肠道上皮细胞吸收,通过β氧化促进细胞增殖并减少凋亡,维持肠黏膜机械屏障;b.分子结构具有广谱抗菌功效,水解降低肠道pH,维护肠道黏膜化学屏障,降低肠道氧化还原电位,提供厌氧环境,利于双歧杆菌、乳杆菌等益生菌的定植生长并抑制病原菌定植生长;c.游离SCFAs能够作为信号分子调节宿主的能量摄入和利用,调控肠道及机体免疫反应,参与肠道电阻及电解质调节进而影响肠道通透性;d.SCFAs作为调控因子,在消化道、代谢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37-39]。
3.2 乳酸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
乳酸是乳酸菌发酵终产物之一。它作为有机羧酸能够解离产生H+,干扰致病菌膜蛋白电位,改变内外电势,破坏细胞膜稳定性并导致细胞壁损伤,增加细胞通透性,造成内容物渗出;形成的乳酸盐能够改变微生态环境的水分活度;影响菌群生长环境,降低致病菌生长繁殖速率,延长细胞分裂增殖代时,具有明显的抑菌、杀菌作用,从而影响肠道微生态平衡[40-41]。
3.3 蛋白类代谢产物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
高蛋白饮食会促进肠道有害发酵产物的生成,威胁肠道健康,但适量的蛋白类底物能够为机体反应提供氮源等多种元素,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及机体代谢。硫酸对甲酚、硫酸吲哚酚是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生的肠源性尿毒素,能够使肠道菌群紊乱、肠壁通透性增加,破坏肠道微生态平衡,甚至影响机体代谢,造成心脏、肾脏疾病的发生[42]。高红肉消耗人群粪便中硫化物、氮亚硝基化合物、甲酚的浓度升高,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相关,生理浓度的H2S却有助于维持正常细胞能量代谢[43]。色氨酸代谢产物吲哚乙酸在结肠中的过量聚集,能够导致上皮细胞损伤引发结肠癌,吲哚-3-丙酸却有助于改变抗生素和富含色氨酸饮食导致的体重增加[44]。另外,苯丙酸、尸胺等能够与人G蛋白偶联受体互作,调控免疫应答,影响肠道健康[45]。
3.4 脂质代谢产物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
膳食脂肪是机体主要能量来源,然而肠道脂肪的过度发酵代谢可刺激促炎信号级联反应、诱导细胞氧化凋亡进而破坏肠道屏障及肠道微生态平衡。作为机体与菌群共代谢产物胆汁酸在肝脏-回肠间循环,能够乳化并促进膳食脂质的吸收,作为特异信号分子与胆汁酸受体结合,参与肠道脂质代谢、糖代谢、能量代谢的调控,胆汁酸代谢系统与肠道微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与消化道疾病、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46]。氧化三甲胺能够通过调节胆汁酸代谢进而调控肠道脂质代谢,并作为渗透剂和蛋白质稳定剂,维持机体细胞稳定[47]。
3.5 药物分子转化代谢产物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
肠道菌群对药物分子的代谢转化是药物分子发挥药理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肠道菌群通过产生不同代谢酶,发生水解、脱羧、还原、杂环裂解、芳香化、脱烷基等反应,参与到不同类型的药物代谢转化中,进而影响药物的活性、有效性及毒性。另外,中药能够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来发挥药效作用。中药以多成分、多途径、多系统、多靶点参与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进而影响机体健康,如服用四物汤能够调整肠道微生物组成、修复肠粘膜损伤、治疗肠道菌群紊乱造成的脾虚气弱症状[48]。
3.6 胞外多糖(EPS)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
微生物胞外多糖具有抑菌、营养、抗氧化、抗肿瘤、免疫调节等多种生物学特性,对于肠道微生态平衡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EPS可以提高菌株对肠道表面的非特异性粘附能力,并通过空间排阻降低致病菌的粘附作用,如双歧杆菌EPS对肠球菌、肠杆菌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49-50]。乳酸菌EPS具有益生元特性,选择性被益生菌发酵为肠道菌群提供营养,促进潜在益生菌的生长与增殖,调节肠道菌群多样性[51]。另外,乳酸菌EPS能够通过非特异免疫及特异免疫反应激活免疫细胞、淋巴细胞调节肠道免疫[52]。
3.7 细菌素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
细菌素主要通过抑制病原菌、病毒的生长繁殖来维护肠道微生态平衡。一类为膜破坏模式,通过静电作用于目标菌细胞壁及被膜,增加通透性,使细胞破裂内容物外泄;另一类细菌素穿过目标菌细胞膜靶向作用于特异性酶或DNA,使酶失活或抑制蛋白质、氨基酸的合成,影响核酸的合成及修复[53]。研究发现,Blautia producta BPSCSK菌株的代谢产物羊毛硫抗生素能够抑制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定植,帮助菌群紊乱患者重建对VRE的抗性[54]。
4 应用
微生物代谢产物对人体肠道微生态平衡乃至个体健康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与作用。如今,国内外关于肠道菌群的代谢研究日趋增长,微生物发酵工程蓬勃发展,探索微生物代谢产物的应用转化恰逢良机。目前微生物代谢产物的应用发展主要分为三大类:
a. 深入研究微生物代谢产物于机体内的代谢及作用机制,将肠道微生物作为治疗靶点,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结构组成及丰度、控制功效性代谢产物的靶向递送及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于各类疾病的预防干预治疗过程中。
研究发现,SCFAs及其盐可以预防高脂引起的小鼠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在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的干预治疗中发挥作用[55]。冯文林等[56]提出通过中医药调整SCFAs代谢进而影响5-羟色胺信号系统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治疗思路。丁酸盐能够抑制肠道炎症,目前已应用于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中[57]。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丁酸盐具有抑制受体表达、预防癌变的功能,目前已被用于一些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58]。某些特异微生物如植物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的胞外多糖具有抗肿瘤、抗氧化等应用[59]。氧化三甲胺通过调控机体脂质代谢,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与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有极大关系[60]。诸多研究证实,黄酮、生物碱、蒽醌、单萜、皂苷等中药化学成分的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具备药效及生物活性,如大豆异黄酮的代谢产物S-雌马酚、红豆杉属内生真菌(Taxomycesandreanae)的次生代谢产物紫杉醇[61],结合肠道微生物代谢反应研究中药的代谢途径及作用机制是当下中药开发利用的新切入点。
b. 将其应用于食品工业及生物工业发酵工程,不断开发微生物资源新型食品及食品添加剂。
乳酸链球菌素(Nisin)是一种新型、高效、安全的天然食品防腐剂,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及酸稳定性、水溶性及高效广谱抑菌活性,广泛应用于食品领域[62],至今已被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使用,我国于1990年将其列入GB2760增补品种,目前已广泛适用于乳及乳制品、预制肉制品、饮料等19类食品防腐保藏中。Γ-氨基丁酸是乳酸菌发酵的次级代谢产物,是一种小分子非蛋白质功能性氨基酸,具有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缓解低血压等功效[63],目前已有富集、强化Γ-氨基丁酸的辣木叶、岩茶、米酒、米糠、糙米发酵饮料产品问世。乳酸于食品工业可用作防腐剂、酸度调节剂,通过细胞循环发酵及同步糖化发酵提升乳酸生产率是微生物发酵生产乳酸的最新研究热点。
c. 某些微生物代谢产物如透明质酸、半乳糖醛酸、花青素、儿茶素等因具有良好的生物亲和性、亲水性、抗氧化性能、抗炎症性能[64],在化妆品、医疗美容领域具有极好的研发前景及应用价值。
5 展望
目前,国内外关于肠道菌群的代谢研究日趋增长,相关研究涉及宏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方向,汇集各类基础领域及临床、应用领域,使生物、医药、食品、畜牧、基因组等学科在此交汇,工程菌、粪菌移植等热点技术的应用侧面验证了微生物代谢活动对肠道、机体健康的重要影响。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进步,针对肠道微生态系统的量化评估正逐步实现,营养、代谢等研究向精准化、个体化方向发展,甚至有望颠覆传统医疗模式,更好的应对目前因生活节奏、运动习惯、饮食结构、环境等因素影响导致的国民健康素质堪忧的现状。
综上,深入研究肠道微生态作用机制,阐明微生物代谢产物对肠道微生态及机体健康的影响,不断开发安全的新型功能性食品及诊疗手段,提升国民健康素质,促进健康产业成为经济转型新引擎,是当下微生物代谢产物未来研究和发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