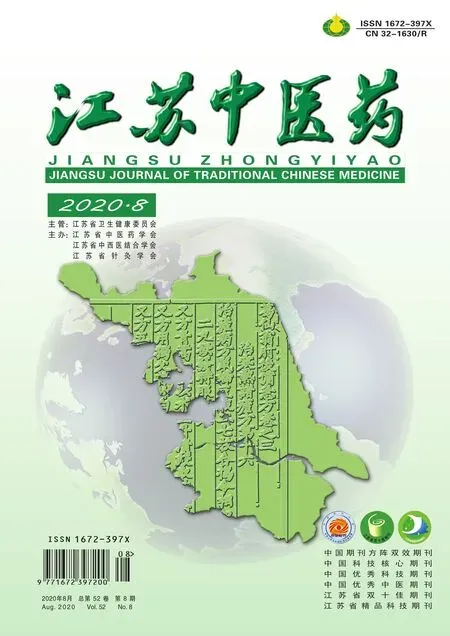从湿热论治慢性肾炎蛋白尿体会
叶可平 谭晓宁 于大君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100091)
蛋白尿是慢性肾炎发病过程中常见的临床表现,尿蛋白量的多少直接影响肾脏病的预后,与肾脏结局的风险呈线性相关[1],因此尿蛋白含量是肾脏病临床预后的重要指标[2]。长期以来中医认为蛋白尿的产生是因脾肾亏虚,精微外泄[3],常从虚论治[4],虽取得一定疗效,但对病情日久、迁延不愈的患者疗效仍欠佳。近年来研究发现,湿热、热毒、瘀血等是慢性肾炎常见的几种实邪,存在于慢性肾炎的各种类型、各个阶段,其中又以湿热之邪最为常见[5]。因此重视慢性肾炎湿热证的治疗,对降低蛋白尿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现将慢性肾小球肾炎湿热证蛋白尿的诊疗体会介绍如下,以就正于同道。
1 湿热分治,因势利导
慢性肾炎患者出现湿热证十分复杂,既有外感,又有内伤,还有内外合邪及药物等因素,其症状繁杂多变不易诊治。望诊常表现为疲乏少神,面色萎黄或偏黑,部分会出现面部油垢或痤疮;舌象表现为舌质红或暗,舌苔常见黄腻苔。症状多表现为上焦的胸闷、头汗出,中焦的食欲不振、脘腹痞闷,下焦的腰部困重、小便黄赤有热感、大便溏滞不爽。脉象上常见滑脉、濡脉、弦脉,也常两种脉象相兼如滑数脉、弦涩脉等。借鉴三焦辨证及临床诊治经验,根据湿热之邪部位分清主次,遣方用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肾炎湿热证也不例外。上焦湿热证常用轻清之品宣泄湿热,如荷叶、紫苏叶、紫苏梗、佩兰、银花、竹叶,可随证加减。中焦湿热证因体质差异和湿热程度不同,又分为湿重于热、湿热并重与热重于湿三种类型。湿重于热者应温中化湿,以砂仁、蔻仁行气化湿,陈皮、厚朴淡渗利湿,茯苓、薏苡仁少佐黄连泻中焦之热;湿热并重或热重于湿应在化湿基础之上,清热燥湿并施,配黄芩、黄连、栀子等,若湿邪重者,苦寒当少用。下焦湿热根据《湿热病篇》十一条“湿热证,湿流下焦……宜滑石、猪苓、茯苓、泽泻、萆薢、通草等味”,临证以此组方治疗湿热阻滞下焦证以分利湿热。然湿热之邪弥漫,下焦湿热为主者常伴有中上焦证候,如脘腹痞满、胸闷呕恶,常需佐入紫苏叶、荷叶、桔梗等予湿热之邪以出路,源清则流洁。
2 脾肾合治,扶正祛邪
湿热的产生与脾肾关系十分密切,脾虚生湿,湿蕴生热,因虚致实,二者互为因果。正如薛生白《湿热病篇》所云:“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肾者主水,肾气的蒸化及肾中阴阳协调使津液得化、输布全身,反之肾虚则气不化津而成水,水湿内生,真阴不足,相火上僭,湿火相合而成湿热。湿热之邪使肾失封藏,从而出现慢性肾炎,临床常见蛋白尿、血尿、白细胞尿等。据此临证常治脾与补肾,扶正与祛邪并施。治脾之法以藿香、佩兰芳香醒脾,以苍术、白术燥湿健脾。治肾之法以泽泻、黄柏泻水中之热,丹皮、地骨皮滋肾清火,玄参、知母补肾水不足兼以清热。在此基础上,补脾药还可加用太子参、黄芪等,补肾药用六味地黄丸中的三补成分——地黄、山药、山萸肉,补肾固涩药可用莲须、芡实、金樱子、菟丝子等,需根据具体病情酌情配伍。理脾配合健脾、补脾,泄肾配合补肾、涩精,使补中有泄、泄而不过,以恢复脾主升清、肾主封藏的生理功能,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而达到治疗肾病的目的[6]。
3 湿盛阳微,顾护阳气
临床治疗湿热之证常予苦寒之品,其虽对症,然湿伤阳,苦寒亦伤阳。阳气损则气化无力,阳不化阴易使湿邪停聚而更伤其阳,《温热论》也提出:“湿热一去,阳亦衰微。”鉴于此,在治疗慢性肾炎湿热证时常加入少量的扶阳药如巴戟天、附子以助其阳,使阳气得化、湿热易祛。附子之意,一则助脾肾之阳以祛湿气,二则阳为湿困,治以温通。巴戟天一药,叶氏言其之用主要有补阴中之阳、辛温通肾络、益火补脾胃、温肾助纳气、温阳止腰痛五大功效[7],取其能补助元阳而兼散邪之用,温而不燥烈,补而不助邪,正宜湿盛阳微之候。
4 湿热日久,兼顾化瘀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云:“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湿邪重浊黏滞阻遏气机,热易灼伤血络煎熬阴血,湿热合则气机阻滞、血运受阻以致瘀血内生。对于这类慢性肾炎患者,湿热之邪久病入络,临床常见舌质偏暗、舌下络脉曲张、面色晦暗等,常用丹参、丹皮、鬼箭羽等散血化瘀、活血通络,对久治不效的蛋白尿案例可取得不错的疗效。丹参一药是师从全国名老中医翁维良教授所得,翁老认为血瘀证应重视活血化瘀药的应用,而丹参性微寒,如兼有热象,用之更为适宜[8]。通过临床观察发现丹参、丹皮、鬼箭羽等活血化瘀药对于肾脏疾病血瘀证疗效显著。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丹参中丹参酮ⅡA通过纠正内皮功能障碍,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抑制炎症,抑制血小板集聚[9]。鬼箭羽亦有抑制炎性介质释放,抑制变态反应,抗氧化等作用,从而达到改善肾血流量,减少免疫复合物沉积,促进肾小球基底膜修复,降低蛋白尿等功效[10]。
5 验案举隅
杜某,女,67岁。2017年5月18日初诊。
主诉:双下肢间断水肿半年,尿检异常4月余。现病史:患者于2016年底出现双下肢水肿,未予重视。2017年1月检查发现尿蛋白(++),血压轻度升高,当地医院予百令胶囊、黄葵胶囊、氯沙坦片治疗未见明显缓解。5月15日查尿蛋白(+++),24 h尿蛋白定量4.0 g。初诊时症见:双下肢轻度可凹性水肿,困倦疲乏,口苦,纳眠欠佳,腰部困重,小便有泡沫,大便黏滞不爽,每天2次。舌质暗、苔薄黄腻,脉沉滑。临床诊断为慢性肾炎(下焦湿热、肾虚血瘀证),治以清热利湿、补肾化瘀。处方:
泽泻15 g,马鞭草15 g,地龙15 g,菟丝子15 g,沙苑子15 g,金樱子15 g,薏苡仁20 g,白花蛇舌草20 g,穿山龙20 g,鬼箭羽20 g,芡实20 g,杜仲20 g。28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
6月22日二诊:查尿蛋白(+),血白蛋白38.6 g/L,双下肢水肿减轻,口苦不显,疲乏、腰部困重亦觉好转,在上方基础上加陈皮10 g、白果仁10 g。28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
7月20日三诊:查24 h尿蛋白定量1.69 g,患者下肢水肿情况明显减轻,腰部不适、小便有沫、大便溏等症明显改善,在前方基础上加用巴戟天15 g、附子15 g、生黄芪60 g。
守方服用2个月后,查尿蛋白(+),24 h尿蛋白定量0.46 g,血白蛋白42.8 g/L。此后根据患者体质状态,或补脾、或益肾、或清热、或化瘀,常随证配伍黄芪、生地、栀子、菊花、丹皮等。2018年5月22日查尿蛋白(-),24 h尿蛋白定量0.13 g,患者诸症基本治愈,未出现水肿、肾炎等临床表现。2019年随访查尿蛋白(-),24 h尿蛋白定量0.09 g,余无不适。
按:该患者病程不长,以湿热标实为主,兼有肾虚血瘀,曾服用百令胶囊、黄葵胶囊、氯沙坦等药,蛋白尿减轻不明显,后转以中医辨证治疗。初诊时患者尿蛋白量偏高,湿热症状明显,然患者病程不长舌质却偏暗,是明显的血瘀表现,故在常规清热化湿的基础上加马鞭草、穿山龙、鬼箭羽、地龙等活血化瘀通络之品以利降蛋白。此外患者在标实的基础上伴有腰部不适、疲乏等肾虚表现,予芡实、金樱子、沙苑子、菟丝子、杜仲补肾固涩,防止精微外泄。三诊时患者尿中蛋白明显下降,湿热证候已去大半。此时加用巴戟天、附子,一是服用寒凉之药已久,恐伤人体阳气,二是湿热一去,阳亦衰微,用以助其阳,使阳气得化。此医案用三焦辨湿热,以脏腑定虚实,考虑患者湿热证及兼证的证候特点,采用活血化瘀、顾护阳气的治法,使得湿热渐祛、脏腑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