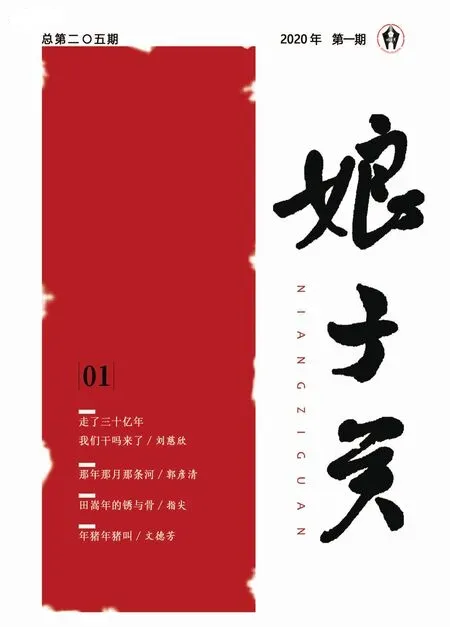年猪年猪叫
文 文德芳
“年猪年猪叫,过年过年到。”
——川南谚语
母亲在电话里说:过年是和腊肉一起来的。
说起腊肉,家乡关于过年的谚语、童谣便穿越时空,萦绕在我的耳畔:“年猪年猪叫,过年过年到”,“……瓢羹舀汤汤,筷子拈嘎嘎(方言,指腊肉)。”雪花飘飞,寒风萧萧,己亥年的冬至已过,远离家乡的山城,冬越来越深了,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而今,刷微信、逛网络,年味儿在掌中的手机里,在拇指间点点刷刷,现代化的列车轰隆隆地飞奔向前,仿佛年味儿的影踪也越跑越远了。而在我内心的一隅,随着家乡的童谣而浮现眼前的人事、年俗、年味儿,依然时翻时新。
那一年,离大年除夕还有十六天,我收到了母亲从家乡快递来的四川腊肉。那段时间,南方多地降温下雪,这些腊肉从万里长江在泸州境内最后一段流域的合江县城出发,经过寒风细雨、漫漫飞雪,翻越巴山黄河,由漫漫铁路,经长长高速路,穿越一城又一城,过了一省又一省,昼夜不歇地转运,到达太行山西麓桃河岸边我居住的这个小城。其间,辗转穿行2000多千米。当这些来自家乡、来自母亲的双手的过年腊肉,实实在在地捧在我手里的时候,忍不住地看了又看,闻了又闻。
在电话里,我从母亲的语气里听出了些许遗憾:城里没有烟熏火燎,虽然是买的土猪肉,也充其量算得上腌肉。不像你爸在世的时候熏制的腊肉打(方言,熏的意思)过柴烟,色泽那么透亮,风味那么醇香。“过年了,只能将就着吃。没有腊肉,哪像过年。”听着电话那端,从遥远的老家传来母亲的声音,我望着眼前棕色纸箱里这些腊肉,它承载着亲情味儿、乡愁味儿、过年味儿、年俗味儿。此时,经年的人生况味中,原本像家乡门前那条大河随波远去的往事,那些与腊肉有关的记忆,都争着抢着叠现在我的眼前。
白浪滔天也冲不走
“红萝卜(方言,指胡萝卜)
蜜蜜(方言读音:min平声)甜,
看到看到要过年,
过年又好耍,
瓢羹舀汤汤,
筷子拈嘎嘎”。
(“嘎嘎”,川南方言,音gaga,去声,一般指的是大人对小孩子说的儿话音,意为腊肉)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过年的童谣,并学唱它,三岁,时间是在腊月初,不是母亲教我唱的,也不是在家里学会的,是和大大(父亲的胞妹)家邻居的孩子一起,在长江合江榕山段的沙坝上玩耍时,与一群大孩子学唱的。
那一年腊月,从大河(方言,指长江)上吹来的风分外刺骨凛冽。
清早,我睁开眼,定了定神,天光已经透过屋顶的亮瓦照进来。“爸爸,爸爸……”我连喊了几声爸爸,应声推门而进的却不是爸爸,是大大(川南方言,音dada平声,前音急,尾音拖音,通常是对父辈姐妹的称呼,有的姐妹多的,依次在大之前加上序号,以示区分,比如三大、五大、八大)。我的大大(dada),是爸爸的八妹,爸爸排行老七。爸爸之上还有一位四哥,我叫伯父,泸州“五老七贤”之一。己亥年过年,我在微信里和伯父聊起家乡的年俗、年味儿的时候,“‘年猪年猪叫,过年过年到’,一直在山西生活,还记得老家的谚语吗?”伯父问我。我回答伯父说:“还能忘得了?在哪里生活也忘不了小时候对过年的盼头,当每年隆冬季节,四周此起彼伏的猪叫声传进耳畔时,就真的要过年了。”伯父还谈起他的母亲,我的奶奶过年做腊肉、香肠时的情景,说奶奶的手多么多么得巧,过年的香肠能做出多少种多少种口味儿,言语里,伯父与其说是对年味的回忆,不如说是对心灵手巧的母亲的怀念。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这些情景,离现在已经有八十年了,我伯父对过年的回忆却还是儿时的这些细节,而不是压岁钱,也不是儿时的玩耍。今年四月,我的伯父在绵阳去世,与他回忆母亲,回忆儿时的这些过年美食,相隔只有两三个月。对于过年的腊肉、香肠,不论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还是如我这样早早远离家乡的人,味蕾的反应都会牵引着我们自然而然地回望过往的岁月、亲情、亲人。
翻寻着我存储的记忆U盘,对过年腊肉的记忆,就是从我的大大家开始的。那个清冷冷的清晨,大大给我穿上棉衣外套,抱我下床。我跑出屋子,在屋外满院子呼喊寻找爸爸。大大从屋里跟出来,“表找了(方言,别的意思),恁爸爸早早坐船回家去了,留你在我这里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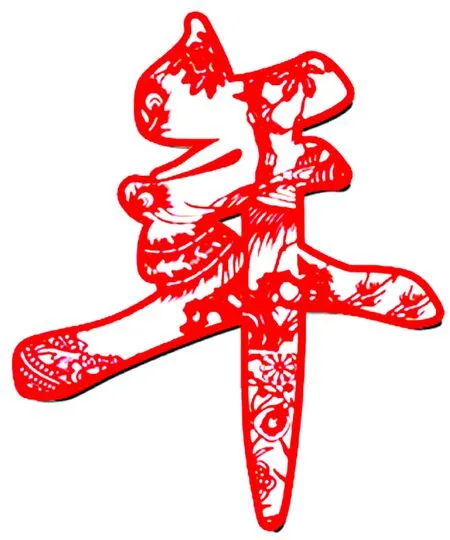
我一听说爸爸回家了,顺着大大家院子边竹林下的青石板路蜿蜒而下,风风火火地往大河边跑。我记得头一天,爸爸背着我乘船而来,下船后就是走的这条路。站在大大家的院子外放眼往南眺望,大河仿佛就从竹林下蜿蜒奔流而去。实际上,需要走一段梯田坎土路,方可到达河岸边。我穿过竹林,顺着河岸边的梯田坎而下,往河边跑。冬天的梯田里,秋收犁耙后灌满了保养的水,水天相映,清波粼粼的。“大女儿,慢点儿,慢点儿,表跑,等哈儿滚水田里了,转来,转来。”大大在她家院子边上一声接一声地喊我。我哭喊着追爸爸而去,大大的呼喊如风吹过,我没有停止往河边奔跑的脚步。眼前大河汤汤、水天相接,岸边是青山连接着的梯田,哪有我爸爸的身影。我也许是真的跑不动了,坐在河边的沙坝上,咧嘴大哭,大大看我没有回转身,便追着我往河边跑,边追边喊,“嚎得跟杀猪似的,表哭了,走,回家吃嘎嘎了。”
大大说,“恁爸爸天没亮就坐船走了,现在快到合江了,追不到了”。我坐在河边,眼里满是一浪接一浪翻滚的河水,浪涛连天。“大女儿,河边冷得很,回家了。”大大说着,拉着我的手就往回走。
穿过一片慈竹林,我又回到了大大的家。大大搬过一张小桌,从碗橱里端出一个粗瓷小碗,碗里盛着已经切成小丁的熟肉,再盛了一碗大米稀饭放在小桌上。“过来,吃饭了。”大大端了一个小板凳放在小桌跟前,招呼我,“表哭了,你看,有嘎嘎,恁爸爸过几天就来背你回家啦。”望着四周一片陌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我,心中满是害怕。我望着碗里的肉,只是哭,没有喝粥,也没有吃肉。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着过年的腊肉。时间才刚刚进入腊月,离过年还有些时日,肉色有些发白,熏得还不到火候。
我哭得没有力气了,大大早已不知甚时出门忙活儿去了,竹林下的四合院里空无一人。我独自坐在院子边上,目光穿过竹林的缝隙远望大河,眺望河上不时飘过的船影。抬眼望竹林里的鸟儿,看鸟儿私语、腮磨、打架。接下来的每一天,我皆是如此度过。
每天只要大大一出门,屋门就落了锁。我进不了屋子,偌大的院子空空如也,便是我的天地。“不要出院门,有背娃娃的,还有豺狼。”我原本就胆儿小,大大出门时再这样恐吓我,我更觉得院子外四处都是血盆大口。我只能独自在院子里发呆,或者坐在檐坎上看鸟儿,每天是竹林中的鸟儿为我壮胆。
大大家的院子边上是一个缓坡,满坡慈竹,一茏连接着一茏,茏茏相连,勾肩搭背、密不透风。竹枝上经常跳跃着各种鸟儿,色彩斑斓地在竹林中飞上飞下。那时候,我除了麻雀,没有叫得上名字的鸟儿。鸟儿们有的成群,有的结对,有的独自徘徊,鸟翼轻盈,鸟羽色彩多样。鸟儿们从这枝跃到那丛,在竹林里,竹枝间弹跃起一个又一个色彩斑斓的弧线,它们的声音或婉转,或短促,或悠长。大大家院子边的竹林繁茂,好似鸟儿们的天堂。那些日子,鸟儿们是我的“玩伴儿”,鸟儿在竹枝上,我在竹根下,看着它们,听着它们,等大大回来,有时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过,只有晴天才能看到鸟儿,雨天的竹林,烟雾蒙蒙、雨水淅沥、寒冷刺骨,是看不到鸟影的。
我在大大家待得时间长了,就和大大邻居家的两个孩子相互熟悉了,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他们是姐弟俩,有时会来找我一起玩儿,他们比我大两三岁,却像主人似的。他们有时带我到后山或竹林下的梯田坎上挖野菜,拔茅草根儿,挑折耳根,我也在那时候认识了折耳根、云英、地丁等野菜,他们还教我生吃过折耳根,咀嚼过茅草根。折耳根(《本草纲目》里又叫鱼腥草),叶子呈心形,叶背淡淡的紫色,放在嘴里,牙齿轻咬,唇齿间会有淡淡的咸腥味儿。茅草根(老家又叫丝茅草根),挖出来细细长长的,用指肚擦去泥土,撕掉柔毛,呈米白色,在嘴里咀嚼,微甜、清香。
有时他们会带我到大河边(大河,指长江。在我的老家合江,长江、赤水、习水,三水交汇于老城的三江嘴,境内山环水绕,人们习惯称长江为大河,赤水、习水为小河)看船看河。清且宽的河面上,一艘一艘的船只来往穿行,“一、二、三……”他们会数着从眼前穿行、往来于川、黔、滇、渝边境的各种船只,还有在水中飘着的竹排,瘦且单的渔舟等,大河上常常传来汽笛鸣叫,一派繁忙而热闹的景象。
大河两岸的山青且绿,冬天也黝黑黝黑的,无论是晴天、雨天,站在大河的高岸上,都可以望见浅绿、深绿到黝黑的色彩。河岸边的沙子细而软,黄灰色的河沙堆积成岸、成坝,顺着大河延伸、蜿蜒,宽阔而望不到边。每次我们到河边,在沙坝里玩耍的孩子都很多,他们多数居住在河岸的高坎上,也有像我这样走亲戚的。孩子们踢毽子、跳格子房、投沙包、跳绳等,这里一群,那边一伙,玩耍的花样层出不穷。有一种玩耍的游戏至今印象清晰,就是丢手帕。孩子们坐在沙坝里,围成一圈,其中一个孩子拿着手帕围着圈外跑,河沙柔软、湿润,在沙坝里跑起来脚步声很小,唱着儿歌欢笑的孩子们,多半察觉不到手帕丢到了自己身后,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跑着圈唱童谣,丢手帕。
“红萝卜,
蜜蜜甜。
看到看到要过年,
过年好耍。
瓢羹舀汤汤,
筷子拈嘎嘎。”
这支传唱过年的童谣,我就是在那样欢快广阔的天地里,在汤汤东流的大河边学唱会的。
带着我挖野菜、看河、看船,学童谣的姐弟俩,是我姑父兄弟家的一双儿女,与大大家隔墙而居,大大让我叫他们哥哥、姐姐,记得我只叫过他们几次,和他们一起下过几次河坝。之后,直到爸爸来接我,我都不敢再和他们一起玩儿。因为他们的谎言,我被大大痛打了一顿,如今忆起,隔着久久的岁月,隔着长长的大河,仿佛还能感受到细竹枝抽在身上的刺痛。
那是一个下午,大大如往常一样出门了,天空阴沉沉的,好像云层里蓄积着积雨,院边的竹林里鸟影无踪,四周一片寂静。我在竹林下的院子外坐着,仰头望竹林,林子里依然看不到鸟儿,再透过竹林的缝隙望河上的天空,灰暗灰暗的,望着望着,我心生恐惧,从院子回到房檐下的门垛上坐了下来,坐着坐着便进入了梦乡。
梦里,爸爸从河岸边的路上来了,我高兴地跑出竹林,边喊着爸爸,边伸出双臂向爸爸跑去,突然“轰隆”一声,我扑了个空,惊醒了。大大家的房后,继续轰隆隆地炸响,接着,院坝里、竹林里落着石块、石子,无数的石块、石子从天而降,我吓得缩着身子坐在门垛上不敢行动。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大大家房后的山上放炮开山造田,开山挖堰塘,幸亏我当时没有在院子外。否则,那些碎石任随一块落到我身上,后果都不堪设想。
随着一波又一波轰隆隆的巨响,石块一波一波地飞到院子里、竹林里,我心里的恐惧一波一波地袭来。此时,邻居姐姐、哥哥从走檐坎上来了。“放炮了,不敢去院子里,要躲石头”,他们告诫我。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在走檐里玩耍起来,飞沙走石被隔在了走檐外,有他们壮胆,我的恐惧也慢慢淡去。他们看到大大家的母鸡在走檐一角带着一窝小鹅,这些小鹅孵出来只有几天,黄绒绒的毛,圆润润的脑袋,杏眼黄嘴,娇憨可爱。姐姐看见小鹅,从母鸡的翅膀下抓一只在手里,抚摸了又抚摸,哥哥见状,一把从姐姐手里抢过那只小鹅,好半天不松手,待他再把小鹅放地下时,小鹅不动了,在地下一直趴着。哥哥干脆把小鹅抓起来,扔到院坝边的一个污水坑里。
傍晚,大大回来了,清点回窝的小鹅,“怎么差了一只?”大大四下寻找,从污水坑里捞起小鹅,它杏眼闭着,两只黄黄的小掌长长地伸着。大大便问他们,是谁将小鹅扔到污水坑的?哥哥、姐姐朝我一扬下巴,没有吱声。我大大眼睛瞪得圆圆的,瞪了他们几秒钟,目光转移到走檐角落里的柴堆上,大大从柴堆里随手抽出一根竹枝梢,两三下掠去竹叶,竹梢上剩下细细长长的竹枝条。随即,竹枝条抽到了我的手上、腿上、脚上,顿时火辣辣地、钻心地痛。我跳着双脚,双手使劲往身后藏着。大大连抽带骂,“……叫你耍鹅儿,看你还敢耍我的鹅儿不了?叫你伙到别个娃儿捣乱?”之后,我的手背上,小腿上,是一道道密密的,纵横交错的红色印子,生疼生疼的。
晚上,大大做晚饭,把我叫到灶火边去烤火。一抬头,灶头顶的铁钩挂架上,是一块一块长长的、红红的腊肉,大大抬手用火钳轻轻地碰了一下那些腊肉,腊肉便在上升的柴烟中晃动起来,然后大大用菜刀在其中一块腊肉上划了一刀,手起刀落,一片红红的瘦肉便捏在大大的左手里了,大大右手张开火钳,夹上那片瘦肉,径直伸到灶膛里,一会儿香气扑鼻而来。再一会儿,大大拿出火钳,只见那片肉滋滋地滴着油。大大把那片肉放在碗里,递给我,说“吃嘎嘎,香呢!”我抽泣着,大大摸了摸我手背、手肘上的红色印子说,“还疼不?”我还是抽泣,没有接大大递给我的火烧腊肉。“香得很,不吃,大大吃了,乖,以后不要耍鹅儿了,你看把鹅儿都耍死了,一窝鹅儿总共才八个,眼看着就破了群,少了一个,几个月长成大鹅就能卖钱了,可惜了!”我说:“我没有耍,是哥哥、姐姐耍了。”大大略顿了一会儿,放下手里的火钳,“来,大大抱抱。”大大向我伸开了手臂。
至今记不得那一晚,我是怎么睡着的。只记得竹枝条抽在身上的疼痛,以及大大抱着我,头顶上柴烟氤氲中晃动的一条又一条暗红色的腊肉。
其实,我一直记得大大出嫁的情景。大红衣服,长长的麻花辫垂到腰间,在催促的唢呐声中,大大眼睛里噙着泪辞别我爸:“哥,我走了!”接着,大大上了花轿,花轿很快没入了长长的迎亲队伍里。而大大长长的辫梢上系着的红绸,如一团火焰,很久很久都在我的眼前跳跃着。当爸爸背着我说去看大大的时候,我是渴望快点儿见到大大的。
然而,我见到大大的时候,离大大结婚的时间并不长,大大却变了个人似的。大大在家的时候,长长的辫子,高挑的身段,走起路来慢悠悠的,瓜子型的脸庞上,一双大而亮的眼睛,未说话先就笑眯眯的了。而现在,大大将长长的辫子挽在了头顶,每天走路脚下生风,放下锄头,又拿起镰刀。一天到晚,我没见过大大闲在家里的时候,只有三餐做饭的时间在家里。每次大大出门,都说是干活儿去,以我三岁的认知,我还不懂得大大作为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白手兴家一天到晚地忙碌、焦愁。
记不得过了多长时间,印象中只记得每天我在大大家的院子里,周围年猪的叫声更密集了。大大在准备过年的团圆饭了,记得来的人很多,爸爸也来了。四方桌上,一盘盘蔬菜的中间,有一碗切片冒尖的腊肉,色泽已经褐红、透亮,油汪汪的,大大往我爸爸碗里夹了一片腊肉,再伸筷子夹了一片放在了我的碗里。腊肉的香味还是压不住我手上腿上冻疮的疼痛。我的手背上,小腿上,大大用竹枝抽下的红印,后来成了冻疮,大多发炎红肿了。爸爸问我大大:“……咋长弄多冻疤哟?”大大说:“可能是河风吹的,今年冬天太冷了。”
从小到大,我的心事都是给爸爸说,但直到后来我上学、离家、长大、成婚,都没有和爸爸说过此事。后来,我虽然离娘家山高路远,不能常回去,但会给爸爸写信,再后来就是打电话。记得我的女儿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爸爸通电话,说起上班、家务、带女儿,一天到晚忙乱不堪。“再忙再累,女儿自小到现在都是我自己带,我不愿意假手于人”。话赶话说到那里,我才脱口和爸爸说了三岁时,在大大家的那些往事,我说得轻描淡写,像故事一样讲给爸爸听。可是,电话里我听到了爸爸压抑的叹息,没有想到事隔经年以后爸爸还记得这件事情。爸爸说:“那时家里顶着‘帽子’,在你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几张嘴,家境艰难,想着送你到大大家去能吃饱饭。过年了,我去接你。背你回家的时候,觉得轻了好多,我就晓得你受了苦。上船的时候,大河里一个浪子打来,差点儿把你倒到河里了,好危险哟,失悔了好久哟,我悄悄压在心里几十年没有说……”
至今,爸爸早也不在世了。但我一直记得爸爸说起那个清晨的语气。虽然隔着长长的时光,波峰浪涌却如在我的眼前,也一直埋在爸爸的心里。那是除夕前一天,清早五点多,天光未明,爸爸又用竹编的座座背篼,把三岁的我背上,大大打着煤油竹筒给我们照路,一直送我们到河边等船。
我大大住的地方,在长江下游。长江水浩浩荡荡,穿山越谷流到合江县城三江嘴的河滩处,与西来的赤水、习水交汇,再分流而下。三水汇合的江水从合江三江嘴出发,峰回路转下流15千米,到那个山水相依叫川天化的央企,河流再顺山拐一个弯,对岸河畔的高坎坡塄上便是我大大的家。这个地方,平常出行无论是赶榕山场,还是到县城,都隔河渡水,只有靠这班机帆船行走水路,水上的路每天只有一班从铜千湾起航,逆流而上,沿路靠几次岸,终点停靠合江县城北门口的机帆船,每天只有一个班(次),如果错过清早这班船就没办法出行了。我大大家门口的河边,是这班船停靠的一个小站,船从靠岸到起锚只有几分钟。
也许是临过年,河面上还看不到船来的影子,而岸边却等候着乌泱泱的赶船人。有挑菜的,有背红苕的,有扶儿携老的,有抬猪牵羊的,有背鸡挑鸭鹅的,还有手里提着腊肉的,腊肉上基本都贴着或包着红纸,那多半是过年亲友间互送的年礼。河岸上有大人,有小孩子,还有老人,小孩子的哭声,大人们的说话声,哭的闹的嚷的笑的,沉睡的河坝早早地醒来了。
等船的人越来越多,嘈杂声越来越大。不知甚时,下起了雪粒籽,落在脖子里、脸上,冰冷的。候船的人来回走动,不时用嘴呵着手,跺着脚。等着候着,下游河流拐弯的地方,水面上出现了亮光,人群里便有人惊呼——船来了,船来了!船越来越近了,船影慢慢清晰起来,船先停靠河对岸的榕山。一会儿,船从榕山站起锚往江对岸而来,汽笛鸣响,接着便看到银亮的浪花涌着船舷,船舷的甲板上挤挤挨挨的人也能渐渐看得清晰了,岸边候船的人便拥挤、嘈杂、骚动起来。船靠岸了,水手将跳板一头搭在船舷边上,一头固定在河岸上,江中的船还在漂动着,赶船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挤上了跳板,当人走到跳板中心的时候,长长的跳板便颤颤悠悠起来,跳板下,银白色的浪花翻滚着,哗啦哗啦地拍打着河岸。
爸爸要上船了,大大将手里一直拿着的红纸包递给爸爸,说:“哥,给你个刀头儿(过年送腊肉给亲友时,送的一方对腊肉的谦称,川南有的还俗称腊肉为扬尘吊儿),回家让嫂子尝尝。”爸爸推让不过,接在手里,与大大在江边分别:“好好过年,过了年回家来耍。”爸爸叮嘱大大。
爸爸背着我,从河坝上一脚跨上了船舷边的跳板,边走向船舱边扭头看向大大“回吧,八妹,落雪了,冷得很了!”爸爸扭头与大大告别的瞬间,江中一个浪头打来,船体猛烈地摇晃,已经走到跳板中心的爸爸,随着波浪颠簸的船体一个趔趄,左手本能地扶住座座背篼里的我,右手一甩,算是保持了平衡,我没有被倒在江水里,可爸爸手里大大给的红纸包却甩了出去,一个高高的抛物线,飞入江中。随即,一个浪涛翻滚而来,打了个漩,一个浪头盖过来,红纸包立即随波漂走了。那红纸包里,是大大送给爸爸的过年腊肉,爸爸从大大手里接过来,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还没有三分钟,手里却空空如也,只望见白浪滔天的江水。
岁月如那江水,一波涌着一波滔滔远去。
42年后的冬至那天,草叶一夜之间上了清霜,比我三岁时在大大家度过的那个冬天更瑟瑟寒冷,父亲被从灵床上抬入了他的千年屋。父亲走完了这个世界的路,将要迈向另一个世界。我自小出外求学,之后远离那个给予我生命的家乡,与我的父亲聚少离多。我不知道父亲后来的人生中,有多少次走过那条吞没了腊肉的大河,有多少次经历心有余悸的江中颠簸。
四十多年的时光,如那冲走父亲手里腊肉的大河汤汤、白浪滔天,流淌不息的江水如春秋更替的岁月,一波又一波滚滚而去,冲走了多少人和事,但冲不走的是家乡杀猪过年的年俗,冲不走的是那褐黄而透亮的腊肉。
“走”了一百多里的年礼
在我的家乡,人们丈量距离的单位习惯称为里,1千米是2里。比如,从我家往西八里地,是留学堂村中心所在地王嘴;从我家往西十五里地是佛荫镇政府所在地,也是佛荫老场,逢阴历三、六、九人们聚集在此,进行物品流通、赶场交易的集市所在地;从我家往西30里地是擂子山村,那是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村子;从我家往南十五里地是赤水河边;从赤水河边往东15里是合江县城……这是我记事以来听人们对周边村子里程的计算法以及地名的叫法。有的村子以地理标志而命名,比如我们村西的擂子山村,因村子里有一座山叫擂子山而为名;有的以历史遗存命名,比如我的村子留学堂,是村子里历史上有一所由乡贤捐资而建的私塾,故而得名。
母亲十一二岁的时候,外公外婆先后离世,母亲跟着二哥长大(母亲的大哥工作外地)。母亲与父亲结婚后,每年正月初二或初三,都会回娘家给二哥二嫂拜年。拜年不能空着手,一定得带年礼,这是长辈沿袭下来的礼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土地承包到户的第一年,时令过了冬至,当孩子们传唱“年猪年猪叫,过年过年到”,数着日子盼过年的时候,母亲喂了一年的猪已经膘肥肉满了。那一年,我家杀了一头两百多斤的肥猪过年,母亲不再为过年送娘家的年礼犯愁了。母亲给二舅背了一块带猪尾巴的坐臀肉(坐臀肉,位于猪后臀上方,北方又叫元宝肉,是猪身上肉质最细腻口感最好的肉),有十余斤重,我和大弟跟随母亲去拜年。
时间推回到腊月初,我们家杀年猪的时候,“带尾巴那个坐臀大大子地砍,熏成腊肉,娃儿他妈过年回娘屋当年礼。”父亲叮嘱杀猪匠时,我在一旁听得真切。肉在陶瓷缸里腌好后,父亲用竹篾子挽成细绳,再将肉穿起来,高高地悬挂在灶火顶上,经过二十多天的烟熏火燎,到过年的时候,这块坐臀肉已经由白色变得黄澄澄的了。
我家去二舅家,中间要经过三四个村子,王嘴、罗伞嘴、尖山子、佛荫场、中坝嘴。从蜿蜒的山路而盘山公路,我们走过山林,走过村子,走过佛荫场,再走过山林,再走过村子,才走到了擂子山村。我和母亲、大弟弟,一上午走了30里路,中午才饿蔫蔫地到达二舅家。
我大嬢儿(母亲的大姐)带着表哥、表妹先到了,舅妈将饭菜已经端上了桌,正要吃午饭。母亲见到二舅、舅妈,相互拜年后,母亲拿出了腊肉,递给二舅,二舅赶忙将端着正要上桌的一碗白菜汤放下,双手从母亲手里接过了腊肉。
大家团坐在四方桌上,方桌中间是一碗肥瘦参半的腊肉。腊肉是川南地区过年必备的大菜,也是过年待客必有的礼数。如果隆重一些,会有盘子菜,七寸盘子里盛的是腊猪肝、腊猪心、腊猪肚、腊猪嘴等腊味,香肠也是不可少的。我舅妈家过年的饭桌上没有这些,除了八仙桌中间一碗腊肉外,就是萝卜、白菜、粉条等素菜,还有米白玉嫩如脂的豆花。
早上临出门的时候,母亲就叮嘱:吃饭要讲礼数,不许穷吃饿吃的样子,拈菜要少少地夹,不要一筷子挑一大箸,尤其是不能随便拈(方言,指用筷子夹)中间那一碗腊肉,得等饭桌上长辈举筷子喊“请”的时候,才能动筷子拈一片腊肉,尤其不能一筷子拈两片,或者筷子在菜碗、肉碗里乱翻,只能夹靠着面前的菜,不能过河到对面夹菜去。我和弟弟虽然饿了,也很想多吃几片腊肉,但是,必须要遵照母亲一向教给我们的规矩。
“哇——哇——哇”,表哥猛一下惊喳喳地哭起来,嘴里的腊肉还没有咽下,大嬢儿刚端着饭碗离开饭桌,去灶屋盛米饭去了。
桌子成四边形,我就坐在表哥对面,将这个场景默默地看得真真切切。在舅妈还没喊“请”的时候,表哥就将筷子伸进腊肉碗里,夹了一片腊肉放在嘴里,刚咀嚼了两下,坐在表哥右侧的舅妈便将手挨了一下表哥,接着就是表哥惊喳喳的哭声。
大嬢儿听到表哥哭,端着饭碗赶紧回到饭桌,一个劲儿地问“咋啦?咋的啦?”
“二舅妈掐我的屁股!”表哥眼泪滚到脸蛋上,再吧嗒吧嗒地掉在饭碗里,筷子杵在碗里,咧着嘴哭泣。
大嬢儿略一沉默,然后褪下表哥的裤子看了一眼,马上哄表哥说,“没来头得,可能是猫儿挠了一下,你看那不是猫儿嘛。”二舅赶紧夹了一片腊肉放到表哥碗里,“来,吃嘎嘎,表哭,等哈儿二舅给你打那猫儿。”其实,二舅的狸猫并没有在饭桌周围,饭桌底下倒是卧着二舅家的看门黄狗。舅妈也附和二舅说:“就是,表哭了,等哈儿打猫儿。”大嬢儿没有再说话,也没有再哄表哥。气氛沉闷着。母亲见状,岔开话题,不断地拉着家常,但大嬢儿没有接话茬,也没有再拿起筷子。
母亲说:“姐姐,快吃饭,等哈儿菜凉了。”
二舅也说:“就是,大姐,吃饭,吃饭。”
大嬢儿说:“恁慢慢吃,我吃饱了。”
大嬢儿离开饭桌出去了,留下了刚盛的那碗米饭,白花花地晃着我的眼。表哥没有大声哭了,但杵着筷子抽泣着,肩胛一耸一耸的。
饭桌中间的那碗腊肉下得很快,一会儿就快见碗底了。“咳,再切点肉来。”二舅对舅妈说。舅妈高兴地去了灶屋,一会儿切来一刀肉,放到碗里,碗里的腊肉又冒尖了。到我离桌的时候,我看腊肉碗里又快见底了。
午饭后,大嬢儿辞别二舅舅妈要回家,二舅让大嬢儿背点儿青菜回去吃,说刚从菜园里砍的菜鲜嫩,城里买不到的。大嬢儿高低不要,无奈,舅妈和母亲送大嬢儿,舅妈把青菜给大嬢儿背到路口,目送大嬢儿和表哥表妹仨走到公路上,上了返回县城的汽车。舅妈对母亲说,“恁二哥在屋头,七妹你带娃儿先回嘛,我要到李珍家耍哈儿的。”舅妈说着就往路口以东的一户人家走。
母亲说:“我都好久没回娘屋了,还真是想看看李珍去了,走,二嫂,我也跟你一路去耍哈儿。”
二舅妈像是望着路边油菜田里葱绿的油菜,略一努下巴岔开了话题,“七妹,你看这油菜长得好乖哟,恁二哥说今年多打点菜籽油,等过年的时候,你来我们就有油炸酥肉吃了。”姑嫂俩一前一后,往大路口东侧的一幢黛青色瓦房走去,我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的身后。
母亲和二舅妈从大路上拐入一条小路,走近了,只见竹树掩映的瓦房,单生独户,青石板铺的坝子,清扫得干干净净。男主人正在院子里淘洗红苕,说是还有两头猪,用红苕和米糠煮猪食。女主人听见说话声,从屋里迎出来。瘦而高挑,短发。无疑,这就是二舅妈和母亲说的李珍了。二舅妈避开母亲,三两步插到女主人面前,拽了一下她的衣角,女主人随即和舅妈返回了灶房。
青石院坝里,一个穿着红灯芯绒外衣,黑灯芯绒长裤的小姑娘正在踢鸡毛毽子,随着毽子上下翻飞,她高高的羊角辫也左右摇晃,“你妈妈是李珍吧”,母亲走近小姑娘问。姑娘点了点头,母亲便停下了脚步,逗小姑娘说,“看到你妈怀着你,一晃都长弄高了,你和我女儿同岁的,你们一起耍嘛。”就在母亲和小姑娘说话的一会儿工夫,我舅妈跟随李珍进了她家灶房,我也跟了过去。
“快点儿,拿个碗”,我舅妈对李珍说。我懵懵懂懂地看到了舅妈的秘密。李珍麻利地打开碗橱,拿了个青色大碗,我舅妈解开围裙两角,一抻一倒,大碗里便是切成片的腊肉,满满的一碗。李珍打开碗橱,将碗放了进去,关上了橱门,眨眼工夫她们俩就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看到这一幕,我才恍然明白了舅妈从吃饭到出来,为什么腰间拴着的围裙一直都高高地挽着两边的裙角了。原来饭桌上碗里冒尖的腊肉很快就碗见底了,不是都吃了,而是大多进了舅妈的围裙里了。人小不明事理,后来,我把看到的这一幕告诉母亲,母亲说:“这是腊肉走了路,不要对别人讲。”当然,小小年纪的我,不懂得什么叫走了路?心想,腊肉又没有长脚,怎么就叫走了路。看当时舅妈神秘的样子,我不敢多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乡村里腊肉精贵,除过年过节和人来客往外,平常难得吃一次腊肉。舅妈将饭桌上的腊肉送进了李珍家的碗橱里。这个秘密饭桌上的二舅不知道,大嬢儿不知道,表哥表妹是更不知道的,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幕。
李珍与舅妈立即从灶房出来,在青石坝上热情地迎上母亲,和母亲拉着家常。而院子里穿着西服淘洗红苕的男主人,看着我舅妈从灶房出来,赶紧从堂屋里搬出小桌、凳子,放在堂屋外宽宽的走檐上,拿出橘子、瓜子、花生、水果糖等,一番热情让座,招呼吃喝。
我在石坝里和她家的女儿玩着踢毽子。她家女儿小名花花,用铜钱做的鸡毛毽有点儿像羽毛球,踢在脚上较有分量。刚开始我把握不住重心,鸡毛毽总是踢偏,花花给我示范了几次。在示范与学习的过程中,我和花花很快熟络起来。花花说这个鸡毛毽子是过年的时候,她爸爸做的,一共做了两个。“鸡毛是除夕杀公鸡留下的翎毛,铜钱是我爸爸从单位带回家的。”花花说,她的爸爸是公家人,工作于场(镇)上。她寒暑假或是周日的时候,偶尔会去爸爸的单位耍。
半下午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女孩子和我们一起玩儿,她叫毛毛,与我舅妈同一个屋基,两家的大门隔天井而相望,毛毛比我和花花大两岁。毛毛将毽子踢得上下翻飞,左右旋转,鸡毛毽子像长在她脚上似的落不了地。
踢累了,我们就势坐在青石坝子沿上。毛毛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小图书《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沉浸在故事的精彩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毛毛不经意地抬头看到花花的父亲,正热情地招呼着我舅妈吃、喝,我舅妈也笑脸相迎,李珍也笑意盈盈的。只有我的母亲站在青石坝边上,望着远方如黛的桐连山,离走檐远远的,没有参与到他们的吃喝说笑中去。毛毛站起来,用手掩嘴凑到我的耳朵边说:“花花她爸与你舅妈是亲戚!”然后毛毛冲我眨了两下眼睛。
我不理解地看着她:“是亲戚有啥神秘的,干吗还要说悄悄话?你眨巴眼睛是啥意思?”此时,坐在我们一边的花花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我们。
“我屋基里的大人都这样说,我听来的,我啷个晓得是啥意思?”毛毛也不再用手掩嘴,一句“啷个晓得?”似乎更有些神秘了,又似乎我们小孩子真的弄不懂大人的世界,就像我弄不懂舅妈送腊肉为何要遮着掩着一样。
毛毛站了起来,合上小图书,装入衣服口袋,对花花说:“不和你玩儿了,走啦!”
毛毛的一句话,仿佛与我像结成同盟似的。我也站起来,与毛毛手拉手,一前一后地离开了花花家。走了几步,我回头,花花站在石坝边上,呆呆地看着我们,“几时又来耍儿?”我定神地望了望她,只见她手里的鸡毛毽子,褐红色的翎毛在风中微微地晃动着。
回到舅妈家,表姐正在堂屋里做作业,她见我和毛毛回来了,放下作业本,邀我和毛毛一起到屋后的晒谷场玩儿。表姐拿上了她的橡皮筋,我们三人轮流抻着皮筋,玩儿着跳皮筋。跳得累了,我们来到晒谷场边的竹林里玩儿竹子。正月里有拜竹子的习俗,说拜了竹子会长得修长、高挑。我们找了两棵距离相近呈平行的竹子,两棵竹子之间只容得下一个人的空间距离,站在其间,双手抓住竹竿,一边摇一边说“竹子妈、竹子娘,长得跟你一样长!”然后双手抻住两棵竹竿,玩起了翻跟头,比赛谁翻得多。这是我们小时候最爱玩儿的,基本都会玩儿。表姐一个跟头翻上去,在双腿贴着竹竿倒立的时候,衣服口袋里倒出了一个鸡毛毽。见此,表姐双腿一个腾跃站定。弯腰伸手捡地下的鸡毛毽,毛毛见状,眼疾手快,抓起那个毽子就跑。“我玩会儿,”毛毛在前边跑,表姐在后面追,“给我鸡毛毽。”一追一抢之间,扯掉了鸡毛毽子上的两根翎毛,那翠蓝色的翎毛在风中打着旋儿地翻飞、飘落。待鸡毛毽回到表姐手里时,已经秃了小半边,我们不欢而散。
其实,表姐的鸡毛毽从口袋里掉落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和李珍家女儿花花的鸡毛毽一模一样,就连包铜钱的花布图案,以及缝的针脚也是一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我静静地观察着舅妈。下午李珍家的青石坝上,舅妈家对门邻居家的女孩儿毛毛冲我眨巴眼睛的表情意味深长——“你舅妈和花花家是亲戚”,而花花的话语也在耳畔回响“我爸做了两个鸡毛毽子”。舅妈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夹菜吃腊肉,花布棉袄的外面仍然系着围裙,但不是中午那一条围裙了,这条围裙短短的束在腰间,束出了舅妈细细的腰线。而晚上舅妈的裙角展展的,并未挽着。我望着橙黄的煤油灯光下,那一碗亮晶晶、油旺旺、肥瘦相宜的腊肉,却不断地想起下午看到舅妈围裙一抻一倒的那一幕。
年味儿是腊肉的味道,谁家煮腊肉,山下弯里,坪上岭顶,真是香飘十里。过年,走亲访友的人情礼往,也在那浓浓的腊肉香味儿里传递。
正月十四,我大嬢儿带着表哥表妹从合江县城出发,到我家已近中午。一进家,大嬢先递给我母亲一个很大的红纸包,母亲打开一看,“姐姐,你在城头,又没喂猪儿,喝口水都需要钱买,吃根葱没钱也吃不着,你怎么还给我带腊肉?”
大嬢儿说:“要带的,要带的。过年呢!不能礼节不周,我就你这一个妹妹!”
母亲打开红纸,一下就认出是正月初二她送给二哥二嫂的坐臀肉,大嬢又送回来了。过年杀的那头年猪,在小猪只有几斤重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母亲被小猪的叫声惊醒,去猪圈一看,小猪尾巴被耗子还是什么野物咬了。至此,直到长大,那个猪的尾巴靠近梢处有个豁口。母亲应当是看坐臀肉上的猪尾巴豁口认出来的。但是母亲没有欣喜,这应该与母亲常说的“恁大嬢儿的日子不好过”有关。
姨伯家是戴“帽”户,大队里有重活儿累活儿,或是没人愿意干的脏活儿就派他去。当时公社大队里搞基建,石材不够,有人就出主意拆生基的石板当石材。说到拆生基,就是拆老墓,那是对墓主的大不敬,是犯忌讳的。大队里谁敢去动?于是,这活儿就自然派到我姨伯的头上。
那时候以成份论,姨伯在村子里甚时都低眉顺眼的,连大话都不敢说,大队派给的活儿哪敢违抗?在拆生基的过程中,我姨伯大拇指被石头打破了。也就奇怪,看似大拇指上擦破了点儿皮,并未伤及筋骨。然而,那个拇指却一直溃烂,直到看得见白生生的骨头。我姨伯多方求医无果,几个月后,正当年富力强的年纪去世了,丢下我表哥和表妹一双小儿女。我大嬢儿带着两个七八岁的孩子,实在生活无着。在我姨伯去世一年多后,大嬢儿带着我表哥表妹嫁给了县城里的一个哑巴。哑巴在县农具厂打制农具,哑巴还有一个六七十岁的父亲。一家五张嘴依靠哑巴一个人养活,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
那一年,大嬢儿和表哥表妹在我家过的正月十五。在我老家,正月十五这个日子,是与大年除夕一样看重的节日。过年前,在“年猪年猪叫,过年过年到”的时节里,我家是杀了年猪的,灶间,长长的竹竿上,挂着熏得正是火候的腊肉、香肠。母亲煮了腊肉,还煮了猪耳朵、猪嘴、香肠等腊味儿。饭桌上,父亲和母亲轮番地往大嬢儿饭碗里,往表哥表妹饭碗里夹肉,添米饭,不是一片一片地夹,而是一摞摞地夹,一筷子下去就是三片两片的。大嬢看着碗里透明黄亮的腊肉,在饭桌上流泪了。大人之间的谈话,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小孩子,我常在一边默默地听。
原来,正月初二大嬢儿带着表哥表妹去舅妈家拜年,午饭时表哥确实是被舅妈掐了屁股。“当时,我褪下娃儿的裤子一看,屁股蛋上是深深的指甲印,都掐进肉里淤血了。”大嬢儿说,“我再穷,但我也是当妈的,这哪是掐娃儿的屁股,这分明是打我的脸啦,还不如面对面地打我两拳,娃儿爸死了,就能让娃儿受这样的委屈?”
初二下午大嬢儿从二舅家临走时,二舅硬让大嬢儿背青菜回去吃,她推托不过,背回家拿出青菜一看,背篼底下是一块坐臀肉,“肯定是二哥放到青菜底下的,看来,饭桌上发生的事情,二哥心知肚明”,母亲继续劝慰大嬢,“大姐,别想那些了,事情过去了,毕竟是自家的亲兄弟。”
“过年呢,家里实在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年礼,就把这块腊肉背来了”,大嬢儿对母亲说。至此,母亲明白了为何她过年送给二舅的年礼,又被大嬢当年礼送到了自己的手里的经过。正月十六,大嬢儿离开我家回去的时候,母亲将那块坐臀肉用红纸包好,放在背篼底下,上面给大嬢儿放上了绿绿的冬寒菜和紫红的油菜薹,让大嬢背回去。
从我家到二舅家,30里;从二舅家到我大嬢儿家60里;从大嬢家到我家30里。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十四,这块坐臀肉用了12天,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我家。正月十六,母亲又送给了大嬢儿,因为母亲认为,带尾巴的坐臀肉,是一头猪身上肉质最好的肉,也有吉祥之意。算起来,那块腊肉,从我家出发,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经过了母亲哥哥姐姐的手,漂流了一圈,行程一百五十里。漂流的是年俗,传递的是过年的礼仪,是亲人之间的温情。也让自小的我,从中窥到了一些人性的幽微。
那根长长的线
“年猪年猪叫,过年过年到”,杀猪过年,是大人们对过年的期盼,也是一年劳作耕种的总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到过年的时候,家里有没有肥猪杀,也是衡量一户人家的年景,或者勤懒的重要标志。过年做腊肉,是南北都具有的年俗,但又因地区不同、气候环境不同而做法和口感都各有差异。
在我川南的老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物资紧缺,谁家有男娃长大了,到了说亲的年龄。媒人向女方提亲时,女方的父母通常会问媒人男方家过年杀年猪了没有?杀了几头?女方到男方家第一次上门相亲的时候,都要到灶间探看一番,看看灶间里挂架上有多少腊肉?光景好的人家,杀一两头年猪的,灶间挂架长长的竹竿上,长的、短的,挂着满满的腊肉。光景不好的人家,遇上女方上门相亲,借也要借几条腊肉挂到灶间充当门面。腊肉,又是乡村冷藏设备不具备的时期,储存肉食最好的一种方法,也是一年到头逢年过节、栽秧打谷、人来客往,保证饭桌上有肉食的一种方式。“5·12”汶川地震的时候,墙倒屋塌的乡村废墟里,不时能看到一竹竿、半竹竿的腊肉,颜色褐黄褐黄的,让人在废墟里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我的家乡,一到腊月天气,四野会传来此起彼伏猪的号叫声,这声音里有猪的恐惧、有挣扎,还有绝望。随着我的渐渐长大,我才意会了三岁那年,爸爸把我独自留在大大家时,大大说我“嚎得跟杀猪似的!”乡村里这样形容一个人的哭泣,也不是大大发明的,凡是哭得歇斯底里的,大概都被说成是“嚎得跟杀猪似的!”
腊月里,空气里飘散的都是年猪汤的香气。
腊月里,杀年猪的喜悦在人们见面的寒暄和问候里。
“杀几百斤哟?”
“两百多斤。”
“某某家杀了三百多斤。”
“人家屋头的那个好会喂猪儿哟!”
年猪杀得大,是家户里女人在乡村的自豪,也是家户好光景的荣光,还是乡村好年景的标志。
所谓年猪有两层意义:其一,一般是头年就买回小猪,只有几斤重,喂到第二年腊月,通常有三两百斤重。猪生长的时间要一年,或一年多,生长的周期是跨了年的;其二,秋收后,粮食归仓,猪吃了一秋天一冬天的大米、米糠、红苕,到腊月,已经长得膘肥肉满了。快过年的时候,便约杀猪匠,准备杀了腌制过年的香肠、腊肉。
我记事以来,家乡的农人们一年到头在田地里耕耘劳作,可谓是靠天吃饭,如果遇上三晴两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收成就好。家禽家畜是一家的经济支柱,娃娃读书、穿衣,以及家庭修房建屋、人情客往的开支,都依靠它们卖钱。家家户户都喂鸡喂猪,猪少的两三头,多的四五头、五六头,喂大了就出栏卖钱,当然希望家禽家畜们顺顺遂遂地长大了。一旦出现了鸡瘟猪病,如同家人生病一样着急心疼。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清早路过一片树林,见我同班同学的母亲在树林下的地角里一边哭一边刨土。见状,我驻足,土边躺着一头猪,猪虽瘦,但看上去架子却不小了。到了学校,我把看到的一幕问同学。她说:“家里的猪病了,不吃不喝,叫兽医打了两次针,今天早上母亲起床发现猪已经死了。”她和两个哥哥被母亲的哭声惊醒,都早早地起了床,她的父亲早早去世,母亲拉扯着他们兄妹仨,一家的经济来源全靠母亲喂猪卖钱,原本指望这头猪长大卖钱,用着过了年家里三兄妹开学的学费、书本费,现在只得埋入泥土里,母亲特别伤心,也特别无助。我的同学说起早上的情形,当然,那时候,她肯定也没有预料到,来年春天,她就此辍学了,因为这头猪死后,她家的另两头猪也相继死了。
因此,杀年猪是有诸多讲究的,也是有仪式感的,预示来年的吉祥,也是老家重要的年俗之一。杀年猪的时候,是不是一刀毙命,放血是否顺畅等,都是格外隆重而讲究的。和乡村里平常操办婚丧嫁娶等,办宴席杀猪的意义又是不一样的。
通常,进入冬至,或者腊月后,由家中的长辈或是家里主事的人,首先要盘算请口碑好的、信得过的杀猪匠。比如:有的杀猪匠一刀杀不死猪,还要补第二刀;有的杀猪匠把猪放血了,按猪的一松手,猪还从板凳上下来跑了;有的杀猪匠下水打理得不干净,剃猪毛不光溜等,这样的杀猪匠都是口碑不好的,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会传得很远,杀年猪是不能请这样的杀猪匠的。
定下杀猪匠后,再与杀猪匠相商杀年猪的时间。十乡八里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口碑好的杀猪匠会很忙,有时一天要跑几家。我的老家,沿大河两畔蜿蜒起伏,大多处于丘陵地区,山与山,岭与岭相连,看起来炊烟相连、鸡犬相闻,一嗓子能喊得应。望山跑死马,山路蜿蜒,走起来却很远,农家居住分散,户与户之间相隔三五里,七八里,十来里都不一定的。杀猪的匠人会根据相互之间的距离、路线,约定下他跑起来比较方便的日期。
杀年猪的日子定下来后,便与三四个平常关系友好的亲友约定,到那天来帮忙按猪。猪杀后,杀猪的当天会请杀猪匠和按猪的亲友吃一顿全猪汤,杀猪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要请乡亲邻里吃年猪汤。其实,这也是邻里乡亲友好往来,建立互帮互助睦邻关系的一种形式,平常红过脸的、拌过嘴的,甚至吵过架的,都会在这热热闹闹的年猪汤中开怀一笑、烟消云散。
杀猪日期定下后,就是等待杀猪匠到来了。小时候,父亲定下杀猪的日期,都会告诉母亲,因为要被杀的年猪头一天不喂食。我当然也听在耳里,看着放学后或者假期里,我找猪草,慢慢喂大的猪,就要被杀掉了,我会很舍不得。我从猪圈的石头缝里伸手去摸摸它的耳朵,蹄子、肚腹、脊背。当我摸它的时候,猪的嘴会一拱一拱地、呼哧呼哧地蹭蹭我的手,然后会慢慢地躺下来,眼神里我看到的全是温顺,没有惊恐,看来猪真的不知道就要被宰杀了。
我从来不敢看杀猪,一般看见背着亮光闪闪的挺杆、杀猪刀的杀猪匠到家,我就会躲出去,但是猪被杀时声嘶力竭的惨叫声会传得很远,躲哪儿都能听到。如今,只要想到杀猪,猪拼命时的惨叫声,仿佛穿过几十年的岁月,还在耳畔响起。
虽然舍不得猪被杀,但吃着母亲熏制的腊肉香肠的时候,又盼着来年过年杀猪,熏制香肠腊肉。内心里,不知是盼着过年,还是盼着年猪带来的美味儿。
母亲说,现在老家好多人家都不喂猪了。腊月时,乡村里很安静,很少能听到杀年猪的猪叫声了。年轻人正月十五还没有过,通常正月初三、初五后,就陆续出外打工了,家中留下老人、孩子,年纪大的,猪也喂不动了。
我母亲也如是。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夜间鬓角飞霜,冠心病加之腿疼,身体大不如前,上街买个菜,也得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可是,在城里生活的母亲,每年冬至过后,进入腊月,就会想方设法托人买土猪肉,腌制、烟熏,做成腊肉,赶在过年前快递给我。去年腊月,我又收到了母亲快递来的腊肉,母亲在电话里反复地说“不像你爸在世时做的腊肉好吃了。”
我懂得,母亲怀念的不仅仅是父亲做的腊肉,而是怀念两人相扶相携杀猪过年,腌肉、熏香肠、做腊肉的那种烟熏火燎的日子。那是最实在的人间烟火味儿,也是最滋润的日子。怀念这种烟火味儿的何止是夫妻,还有远在他乡的游子,那是思亲之味儿,也是家乡的味道。
父亲在世时,年年家中杀年猪做腊肉,每年父亲早早地在灶火上方备上挂架,搭上长长的竹竿,将腌好的腊肉、香肠挂上去,利用每天做饭的柴烟,飞升上去慢慢熏制。在熏腊肉的时间段,所用的烧柴,父亲会有意识地准备一些柚子叶、柏树枝、橘子皮、香樟树枝、芭茅草、甘蔗叶、花生皮等。每年老屋前的那株老桃树开花的时节,我便回家,母亲煮熟切片的腊肉,看上去通透明亮,黄里透着微红,吃到嘴里,满嘴溢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年,母亲为了让我能吃上色泽美、口感好的腊肉,真是煞费苦心,不辞劳苦。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年,过了冬至,在城里居住的母亲就打电话回老家,从好友那里得到消息,老家有的人家要杀年猪卖肉,肯定是喂红苕、米糠、猪草的土猪。于是,母亲托她的好友帮着预订下一头猪的后腿肉。
杀年猪那天,母亲从县城出发,背上食盐、花椒、白砂糖、茴香等,乘车近20公里,再步行二三公里山路,到了那户人家。肉过了秤,母亲付了钱,拿出预先备好的腌肉材料,随即将鲜肉腌好,临走时,母亲另拿了些钱,拜托人家说“劳驾你肉腌三四天后,帮我翻一翻,一周后再提出来挂在你家的灶火架上,帮我烟熏上,快过年了我再来背。”
“举手之劳,乡里乡亲的,买肉已经开了钱了,不要再拿钱了。”那户乡亲执意没有收母亲多付给的钱。快到过年的时候,果然,那户乡亲帮母亲把腊肉熏得色泽漂亮,入口醇香。母亲虽然不惜腿疼往返乡下两趟,但是母亲高兴,备好了熏制火候到位、黄澄澄的腊肉过年。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老家没有人家再杀年猪卖肉了。母亲又想了个办法,早早托市场里卖肉的老板,“到乡下订货遇到土猪肉,帮我买两个后腿。”果然,冬至后,母亲买到了乡下农家喂的土猪肉,还是后腿,为了方便熏制,肉店老板给母亲将肉切成了六条,每条有五六斤重。
可是,肉腌好后,母亲却犯了难,城里那种自制熏笼的急熏方法,母亲一直就不赞同,一方面是担心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母亲认为那不是熏腊肉,充其量算是火烤肉,影响肉质的鲜美、口感。母亲左右思量,打电话给大大:“嫂子,要得,你背来熏嘛,我每天做饭,挂灶房屋里顺便就熏了。”大大热情地回应母亲。母亲背上已经腌好的土猪肉,乘车七八公里,步行一公里,到了我大大家。母亲和大大一同把肉挂在灶间的挂架上才放心地回家。母亲回城后,眼瞅着过了腊月二十,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高高兴兴地乘车去大大家,将腊肉背回县城,然后再快递给我。
那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同样收到了母亲快递来的腊肉,但是母亲从没有和我说腊肉熏制的周折。直到清明节,我回家祭奠父亲,母亲才和我轻描淡写地谈起。“妈,以后不要给我做腊肉了,现在不比以前了。以前,爸爸在世的时候,猪是自己喂的,柴烟是自己家的,不用麻烦人帮着熏制。现在,看您做腊肉多费周折呀。我怎么能吃得下去?”
哪知,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还有16天过年的时候,我又收到了母亲快递来的腊肉。今年的腊肉与以往的不同,母亲说,没有用柴烟熏过,城市里,实在没有办法熏。何止是熏,就是买肉这一个环节,母亲就颇费辛苦。这是我收到肉以后,弟媳在微信里告诉我的,母亲却只字未提。
现在乡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老年人喂猪的越来越少了,肉店老板也很难买得到乡村里的土猪杀了。母亲冬至前就在肉店老板那里预订了土猪肉,但眼瞅快到腊月半了还没有买到。母亲等不及了,早上七点钟市场还没有开门就去排队。原本肉店老板,偶尔在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能从乡下买来一头土猪肉,但肉一送到店里,就被早早等在肉案前、年轻力壮的顾客,你一块肉,他一条腿,一抢而空,一头猪两三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就抢光了,土猪肉供不应求,腿疼的母亲根本抢不到手。
冬天的寒风,湿冷湿冷的,70多岁的母亲连续去市场排了四五天的队,每天都空手而归。肉店的老板实在看不过去了,加之母亲一年到头都是她家的老顾客,而且还是提前预订了的。有一天,老板在没有开卖之前,先给母亲砍了一个后腿留着,直接过秤卖给了母亲,母亲才算买到了土猪肉,虽然一斤肉贵了两三块钱,但买到了母亲就高兴。
母亲提着20多斤肉,平地走着还好一些,遇到上台阶就困难了。偏偏合江县城是背山临河的城市,城市里九沟十八巷,到处都需要爬坡上坎。从市场回母亲家,要经过大寺巷,张家沟等,要走好几处台阶,其中一条最长的台阶,有五百多米长,一路上坡。走在这些青石台阶上,母亲腿疼,走不动,加之冠心病,走起来喘得呼哧呼哧的。母亲左手抓着台阶外的栏杆,右手提着肉,走几步停下歇歇,一步一步地往坡顶上爬着。
清早背菜到市场卖的一位妇女,从母亲身边走过时看到母亲走得吃力,“你咋不拿个背篼背哟?来,我帮你提到坡顶上,到平路你再提嘛。”那个妇女本身自己都背着菜,还从母亲手里接过肉,一直帮母亲提到走完长长的台阶。“你慢慢走,我等着你。”妇女先母亲走到坡顶上,一直等着母亲慢慢爬完台阶,才把肉递给母亲,让母亲在平路慢慢地走。她才背着菜往菜市场匆匆而去。
当弟媳告诉我时,我望着母亲寄来的腊肉,想着那位早起卖菜的妇女,以及那位到乡下买土猪肉卖的肉店老板,想着快递过程。在山西的我,要吃上腊肉,得经过多少环节,经过多少人的双手。可是,母亲总是坚持地说:“恁爸在世的时候,年年过年能吃上腊肉,不能说恁爸不在世了,女儿们就连腊肉都吃不上了,没有腊肉,怎像过年?”
这就是母亲,望着那些经过母亲的手腌制,长路迢迢寄到我手里的腊肉,想着我的鬓发霜白的母亲,疼痛着腿一步一爬行,以及寒风中排队买肉的情景,我怎么能吃得下去?这就是我的母亲,和所有天下的母亲是一样的,她对儿女的爱,只有那腊肉的醇厚浓香能够企及。
我合江的一位文友,也是一位母亲。今年过年的时候,去巴黎陪伴坐月子的女儿,行囊里装着她亲手熏制的四川腊肉。也许她的女儿也如我一样,远在异乡,味蕾对家乡风味儿的渴望,其实是对亲人的相思。腊肉的味道,对于远在他乡的游子而言,就是过年的味道,就是浓浓乡愁的滋味。
2017年4月21日,在两岸志愿者的帮助与陪同下,97岁的抗战老兵胡定远先生,终得以回到家乡——合江县白米镇转龙湾村,与外甥们团聚。1940年,胡定远离开家乡出川抗日,于1946年辗转去了台湾,一去未归。相隔77年的时间,已然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胡定远先生与家乡亲友共进家宴的时候说:“最想念的就是家乡过年,母亲做的腊肉、香肠。”老先生拈了一片橙黄而透亮的腊肉放在嘴里,牙齿慢慢咬合、咬合,并不住地点头——“嗯,嗯,就是这个味道,记忆里母亲过年做的腊肉,就是这个味道,千变万变,家乡过年必熏制的腊肉味道没有变。”胡定远先生感叹家乡的老屋没有了,代之的是宽阔的柏油路,美丽的高楼,繁华的街景,他在台湾经常做梦梦到这里。可是,在胡老先生看来,家乡外甥们的亲情没有变,家乡的腊肉味道没有变。对于海峡对岸的胡老先生而言,多少年里,乡愁是一碗过年的腊肉,思在睡梦里,想在心坎坎里,望在眼窝窝里。
胡定远先生颠沛辗转77年,总算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从台湾回家了。在亲友的搀扶下,他来到父母双亲安睡的坟前,供上了一碗腊肉,焚香跪拜、泪水横流地说:“爸妈,儿子不孝,多少年过年没有回来,多少年清明没有回来,而今,儿子终于回来了……”
看着老兵胡定远先生从台湾海峡对岸归来,把一碗腊肉供奉在父母双亲坟前的情景。我在思索,如果胡定远老人的人生按前天、昨天、今天分成三个阶段——前天,胡定远在家里过年,母亲为他做腊肉;昨天,他在海峡对岸,想念母亲过年做的腊肉;今天,他回来了,捧上了一碗外甥过年做的腊肉,供奉在了父母双亲的坟前。
腊肉的味道,是过年的味道;腊肉的味道,是年礼的味道;腊肉的味道,是乡愁的味道;腊肉的味道,是亲情的味道……“年猪年猪叫,过年过年到”,一句只有十个字的家乡谚语,是拽着在异乡的游子回家过年的那根长长的线。无论走得多远,即使隔山隔水,也被牵引着,回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