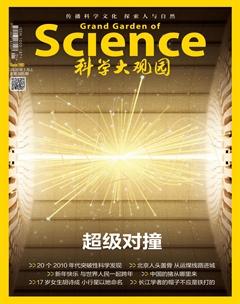争议中挺进

今年的诺贝尔奖依旧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间接反映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顶尖基础科学的缺位。
在年复一年的关于中国基础科学何时有全球领先性成果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指出,中国的基础科学正处于播种的阶段,还远未到收获的季节。由此拆分这个观点,如何“播种”又成了另一道难题。
正在接受评估的中国超大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以下简称“超大对撞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投入,成为杨振宁、丘成桐两位顶级科学家多次公开讨论的争议焦点,更考验着中国现阶段在建设大科学装置上的决策和决心。简而概括之,“反撞者”(杨派)认为此事时机未到,“挺撞者”(丘派)认为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时至今日,CEPC 这一牵动整个中国高能物理界神经的项目,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命运走向?
CEPC《概念设计报告》诞生
1984年10月,中国开始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启了中国大科学工程建设的新时代。
2007年10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开始建造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工程,并于2012年3月宣布:在世界上发现了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王贻芳等科学家还因此而获得2015年美国基础物理学突破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学家在2012年又提出了建造CEPC的建议。
2018年11月14日,两卷本的CEPC《概念设计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这一报告阐述了加速器和探测器的可行性设计方案,以及该项目的科学意义。同时也详细地评估了 CEPC 相对于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在科学上的优势。引人注目的是,《概念设计报告》吸纳了全球高能物理学界多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见,全球有上千位科学家参与了这项研究。国际未来加速器委员会和亚洲未来加速器委员会主席、墨尔本大学 Geoffrey Taylor 教授,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领导LIGO实验发现引力波的加州理工大学教授Barry Barish等都对CEPC《概念设计报告》的完成表示了祝贺和称赞。
CEPC机构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高原宁表示: “《概念设计报告》标志着我们完成了整个项目的加速器、探测器和土木工程的基本设计。下一步将重点关注CEPC关键技术和原型机的研发,希望今后能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2019年12月中旬,CEPC 的主要发起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再次回应中国建设超大对撞机的种种争议,并透露 CEPC 目前所處的阶段和取得的进展。
王贻芳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高能物理学家之一,曾师从丁肇中。过去10年间,他领导了国内两大粒子物理实验。其中,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被《科学》杂志评为 2012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团队测出“幽灵粒子”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也曾被誉为“中国本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他成为第一个斩获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人。但王贻芳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中国建设下一代超大对撞机,他是最核心的主张者之一。
“中国的粒子物理如果有CEPC,我就尽到了我的责任,这是从规划的角度而言。我可能没有机会在上面做研究了……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在GDP世界第一的时候继续做着二流、跟风式的科学研究,应该在最核心、最重要的地方去跟别人竞争。”在最新的采访中,王贻芳如此表示。

“用不了1400亿”
时至今日,回顾人类的科技文明史,诸多突破和进展无非基于人类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探索能力:更宏观的世界以及更微观的世界。而对这两个世界的探索越为深入,大型科学装置的存在感就越强。
环形超大对撞机,正是一种在高能物理领域用以探索和理解微观世界中的基本粒子、寻找新的物理规律的大型科学装置,由中国科学家于2012年提出建设。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理想选择,是能够引领世界基础物理研究最好的机会。”王贻芳进一步进行了充分解释。
首先,希格斯粒子是目前粒子物理研究未知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
其次,希格斯粒子质量不是特别重,环形对撞机是一个理想的希格斯粒子工厂。相对于直线对撞机来说,这是效率更高的一种设计。
再次,国际上我们很多的竞争对手(欧洲、美国、日本),他们的手上都有其他正在进行的项目,暂时腾不出手来做环形希格斯粒子工厂。
最后,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刚好是我们会做的,我们有30年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验。
同时,这样一个装置也会推动国内现有的一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包括精密器械、真空、自动控制、计算机、超导磁铁、专用集成电路等等。特别是可以填补国内空白,培育一批企业在超导高频腔、高场超导磁铁、高功率微波功率源、大型制冷设备等方面国际领先,并发展出诸如高温超导之类的革命性技术。
据了解,在 CEPC 的产学研版图中,现已有将近 70 家国内企业在合作名单内,一起开展关键技术的研究、关键部件的研制,推动很多国产化项目的进行。
王贻芳进一步指出,科学的发展从早期的手眼并用,到后来实验室中的显微镜、望远镜等各种各样的设备,再发展至今人类有了大型的空间望远镜、地面大型望远镜、地面大型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已成必然。
“我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难,我们研究的对象要么越来越大、要么越来越小,这都是人力极难触及的,所以借助越来越大的仪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是,大型科学装置,也对应着其建设过程中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这正是引发“杨丘之辩”的核心矛盾点。
此前有报道称,建设中国的超大对撞机,将耗费近30年1400亿元:第一步正负電子对撞机(CEPC)建设阶段,约在 2022—2030 年间,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 400 亿人民币;第二步超级质子对撞机(SPPC)阶段,工程造价在1000亿人民币左右,时间是在2040—2050年左右。
王贻芳澄清道:“很多人说这个项目要上千亿,我们从来没有说过。CEPC 需要 360 亿元人民币,这是我们两次估算出来的结果。”
他表示,CEPC 建成之后,其100 公里的隧道具有可重复利用的价值,未来的可能性包括用以做质子对撞机、电子质子对撞机,或者重离子对撞机等,这是第二阶段的可能性。
是否开展第二阶段的建设计划,将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一个,CEPC 需要有重大的科学发现;第二,我们的关键技术要有突破,例如高温超导。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如果我们把高温超导做出来了,它对社会的贡献就不是百亿、千亿了,恐怕是万亿以上。”
时至今日,回顾人类的科技文明史,诸多突破和进展无非基于人类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探索能力:更宏观的世界以及更微观的世界。而对这两个世界的探索越为深入,大型科学装置的存在感就越强。
开建时间点或晚于2022年
按照2018年11月14日发布的设计报告,中国团队的 CEPC 研发初期的资金来自中国政府,但有许多国际上的物理学家参与设计工作。
而在时间的规划上,CEPC 开建的时间点很大可能将晚于此前所设定的 2022 年。
王贻芳说:“一个项目的推动依赖于很多方面,我们最初(2013年)计划了CEPC于2022 年开始建设,认为团队差不多需要10年左右的准备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是在按计划推进当时设定的 10 年任务。”
“现在距离 2022 年还有 3 年,实事求是地说,团队还有很多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而这个也同时取决于国家未来‘十四五规划和其他整体性的计划到底会怎么执行。我们也在等待更宏观的各种各样项目计划的启动,这也不是某一个项目的问题,是许多项目的整体规划的启动,看起来还需要点时间。”
“未来中国能否实现建设超大对撞机,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是科学界需要回答的最中心、最关键的核心基本问题。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有没有勇气、能力,以及社会和公众的支持,来做未来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研究的绝大部分问题、所谓竞争的成功点,相当一部分像在打‘游击战,更多在边缘、空当、容易的方向上投入和取得成绩。我们敢不敢做,代表着中国未来科学发展是否能走到舞台中央。最终你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先地位,靠的是在最核心、最困难、最重大的科学问题上领先。目前为止,中国还未在最关键、最难、最核心的科学领域打过攻坚战。”
◎ 来源|综合微信公众号“ DeepTech深科技”、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