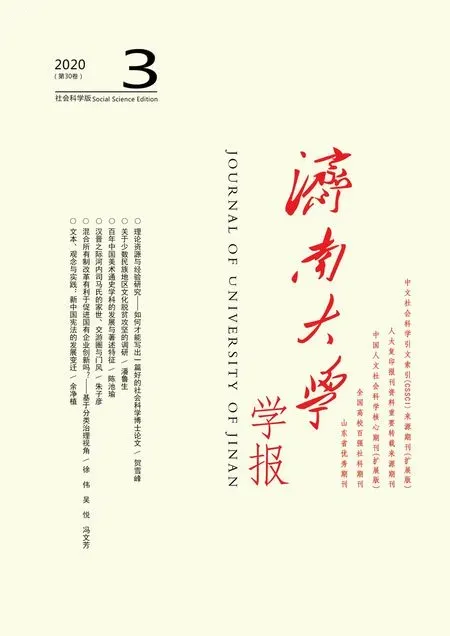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诗歌功用的作者之维
张 英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本文采用的“诗歌”概念是广义上的,是指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形象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具体到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和辞赋等有韵之文的一部分。提起文学功用,人们大多默认其指向的是读者,以及由读者所连结的社会。无论是中国文论中的“兴观群怨”“美刺”“教化”还是西方文论中的“净化心灵”“寓教于乐”都是如此,就连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等影响而主张的“非功利”“无目的”,也是将文学的功用指向作品对于读者在审美教育、情感慰藉方面的功用,而并非指向作者。实际上,作者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和第一读者,与作品的关系极为紧密,文学之功能作用,在辐射读者之外,理应反照作者一维,且波及作者所属的时代与社会。另一方面,如张炯教授所说:“以往,人们在讨论文学的功能与价值时,常常只讨论文学普遍具有的功能与价值,而忽视不同文体、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会具有各自特殊的功能与价值。”(1)张炯:《文学功能与价值新探》,《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8页。就中国古代诗歌而言,其功用便与同属抒情文学的词、曲有所不同,与戏剧、小说这种叙事文学更是差异极大。本文所探讨的,正是中国古代诗歌功用的作者层面,其中既包括对作者的功利性效用,也包括非功利性的价值,明确这些功用,才能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某些特殊性产生的原因。当然,即便是只针对作者,诗歌的功用也无法尽数,但究其要者,包括以下四端。
一、登第科举,晋身仕途之用
以诗歌作为科举晋身之用,是中国古代诗歌对于作者最为直接的功利化表现。无论是平时为应考所作的诗歌练习、行卷投赠,还是最终在考场的发挥,都指向出人头地、进入官场的目的。这种非常功利化的功用首先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有关,他们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游离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即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无恒产”有别于贵族,他们需要凭自己的本事得到君王赏识,方能获得政治地位与经济保障;“有恒心”区别于平民,平民无远志,而士人则欲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其能否实现,依然要靠君王赏识。这种阶层处境决定了古代知识分子对君王的依附性,王向远《从宏观比较文学看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特性》一文指出,和西方知识分子多出自贵族和教士阶层不同,中国传统文学的特性之一就是“作家官吏化”,“有能力的人别无选择,只有纷纷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只有跻身官场才能争得一个体面的地位。”(2)王向远:《从宏观比较文学看中国文学的文化特征》,《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第124-129页。跻身官场的途径并不单一,但从隋唐开始,最为重要的人才选拔就是科举,而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中,诗歌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诗人们写诗也就与自身的前途产生了密切关联。
这种功用无疑在唐代最为明显。根据俞钢《唐代举子行卷文体考论》,“唐代进士科起初仅试策文, 高宗显庆时始见试表和箴体, 永隆后增试杂文二篇, 往往兼用诗、赋体或箴、铭、论、表、颂诸体, 至天宝年间则专用诗、赋体。德宗建中二年后, 杂文试一度用箴、论、表、赞诸体代诗、赋体, 大约到贞元四、五年后又复旧制试诗、赋。”(3)俞钢:《唐代举子行卷文体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6-64页。可见诗赋在唐代科举中地位之重。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在地位上远远高于考察经书记忆的明经科,《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门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致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4)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进士既然如此受重视,而平均每次录取人数仅几十人,因此竞争十分激烈。且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因为不糊名,所以某年某科有谁参加考试、哪本试卷属于谁,都是公开的,这就使得主事官除了评阅试卷之外,还有参考甚至完全依据举子们平时的作品和誉望来决定去取的可能;也使得应试者有呈现平时的作品以表现自己和托人推荐的可能;也使得主试官的亲友有代他搜罗人才,加以甄别、录取的可能。”(5)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见《程千帆全集》第八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于是举子们在考试之前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文加以整理,呈送给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以增加自己进士及第的可能性,谓之“行卷”,当是时,“天下之士, 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6)马端临:《文献通考·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正如宇文所安说:“诗歌被作为入仕的资格考试,作为引荐信,作为求官书,或作为伸冤的倾诉。通过诗歌,人们能够被认识和理解。”(7)[美]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9页。
既然目的是为得到赏识,进而取得功名,行卷中的诗歌务必要展现自己的才华、见识和境界,换句话说,要展示自己的优长之处,塑造个人的正面形象,这种行为本质上与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并没有什么差别。白居易当年应举,进京之后向当时的文坛领袖顾况行卷,顾况颇为不屑,调侃白居易的名字“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开卷读其首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大加称赏:“得道个语,居亦易矣”,于是“为之延誉,名声大振。”盖因白居易这首诗一读之下少年人的蓬勃朝气扑面而来,且内中又蕴含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心与生命力,打动了顾况。李贺向时为国子博士分司的韩愈行卷时,韩愈“送客归困极,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见其首篇即《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诗句的磅礴气势令韩愈赞不绝口,“援带命邀之。”(8)张固:《幽闲鼓吹》,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0-1451页。与之相反弄巧成拙的典型是崔颢,《唐国史补》卷上云:“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乃不接之。”(9)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崔颢原诗题目为《王家少妇》,全诗为“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乃是江南民歌风味,并未凸显自我形象中的优长之处,反被李邕认定为言语轻薄,卖弄风情。由此可见,诗歌既关系到诗人前途与功名,必须谨慎对待。
宋代科举内容对唐代有所改良,宋神宗熙宁四年将诗赋与经义分为两科:“神宗始罢诸科, 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 其后遵行, 未之有改。”(10)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04页,第427页,第3631页。到钦宗靖康元年变成“复以诗赋取士”(11)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04页,第427页,第3631页。。南渡后诗赋和经义考试颇无定数,到建炎三十一年始以两科分试为定制。“礼部侍郎金安节言:‘熙宁、元丰以来, 经义诗赋, 废兴离合, 随时更革, 初无定制。近合科以来, 通经者苦赋体雕刻, 习赋者病经旨渊微, 心有弗精, 智难兼济。又其甚者, 论既并场, 策问太寡, 议论器识, 无以尽人。士守传注, 史学尽废, 此后进往往得志, 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请复立两科, 永为成宪。’从之。于是士始有定向, 而得专所习矣。”(1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04页,第427页,第3631页。由此可见,宋代科举考试中诗赋比重有所削弱,但仍然是科举的重要内容。就行卷情况来看,宋初沿袭唐代科举方式,行卷之风仍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曰:“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13)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页。柳开、田锡、王禹偁等人皆有过行卷之举。到真宗、仁宗以后,进士考试采用了“糊名”“誊录”的方式,行卷风气有所减轻,但仍然广泛存在。钱建状《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宋代进士行卷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在北宋元丰年间,士子为应举而向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行卷,仍是一个客观事实。以至大观年间,举子行卷甚至形成了一定气候,朝廷不得不下明令禁止。”文中还分析了宋代进士依旧行卷的原因:“考官如果通过行卷欣赏自己,便可能进而愿意关注和熟悉自己的文风,从而存在将自己从万千试卷中识拔出来的可能性。”而考官依据举子行卷文风辨认出糊名后的试卷作者的能力,“在特定的语境下,往往被人为地修饰成另一种光环,如知人、精鉴等等”。甚至直到南宋,“考官通过文风辨识考生姓氏的事例仍然存在。《宋史》吕祖谦本传载 :‘(吕祖谦)尝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考试礼部,得一卷,曰 :此必江西小陆之文也。揭示,果九渊,人服其精鉴。’”(14)钱建状:《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
元代异族统治下排斥汉人,一度废除科举,诗文无用,大批知识分子流向市井谋生,成就了元杂剧的辉煌。到明清,则颠覆了唐宋以来以文学为考试中心的传统,虽乾隆十二年以后在科举中加入“试帖诗”,但没有改变八股取士的基本格局。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从表面上看, 明清时期从事诗文创作的群体十分庞大, 而实际上真正专力于此并取得较高成就的, 往往限于摆脱了科举制约的两个群体:一是‘早得一第’者, 二是‘穷老自放’者。……在根本上中断了唐宋时期群众性参与的基本格局。”(15)付琼:《科举背景下的明清教育对文学的负面影响》,《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由此可见,诗歌对于作者的科举晋身功用的大小,与诗歌写作之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诗歌创作的风向标。
中国古代诗歌本有“诗言志”的传统,也即宇文所安所指出的“非虚构性”的特征(16)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传统诗学:世界的征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因此诗人的自我形象在诗歌中有鲜明的表现。而在诗歌作为“仕途敲门砖”之用的情况下,出于对个人前途利益的考虑,这种“自我形象”则难免有“精心设计”的成分。我们绝不能说诗人们言不由衷,但可以肯定的是,诗人一般不会在诗歌中呈现于自己不利的一面,他们会避重就轻,在以诗歌彰显才华之外,呈现一个符合官吏选拔标准、符合士大夫阶层品味的,政治正确、道德高尚、审美雅致的自我,对人性本身的表现和刻画达不到十分深刻的程度。正如王向远所说,中国古代诗人们“对于人灵魂深处的犹疑彷徨,矛盾冲突,精神痛苦,对于人的善恶双重人格、病态心理、心理与行为的分裂、自我内部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下意识行为等人性的,人类的灵魂的全部复杂性……表现得很不够。”(17)王向远:《从宏观比较文学看中国文学的文化特征》,《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如果我们考虑到诗歌对于作者所承担的这种与仕途密切相关的功利性作用,就会理解这一情况的由来。而这一点,在以下三种功用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二、汇入群体、融洽关系之用
虽然古代诗歌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传播的范围也似乎相当广泛,有的诗人甚至会自诩“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18)董诰等:《全唐文》,第67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2页。但必须承认的是,大部分诗歌,主要是流传于士大夫精英文化圈内部。这个精英文化圈是一个“文学共同体”,只有在这个共同体内部,诗歌才能够被正确的理解和阐释(19)参见李春青:《论中国古代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及其阐释学意义》,《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对于诗作者来说,诗歌在这个文化圈中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手段,是“诗可以群”在作者层面的用处:通过诗歌,诗人能够汇入群体,得到这个群体中他人的了解、认可和赞许;也能够在亲朋师友以及同僚之间促进更为密切、融洽的关系。这种以诗歌为媒介的社交实际上包括了上文所说的科举之前以“求提携、求赞赏”为目的的行卷。而在并未实行科举制度之前,也大量存在以诗文进献权贵以求得到赏识、提拔的类似行卷的行为,如鲍照献诗于临川王刘义庆便是如此。除此之外,诗歌的社交之用更为集中地表现在应景诗(20)这类诗歌在学术界并无同一的命名,这里按照宇文所安《初唐诗》中贾晋华翻译时的命名“应景诗”。和酬和诗中,前者属于群体性书写,后者属于互动式书写。
应景诗写于特定的群体集会场合,如宫廷宴会、文人雅集。这类诗歌在题目或题材内容上有限定性,往往是众人同题或同类题材,与集会主题、时令节序等密切相关。在写法上也有一定之规,多限定体裁,限定韵脚,并限定写作时间。在明确的限定之外,还有潜在的约束,那便是符合当时士大夫精英阶层审美品味的辞藻和风格。因为这些诗歌的读者对象是与诗人处于同一文化层次并交往密切的朝臣(有时还包括皇帝),有着相互的利益往来和共同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或者说,因有着相互的利益往来而必须拥有共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宫廷应景诗当中,由于帝王的参与而需要格外谨慎。宇文所安《在708年如何写宫廷诗:形式、诗体和题材》一文中说:“宫廷诗是一种规范化的艺术,体现在结构、主题范围、词汇范围及摒弃强烈的政治道德和个人感情。”(21)[美]宇文所安:《在708年如何写宫廷诗:形式、诗体和题材》,《国学》,2013年第3期。所有的这些限定,目的是开展符合特定场合氛围的诗歌竞赛、品评和娱乐。最末完成或不能完成者往往要罚饮一定数量的酒,而能够承命迅速写出优秀的诗篇者则可得到奖赏和众人的艳羡。应景诗的多重限制并不利于真正优秀作品的产生,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它们抑制勇于创新的诗人,扶助缺乏灵感的诗人,把天才拉平,把庸才抬高。它们允许普通的朝臣写出诗来,能够不太难堪地在最优秀的宫廷诗人的作品旁边立住脚跟。”(22)[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页。这一点正是由应景诗的社交目的所决定的,对于参与宴会,写作应景诗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身份并非是纯粹的文学家,也不抱有纯粹的文学目的,诗歌在这里仅仅是手段,以之在这个精英阶层的小圈子里按照规则应对自如,便汇入了群体,得到了归属(归属往往意味着潜在的利益),如果能更进一步以才思敏捷得到赞誉、认可,便已达到了这种社交的最高目的。
酬和诗又可称为“酬唱诗”“酬赠诗”“寄赠诗”“赠答诗”,一般来说,其期待读者范围比应景诗小,酬和对象一般是与诗人本身交往密切的同僚、亲属、好友等,起到的往往是更实际也更紧密的社交功用。这类诗歌数量众多,其写作有各种因由,其中较为常见者有三类。其一是同僚赠别。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便属于此类,其中有“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之句,道出古代文人漂泊于仕途的常态,而同僚以诗赠别,也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饯别礼仪。此类诗歌中有大量佳作,悲壮者如“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豪迈者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对于离别者的惜别与勉励背后,是对自身身不由己漂泊不定的命运之深切体察和悲叹。但赠别诗中也有很多只是官场中惯例的应酬,其文学水准并不是诗人所着意追求的,质量高者固然更佳,但符合礼仪的平庸之作,也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如曾巩《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就谈到三馆秘阁中送同僚赴外任的惯例:“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浸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2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3 册卷一二五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 页。在这种社交场合中更重要的不是诗歌的内容和诗歌的质量,而是诗人酬唱的行为,只要有其行为,便已能够符合礼仪地表达出对外任同僚的尊重。其二是以诗代信。在相隔异地的亲友之间,书信往来最为普遍,而以诗歌代替普通的文字表述,则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更为雅致也更为精妙的沟通方式。“文人之间,从唐代开始就有人认为诗歌酬答可以超过书信,到了宋代更是如此。”(24)吕肖奂,张剑:《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如苏轼在《次韵答王定国》云:“每得君诗如得书,宣心写妙书不如。”这类诗歌虽然在文学性上远远超过普通书信,但其主要功能却仍然是书信的功能,而并非全然为了抒情和审美。其三是文学上的切磋,特别是酬唱诗中的和韵诗。这些诗歌也有群体性的,特别在各类诗社当中,与上文所说的应景诗有相似之处,也有两三人之间这种更小范围内的和韵。这种文学上的带有一定游戏和竞技意味的切磋,同样具有促进酬唱成员间更密切关系的作用。
应景诗、酬和诗之外的诗歌,虽无明确的读者对象,但其潜在的期待读者群体仍为士大夫阶层。在诗人主动参与式的传播之外,通过其他各种传播途径,仍可使自己被他人所了解,从而构筑了潜在的社交基础,就如许多小说中所写的见面情景一样:“早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可以说,诗人在未入仕前,诗歌是应试的准备,是仕途的敲门砖;待入仕之后,诗歌又很大程度上成为士大夫精英文化圈中互相交流并期望得到认可的“羔雁之具”。这类诗歌数量庞大,正如吕肖奂、张剑《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一文中所说:“中国传统诗歌之所以长盛不衰、生生不息,主要取决于‘关系本位’社会的基本需要,尤其是中古以后(自汉魏始)的诗歌——多数并非出于诗人感情抒写的需要,而往往是出于人际关系交往的必要。”(25)吕肖奂,张剑:《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担负这种功能的诗歌,其中所言之“志”必然是士大夫阶层所共同认可的“志”,不可能走向深刻的人性反思,自我剖析,也不可能真正展现普罗大众的市俗世界。“在社交应酬中,酬唱者常常无法脱离尘世而显示个人的清高或孤高,处于尘世中的诗人,必须人情练达,至少需要饱谙世故,而人情世故,就是‘社会性’,‘社会性’往往显得卑俗”。(26)吕肖奂,张剑:《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三、留名后世、精神不朽之用
诗歌对作者的功用不仅表现在诗人生前,在诗人死后,诗歌还可以作为他精神生命的延续,成为后人了解他、评价他的重要线索和依据。这一点也是由中国诗歌独特的“言志”特点所决定的,“诗言志”的写作传统使诗歌切近诗人的实际生活,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在诗歌中,诗人塑造了生动鲜明的自我形象,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印记,并以此获得了肉身陨灭后精神不朽的可能性。
这里所说的“精神不朽”,与宗教文化中的“灵魂永生”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儒家文化所特有的产物。在死亡所带来的终极恐惧面前,不同文化衍生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多数宗教采取的是虚构一个死后灵魂可以归往的彼岸世界,如佛教宣扬六道轮回,善恶果报;基督教中有末日审判,天堂地狱;伊斯兰教中有天园、火狱等,在这些宗教的观点中,现世只是人暂时的居所,死后方有永恒的归宿。儒家文化与此相反,它并不主张探索死后的虚妄,而是执着于对现实秩序的整饬维持。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在积极入世的同时,难免对于死亡后未知的虚无有着更深切的恐慌,面对“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陶渊明:《拟挽歌辞》)的命运,儒家采用的是两条策略:其一是延续血脉,让后世子孙成为自己肉身的变相替代物,故孟子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辞;其二是努力让自己在世时的所作所为进入后世的历史记忆当中,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后世,精神不朽”。两者相较,古人更推重的无疑是后者,《左传》中叔孙豹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而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79页。这便是儒家至关重要的人生追求——“三不朽”。
“诗歌”本与“三不朽”中任何一项都无关。“立德”要能垂范后世,“立功”要能力挽狂澜,“立言”则是那些与“德”和“功”相关的言,是德和功的反映,又要有助于德与功的实现,纯粹文学范畴内的“言”并不在此列。故汉代扬雄晚年有悔悟之心,斥辞赋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只有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枯槁生活中写就的《太玄》《法言》之流差可作为立言不朽之策。但虽说如此,“诗歌”作为“言”之一种,至少在借助文字载体得以流传后世方面与其他所有的言并无二致。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28)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20页。,这里所说的文章便绝不仅仅限于那些立古今之言教化千秋万代的宏篇大制,具有“无穷”流播之可能性,并超越于“年寿”与“荣乐”之限制者,显然包含了各类文体。曹丕又说:“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29)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20页。在曹丕看来,以“文章”作为不朽之计,比“立德”与“立功”更具有优势,因为“文章”可以实现“自控”,不需要倚靠良史的评判,也不需要借助权势的力量,只要你手里有一支笔,你就有可能创造出不朽的可能性来。
更近一步,“诗歌”在所有的“文章”类别中,又独具精神不朽的优势。诗歌是“言志”的,狭义的“志”是与那些与家国命运相关的志向、抱负;广义的“志”又与“情”界限模糊,包含了人对人生、对世界的一切洞察、感受。细小微妙者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暧昧恍惚者如“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廓落玄奥者如“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均包含在内。而不管这志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总归是出自诗人的内心,因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性较强的文体相比,诗歌与诗人自己的人生更为贴近,也更为生动鲜活。直至今日,那些诗人的音容笑貌、所思所想借助他们所写就的诗歌仍然能够跃然于纸上。我们读“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燕歌行》)、“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杂诗》)、“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大墙上蒿行》),看到了一个虽身居高位却内心多愁善感的曹丕;我们读“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白马篇》)、“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赠白马王彪》)、“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七哀诗》),看到了曹植从一个天性勇武的俊爽少年渐渐走进了人生的困境,却仍然不惜以低到尘埃里去的姿态作祈求与挣扎。我们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看到了李白的热望与狂傲,也看到了他的尊严、底线与有所不为。我们读“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看到了杜甫的忠爱与厚重,读“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又看到了杜甫细致有味的日常生活。我们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看到了混迹于欢场的杜牧失意而愧疚的复杂内心;读“秋风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看到了虽身体孱弱却呕心沥血的李贺几乎咬紧牙关的悲愤与不甘。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提到:“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一种是所谓一般的不朽,亲友对一个人的怀念;另一种是伟大的不朽,即一个人活在从来不认识他的人的心目中。生活中有一些途径,可以从一开始就让人面对这种伟大的不朽。当然,并不一定十拿九稳,但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就是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道路。” 中国古代诗人恰恰结合了艺术家与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身份,而他们在政坛上失意与失败又刺激了他们在诗歌中的不平之鸣,成就了艺术上的辉煌。这些诗人们,无疑是那些早已被滚滚长江浪淘尽的风流人物,但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们得到了复活与永生。然而,如果我们要问,在其作品中得到“复活与永生”的,究竟是诗人本来的样子,还是他所刻意塑造的愿意展露给后人的样子?答案一定是后者。他们知道,最终的评价者并非知道你内心所有隐秘的上帝,而是后辈活生生的凡人,他们只能依靠文字来对你进行判断,给你留下或美或骂的名声。古人一再强调“慎言”,其中一种原因,恐怕正如著名的“米兰达警示”中所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是的,诗人们所写下来的一切都将成为后世的“呈堂证供”,关系到死后声名,这种情况下,哪位诗人能够像卢梭《忏悔录》一样坦白自己的缺点甚至恶行?他们所言之“志”,所塑造的形象虽然各有其鲜活特色,但恐怕终究超不出“政治正确”“道德高尚”“审美雅致”这种涉嫌自我美化、礼赞的樊篱。
四、倾诉情感、慰藉心灵之用
杜甫曾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对于诗人来说,写诗除了写给考官、写给权贵、写给亲朋、同僚、写给后人看之外,还有很多诗是写给自己的,他们在提笔之际也许并不刻意心存目的,只为“遣兴”而已。宋人方岳有诗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人生一世不能免于事业坎坷、心灵孤独,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物不得其平而鸣”“吟咏性情”,其“言”“鸣”“吟咏”,固然可能引发他人震动,但对于作者来说,更大的功用乃是通过文字的自我倾诉来慰藉心灵。
从古代文人的仕途来说,士人阶层的依附地位和政治竞争环境使得终身得意者少,流离贬窜者多,故“发愤抒情”“穷而后工”的现象在诗坛上蔚为大观。虽然后世在评价这些诗歌时往往将其意义指向政治和道德,但实际上无论从文学传播的客观条件还是从封建集权政治的现实情况来看,“发愤”之作“上达君听”或“教化民众”的效用都较为渺茫。这些作品更直接也更有效的功用乃是指向作者(其同时又是作品的第一阅读者),使其在政治理想落空的失意中得到心灵上的慰藉。这种慰藉何以能够实现?从心理学上说,“倾诉”是缓解心理压力,打开内心郁结的重要手段。人们在向朋友倾诉时,即便得不到对方实质性的关于解决问题、打破困境的有效建议,倾诉本身就已经能够达到良好的心理调适效果。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对方在倾听中的耐心与理解,以及倾听之后对我们人生隐秘的保护,这也是合格的心理医生最基本的职业修养。如果现实中找不到适合对之倾诉的人,人们便会采用其他的替代手段去释放情感,文学创作就是其中最为合适的方法之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写作何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脱诗人的心理困境:其一,情感被有序化。在写作过程中,诗人内心郁积的情感得到了文字方式的整理和有秩序的表达,不再是混沌一团的迷雾。诗人能体会到倾吐之畅快,不复有骨鲠在喉之感。其二,情感被客观化。在写作结束后,诗人与承载着诗人情感的诗歌产生了分离。这种分离使得诗人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客观化了,当诗人在阅读自己的诗歌时,诗人能够相对冷静地审视这一情感困境而非沉溺于其中。其三,情感被审美化。诗歌的审美特性使得情感在表达中获得了审美化的改变与提升,由此而使诗人在创作和阅读中超越了现实的痛苦,而获得了审美性的愉悦。其四,诗人与作品之间产生了虚拟交流。诗歌虽然为诗人所创造,但因其承载着情感而仿佛具有生命,由此可以与诗人之间有相互的对视和交流,在这一虚拟的过程中,诗人得到了虽源于自我但却又超越于自我的,更加宽泛的包容和理解。又因为这种交流发生在自我与自我之间,与他人无涉,亦不受他人制约,由此又增加了心灵自由所生发的怡悦之感。我想这几个方面便是作者在面对桌案纸墨倾诉肺腑的“发愤抒情”背后的动力。
除事业上的“挫败感”之外,“孤独感”更是人生一大死结,这一点与现代人并没有任何不同。文学作品与影视剧制造了无数现代童话,告诉人们浪漫的爱情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美满婚姻是打破孤独困境的唯一通道,而事实上,在令人心迷神醉的书写背后,所揭示的正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古今,男女之间的美好恋情都是世上的稀有珍品。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又有三重阻碍令男女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无法成为消除孤独感的途径。其一,古代婚姻并无自由恋爱、自由选择的过程,而是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而结合,男女方之间在婚配之前,彼此之间往往不曾有任何接触和了解。这样的婚姻大概率上不会产生真正的爱情。其二,在古代社会,男女的“分型培养”使得两性之间在教育程度、家庭地位、人生观念等种种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夫妻很难成为彼此的灵魂伴侣。其三,古代知识阶层的男性回归家庭的时间并不多,在他们的青壮年时期,大部分男性是奔波于路途,辗转于各地,或漫游,或为宦,女性留守家中,仅担负着养育儿女、侍奉公婆的责任。相处的时间既少,更无济于孤独感的消除。
男女之间如此,放大到在其他各种关系之中,人们也同样存在找到“知我者”的难度。“三纲五常”所说的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中,有四种具有明显的地位差异,这使两者之间构成的是主从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人们唯一可以为打破孤独感寄予希望的似乎是第五种关系——朋友。事实上,将“朋友”关系列入“五常”当中,与其他四种具有鲜明的家族观念与血缘连结的关系并列(君臣关系实际上是家族观念在政治中的转型和隐喻),就已经表明古人对这种关系的重视程度。人们对这种关系之寄予厚望到了一种理想化的程度,甚至具有某种在自恋基础上的道德洁癖、精神自虐的意味。朋友应该是“知己”,是“知音”,是能够听我言说懂我心意,能够解读我表达中所设置的复杂密码,能够超越语言及其他任何一种表意手段的局限,直接触摸我心灵的人。钟子期对俞伯牙琴声“高山流水”式的解读堪称“知音”的典范,而俞伯牙在钟子期死后弃琴不奏也就成了对朋友最好的酬谢表现。高山流水的故事表现了人们渴望被理解的需求,“在说者和听者的关系中,……听鼓励了我的说,听者的存在证明了我的存在,证明了我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听者使我的存在对象化了,它内蕴着人的一种同一性证明的心理需要。”(30)蔡翔:《渴望理解——中国文学中的“知己”问题》,《文艺评论》,1992年第5期。此外,朋友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一旦出现三观不一致,“道不同,不足为谋”,于是管宁和华歆“割席分坐”成为一种值得称颂的模范行为;朋友应该是可以赴患难而不惧生死者,故司马迁感于身世而盛赞游侠,“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报,身坐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31)龚鹏程:《大侠》,台北:锦冠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古人一方面渴求知己,“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鲍溶:《壮士行》),另一方面又陷入了知己难求的自怜自伤。李贽说:“唯天下无真相知,则虽谓天下无交可也。故有神交于百世之后,而不能不痛恨于当世。”虞仲翔曰:“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可以不恨。士之难交,不益宜叹。” 张彦直曰:“其有知我者,胡、越可亲。苟或不然,毋宁独立。”(32)李贽:《初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3页。
渴望知己而知己难求,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与作品之间的虚拟交流可慰藉孤独之外,他们转向了当下之外的辽阔时空,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于“异代知己”的讴歌、怀想与期盼。王绩黄昏时独立东皋,与从事放牧、打猎的劳作者形同陌路,寂寞地追忆着伯夷叔齐:“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李白于月下徘徊,追慕着谢朓的文采风流,将他人全不放在眼内:“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长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白居易敬慕陶渊明:“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诗人在面向过去,与古人为友的同时,又热切盼望自己死后能够得到未来某位知己的关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便有这样的期许:“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面向过去的追思仰慕,与来自未来的渺茫回应,通过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构筑了一种虽虚幻却有效的慰藉。另一方面,诗人们又转向了自然山水,创造了“山水惊知己” 式的物我交融之境(33)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语:“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502页。。山水诗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儒家“比德”式的山水道德观和玄学家“山水以形媚道”的阐述模式,形成了心物感通、心与物游的境界。在诗人们眼中,自然山水与人一样具有生命和情感,可与之互诉肺腑、倾心交流。李白可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独坐敬亭山》),王阳明说“正需闭口林间坐,莫道青山不解言”(《次栾子仁韵送别四首》)。诗人的情感既兴发于外物,又投射于外物,“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甚至“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诗人们就这样在诗歌中把自己重置于万物之怀,消解了孑然孤立、知己难求的悲哀。
当然,除了“挫败感”和“孤独感”之外,人的情绪复杂多样,在此不能尽数。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种以“遣兴”为目的,看似“独白”“自语”式的诗歌,也仍然有可能同时具有前三种功用。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兴”都可以用诗来“遣”。换言之,诗歌所能够言说的,基本上是诗人认为可以传播于当时和后世的内容。诗歌所不适合言说的,便有其他的文体来补充,如词、曲等等。
结语
综上,中国古代诗歌在作者层面主要有四重功用:其一,登第科举,晋身仕途之用,这类诗歌的主要期待读者是考官以及可以提携自己进入仕途的权贵。其二,汇入群体、融洽关系之用,这类诗歌的主要期待读者是各种群体集会活动的参与者以及同僚、亲友。其三,留名后世、精神不朽之用,这类诗歌的主要期待读者在后世。其四,倾诉情感、慰藉心灵之用,这类诗歌最重要的品读对象是诗人自己。这四种功用并不能截然分开,其背后的期待读者也往往是混杂的。可以看出,对于古代诗人来说,写诗能够给自己带来多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或许并不是诗人写诗的明确动机,但却在事实上具有这样的功用效果。而这些功用反过来一定作用于诗人的创作,构成中国古代诗歌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如诗歌内容与诗人生活的密切关联、诗歌所塑造诗人自我形象的群体性与片面性特征、诗歌中抒发情志的限定性等等。关于这些,笔者还将另外撰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