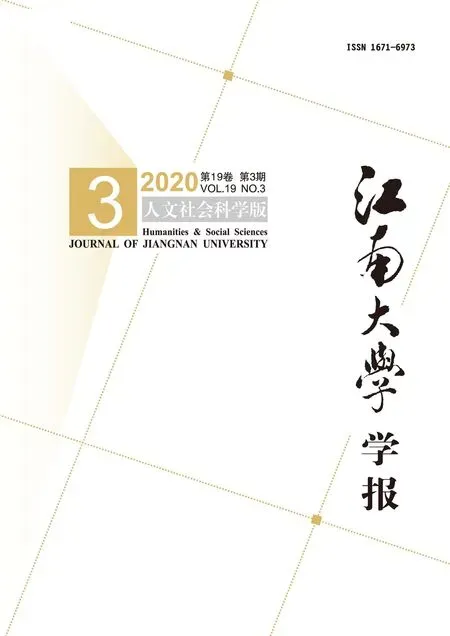不“格义”,怎么办?
何玉国
(天津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222)
一、引 言
作为异质文化的佛教,传入我国初期,彼时并无印刷术或其它可以凭借的手段,只能依赖口口相传:
“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1)原文出自《大正藏》,本文转引自顾伟康:《佛经翻译与“格义”时代的跨越——以中西哲学比较为前提》,见《学术月刊》2009年3月,第30页。。
“仰寻先觉所说,有六十四书,鹿轮转眼,笔制区分,龙鬼八部,字体殊式……西方写经虽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国往往有异”(2)原文出自《大正藏》,本文转引自顾伟康:《佛经翻译与“格义”时代的跨越——以中西哲学比较为前提》,见《学术月刊》2009年3月,第30页。。
根据材料二,正是因为口口相传,口授相付的传播方式,使得虽然同属印度梵文的佛教的六十四本典籍,流传至西方三十六个国家竟然皆有不同之处。然而,口口相传,记忆力是关键,因此,齐梁时代的僧祐法师(445-518)在听他人口授传诵的同时,还要用民间药方检测一下对方“记忆力如何”,以免“遗谬”:
“耶舍先颂《昙无德律》,伪司隶校尉姚爽请令出之,姚兴疑其遗谬,乃试耶舍,令诵民籍药方各四十余纸,三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众服其强记”(3)原文出自《大正藏》,本文转引自顾伟康:《佛经翻译与“格义”时代的跨越——以中西哲学比较为前提》,见《学术月刊》2009年3月,第30页。。
所以,即使到了东晋,道安大师(314—385)还是不禁感慨:“音殊俗译,译人口传,自非三达,胡能一一得本缘故乎?”(4)原文出自《大正藏》,本文转引自顾伟康:《佛经翻译与“格义”时代的跨越——以中西哲学比较为前提》,见《学术月刊》2009年3月,第30页。。
之所以转引如此多文字,意在说明:此乃佛教初传时的困境,以及在我国本土引起的焦虑和反思。然而,这只是停留在“僧人与僧人之间”的“僧讲”层面[1],接踵而至的“俗讲”——“僧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传播时,困难更是重重。
彼时的佛教传习者,该怎么办呢?会怎么办呢?这就是作为“中国学者企图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第一种方法”[2]231——“格义”诞生的语境。作为概念的“格义”,在20世纪30—60年代,曾引起过陈寅恪、汤用彤、吕澄等人的关注和研究。
然而,在21世纪初,随着老庄研究学者刘笑敢提出“反向格义”(或“逆格义”)(5)据刘笑敢言,台湾学者林安梧曾提出“逆格义”,2004年刘笑敢受其启发,提出“反向格义”,但刘笑敢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提议“反向格义”在2006年。但又据彭国翔调查,林安梧并未提出“逆格义”,其发明权应属他人。当然,在“反向格义”之前,还有其它类似说法。从公开的学术文献来看,赵敦华提出的“双向格义”是2003年,但赵敦华的“双向格义”并未引起太多的学术关注,相反,自从刘笑敢2006年在《南京大学学报》公开提出“反向格义”以后,有关“格义”问题才引起了学术界的重新讨论。参见:赵敦华:《中西哲学术语的双向格义——以〈论语〉为例》,《中国哲学史》2003年3期,第25-31页;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人文版)2006年2期,第76-90页;彭国翔:《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7年4期,第77-87页。以后,有关“格义”又引起了新的关注和论争(6)在2006—2012年间,刘笑敢,张舜清,张汝作,彭国翔,方旭东,谢遐龄,白欲晓,陈少明等人分别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批评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持中立者亦有之。
继续“格义”,固然有理(后文详论之);然而不“格义”,我们该怎么办?“后格义”时代,我们应何为?
本文在借鉴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论证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异质文化间交流方式的“格义”既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又有今后继续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反向格义”也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辅助“合本”观念,倡导“问题意识比较”,应该成为“后格义”时代中西研究的新方向。
二、“格义”:异质文化之间交流的必然选择
接续上述问题:佛教传至我国,仅靠口口相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然而,这只是在“文本记录”或文本翻译(从口传梵文到书写汉文)方面,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如何释义?
据史料记载,最早将印度梵语佛教翻译为汉文的著名人士,有西域安息人安世高(约2世纪)[2]235和西域月支人支娄迦谶(约2世纪)。前者所译主要在小乘佛教,偏重于“禅数”;后者主要在“般若”;“禅数”强调“理论”,重“养气”;“般若”既强调“理论”,又强调“传习”;显然,这些“名相”“事数”都是中国传统典籍中所没有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然也是无法理解的[3]。那么,如何释义?这必然是佛教传入我国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关于此,常被后世学者引用的一段材料,或可以予说明:
“法雅,河南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咨禀。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4]152-153。
此段材料出于梁代释慧皎(497—554)的《高僧传》卷四《晋高邑竺法雅》。整段文字不难理解,关键在“事数”“格义”“外书”等措辞。
据佛教史家汤用彤(1893—1964)的理解,所谓“事数”也即“佛义之条目名相”;“格义”,“格义者何?格,量也。盖以中国思想,比拟配合,以使人易于了解佛书之方法也”[5]178;而所谓“外书”,指“中国‘人(入)世间’的著作,非宗教的文献,用来对比佛教出世间的学说。再则,据印度和中国佛教(一般)的观点,恰当地称佛教经典是‘内书’,中国原有的(引者注:人世间存在的)著作是‘外书’”[2]232。
因此,“‘格义’是一种用来对弟子们教学的方法”,是“用原来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习)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2]232。简而言之,所谓的“格义”就是“把佛书的名同中国书籍内的概念进行比较,把相同的固定下来,以后就作为理解佛学名相的规范。换句话说,就是把佛学的概念规定为中国固有的类似的概念”[6]。而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乃最有以内外相比拟之资格者。其弟子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则善诱之方,应在使其由世典以悟入佛理,故用格义,外典内书,递互讲说,以使生解也”[5]179。同时,由于法雅的弟子们是中国人,而且对中文(原有)的概念已经有所了解,所以法雅教他们用已经了解的中文概念,去理解佛教思想,去接近佛教典籍[2]232。这样就完成了有关佛教典籍的“如何释义”问题。
这样的“释义方式”在彼时应该颇为流行,陈寅恪曾言“盖晋世清谈之士,多喜以内典与外书互相比附”,“格义”作为“僧徒之间”的一种具体之方法,“虽罕见载记,然曾盛行一时,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7]166,彼时用中国既有文化中“五常”“五行”“五经”“格义”佛教“五戒”,用中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格义”印度的“天竺七僧”也是常有之事[7]170-172,用老庄之“无”“格义”佛教般若“性空”之学,也属司空见惯[8]。
因此,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方式,“格义”应该是一种必然选择,正如汤用彤所言“早先中国人皈依佛教(的信仰),在阅读佛教的典籍,必然会获得一种印象,有许多全新的观念和名词,那不仅带来麻烦,而且是难于理解的。因此,像(竺)法雅这样的人,从中国(原有的)书本中搜寻出相似的(概念)分析,用来跟印度(佛教)的比较,并且形成了大量的事例,应用这种方法(在讲解中),让他的弟子们在心中产生理解”[2]233。大而化之,任何一种异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流经“异域他国”,面对“本土化”“落地化”的必然要求,“格义”都将会起到一种文化上的“摆渡”作用,并为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某种“方便法门”[9],也如汤用彤所言“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辟途径。名辞多都有含义,往往为他族人民所不易了解。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及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于二族思想,固有相同处。因乃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此晋初所以有格义方法之兴起也”[5]178。
但是,作为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文化交流方式的“格义”,其影响毕竟非常有限。
“格义”主要流行于“把佛书的名同中国书籍内的概念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其本身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流弊(7)“格义”发展到后来,彼时僧人便有所觉悟和体察,认为此种“格义”“译疑变意”“于理多违”“迂而乖本”,“胡文”成“晋言”也较为普遍,但一致缺点就是不够“允惬”(允当而惬意)。具体参看: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汤用彤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241页;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1932),《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70页;顾伟康:《佛经翻译与“格义”时代的跨越——以中西哲学比较为前提》,《学术月刊》2009年3月,第30页。,影响范围也主要在西晋以前的黄河以北地区,到了东晋“格义”也便逐渐停歇,鲜为人知了(8)不过,停歇和鲜为人知的原因,在汤用彤看来,主要是因为玄学兴起,轻视比对,讲求“得意”,“格义”也自然被淘汰。参见[2]第241页。,正如汤用彤所言,随着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持续深入,异质文化与既(旧)有文化,彼此了解、认识不断加深,“审知外族思想,自有其源流曲折,遂了然其毕竟有异,此自道安罗什以后格义之所由废弃也”,“及释教既昌(明),格义自为不必要之工具矣”[5]178。
不过,以上所言是作为文化交流方式的“格义”。如果进一步作更深层次的理解,“格义”同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格义’不是简单地、宽泛的、一般的中国和印度思想的比较,而是一种很琐碎的处理,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观念或名词做分别的对比或等同;‘格’,有‘比配’的或‘度量’的意思;‘义’的含义是‘名称’‘项目’或‘概念’;‘格义’就是比配观念(或项目)的一种方法或方案,或者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对等”[2]232-233。
也正是将“格义”理解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比配、对比的一种思维模式,汤用彤才将原本在西晋已经逐渐消亡的、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格义”,进一步上可追溯至西汉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的“人副天数”观念和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刘安(公元前179—前122)的某些思维范式,比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有言:“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10]。只不过汉代董仲舒在此“比配、对比”的“天人关系”,而不是佛教中的“梵文与汉文”之间的关系而已,因此,汤用彤进一步认为,西晋时期以法雅为代表佛教僧人的“格义”行为,不过是汉代流行了好几百年的思想模式的延续而已。
现在来看,“格义”自有其弊端,如北魏僧人昙静以中国儒家“仁、义、礼、智、信”“格义”佛家“五戒”(不杀、不邪淫、不饮酒、不盗、不妄语),认为其“大意与同,名为异耳”[7]170;着实存在不少人为的“暴力阐释”和“强制解释”。与法雅一同学习的道安法师曾就“格义”提出异议:“(释僧)先旧格义,于理多违背”[4]195,但道安也并没有摆脱“格义”的影响,其弟子依然儒家和道家经典牵强附会来宣扬佛教内容[11]。
“格义”的实际操作过程,其实也是有意将概念本身的“内涵”简化和“外延”缩小,比如儒家的“礼”原本包罗万象,涵盖人世一切,上至“戎”与“祀”,下至“生活日常”,虽然包含“饮酒”,但并非仅指称“饮酒”。当佛教僧人以儒家“礼”“格义”佛教戒律中的“不饮酒”时,这就是“格义”中比较普遍的“内涵”简化和“外延”缩小现象。再如佛教般若中的“空”,本有两层含义:“非有”“非无”。但用老庄的“无”去“格义”时,却没有了“非有”“非无”的双重含义,而只剩下了单一的“无”[9],这显然也是一种“内涵”简化和“外延”缩小现象。
但在西晋时期,“格义”俨然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释义手段和方式。其不成熟的存在形式还有“配说”,这是在汉魏时期的佛教传播活动中早已存在的事实。因此,汤用彤就指出,无论“配说”还是“格义”,都是“在汉魏时期解说(佛教)经典时经常存在使用比配中国和印度两边名词的方法,西晋竺法雅则在更大范围应用并加以系统化而已”,并且有了详细而确定的方法和较为严谨的程序步骤[2]233-234。
由此可见,“格义”最先是以一种隐性的比对或对比的思维方式而存在的。那么,显然,这种比对或对比的思维方式,是绝对不会随着佛教“格义”行为的停歇而消失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且不论陈寅恪所谓北宋以后的“格义”之“变相”与“支流”(9)陈寅恪认为,“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而“佛藏”“融通”,“亦莫非‘格义’之流也”;后禅宗(华严宗)“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之变相也”。总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1932),《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73页,第185页。,也暂不表比如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播基督“福音”,有意以中国文化中的“天”“上帝”“格义”基督教中的“天主”,以儒学中“格致”“格义”西学中的“物理”或“科学”;以老子之“道”“格义”“逻各斯”等等[12];仅以近代“革命家兼学者”的梁启超,将朱熹释义的《大学》比之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13]87,将王阳明的良知之论,比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13]166,以中国既(旧)有哲学“主动比附”西方哲学的做法,就实属“格义”无疑(10)当然,作为思维方式的“格义”也并非局限于哲学领域,就笔者所知,地理学界、法学界都有显著体现。参看:唐晓峰:《“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9年2期,第81-91页;喻中:《格义的再现:法家学说与法学对等关系之建构》,《现代法学》2017年4期,第3-18页。。
因此,本节结论认为,无论是作为异质文化之间交流方式的“格义”,还是作为隐性的比对或对比思维方式的“格义”,其既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格义作为佛教讲经方法被认可的主要依据,是基于佛教与儒道经典中的相似性,这种教学方法以求同为主要价值取向,‘外典佛经递互讲说’的目的即在于具体分析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14]。同时,其又有今后继续存在的现实必要性,除非世界文化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完全“同质化”(11)至于有人认为,“特定背景下滋长的特定文化有其特定的内涵。不同的文化固然基于人类的共性而有契合映照的地方,但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是不能抹杀的。中华文化是一种独立产生、发展且在质上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有文化”,“我们反观今日之作为言‘道’方式的‘格义’(引者注:即后文将要详细论述的‘反向格义’),则完全是今之某些学者对自我文明自卑心理的体现”(参看张舜清:《对“格义”作为言“道”方式的反思》,《学术论坛》2006年6期,第22-35页)。笔者认为,将“反向格义”视作一种民族自卑心理,不免有些“上纲上线”夸大其辞了。当今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更侧重于交流的一面,在相互激荡中,共同面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努力筹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每一个文化主体(即人),都应该积极迎接和接受优秀的异质文化,就此而言,目前人类面临的文化大传统,是“三四百年以来居于优势地位而主导当今人类的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传统”(参见:邓辉:《“反向格义”与现代中国的“小传统”》,《探索与争鸣》2015年12期,第111-115页)。难道我们要拒绝这一“文化大传统”?那岂不是又要重新陷入“固步自封”的地步?由此可见,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反向格义”等同于“自我文明(化)自卑心理”。我们不能反对“格义”,而是要反对简单、粗糙、不“允惬”的“格义”。这也是本文的主张和观点。,但即使这样,作为思维方式的“格义”,也必然存在于个体的“私人经验”之中(12)即使世界文化实现了“大同”(同质化),我们每个个体对于这种“大同文化”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不会完全一致的,那么,人与人之间要“共享”这种感受和体验,就需要用到“作为思维方式的‘格义’”,用我们日常的用语来表示就是“你说的情况,我不太理解,不过是不是就像……”,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上的“格义”,用我们中国本土的语言来说就是“譬喻”——文化内部的一种“格义”。。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并且不可以忽略“格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或思维方式其本身固有的弊端,因为,从佛教本身而言,格义显然“有将佛法混同为世间学问的危险倾向,因而会导致中国佛教的变形和异化”[14]。
三、不“格义”,怎么办?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以往哲学研究中的依傍西学、唯“西”视瞻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路径的反思,刘笑敢依“格义”提出了“反向格义”(或“逆格义”)的概念。
就“反向格义”(或“逆格义”)本身而言,刘笑敢认为,“反向格义或许可以分为广狭二义。广义可以泛指任何自觉地借用西方哲学理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国哲学的做法,涉及面可能非常宽,相当于陈荣捷所说的‘以西释中’。狭义的反向格义则是专指以西方哲学的某些具体的、现成的概念来对应、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或概念的做法”。显然,刘笑敢是偏向于狭义的“反向格义”理解的,不过,其又强调“当然,广狭二义之间也难有截然可分的界限。对狭义的反向格义的反思应该会对广义的反向格义之认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广义的反向格义范围、做法、结果会复杂和丰富得多,决不是狭义的反向格义所能代表和涵盖的”[12]。
同时,刘笑敢还在他处强调:“简单地说,除了方向相反以外,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的、启蒙性的、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的‘反向格义’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却是学术性的、专业性的,是提高的需要,是长期的方法,而不是工具性的权宜之计”[15]。
由此可见,刘笑敢所谓的“反向格义”主要有二个特点:1、“反向格义”的概念是依据传统“格义”而言的,“反向格义”的核心内涵是以“西方哲学”“格义”“中国思想文化”;这与传统“格义”的“以‘中国思想文化’‘格义’西方哲学”刚好“方向相反”。2、“反向格义”的“双方”是“概念对概念”,也即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格义”中国思想文化的“概念”(13)至于“反向格义”的其它方面,诸如是不是“长期的方法”?是不是“权宜之计”?这两个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刘笑敢认为“事实上,只要是透过西方的哲学概念,特别是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的对立二分的概念体系来透视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即使没有政治压力或意识形态干扰,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或尴尬”,“中国也有很多成对的概念,但这些成双成对的概念之间是pair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分离的关系,因此,用西方近代的哲学概念来‘格’中国古代思想之‘义’总是不能契合”[12]。
如果笔者以上的理解无误的话,那么,虽然赵敦华提出的“双向格义”在前,彭国翔提出的“援西入中”在后,但其二者基本上都与刘笑敢的“反向格义”存在着涵盖关系,也即刘笑敢的“反向格义”只是赵敦华的“双向格义”(14)赵敦华认为,“既用西方哲学类比中国传统哲学,又用中国传统哲学类比西方哲学的解释方法”,这就是“双向格义”,简单说就是“用西语‘格’汉语、用汉语‘格’西语”。那么显然,刘笑敢的“反向格义”就是赵敦华“双向格义”的一个方面,即“单向格义”。具体参看:赵敦华:《中西哲学术语的双向格义——以〈论语〉为例》,《中国哲学史》2003年3期,第25-31页。和彭国翔的“援西入中”的一个方面或维度(15)彭国翔的“援西入中”分正负两种模式,其中,那种以西方哲学观念和理论框架进行裁决、框置中国哲学思想内容的方法和做法,就是“负面的、消极的”“援西入中”;“‘反向格义’或‘逆格义’不过指示了其不良的一面,即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使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和特质逐渐丧失,思想内容逐渐沦为单纯被解释的材料”。由此可见,在彭国翔看来,刘笑敢的“反向格义”应该属于“‘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或者是其“援西入中”两种模式中“消极的、负面模式”。具体参见:彭国翔:《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7年4期,第77-87页。。可以说,“需要以西方哲学概念‘格义’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概念”这一点上,无论“双向格义”还是“反向格义”,或者说“援西入中”,基本上达成了一点学术共识。关于这一点,虽然刘笑敢有些听起来似乎过激的言辞(16)刘笑敢曾指出,“自胡(指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指冯友兰1930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西方哲学就成为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一日或缺的学术背景、理论指南和照亮方向的灯塔。不懂西方哲学似乎就完全没有资格谈论中国哲学……为什么研究中国哲学一定要有西方哲学的训练背景?”参看: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哲学研究》2006年4期,第34-39页。,但是从其依据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有关“思想体系”的四个判断标准和“哲学概念”的四个标准(17)“思想体系”其四个标准是:一、其思想以讨论哲学为主;二,思想有丰富的侧面内容;三、其思想的多个侧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四,其思想具有独创性特点。哲学概念的四个标准:名词化、有固定形式,用于普遍性论述,以及作为判断的主词或宾词。分别参看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第32-40页;刘笑敢:《中国哲学妾身未明?——关于“反向格义”之讨论的回应》,《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人文版)2008年2期,第74-88页。,到对哲学研究史上关于老子之道“唯心/唯物”的定性研究及其批判[12],再到其在阐释“反向格义”的弊端时认为“借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定义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术语所难以避免的枘凿不合”的观点[16],皆可加以说明,甚至还可以延伸推论:西方哲学之于刘笑敢早已烂熟于心,“反向格义”之于其思想和学术,也早已渗透融化(18)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刘笑敢将‘道’诠释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和总根据或世界统一性的象征符号,固然避免了狭义的反向格义的困难,但并没有拒绝现代哲学或西方哲学思考的洗礼”。参看:方旭东:《通过诠释以建立哲学:内在机制与困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年2期,第89-98页。。
另外还有一点学术共识就是,西方哲学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参照(19)刘笑敢曾言,“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不用西方的概念术语来研究中国哲学吗?笔者的回答是,就无意识的层面来说,就绝对的意义来说,当然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普通语言表述中都无法避免西方传入的概念和术语。但是,就自觉的学术研究来说,就努力避免套用西方哲学概念和术语来理解、定义、解释和阐发中国古代的思想来说,这是完全可能的”。接着,刘笑敢举例“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进行了说明。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究竟是否避免了西方的概念和术语?暂且不表。但由此可见,刘笑敢也认为西方哲学对于研究中国哲学不可或缺。参见:刘笑敢:《中国哲学妾身未明?——关于“反向格义”之讨论的回应》,《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人文版)2008年2期,第74-88页;其实,刘笑敢并不是彻底反对“反向格义”的,他反对的是简单、粗糙的、一味的“反向格义”,这一点上文已有所论,所以“西方哲学”亦应属刘笑敢的“参照域”,而赵敦华主张“双向格义”、彭国翔主张“援西入中”,显然“西学参照”也是应有之义。,但坚决反对简单、粗糙的“格义”也即为“格义”而“格义”的形式主义,和完全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格义”。这一点正如彭国翔所言,“以诠释者自己所掌握的某一种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为标准,去裁剪、取舍、范围中国哲学史的丰富材料,所谓‘削足适履’”;“这种‘喧宾夺主’的‘援西入中’”,“与其说是诠释中国哲学的思想内容,不如说只是利用中国哲学的文献资料给西方某一家的哲学思想提供证明。一部中国哲学史,最后不免成为某位西方神圣哲学理论的‘中国注脚’而已”[17]。
那么,在此两点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或可做进一步思考:继续“格义”——“以西方哲学概念”“格义”“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概念”,如何避免“简单、粗糙”以达到“允惬”的效果?如果“不‘格义’”——不仅仅停留在“概念对概念”的“格义”,我们该怎么办?(20)对于这两个问题,刘笑敢也曾言,“面对这种困难,我们可能只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继续借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术语,但同时指出这一西方概念用于中国古典语境时的局限和问题。另一种是尽可能不用西方或现代的现成的概念,以避免不必要或错误的理解和联想”。但显然,刘笑敢的第一个方案,学界基本上认同了,但操作方式还有差异;而对于第二个方案,学界基本上持批判态度,毕竟在“西方哲学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参照”这一学术共识下“尽可能不用西方或现代的现成的概念”,实在可能性非常小,正如学者方旭东所言“在理论上,不能保证常用的现代汉语与西方哲学概念完全绝缘。事实上,有些西方哲学概念已经渗透到日常语言当中,不再被当作特殊词汇看待,比如物质、精神,又比如现象、本质。实在说来,我们固然可以做到不使用某一支某一派的西方哲学概念与理论框架,却无法做到不使用一点西方哲学概念与理论框架。这是因为,无论你承认与否、喜欢与否……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概念与理论框架已经深深渗入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这是一个谁也遏制不了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改变的命运”。分别参看: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人文版)2006年2期,第76-90页;方旭东:《通过诠释以建立哲学:内在机制与困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年2期,第89-98页。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何避免“简单、粗糙”以达到“允惬”?从张汝伦对牟宗三“反向格义”过程(21)按照张汝伦的观点,熊十力和牟宗三是误解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然而其师徒二人又以其“误解”的“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格义”了中国古典哲学。参看:张汝伦:《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人文版)2007年4期,第60-75页。中对西方哲学“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误解,到刘笑敢对牟宗三“反向格义”的高度赞赏(22)刘笑敢认为,“我们说牟宗三的思想体系空前庞大,这主要不仅是因为他的著作卷帙浩繁,而且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横跨儒、释、道,又贯通康德与黑格尔……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牟宗三所建构的哲学体系,我们都不得不承认,牟宗三是现代中国少有的能够借助经典诠释而建构哲学体系的成功者,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在现代中国的突出代表”。誉美之词,无以言表。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6-47页。,再到赵敦华对孔子《论语》关键术语“仁、直、己、中庸”的“中-西”“双向格义”复杂性的陈述[18],不难看出,要做到避免“简单、粗糙”以达到“允惬”的“格义”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不过,学界似乎一直都注意到了陈寅恪和汤用彤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关佛教的“格义”的研究(23)目前学界有关“格义”的研究最有分量的两篇文章,还是陈寅恪的《支愍度学说考》(1932),和汤用彤的年的《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1948),不过,从汤用彤的行文来看,似乎也受了陈寅恪的影响。分别参见:汤用彤:《汤用彤全集》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而忽视了陈寅恪在同一篇文章中的佛教“合本”思想,兹摘录如下:
“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不可不辨也。支敏度与此二种不同之方法,间接直接皆有关系。……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7]181。
“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附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当日此二种似同而实异之方法及学派,支敏度俱足以代表之”[7]185。
“前所言之‘格义’与‘合本’皆鸠摩罗什未入中国前事也。什公新译诸经既出之后,其文精审畅达,为译事之绝诣。于是为‘格义’者知新译非如旧本之含混,不易牵引附会,与外书相配拟。为‘合本’者见新译远胜旧文,以为专据新本,即得真解,更无综合诸本参校疑误之必要。逐捐弃故技,别求新知。所以般若‘色空’诸说盛行之后,而道生、谢灵运之‘佛性’‘顿悟’等新义出焉。此中国思想上之一大变也”[7]186。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原文抄录,其用意主要有三:其一,在佛教东传过程中,“合本”是与“格义”相伴而生,或者说“合本”就是同一文本经过不同人的“格义”后形成的“大同小异”的诸多本子的“合集”,其存在是以备其它参读人员(或研究人员)作为“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以尽可能克服“格义”的弊端;其二,正如佛教东传过程作为文化交流和文本解释活动的“格义”,我们可以将其进一步引申理解为一种“比对和对比”的思维方式一样,“合本”本义是佛教信教人士编撰整理的“‘同本异译’文集”(“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但我们可以作进一步引申理解,认为是一种“多方参照、比对求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其三,今日学界所谈论的“格义”或“反格义(逆格义)”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弊端,在佛教“格义”的环境中也存在着,所以今日所谓对“弊端”的种种探讨,其实也可以回归到“合本”的立场上,也即无论中-西概念,多方求真,“以资对比”,妄作“牵引附会”,从而真正实现“与外书相配拟”,达到于西方文化的真正交流、沟通之目的。这一点从张汝伦对熊十力和牟宗三有关“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误解的批评,也可以得到验证(24)张汝伦是通过“回到文本-再回文本-三返文本”的思路来对熊十力和牟宗三的西学“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认知展开批评的;具体做法是先“回到格义文本”——牟宗三和熊十力的文本进行观点总结,然后“再回‘被格义’文本”——回到西方哲学中相应概念诞生的最初语境,结合“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来说,就是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最初语言环境,最后“三返文本”——第三次返回到“第三方对于同一概念的‘格义’文本”——回到其它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有关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文本,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熊十力和牟宗三是误解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但是其师徒二人又以其“误解”的“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格义”了中国古典哲学。有关张汝伦的研究,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结论,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但其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却基本上与佛教东传过程中形成的“格义”和“合本”观念相互暗合。当然,这也是当下学术界大多数同仁的做法,不过在“参照多方”的过程中,悬置“先入为主”观念,杜绝“前置理解”,就是十分困难,或者因人而异了。参看:张汝伦:《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人文版)2007年4期,第60-75页。。
所以,如果以上理解基本无误的话,那么,运用“合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或可尽可能避免“简单、粗糙”的“概念对概念”的“格义”,以期达到尽可能的“允惬”境地。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格义’”——不仅仅停留在“概念对概念”的“格义”,我们该怎么办?对此,笔者认为彭国翔一文在行文过程中“点到为止”的提及一点[17],甚有创见,但囿于其运用“援西入中”概念,容易引起被人误解为重新落入“中西AB”简单比较模式[16],且大作笔端更多落于对“反向格义”的批评,本文在此承接这一创见,结合个人研究心得,对此加以申论。
彭国翔在其文中提出,“在诠释中国哲学史上各个哲学家的思想时,首先要从其自身的文献脉络中确定其固有的问题意识……可以相应援引西方哲学甚至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内容作为诠释的观念资源……西方的观念资源只有在有助于阐明中国哲学自身观念的情况下才有意义”[17]。其中“问题意识与西学资源”之关联,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创见较之以往有两点创新。
第一,“问题意识”,这一说法,虽在学界并不新鲜,但以往提法多针对于“读书要有问题意识”和“写文章要有问题意识”,但将其运用于“比较哲学”或“中西比较”或可做另外理解。
第二,“比较哲学”或“中西比较”过程,虽也偶有提及“问题意识”,但多数又最终转化为“比较的原则”“相似点”“异同点”的“简单比较模式”序列中的“问题问题”,比如前文所言的,牟宗三、熊十力所谓的“中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宇宙论和形而上学’问题”[19],这样研究的结果就不免有沦落为“A与B”的简单粗糙比较模式,这是一种“A与B(是)怎么样”“问题比较”,举例来说,就像日常考试中“简答题”,不免是一种“罗列要点”的作答方法,而现在提出“问题意识”,就像日常考试中的“论述题”,不仅要问(1)“A与B(是)怎么样”,还要问(2)“为什么(是)A与B(而不是其他)?”、(3)“(是)A与B(比较)然后怎么样”。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误的话,这就是彭国翔所谓的“西方的观念资源只有在有助于阐明中国哲学自身观念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一语的内涵。
当然,彭国翔提出的比较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还可以做延伸或扩大一点的理解,那就是“不同文化语境中‘共同(通)性问题’”。把原有的“A与B”,不再是作为概念的“A”和作为概念的“B”之间的“比较”,而是“作为文化语境A”和“作为文化语境B”中“共同(通)性问题”之间的“比较”,这就将旧有的“比较意识”和“问题意识”引向了更深的层次。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发现“不同文化语境中‘共同(通)性问题’”,这就是彭国翔所谓的“可以相应援引西方哲学甚至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内容作为诠释的观念资源”中“相应援引”的“引介点”,也即从这里——“不同文化语境中‘共同(通)性问题’”来“援引”“西学资源”。关于这一点可以笔者的研究,作一个简单概说。
众所周知,以欧洲概念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其逻辑思维核心就是“‘感性’与‘超感性’的二元对立”[20],用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说法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21]。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君临天下的时候,这种思维模式就遭到了各方挞伐(25)可以以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海德格尔为例。总之,作为欧洲概念模式的“二元对立”,“非西方国家把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规范力量’完全偶像化、极端化,顽固地坚持‘用欧洲语言来表达所探讨的事情’,‘把所谈的一切都欧洲化了’。其结果是,‘欧洲式的’‘道说’‘摧毁’了‘去道说所讨论的内容的可能性’,最终导致其他地区诸如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就被彻底掩盖,把自我的丰厚传统和优秀文化‘贬低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并且丢弃在另外一种所谓‘格格不入’之中”。参见:何玉国:《当海德格尔与老子研究相遇》,《理论月刊》2018年2期,第48-53页。,但是也有人认为即使其弊端显著,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代替,毕竟“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不能在一种明确的秩序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22]。这就是一种“格义”思维、一种隐性比较,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思考:我们必须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吗?如果有必要,那么是否合适,是否恰当?如果不必要,那么,我们有没有可以替代的“认知方式”?笔者通过对老子《道德经》文本的分析,提出以“体验-回溯”为研究路径,重新审视“欧洲概念是否必要和合适”,重新探讨开启“道说(论)”方式的新的可能性,规避以西方本体论、价值论、存在论和形而上学论等概念和内容“简单、粗糙”“格义”中国哲学的弊端[23]。
再比如,在西方理论资源里,“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一直是理论的核心问题。但到了后现代主义这里也成了批判的“虚假问题”[24]。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人为规训”一说[25]后,“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也不免沦为“规训产物”的定论。但是“文学”是如何被“规训”的?这个问题,西方世界没有人研究过;中国文化中,虽然文献浩如烟海,但也缺乏详细记载,不过,将“不同文化语境中‘共同(通)性问题’”——“文学”是如何被“规训”的——作为“援引”“西学资源”的“引介点”,可以通过以孔子“在陈绝粮”这一“历史事实”在后世文本中的“几经翻转”的研究分析,认为“文学作为‘史’之余、作为‘非史’之外的存在物(如不可能的事,甚至包括丑闻、丑恶等)的‘寄存方式’而存在;部分则来源于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规训和惩罚’机制,同时也是后者的不断强化和引导,成就了今天所谓的‘文学之为文学’,而所谓的‘文学性’‘文学边界’等基本问题不过是现今学者视野内的问题罢了,它们绝对不是‘文学之为文学’亘古不变、千秋万代的根本问题”[26],从时空并置的角度,探讨了“‘文学’是如何被‘规训’”的可能性。
再比如,在世界文化范围内,存在着许多“难以言说”但又“不得不说”,可是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比如西方语境中的“‘上帝’”问题,康德的作为认知的界限的“物自体”问题;东方语境中的难以界定的佛教中的“空”,和以中国文化的老庄之“道”(含“无”)等等,这是一个具有共性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问题。西方有资源可用,比如“隐喻研究”“象征理论”,但其理论资源是零散,没有集中在一个理论家身上的系统言说,我们可以用来研究老子“‘道’论”,将其言简意赅、“体验-回溯式”书写方式加以细微化、理论化的同时,发掘老子“‘道’论”所具有的既有“西学资源”所没有的内容,那就是“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笔者认为老子“正言若反”的“‘论’道”句式表达,“既达到了‘言道’之目的,又给体道者指明了方向。有‘言说’兼‘实践’,这是中国经验对世界问题的有益探索,也是中国先哲对世界类似问题做尝试性回答的积极贡献”[27]。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哲学”或“比较研究”的最核心问题:“比较是为了什么?”如果说以前的“(因)为什么比较?”是为了确定“比较对象”或“比较点”——或者“可比性”的问题的话,那么,现在问“比较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满足“学术共同体”的根本目的:为了借鉴和汲取外来哲学(他者)有益成分,充分发展本民族哲学,丰富本民族“文化经验”,积极回应和尝试性解答共同(通性)“世界问题”,这也是世代学人的共同信念、理想和目标。
总之,佛教东传,为了“得意”,“格义”盛行。但作为异质文化之间交流的必要手段,“格义”以中国旧有观念类比西学的释义方式,并未绝迹。20世纪,随着学术现代化观念的不断觉醒,作为“格义”的衍生范畴,“反向格义”(“逆格义”)成为主导,这种以西学观念框定、摆置中国学术的做法,在21世纪初,受到了学界广泛探讨。本文通过追本溯源,文献考证,认为“格义”依然有存在的必要;而“反向格义”虽然本意是指“概念对概念”的“比较研究”,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但是辅助以“合本”观念,也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同时,本文借鉴学界前辈研究,倡导“问题意识比较”,认为其应该成为“后格义”时代比较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