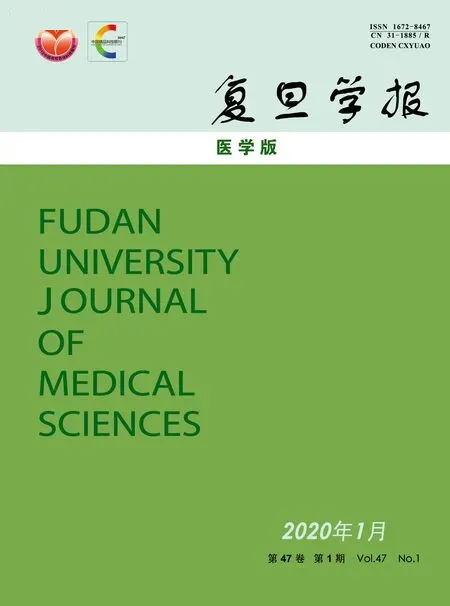经皮血管腔内支架成形术在肝移植(LT)术后静脉流出道阻塞(VOO)患者中的应用并附长期随访报告
张 华 王建华△ 刘 嵘 钱 晟 路会林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介入治疗科 上海 200032;2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上海 200032;3新乡市中心医院介入科 新乡 453000)
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LT)术后静脉流出道阻塞(venous outflow obstruction,VOO)在临床上并不多见,相关文献报道其总体发病率约为3%[1],主要包括下腔静脉狭窄(inferior vena cava stenosis,IVCS)和肝静脉狭窄(hepatic vein stenosis,HVS)。如不及时处理将严重危害移植物功能。相较于LT术后VOO的传统治疗方式,介入处理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更高效、便捷等优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推荐将介入作为LT术后VOO的首选治疗方式,但所采取的具体介入处理方式尚无定论且缺乏长期(特别是10年以上)随访结果。本文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3年1月至2015年12月收治的21例LT术后VOO患者的介入处理方式及长期随访资料,总结相关介入处理经验,评估其近期及远期疗效。
资料和方法
临床资料选取2003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肝外科/肝移植中心收治的经血管造影证实并接受介入治疗的21例LT术后VOO患者。其中,男13例,女8例,年龄9~61岁,平均(44.4±15.6)岁。19例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1例行亲体活体肝移植。1例行减体积肝移植。原发疾病中肝恶性肿瘤9例,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6例,肝豆状核变性2例,酒精性肝硬化1例,多囊肝1例,先天性胆道闭锁1例,自身性免疫性肝病1例。
手术方法经右侧股静脉/颈静脉入路,引入4F猪尾导管行下腔静脉造影,单弯/SIMON导管超选进入肝左、中、右静脉。若下腔静脉/肝静脉存在狭窄、扭曲、侧支循环等情况,则引入测压导管,测量狭窄两端的压差,交换球囊导管,扩张狭窄段,无需追求影像学上的完美,引入支架推送系统,释放支架,复造影,引入测压导管再次测压(图1、2)。注意事项:(1)多支的肝静脉狭窄,一般情况下只需开通其中一条肝静脉即可。(2)经股静脉、颈静脉入路均无法超选入肝静脉时,可借助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肝静脉入路。
随访方法随访起点为患者安全康复出院,随访期间复查彩色多普勒超声、肝肾功能、血常规及凝血功能,每月1次。如果患者出现可疑的再狭窄或阻塞则进一步行CT/MRI增强扫描明确诊断。如果随访期间无可疑的再狭窄或阻塞,每年1~2次复查CT或MRI。随访时间终点为2016年12月30日或患者死亡。
统计方法采用SPSS.16软件处理数据,连续性变量采用进行统计学描述。采用Kaplane-Meier法计算静脉血管通畅率。采用Pearson法评估术前压差与静脉血管狭窄程度、术后压差与静脉血管通畅时间之间的相关性。
结 果
一般资料21例VOO发生于LT术后7~2 711天,平均(479.6±750.0)天。其中,下腔静脉狭窄16例次,肝静脉狭窄9例次。
术前压差与静脉狭窄程度术前跨狭窄压力梯度为3~31 cmH2O,平均(12.7±8.3)cmH2O,21例VOO患者均采取经皮血管腔内球囊扩张联合自膨式支架植入,术后压力梯度为0~5 cmH2O,平均(2.2±1.5)cmH2O。术前压差与静脉血管狭窄程度不相关。
术后压差与静脉长期通畅时间术后压差与静脉血管的长期通畅时间不相关。21例VOO患者共植入支架25枚,其中下腔静脉支架直径分别为30 mm(成人)和18 mm(儿童),长度分别为75 mm(成人)、100 mm(成人)和60 mm(儿童),肝静脉支架直径为8~14 mm,长度为60 mm。
手术成功率技术成功率100%,临床成功率为100%,患者因VOO等表现出来的类布加氏综合征(如腹水、胸水、双下肢水肿)在2周内基本消失。肝功能异常现象在1周内基本恢复正常。与介入相关并发症1例,1例患者采用经皮穿刺肝静脉路径植入肝静脉支架,术后出现肝脏包膜下出血,急诊介入弹簧圈栓塞,出血停止。
随访结果随访期间,除1例儿童患者外,余20例VOO患者均未出现再狭窄现象,随访时间为6~127个月,平均(98.3±32.6)个月。静脉流出道的1、3、5和10年通畅率分别为100%、100%、100% 和95%。1例9岁儿童肝移植患者术后因顽固性腹水而行下腔静脉肝左静脉支架植入术,7年后出现下腔静脉支架移位、肝左静脉支架再狭窄(图3),给予支架内球囊扩张及肝中静脉支架植入,患者症状未见明显改善,后死于肝功能衰竭。
讨 论
经皮血管腔内介入治疗肝移植术后血管狭窄性病变简便易行,疗效确切[2-4]。单纯球囊扩张具有即时开通率高、可重复、对二次肝移植无影响等优点,LT术后VOO的早期处理多采用单纯球囊扩张[5-8]。只有出现反复流出道狭窄或原位移植术后早期(术后4周内)出现的腔静脉狭窄,球囊扩张有引起新鲜吻合口破裂的风险,才考虑支架植入[8]。但单纯球囊扩张术后再狭窄率高,为了保障移植物血管长期通畅率,避免反复狭窄引起的移植物损伤,多数学者认为早期球囊扩张联合支架植入可更好地保护移植物功能[9-11]。本组所有患者均一期植入支架,获得了良好的血管长期通畅率,这也证实了上述观点。
Ko等[12]认为儿童移植的肝静脉管径与成人一致,支架与个体生长不相关,其中青少年的血管和成人更加相似,植入成人直径的肝静脉支架,可获得更好的长期通畅率。本组1例儿童肝移植患者采取早期支架植入,维持静脉流出道通畅7年后出现下腔静脉支架移位、肝左静脉支架再狭窄,分析原因如下:患者年龄较小(9岁),生长发育尚未完善,术后身体发育变化巨大,所选腔静脉支架直径相对较小,使得术后7年发生腔静脉支架移位;该儿童采用成人活体肝移植,术中供、受体血管直径匹配度低,术中血管修剪、成形,吻合操作难度大,导致术后肝静脉吻合口狭窄程度高,采用成人直径的肝静脉支架虽可即时开通血管,但有引起内皮细胞损伤及血管内膜增生稳态失衡而并发支架植入后再狭窄的风险。因此,对于儿童LT术后VOO能否使用支架、支架直径、支架植入时机等有待进一步商榷[13]。
对于多支的肝静脉狭窄,我们的处理经验是:先行开通肝右或肝中静脉即可明显缓解多数患者的临床症状(类布加氏综合征肝静脉型),其余狭窄的肝静脉也可由随后侧支循环的形成所代偿,且先行开通一支肝静脉对于减少费用、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后相关并发症等具有一定意义。对于首支肝静脉成形术后狭窄段纠正少于50%、压差下降不明显或开通单支狭窄肝静脉临床症状不缓解的患者,则应多考虑开通剩余狭窄的肝静脉。
压力梯度在诊断静脉狭窄、阻塞及评价后续介入疗效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能引起临床症状的最小压力梯度,国内外报道各不相同且尚无定论。跨狭窄两端压力受系统动脉压力、门静脉压力、中心静脉压力,甚至患者体位、麻醉状态(局麻或全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4]。狭窄两端的压力差常与静脉阻塞程度不完全相符。术前压差与静脉血管的狭窄程度不相关,术后压差也不影响静脉血管的长期通畅率。
对于支架的选择,我们主张使用Wallstent、Gianturco等自膨式支架,此类支架扩张性良好且具有倒钩,可有效防止支架植入后因腔静脉管腔直径变化而引起的移位。此类支架金属钢丝之间的间隔较大,可大大减少因腔静脉支架植入引起的肝静脉回流不畅等问题。如果在腔静脉支架植入后患者再次出现肝静脉狭窄现象,还可通过金属支架间隔对肝静脉再次进行介入操作以解除肝静脉狭窄。Weeks等[15]报道了9例经原腔静脉支架金属网格间孔置放肝静脉支架的案例。植入过大直径的腔静脉支架有引起肝静脉扭曲变形的风险,我们认为选用比正常腔静脉直径大3~5 mm为最佳。
自膨式支架在释放过程中需配合推动杆经过较长、较硬支架输送鞘管,在支架完全释放时,可能出现支架“前冲”,所以操作时应格外仔细。Lee等[16]提出可运用12F大直径、薄壁输送鞘,在推送支架过程中更为顺畅,可大大减少支架“前冲”现象。另外,球囊扩张式支架现已经应用于LT术后相关静脉流出道狭窄等并发症,其理论依据主要有:(1)相较于自膨式支架来说球扩式支架在释放后支架自身缩短的程度更小。(2)球囊扩张式支架具有更强的纵向抵抗力,中等大小的球囊扩张式支架的箍强度远大于同等大小自膨式支架[(18.8±1.2)N/cmvs.(0.39±0.03)N/cm][17],可明显减少因血管损伤纤维化造成的组织回缩,保持静脉流出道的长期通畅。(3)释放球扩式支架无需支架输送、推送系统不会存在支架“前冲”引起的支架移位问题,因此定位更加精准[18]。但我们认为球扩式支架一旦释放,其自身直径不会随着腔静脉直径的变化而变化,而腔静脉的直径具有较大可变性,有引起支架移位的风险,因此本组患者均未采用球扩式支架。
经颈静脉入路是介入处理移植术后静脉流出道狭窄问题最常采用的途径,此为从穿刺点到腔静脉最直接的路径,导管易进入目标肝静脉,特别是在采用背驮式肝移植的患者中此路径的优势更加明显[19]。股静脉途径释放支架有支架“前冲”而误入心房的风险,所以对于距离心房较近的下腔静脉狭窄,我们认为应首选经颈静脉入路。
对于经颈静脉或股静脉入路导管均无法进入目标肝静脉的患者,可在超声引导下直接穿刺肝静脉,但有引起肝脏出血、穿孔等风险。我们的经验是建立穿刺道时尽量减少穿刺次数,穿刺未能成功时针尖退至肝包膜下3~4 cm处重新穿刺,在封堵穿刺道时采用3~4 mm的弹簧圈自穿刺道进入肝静脉分支开始严密填至肝包膜下。对于经皮直接穿刺肝静脉的患者,在最后封堵穿刺道之后建议术中联合肝动脉造影,排除肝脏损伤。本组只有1例患者采用经皮穿刺肝静脉路径植入肝静脉支架,封堵穿刺道后因未行股动脉造影,术后出现肝脏包膜下出血,急诊介入弹簧圈栓塞,出血停止。
对于术后是否需要长期抗凝及采用何种抗凝方案同样存在争议。多数学者推荐术后使用小剂量阿司匹林(不推荐华法林,以减少出血风险)口服抗凝3~12个月,可降低支架内血栓形成风险从而延长支架长期通畅率,但抗凝方案需视长期随访过程中支架内是否有血栓形成而做出调整[19-20]。我们认为腔静脉为大血管,只采用术中肝素水灌注导管(5 000 U/500 mL)而未采取任何额外抗凝,在术后及长期随访中未出现支架植入后血栓形成,所有患者均获得比较满意的长期通畅率。
综上所述,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治疗LT术后VOO操作简便,疗效确切,可获得良好的近期及远期疗效,可作为LT术后VOO的首选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