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女不好惹
蔓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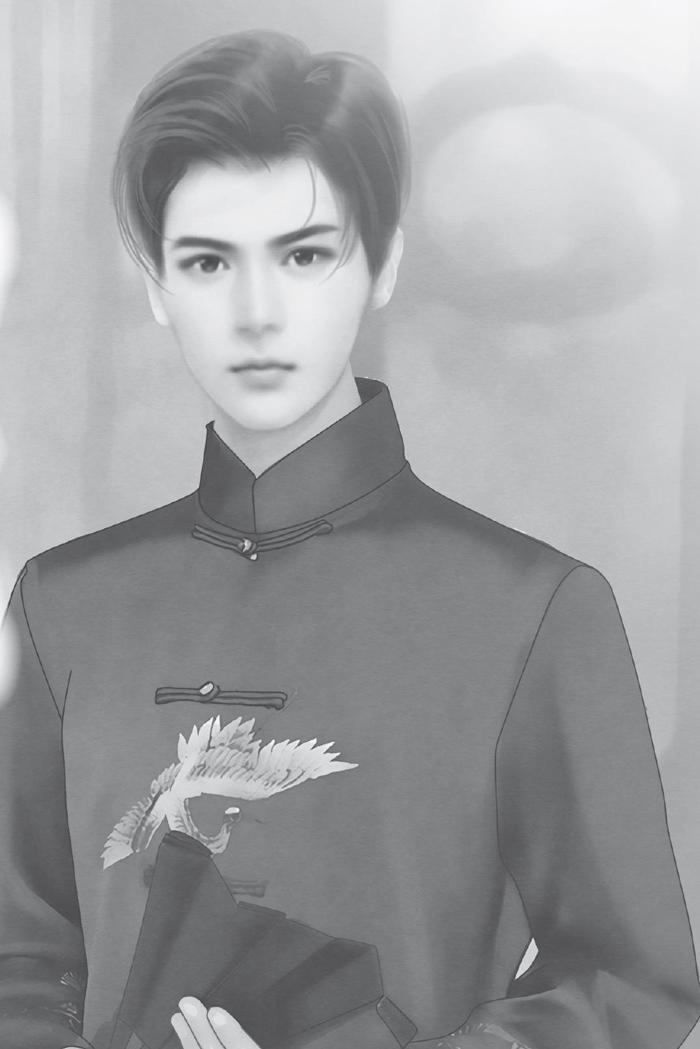
简介:商思是宁城出了名的恶女,人人都怕她、厌她,此时,有一个骗子找上门来。她心里清醒,却又忍不住沉迷其中,一个人被冷待了太久,只有要一丝温暖出现,都会尽全力去抓住,谁会在意这温暖的背后藏着什么呢?
1、
宁城现下风头最盛的便是商二小姐。
听闻商家只有个集千宠万爱于一身的小姐商蕊,可去年商蕊出嫁前夕,商家突然多了个二小姐商思。
商蕊出嫁后,商家偌大的家业便都成全了这个商思。
宁城的人最眼红别人飞上枝头,也最爱看商思的笑话。
“你竟然敢不赴我的约!”商蕊的脸色不太好,有种病态的美,但丝毫不影响她盛气凌人。
一杯水泼得对面的女人妆都花了,挨得近的客人皱着眉,一脸嫌弃地走远,还用手帕擦了擦衣袖,然而上面并未真正溅上去水花。
商思面无表情,只是冷冷地看着台面上沁入桌布的水,忍了半晌,才低声认错:“我错了,姐姐。”
商蕊这才快意了一些,起身在用人的搀扶下离去,临出门时,她顿住脚,慢悠悠地道:“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别不知好歹,知道了吗?”
“是……”
門一开一合,直到人彻底走远,商思才露出眼底的戾气,厌恶地掀了桌布,杯碟碎了一地。
周围的人避之不及,唯独角落里那一袭白衣的身影还在。她恶狠狠地朝他看去,道:“怎么着,还没看够?”
那男子从暗处慢慢走出来,似乎犹豫了片刻,将饭店里的手巾递到她眼前。
商思嘴角上扬,讥讽的话如同刀子一般尖锐:“你是什么身份,也敢往我面前手巾?!”
男子轻轻地叹了一声,微微侧过身,挡住了身后所有人的视线,用手巾擦着她脸上的水。小声说:“哭吧,不丢人,他们看不见了。”
一直强行憋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不听话地滚落,商思仰头,看见一张俊秀的脸,五官深邃却温和,她看他时,就如同跌进了一汪春水。
温柔得太过刻意,便失了真。
她上下打量了一眼,轻慢道:“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穿长衫袍子,不是迂腐就是穷。”
男子的脸慢慢红了。
商思还是那样张扬、恶毒,彻底在男子面前坐实了自己宁城恶女的名声。
商思凌厉张扬,天不怕地不怕,去年撞上宁城赫赫有名的贺三爷,三言两语便讽刺了对方一顿,贺三爷当即把人拿住,她却一副不怕死的架势,自己往刀刃上贴,冷笑道:“千万别手软。”
这让道上的爷们儿都不想去惹这位姑奶奶,从此往后,商思恶女的名声就远扬了。
宁城名媛们从不主动邀请商思,商思却偏不如她们的意,得了信儿就赶过去凑热闹,存心坐在那儿让那些人不自在。
她们不自在,商思便自在了。
这晚是局长千金董玲组的局,商思照旧待了大半宿,她一时高兴,还多喝了两杯,离开的时候在门口吹了半天冷风,管家还没开车过来。
商思摇摇晃晃地走路,极细的腰肢让人遐想。
晦暗的巷子口,她跌撞进一个熟悉的怀抱,那人扶住她,她攀着他的手臂,身子贴靠在他的衣料上,一层薄薄的料子下传来他“扑通扑通”响的心跳声。
商思勾唇一笑,妩媚动人,酒气催得她的大脑不能思考,却也只是坏心眼儿地吹了吹他的耳朵。
男子浑身一颤,往后躲了一步,却让商思险些摔倒,他又忙上前扶住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当真是狼狈。
商思醉眼蒙眬地问他:“喂,你叫什么名字?”
他简单地回答:“穆白。”
“白色不好看。”她摇了摇食指,娇俏地笑道,“不如染成黑的。”
她拉扯着他跌进身后的屋子里,一路退至床边。商思一再热情主动,穆白便彻底没了辙,只能红着脸躲开她的红唇,阻止道:“商……商小姐。”
她不悦地瞪他:“你到底行不行?”
男人最听不得这话,回应她的是更加猛烈的吻。
2、
穆白第二日醒来时,身侧早就没人了,微微凹陷的软枕上还残留着余香。他揉着太阳穴,余光瞥见那抹红色,眼神怔愣,半晌才茫然地抬头。
商思这两年睡得不安稳,总是凌晨四点就醒了,她悄悄地离开,回去时正看见在宅邸门口候着的徐叔。
徐叔“嗤”了一声,冷声道:“您可算回来了。”
“这么担心做什么?我又不会死在外头。”商思的嘴里就没个忌讳,颇不耐烦地擦过徐叔的肩往里走。
“这是自然,大小姐还指望您能多撑几年呢!”
商思脚步一顿,没吭声,径直往里走,头也不回。
这十来日,商思的身子不大利索,病恹恹地在宅邸待着,外头倒是乐得快普天同庆了。
徐叔才备好了药,正准备给她端去,她却打扮得光鲜亮丽地要出门,徐叔没办法,只得开了车载她四处逛逛。
宁城就这么大,商思早就腻歪了。
车停在一个小店铺前,她听到穆白的声音,顿时眼角上扬,笑吟吟地下了车。
穆白还是穿着一身旧长袍,有些羞赧地跟老板讨价还价:“我多买几本,您不如就便宜些吧?”
商思打眼一看,发现是几本小孩子用的课本,还颇旧。她从前三教九流都接触过,看人挺准,猜到穆白这是想淘几本旧书去做私塾先生。
“这些书都旧成这样了,市面上早就不卖这种了吧?”商思走进店里,用手夹起书本,嫌弃得眉头紧皱。
老板面上一窘,穆白却从看见她的时候便不自在地低垂了眉眼,大概是想起那晚的事,慌得手都没地儿放。
“既然没得卖,那就是孤本咯?”商思挑了挑眉,眼见穆白愣了一下,她继续说道,“孤本的价格应当更贵才是。”
老板见商思添油加醋,登时顺杆往上爬,忙不迭地点头。
穆白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清秀的眉眼微微皱着,看了商思好半晌,确定她是故意来打趣自己的,抿紧嘴唇便要离开。
商思伸手一拦,瞧着他说:“不如我聘请你当我的私人老师,工资随你开。”
穆白不搭理她,还是要走,商思便凑近了些,声音轻飘飘地说:“你就当是那晚的钱。”
穆白手一抖,耳根子瞬间染红。
回到宅邸,商思一下车,便被徐叔叫住。
徐叔的眼底浮着轻蔑,一如既往地瞧不上她。他提醒道:“一次两次还能当是巧合,三回都只撞上您,可就得当心了。”
商思挪开眼,没回话,仿佛一点儿也不在意。
徐叔又加重语气:“您该知道,您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自然是臭名昭著,整个宁城都厌恶她,怎么会有男人真心喜爱她?
可商思只是轻笑一声:“我呀,是一个特别有钱又好看的女人。”
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没有什么东西得不到。
她一贯这么认为。
3、
徐叔说得没错,穆白打从一开始就盯上了商思。
穆白手里拿着一份商思刚才在店铺里随手写的聘请书,字迹潦草,说希望聘请穆白做自己的老师,她还很轻佻地在纸上落下唇印,仿佛盖章。
他深眸低敛,一身温柔早已褪去,一步步朝家里走。
大门敞开,贺三爷嚣张地抛着刀子玩儿,他盯着穆白,许久才露出玩味的笑。
“我算是小看你了,攀上商思算你有本事。三爷我这人说敞亮话,你要是能把债还清了,卖身契我还给你,日后还祝贺你凭着商二小姐平步青云,道一声恭喜。”他边说边抱拳朝一侧拱了拱手。
穆白冷冷地一笑,眼神落在那似有似无的唇印上,把纸揉成一团,弃之如敝屣。他缓缓地抬起眼,矜傲和漠然俱现,道:“我等着三爷的这声恭喜。”
穆白不是个文绉绉的读书人,他从没上过学堂。他自小便被拐子带离家乡,坑蒙拐骗,什么都干过。
九年前,他没长眼,顺了贺三爷的钱袋,被毒打了一顿不说,还被逼着签下了卖身契,当初他偷的那袋子零花钱如今利滚利,成了天价。
他对周遭的一切都厌恶至极,发誓自己一定会飞黄腾达,做人上人。
贺三爷啐了他一脸,说:“行啊,商思那恶妇就是你的捷径,只要你下得去手。”
然后穆白便去了。
他在心底讥讽,区区商思,也不过如此。
商思的这份聘书拿得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难,但在登门之前还是做足了功课,以防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商二小姐看穿他的身份。
穆白进府,由徐叔在前带路,一径的华贵装饰让人挪不开眼,他却始终低垂着眉眼,看也不看。
二楼的小阳台上,商思侧身躺在躺椅上,轻轻扇着羽毛扇,眼皮微掀,看见穆白在午后的阳光下挺拔地走来。他周身仿佛镀了一层光,熠熠生辉。
听到身后来人,商思懒懒地说:“替我捏捏肩。”
身后没有动静,那人似乎犹豫了片刻才放下书本,伸手轻轻地揉捏着她的肩膀。
商思又眯了半晌,才听见穆白说:“二小姐,什么时候开始讲课?”
她慢悠悠地回眸,明明她躺着,他站着,她却能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睨着他说:“课,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穆白眼神微暗,却没有说话。
商思比他所想的更好伺候,在穆白眼里,她就像一只凶狠的野猫,警惕又怀疑任何靠近她的人。可倘若他只是在一定的距离外轻轻地给她顺毛,她便心安理得地享受。
一连半个月,穆白进出商宅,不过做了些陪伴、消遣的事,唯一跟上课沾边的,大约便是商思无聊了,让他念些新闻给她听。
4、
那日是商思的生日宴会,收到徐叔送去请柬的那些人原本对此事是避之不及的,但碍于老一辈的关系,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穆白在一侧看着觥筹交错的人群,嘴角忍不住浮现出一丝讥讽的笑。
这场宴会布置得要多奢华有多奢华,仿佛要借一场生日宴嚣张地告诉众人,她商思就是有钱。在场所有来宾眼神中的轻视、言语间的鄙弃,她都置若罔闻。
商思这人果真是又愚蠢又虚荣。
便如所有人预期的那样,商蕊不请自来。
商蕊常年喝药,眉宇间仿佛总缠绕着病气。这俩姐妹也真是奇怪,说是互相怨恨吧,当年偏偏是商蕊费尽心思把商思找回来,为她正名,坐上商二小姐的位置;若说是相亲相爱吧,商蕊又好像见不得商思好,但凡商思耀武扬威的场合,她必定出现,让商思下不来台。
这场生日宴把商蕊气得不轻,叫人直接把订制的鲜花踩烂、蛋糕摔坏。用一个月前从国外订回来的红酒,把商思泼得狼狈不堪,商蕊才离开。
宾客皆散,捂着嘴偷笑,有人刻意抬高声音说:“就说这野鸡,装扮得再像,到了真凤凰面前就露怯了。”
这一幕与他半月前撞见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穆白抱着手臂,在一旁冷眼看着,漫不经心地品尝了一口红酒,唇齿留香。
别人都散场了,他的戏却要上演了。
穆白找到她時,她坐在小阳台上,支着下巴瞅着满天繁星,眸子里没有一点儿波澜。
空气里有一股清甜的桂花香,她才梳洗过,头发微湿,贴在那被蓬松睡裙包裹的身体上。
穆白走近,语气似有踌躇,宽慰道:“二小姐别放在心上,大小姐可能是心情不畅,过几天就好了。”
商思淡淡地回答:“有什么可安慰的,我天生命贱,不配这些好东西。”
他心头一颤,抬眼望着她寡淡的神情,又仿佛回到了早年自己受苦的那段岁月。
那时他被人踩在地上,自尊碎了一地,他发狠道:“等老子以后发达了,用最好的东西,找最靓的婆娘,让你们都跪在我跟前叫大爷!”
那些人嘲笑他说:“你就是个贱骨头,天生的软虫,配不上那些好东西!”
穆白收回思绪,他喉咙发紧,最后垂着眼低声道:“二小姐说笑了,您可是金枝玉叶。”
商思白皙的面庞因为这话笑得染上紅晕,她目光挑衅地瞅着他,掰着手指头数道:“我没上过学堂,父亲也从来不像别人那样去接过我;我姐姐讨厌我,小时候和别人打架,她都是帮着别人教训我;我这人性格坏、脾气差,没有男人愿意亲近我……哦,你嘛,算是我强扭的瓜。”
黑沉沉的夜里,她那双眼眸亮晶晶的,闪着狡黠的光,仿佛在跟他比惨,非要在口头上赢了他不可。
穆白望着她的眼睛,有些挪不开视线,微风吹过他微热的胸口,他缓缓地道:“二小姐值得更好的。”
5、
慎行学堂位于杨柳街的尽头,学堂是位老秀才办的,这几年因为生活窘迫,收费便宜,周围邻里才送自家孩子过来学几个字。
听说她没上过学堂,穆白便四处找学堂,但哪里那么容易,宁城人都怕死商思了,还是穆白百般求情,这位老秀才才答应让商思来学堂上课。
商思坐在最后一排,看着老秀才摇头晃脑地读着又臭又长的文章,一堆矮萝卜头咿咿呀呀地跟着念。
十二点刚到,老秀才就喊了声下课,那群小孩子们撒欢似的往学堂外奔。这场景有些奇异,她捧着腮饶有兴致地瞧着小孩子们背着书袋往外跑,想起从前她怯生生地躲在学堂外偷看,被先生发现后,一顿训斥将她赶走的情景。
她拍了拍身上的灰,慢慢往外走,出门看见穆白的身影时却愣住了。
学堂前有一棵歪脖子树,许多家长都躲在树荫下接自家孩子,参差不齐的人影里,穆白高挑的身影仿佛鹤立鸡群。
他抬眼见她出来,伸手招了招,脸上是熟稔自然的微笑。
她心头涌过密密麻麻的酸涩,一时看呆了,只觉得站在那里的人好似从前渴望了许久的父亲,可再打眼一瞧,是穆白。
等商思走近,穆白轻轻摘去她肩上的落叶,像是接过她千百次那般自然地揽住她的肩膀往前走,语气温和地说道:“学堂好不好玩儿?”
商思心底软软的,面上却依旧是嫌弃的样子,她“扑哧”一笑,说:“你在过家家呢?今天打算扮我爹?”
穆白摇头微笑道:“不敢。”
商思斜眼瞅着他,眼底却藏不住笑意,她说:“那是当然,敢占我便宜的人还没出生呢!”
可这过家家的游戏她却玩儿不腻,一连一个月都跑去学堂,每回都骄纵地指挥穆白必须准时准点来接她放学。
这事儿在宁城传开了,那些人背地里都在嘲笑商思和一群小孩子挤在学堂不像样,更是阴阳怪气地念叨一声穆白这人了不得。
就连徐叔都忍不住在发月薪时讽刺:“穆白先生好手段,哄得二小姐高兴,多少银钱都愿意往你身上砸。”
穆白接过钱票,微微颔首,不卑不亢地道:“客气。”
“穆白!还不快点儿出来!”院子里的商思已经在不耐烦地催促,新一季的服装都到货了,她照例要先去买第一批款式的。
穆白朝徐叔示意:“烦劳您开车。”
徐叔哼了一声。
商思花钱向来大手大脚,逛街一事最能让她兴致勃勃,她拉着穆白试了十几件衣服,最后全都包了起来。但她自己却没什么兴趣,只是命人把新款全都买下,却再也没看过它们一眼。
穆白指着店里展示的那件红裙子,道:“那件很适合二小姐,款式独一无二。”
“是吗?”商思摸了摸下巴,眯眼笑说:“那行,买下!”
巧的是这件裙子也被董玲看中了,这两个女人一向不对付,商思当即就和董玲杠上了。
董玲气恼,不肯松开衣服,讥笑道:“这裙子我三天前就付了定金,二小姐竟然肯花十倍的价格买下,也不怕回去了心疼?”
商思的手同样紧抓着裙子不放,跋扈又张扬地说:“千金难买我乐意!”
“你!”董玲眼珠子一转,轻笑着说,“听说大小姐最见不得二小姐用顶好的物件,也不怕还没穿几天就让大小姐拿红酒再给泼坏了?”
商思脸色铁青,刚要发作,可就在这时,穆白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把剪刀,一剪子下去,裙子便毁了。
穆白护在商思前面,神情柔和地看着董玲,风轻云淡地说:“二小姐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
“穆白!你讲不讲理?!”
穆白笑着说:“我偏疼谁,理就在谁那儿。”
董玲气冲冲地跑了,商思笑得腮帮子都险些发酸,她乐不可支地扶着穆白的手臂,道:“这回扮得是谁?宠爱任性妹妹的兄长吗?”
穆白漆黑的眸子望着她,微不可察地挑了下眉,问:“二小姐不高兴吗?”
“高兴至极。”
6、
商蕊的身体状况有些不稳定,让人过来请商思。
商思到的时候,只见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病恹恹地躺在床上,面白如纸,商思看着觉得她也没有以前那么的面目可憎了。
商蕊唤她靠近些,她便干脆坐在床侧,冷眼看着商蕊咳嗽咳出血来。
商蕊牵动嘴唇,问了一句:“你恨我吗?”问完又觉得好笑,径自摇头,幽幽叹气。
怎么会不恨呢?
商思是商父和歌女的私生女,身份上不了台面,从小在商宅做下人,成天被商蕊欺负,后来商思的母亲过世,她也被赶了出去。
商家的羞辱、商蕊的刻薄、商父坚持的脸面,她统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没有哪一日不恨的。
商父早年病逝,商家发生内斗,幸亏还有徐叔帮衬。商蕊从小定下婚约的未婚夫看中了她的一身陪嫁,强娶了商蕊过门。但这位大小姐心气儿高,自带家族的骄傲,赶在成婚前把商思带回来认祖归宗,家业也顺理成章地给了商思。
当年为她正名时,商蕊恨恨地啐了她一脸道:“便宜你这个破落户了,这几年就好好享受吧,好歹商家的钱都能留在商家血脉的手里。”
人人都说商蕊撑不过明年开春,商蕊茫然地看着窗外正盛的日头,缓缓道:“穆白那人,俊是真俊,可你别认真,当心到最后伤心一场。”
商思再也坐不住了,也不知道是商蕊这惨状让人扎眼,还是这话让人扎心,她冷言嘲讽道:“我像是个会认真的人吗?”
再后来,她得到了整个商家,拥有无尽的财富,代价却是商蕊亲口告诉她,商家有家族遗传病。
父亲底子好,撑到了三十九岁,商蕊自小被精细照顾,但是娘胎里带来的虚弱,凭着药物吊着,也不过才撑到二十七岁。
而她呢,她今年不过二十三岁,人生就要到尽头了。
这一生,真是可笑又可悲。
8、
又这么过了半年,穆白的眼里、心里只有商思,她再也没从别人嘴里听到穆白和董玲的绯闻。
他似乎待她是真的好,好到有时候令人迷惑。
商思一直知道穆白私下的动向,一切都由徐叔在暗中监控。她还知道这两年穆白采买货品需要用船,为了不让自己知道,他去联系了私船。
前段时候海上风浪大,他的私船翻了,货没了。但那些订单催得急,都是老早就签下的合同,如果不能按时交货,那他这两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邻城的商人有货,却故意抬高价钱逼着他去买,他拆东墙补西墙也凑不齐,最后竟然应了董玲的邀约。
商思一直咳嗽,纸巾被血染成樱花色,她看着直发笑,这就像她去见商蕊最后一面的场景。
徐叔说穆白回来了。她不慌不忙地在徐叔的搀扶下坐起,涂抹了一点儿口红,整个人看起来有了点儿气色。
穆白心里着急,董玲知道他缺钱,再次抛出橄榄枝,他拒绝了,犹豫再三,还是过来找商思借钱。
商思似乎十分不解地看了他好半天,柔声问道:“你只说急用,但又不肯说理由,明明随便哪一个理由都行,你怎么就不肯说呢?”
穆白抿着唇,沉默地摇了摇头。
他已经做不到继续骗商思,哪怕一个字都不行。
商思的眼底闪过失望,她在想,他连骗自己都懒得费心了,他在董玲那里又是怎样的姿态呢,是不是就如当初他引诱着她上钩时那样?
想到这里,她不可遏制地觉得酸涩、难受,她又要开始准备竖起浑身的刺去扎人了。
他好像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可是她临了又偏要执拗这一回。
商思往后一躺,躺椅微微摇晃,她伸手示意,徐叔很快拎过来一只箱子,摊开放在桌面上,里面满满的都是钱。
她道:“一声我爱你,一万块钱,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穆白眼神暗沉,面有愠怒,竟然伸手挥落了一桌的钱,钞票漫天飞扬着落地。
商思面露疑惑,道:“你从前花样百出地哄我开心,逗得我顺意,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怎么今天连说一句‘我爱你都不肯?”她自顾自地笑了,言语中尽是刻薄,“还是说,你爱上我了,如今再向我低头,对我低声下气,就觉得伤了自尊?”
他气得一个字都吐不出。因为他无法辩驳,他的确爱上了她。
可这个女人如此坦然地说出一切,还嘲笑他,仿佛把他踩进泥里。
这是他的报应,难道他还要厚着脸皮继续乞求她的爱吗?
穆白深吸一口气,自嘲地笑笑,深深地看了她最后一眼,然后转身离开。
9、
商思和穆白闹掰了,不过七天,宁城的人就都知道了。
那几天他成日买醉,全然没了平日杀伐果决的样子,连公司那边也不在乎了。
那晚他烂醉如泥,躺在酒店,莫名其妙来了一位律师找他,他懒得理会,翻过身继续喝酒。
律师公事公办地念道:“商思女士的遗嘱说,在她死后,商家的一切财产将由您继承。”
蓦地睁眼,漆黑的眸子阴沉得仿佛要杀人一般,他死死掐住律师的脖子,道:“你有胆子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律师哆哆嗦嗦地解释,穆白只觉得脑袋里一片空白,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他红着眼拼命朝医院跑去。
商思已经在医院住了七天,这天大概就是最后一天了,她的病房里围了不少人,她费力地睁开眼,从人群的缝隙中看到愣愣地站在门外的穆白。
她慢慢启唇,伸出手揮了挥。
他的眼神茫然又悲恸,仿佛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一句话也说不出,看着商思竟然只剩下眼泪可流。
商思轻声道:“那些钱,拿去救你的公司。”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徐叔慢慢道:“这是家族遗传,大小姐靠药吊着才撑了这些年,二小姐自从回到家的那天起就不曾喝药,生生折腾得自己比……比大小姐的时间还短。”
医生眉头紧皱,推开他靠前检查,商思病危,开始呼吸困难,她却摇了摇头,看向穆白:“你抱我去外面看星星吧。”
她露出苍白的微笑,穆白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痛得快要窒息了,他强忍着痛意抱起商思往外走。他抱着这个女人,一直哽塞的喉咙仿佛能出声了。
他流着眼泪,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我爱你”三个字。
商思缓慢地笑着。
她的一生过得很糟糕,短短二十几载,颠沛流离,受尽嘲讽和虐待。一朝拥有大笔现金,却空虚到不能救自己。
她还遇到了一个骗子,骗走了她的钱,也骗走了她的心,可临死前的最后一瞬,却只剩下感激。
她一生没得到的东西,其实他都给她了。
在乎、鼓励、认可、容忍……
这个可怜又孤僻的商二小姐,最后像个孩子一般笑得天真,她摸着他的脸颊说:“遇见你,真好。”
她挣扎着仰起头,干涩的唇轻轻吻住了他的唇,她稍稍用力咬破了他的嘴唇,殷红的血染红了唇瓣。
她故作可恶地笑着说:“这一个临别之吻,是我送你的最后的礼物。既是爱,也是惩罚。”
天边即将破晓,大地的黑暗渐渐褪去,他们周身开始染上太阳的光芒,而她眼底的光芒却逐渐黯淡。
穆白僵硬着低头,看了她好半晌,才颤抖着将她的眼睛合上。
他重新抬头看向天边的日出,把怀里的人抱得更紧,眼底含着悲哀的笑,低声道:“如你所愿。”
他的嘴唇在痛,这痛一辈子都不能消退。
此后余生,他的心像反复被放在火上煎烤,受尽折磨,所有的爱与眷念都化成了“求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