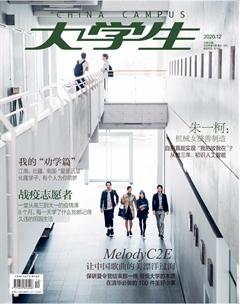记忆失落,文化如何延续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民俗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组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
保护好我们的村落

在泥河沟村调研的学生们 摄影/刘虎卫
广西龙胜的龙脊梯田、湖南新化的紫鹊界梯田、江西崇义的客家梯田、福建尤溪的联合梯田看到这些中国的美丽梯田,你看到的是美景,是农业景观,是文化景观。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了村落,如果村落里的守望者相继离世,这样的村落,这样的田地,这样的农业景观还能够持续多久?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很多人等同为民俗学,人们只知“非遗”,却不知农业文化遗产。我跟导师乌丙安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老爷子说农业遗产是体,“非遗”是皮上的毛,如果体和皮不在了,毛就真的无法存在了,所以要重视农业遗产的保护。为什么要先保护“非遗”呢?老人家说,因为“人绝艺亡”,记忆流失得太快。那块田地可能还能保留一段时间,但是农人一死,记忆就没有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先来保护“非遗”。我很接受老人家这种说法。从这个意义上來说,无论是研究农业遗产还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一体的。我国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从2013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开始进行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审批工作,到目前已经有5批118项农业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名录。前面提到的美丽梯田都是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对我要进行的乡村建设来说,更多的是具有一种文化干预的性质。
千年古枣园的文化如何挖掘
农业文化遗产和村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没有村落,也就没有乡土社会了。中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实际上和乡土社会的存留与保护是一体的。村落不只是由砖和瓦叠加在一起的聚落空间,而是经由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的人们,世代累积的情感、文化和意义体系。你别小看村口那棵树,是他们几代人儿时爬上爬下快乐玩耍之所,那棵树上的鸟窝是几代人的记忆,所以才能够转换成为老百姓家乡认同的情感依据。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文化和记忆体系转换成可以操作的文化符号,继而让我们的老百姓充分地认知这些乡愁的栖息之所?
陕西省佳县泥河沟村是黄河近旁的村落。这里地处晋陕大峡谷,风景很美。但是,它是中国吕梁特困片区中的1个村庄。2014年,我和学生们进泥河沟村时,全村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158人,60岁以上的111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老人村落。村庄的周围36亩古枣园就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里有1100多棵枣树,年龄最长者1300多岁。这片枣林在这里1000多年,看了一辈又一辈人的故事,听惯了黄河的流水声,但是它不言语。
泥河沟村的古枣园被评为全球农业遗产后,我和学生说,枣树是人工培植的,与枣园相伴的村落里那得有多少丰富的资料!我们去那里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生态智慧和文化积累。可是去了之后,我们非常失望。当地人讲陕北话,我们听不太懂,看到的是破败的窑洞。更为遗憾的是,我们翻阅县志和所有的文史资料,对这个村落没有超过300字的记载。有的学生说:“这里只有河神庙、龙王庙和观音庙,其他也没啥,我们还留下研究它吗?”我说:“你没有看出来,那是你缺乏慧眼,缺乏专业的素养。如果能够在平淡的日常中发现那些别人不能看到的文化特质,那才叫做训练有素之人。”
在泥河沟村,我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村落?如何破解它的贫困之根?我们在那里前前后后工作了三年半的时间,以文化干预的方式,通过老物件、老照片的收集,重现了村民渐行渐远的生活往事,为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落,存留一份属于他们的文化记忆。这是用文化干预的方式去撬动乡村建设的一个实验。
唤醒乡村记忆
编撰村落文化志是我最先设定的目标。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老人们讲述得有声有色,有心酸、有泪水,也有欢乐。黄河带给他们灾难,也带给他们幸福。

2018年的泥河沟大讲堂 摄影/于哲
这些老人走进了我的生活,走进了我的记忆。我不仅知道村里老人的名字,他们的祖宗三代、他们的儿子孙子在哪打工我都清楚。族谱天天翻,去采访的时候,每一个故事都能让你跟他一起落泪,这样过心又过脑的日子,你会把他们忘掉吗?在我们那本50多万字的口述史《村史留痕》中,每一个人的故事足以让我讲上半小时、一小时。
我和18位学生联手,协同村民一起工作。这个几乎没有文字记载的村落,因为学生们的努力,因为老百姓的大力协助,最终我们出版了三本厚重的书,有泥河沟村的口述史、文化志,还有影像集。你不要小看它们,仅仅是一本一本书吗?为了让老百姓能看懂,我们的设计师朋友专门设计了一本图册集《乡村记忆》,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看到自己爷爷奶奶的形象,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唤醒乡村记忆的力量,是一种内生性的力量。所以我才说,这是乡村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特质,从此这个陕北村落里就拥有了。

在泥河沟村调研 摄影/侯玉峰
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存在,搜集了他们身上所携带的几十年的生活记忆。黄河的记忆,那沟沟坎坎的湾塌坡峁梁的记忆,每一种地形都带着他们对生存环境的神奇想象。泥河沟村一共有144个地名,每个地名只要你提及,就宛如村民自家的宝贝一样。今天生活在乡村的人,有几个还知道家乡那么多神奇的地名,那是祖先们对于那块土地的认知之后给我们的一种最直观的传达。在这里,有过很多的瞬间,这些瞬间让我意识到,人,必须在乡村振兴当中被重新发现,乡村自身存在的力量,需要外部力量去唤醒。
成为文化遗产的参与者
怎么能够让村民在和你一起工作的过程中,觉得他不是遗产保护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呢?那必须得唤起他们的热情,他们讲述的热情,他们关注家乡发展的热情。在村的就100多人,在外的几百个年轻人,何时能够关注它、研究它?所以,我们举办了三届泥河沟的大讲堂,举办了三届泥河沟的庆典晚会。有位82岁的老人家,大字不识,但是庆典晚会上,他能登台现场创作快板,看到什么就能说出什么,是不是本事啊!

黄河边上的泥河沟村 摄影/熊悦
再来看看泥河沟大讲堂。很多人疑惑我们到底讲什么,讲今天的乡村建设吗?离他们太远了。我们讲泥河沟的垃圾谁来收拾;泥河沟破败的窑洞怎么利用;泥河沟作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地,当别人来村里观光的时候,应该报以怎样的笑脸。专门邀请建筑设计师团队,给村民们讲为什么这样设计和改造。所以,大讲堂举办时不少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老人家很早就在那里等待,一个又一个的夜晚,不论冬夏,都如此充盈丰满。
2018年6月15_17日,有三天的大讲堂活动。与前面的调研不同,我的学生们毕业了,我是光杆司令。但是,县里说有枣花节,希望我再去做大讲堂的活动。我就去了。我没想到的是,两辆大巴拉来了上百号人,据说有省城里的,有榆林市的,还有对口扶贫单位的。

志愿者團队探访泥河沟村 摄影/熊悦
2018年的冬天,泥河沟村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跑到北京,到我家里。他们说,教授在泥河沟工作这么长时间,泥河沟现在确实比原来好多了,但是老百姓的兜还是空的。那一刻,我挺伤感的。这其实是在质疑我,教授你在这里的工作确实做了文化的挖掘,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赚钱啊!我说:“如果我既能够挖掘,又能让老百姓赚钱,我还是我吗?县委书记干什么去?那么多企业家干什么去呢?”在我家谈话的时候,我告诉书记、镇长,我带着学生工作了三年半的时间,做的是打地基的工作。文化资源的挖掘,如果能够利用好,就是乡村致富的一个前提。那36亩的古枣园,就是咱村的聚宝盆,你们会利用它吗?从哪里利用它?这是考验地方官、考验村民智慧的时候,哪里是一个教授可以包打天下的。
当然,我和那里的乡镇干部、县里的干部相处得非常好,泥河沟村在他们的努力下,在变化着。但是,通过这次对话,告诉我的一个事实是,做文化挖掘的工作,可能不像产业振兴那样,一下子就给村庄带来百万甚至千万的收益,它所发挥的效用是柔性的。恰恰因为它是柔性的,所以它是具有弹性的,所能发挥的社会效益又绝对是刚性的。这就是一个做民间文化研究的人应该具有的自信。因为有这份自信,我们才觉得从事这个专业是可以为乡村做实实在在贡献的。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