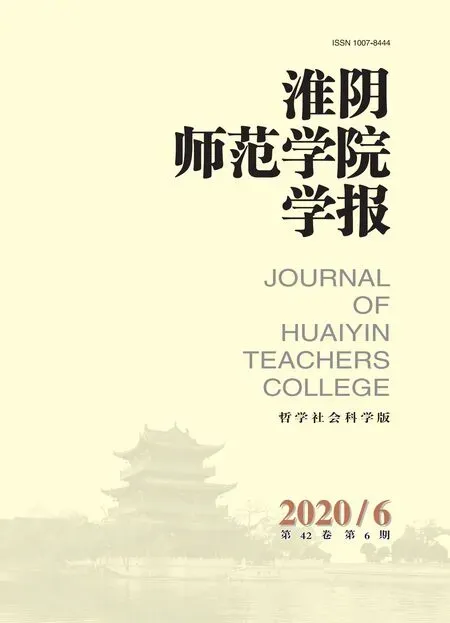有限经验活动域中的德性发动:孔子伦理思想中相对与绝对、基础性与后发性问题发微
朱光磊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孔子的伦理思想以仁为基础。仁既具有德性,又具有理性。在仁的自觉作用下,人需要通过理性认识来完成德性生命,不断超越气化生命的有限性,从而呈现无限的道德意识,并由此逐渐改善天地万物的有限气命。
气化生命本身既是有限的,又是活动的。仁的发动,需要在面对他者的前提下得以生成,而这些他者,既包含家人、朋友、社会上的陌生人等具体的个体,又包含家庭、国家这些抽象的整体。故仁在不同对象上,就要赋予其不同的德性意义,并产生相对与绝对的责任,基础性与后发性的德行。
一、道德心与认知心
孔子之心灵,可以从智、仁、勇三个角度来阐述。仁是道德心,为心灵之基础;心灵为了获取道德心,必然对道德意识具有清醒的认知,此为认知心,即为智心;获取了道德心之后,必然由内向外产生成就心灵所面对事物的行为,即为勇心。如此,智、勇,皆通过实践融合于仁心之中。蔡仁厚先生说:“儒家学问重实践,而不习惯于作概念性的思辨和知识性的论证。所以,儒家之学应该是行为系统的学问,而不是属于知识系统的学问。”[1]7虽然智含有知识的意味,但智本身不能独立存在,必然依附于仁之价值与勇之行为之中。仁作为道德心与智作为认知心,两者的地位并不等同。应该说,认知心并不具有核心的地位,但为了成就道德心而不得不辅翼之。然而,道德心倘若缺乏认知心,亦难真正成就真正的道德心。
两者的主辅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其一,从认知心说道德心。其二,从道德心说认知心。
(一)从认知心说道德心
认知心将世界分作主客,即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认知对象可以包含道德,也可以不包含道德。当认知对象是道德时,认知主体将获得关于道德的知识。而关于道德的知识,并不等同于道德。故而,纯粹从认知心出发来学习道德知识,理论上并不能保证人具有真正的道德。但是,当我们承认人本身具有道德心时,那么在本身的道德心的动力或者方向的作用下,辅翼的道德知识就会帮助道德心更好地体现出来。
这样一种理路,可以在后世朱子学的开展中获得印证。朱子讲格物致知,又讲理一分殊。实则朱子之心虽为气心,但在理气不离不杂的格局下,气心亦有性理之降衷。只是此性理的力量只是给予心体一个道德方向,并没有如阳明学那般既有方向又有动力。在本有的性理给予气心方向的基础上,气心贞定此理一,继而通过格物致知,一方面获取事物之理,一方面开拓心中之性,由此将理一落实到具体的分殊之事物上。
(二)从道德心说认知心
道德心本身主客不分,天下万物与我一体,故而道德心中所面对的事物,道德心无不愿成就之。但这一道德愿景一旦要落实,则如何成就之就成为一个问题。成就某事物,需要顺着某事物气命之条理来成就之,不能毁坏其气命之条理来成就之。这样一来,道德心就会转出一个认知心来,需要客观地观察认知对象,将气化对象中的条理总结归纳出来,从而才能够知道如何进一步改善成就之。
这样一种理论,可以在后世阳明学的开展中获得印证。阳明讲致良知,致良知不能是空头的玄谈,而需要具体的落实。比如,落实在父母身上就是孝心,孝心需要知道温凊定省之仪节。温凊定省之仪节的掌握,就是一门知识,需要认知心去发生作用。在道德心的动力下,心灵生成认知心,从而更好地落实道德心。一旦将道德心置于勇的实践领域,则认知心必然包含在此进程之中。
人生活于天地之间,天地之间万事万物本就参差不齐,而面对此参差不齐之气化世界,儒家主张自身的心灵要无待于此不齐,而从无限而人人皆有的道德心出发来改善此不齐的世界。改善不齐的世界,是道德心,而一旦落于实践,则必然需要用认知心来认知此不齐的特征。
因此,无论哪条进路,为了成就道德,认知心与道德心皆不可废。朱子与阳明的道路都包含于孔子所开出的理路之中。对于此两种心灵状态,孔子希望在道德心的主导下来引发认知心,而不希望仅仅专注于认知心却遗忘了道德心。从前者看,比如: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
人天生具有道德心和认知心,但此心灵功能只是形式化的,没有内容的。具体实施时,需要后天的内容填充进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孔子不是天生就知道事物之条理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一方面,面对各种事物,以自己的道德判断进行抉择;另一方面,见多识广,记住很多经验知识。
从后者看,比如: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孔子不希望樊迟仅仅在学稼学圃这些具体知识上用功,而是希望其突破具体知识的限定,呈现自身的道德心。如果学习者一味将自己陷于某一具体的事物知识中,而埋没了其道德心,那就是器。孔子不赞同这种学习方式,故主张君子不器。
二、伦常与正名
人的一生,开端于家庭,成熟于社会。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有所不同,家庭环境相对稳定,而社会环境则复杂多变。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里面的各种条理规则,也是气化世界的变现,故而参差不齐,可谓气化世界之有限性。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人终其一生,不能是一个无有肉体的灵,必然要落实在此有限的人生成长轨迹上来成就其仁,故必在道德心的观照下来成就之,既成就自己,又成就他人。“己立己达是对自己尽责,立人达人是对他人尽责,二者在实现时,难分其先后,且都是一无限过程。”[2]他人,既可以是家庭领域内的亲人,也可以是社会领域内的陌生人。而这种成己成人,需要凭借家庭、社会的存在来认知其不同特征,成就不同限定特征下的自己与他人。
(一)人在家庭、社会中的限定性关系
在儒家思想中,人的存在,并非首先是独立的个体而后自由地订立契约结合成社会组织,而是天然地内嵌在各种人伦关系之中,并需要在各种人伦关系中尽其应有的道德责任。
从经验层面看,我必然具有肉体的出生,故而我天然地内嵌在父子关系中;如果父母还生了其他的兄弟姐妹,于是我又内嵌在兄弟关系中;社会上不可能仅仅只有一个家庭或家族,我从某一个家庭或家族结识其他家庭或家族的成员,于是我又内嵌在朋友关系中;我与其他家庭或家族的异性重新结合构成一个家庭单位,于是我又内嵌于夫妇关系中;我与各类人等一起为了共同志向而奋斗,构成一个组织,具有职业的分工与协助,于是我又内嵌于君臣关系中。在这种五种关系中,父子、兄弟是纯粹家庭或家族的内部关系;朋友、君臣接连多个家庭或家族,属于社会关系;夫妇是两个家庭或家族的结合,属于家庭与社会皆有之的关系。这五种关系,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常态,也是常人生活难以去除的关系。儒家认为,人不应该逃避这种关系,而是要认知这种关系,并赋予这种关系以道德意义。
(二)五伦:横向的道德心灵的发动
上述的经验性的关系存在,构成了人的五伦。尽管五伦并不直接出现在《论语》中,但在《论语》中已经具有类似的记载,比如: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一入一出,展现出两种伦理原则。在家庭关系中,以孝、亲的道德原则来处理;在社会关系中,以悌、信、爱的道德原则来处理。不同的伦常关系,配备了不同的道德原则。这样的配比方式,在后来的孟子思想中获得了更为规范的整合。孟子说: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五伦是气命的限定,也是人的存在的特征。如果要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需要在此五伦的基础上配以五种德性。此五种德性,皆可看作普遍的道德意识从具体的人的存在关系这一通孔中表达出来的特殊性,对于关系双方都具有指导意义。此特殊性虽然附着于各种具体关系上,但都具有成就他人、成就自己的共性,在关系双方中共同构建理想的世界。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五伦只是粗线条地把握人的存在关系,更为细致的关系都会因人而异发生各种变动。(1)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的伦常是建立于血缘宗法制基础上的。其实不然。儒家的伦常是建立在普遍的道德意识与具体的气命限定特征上的。在先秦,气命限定所呈现的社会状态是宗法制,故儒家的普遍的道德意识需要就着宗法制来呈现,一方面无待于宗法制对于人的束缚而挺立人人具有的道德意识;另一方面以道德意识为动力来尽可能地改善血缘宗法制。在现代社会,血缘宗法制的色彩大大淡化,而呈现出新的限定性特征,故儒家的道德意识仍需要在当下的社会存在的气化限定中来谈具体的落实。
五种德性,从根源上说,来自人的普遍的道德意识。但由于伦常是人的生活的常态,故此德性的五种主体性的发动,就会客观化为道德规范。倘若人能够自觉到自身道德意识的流露,则会把这种德性的完成看作自身的道德责任;倘若人无法自觉到自身道德意识的流露,就会把此道德规范看作外在于我的强制性命令。在前者意义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伦常以及伦常所赋予的道德责任。倘若人人都承担其所在伦常关系中的道德责任,那么伦常关系就会成为一种合作关系,呈现出道德的价值。在后者意义上,如果人人都不愿意承担伦常关系中的道德责任,那么伦常关系会成为一种束缚——气化生命的限定性对于自由的、情感的、欲望的心灵的束缚。
(三)正名:纵向的道德心灵的发动
人是否愿意承担伦常中的道德责任,在自由心灵中没有必然性的发动。但一个社会的存在,必然要求每个人在其关系中有必然如此的发动。如果某人不能如此的发动,则其游离于存在关系之外。伦常关系的存在,对社会的存在具有规范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伦常关系虽然发生于主体与主体之间,但是这种关系客观化之后,就与主体一定程度的脱节。客观化的伦常关系具有自身的运作规律;主体无论自愿与否,都需要投身到伦常关系中去。伦常关系的自身运作规律,不是出于某些个体,而是出于人的普遍的道德意识,故单独的个体虽然偶尔游离于普遍的道德意识,但必然遭到以此普遍的道德意识为标准对其进行的判决。这种以普遍的道德意识出发来谈人的伦常关系,并赋予伦常关系以客观而必然的道德责任的做法,就是正名。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正名。前者是指具体的在此位的人,后者是指在此名位所需的道德责任。君君是指处于君位的人要具有君王的道德责任;臣臣是指处于臣位的人要具有大臣的道德责任;父父是指处于父位的人要具有父亲的道德责任;子子是指处于子位的人要具有子女的道德责任。人处在什么关系中,就需要具有这个关系中的道德责任,就能发挥此限定性的优长;人若不能承担这个关系中的道德责任,就会被此限定性所束缚,甚至任由此限定性的缺点发挥恶劣的作用。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正名是基于普遍的道德意识而对于人所处的共同的限定性关系进行道德的改善。故名分后面的道德责任虽然根本上源于每个人的道德意识,但一旦客观化之后,就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普遍的道德应然性,指向了一种制度建设。一切治理秩序与治理措施都由此正名为出发点。正名可谓普遍的治理伦理。
三、家庭伦常与社会伦常的异同
在五伦与正名所贯穿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伦常正名与社会的伦常正名既有一贯性,又有所不同。
从一贯性上看,家庭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都是道德意识的贯彻实施。比如: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仁者的好人、恶人,为其本有的道德判断,是道德心的表现。这种道德心所好人、恶人的范围,既可以是家庭的,也可以社会的。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一个人在家孝悌,说明他比较容易发动其道德意识。“仁心之显发,首先表现为孝弟,故行仁当从孝弟始。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孝弟是仁心最自然最直接的显现。”[1]86同样的道德意识,既然能够在家庭对象上发动,自然也能在社会对象上发动,故其对于国家也会具有忠诚的道德属性。这样的一贯性,一方面需要承认天理的发动扩充的次序,由互动最为密切的家庭关系出发,而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论语·学而》),另一方面又鼓励推己及人,不能将天理的扩充仅仅停留在家庭范围,而是需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由自己家人而推广到其他人,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2)这种不同,被称为等差之爱,亲亲之杀。然而,对于儒家主张的等差之爱,亲亲之杀,我们需要较为灵活地看待。一方面,儒家并没有让人永远停留在等差之爱上,而仅仅是承认等差之爱是起点,最终要完成的是天下万物一体之仁。另一方面,等差之爱不是道德意识本身,而是道德意识在有限性上的落实的表现。人与人的亲疏远近,基于人的有限性,基于天地生物之不齐。这是生命存在的限定性,亦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人的道德意识本身,则是纯粹的无限,故没有亲疏远近之别。然而,道德意识必然从有限的形下心灵中显现出来。形下心灵是具体的,存在于有限的时空中,而对对象具有远近亲疏之别。故道德意识之普照,也在形下心灵的影响下,而有了等差之爱,亲亲之杀。当然,这种远近亲疏也是从大体上如此说,具体展现是因地而异的。比如:如果一个人自出生以来,父母不去照管他,而是孤儿院之员工照管他,那么他的爱就会先顾及孤儿院之员工,而不会顾及自己之父母。如果孤儿院之员工对待他极尽刻薄之事,那么他也不会爱孤儿院之员工。爱的具体流露,需要人与人之间不断地友好互动,家庭这样的环境最利于友好互动,故爱最容易在家庭这样的环境中表现出来。
从不同性上看,家庭的伦常正名较为主观化,容易随意地发动变化;同时伴有亲情的润滑,容易发自于内心;社会的伦常正名较为客观化,不能随意地发动变化;同时伴有律法的准则,容易成为他律的规范。
从对父母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家庭伦常的特征,比如: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孝道需要子女继承父母的志向。但这个志向需要符合普遍的道德意识,如果仅仅是父母私人情感欲望的志向,则子女非但不需要继承,还要对父母进行劝诫。但这种劝诫又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具有柔性的。一次劝诫不听,就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就来第三次,隔一段时间再劝,慢慢让父母回心转意。当然,如果子女犯错误,父母更是可以用各种方法对之进行教育。双方以柔性的、可修复的互动关系为主。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对伦常关系进行多次实验,进行多次试错,最终演练出一个具有常态化的道德意识的人。也就是说,在伦常关系中,当一方不能履行其道德责任,另一方不能主动退出,仍旧要不断去帮助促成另一方履行其道德责任。
从对朋友、君臣的态度上,可以看出社会伦常的特征,比如: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所谓“无友不如己者”,即对于品性不好的人,可以与其断绝朋友关系。同理,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仁政的主张,但若没有君王采纳其意见,孔子亦非必须卖于帝王家。其言: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孔子可以离开家邦,去海外之地、蛮夷之乡传播其学说。这显示出儒者与君王不合作的态度。其后面的道理与“无友不如己者”是一样的,即在社会关系上,如果一方不能履行其道德责任,另一方为了对道德责任负责,可以不对前一方负责,而是与能够承担道德责任的其他主体建立起新的伦常关系。
家庭伦常与社会伦常的差别,在于家庭伦常中的关系主体不可退出,一旦退出家庭伦常就崩溃瓦解;社会伦常中的关系主体可以退出,一旦退出,可以组建新的社会伦常,社会照常可以良性运行。但是,社会伦常由于具有客观必然性,刚踏上社会的人就需要演练之后才能熟练掌握其运行规则,故家庭伦常的存在就是人的演练之所。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出门使民,都是社会关系中的行事。见大宾,承大祭,这种客观性的德性发动,需要在家庭家族中演练。当人掌握这种行事法则之后,再用到社会交往中,就能与社会的道德运行法则较为和谐地融合了。因而,虽然家庭的演练,从社会的角度看来,仿佛不甚规范,但它是社会规范得以遵守的前提。
由家庭伦常与社会伦常的区别,可以引出一个关系双方处事原则问题。家庭伦常可以引申为私人关系,而社会伦常可以引申为公共关系。两个主体之间,既有私人关系,也有公共关系。一般而言,两人处理公务,或者仅仅是路人之间的礼节性交往,则以公共关系为主;倘若进至私人情感的交涉,则以私人关系为主。然而,人与人之间,可能有价值性的正向与逆向的交往,对于这一点,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言: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以德报德,既有公共关系的回应,也有私人关系的回应。受恩之一方,既要秉持公心,以一般社会规范要求来回报施恩者,也要有个人的感激之情来对待施恩者。而以直抱怨,则仅仅具有道义为保障的公共关系的回应,不具有私人关系的回应。受怨之人需要从一般社会规范要求来惩罚施怨者,但同时尽量去除个人的私愤。这样一来,被罚的施怨者能够心悦诚服地受罚,不会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世代为敌。相反,如果采取以德报怨的方式,固然可以期待对方被自己道德感化,但此感化并不具必然性,反而为公共关系的不平等性开了错误的先河。一旦以德报怨成为常态,那么其他受怨之人想要以直报怨就容易受到道德的谴责,这反而会助长施怨者肆无忌惮地去做坏事。因此,人与人的社会交往都需要以公共性的道义为支撑,进行公平合理的交往;如有损益,需要进行规范化的弥补。而在个人私人的心灵上,则要感激施恩者,而不去计较施怨者。
四、家人之爱与故国之情
仁的发动,根源在于性,主动权在于心,所发在于情,情之必然性则谓之义。性具有必然性,道德之性是先天自主的确立,命定之性是先天限定的确立。道德之性落实在限定之性上,则就着限定之性而表现为心的活动。心所发动,即为情感,此情感既可以被限定的事态所牵引而遗忘了道德性的方向,也可以就着限定的事态来自觉地发出道德性的方向。心时时刻刻都处于一个具体的场景之中,故限定性不是如此就是如彼,心所发动的道德性亦是就着如此或如彼的场景来发动,故其所发之情,亦是千变万化,各有千秋。
(一)道德情感的正面发动
在心所处于的不同场景中,有些场景有利于情感中的道德性的发动,有些场景不利于情感中的道德性的发动。为了维持情感中的道德性的发动,故对于那些有利于情感的道德性发动的场景,需要加以特别的重视;在这些场景中所萌发的道德感情,也需要加以特别的珍惜。人的存在,最亲爱的场景莫过于自己所在的家庭,莫过于自己所在的祖国;故这种最为自然的道德感情,从小处看是家人之爱,从大处看是故国之情。对于家人的爱与对于故国的情,是人的情感发动中最为容易生成道德性的地方。(3)纯粹从德性的发动来看,倘若心所处的场景为中性,既不有利于道德性的发动,也不有碍于道德性的发动,则更能显现出德性本身与后天经验无关,而具有先天必然性。而在现实场景中,很少有完全中性的场景,反而有许多有碍于道德性发动的场景。然而,如下的场景——在与家人的关爱中,在与祖国的关爱中——则会有利于主体的道德性发动。
人在生命成长过程中,由家庭生活开始,慢慢进入社会生活。由亲人的小天地,慢慢进入陌生人的大世界。由家庭中的直观的情感慢慢演变为社会中的抽象的公共秩序。在家庭生活的直观情感中,个人感受的家人的爱,最为容易产生情感的回应。在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中,个人开始反思秩序与文化对于个体成长的塑造,并能够意识到国家与自我的千丝万缕地关系,而产生更为宏大的情感回应。因此,对于家人的爱,是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最为自然的道德情感;对于祖国的爱,是人在生命成长的反思过程中最为自然的道德情感。
这两种情感,可谓人的两大最为重要的道德情感。关于家庭之爱: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孝是家庭生活中重要的德行。这是个人生长过程中第一个形成的德行,也是最自然的德行,对限定性家庭经验赋予了超越的价值。“孝爱表明人的实际生存确实是超功利、超手段,甚至是超进化的,由生成意义的亲子时间而非生殖时间和物理时间所发动。”[3]孝道是以德性为基础衍生出来的第一个具体化的道德情感,在此基础上,可以随着生活空间的扩大而继续衍生出更多的德行,比如悌、信、爱、学文,等等。
关于故国之情: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
此言虽为孟子所载,大致也符合孔子之意,可以看为儒家传统中对于故国之情的注重。(4)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的故国之情,并非不分是非的狭隘的爱国感情,也不是对于三桓政权的愚忠,而是对于久浸于斯的乡土与文化的眷恋。孔子的学说,并不仅仅局限于鲁国,而是对天下广泛有效,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子欲居九夷”(《论语·子罕》)。
家庭之爱与故国之情,是人伦中最为基础的道德感情。如果连这些感情都违背了,很难说在其他领域中可以建立纯正的德行。所以,一个儒家的君子,如果他有家庭之爱,有故国之情,这样的人就可以很顺当地由爱家人而推及爱社会上的人,由爱自己的故土而推及尊重别国之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母国之爱。反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怎么能爱社会上的其他人;一个人连自己的母国都不爱,怎么能尽心尽意为其他国家服务?如果他表面上能做到这些,那么很有可能他的心中藏有更多的诉求与阴谋。
为仁,就是仁的表现。孝是仁的表现的第一站,也是仁的诸多表现的前提。有这个前提性的表现,那么在之后的诸多表现中,都能够步步趋实,不犯上,不作乱。
(二)基础德行与后发德行的矛盾
在儒家思想中,一般说来,仁表现的基础性德行与仁表现的其他德行具有一致性,都是德性自身在不同的生活场景的发动。但是,如果碰到某些特殊的情况,比如仁表现的基础德行与仁表现的其他德行之间产生矛盾,则儒家主张主体在个体身份的意义上暂缓后一种德行,而保证前一种基础性的德行。
在保证家庭德行的意义上,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亲亲互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父子之情是德性在家庭生活场景中所发动的德行。而社会公义是后发的德行。两者之间产生直接的冲突时,主体应该先保全前一种更为基础的德行,并通过非直接对抗的方式来协调社会公义的要求。比如,父亲顺手牵羊,儿子没有必要去检举揭发,而是劝了父亲之后,把羊还回去,并声称自己送回了走失的羊。
如果儿子并不是个体身份,而是一村之长,收到失羊人的报案,他要么辞掉村长的职务,以个人身份来协调矛盾;要么不辞掉村长职务,对父亲依照律法进行惩处。儿子以个体身份,是为了保持其德性发动的基础德行;儿子以村长身份,则是为了对于村长身份的道德责任负责。故无论如何选择,都是正确的,但儿子不能以村长身份来包庇自己的父亲。
在保证故国之情的意义上,也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伯夷叔齐。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齐景公非常富足,但其死后,老百姓都不称赞他。因为齐景公虽富而无德,其富足并没有与老百姓共享,而仅仅自己一人独享。伯夷、叔齐虽然不富,但有德行,故老百姓一直称赞他们。伯夷、叔齐的德行表现在哪里?程子曰:“伯夷、叔齐逊国而逃,谏伐而饿,终无怨悔,夫子以为贤,故知其不与辄也。”[4]97程子所赞扬的,是逊国而逃、谏伐而饿两事,伯夷叔齐对此终无怨悔,如孔子所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故逊国而逃、谏伐而饿都是求仁而得仁之事。
若说逊国而逃为仁,比较容易说得过去,朱子曰:“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4]97但说谏伐而饿为仁(亦即“饿于首阳之下”为仁),则需要作出一番阐释。
依照儒家义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可谓以武王之正义对抗纣王之不义。而伯夷、叔齐竟然叩马而谏,并且不食周粟,饿死首阳,明明是怀念商的天下,而不承认周的天下。伯夷叔齐这种遗民的态度,被认为体现了求仁得仁的至理,非但没有受到儒家的谴责,反而受到儒家的赞扬。伯夷、叔齐对于殷天下的情感是较为基础性的德行,而对于周天下的承认是后发的德行。两者产生矛盾时,儒家主张以个体身份保持基础性的德行,而暂缓后发性的德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故国之情,具有超越于政治立场的作用。无论当下的主流政治形态如何,遗民都可以保持对于旧朝的情感,并仍旧受到儒家的尊重。遗民的态度即个体身份的选择被儒家予以尊重,允许其个体与本朝保持不合作的态度。这样,既保全前一种基础性德行,同时不与后一种德行产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但若此人是一个商朝的将领,他要么以将领身份誓死抵抗周,成为顾炎武说的“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日知录·正始》);要么放弃将领身份,以个体身份做不合作的遗民。从儒家传统对于殷周之变的评价来看,以将领身份继续抵抗,虽然成就个人职务之私德,但助纣为虐,于天下为更大的不仁不义,故儒家可能更为主张后者的遗民态度。
综上所述,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作为仁的道德心给予实践的方向与动力;作为智的认识心给予识别具体而有限的对象的能力,两者之合力则是促成事物趋向完善。在人的生命中,作为根源的德性通过家庭环境而勃发,继而推广至社会,甚至于天下。由于人的经验认识是以主体自我为视角的变动性的有限活动,故家庭活动、社会活动,甚至游走于世界,都可以视为经验性的有限活动,并由此而生成不同的德行,具有相互性和绝对性的属性。在具体的场景中,可以有不同的德行的发动,但基础性德行优先于后发性德行。在两者一致的情况下,基础性德行与后发性德行可以相互融贯;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下,主体可以退出公共性伦常而以个体名义来选择保持基础性德行。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