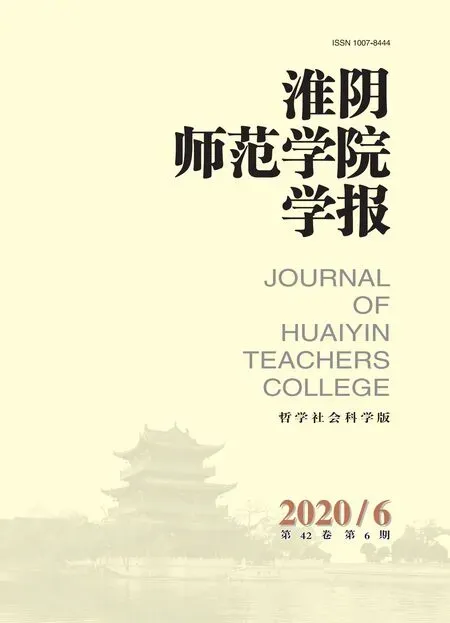“明刑”何以“弼教”
——唐律教化功能研究之一
厉广雷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着教化的传统,受此影响,中国古代法制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融合了诸多教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了丰富的法律教化思想,其中以儒家法律教化思想为主要代表。在中国古代法律史的历史长河中,唐代不仅以《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法律思想方面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在法制发展方面,还是在法律思想方面,到了唐代,基本上已经定型。因此,相较于其他朝代而言,唐律的教化思想和教化功能更具有鲜明的特性。唐律在传统儒家法律教化思想和唐代以前各朝代立法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在唐代法律教化思想的影响下,具有了鲜明的教化特性和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唐律的修订和具体规定之中。唐律的教化特性和教化功能以“明刑弼教”最具代表性。《唐律疏议·名例》中明确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那么,唐律的“明刑”是何以实现“弼教”的呢?
一、儒家法律教化思想对唐代立法的影响
唐律的修订历经《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律疏》而成现在所见的《唐律疏议》,其间的历史沿革离不开各个时期帝王的政见和立法旨趣。作为唐朝建立后修订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武德律》在颁行之初,唐高祖特意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发布了《颁新律令诏》。诏曰:“古不云乎:‘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故九畴之叙,兴于夏世;两观之法,大备隆周。所以禁暴惩奸,宏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自战国纷扰,恃诈任力,苛制烦刑,因兹竞起。秦并天下,隳灭礼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内骚然,遂以颠覆。汉氏拨乱,思易前轨,虽务从约法,蠲削严刑,尚行菹醢之诛,犹设锱铢之禁。字民之道,实有未宏,刑措之风,以兹莫致。”[1]470从这个诏令的内容来看,唐高祖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规律,治世需要教化,乱世才任刑法,显示出唐律的制定是为了“禁暴惩奸,宏风阐化”,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化,并总结出“安民立政,莫此为先”。当然,“永垂宪则”也罢,教化也罢,其终极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刑措之风”。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在《述古三首》中说:“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2]2316可见,法令的繁简程度对于法律的实施及其社会作用的发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唐律在制定之初就定下了“科条简要”的格调。作为有唐一代的开明君主,也是初唐时期有为的一位君主,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3]350这显示出唐太宗对待法律的慎重态度。他认为法律需要天下人共同遵守才能得到实施。同样,在制定了《永徽律》之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九月也颁行了诏令。《颁行新律诏》曰:“象服画冠,化隆上叶。道德齐礼,刑清中代。暨乎大道既隐,淳风已衰,圄犴所以实烦,手足为之无措。”[1]470这段话同样透露出教化不再的时期实施刑法的不得已,只有实施刑法,才能回到风清气正的教化时代。孟子早就说过“徒善”是无法“为政”的,必须把“善”和“法”结合起来才行,这一点在唐代得到了直接的体现。也就是说,要把儒家式的“德政”转化为儒家化的“良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唐初统治者制定并颁布了《贞观律》和《永徽律》,唐代由此开创并进入了“律令制时代”[4]。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帝王总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故在立法方面,帝王就是享有最高权力的立法者。也正因为如此,帝王的思想和言行总是影响甚至决定着法律的内容和旨趣。故唐初的这几位帝王对待法律的态度以及制定法律的旨趣为唐律教化功能的实现定下了基调。
通读过《旧唐书·刑法志》和《新唐书·刑法志》的人都会发现,其内容过少,很难与作为中华法系典型代表的唐律的地位相匹配。但我们很快又可以对这种现象表示理解。我们知道,史官修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通例,但众所周知的是,史官大多是科举出身,也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职是之故,他们不可能对法律文献或者法典判例做过多的记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二十五史”中大多的《刑法志》内容较少(1)“二十五史”中只有“十三史”记载有《刑法志》。参见张伯元:《法律文献学》(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44页。详细内容亦可参见邱汉平编著:《历代刑法志》,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甚至可以说只是简略记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一部好的法律对于国家政权的意义是重大的,而判断的标准就是轻重有序、宽猛有方。对此,长孙无忌在《进律疏表》中进行了精准概括:“轻重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斮胫剖心,独夫于是荡覆。”[5]1意即,良好的法律不仅有惩罚的作用,还具有很好的教化功能,而且后者的作用更大一些。所以,《唐律疏议》开篇就强调了“教”与“刑”的关系:“因政教而施刑法。”[5]1也就是说,是为了实施政教,才施行刑法,刑法的教化职责和功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们知道,《唐律疏议》是对《唐律》的逐条解释,可谓官方的立法解释,其目的是为司法官员在审判中适用法律提供必要的解释,并规定与法律原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这是《唐律疏议》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唐律疏议》还有另外一种功能,那就是为了更好地对老百姓进行教化。由于法律条文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老百姓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上会出现不理解或者理解有歧义的情形。《唐律疏议》则有效地避免或者减少了这种情形的发生。这是因为《唐律疏议》在解释时不仅是逐条解释,而且运用了多种方法进行解释,从而让法律条文在理解上更加清晰明了,最大程度地方便了人们理解和遵守。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法制》中说:“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6]376这段话可谓对法律教化功能的经典概括。从字面意思来看,顾炎武认为君王之所以不舍弃法令,并不是想依赖于法令来治理,而是为了更好地使老百姓的心变得正,使社会的风气变得纯净淳朴。如果做深一步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法律与教化的关系上,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用”与“本”的关系。也就是说,毫不松弛地推行法制禁令是为了更好地教化,让人们形成言行规范、心正意诚的良好习惯,从而让社会变得风清气正。与此类似,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也认为法律的功能主要在于教化。《史记·循吏列传》中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7]2373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这是养成宽仁温厚,维持人民内部和平和良好秩序,以及消灭由暴戾性情所产生的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当的方法。”[8]373-374从孟德斯鸠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的立法中包含了大量的“礼”的内容,或者说是很多原本属于“礼”的社会规范由于“纳礼入律”而被法律化了,这一点在《唐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外,受其立法目的(也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大家“相安无事”)的支配,法律的功能就被定位在了对老百姓进行教化。其具体方式就是让人们相互间“负有义务”,法律(包括法律化的“礼”)的教化就是达至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因为,法律的教化使得人们养成了良好的性情和习惯,个人性情变得“宽仁温厚”,个人行为也没有了“暴戾”和“邪恶”,社会秩序也就变得和平而良好。这一点也体现在《唐律》当中。
综上可知,无论是统治者的诏令,还是官方所修订的史书,抑或中西方思想家的著述中,均充斥着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教化的观点。唐人对于法律教化功能的认识在《隋书·刑法志》中更是得到了清晰的表述[9]695。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律的功能主要在于对民众实施教化,这一点在唐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笔者通过查阅儒家和法家经典文献,以及唐律的具体规定,发现唐律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明刑弼教”“辟以止辟”“刑期于无刑”和“移风易俗”。这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有着一定的交叉性,基本上把唐律在维系社会秩序和巩固国家统治方面所具有的教化功能体现出来了。其中,“明刑弼教”则是唐律教化功能的主旨和总纲,是研究唐律教化功能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明刑弼教”的基本含义
“明刑弼教”最早出自《尚书·大禹谟》。原文是:“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10]40经后世概括,形成了“明刑弼教”这一较为固定的说法。
关于“明刑弼教”的含义,从字面来看,“明”是宣扬、彰显、阐明、严明的意思;“刑”本意为刑罚,可引申为法律;“弼”是辅佐、辅助、助推的意思;“教”本意是教育、礼教、教化,可引申为道德伦理的教化。简言之,“明刑弼教”就是突显刑罚,强调礼刑关系中“刑”的作用,以辅助礼之教化功能的实现。其“刑”与“教”之关系定位甚为明确:“教”是目的,“刑”是手段,二者不可或缺,从而使人们因害怕刑罚而遵守法律,进而达到单独实施教化所不能实现的效果。
“明刑弼教”并非后世所加。据史书记载,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明刑弼教”这一说法。《全唐文·张说》载:“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辅皋陶,明刑弼教。”[11]985实际上,早在《左传·成公二年》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12]440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要提倡道德教化,而对于刑罚,则要谨慎和避免。其虽未明确表达出刑与德之间的轻重关系和主次地位,但对二者的偏好程度已显而易见。其言下之意,就是说道德教化要优越于刑罚惩罚。
由此可见,“明刑弼教”这一说法不仅在古代一直被使用,而且相对比较固定。既然“明刑弼教”能够准确表达“刑”与“教”之间的关系,又符合唐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唐律在制定时对其加以运用和体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明刑弼教”在唐律中的实现方式
作为唐律教化功能的总纲,《唐律疏议·名例》在开篇的“篇目疏议”中就明确表达了“明刑弼教”的本意:“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识沈愆戾”,“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5]1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统治者是“因政教”才“施刑法”的。其原因是老百姓当中有人“情恣庸愚”或者“识沈愆戾”,因此必须依靠法律予以制止,从源头上消除这种迹象,以维护礼教的权威。法律必须制定和实施,既是不得已的做法,也是人类社会的经验所在。“明刑弼教”可从国家、社会和家族三个层面去进一步认识。
(一)国家层面的“明刑弼教”
国家层面的“明刑弼教”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设定唐律的属性、目的和功能,从而为唐律在国家范围内具体实施时定下基调和准则。关于“明刑弼教”,唐律中最经典的一句概括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5]3这句话概括指出了唐律的功能,就是维护“政教”,其方式有二,但“德礼”为根本,“刑罚”(法律)为手段。这实际上就是对“明刑弼教”的变相解释和运用。唐代在实施和适用唐律时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有论者指出:“唐初确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指导原则,实现了封建伦理精神与封建法律内容的有机结合,构筑了严密的统治罗纲。这一基本精神一直贯穿于中唐,乃至唐末,而无大的变化。”[13]190
唐律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刑罚的适用方面,《唐律疏议·名例》“笞刑五”条的“疏议”解释说:“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诫,故加捶挞以耻之。”“故《书》云,‘扑作教刑’,即其义也。”[5]4可见,笞刑主要是对违法犯罪轻微之人进行训教,使其感到羞辱,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效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滥用笞刑。《唐律疏议·名例》“徒刑五”条的“疏议”解释说:“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置以圜土而收教之。”[5]5从中可以看出,徒刑的本意是以奴役来对犯罪之人进行羞辱,并通过劳作进行教化。由此可见,唐律不仅对刑罚本身的含义进行解释,还通过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强化,以显示出刑罚的本意在于教化。
在罪名规定方面,《唐律疏议·名例》“十恶(问答二)”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性质最恶劣的犯罪行为,并对每一种犯罪行为进行了详细解释,有的甚至还对犯罪行为的对象、方式、具体情形等进行了列举,以达到让人们充分理解该行为危害性和后果的目的[5]6-16。此外,该条还对其为何放在篇首进行解释道:“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其数甚恶者,事类有十,故称十恶。”[5]6由此可见,即便是被放在了篇首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其定位也只是“以为明诫”。此外,对于“十恶”中理解起来有歧义,或者比较复杂的情形,则结合儒家经典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解释,如对“大不敬”和“不孝”的解释。可见,“疏议”对“礼教”的义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使其更加具体化而具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那么,唐律为何不惜花费大量篇幅对“十恶”进行解释呢?细究起来,可以发现“唐律中规定的这十种严重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疏议’中所说的‘亏损名教’和‘毁裂冠冕’,也就是违背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传统纲常礼教和侵犯以君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犯罪。”[14]115实际上,除了“十恶”对国家统治的威胁最大这个原因之外,详细的解释可以使人们知晓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之大以及这些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为人们遵守法律提供具体的行为标准。另外,关于为何设立“十恶”之条,《唐六典·尚书刑部》中给出了非常经典的概括:“乃立十恶,以惩叛逆,禁淫乱,沮不孝,威不道。”[15]186可见,无论是“惩”和“禁”,还是“沮”和“威”,从其具体对象来看,无不关涉教化。这就显示出了“十恶”非常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对老百姓的言行进行规范,使其符合儒家教义,从而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目的,同时也显示了“十恶”罪名所要服务的终极目的——“教化”。
综上可见,在唐律中,无论是刑名的设定,还是罪名的规定,其中都蕴含了教化的本意。唐律在开篇就把“五刑”列出来,紧接着把“十恶”列出来,显示出教化的实施离不开法律的助推。这就是所谓的“明刑弼教”。
(二)社会层面的“明刑弼教”
社会层面的“明刑弼教”是相对于国家层面的“明刑弼教”而言,旨在对社会的特定群体进行教化。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便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2)《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参见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内言·小匡第二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职业分途的社会(3)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可以发现士、农、工、商四类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同而形成的,因而中国古代社会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职业分途的社会。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故对这四类民众进行法律教化,对维护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律中不乏这方面的规定。《唐律疏议·职制》“玄象器物”条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5]161在该条的“疏议”部分对“玄象”“天文”“谶书”等概念进行了解释,并对其范围进行了限定。在唐代,对于涉及天文气象事宜必须由秘书省太史局掌管,其他人不得涉猎。[15]302-305该规定旨在对“私有”玄象器物、“私习”天文等行为进行惩治。中国古代帝王自诩为天子,并认为其统治合法性来自天意,而天文气象关乎国运,故对天文气象之类的东西必须加以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对民众进行说教的事情必须由帝王来做,以便让民众“安分守己”,从内心接受统治。《唐律疏议·职制》“事应奏而不奏”条对“应奏”还是“不应奏”,“应言上”还是“不应言上”,“应行下”还是“不应行下”等进行了规定[5]166。这条规定看似很难把握,但在唐代社会,官员们对这些标准的把握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的。试想在整个社会都奉行儒家礼教的情形下,大家对所言所行是否得当,还是有一定的衡量标准的。即,只要是儒教要求的,也就是可以做的;反之,则不可以做。类似的还有《唐律疏议·断狱》“应言上而不言”条的规定。[5]476这也反映了唐代在推行法律教化后所取得的社会效果。
严厉禁止“造畜蛊毒”和“厌魅”行为。《唐律疏议·贼盗》“造畜蛊毒(问答四)”条规定,对于造畜蛊毒害人者要处以绞刑,而且规定,同居家口、里正或坊正、村正等要及时制止[5]285-286。唐代之所以对“造畜蛊毒”这种重大犯罪行为加以重处,是因为这种行为的实行者往往“心术不正”,并且这种行为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慌,从而使得社会秩序和国家统治出现危机。类似的行为规范还有《唐律疏议·贼盗》“憎恶造厌魅(问答一)”条的规定。对于以“造厌魅”或者“造符书”欲以杀害人的犯罪行为,以谋杀论减二等处罚[5]288-289。相对于具有实际行为的造畜蛊毒而言,这种行为具有巫术性质,故在处罚上相对较轻一些,但其主观恶行程度还是不小的,故统治者也极力加以禁止。此外,“十恶”之“不道”中对“造畜蛊毒”和“厌魅”也有所规定。可以看出,对于这些“旁门左道”,唐代统治者是严厉禁止的,旨在积极引导人们“改邪归正”。
应当说,相较于国家层面的“明刑弼教”,社会层面的“明刑弼教”更具有实际意义,所规定的行为都是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的。社会中的各个群体能否按照统治者的要求,从事合乎法律规定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法律教化推行的成败得失。
(三)家族层面的“明刑弼教”
如果说国家层面的“明刑弼教”是顶层设计,社会层面的“明刑弼教”是中流砥柱的话,那么家族层面的“明刑弼教”则是基础,因为它关系“明刑弼教”能否深入人心。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是以家族的形式聚集而居的,唐代也提倡家族式生活,故家族内部的管理是很重要的,它关系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唐律对不利于家族和谐稳定的行为也是加以惩处的。《唐律疏议·斗讼》“子孙违犯教令”条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谓可从而违、堪供而阙者。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5]375从该条律文的内容来看,“教令”一词的含义应当是指祖父母或者父母的意志或者命令。也就是说,子孙必须听从祖父母、父母的教令,还有就是要孝顺,否则就要加以惩处。服不服从教令本来是家族内部的事情,但唐律却对此加以规定,显示出唐律对家族秩序的重视。类似的规定还有许多,最明显的是唐律在“十恶”中对“不孝”也有详细规定。有论者指出:“在传统社会中,父祖家长对于‘不听话’的子孙,除自己动用笞杖教训督治以外,还可以借助官府的力量加以惩治。”[16]126唐律的规定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教令”一词在唐律正文(律文和疏文)中共出现47次之多(4)该数据统计所依据的唐律文本为岳纯之点校:《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在正文所包含的不同的律文或者疏文中,“教令”一词有的作为动词使用,有的则作为名词来使用,但无论怎样,都含有命令的意思。《唐律疏议》中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教令”,显示出唐律在家族内部教化中的重要性。一方面,这是对祖父母和父母行使教令权力的认可;另一方面,则是以国家强制力对祖父母和父母行使教令权进行保障。可以说是典型的“明刑弼教”。
综上,唐律之所以把家族内部的事务纳入法律的具体规定当中,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和礼教秩序,进而使人们形成“孝”和“忠”的观念。从作为“小家”的家族到作为“大家”的国家,从服从家族的教令到服从国家的礼教和法律,是层层递进而一脉相通的。可以说,家族层面的教化是整个国家教化体系的最基本单元,也是最重要的单元,这关系整个国家教化体系运转的好坏,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
四、“明刑弼教”——唐律教化的主旨和总纲
对于奉行儒家礼教的唐代统治者而言,唐律具有教化功能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因如此,唐律中充斥着大量的具有教化特性的法律条款和法律制度。这首先体现在唐律的目标定位上,即“因政教而施刑法”。就唐律教化功能在立法中的体现而言,“明刑弼教”可谓具有总纲性质,直接指明了唐律中“刑”与“教”的关系。长孙无忌等人在《唐律疏议》中的具有总则性质的《名例律》中即道出了唐律的旨趣,即“德礼为本”,而“刑罚为用”。这是对“明刑弼教”的另一种表达。
总之,唐代统治者从以往各朝代的立法经验和儒家法律教化思想出发,结合唐代法律教化思想和唐代社会的特殊性,坚持“德礼为主,法律为辅”的理念,制定出具有教化功能的唐律。唐律为了表明其“明刑弼教”的特性,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家族层面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表述,显示出唐律的目的就在于推行教化。可以说,“明刑弼教”不仅道出了“教”和“刑”之间的先后和主次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辅相成关系,而且是对唐律教化功能的非常直接而形象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