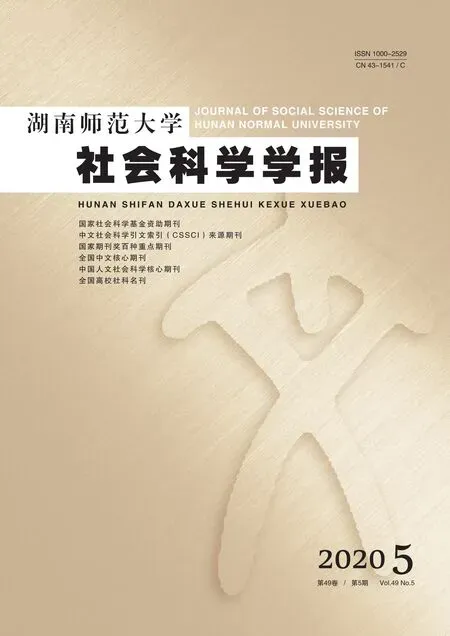近代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
张华清
一、近代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瓦解的主要表现
家族是我国古代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基层组织。它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消亡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全过程,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父家长制家族、宗法式家族、世家大族式家族和近代封建家族四种形态,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家族制度[1]。家族制度,作为我国古代基层社会一项传统管理制度,长期肩负着巩固国家政权、辅助社会治理的历史使命。但是发展至清末,作为封建专制统治两大柱石的传统家族制度与科举制度,已经成为延缓专制统治、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传统家族出现分化,新式力量迅速崛起,传统家族制度逐步走向瓦解。
(一)传统家族分化
1.多数家族趋向没落。明清两朝,在科举制度的鼓舞和导引下,各地家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山东地区,明清两朝涌现出二百余家科宦家族,其中在省内比较著名、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就有六七十家;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收录了明清江南地区三百余著姓望族;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列出嘉兴地区望族便有九十一家之多。足见明清两朝家族发展之盛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止,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宣布灭亡。这些重大变故,给科举起家、依靠封建统治庇护的传统家族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传统家族立足的平台被摧毁。科举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自开设以来便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家族开启了一条通过读书科考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跻身上层社会的途径,造就了大批地方家族。地方家族的兴起,为封建统治培养了精英人才、整合了社会资源,巩固了基层统治。故而,李志茗在《科举制度之废除及其后果——兼析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称:“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既是一种极富创意的文官考试制度,又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社会整合机制。”[2]科举制度的废止,堵塞了士子文人通过科考跻身上层社会的途径,摧毁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家族的发展平台,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传统家族的衰落。另一方面,地方家族的经济来源被切断。明清以来,在科举制度引导下,在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制约下,我国地方家族秉持“诗书传家,科宦兴族”原则,推动家族发展。故多长于治家,拙于经营。家族经济来源相对单一,大部分家族依靠官员俸禄、田产、房产租赁收入维持家族开支。其中官员的俸禄收入不仅是家族的重要经济来源,而且还是家族在乡邑间威望和地位的重要标志。科举制度的废止,不仅断绝了地方家族通向仕途的渠道,也大大减少了家族的经济收入。多数传统家族羞于经商,拙于经营,而又仕途无望,一时难寻新的生存之道,只能坐食山空,导致家族逐步衰落。
2.少数家族革新转轨。读书科举虽然是我国古代家族发展最理想的途径,但是由于名额所限,注定无法满足大部分人对于功名的渴求。即使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明清时期,科举之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得通。冯尔康曾推断称:“科举制度下有功名的士人名额所占比例最多不超过10%,最低只有1%左右。”[3]故而,在家族发展中,不乏有识之家,根据族人实况为族人制定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湖南长沙曾氏家族教导子弟要勤劳、节俭、谦虚、廉洁,倡导耕读持家。曾国藩就曾提出:“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4]嘉兴姚氏家族规定:“至十五六岁而不能造就读书者,宜早乎学习商业。”[5]嘉善顾氏家族规定:“若十八九岁学业勿进,宜早令别治生理。”(《顾氏新谱·遗训》)桐城刘氏家族坚持“耕贾并重”(《同治桐城刘氏宗谱》卷一《家规》)。广西西林岑氏家族将“耕读工贾俱为本业”写入族谱(《光绪西林岑氏宗谱》卷三《祖训》)。科举制度废止后,甚至在科举制度废止前,这些家族便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他们或者接受西式教育,或者从事商业活动,或者继续坚持耕读结合,成功实现革新转轨,推动家族继续发展。这其中以湖南长沙曾氏家族为代表。
曾氏家族是清代后期崛起的地方家族,曾国藩是家族的代表人物。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人。他一生谦恭勤政,功勋卓著,被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家书》包含着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治军从政等多方面的经验和心得,成为后世家族教育的成功范本。曾国藩深知官场之艰险,认为科举误人太深,不希望后人当官。他在给四弟家书中提道:“吾精力日衰,断不能久作此官,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之家为本,乃是长久之计。”[4]耕读持家,以耕养读,以读促耕,两者相辅相成。故而,科举废止后,曾氏家族没有受到重创,依照家训推动家族继续发展。在数学、外交、化学、文学艺术、军政实业、翻译诸多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卓越人才:如曾广钧、曾昭权、曾昭桓、曾宪源、曾宪琪、曾宪澄等都在数学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曾广植及其子女曾昭氚、曾昭氙、曾昭氕,在化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其子女多是留美化学硕士或博士;在文学艺术方面,涌现出美术教育家曾昭杭、文博专家曾昭燏、篆刻家曾绍杰、导演曾宪涤、画家曾宪杰、清史专家曾宪楷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氏家族后人还担任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如曾昭抡为著名教育家和化学家,曾任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燏为著名考古学家,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宪植,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第四届执委会副主席,还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曾氏家族成为近代传统家族革新转轨的成功典范。
(二)新式力量崛起
科举废止、清朝覆灭,导致传统家族制度走向瓦解。以西式教育家族与军阀集团为代表的新式力量迅速崛起,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辛亥革命后数十年间掌握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命脉。
1.西式教育家族的涌现。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列强势力的深入和西学的渗透,部分先行者率先接触到西方科技、文化与思想,并接受西式教育,培养子女,从而造就了一批西式教育家族。这些西式教育家族与成功转轨的旧式家族有所不同。成功转轨的旧式家族,如湖南长沙曾氏家族、江南钱氏家族等,也多有子弟前往国外接受西式教育。但是,旧式家族均有着悠久发展历史和文化积淀。而西式教育家族多是白手起家,或者是商业家族,借助西式教育实现家族发展。其中海南文昌宋嘉树家族便是最突出的代表。在中国近代家族中,宋氏家族权势之鼎盛,人才之济济,影响之巨大,罕有其匹。考其家族发展,宋氏家族并不是累世大族,主要依靠实业起家,教育兴族,是新兴的西式教育家族。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的宋嘉树(1864—1918年),字耀如,生于海南岛文昌县,原名韩教准,后随堂舅之姓改为宋。他出身贫寒,迫于生活压力,幼年先后游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与美洲古巴等地。1880年进入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神学院学习,1885年毕业,次年回国,曾在苏州、上海等地传教,并执教于教会学校。1892年后,宋嘉树辞去教会职务,开始创办实业,投资创建书馆、面粉厂、烟厂、棉纺厂,积累了丰厚的财富,成为上海著名的实业家。在游历和创业过程中,他较早接触到西方文化与教育,为宋氏家族接受西式教育、实现家族崛起打下基础。宋嘉树先后育有6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宋氏六姐弟均接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长女宋霭龄就读于美国乔治亚州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是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的女性;宋庆龄少年时代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新式教育;宋美龄幼年在家学英文,后就读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子大学;长子宋子文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次子宋子良曾到范德堡大学学习,三子宋子安就读于哈佛大学。良好的西式教育,以及宋嘉树广泛的交际与社会影响,为宋氏六姐弟参与政事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宋霭龄与孔祥熙联姻,宋庆龄与孙中山连理,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凭借孔、孙、蒋家族的强力支援,宋氏家族活跃于政治、外交等领域。宋氏家族“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家族”[6]。纵观宋氏家族发展,其以实业起家、以西式教育兴族,而又依靠婚姻关系得以壮大。宋氏家族的兴起,为近代家族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2.新旧军阀集团崛起。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军人在巩固国家政权和捍卫疆土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军事家族却始终得不到充分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军队与政权之间的微妙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军队能够巩固一个政权,同样也能推翻一个政权,历史上不少开国之君便是通过兵变实现了朝代的更替。所以,历代统治者多重文轻武,对军人尤其是军事将领是爱恨交加。再加上科举制度侧重于文官的选拔,故而传统家族多是文化、科宦家族,军人之家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
近代军阀集团的崛起,是随着科举的废止、封建统治的土崩瓦解而出现的。军阀集团的崛起,正是我国传统家族制度走向瓦解的重要标志。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传统家族制度遭受重挫,禁锢在军人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为封建旧军阀、新生革命军阀形成以及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提供了生长的沃土。清亡时,军队内已是派系林立,其中以袁世凯一系实力最强。袁世凯死后,军阀为争夺领地,北洋军阀、西南军阀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北洋军阀派系繁多,分为直系军阀、皖系军阀、奉系军阀、西北系军阀等;西南军阀分为滇系军阀与桂系军阀。国民党军队也分为中央系列、晋系、新桂系、湘系、川系、粤系、黔系、陕系及新疆系。新旧军阀之间开展了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不仅如此,在剧烈的时代变革中,军人反而以自身的独特优势掌握了社会发展的主动权。杨天宏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传统的重文轻武价值观念的变化,知识阶层地位下降,军人地位急剧上升。更重要的是,科举这一维系文官政治的制度的废弃,为军人秉政打开了方便之门。”[7]同时,“一筹莫展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纷纷弃文从武……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8]。军人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促进民国时期“政治掮客”盛行和军政体制建立,影响了近代中国数十年的发展方向。
二、近代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瓦解的原因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传统家族制度的形成“必有其不得已之故”[9]。同理,它的瓦解也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根本原因: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作为农业大国,男耕女织、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长期统治着我国古代社会,传统家族制度也正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基层组织制度。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农业受到重视,商业发展缓慢,经济运行平缓,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巩固国家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家族制度正是契合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与科举制度相互配合,在巩固封建统治、培养精英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八世纪中后期始,世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英法德意等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而此时,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我国各地悄然出现,并在南方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科举制度以及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形成的传统家族制度,明显无法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已经成为维护和延缓封建专制统治、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久闭的大门,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签订。印鸾章所编《清鉴》中详细记载了清末政府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通商开埠条约:“(丙戌十二年)中法天津条约第六款内开北圻与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各省陆路通商章程”[10]“(丁亥十三年)五月奕劻孙毓汶与法使续议界务约五款、商务专约十款”[10]“(丁亥十三年)冬十月奕劻孙毓汶与葡使罗沙议订中葡条约及专款”[10]“(癸巳十九年)冬十月与英议定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条约”[10]“甲午光绪二十年春正月,驻英使臣薛福成与英外部续议滇缅条约二十款”[10]“甲午光绪二十年,二月驻美使臣杨儒与美外部续订华工条约六款”[10]“乙未二十一年,三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订立马关和约十一款”[10]。这一系列条约的签订、租界商埠的开设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不仅促进了沉寂数百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复苏,同时也唤起了国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意识。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议》中指出,我国数千年来以锁国主义立于大地,所依赖的便是包括家族组织在内的群治。这种方式有利有弊,在“内竞”的单一背景下尚可推动国家的进化和发展。但是,在“外竞”形势形成后,包括“家族组织”在内的诸多群治现象必须加以“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11]。由此可见,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要求,终止八股科举,消灭传统家族制度,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和时代的呼声。
2.直接原因:科举废止与清朝覆灭。一方面,科举废止冲击了家族制度的存在基础。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究其原因,科举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家族子弟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跻身仕途,进而反哺家族,推动家族不断壮大,造就了一大批地方大族。科举制度的废止,冲击了传统家族存在的基础,造成传统家族的分化和混乱。刘佰合、蒋保在《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中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社会整合中心趋于模糊,从而逐步造成了社会分化瓦解、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12]同时,新式学堂建立,“旧有书院一时改为学校”[13],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14],使早已习惯八股科考的地方家族文人士子失去了进身的平台,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侯光陆、陈熙雍《冠县县志》“风俗”称:“迄光绪三十一年停止科举,创办学堂,幼年士子无路进身,乃改肄新学以为弋取功名计。热心向学者寥若晨星。”[15]文中描述的虽然是科举废止前后冠县的地方家族及文人士子的状况,却也是当时整个国家教育形势的缩影。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科举制度的废止给传统家族带来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清朝覆灭摧毁家族制度的政治保障。科举制度、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政权,三者密不可分,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家国同构观念的笼罩下,科举为地方家族提供晋升的阶梯和持续发展的平台;而地方家族为科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为朝廷培养所需的优秀人才。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较长的时间里共同承担着保障我国封建社会协调运行的重任。而封建政权又是科举制度、传统家族制度得以运行、发挥作用的政治保障。清朝的覆灭,标志着我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从根本上摧毁了家族制度存在的政治保障,传统家族走向没落,家族制度失去了依附。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时期,封建家族制度“已竟不能维持”[16]。
三、传统家族制度瓦解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经说:“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17],家族制度的瓦解既有其积极推动作用,又有其消极社会影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一)积极推动作用
在封建社会后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发展时期,家族制度“从总的倾向说,起着十分恶劣的作用。它阻滞社会生产的发展,维护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宣扬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根源”[1]。近代家族制度的瓦解,在改变社会结构、破除劳动者人身束缚、加速封建专制覆亡、推动民主革命开展、开启近代女子教育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1.改变传统社会结构。我国自古崇尚儒术、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管子·小匡》便有“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的论断,“率视工商为末务”,认为“(商业)虽于民生国用非不讲求,究皆成法相仍,未能别开生面,以为耕田凿井,安甿庶之常规,服贾牵车,逐锥刀之微利耳”[18]。这种社会结构和思想认识在我国古代持续了数千年。明朝中后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其局限性越发明显。家族技术垄断、劳动力缺乏人身自由、商业受到抑制等都严重制约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传统家族的解体,进而封建王朝的灭亡,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士阶层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平台与阶梯,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明显下降;商业发展桎梏被破除,并受到充分重视。近代启蒙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称:“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19]而军人作为一股新兴势力迅速崛起。罗志田也在《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指出:“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团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20]而且军商结合,如鱼得水,掌控着中国近代政局发展。相比之下,“农”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至此,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得以改变,为新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
2.破除劳动者的人身束缚。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由的劳动力。早在明末清初,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有些商业发达地区,甚至出现“小民做工或负贩就食他乡者什之九等”的状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三·徽州府》)。但是,传统的家族制度对劳动者的人身束缚却没有放松。一方面,传统家族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重视科举,轻视农工生产,不允许族人外出务工、从事商业活动。另一方面,族内大量事务如婚丧嫁娶、时节祭祀等都需要族人随时参加。不按时参加族内活动便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以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为例,每年春秋、元旦都要在家庙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每年祭祀之日,族人群集到祠堂签到,由族长主祭。除了庙祭外,每年清明、十月、冬至等时节,族众还要到先人墓所进行祭奠[21]。这就需要族人长期稳定地待在家族所在地,限制了族人外出的自由。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家族的管束放松,打开了长期束缚在族众身上的枷锁。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以南京为例,1912年人口为269 000人,至1936年增加了数倍,达到了1 006 968人[22]。增加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自由劳动力。
3.加速封建专制覆灭。科举制度和家族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存在和维系的两块柱石。尤其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和家族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巩固封建统治、维系明清国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地方家族,不仅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也是科举制度的忠实守护者,肩负着多重历史使命。而家族制度便是协调家族关系、组织族众担负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故而,徐扬杰在《中国家族制度史》中称:“家族制度成了封建政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成了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血缘关系产生的族权成了仅次于政权的一种有系统的权力,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在一定程度上讲,清朝统治的延续,得益于传统家族制度“维护和延缓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1]。
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式教育的兴起,地方家族迅速衰落,传统家族制度走向瓦解。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打破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淡化了忠孝一体观念,动摇了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柱石,加速了清朝统治的覆亡。
4.推动民主革命开展。科举制度的废止、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打破了禁锢在国人思想上的枷锁,民主和科学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清末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民国五年二月十四日记载:“自光绪庚子以后,改设学堂,不数年停止科考,并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学洋夷之学,留学日本者至数万人之多,赴西洋各国之学生数亦不少……洋学既兴,孔孟之学遂无人讲,中国人均尚西学,则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皆置诸如何有之乡,遂养成许多叛逆,未越十年,即行返国,凭据要津,至宣统三年,突然蜂起,革我清之命,改称民国,号曰共和,而乱臣贼子乘势行其素志,窃据神器,号令天下,暴敛横征,民不堪命。”[14]文中,刘大鹏以满清遗老的视角看待社会变革,对民主革命认识多有偏颇。但是,透过字里行间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举废止后,传统家族制度走向瓦解,新式学堂、西式教育以及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从而导致了民主革命的爆发,清朝由此走向了灭亡。不仅如此,之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提出、中华民国的建立,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乃至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都是民主意识深入人心、专制思想受到批判的重要表现,也都是传统家族制度进一步走向瓦解的过程。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土地革命、农民政权建设等消灭了家族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终止了族长族权的统治,彻底消灭了传统家族制度。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进一步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开展。
5.开启近代女子教育。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为长期被拘于闺阁内院的女性打开了枷锁与牢笼,拉开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序幕。在我国古代数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相夫教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剥夺了女性接受教育、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从而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科举制度废止后,传统家族走向瓦解,束缚女性的两道藩篱被打破,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取得快速发展:首先,形成完备的女子学校教育体系。各地设有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师范学堂,并发展女子留学教育,设立专门的女子学校。就初等教育来看,1907年,除个别偏远的省份外,各省都建立了女子学堂。全国女校391所,在校女生11 936人,占当时学生总数的2%。到1918—1919年间,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教育都有了长足发展。初等小学女生人数已增至190 882人,比例也上升到4.3%。高等小学女生24 744人,占全国5.5%(《最近卅五年之中国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和留学生教育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其次,课程设置齐全,当时的师范学堂的基本课程,已经包含了修身、教育学、国文、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等,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在吸收西式教育课程设计基础上,保留传统教育内容。再次,女性教育师资得到充实。如嘉兴县,1905年王琬青创办女子学堂,1906年更名为嘉秀公立女子学堂,民国后更名为县立女子初等高等小学。该校设有五个初小班、三个高小班和一个初中班,在校生二百人。而且配备大量女性教师。据统计,当时全校有教师40人,其中女教师38人[23]。由此可见,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破除了禁锢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拉开了近代以来我国女子教育的序幕,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同时,培养了诸如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秋瑾、何香凝、雷洁琼、邓颖超、曾宪植等一大批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乃至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女性。
(二)消极社会影响
家族制度在我国历行数千年,至清末虽弊病百出,但仍有其可取之处。近代家族变迁,昭示着传统家族制度逐步瓦解并走向消亡。这虽然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加速社会改革进程、促进新式教育崛起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旧的制度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国情怀、冲击了精神信仰,造成了人才断层,对我国近代社会产生消极影响。
1.弱化国人家国情怀。儒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治理体系。家国同构,是我国古代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家国情怀便是家国同构理念影响下形成的重要情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精神命脉。在这个视域下,家是浓缩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历史时期,地方家族在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家族教育与管理、维护地方安全稳定、营造良好的乡风民俗等方面为朝廷、地方政府分忧,做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成为封建王朝思想意志最为坚实的支柱和忠诚的执行者。而地方家族士绅阶层,秉承“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原则,牢固树立族群同心、家国一体理念。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无数的国人牺牲自我,顾全大局,以实际行动抒写着家国情怀,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共识。
科举制度的废止、清朝的覆亡,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家族制度存在的基础,使士绅阶层失去了进身的平台,致使地方家族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立场和坚守,去寻找新的发展出路,从而出现了家族变迁局面。所以,吉尔特伯·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指出:“各地方政府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体化开始衰落,它消弱了家庭、血缘亲族以及其他形式的地方主义。”[24]如此一来,家国同构的体系走向瓦解,个人主义抬头,传统的家国情怀逐步弱化。
2.冲击传统道德精神。我国传统家族,尤其是宋代以来以科举起家的各地家族,作为封建统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封建社会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肩负着诸多的历史使命。其中,开展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是其重要职能。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另有一番道德精神之维系主持,种种制度,全从其背后之某种精神而出发,而成立。”[25]科举制度维系封建道德精神、传承儒家价值体系的使命,很大程度上由地方家族承担。传统道德精神固然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纲常名教内容,但也有着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睦邻里等优良传统和礼义廉耻的行为规范。科举的废止、传统家族的没落,将传统道德精神一并予以否定,给地方家族和士人精神信仰带来巨大冲击,进而导致乡风民俗的恶化。民国版《冠县县志》描述了清亡后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称:“近年新政迭颁,扞格不入,时髦乘机睥睨纵横,公德堕落,欲望蓬勃,浑厚古风已一落千丈,而新旧隔阂亦愈去愈远。三十年前向无土匪,自民国后连年匪患,遍地萑苻,烧杀劫掠,民无宁日。民变而匪,固由生活之艰,亦由人心之败坏。”[15]《退想斋日记》亦有记载“变乱以来民气不靖,打架斗殴之案层见叠出,只因刑罚太轻,民不畏法,而杀人命案日见其多。凶犯一经逃脱,日久无人缉获,官亦视为固然。草野人民皆谓上既无君,吾等皆可横行矣”[14]。山东冠县、山西晋祠的状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废止、清朝覆亡、家族变迁促进传统道德体系瓦解,进而导致信仰缺失和公德堕落的社会状况。
3.造成人才培养断层。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地方家族重视教育,建私塾,延名师,在家族子弟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家族教育体系。地方家族教育在弥补政府教育资源不足、加强教育体系建设、推动基层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培养社会精英人才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直接导致家族变迁,加速了家族制度的瓦解,进而造成了社会精英人才断层和乡村教育倒退。
一方面,造成精英人才断层。科举制度自产生起,作为官吏选拔制度,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为巩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起到重要作用。萧功秦对其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称:“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26]而科举制度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广大地方家族的努力和付出。在科举制度导引下,各地家族重视教育,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家族教育模式,源源不断为朝廷培养精英人才,造就了一大批蜚声海内的科宦世家。清末,科举制度戛然废止,传统家族和士人丧失了立足的平台和进身的阶梯。所以,何怀宏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中指出:“由于将文化精英补充进上层的渠道实际上已经中断,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数量就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文化精英的延续接替出现了‘断层’,这种‘断层’甚至意味着断绝。”[27]以浙江定海县为例,科举废除至民国十二年近二十年间,接受高等教育并取得新式学位的共十一人:理工硕士二人,农学硕士一人,管理学硕士一人;文学学士三人,法学学士一人,商学学士一人,工学学士二人。十一人中,五位留学美国,一人留学日本,四人毕业于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大学,一人毕业于国立复旦大学[13]。而且,这种精英人才断层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精英人才培养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高校205所,本专科在校生11.7万人,研究生629人,教师1.6万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如内蒙古、青海等地尚未设立高等院校[28]。
另一方面,导致乡村教育倒退。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地方家族长期担负着开展乡村教育的重任。从教育形式来看,主要包括父祖亲教、塾师教育、书院教育;从内容来看,包括文史教育、科举教育、荣誉教育等。各地家族举全族之力,为家族子弟乃至同乡异姓子弟提供优质的系统教育,弥补了国家正规教育的不足,确保了乡村精英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和体系性,使我国乡村教育长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式学堂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清王朝的灭亡,传统地方家族走向衰落,乡村教育体系难以维系。从而导致乡村受教育人数锐减,精英人才断层,地方士绅阶层瓦解。夏曾佑在《论废科举之后补救之法》中指出:“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29]侯光陆、陈熙雍《冠县县志》“风俗”也称:“自改建民国,一般心理渐向科学。惟以旧学潜势颇生阻挠,入主出奴,门户标榜。是以统计全县人数,受高等教育者不过千分之一二,普通读书识字者尚不及百分之十。教育既未能普及,公民程度自尔低落。”[15]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据统计,1949年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其中90%的文盲在农村[30]。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家族教育体系瓦解,从根本上讲是传统家族制度瓦解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近代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历史的选择。它在改变传统社会结构、破除劳动者人身束缚、加速封建专制覆亡、推动民主改革进程、开启近代女子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国人家国情怀弱化、精神信仰受到冲击,并在一定时期造成人才断层,对我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