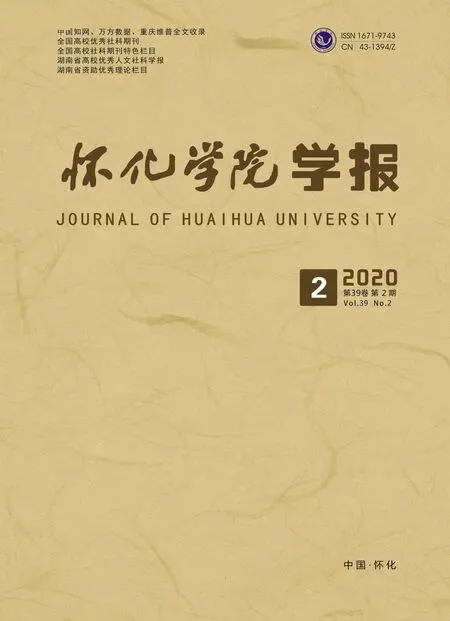是“旁系别支”还是“田氏篡齐”?
——论湘乡派之成立
欧阳春勇
(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怀化418000)
湘乡派可说是以曾国藩为该派盟主,曾门之中的“四大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为核心骨干,另加曾国藩的一众幕府宾僚以及人数可观的湖湘文人作为羽翼的一大古文流派。
一、问题的提出
湘乡派最早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1]888《论桐城派》一文:“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由此可知,李详主张曾国藩开创了湘乡派,而桐城派则是该派远祖,换而言之,湘乡派是桐城派的一个旁系别支。这可不是个别观点,如姜书阁[2]75先生在《桐城文派评述》中亦云:曾国藩“中兴桐城文派”,“曾国藩之湘乡派——桐城派之别支”。与之大为不同的是,吴孟复[3]150先生在《桐城文派述论》则言,“‘桐城’自‘桐城’,‘湘乡’自‘湘乡’”,特别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别。舒芜[4]154的《曾国藩与桐城派》中,明确表示曾国藩与其说是桐城派之“中兴元功”,不如说是创湘乡一派“干的是‘田氏篡齐’的勾当”。总的看来,这两种观点尽管大为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都认同曾国藩开创了湘乡派,分歧则在于前者倾向湘乡派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后者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的独立文派。而与这一前提截然相反的看法则是根本就否定曾国藩开创湘乡派,且不认为存在什么湘乡派之说。如曾国藩之好友吴敏树不满曾氏将其纳入桐城派之中,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指出,文章艺术所以有流派之分,只不过是风气大概罢了,其中往往是无能之人,假托门户以自重,像唐代韩愈、柳宗元,文章承八代之衰,却是柳宗元不师法韩愈,而与之并起,那些为文有一定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5]394吴敏树对宗派之说不以为然,认为一代文宗韩愈尚未创派,又遑论后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胪列清代古文家文集之时,用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三种类别来归纳概括,而将曾氏列入“不立宗派古文家”这一类。由此可见,在张之洞心中也不认为曾国藩开创了什么湘乡派。只要稍加留意吴、张二人之言论,还会知晓,他们不但否定曾国藩开创湘乡派之说,甚至都不认为曾氏归属桐城派。而王先谦[6]2则针对张之洞《书目答问》未将曾国藩列入桐城派,在其《续古文辞类纂·例略》中写道:“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与!”显然,王先谦主张曾氏理应归入桐城派。其实,王氏不仅主张曾国藩应归入桐城之列,而且还是桐城的大功臣。如言:“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7]33而刘声木[8]3则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完全依仗桐城派文学风尚漫延天下的指导思想,将“上至明代归(有光)、唐(顺之),下逮近世马(其昶)、姚(永朴、永概)、贺(涛)、王(树楠) 诸老”[8]180,统统纳入桐城派师承传授格局之中,认定曾氏论文宗旨就近而言祖述姚鼐,为文义法则取之于桐城诸贤,即使扩以汉赋之气体,“亦颇病宗桐城者之拘拘于绳尺”,但仍无改其属于桐城派的本质属性,所以干脆将其编排在卷四姚鼐名目之下,显然是把曾氏当作姚门弟子来看待的。
综上所述,可见湘乡派是否成立存在争议。鉴于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是各家倾向急于给出自己的结论,而没有做出科学而严密的学理论证,因此本文就其能否成立尝试做一番详细的学理探析。
二、核验文学流派成立的必备要素
考究“流派”一词的用例,较早的如唐释玄奘[9]506《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之“漕矩吒国”条中有云:“鹤萨罗城中踊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初唐时,张文琮《咏水》诗曰:“标名资上善,流派表灵长。”[10]504显然此处“流派”均指水的支流,用的是该词原义。而从原义引申,用例早的如程大昌[11]112《演繁露》:“摴蒱之名,至晋始著,不知起于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所引说明流派最早是指水之分流,进而引申为事物之别支。
中国学术流派源头最早可追溯至班固《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之说,当然班固所言尚非指向文学流派,还只是将溯“流别”之法用于学术史研究,从不同源流来探寻各家缘起。而溯“流别”之法用于文学批评领域,例证不胜枚举。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有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12]82,显然是用水的同源分流现象比喻文体之间的离合。章学诚[13]179《文史通义》卷五《诗话》在比较《文心雕龙》和《诗品》时曾言:“《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钟嵘《诗品》以溯“流别”著称,书中品评了自汉以来120多家作品,并对其中30多家一一寻其本源,最后归为《国风》《楚辞》 《小雅》三大体系,犹如水“流别”而成三大“派”一样。
就湘乡派而言,从上文所述,可知其究竟能否称得上是一个独立文学流派,还颇具争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需首先对其予以“正名”,解决“湘乡派”的成立问题。至于它与桐城派的关系究竟怎样,是趋于顾盼牵连的内部分化,还是偏向悬崖撒手的双峰对峙,则是另一紧密相关的问题。探讨文学流派的成立,学界一般主张对其整体创作风味进行确认。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指出了把握文学流派的有效方法,就是“以味不以形也”。诚然,文学流派整体而又独特的创作风味是其生命所在,但是,人尽皆知,味者,玄之又玄,岂易言谈。何况派中成员之间,肯定存在个人风格差异,如此,何以确定文学流派的同一性,在文学流派的实际认定中,要拿捏准确相当棘手。
按照新版《辞源》中对文学流派的界定,它是指“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的作家之自觉(如江西诗派) 或不自觉(如边塞诗派) 的结合”[14]3519。自觉型的,领导者与追随者往往同声相应,相互唱和,共同切磋,“不但产生了一批风格相近似的作品,而且结成了文学见解相接近的创作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在活跃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名目”[15]1-2。而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则与之不同,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具备自觉结合的创作群体,也不存在某位领袖人物有意识地发表创作声明,但是他们在精神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心灵上也达到一定的契合度;若是从创作题材、审美趣味及表现技法等方面考察,则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有所仿效和师承,已经形成审美趣味、艺术风貌上大约一致的作品系列,细细琢磨品味,从而可以发现他们作为流派的大致脉络和基本特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在定义文学流派及其基本类型时,也有类似而更为详细的观点,认为文学流派是指“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16]1243。其中又可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的……是自觉的文学流派。”“另一种类型是……半自觉或不自觉的集合体……被后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冠以一定的派别名称。”[16]1243
学界一般认可江西诗派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型的诗歌流派,但是本派宗主黄庭坚在世时也未知“江西诗派”名号,其得名于人们对它的研究后之追认,得名时间晚于流派本身的形成时间。因此“我们观察古代文学流派,即使是如上述自觉型的流派,也不能先看他们在形成当时是否挂起‘招牌’,而是要更加注重他们的‘货色’,即他们是否够得上一个流派”[15]2。那么,论证湘乡派的成立与否,也不能局限其是否打出流派名号,而要看重其是否兼具能够成派的核心要素。换而言之,就是先需确定该派成立的基本标准是不是已经达到,若已齐具,自然就成立。但是依据上述界定在具体考察一个文学流派时,究竟其属于“自觉”还是“不自觉”型,常会陷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因为对之如何确定,难以拿捏到位,甚至还隐然含有将其划分等级的倾向。为此陈文新[17]8-9先生对流派问题重新做了深入探究,带着质疑“常识”而又提供新的“常识”之学术锐气,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为行之有效核验流派的方法,就是从文学流派成立的基本标准,即“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流派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来考察。据此,我们可以从这三大要素逐一考核湘乡派,看其是否兼具。若是齐具,自然成立。
三、湘乡派之成立论析
首先,从流派统系方面核验湘乡派。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文学活动的展开都将处于一定的文学传统之中,一个文学流派对统系的选择,不仅决定着该派的艺术追求,也影响其艺术水准。若是选择统系不当,这一流派的创作成就也会随之降格。“统系意识在流派事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一个流派在艺术追求上的主动状态”[17]12。
那么,湘乡派是否有自己的统系,统系为何?李详[1]888在《论桐城派》一文中指出:“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钱基博[18]19《现代中国文学史》亦写道:“湘乡曾国藩……自称私淑桐城”,“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伟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曾国藩出而矫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由此可见,李、钱二氏所云,在肯定曾国藩开派之功时,都强调了该派对桐城派有所承袭。而桐城派的古文统系脉络中的代表人物早就已是学界常识: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与曾巩以及明代的唐宋派之归有光。桐城派以辞章为凭借,注重“文人之能事”,其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义法”论文,但是实际更为看重为文之“法”,而不是作品之义理。其第二任盟主刘大櫆将方苞所重之“法”在《论文偶记》阐释相当清晰,注目“神”“气”。其第三任盟主姚鼐虽然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学相济,其实落脚还是在于文辞,注重文之意境。正如姚氏[19]94所言:“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自然界中的事物和现象有阴阳刚柔之别,文学风格亦有阳刚阴柔之分,但是桐城诸老“气清体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少创雄奇瑰伟之境。
湘乡派宗主曾国藩立足桐城前辈之肩,扩充统系,欲救其懦缓之失,别于姚鼐《古文辞类纂》不选经、子以及六朝之文,而另编选《经史百家杂钞》,增选一些经、史、诸子之文以及辞赋作品,又从时事需要,着眼政事,另列叙记、典志之类。湘乡派另一重要代表黎庶昌,又在姚、曾二氏选本基础之上编定《续古文辞类纂》,以之强化统系。姚鼐[20]146《古文辞类纂》文体类分十三,其《序》有曰:“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黎庶昌另又指出:“姚氏纂文之例,首断自《国策》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21]375姚鼐依尊而不录之法,削去了“六经”和子家作品,黎庶昌变为既尊应录原则,依其类目续本除了赠序和碑志两类无补,增补了其他十一类,而且又依曾本之目补了叙记和典志两类。续选本来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极费周章,因为既要保持“续”之本分,又要体现一己特色。总的来看,黎氏选本搜求古文共计四百有余,经史百家,无不兼备,补充了姚氏《古文辞类纂》的不足。其选本内分上、中、下三编。上编选经、子之文,中编采《史记》 《汉书》 《三国志》 《五代史》及《通鉴》之作,下编则基本为方、刘前之文。每编分若干类,却悉能依其性质为依归,做到搜辑完备,而又无偏颇拘谨之嫌。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黎庶昌,深受曾国藩影响,其续本没有亦步亦趋姚氏,而是针对桐城末流孱弱弊病,推崇曾氏“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21]375的魄力,选文之时态度严谨、标准周密。他在续本《序》中写道[21]376:
昔孔子论文,义主修辞,而以立诚文本……余今所论纂……凡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有一不备者,文虽佳,不入。
黎氏强调选文“立诚为本”原则、“辞工且雄”标准以及合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要求,既有矫正桐城末流文风之功,也有宣传湘乡派文统之意,价值不容忽视。
其次,从流派盟主(代表作家)方面核验湘乡派。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会有自己的盟主或说代表作家,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既会考察其理论主张,更会看重其文学创作,其中盟主或者代表作家不论是他们的理论贡献还是创作成就都显得举足轻重。一则在于他们为本派赢得了显赫声誉,二则是其理论成就或创作实绩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甚至很大程度上流派的兴衰嬗变,实际是其代表作家兴亡递变的体现。
就湘乡派而言,其盟主自然要推曾国藩,代表作家则为其门下四大高足——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与吴汝纶。李详[1]888指出:“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钱基博[18]19亦云:湘乡曾国藩“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可见李、钱二人关于湘乡派的宗主及代表作家的看法倾向基本一致。陈三立[22]621则有诗句声称:“湘乡接桐城,雄跨欲无对。羽翼郭与吴,云龙瞻进退。”诗句中之“湘乡”指曾国藩,“桐城”指姚鼐,“郭”与“吴”则分别为郭嵩焘和吴敏树。陈氏将曾国藩视作文派领袖,以郭嵩焘和吴敏树为其羽翼。郭嵩焘志在事功,与曾国藩趣味相投,文风相近。而吴敏树一介文士,生平际遇迥异于曾、郭,而且独立意识强烈,不仅反对时人宗派之说,且因歆慕欧、归简淡文风,又得洞庭山水之助,文章“逸趣横生”“神愉而体轻”[23]563,与曾国藩行文雄奇骏迈大相径庭。因此好像吴氏唯曾马首是瞻的“云龙瞻进退”之说不符吴氏本心,所以视吴氏为曾之羽翼,值得商榷。但是,总的来说,湘乡派以曾国藩为宗主,像其挚友郭嵩焘,以及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的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均为其代表,却是无疑。
最后,从流派风格方面核验湘乡派。一个文学流派成立的基本标志是其独特的创作风格,统系的选择确定以及流派盟主或代表作家的出现,当然其终极指向还是文学流派的整体创作风格的形成。同一时期各个流派的较量,或者后起流派对其前流派之抗争,其焦点所在还是钟于流派风格之上。
就此核验湘乡派,那么,其整体风格会是怎样呢?其代表作家各自风格,前人多有经典表述,不妨先从此入手。李详[1]888评价曾国藩文时曾说:“文正之文……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然有声。”钱基博[18]143评价曾文基本沿袭李详之说,但又有所补充,还论及湘乡派重要代表作家之文风,指出:
自曾国藩倡以汉赋气体为文,力追韩昌黎雄奇瑰伟之境,欲以矫桐城缓懦之失……而裕钊笔遒而气未雄;汝纶则气恢而力未浑;然造语洁适,特为简练……武强贺涛……特为朴厚,章妥句适,自然雄肆,不同曾氏之为缛瑰,亦异张吴之少遒变……其次新城王树楠……以沉郁跌宕,生创奋勃,得韩公风力之骏迈,而不徒寻章摘句之瑰伟;此其所以胜曾氏而为张吴之所畏也。
湘乡派以曾国藩为宗主,一些挚友和亲传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均或深或浅地受其影响,行文亦为之感染。上述引文虽是谈及该派成员个人风格,若再察究湘乡派作家实际古文创作和理论主张,不难得出其流派创作风格则是气势与声采兼备。其实,湘乡派人士多热心济时,创作多为经世之文。综合来看,湘乡派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都独具特色,迥异于桐城派。
湘乡派作家不是坐而论道,空言理论,古文批评、写作思想都是紧密联系创作实践,体悟得来。湘乡派古文写作超越桐城,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文章思想内容上的拓张、充实,注重经世致用,联系社会实际。刘师培在名作《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曾批评桐城派方苞,认为其文“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但是“桐城文士多宗之”[24]240。而湘乡派博涉宏通,不泥一端,如曾国藩在熔铸姚鼐之考据、义理、辞章三合一说基础上,又采刘大櫆、姚莹列“经济”为“行文之实”之见,主张四者缺一不可,并将四者比附上孔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用以显其权威。湘乡派古文写作越出桐城,另一突出表现就是文风取向上力矫桐城派的平缓柔弱而尚雄奇刚健,这也正好与其文学经世主张及其所写文章思想内容相协调。桐城派初祖方苞倡为雅洁之说,定下严格词语禁戒,追求语言清澄无渣。而后之作者谨守其义法,更有枵腹之徒,依托门户自重,用以文其疏陋,于是为文力求平稳板正,不用瑰玮华丽之词,不发慷慨激烈之语,因而既缺声采,又乏气势,淡乎寡味,窳弱不堪,犹如黎庶昌[25]44一语中的那样:“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
总而言之,抛开过往以自觉或不自觉两类实难以在操作层面达成共识的衡量流派之尺度,综上依次从流派的统系、流派之盟主(或说代表作家)和流派整体创作风格考察湘乡派,显而易见,其流派成立必备要素齐具,因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湘乡派是一个能够成立的文学流派。不仅如此,由上述论证亦可看出,其与桐城派在流派统系、流派盟主(或说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等三个方面也大为不同,所以说湘乡派不应仅作为文学集团或创作群体来看待,而且他也不应只是依附于桐城派的一个旁系别支,而是一个摆脱桐城派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但是,从上述的分析中也不难发现,桐城派总是与湘乡派纠葛在一起,是其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至于湘乡派与桐城派之关系究竟如何,那还需另外专题论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