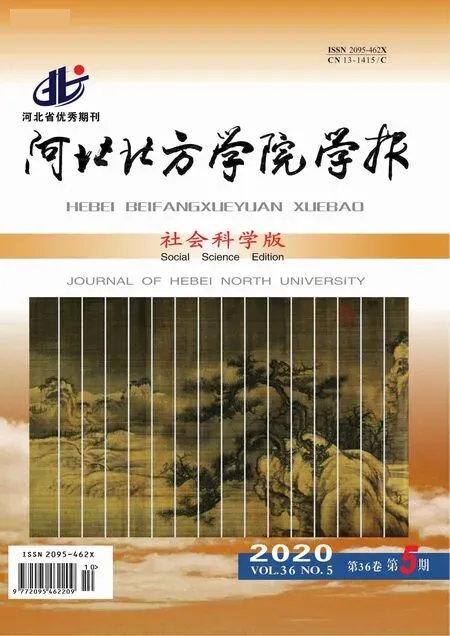论汤显祖《南柯梦记》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陆 敏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汤显祖的《南柯梦记》是一部极具说教意义的传奇剧本,告诫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1]1。戏曲理论家吴梅也曾评论:“托喻乎落魄沉醉之淳于生,以寄其感喟。”[2]但《南柯梦记》的剧本情节皆从贴近生活的角度展开,汤显祖以主人公淳于棼“一醉入梦”“梦了为觉”以及“情了为佛”的一生为引,穿插众生在饮酒和穿衣等方面的生活细节,传达出其对日常生活中寻常物象的审美态度。
一、日常生活的众生相
日常生活在个体生命中留下了相似又相异的轨迹,并与世间一切活动紧紧相连。汤显祖以精湛的笔法塑造出《南柯梦记》里的众生相,他们有喜有怒,有怨有恨,有啼有悲,这些人物心理的诸种变化皆是日常生活中每一平凡个体的缩影。按照性格特征,剧中人物大体可分为3类,即生活化人物、模式化人物与多面式人物。
(一)生活化人物
生活化人物通常最能折射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真实状态,这类人物在《南柯梦记》中既有社会底层人物也有上层权贵。他们或是在对话中多用日常口语进行交流,以溜二和沙三为代表;或是与平常人一样有最普通却又至真至性的情感,以槐安王后为代表。
溜二和沙三是扬州城出了名的游手好闲之辈,衣衫破落,整日借着口才钻懒帮闲,勉强度日。在接到淳于棼的吃酒邀请后,他们一同应道:“便去,便去。”[1]22淳于棼向新结识的两位友人问候“久闻才识面”[1]22时,溜二和沙三却错以为“九文才食面”,回复道“十个更酸咸”,并解释“把九文钱吃个面,没盐醋的,因此小人加上一文”[1]22,又戏称自己平日里“玲珑剔透,人前打眼睛”,“哩嗹花啰能堪听,孤鲁子头嗑得精”[1]23。可以看出,溜二和沙三在自述与交谈间全用俗语俚言,极具个性化特色,符合市井人物的身份,也贴近受众对这类人物的日常认知,读来真实可感。槐安王后作为上层人物代表,先是担忧爱女的婚姻大事,亲自安排琼英郡主、灵芝夫人和上真子等人前往扬州孝感寺听经,还特意叮嘱她们“但有英俊之士,便可留神”,“不少的儿郎俊,打叠起横波着人”[1]20;再是忧心女儿的身体,特意求来《血盆经卷》,一心盼望病重的爱女可以得此脱离苦海;当爱女芳陨,地位尊崇的王后亦如寻常老妇般闷头痛哭,念叨着“俺的儿呵”[1]129。在《南柯梦记》里,无论以溜二和沙三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物,还是以槐安王后为代表的上层权贵,他们虽在社会阶层上有高低之分,但都以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化语言表达了与常人相同的喜怒哀乐。汤显祖依据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观察,用细致的笔触表现出众人在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性情。
(二)模式化人物
模式化人物通常性格单一,形象扁平,但又往往极具概括性,如瑶芳公主和右相段功。前者是淳于棼的妻子,后者是淳于棼的官场对手,他们都对淳于棼的人生历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瑶芳公主是《南柯梦记》里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自小便受到中国传统式儒家教育——“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而从子;四德者:妇言、妇德、妇容、妇功”[1]19,在这种教育熏陶下的瑶芳公主有比一般女子更温良恭俭的脾性。如第十六出《得翁》,瑶芳公主看到夫婿淳于棼因未得知生父的下落而困扰,遂即主动请缨向蚁王探听消息,“早已做下长生袜一双,福寿鞋一对”[1]64,同时又询问驸马“你如今可想做个甚么官儿”,“卿但应承,妾当赞相”[1]65。再如第十一出《召还》,病重之际的瑶芳公主仍惦念“驸马久在南柯,威名太重……待俺回去,替他牢固根基”[1]120。从始至终,她都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守护者形象。《南柯梦记》中的反面人物非段功莫属,他作为槐安国权臣,对上逢迎,对下剥削,最担心的便是有朝一日大权旁落。从淳于棼进入槐安国起,他便“则怕此君权盛之后,于国反为不便”[1]66。淳于棼初任南柯太守时,段功虽认为他贪恋美酒难堪大任,但鉴于淳于棼驸马的身份暂时闭口不言;听闻堑江失事,段功作为一国之相不担忧战情,反而庆幸淳于棼威名少损;及至瑶芳公主病逝,段功将淳于棼先前的错处一一向蚁王进谏,“中宫宠婿,所言如意,把威福移山转势。罢了!非俺族类,其心必异”[1]144,致使淳于棼失去蚁王信任,最终被遣返人间。在明朝社会中,权臣也常相互倾轧,淳于棼的遭遇实为明朝官场的一大缩影。汤显祖用精湛的笔法将一代权臣内心的衡量计算刻画得淋漓尽致,也将明朝官场的阴暗面真实呈现在受众面前,引人深思。
(三)多面式人物
这类人物通常处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内在性情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变动,给人以立体感和丰厚感,淳于棼便是一个典例。淳于棼在进入梦境成为槐安国驸马前,整日里饮酒千杯,酣醉如泥。从凡界偶然进入蚁国世界,他不仅寻得良缘,还借着裙带关系成为南柯太守,更将南柯治理得“物阜民安,辞清盗寡”[1]98。汤显祖通过设置“醉梦”这一情节,不仅帮助主人公淳于棼实现了姻缘与功名的双重夙愿,也使这一人物形象更为立体:淳于棼既有纵酒贪杯与眷念权势的欲念,也有为情所执和重情重义的柔情。如在选择瑶芳公主墓址一事上,右相坦言蟠龙岗乃国家命脉,淳于棼却坚持认为蟠龙岗更能庇荫子孙,期待“生男定要为将相,生女兼须配王侯,少不的与国咸休”[1]132。及至返回人间,淳于棼眼见瑶芳公主将要飞升天界,深情相约此后重做夫妻,言语细致入微,感人至深。由此可见,淳于棼身上交织着人性中的美与恶,他并非是一个完美的人物,而更像是一个对情痴迷和对权执着[3]的普通人。
汤显祖在《南柯梦记》中塑造了不同社会阶层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同时也从人物真实性的角度加以细致考量,将现实社会里凡人的子女之情、朋友之谊以及对权力的贪欲融合到剧中人物身上,使他们不再仅存活于书本中,而是以更贴近日常众生的形象走到受众面前,使观众在欣赏这些剧中人物时,亦可看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态。
二、入世与出世的精神向度
汤显祖在《南柯梦记》中刻画的芸芸众生,在处世方法与精神层面都受到儒家和佛家的双重影响。以淳于棼为例,他的一生大致分为醉梦前的贪酒好眠、醉梦中的平步青云以及觉梦后的立地成佛3个阶段。在这3个人生阶段中,儒家的入世思想与佛家的出世思想始终影响着淳于棼的人生选择。
儒家思想倡导入世情怀,鼓励世人通过修身、齐家、治国以及平天下来实现对社会和家国的责任。从醉梦前淳于棼的日常生活看,他渴求建功立业与封妻荫子,但种种愿望在现实生活中都遭受到不可估量的阻力,先是因酒后误事被贬官职,再加上已到而立之年,却依旧“名不成,婚不就,家徒四壁”[1]40。他整日消极倦怠且无所作为,唯有通过呼朋唤友和饮酒作乐打发时光。而在梦境中,淳于棼成为槐安国驸马,并担任南柯太守这一要职。“梦代表着一种愿望的满足。”[4]当现实无法满足人的愿望时,梦境便成为实现人们内心欲望的途径。可见,建立不朽功勋与获得美满姻缘皆是淳于棼深藏在心底的主观愿望。治理南柯时,淳于棼坚持采用儒家之道,宣称“只用孔夫子之道,这佛教全然不用”[1]88。他还以《孟子》学说教化蚁国众人要懂得“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梦中醒来后,淳于棼在契玄禅师织造的幻境中得以与生父相见:
淳于棼父:我儿,你今后如何生活?
淳于棼:依然投军拜将。[1]167
尽管淳于棼在梦中已切身体会到官场险恶,但他依旧期望能够重返沙场建功立业直至官拜将侯。无论醉梦前、醉梦中还是从梦中初醒,淳于棼的言行都体现出儒家“入世”思想对众生的深刻影响。
佛家的最终修学目标是倡导出世,即通过修行使人勘破宇宙万物,摆脱世间情欲与功名利禄,在精神上获得超脱与涅槃。从梦中返归现实后,淳于棼仍执着于梦中经历。在游僧指点下,他清斋闭关且日夜念佛,后又在契玄禅师所设的水陆无边道场上“燃指为香,诚心发愿”。契玄禅师先将梦境中的因果向淳于棼一一解释,道明诸种点滴不过是情障所致。“情障”,佛经解释“爱恨恩仇,皆是情障”。淳于棼一点痴情顿起,便自此沉醉梦境当中。第一次在盂兰节听经时,淳于棼对瑶芳公主敬献的金凤钗和通犀小盒等物什赞不绝口,并直言人与物什都是世间罕有。按照佛教的说法,这是动念[5]。契玄禅师原本想借观音座前白鹦哥叫醒淳于棼,无奈其只将“蚁子转身”错认为“女子转身”。睡梦中淳于棼的魂魄在紫衣使者的带领下进入蚁国,并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另一个世界,流连于对权势的眷念中,这是因空见色。但最终,淳于棼妻离子别,被遣送人间,方知色即是空。契玄禅师进一步道破:淳于棼在盂兰节听经时所遇到的女子本是蝼蚁,而女子所持的金钗犀盒不过是槐枝和槐荚子。至此,淳于棼大梦骤醒,终于看破红尘,立地成佛。《般若无知论》载曰:“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6]所谓“泥洹”,即“涅槃”,这一佛家用语意指众苦永寂、不生不灭,远离情感和欲望的生存境界,也即成佛。经过渡化后的淳于棼由先前对名利富贵的贪恋步入禅宗所宣扬的空无虚境,最终回归到人的本真状态。
“从热眼看世界,到冷眼看世界;从凭剑改造现实,到以笔揭露现实”[7]是汤显祖一生的缩影。万历二十六年(1598)前,汤显祖把满腔热忱都倾注在政治改革上,为官期间政绩斐然,深受百姓拥戴,但却遭到上级官吏与地方势力的敌视。万历二十六年(1598)后,历经仕途坎坷的汤显祖辞官回乡,专注戏曲创作,这一时期他与达观禅师来往密切,思想上也深受佛家影响。1600年,汤显祖创作完成《南柯梦记》,以巧妙的艺术构思将自身的人生阅历折射到主人公淳于棼身上,将其塑造成一位从热衷入世到最终看破红尘而选择出世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儒佛两种思想在淳于棼身上并非各自独立存在,而是在他的不同人生阶段显露出争锋与交融。在入世与出世两种思想的熏陶下,淳于棼最终建立起一种随遇而安、随缘任运与达人大观的处世态度。这既是淳于棼对入世与出世两种境遇的选择,亦可看作是汤显祖在历尽人间沧桑后对入世与出世的深刻思索。
三、生活物象的审美书写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列斐伏尔主张“让日常生活变为一种艺术品”[8],即通过艺术化的审美方式重塑日常生活。汤显祖在《南柯梦记》中以一种别致的视角发现日常生活中潜藏的乐趣,以审美式的态度凝神观照一酒一槐与一钗一衣,并饰之以惊艳的辞藻,将美还原到日常生活中。
主人公淳于棼在弃官后长居广陵城中,“庭有古槐树一株,枝干广长,清阴数亩,小子每与群豪纵饮其间”[1]3。在这片小天地里,他和一群酒友远离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千百年来,“酒”广泛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与沟通的载体。依偎在古槐之下,淳于棼与友人自由地饮酒谈心,高声歌唱“人生只合醉扬州”[1]3,分别时亦“恨不和你落托江湖载酒游”[1]4。淳于棼在遭遇贬官挫折后并未就此断绝入世的心思,“酒”便成为他失望又无望处境下的唯一寄托。汤显祖凭借自己多年的人生体验,将淳于棼落寞、孤独和期待的内心活动全部投射在“酒”这个日常物象上,也使其对酒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依赖。此外,汤显祖在《南柯梦记》中描绘了一系列受惊时借酒安慰和凯旋时喝酒庆祝的场面,甚至通过周弁之口道出“从古来谁不饮酒?天若不爱酒,天应无酒星;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1]113的豪言壮语。饮酒与品酒成为淳于棼日常生活中最顺理成章而又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
“槐树”在《南柯梦记》中不仅是淳于棼居住场所中的一个重要物象,也是淳于棼梦中大槐安国的栖身场所,蚁王更是亲下诏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曾提及早期人类对树木花草的崇拜:“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它们跟人们一样都有灵魂,从而也像对人一样地对待它们。”[9]中国从周朝起便将槐树作为社树,并赋予其“吉祥”之意,民间更形成一种“槐树崇拜”的原始信仰。因此,槐树拥有最美好与祥和的外在形貌与内在底蕴。例如,槐树在淳于棼眼中展现出翠幽之色,在蚁王眼中呈现出“绿槐风下,日影明窗罅”[1]6之态,在瑶芳公主的视野里流露出“绿窗槐影翠依偎”[1]63的绵绵深情。“秋到空庭槐一树,叶叶秋声,似诉流年去”[1]3,汤显祖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出发点,将槐树赋予神性与灵魂,使庭院中的槐树不再仅有装饰这层意义,更将其化作可以听懂人的心声并与人交谈的对象,成为淳于棼在夜静无人时的知心朋友。“此中槐树,号为声音木,我国中但有拜相者,此树即吐清音。”[1]120可见,人们对于通灵的槐树可以预知吉兆与带来好运深信不疑。此外,通灵的槐树也在淳于棼立地成佛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盂兰节听经时,淳于棼对着金钗与犀盒赞不绝口,直到经由契玄禅师的点拨方才明白这些不过是槐枝和槐荚子一类的物什。至此,淳于棼的欲念与心境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从贪权倚势与迷恋红尘,回归到了“悟真假虚幻,参透色空本空”的本真状态。
衣着饰品作为人的外在面貌,通常象征着人的审美水准和社会地位。汤显祖将审美眼光凝着在众人日常生活的穿衣打扮上,并将审美式的情感体验投射到这些服饰中。如剧中男性角色偏爱“素、朱”,而这两种颜色又都是槐安国蚁王的专属。他出场时身着素锦雪袍,遣送淳于棼返回人间时则是一身朱衣,天子的威严与尊贵自不待言。女性角色则偏爱“红、翠”,用“翠、红”表现少女服饰的颜色,用“翠”表现女子首饰的颜色[10]。贴众出场时穿着“一尖红绣鞋”[1]27,饰以“双飞碧玉钗,小玉纳汗巾儿”[1]27;瑶芳公主身着藕丝碧罗衣,佩戴缕金香穗,作为蚁族中人,也学得世间女子般“施朱傅粉,一般人物娇和嫩”[1]19。美学大师朱光潜以为,“红是火的颜色,所以看到红色可以使人觉得温暖;青是田园草木的颜色,所以看到青色可以使人想到乡村生活的安闲”[11]。在“红、翠”一类暖色词的映衬下,《南柯梦记》中的女子更加明艳可人。
汤显祖以高超的笔法与巧妙的艺术构思勾勒出《南柯梦记》里的众生相,又通过淳于棼“梦了为觉,情了为佛”的人生经历,道出常人的处世观念与精神向度。汤显祖还以一种审美书写的方式展现出日常生活中细微物象的意义与价值,赋予寻常物象以人的情感。这些对身处审美泛化、美感淡化和审美异化[12]时代下的人们重新找寻到日常生活的魅力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