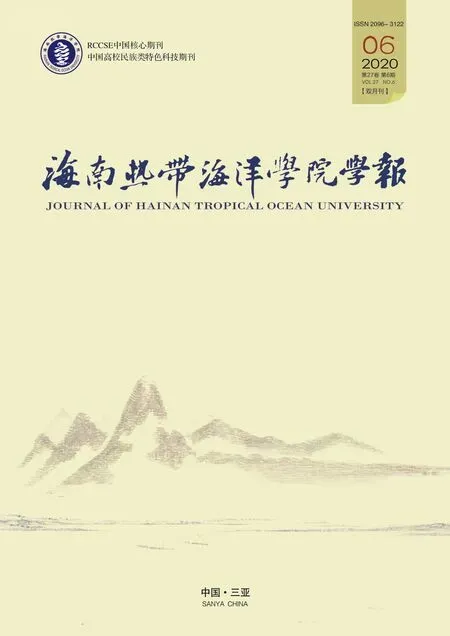徙谪与戍边
——秦朝南海区域的徙民边策辨析
顾丽华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民族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南方越人据山险而居的南海区域(1)本文所谓“南海区域”虽为当代区域表述用语,但在本文中特指秦帝国时期在南部边地分置的南海、桂林、象三郡,大约相当于今中国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行政区及越南北部地区。这些区域大体上为秦帝国时期南部边地越人所居之地。向来为秦帝国所重。以往学界侧重秦帝国南边置三郡及其经济开发意义(2)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代表性成果可参见王子今和张荣芳先生的相关研究,因成果较多,此不一一罗列。。然而对秦帝国在南海区域所施行的具体策略则尚有模糊不清之处。近来有学者引《史记》秦北筑长城“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的材料,敏锐地指出“秦的边策‘徙適’与‘戍边’并称”[1],言下之意二者是并行的两个边地政策。实际上秦帝国亦在南海区域行“徙適”与“戍边”之策,早在汉初文、景时晁错即在《汉书·守边劝农疏》中曰:
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耐)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壻、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2]2284
今人对此亦有所论。晁福林先生曾指出“有谪罪去戍边的‘谪’是和普通身份的民众被征发戍边是有明显不同的”[3],惜未展开讨论。高恒先生亦曾言“实行谪戍的原因是戌卒太苦,人民不愿行戍”[4],虽注意到二者间有因果关系,但并未深究。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辨析秦帝国南海区域所行谪戍制与戍守制两个边策及其相互关系,探析气候环境因素的巨大作用,并透视其背后隐伏的帝国边地秩序理念和战略抉择的内在逻辑。
一、 谪戍制的基本特征
《史记》中的“徙適”即谪戍制。尽管学界对秦的谪戍制某些细节仍有分歧,但对其基本特征已取得一致认识,大体有四:
其一,谪戍制实施的对象是罪人,按照谪罪律征发徙民。《说文解字》“谪,罚也”[5],又释“罚,罪之小者。”“適”系“谪”之通假,“適”与“适”(3)关于“適”与“适”通的问题学界仍有争议,如臧知非先生就认为“今人或读之适之通假,误”。参见臧知非《战国秦汉行政、兵制与边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讁”皆通,“惩罚”之意。出土律简中有“谪罪”记录。《秦律十八种·司空》规定:“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殹(也)而欲为冗边五岁,勿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或赎罨(迁),欲入钱者,日八钱。”[6]91说明“谪罪”至少形成于战国。戍,守也。“谪戍”即惩罚犯有谪罪的人去戍边。秦汉时人丽食其提及秦对“谪卒”的使用时曰“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对此颜师古注曰:“适读曰谪。谪卒谓卒之有罪谪者,即所谓谪戍。”[2]2108秦简中有因娶商人子而被適戍者,简8-466曰:“城父蘩阳士五(伍)枯取(娶)贾人子为妻,戍四岁。”[7]161里耶中还有出贷適戍记录,简8-1029“已朔朔日,启陵乡守狐出贷適戍□”[7]265;简8-899“贷適戍士五(伍)高里庆忌”[7]245。谪发有罪吏及家属戍边一直史不绝书,作为罚有罪戍边的制度,谪戍制始于商鞅变法,讫于东汉末年,与秦汉时代相始终[8]。因谪戍制实施的对象是犯有谪罪的人,则其所涉及的社会范围就是有限的。秦帝国南海区域谪戍徙民是在秦国原有“谪罪”基础上的扩大使用。
其二,谪戍制所发对象皆是秦军功爵体系的身份序列秩序中地位较低者。秦帝国所发谪戍对象如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9]253;三十四年(前213)“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9]253;唐人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曰:“秦时以适发之,名适戍。先发吏有过及赘壻、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秦亡。”[2]1126-1127可见,秦时具体谪戍对象主要有“尝逋亡人、赘婿、贾人”“治狱吏不直者”“吏有谪”“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闾左”。“尝逋亡人”就是曾经逃亡被捕的人。“赘婿”,据裴骃《集解》引臣瓒曰:“赘,谓居穷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壻。”[9]253即入赘女家的贫穷男子。赘婿地位不高,从《说文》释“赘,以物质钱”可见入赘妇家的男子有碘卖的性质。“吏有谪”“治狱吏不直者”类同,即秦司法刑役系统下犯有过失的官吏。“吏有谪”即犯有谪罪的吏,具体不详。“贾人”“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涉及源于西周的“市籍”经商群体。在耕战为首的大环境下,其社会身份地位自然不高。“闾左”是否属于谪戍范围及其确切含义仍有分歧,尽管诸说纷纭,各有所据,但基本认为闾左是秦时的贱民。虽然学界对“谪戍”对象的理解仍有细节上的差异,但从整体上看,谪戍对象在身份上都属秦帝国身份序列中地位较低群体。秦自商鞅变法便将滥觞于周的爵制逐渐发展为沟通社会上下阶层的二十等军功爵,以表贵贱尊卑秩次等级。秦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9]2230。有学者据新出秦汉简牍认为:帝制早期的身份序列实为“爵刑一体”,有爵者、无爵者、司寇徒隶,全体社会成员基本都可纳入这个身份序列,衔接爵刑序列的中间过度身份即庶人[10]。秦时谪罪涉及的多数对象都属有罪,身份序列当在庶人之下;赘婿身份不准立户;商贾登记在“市籍”中,地位稍高于庶人;闾左既然与其他谪戍群体并立其身份地位必然不高。
其三,自备粮食或向政府借贷。由新出简牍看,谪戍需自备粮食或向政府借贷。前引里耶8-1029简“启陵乡守狐出贷適戍”和8-899简“贷适戍士五高里庆忌”,虽然適戍来源地不明,但適戍粮食发放方式为“出贷”是确定的。“出贷”就是自备粮食。现有研究也认为里耶秦简中“屯戍”以外的戍卒原则上需要自备粮食,如果无法自备的话就借粮食[11]。里耶简所见出贷对象有:吏以卒戍士伍(8-1094)、谪戍士伍(8-899)、居赀士伍(8-1094)、居贷公卒(8-1563)、罚戍簪褭(8-781+8-1102)、罚戍士伍(8-761)、更戍士伍(8-1000)等[12]。都属于有一定罪责的戍卒。这也间接证明了谪戍群体的罪人性质。
其四,谪徒的某些权益受限制。谪徒低贱的社会等级身份决定了其某些权益受到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不能通过“冗边”“归爵”等方式来赎免家人,必须去边地服务。在秦代,国家所赏赐爵级制身份是与社会权益紧密相关,谪徒不能爵赏,不能积功,附丽爵制的田与宅等权益要素就无从谈起。前引《秦律十八种·司空》规定:“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殹(也)而欲为冗边五岁,勿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或赎罨(迁),欲入钱者,日八钱。”[6]91即“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冗边”“归爵”来赎免家人的隶臣妾身份为庶人,如果有适(谪)罪,则是不可以赎的。研究认为这段资料还反映出谪戍者必须去边地服务的特点[13]。
二是谪戍者不能计功劳,只能减刑。秦汉时期出现“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累日积劳”的官吏晋升制度。大庭脩[14]在《秦汉法制史研究》第四篇《关于官僚制度的研究》的第六章“汉代的因功次晋升”已注意到“官吏因积功、积劳而晋升”,“劳以出勤天数为主,出勤状况是增减劳的依据,劳的多少表示官吏业绩的高下”,并认为《居延汉简》对边地军吏戍卒也有积功积劳而减免升迁情况。此后学界持续关注秦汉功劳问题,不断取得进展。胡平生[15]首次厘清功与劳之间的递进换算关系,提出“一功”是积“四岁”之劳的重要观点。蒋非非先生[16]将“功”“劳”进行了析分,认为功指军功,劳指军功之外一切为政府的服务。劳绩的计算,除了常规考勤外,某些奖惩的折算也应包括在内[17]。由于汉承秦制,这一制度应渊源于秦。秦在边地服役的戍卒也实行计功劳以奖赏减免制度。如《汉书·晁错传》:“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株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2]2284秦《睡虎地秦墓竹简》《军爵律》载有从军劳绩赐爵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未拜而死,有罪法耐罨(迁)其后;及法耐罨(迁)者,皆不得受其爵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法耐罨(迁)者,鼠(予)赐。”[6]92显然这样的规定包括正卒边地服军役。与之相比谪戍者不计功劳。《史记·大宛列传》贰师将军发兵击宛取得胜利而归,论功行赏,“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金”[9]3178,徐广曰认为“此卒以適行,故功劳不足重,所以绌降之,不得与奋行者齐赏之”[9]3179。谪戍者因前罪而不计算功劳,不能与奋行者一起获得赏赐。尽管谪戍者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其在战场上积累的功劳只能用来减免以前的刑罚。
二、 戍守制的基本特征
首先,戍守制的实施对象是所有在籍成年男丁,按照户籍由县尉征发,无偿向国家服役期为一年的普遍性屯戍边地兵役。戍守边境在战国时已见于记载。《战国策·魏一》载:“魏地……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18]商鞅旧律中亦有“一岁屯戍”的规定。时至秦帝国时期规定除了从正卒中选拔的材官骑士只服地方兵役(一年服地方常兵,即为郡国兵,一年做京师卫士,不服戍边兵役),其他所有开始傅籍到五十六岁老免年龄的成年男子一生之中都要有一个月在本郡县服劳役,即属于力役的徭役。另外还有一年的地方兵役,一年的屯戍边地的兵役义务[19]221-289。戍边兵役制与户籍制关系密切。秦献公十年已开始建立其税收、劳役兵役制度的户籍基础,即“为户籍相伍”。秦王政十六年(前231)随着秦吞并天下的大规模战争展开,为了掌握“新兼并地区的六国臣民的应役年龄”“户主及男性家口的年龄录入‘年籍’,即‘年细籍’”而“初令男子书年”[19]73-90。此后,国家通过登录年龄进一步掌控编户民,“年龄取代身高成为征派赋役的主要依据”[20]。学界对于秦“始傅”年龄仍有争议,有学者偏向“17岁”说[21],也有学者偏向15岁说,并且认为其与爵位呈正向关系,提出15岁至17岁“仅服部分劳役”,18岁及以上者服全役[22]。无论秦的始傅年龄从何时计算,都不影响边地兵役制度的现实运作。傅籍以后即标志着成年,即为正卒。秦汉时期的屯戍之役是以县邑为单位征发,以郡国为单位发遣,由关东郡国定期轮番的,屯戍管理组织严密,是常制[19]221-289。总之傅籍的成年男子要向国家服为期一年的戍守边地的兵役,《戍律》说明秦帝国戍守制的规范化、法律化与常规化。
其次,戍卒不仅可积功劳除戍,还可雇佣代为完成边地戍守。戍卒平时作为编户齐民而拥有爵赏等各种权益,自不待言。其在边地服兵役期间也享有徒隶阶层未必拥有的优待,如可积功、除戍、请假及“遣戍”时“同居毋并行”。《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中《戍律》涉及正卒应皆能享受到的诸多权益:“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为除戍一更。遣戍,同居毋并行,不从律,赀二甲。戍在署,父母、妻死(简184/1299)遣归葬。告县,县令拾日。繇(徭)发,亲父母、泰父母、妻、子死,遣归葬。已葬,辄聂(蹑)以平其繇(徭)。(简185/1238)(缺简)而舍之,缺其更,以书谢于将吏,其疾病有瘳、已葬、劾已而遣往拾日于署,为书以告将吏,所【将】(简186/1255)疾病有瘳、已葬、劾已而敢弗遣拾日,赀尉、尉史、士吏主者各二甲,丞、令、令史各一甲。(简187/J46)”[23]129-130“君子”指戍卒中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人。可见,“君子”居官处理政务满40天以上,皆可免除一月之戍役。除戍显然是对戍卒积功劳的优待。此外,《戍律》规定“遣戍,同居毋并行”。“同居”即同户。官府征发戍卒时,为了不耽误农业,一家有两个戍卒的要留下一个。“同居毋并行”是针对正卒的征发待遇。戍卒“亲父母、泰父母、妻、子死”时,可“遣归葬”;正卒自己生病也可请假。所谓“戍死者固十六七”“秦民见行,如往弃市”,故有人不愿自行戍边,就雇佣他人代为戍守,即“取庸代戍”制。“取庸代戍”制属“戍律”,《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戍律》载:“下爵欲代上爵、上爵代下爵及毋(无)爵欲代有爵者戍,皆许之。以弱代者及不同县而相代,勿许。(简182/1414-1)【不当相代】而擅相代,赀二甲;虽当相代而不谒书于吏,其庸代人者及取代者,赀各一甲”(简183/1298)[23]128。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爵位的差异并不重要,二者之间必须以强代弱,具体以年龄大小来区分身体强弱,互相雇佣代戍条件须为同县。相关文书应遵循一定的文书格式,详细记载了雇主和被雇者之间姓名、年龄、籍贯、爵位、身高和颜色等基本信息以便官府管理。
最后,戍守主要作备塞之卒而候望示警、“缮治城塞”,不得“令为他事”。云梦秦简《秦律杂抄》:“戍者城及补城,令姑(嫴)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令戍者勉补缮城,署勿令为它事;已补,乃令增塞埤塞。县尉时循视其攻(功)及所为,敢令为它事,使者赀二甲。”[6]148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戍律》规定:“城塞陛鄣多 (决)坏不修,徒隶少不足治,以闲时岁一兴,大夫以下至弟子、复子无复不复,各旬(简188/1267)以缮之。尽旬不足以(索)缮之,言不足用积徒数属所尉,毋敢令公士、公卒、士五(伍)为它事,必与缮城塞。(简189/1273)岁上舂城旦、居赀续〈赎〉、隶臣妾缮治城塞数、用徒数及黔首所缮用徒数于属所尉,与计偕,其力足(简190/1248)以为而弗为及力不足而弗言者,赀县丞、令、令史、尉、尉史、士吏各二甲。离城乡啬夫坐城不治,如城尉。(简191/1249)”[23]130-131可见,戍卒候望和缮治城塞乃其基本任务。秦帝国在岭南的戍守防御奠定了此后中央王朝治理此地的政策基础,并得以延续。如在宋代为了防御当地黎族就设立有寨栅派驻兵戍守之策[24]。
此外,屯戍作为正常的屯卒,口粮或许由国家供应。戍卒粮食由国家供应已为学界共识。如吕思勉先生就认为“既然有发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25]。再如管东贵先生亦认为:戍守者的粮食“主要都是靠内地转输供应;因耗费太大,致百姓糜敝”[26]。此即简牍中的“出廪”。宫宅潔[11]检索里耶秦简6例“屯戍”粮食发放的方式都是“出稟”,并认为屯戍没有自备粮食的义务,对他们是无偿提供的。
总之,谪戍与戍守在对象、范围及权益等方面皆不同,应是在南海边地施行的两种徙民策略。谪戍徙民的施行带有弥补和消除戍卒守塞政策带来的巨大社会不满情绪之目的。屯戍制度为谪戍徙民带来了安全保障,二者之间互相弥补,共同稳定边地秩序。
三、 气候环境与秦帝国边策选择
谪戍制之所以作为边地戍守制的补充,与气候环境因素密不可分。
南海区域“负山险,阻南海”,以五岭为界,其以南所属区域,即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行政区及越南北部地区,属典型的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海南岛热带季风气候为主。两广地区每年春季持续阴雨低温倒春寒形成梅雨季和潮湿发霉回南天;夏季暴雨、台风、高温等导致闷热,湿热,湿冷。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大体为地处赤道两侧热带,全年阳光强烈,气候炎热,湿热,闷热。闷热潮湿冷热交替的气候导致带有“地方”特点的疾病横行,甚至时至今日已经形成颇有医学影响的所谓“热带病”。现代医学上“热带病”包括古籍中屡现的南方特有的“瘴病”。具体症状表现多元而复杂,诸如疟疾、脚气、痢疾、消渴、黄疸、沙虱热、克汀病、瘭疽以及高山病、瘴毒发背、硒中毒、青腿牙病等,也包括因空气污染所导致的汞中毒、硫中毒、一氧化碳中毒等症状。尽管秦帝国时对南海区域的瘴病认识“是建立在中原华夏文明正统观基础上的对异域及其族群的偏见和歧视”[27],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以秦帝国南海区域戍守士卒的真实而宝贵的生命为代价的。
中国秦汉时人通过与南海区域日渐频繁地接触,已经对南方气候和致病后果有深刻的认识。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就评价南方“土薄水浅,其恶易覯”[28]。虽然秦帝国除了政策选择与更变未能留下更多资料,但大约成书于汉初景、武时期的《淮南子》在《坠形训》中载有“障气多喑”[29],“障”即“瘴”,记载了后来屡见于南方的“瘴病”。汉武帝时人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多处涉及对中土士兵遭遇南方热带气候所带来的严重损失。《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后时曾遣将军隆虑侯灶征讨南越,但“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9]2969。《史记·西南夷列传》亦记汉军在西南遭遇“罢饿离湿,死者甚众”[9]2995。汉初“暑湿”导致的“士卒大疫”严重影响了军事进程。东汉前期的班固在《汉书·严助传》中载有南越国所处的恶劣环境,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用兵南越时曾言:“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2]2781说明当时人对南越国的气候及其会导致的可怕疾病已经有相当深刻认识。班固亦对将士被南方气候环境所伤情形有所感怀。《汉书·王莽传》“僰道以南,山险高深”,“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2]4145。《汉书·贾捐之传》:“(骆越之地)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2]2834可见南海区域气候环境对军队的杀伤力甚剧。
南海区域气候环境所伤者多为关东人。尽管中原在南海区域的政治、军事实践正式始于秦帝国置南边三郡,但实际上中原人与南越人的正面交锋大约在平息荆楚之后即已开始。王政二十五年(前221)左右,秦帝国王翦在普遍“平荆地为郡县”之后又去征伐错综杂处“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各有种姓”的所谓“百越”族群[2]1696。尽管王翦对百越作战只是灭楚之役的一个自然延续”,已属“征越”,越人对南来灭楚的秦军亦抱持敌视态度[30],但秦军经过大约八年左右的艰苦进攻作战,终于设置南边三郡。在军事征服与戍守南海区域过程中,秦帝国军队必然要面临南海区域热带气候环境和热带病对军队的猛烈冲击,汉初晁错所谓“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稀)毛,其性能(耐)暑。秦之戍卒不能(耐)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2]2284,不过是冰山一角。环境之所以带来如此大的冲击,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秦帝国徙入南方热带区域的人皆非南海本地土著。汉初晁错建议移民实边时说“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2]2286,敦煌、居延等地汉简所见戍卒来源地“西不入关,南不越江淮”[31]与晁错之说吻合。汉承秦制,秦帝国戍卒或亦有以山东六国人为主的特点。若果真如此,派来南海区域戍守的六国人千里跋涉来到“南方卑湿,蛮夷中间”[9]2970,必然因对南海区域热带气候条件不熟悉而缺少防范传染性疾病经验,以至于死亡,亦在意料之中。
如上所述,针对所有适龄男子而普遍实行的义务性戍守制与针对有罪者而在有限范围内实行的谪戍制实际上完全是两种制度。二者是秦帝国在南海区域“少阴多阳”、南来的“戍卒不能(耐)其水土”的气候环境背景下做出的政策选择和调整。二者之间虽能互相弥补,共同稳定边地秩序,但从气候环境角度看,谪发而南来的“谪戍”群体并不能克服自然气候环境所带来的各种疾役威胁,秦帝国“以谪发”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并非南海边地戍卒不满情绪的根本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