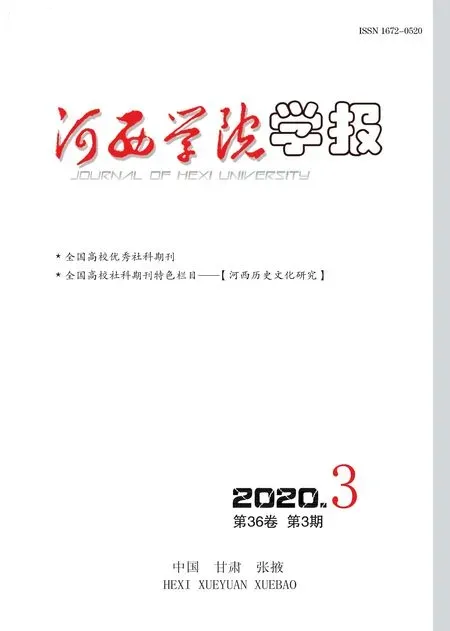民间丧葬仪式研究综述
李贵生
(河西学院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民间丧葬仪式的研究已有百年的历史,国外人类学家对中国丧葬仪式的研究相对较早,其后国内人类学家对丧葬的研究承袭了国外的理论。二十一世纪以来,研究民间丧俗、丧葬仪式的学者增多,成果颇丰。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题目中包含“丧葬仪式”的期刊论文作为论述对象。从学科领域来看,民间丧葬仪式的研究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音乐学、民族学等领域;从研究的侧重点来看,有对丧葬仪式的阐述,有对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的阐释,有对丧葬仪式中的音乐舞蹈的探讨,有对丧葬仪式中的宗教信仰的考察,也有对丧葬仪式中的传统文化的论述;从时空维度来看,有对丧葬仪式的历史考证,也有对现代当下的研究,既涉及到不同地域汉族的丧葬仪式,也观照了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
一、民间丧葬仪式的人类学视角
国外关于丧葬仪式的研究者大都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主要从仪式的象征意义、社会和宗教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
法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志学的创始人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创立了“过渡仪式”理论(1909年出版《过渡仪式》),他认为“过渡仪式”是由“分离阶段”“过渡阶段”“整合阶段”组成的人生仪式,丧葬属于过渡仪式,他指出“研究仪式并不是研究仪式本身,而是研究它们的重要意义。”[1]“过渡仪式”理论对后世仪式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意义。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继承并发展了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从“边缘仪式”的“阈限”发展出了“阈限性”,提出“围绕仪式展开的‘阈限前—阈限—阈限后’是一个‘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程”[2]。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杜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将丧葬仪式分为葬礼、丧葬礼仪、送葬礼仪等,他认为“灵魂与人体的关系极为密切,二者结合为一个整体……灵魂在人体的最深入”,丧葬仪式目的就是使灵魂离开躯体回到自己的国度(故乡)[3]。
国内人类学家对丧葬的研究承袭了范热内普、特纳的理论,他们的研究阐述了丧葬仪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具有功能主义的烙印。
林耀华从《拜祖》到《义序的宗族研究》实现了由中国早期传统人类学研究的文献考据到实际田野调查研究范式的转变,他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结合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宗族理论研究范式,他描述并分析了“过世”“报丧”等丧葬仪式,认为其具有调节家庭、整合社会的功能。[4]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在其代表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中论述了葬礼的功能:送灵魂早日平安到达灵魂世界,使灵魂在灵魂世界平安舒适,表达亲属对逝者的依恋与悲痛的情感,确保死亡不再引起任何灾难。[5]
当下学者们对中国民间丧葬仪式的研究基本上继承了前辈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利用“过渡仪式”分析丧葬仪式,并进一步探讨丧仪的象征意义和功能。
卢敏飞根据“过渡仪式”理论,探讨罗城仫佬族的丧葬活动,将其分为分离、边缘和结合三个大阶段,分离阶段是“送终买水”到“换床沐浴”,边缘阶段是从“装殓盖棺”到“下葬”,结合阶段是从“上新坟”到“脱孝归宗”。[6]杨焰的《回归之旅——云南拖姑村回族丧葬仪式分析》[7]分析了回族丧葬仪式中的“过渡仪式”。曹媞的《淮北汉人社会丧葬仪式过程及其分析——以淮北地区颍上县农村葬礼为例》[8]运用“过渡仪式”理论分析了淮北汉人社会丧葬仪式。
马惠娟分析了胶东农村丧葬仪式三个方面的的象征意义:一是关于传统的象征性调适,二是关于生命的象征符号集合,三是关于伦常的象征秩序。同时分析了其功能:对至亲的慰藉功能,对秩序的调整功能,对社区的延续功能,对传统的突破功能。[9]
二、民间丧葬仪式的社会学视角
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从个体心理和社会角度分析丧葬礼仪及其信仰功能,他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说全世界丧礼的相似点是死亡来临时亲属总要聚在一起,从而维持了文化传统的持续。[10]英国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结构—功能主义创始人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1881~1955)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机体”,他把仪式的功能归结在了建立和维持整个社会结构的正常秩序上。[11]
前辈社会学家对中国民间丧葬仪式的研究也是承袭了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社会学家杨懋春(1904~1988)《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从内部家庭关系的角度对丧葬仪式进行描述阐释,认为丧葬礼仪跟家庭经济状况、死者年龄、活者的辈分及村庄的评价机制等有关系,他强调丧葬仪式对家庭社会有再生产的意义。[12]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杨庆堃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丧礼仪式的功能,认为丧礼仪式“有助于保持群体对宗族传统和历史的记忆,维持道德信仰,群体的凝聚力借此油然而生。通过所有家族成员参与的仪式,家族不断地强化自豪、忠诚和团结的情感。”[13]
当下研究丧葬仪式的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丧葬仪式中的人际关系和丧仪的社会功能。
李汝宾阐释了传统丧葬仪式在沟通家庭、宗族、村落关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出传统的丧葬礼仪就是通过人情互动、礼物互惠、劳力互助的交流,抚慰着逝者亲属,和谐着人际关系,进而促进了村落社会的整合与发展。[14]陈小锋的《传统仪式的社会学解读——以陕西关中地区丧葬仪式为例》运用事件、过程分析方法,以陕西关中地区丧葬仪式为例,分析了一个完整的丧葬事件,透视了农村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方式、生存价值以及社会秩序。[15]刘小雯、张雨的《丧葬仪式变迁对人际传播的影响——以重庆南岸区为例》以重庆南岸区为例分析了丧葬仪式变迁对人际传播的影响,指出丧葬仪式沟通了家族内部的情感,增加了家族凝聚力、向心力、认同感、归属感,也加强了邻里部落之间的人际互动,促进了村落社会的整合与发展。[16]
张大维、安真真、吴渊以三峡库区GZ镇丧葬仪式为例,分析了移民搬迁中传统丧葬风俗的重塑,指出与传统丧葬仪式由家庭举办的情况不同,移民家庭的丧葬事件中安排酒席、停灵、入殓、下葬等事件基本上交由当地村民来具体操办,由此形成了传统风俗与现代形式相结合的“接点经济”——“仪式经济”。[17]
一部分学者探讨了丧葬仪式的社会功能。赵文、王明利认为丧葬仪式具有构建和谐的家族关系、调节邻里之间的关系、调整家族关系、凝聚家族力量以及教育感化等功能。[18]何秀琴的《浅谈农村丧葬仪式的社会功能——以湖北农村传统丧葬仪式为例》[19]探讨了丧葬仪式四个方面的功能。
三、民间丧葬仪式的民俗学视角
关于丧葬习俗的研究绕不开丧葬仪式,对于丧葬仪式的考察,遍及全国各地。
陈烁将敦煌遗书中的丧葬仪式概括为七个步骤,即临终、停丧、吊丧、入殓、出殡、下葬和斋祭。[20]董湘漪、孙振玉考察了位于宁夏、甘肃两省交界处的南长滩村的丧葬仪式,将整个葬礼全程分为准备、起经、收尾三个阶段。[21]赵文、王明利对关中东部地区丧葬礼仪进行了考察。[22]刘璐阐述了东北传统的丧葬仪式的几个主要步骤:送终(老人生命垂危时,子女等直系亲属陪护在其身边,直到老人去世),沐浴、穿寿衣,报丧(东北俗称“对信”),请灵与送灵(请灵仪式,也叫招魂仪式),送盘缠(活人为逝者即将归于另一个世界的时候,送上吃、穿、花、用等物),出殡(东北又叫“拉棺”),落葬。[23]钟静静将河北省献县地区的丧葬仪式分为葬前仪式、埋葬仪式和服丧与祭祀仪式三个阶段。[24]
李素娥、余熙考察了鄂西北十堰市竹溪县红石岩村丧葬仪式的整个过程,其仪式主要是两天一夜仪式过程与程序:第一天白天仪式包括开咽喉,挂菩萨,念忏经,请亡,请水,祭灵、交灵、化包等;第一天夜晚仪式,其过程分上半夜与下半夜,上半夜仪式包括开歌路,唱孝歌,下半夜仪式包括烧更纸,唱散歌,还阳;第二天白天仪式包括出丧与下葬;后续葬礼仪式包括烟苞(送火),圆坟,四煞,七期,百天等。[25]杨田华将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刘村丧葬仪式概括为道场、吊唁、筵席、庆典演出、下葬等几个环节。[26]25
胡晨晨将民国广东丧葬仪式的主要程序分为居丧礼仪、殡葬礼仪和祭祀礼仪。居丧礼仪包括装殓(人死后,为死者进行梳洗打扮,称为“小殓”),成服(披麻戴孝),报丧(大部分地区在人丧亡后马上报丧),吊孝(亲朋戚友接到报丧之后携带祭礼到丧家祭奠死者);殡葬礼仪包括出殡,下葬,酬谢亲友和助丧者;祭祀礼仪包括七七祭、百日祭和周年祭、其他祭礼(如家祭、门祭、路祭、墓祭、点主礼)。[27]
四、民间丧葬仪式的宗教学视角
一些学者探讨了丧葬仪式中儒释道的融合。汤洁考察了博爱县北石涧村的丧葬仪式,指出北石涧村的丧葬仪式具有佛道合一的特点:佛教对丧葬仪式的影响,表现为它带来了一种死亡观念,如“善恶相报”“转世托生”等,与中国上古信仰中的报应有类似之处,为人类的死亡世界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并且由于佛教教义的系统化、明确化,因而为民众广泛接受。道教的影响也深深体现在丧葬仪式中,如相墓术、看风水等等。[28]124孙芙炬考察了贵州省桐梓县的丧葬仪式,指出其丧葬仪式的主角是道士,他们秉承道教、佛教、巫教、儒家等教义,以道教和佛教的仪式为基础,以巫教的表演方式,以儒家的思想等为基础,推动丧葬仪式的进行。贵州省桐梓县的(道士)主持的丧葬仪式属于“阴坛”,其仪式包括开灵、开旛、破白、开坛、请圣、会将、搬诏、破药、召请、安位、诵经、礼忏、建坛、放赦、进表、请水、贡天、利幽、资亡、犒赏、发丧、出魂、圆满等。一般时间为三到五天,多则七天、九天甚至到四十九天。[29]杨田华考察了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刘村丧葬仪式,指出其丧葬仪式的主持道士虽名为“道”,实际却为佛门俗家弟子,其丧葬仪式道场糅合了佛教关于因果业报的思想,渗透着儒家孝道的伦理道德,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伦理道德、强调人际秩序的社会文化规约。[26]28
一些学者对道士主持的丧葬仪式或丧葬仪式道场进行了研究。李文军指出萧山道教供奉的神灵是“三清”,中间元始天尊,右为灵宝天尊,左为道德天尊,其丧葬仪式分为布置道场、请圣拜忏和放焰口(施食)三个部分。[30]112肖潇考察了湖南岳阳南边道场丧葬仪式,指出其仪式包括起寝、扎司命、迎尸、成服、请水、朝庙、开五方、破狱、渡桥、解结、奠酒、出殡、赞坟。[31]
一些学者就佛教对丧葬仪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陈烁认为敦煌地区的丧葬仪式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七七斋就源自佛教,“在逝者新亡49天内,逢七设斋奉祭,可以减免亡灵生前罪过,使其得以顺利升入天堂。”[32]据王铭的研究,丧葬仪式中的引魂幡出现于唐代,它是引路菩萨手持之物,是佛教所创制的为死者引路的丧仪旗幡,以接引亡者往生。[33]
学者们对其他教派的丧葬仪式也进行了阐述。杨焰指出回族的丧葬仪式依《古兰经》的圣示而行,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34]张明比较了基督教与三一教的丧葬仪式,指出三一教融汇了儒道释各家教义,其丧葬仪式凸显了三种文化体系的鲜明意义,而基督教的丧葬仪式更是严格执行教义的解释,反映了人们对宗教的思考和彼世想象,因此丧葬仪式最能显示宗教信仰对世俗生活的影响。[35]
学者们对丧葬仪式中的民间信仰也有探索。李汝宾认为山东潍坊的大部分地方,特别是农村,无生老母信仰是在当地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民间信仰。井塘村大部分女性村民不但笃信四季老母,她们还信仰着村里另外两个神灵——玉皇大帝和关圣人。[36]
五、民间丧葬仪式的音乐学视角
一部分从事音乐研究的学者对丧葬仪式中的音乐和舞蹈进行了探讨,其内容包括曲牌曲调、乐器、仪式音乐、舞蹈等方面。
常芳、赵桂珍调查了丧葬仪式中的晋北鼓吹使用的曲牌。[37]52-55柳亚飞对上党地区长子县的八音会演奏的曲牌进行了调查,指出八音会为了配合丧葬仪式的进行,往往即兴将许多曲牌灵活地串联在一起。[38]肖潇调查了湖南岳阳南边道场丧葬仪式中的音乐曲调,指出曲调都采用传统的五声调式。[39]
康莉调查了甘肃陇东丧葬仪式中的鼓吹乐器——唢呐、板胡、笛子、管子、堂鼓、铙、镲以及云锣等,指出唢呐是鼓吹乐中的主奏乐器。[40]常芳、赵桂珍探讨了晋北鼓吹乐器,指出唢呐、管子为主奏乐器,笙为主要伴奏乐器。[37]52-55李文军考察了萧山道教丧葬仪式所用打击、拉弦、弹拨等乐器。[30]112-113汤洁阐述了博爱县北石涧村丧葬仪式音乐的乐器,指出用于乐队演奏的主要是唢呐。[28]125
徐海波调查了张掖市甘州区丧葬仪式音乐,认为其音乐基本可分为具有巫术性质的招魂音乐与以唢呐、鼓、钹等为主要乐器的鼓吹乐两类,二十余首各类曲牌中,宫调式居多,羽、商次之,徵调式最少。[41]赵书峰对湖南新化民间道教仪式音乐进行了民族志考察,指出,在不同的仪式中使用相应的仪式音乐,同一仪式音乐可以“一曲多用”,但在不同的仪式中演唱的韵腔形式到调高的选用都有明显差异。[42]
杨和平对浙江省苍南县蒲城的丧葬仪式乐队5个班社的人数、曲目来源、组织形式、活动范围、年龄结构、经济分配等进行了调查,对其演奏的曲目和使用的乐器进行了说明,并对其音乐中的民俗元素、宗教元素和外来元素进行了分析。[43]
陆栋梁考察了灌阳县丧葬仪式“大歌”的模式性结构特征,认为“大歌”的结构是一个由三重模式复合而成的复模式结构。[44]肖艳考察了湖南衡山地区丧葬仪式道场中的祭歌“散花”和“丧堂祭文”。[45]
杨丽芳对泉州丧葬仪式中的舞蹈进行了调查,指出泉州丧葬仪式中的舞蹈形式繁多,种类丰富,一般来自泉州传统的地方戏剧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或称师公戏,即所谓“南戏”。[46]王松阳对桐柏县丧葬仪式“开路”仪式中的八卦舞谱进行了探讨。[47]
六、民间丧葬仪式的民族学视角
一部分学者对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对彝族、土家族、苗族、壮族、回族、纳西族、藏族的丧葬仪式研究较多。
余舒详细地阐述了彝族的丧葬仪式,从风水观念、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三个方面阐释了象征意义。[48]陈棣芳用“过渡礼仪”理论分析了彝族的丧葬仪式,将贵州盘县蒋底村彝族丧葬活动分为分隔阶段(落气—衣敛)、边缘阶段(换床—下葬)和聚合阶段(合灵—脱孝)三个阶段。[49]张泽洪、高翔对水西彝族的丧葬仪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揭示了其文化内涵。[50]沙呷阿依从民族舞蹈学视野考察彝族丧葬仪式舞蹈,阐释了云贵彝族丧葬仪式舞蹈蕴含的感恩、传德与教化等内涵。[51]
刘琼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对澧水流域土家族“做佛事”的丧葬仪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指出澧水流域土家族“做佛事”仪式既区别于佛教的超度仪式,也区别于道教的斋醮科仪,有着厚重的传统积淀,体现了土家族宗教信仰的兼容性和功利性。[52]秦懿从音乐民族志的角度对石柱县土家族特有的音乐形式“坐堂锣鼓”在丧葬仪式中的功能以及背后的文化隐喻进行解读。[53]许甜甜分析了土家丧葬之仪式行为、音乐形态、文化内涵,论述了土家族丧葬仪式歌在生命意识、信仰理念、情感心理、社会功能方面所体现出的动态平衡,揭示出土家人“执著于生,超越于死”的生死哲学以及豪迈豁达、乐观向上的生存智慧。[54]彭达先从象征功能角度对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细节进行了研究,认为土家族丧葬仪式体现了来世观念、灵魂观念和赎罪观念。[55]
杜朝光对苗族牛丧葬仪式中的皮鼓进行了人类学阐释,认为“牛皮鼓”在丧葬仪式中预示着亡者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转换到另外一种状态,并通过牛皮鼓而达到另一种生命的延续存在。[56]
韦浩明对壮族丧葬仪式参与者的变迁进行了解析,认为“传统乡村丧葬仪式的参与者,重在构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凝聚力;而社区仪式的参与者,牵涉到家族、宗族、社区三个主要聚居群体,带有明显的家族、宗族与社区结合的特征,既有构建血缘群体凝聚力的成份,又增添了地缘群体凝聚力构建的内容。”[57]
罡拉卓玛探讨了宗教信仰对藏族丧葬仪式的影响,认为早期藏族的丧葬仪式受苯教理论体系的影响,佛教传入后,佛教理论体系替代了丧葬习俗的“文化阐释权”。[58]王丹阐述了硗碛藏族的丧葬仪式,并分析了硗碛藏族丧葬仪式的功能。[59]
其他少数民族丧葬仪式的研究也基本上在阐释丧葬仪式的基础上,揭示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社会功能,或者借丧葬仪式分析生死观、社会关系等。
七、民间丧葬仪式的传统文化视角
一部分学者从传统文化视角探讨丧葬仪式中的孝道等观念。李永萍对关中地区丧葬仪式进行了田野考察,指出丧葬仪式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完成子代的送终,从而实现亡者的“善终”,这是孝道的基本内涵。[60]杨帆对鲁西南“过三年”丧葬仪式进行了文化解读,认为在鲁西南菏泽一带的“过三年”仪式,体现了慎终追远的孝道观念。[61]吴孔军指出,安徽霍山县农村的丧葬习俗中守灵、哭丧、二次葬、满五七、新七月半、守孝、坟地的选址与坟墓的维修等仪式中充分体现着孝道思想,死者死后三年之内孝子穿白鞋,不可以结婚,三年内过年时门上的春联不可以是红色的,这相当于“守孝三年”。[62]张迎雪探讨了鱼木寨丧葬仪式中的土家族孝文化,指出土家族的丧葬风俗体现了鲜明的土家族孝文化特点。[63]宋瑶分析了中西丧葬仪式中的不同,指出西方宗教是对上帝的敬畏,中国则更加注重忠孝。[64]
个别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丧葬仪式中的舅权思想和命运观念。王植槐、邬林明的《乡村丧葬习俗中的舅家权威——以浏阳市社港镇丧葬仪式为例》考察了丧葬习俗中的舅家权威指出舅家在葬礼筹备阶段具有知情权与监督权,对治丧法事安排具有建议权,在治丧法事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65]肖坤冰、彭兆荣考察了了川中地区丧葬仪式中“找中线”环节,分析了其中蕴含的汉族传统的“命运观”。[66]
总之,丧葬习俗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呈现,是考察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民间社会不可或缺的活化石。对于丧葬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将其看作孤立的仪式看待,“必须将其放在家族文化和制度再生产的历史实践纬度中解释,将其看作祖先崇拜的一个仪式环节,国家治理、地产分配、风水实践、生育观念、阶层分化、市场体系等诸多要素会有机地整合在这一制度再生产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将政治、经济、文化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