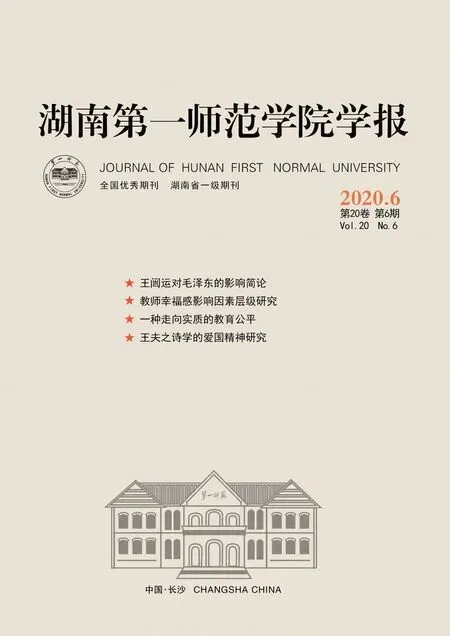马基雅维利:“性恶”论者?
常远佳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引言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他在其著作《君主论》中对人性发表了大胆赤裸的看法,使国内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宣称他为“性恶”论者。如祝琴在《论马基雅维利人性观》中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为数不多的持人性‘本恶’观点的政治思想家之一”[1]24。李淑梅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2]1。高亮则援引马基雅维利的话证明马氏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3]122。仅有极少数学者指出他人性观的复杂性,如胡义清指出,马基雅维利“在正视人的自然性的同时,还坚信人有理性,能够依靠自身努力克服缺点战胜命运”[4]。
倘若仅仅关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于人性零散的描述,得出马氏为“性恶”论者的结论自然不难。但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认识真的能以“性恶”一言而概之么?马基雅维利以前无古人的大胆笔法分析权力的本质,创立了现实政治学。他对人性的认知,是其政治学说的基础,是建构其政治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点。因此,从其政治学说我们也可以反窥其人性观点。相比《君主论》中对于人性零散的描述,本文认为其政治观更具系统性和可靠性。
另外,《君主论》一书有着特殊的出台背景。马基雅维利在美第奇家族的敌对政权当政时投身政界。因此在1512 年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时,他不但失去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而且被逮捕。为了重新谋得职位,他将《君主论》作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礼物献给洛伦佐·美第奇。他在《君主论》的扉页中写到:“现在我想向殿下奉献本人对您的一片忠诚”[5]1。《君主论》一般被认为是一本富有创见但十分恶毒的暴君手册,而马基雅维利另一部著作《论李维》则被认为是一本怀古的、品德高尚的共和派手册。至于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写下两本截然对立的著作,不同学者有不同见解。但他是否为了迎合专制君主而在《君主论》中故意鼓吹暴君论;或者为了哗众取宠而故意夸张某些观点?这种可能性未必没有。
一、“欲望”说是否等同于性“恶”论?
有些学者将马基雅维利归结为性恶论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是被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驱动的。就此有学者总结,“马基雅维利认为,欲望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同时,他认定人类的欲望只是低级的物质欲望”[1]24-25。马基雅维利的确认为人有强烈的物质欲望,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认为人类仅有低级物质欲望,仅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另外,他是否认为物质欲望一定会导向“恶”?
马基雅维利的确承认人为物质欲望所驱动,但肯定人有物质欲望并不等于认为人仅仅有物质需求,甚至籍此否定人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高度赞誉罗马人勇敢顽强、不惜生命保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论道:“罗马人的顽强精神胜过拉丁人,……部分地因为他们的德行,使得托克图斯必须杀死自己的儿子,德希乌斯‘必须自杀’身亡。”[6]252马基雅维利论及的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40 年。在罗马与其拉丁同盟的其他成员爆发的一场战争中,罗马执政官托克图斯为了严肃军纪,下令将违反军令的儿子在全军面前斩首;而另一位执政官德希乌斯为了罗马的胜利,主动将自己献祭给死神和大地母亲。这一战中,罗马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基雅维利由此将罗马军队致胜的原因归结于其“精神”和“德行”。这里的“德行”与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德行”显然有所不同。马基雅维利的德行观被打上强烈的个人印记。一般而言,德行指为达到特定成果所必需的能力、技能、力量、智谋或勇气等;其核心标准是实现目标的能力,而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但很明显,此处的“德行”并非指马基雅维利式的“德行”,而是指为了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甚至子女生命的无私无畏的高尚的爱国精神。他认为罗马军队之所以所向披靡,正是因为罗马人“具备这种精神,则军队不会后退”[6]252。马基雅维利反复强调高尚的爱国精神才是罗马军队常胜的法宝。倘若他真的认为人性只是自私冷酷极端趋利,他又怎能相信并推崇人会为了国家及荣誉牺牲自己或者至亲呢?
与此形成佐证,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一书中的第10 章,言辞凿凿地说,“金钱并非如俗见所言,是战争的筋骨”[6]235。世俗看法认为,金钱才是战争的筋骨,而他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他的看法不同于“俗见”正说明这一观点是他的创见。他不但不认为金钱是致胜关键,相反,他还认为金钱根本买不来效忠的将士。在讨论如何建设国家军队时,他认为:“雇佣军是毫无用处而且很危险的军队”,因为他们只是“为了那一点军饷”而战,决不会为雇佣国尽忠[5]70。同时,他反复强调“共和国用兵时则必须委派自己的公民去指挥作战”[5]71。为什么只有自己的军队才可靠?因为维系自己军队是“同舟共济的”的“情义”,而非金钱。换句话说,马基雅维利认为“情义”远比“金钱”更可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马基雅维利认为真正能够维系军队的是“情义”——是比物质需求更为高尚的精神需求。如果他认为人人都是金钱至上主义者,为何雇佣军远不及本国军队?如果他认为人人贪财而畏险,何来他口中的“德行”与“精神”?
从以上他对军队的分析可以看出来,马基雅维利显然不认为人与人之间仅仅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存在。他承认人有趋利的一面,但同时并不否认人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牺牲自我保全国家的大义。实际上,我们从他论述军队建设中可以看到,相比物质的驱动性,他认为精神的力量更胜一筹。从他热情讴歌罗马人的爱国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肯定人有高尚的无私的献身精神。
其次,从马基雅维利对“自由”的重视,我们可以推论他肯定人类基本需求的合理性。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说:“精明的人创立共和国,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自由构筑一道屏障。”[6]58马基雅维利极为推崇人民的自由,他甚至将对“自由”的自觉维护和反抗强权提升到道德的高度。他将“腐败”的原因归结于人民“对自由生活的蔑视”,因为这种腐败,“使民众懵懂无知,居然看不到他们正套到自己脖颈上的缳轭”[6]97。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放弃反抗强权才是人民腐败的根源,因为强权都是以压迫和剥夺他人的基本自由和权益为基础,而人民放弃自由的权利就等于放任强权。马基雅维利认为强权才是真的腐败:因为只有不加遏制的私欲才会导向罪恶。而热爱和积极捍卫自由反而能够遏制强权,使国家和人民免受强权之害。
第三,马基雅维利肯定人的基本需求,但同时也看到人性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容易趋于腐败。但他的解决办法既不是压制人性,也不是寻求上帝的帮助。他非常有创造性地提出以权力制衡来避免当权者专权。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纷争备受传统政治观的诟病,他却对此持独到见解。他认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纷争“正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元素”,至于其危害,实在是微不足道。他论道:“凡300 年有余,罗马的纷争甚少导致流放,更鲜有流血发生。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因内部分歧而被流放的公民,不过8 人或10 人,岂能断言这些纷争有害或分裂了共和国呢?”。相形之下,其益处却是极为彰显,共和国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德行之楷模,皆因“优秀楷模生于良好的教养,良好的教养生于良法,而良法生于受到世人无端诬责之纷争也。”[6]56他甚至高度赞赏“纷争”的益处:“不只让民众享有治权,且为罗马的自由树起一道屏障”,因此“应给予纷争至高的赞扬才是”[6]57。哈维说,“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位称赞党争有益的政治哲学家。”[6]15
马基雅维利认为倘若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就能够保证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无法凌驾于其他利益集团之上,从而能够客观保障任何一个团体的利益不受或较少地受到侵害。权力制衡使任何人都无法行使过度的权力,避免了个人腐败和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他人的自由之上。马基雅维利的制衡论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西方近现代政治。
马基雅维利承认人有私欲,但并不籍此否定人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人除了有物质利益需求,更有精神需求,也不乏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此外,从他论证共和国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人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承认人的合理需求。马克思也肯定人类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因为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人类才能生存。物质需求、生活需求的满足是人的所有物质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即人的本性之中包含需求性[7]。马基雅维利并不认为人的本性需求一定会导致“恶”。只有不加遏制的私欲才会导致恶。他主张合理的制衡制度能够利用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需求相互挟制,从而使国家能够良好运转。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客观承认人的本性需求,同时在基于人性客观认识的基础上,依然可以建立合理的制度来挟制人性。以上分析表明,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人有私欲,他同时对人类的精神信念和信仰有充足的信心。
二、并非无道德论者
也许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发表的耸人听闻的暴君论和人类忘恩负义一说,从而使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说他认为人毫无道德可言。如李淑梅认为,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而毫无社会道德可言”[2]1;祝琴认为,马基雅维利认为“从古到今,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利欲的驱使,所有人都毫无道德可言”[1]25。谢慧媛总结国内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研究的共识之一是:马基雅维利主张非道德主义或者超道德主义[8]。马基雅维利真是非道德主义者么?
马基雅维利的确在《君主论》中抨击过人类的忘恩负义、朝三暮四和贪得无厌。但人是复杂的,马基雅维利虽然承认人的道德选择有一定的复杂性,但他并没有从本质上否定人的道德。他在《论李维》中反复论证倘若要有长久稳定的统治,君主须有美德,人民须有美德。尤其重要的是,他在论证自由的时候,特别强调自律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必然基础。如果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作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会得出结论,将他归结为一个非道德主义者是对他的误解。
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反复论证君主须有美德,暴君的统治不可能长久。他认为,如果君主抛弃优秀品德,“众人把君主视为不务正业、骄奢淫逸、肆意妄为无出其右。是故君主开始遭人憎恨;既遭憎恨,遂生畏惧;心存畏惧,未久即滋生侵扰,由侵扰而旋为专制矣。此乃败亡之始、密谋弑君之始也。”[6]75他以历史事件证明他的看法:“卡里古拉、尼禄、维特利乌斯和许多暴虐的皇帝,东西两支大军也无法从敌人手里救出他们的性命。”[6]75君主一旦失信和失职于民,不但王位不保,甚至性命都不保。他在《论李维》中多处反复强调德行的重要性。前文提到,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帝国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德行[6]210;在《论李维》第19 章中,他论证进行扩张的共和国若是治理不善,不按德行行事,只会走向覆灭[6]265;在《论李维》第30 章中,马基雅维利强调真正强大的共和国君主想获得友情,靠的不是金钱,而是德行和强盛的威名[6]300。他反复强调君主的德行,并且在论证国家政治不同方面时都提到君主需有德行,他的观点完全可以相互映证。据此我们可以推论重视德行贯穿其思想之始终,并非一时兴起的观点。
马基雅维利在论及君主治国之道时,处处强调君主的道德。那么如何解释他与此相矛盾的“暴君论”呢?他的“暴君论”只是乱世的权宜之计,并非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乱世之中君主倘若一味以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势必只能成为牺牲品,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马基雅维利只是不加虚饰地道出这点。“暴君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强调,“如果可能的话,君主还是尽量不要背离良善之道”[5]103。
其次,马基雅维利不但认为君主须有德行,而且他认为民众也须有德行,他认为建立理想政体的必要前提就是公共道德。在论及如何建立自由城邦时他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腐败,则骚乱与耻辱无伤大雅;只要有腐败,则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6]97他认为如果民众腐败,法律也无济于事。同时,他认为一个权力超常的明君虽可以保城邦一时之良善,但无论君主多么贤明,如果民众缺乏公共道德,良好的统治也难以为续。统治若“不是因为维持着良好秩序的集体德行。此人(明君)一死,它(腐败的城邦)便会重蹈覆辙。”他说“良好风俗之存续,需要法律;同理,法律之得到遵从,也需要良好的风俗。”[6]99从马基雅维利的论述中可见他对公序良俗的重视。在他看来,人民有良好公德是城邦正常运行之根本。
马基雅维利虽然对人性有一些负面之词,但在《论李维》中,他数次提到人民具有真正的美德。他说,人民“爱护自己祖国的荣誉和公益”[6]197;说到做事的“精明和持之有恒,我以为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6]197;“当人民做主时,如果法纪健全,他们的持之有恒、精明和感恩,便不亚于君主,甚至胜过一个公认的明君。”[6]196
本文对带楔板/凹腔结构的燃烧室氢气喷流燃烧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细致分析了不同进口条件下氢气喷流穿透深度、 喷口前后回流区、 掺混效率与燃烧效率等流场结构与典型流场参数的变化特性, 得到以下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在论证自由的同时十分强调自律。他认为自由和自律密切相关,自由并非绝对自由,而是相对的自由,其必要保障是自律。只有每个个人都尊重其他人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国家要保障个人自由,而实现个人的自由必然有赖于每个个体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因此,自由政体的存续有赖于每个个体的自律。所以,马基雅维利所阐述的自由不但包含对个人自由的维护和捍卫,也包括对公共自由的认同和自觉维护,即对公共秩序的尊重。马基雅维利论证他的理想政体不仅自由,而且必须“秩序井然”。要维护自由,公民也要具备“自我治理”的能力。自由的理想政体的建立和维护一定建立在公民对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上,这是马基雅维利所论证的公德的含义。他强调缺乏公共美德,再完美的法律制度也无法持续。
很多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本恶基于他认为人无道德,但实际从他论证美德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来看,他并非无道德主义或者超道德主义论者。相反,无论是论及君主治国还是论证自由城邦的维系,他都十分强调道德的必要性。道德是指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其根本作用在于调解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从马基雅维利讨论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民内部之间的关系来看,他无不强调自律及自治的重要性。道德含义中节制自我的重要性都在这些论证中得到体现,由此可见,指责马基雅维利不讲伦理道德实在是对他的误解。
只是他论证道德的角度跟传统古典政治学的角度有所不同。他认为公民的美德来自保有追求自由的客观需要,这一认识基于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客观要求,并非源于个人的道德追求。这一认识也许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客观认识,“人性并不存在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善和恶总是相对而言的,他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视目的和结果而论。无论是善良还是邪恶都不是人的本性,也不是支配人们活动的首要因素,它们是选择的结果”[9]。他对政体和道德伦理的认识摆脱了空洞的道德目标,建筑在客观的人性认识的基础之上。他思考美德不是为了追求道德上的完善,而是认为培养美德、为共同利益效劳,是我们的自由能够得到保证的客观基础,是一种必然的需求。
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人性论
国内学者都十分强调马基雅维利对西方性恶论的影响。如祝琴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将性恶论引入近代政治原则的始作俑者”[1]25;强世功认为,马基雅维利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系统论述人性恶的第一人[10]。事实上,西方“性恶”论的真正源头是基督教原罪论。早在马基雅维利提出他的人性论之前,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就提出了原罪论。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都把奥古斯丁奉为理论权威,他的原罪论对基督教思想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马基雅维利生活在基督教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十六世纪,受到“性恶”论的影响不足为怪。相反,值得注意的并非他与基督教原罪论的相似之处,而是其思想与正统基督教思想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体现了马基雅维利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光芒。
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造成人类本性的堕落,亚当夏娃的子孙天生就有罪。籍由原罪论,奥古斯丁创造了另一个新的哲学概念:意志论。奥古斯丁承认人有自由意志,但在原罪的影响下,人类失去了自主向善的能力。他说:“那在无知中所作的恶,和那不能如愿而行的善,都称为罪,因为他们都是从自动所犯的第一次罪而来,是第一次罪所产生的必然结果。”[11]132只有意志本身“被上帝的恩典从罪恶的奴役中释放出来,并从上帝得到帮助来战胜它的恶”,人才能过上正直敬虔的生活[11]153。
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并没有变得更乐观。以新教改革家路德对人性的看法为例,他认为:
人类的意志被放在这二者“上帝与魔鬼”之间,好像驮着重担的畜类。如果神骑上它,它会以神的旨意作为它的意志并行事为人,正如诗篇所说的:“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如果撒旦骑上它,它就会以撒旦的意志作为它的意志并行事为人;它也不能选择,要跑向或寻找这二位骑士中的任何一位,但是这二位骑士互相竞争想要骑它。[12]
路德认为因为原罪,人类没有能力选择自主向善,除非神主动控制人类的意志,使其向善。奥古斯丁认为上帝赐予人的完全的善自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时就被破坏。人本身无力洗涮原罪带来的“恶”,人只有藉由上帝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基督教正统观念因为强调人的原罪,因此基本否定了人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可能性,更不认为人本身有能力完善自身和治理好社会。
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与此相比较,我们就能看到二者的重大差异。马基雅维利认为人虽有恶,但并不影响人本身创造合理的制度来解决欲望遏制的问题。有限度的自由从不会产生“恶”,只有不加限制的权力才会导致“恶”, 而权力制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将解决人性“恶”的方法置于人手中,而不是置于上帝手中。马基雅维利对制衡论的论述体现了他对人的信心和信念,这一观点比传统基督教性恶论更为积极乐观。这是马基雅维利对人性新的积极的认识,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体现了其人性思想的进步性。
马基雅维利与传统基督教思想的重要差别之二体现在对待世俗欲望与需求的不同态度上。传统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其欲求会导致人类堕入罪恶的深渊,因而人类的欲求需要压制。马基雅维利承认人有世俗欲望与需求,但他并不认为人对世俗愿望的满足一定会滋生不可逆转的“恶”,因此他并不主张压制人的本性。这一点从他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基本权力视为国家的基本职责,极端重视和推崇自由都可以得到映证。这也从侧面说明他不但认为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是正常的,而且这一需求有必要得到保护。马基雅维利客观承认人的本性需求,摆脱了基督教反人性的认识,体现出马基雅维利比传统基督教性恶论的更加积极之处。
结语
人性之善恶,历来为人所热议。关于人性本身及其善恶,中国哲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老子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儒家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墨子》提出兼爱、非攻、节用等主张,认为人性本善;《荀子》提出人具有“善假于物”“能群”“有义”等特征,但又认为人性恶。《韩非子》主张人性本恶。中国的人性善恶学说,基本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
人性论除了有善恶一说,还有人性抽象论。人性抽象论者认为人性是人类普遍抽象的一般共性,如姜晶花认为“人性即所有人都普遍地、共同地、无一例外地具备的本质属性。”[13]2有些学者虽然同意人性抽象论,但同时也认识到人性具有可变性,在此观点上做了修正,如王海明虽然一方面认为人性是“一切人与生俱来、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14]9,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人性可能随环境而变化[14]11。这类观点都为马克思人性论者所摒弃。马克思指出,那种抽象的人,一般的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提出“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性由各种社会关系在现实中造就,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13]136-37。
性善性恶论一方面基于将人性归结于统一抽象的本性,另一方面,将善恶标准抽象为统一不变的标准。事实上,善恶的标准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时代性和可变性,因此并不存在亘古不变或者适用于一切的善恶标准。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在善恶并存的社会里,人的行为并非一定善或一定恶,也非无善无恶,而是善恶并存的”[15],并且只有具体行为可衡量其善恶。因此,以善恶论人之本性,一方面将人性抽象化,另一方面将善恶标准固化,本身就有值得商榷之处。
马基雅维利没有将人性抽象或简化为性恶论。基于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认识现实、直观,既没有理想化人性,也没有丑恶化人性;他对人性的看法不但没有局限于“恶”的一面,反倒有积极的肯定。他的人性观较之于传统基督教人性观更为乐观进步:他认为人的基本需求合理合法,人具备理性,有自律之需求和能力,能够不断完善自我和社会。他对人性的认识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特征,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他对自由、国家的论述基于对个人权力的肯定和人性的客观认识,体现了民主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