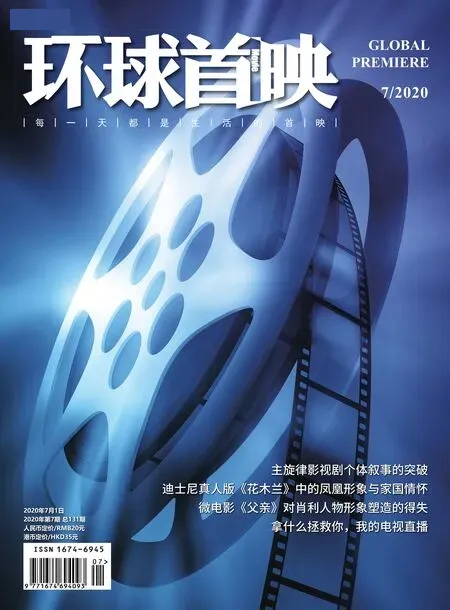贾樟柯“新现实主义”的电影美学
葛厚余 韩国清州大学
一、底层视角与边缘人物
贾樟柯所表现的人物大多数为在城镇成长、被城镇文化滋养的普通底层人民。贾樟柯善于用底层的视角去体会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氛围,体会生活于其中人们的躁动与不安。相对于“第六代”大多数导演所秉持的精英立场,贾樟柯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平民的姿态。这种注重个人独特体验的精英视角,在观念上与法国新浪潮的“电影作者”的观念非常接近,而贾樟柯的电影观念则在更大程度上师承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及至"故乡三部曲"之后,贾卞章柯的镜头不再聚焦于城镇,而寻找更广阔的图景,但对处于社会底层罾通人民的关注却一直如初。
二、城镇图景与社会变迁
城镇成为贾樟柯作品表现的主要题材。在贾樟柯之前,“城镇”是中国电影中的一个边缘题材。略去众多回避现实而醉心于古代故事编造的影片,大部分中国电影的故事背景,不是如《非诚勿扰》和《非常完美》等的繁华都市,便是如《秋菊打官司》和《我的父亲母亲》等的落后农村。“城镇”的形象淡出中国电影的镜头,即便是新生代的电影,大部分也是表现大城市的边缘地带,而非夹于都市与农村之间广阔的“城镇”图景。而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城镇”,将这个不同于已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繁华大都市,也不同于尚在落后的农耕生产中感受贫穷的农村的过渡地带挖掘出来。
变化中的社会和人是贾樟柯电影的一贯主题。在他的大部分电影中,拆迁中的破旧楼房、废弃的旧式工厂和建设中的高楼大厦是一再出现的场景。变化中的社会与身处其中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导演真正关心的主体,也是贯穿其影片的重要话题。在《小武》中,对小武来说,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是艰难的,第一次在卡拉OK时表现出的羞淫便是其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无法定位自己的表现;但即便是这种滞于改变的人,在面对时代变迁时也不得不去做出适应,他最终在女友梅梅的引导之下,也拥有了在歌舞厅"潇洒"唱歌的姿态。《任逍遥》的主角斌斌和小济身处下岗失业已为常态的老工业城市大同,两人作为无业青年终日游荡,虽了解外面世界的精彩,却只能面对现状的灰暗。这两人渴望改变却不知从何改变,对“任逍遥”式自由的追求也显得盲目无知。媒体的入侵向他们展示了《低俗小说》式的自由方式,因而,斌斌和小济为自己导演了一出“改变”自身处境的戏-抢劫银行,最终也只能以闹剧终结。
三、纪实美学
纪实性是贾樟柯重要的电影观念,是其作品突出的美学特点。是对现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最本真的书写,纪实无疑是关切社会真实、忠诚于城镇图景和底层视角的最佳手法。他的作品能够在国外著名的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很好的吸收和消化了西方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特别是对巴赞的推崇和继承,成为中国现实文化语境下对于巴赞电影美学的强有力的回应。
贾樟柯的电影美学是与“第五代”影像美学的一次决裂。“第五代”导演追求深重的历史感、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寻根及反思,在电影视听语言上,注重景物造型、色彩和电影空间的处理,常常以象征化的手法给予其特定的含义。相比于此,贾樟柯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与“第五代”显现出全然不同的风格。贾樟柯追求对当下现实的关切,如上所言的底层视角与城镇图景,而在视听语言上,相较于“第五代”的“华丽”,则显现出“质朴”的风味,使用实地拍摄、自然光、长镜头、同期录音等种种纪实美学手段。
贾樟柯电影一直忠诚于纪实性,倾向于在生活中寻找戏剧性,不刻意渲染情绪或戏剧化情节,使电影在淡淡的时间过渡中呈现一种自然的诗意。电影的结局往往是开放性的,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相比于其他作品的“震撼人心”的结尾,体现的是作者对真实的尊重,不人为地强加一个戏剧性的结局。
体系性与互文性是贾樟柯电影另一个特殊的美学现象。他的前几部电影形成了一个体系。在整个国家发生着历史性大事的同时,小人物自身的历史也在行进。除了人物,还有符号、叙事上的交互指涉、互相书写,这些方式形成了电影文本的互文,是对意义空间的扩展,更好地体现其体系性。也正是这个完整的体系,为中国的底层人民谱写了从改革开放至今属于普通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