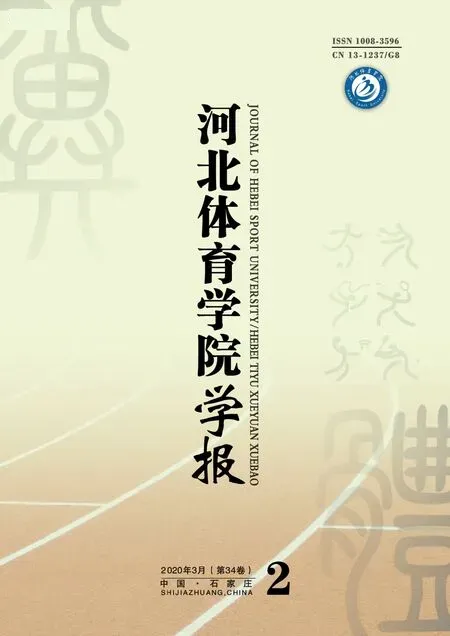远征、探险、朝圣:球迷异地观球现象的文化学释读
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
球迷有异地观球的习惯。通常而言,足球联赛制中的主客场比赛可以给本土球迷带来充分的享受,也能让赛事更公平,但增加了球迷看球的成本。奔赴客场看球劳神费力,而深度迷恋足球的人会在奔波状态中寻找到独特的快感,体验一种被人遗忘或忽略的美感与价值,进而缔造出一些非常性镜像,这也是球迷很少为奔波观赛叫苦的原因。客场观球和主场看球差异很大,其在领地意识、漫游精神、武士远征、极限探险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解读空间。无以否认,球迷的异地观球之举带有旅行、探险、朝圣、远征之类的意味,这样的球迷群体无可避免地存在集体性的强直心理。球迷异地观球的强劲动能来自足球内部显性的信仰,这促使球迷脱离了常态的价值观,并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超越社会常规的行为。
1 具有高度的仪式感和独特美学价值的朝圣式异地观球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有追求自由迁徙的权力,球迷异地观球就带有此种特质,与候鸟类似,球迷的自由迁徙展示出人和自然高度和谐的镜像。人类世界的移民式迁徙往往以家庭为单元,但异地观球的球迷却以男性为主导,于是这一行为就带有了探险和远征的象征意义,其中涉及男人与新领地的内在关联点。如果说奔赴异地的足球队员是出征远方的探险家和战士,那么异地观球的球迷就将自己视作他们的同道和战友与之共赴使命,借以在异地完成找寻并开拓新领地。异地观球由此具备了崇高感。
莫里斯不仅将足球圈子看作是一种部落社会,还视异地观球的球迷为远征者或远征队伍的追随者。“在比赛日,通往球场的道路上一派喧嚣,那幅场景就像一支中世纪的军队在为即将开始的战斗集结。这些人是部落追随者,是他们让足球比赛更加令人兴奋,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球员本身。”[1]208足球毕竟不是真实的战争,于是,球迷探险或远征现象很快就转变成一种朝圣行为。朝圣与探险、远征的区别在于朝圣具备了更多的虚拟节日的成分,朝圣可以极大程度地化解真实的社会危机,亦可以在象征性意味上笼括住探险与远征。尚需分析一下朝圣者主体成员的阶级属性。莫里斯已然看到了朝圣者球迷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他们带有鲜明的尚武精神,在他们心中,自己和部落武士并无二致。正因如此,为了支持自己的球队,朝圣者会付出超常的能量。
在此意义上看,朝圣者与远征往往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朝圣或远征带有一些身体极度自律乃至自虐的倾向。除了常见的奔赴异地观球的人潮,那些不辞劳苦连夜排队购票的群体同样是另一种形态的朝圣者。“重大比赛的入场券提前一个月就被抢购一空。不少球迷为了获得一席之地,甘愿几天几夜在指定的售票处门口安营扎寨,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口自来水。他们当中,多半是普通老百姓,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在购买足球门票时从不吝啬,甚至不惜节衣缩食。”[2]166不难看出,这样的购票行为带有鲜明的身体和精神的自虐现象。球迷苦中求乐,排队变成了一种入会仪式,足球强大的内聚力将很多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排队的场域变成了一种共同信仰集散地,其中蕴含有极为鲜明而强烈的信仰或类宗教的情结,以及一种强直的狂热性。很多人认为球迷朝圣的原始动机是为球队服务,其实不止于此,朝圣的球迷奔赴异地其实是将自己假想成参赛队员了,并想以此来提升球队的竞争力。
南美球迷一度展示出超强的朝圣欲望,因而带有强烈的仪式感。“1930年7月,首届世界杯足球赛在乌拉圭举行。决赛是在乌拉圭队与阿根廷队之间进行。为了给本国足球队助威,4万名阿根廷的球迷们高举横幅,手持彩旗,从全国各地涌向巴拉那河的出海口,因为从这个出海口到达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的路程最近。声势浩大的阿根廷球迷五人一伙、十人一帮,纷纷跳下宽阔的大河,高唱着‘不战胜则死亡’的歌曲,迎着滚滚波涛,向乌拉圭海岸挺进。这种气吞山河的声势,可谓壮观之极。”[3]10-11这种赴汤蹈火式的朝圣行为,融合了殉教精神、探险意志以及残酷仪式元素,展示出足球超常的精神感召力。
正是球迷这种宏大叙事将足球的能量扩张到极限,为此,不少人将球迷看作是疯癫的人群。再以足球王国巴西为例。巴西球迷的观球欲望几乎一直是他们奔赴远方的巨大动力。朝圣的仪式感甚至会压倒朝圣的意义本身,令置身其中的人无法自拔。“一些如醉如痴的足球迷,为了能够亲眼目睹一场称心如意的足球赛,简直是不远万里,不惜一切代价。1981年11月20日,24岁的巴西足球迷若泽·热拉尔多·德索萨只身骑自行车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发,穿过南美洲,横跨巴拿马,途经美国进入欧洲,赶到西班牙,观看了巴西队在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全部比赛场次。虽说他为了解决旅途费用,沿途给餐厅洗盘抹桌挣钱,吃尽了苦头,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4]球迷的朝圣行为由足球的本性决定,它超越了地域、人种和价值观,因而带有世界性、普泛性和同一性。
足球中的朝圣之举还包括对固定的单一崇拜物的朝圣行为,其中强烈的仪式化氛围可以给朝圣者带来一种激情,而这样的激情往往具有天然的非理性元素。“就说贝利吧,只要一提起这一名字,年龄稍长的球迷会向你如数家珍地谈起贝利的一切。最令人难忘的是1977年7月18日,巴西足协为贝利举行了最后一场告别赛,对方是南斯拉夫队,有18万球迷到场观战,有的只是想一睹这一代球王最后的风采,不远万里来到巴西,如同基督徒到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到麦加,佛教徒到印度一样,那完全是一种朝圣。”[5]朝圣的外在性与内在性一直处于高度统一状态。仅从外在表现就可以看到,那里呈现出一种新型的宗教形态,而解读此类现象也只能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切入。
从各种文献中可以获悉,不少球迷的朝圣行为充满了强迫性特征。疯狂的朝圣心理驱使球迷奔赴远方,并将远方设想为彼岸世界,他们宁愿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切。朝圣的过程几乎就是一种放弃自我享乐、甘心牺牲自我的过程。“居住在英国普茨第斯的球迷比利,虽已74岁高龄,仍酷爱足球,他把他大部分的收入都花在为英国的足球队打气上了。每年,这位老球迷都不惜在‘足球旅游’上花去五千至一万英镑。只要英伦三岛的任何一支球队出国比赛,他必定跟随前往,观战助威。”[3]86当足球中的理想主义压倒了世俗精神之后,球迷会放弃足球以外的任何事物,从而单独选择足球,并视之为生命源泉。英国的托尼·英森佐就是这样的部落战士。“他不像一般球迷那样只捧某一个强盛的足球俱乐部,而是对全英所有的92个足球俱乐部都兴趣十足。他刚满18岁时就已经游历了整个英国,光顾了英国足球协会所属的每一个俱乐部的比赛场地。18个月后,也就是在1987年9月,他又来到皇家园林队的爱勃罗克斯体育场观看了一场足球赛,从而完成了对英格兰足球协会所属的全部38个俱乐部场地的拜访。出于一种着迷的心态,他去过150个不属于足球协会的球队的球场观看了比赛,并同50多个球友建立了通信联系。这个学生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几千英镑花在这些活动上,但他一点也不惋惜,认为太值得了。”[3]114足球朝圣现象充满了神奇的动能,心态强直的朝圣者球迷行为中也会充满自我陶醉感,而这样的陶醉感在每一个朝圣者的心里极有可能会演化成一种柔化的情感,自然而完整的人性在外向型社会释放和成长会显得更为柔和,并显示出人性的多维度价值。足球的内在丰富性在此得到了体现,球迷朝圣行为的美学理念也在此语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异地观球之习源自足球赛事本身的特质。可以从审美的角度为球迷的行为找到依据。质言之,球迷受到了来自远方、异域或身外世界之美的诱惑,从而坚定地放弃了自己既有的人生方向,足球和球迷由此展示了各自的价值。足球的确是一种人本位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足球或许仅仅是一种高度感性化的娱乐方式,其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美学符号,因此,尚须从美的诱惑角度认知足球。《足球与哲学:美丽的运动,激情的思辨》一书的译者曾说:“从尼采哲学的视角来看,足球是唯一一个被认定为美的享受的运动。足球是有灵魂的。……‘我们爱上一支球队就像我们爱上一个人一样,我们是爱上他独有的特质。’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数以亿计的球迷追逐他们所爱的国家队抑或是俱乐部的狂热行为——一支有吸引力的球队一定有其他球队无法复制的东西,这无关优劣。”[6]从这个意义上看,球迷奔赴远方还有一种分享、扩散、传播自己美学观的意愿。它不仅涉及足球自身的魅力,还有一种球迷深刻的爱恋之情。
2 以朝圣为核心的远足旅行展示出丰富多元的文化镜像
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探索球迷的行为动机无疑充满了挑战性。球迷不辞劳苦地奔赴异地观球,动机可能并不单一,其中不乏旅行、朝拜与远征之类的复合性的内涵,而其核心动机则是朝圣心理。朝圣心理是一种人性本然的行为动机。它来自人们追求新领地的冒险冲动,也有求取完美生存空间的极限思维动能,还有满足自我意愿的祈福灭灾心理。面对如此语境,不少学者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解读球迷的种种行为,其中就包含了球迷异地观球的内容,并认为这是球迷心理疾病的外在分泌物。
其实,当一种事物上升到绝对高度的时候,其自身的相对性就会呈现出来。人如果一味地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当做一种最高理想,那么自然本位的思想就会受到排斥。因此,还应将球迷的朝圣行为置于一种自然进化的宏大叙事程序中去考量。当此之际,人们可以更好地看到有关球迷朝圣行为的多维度的解读路径。质言之,球迷更像一个高度维持人的动物性的新物种,他们秉持着一种简单而强直的思想。他们一定会认为不奔赴异地看球的人是一种失去责任感、勇敢心与极具惰性的人。足球中的朝圣者与非朝圣者的分野就在这里。在一种精神对立的领域内,朝圣类球迷和非朝圣类球迷暂时性地失去了对话的必要性,就如同球迷和非球迷之间的隔阂一样。
很多信仰都是相对孤立的,且带有很强的自我化的特质,信仰者群体与非信仰者群体间充满了对立性。换言之,在充满高度对立性的信仰秩序中,很难彻底理解彼此的行为,能做的只有彼此宽容。当然,球迷的异地观球现象还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除去远征、探险等之后,人们还会认可其朝圣价值,至少在表面看来,如此举动或许仅仅是一种旅行,因为任何一位球迷都没有刚性的工作任务。旅行也是一种人类的天性,西方文化学家早已将旅行与朝圣视作一种事物的两个方面。旅行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奴隶主在旅行中进行一些游览活动。例如,在我国西周有周穆王游西王母国的传说;在埃及的法老墓碑上有反映王朝旅行和娱乐的雕刻;罗马帝国除从事商业的旅行外,还有体育、朝圣等包含游览内容的旅行活动。”[7]体育、旅行和朝圣发展到当下则出现了合流现象。“吉布森、威敏、霍纳克的实证研究认为小型体育节事在增加城市旅游收入、塑造社区精神的同时造就了狂热迷、体育朝圣迷。”[8]从“体育朝圣迷”这一概念中不难看出,旅行和体育原本就有血缘关系。足球中的旅行看球是足球朝圣的显性指标。
正因如此,用旅行观球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异地观球行为的合理性还远远不够。足球迷超越常态的举动主要体现在对神圣价值的膜拜层面。异地观球由此而充满了神圣感。且以乌拉圭的曼努尔老人为例。第13届世界杯期间,“曼努尔老人为观看自己国家足球队在足球大赛的比赛,从乌拉圭动身,整整步行326天,途中经过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历经了千难万险,最后才得以到达墨西哥。”[3]60他和上文提到的边打工边骑自行车到西班牙看球的德索萨一样,并不以之为苦,反而乐在其中。对那些习惯观看现场足球的球迷来说,奔赴异地看球就只能是朝圣行为而非其他。
既然朝圣成为唯一的动机,那么旅行的目的就不仅仅限于观球,其还包括对足球圣地的考察。对中国的足球观众而言,巴西是一方遥远而充满足球魔性的地域,他们的巴西之旅往往带有足球朝圣的性质。2013年,一位中国足球观众前往巴西旅游,坐一位新华社驻站记者的车经过里约市内一段高架路时,他指着下面一破旧的球场说:“看,那是罗纳尔多踢出来的地方。待我拍两张照片。”车速加快,他又说道:“前面左手边那片贫民窟,那是阿德里亚诺出生的地方。”[9]这位中国旅行者的旅行便兼具了足球文化考量与普通旅行朝圣的双重价值。与之类似的还有颜强。卢劲在《捕捉民生化足球》一文中曾经描述过,《足球周刊》的编辑颜强独自“行走在英格兰,行走在足球朝圣路上”,听到《You’ll Never Walk Alone》时,萌发出“一种莫以名状的激动,让我泪水盈眶”的情景[10]。比为观球而旅行更为极端的行为则是移民。“英国球迷伊恩·克拉法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自称是球星莱因克的超级球迷。为了能常常观看他心中的球星偶像——莱因克的比赛,他卖掉房子,辞去工作,移居西班牙。”[3]63人们仍旧可以用旅行的概念来解读球迷异地观球行为,但是,旅行的原始支点也在于朝圣。足球的价值体系来自诸多故事链,其中最惊艳的就是球迷的朝圣之旅。这里已然涉及朝圣式观球与偶像膜拜现象的合流问题。
探究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学者已然看到了朝圣现象的合理性。“偶像崇拜的虚拟性情感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填补了神灵缺席下青年对意义的需要……它完成着对青年人日常生活的解释,给年轻群体铺设了一条世俗化的朝圣之旅。”[11]超强的朝圣冲动使得球迷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世俗性烦恼,但是,人世间到处充满了危境,球迷们摆脱世俗烦恼的同时,却极有可能面临非世俗性的烦恼,那里同样存在无以摆脱的巨大精神压力。为了将非观球时期累积的不良记忆排遣出去,球迷们只能长年累月地奔赴异地观球。
球迷观球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那种朝圣的内在指向是对本方足球的强力支持。莫里斯曾经对此有过深刻的认识。“庞大的粉丝军团用咆哮和鼓掌表达自己的支持,还展示着球队的颜色,球员们会感受到更大的激励并更加自信。他们会感觉自己‘不能让粉丝失望’。……最热心的粉丝会专门组织大巴把他们运送到球队的客场,或者乘坐长途火车,给远离主场作战的球员创造更有支持性的气氛。这些旅行客场粉丝的数量很少会超过主场粉丝,不过某些球队能够享受到十分狂热的支持,以至于无论他们在哪里比赛,都有‘在主场’的感觉。”[1]284-285在莫里斯看来,不辞劳苦奔赴客场的粉丝是一种足以赢得同伴认同和尊敬的人。
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足球朝圣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不乏涉及足球本体运动形态的类型,而颠球旅行则是其中的一种富有创意的品类,它兼具表演与朝圣的双重价值。“吉林省延吉市啤酒厂26岁朝鲜族青年工人足球迷金振光,为了支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从延吉徒步颠球行走1 677公里,于1993年8月9日上午9时30分抵达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完成了这一壮举,并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3]130朝圣的仪式感在这位球迷的颠球行为中得到了最大的彰显。当然,颠球朝圣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非常人所能做到,人们在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种由球迷们组织起来的朝圣式旅行活动,这里面就不得不提球迷组织及球迷领袖的功能。北京球迷协会成立于1988年10月26日,“他们先后赴沈阳、广州为中国男、女足助威,并利用首都的天时地利,为全国球迷提供邮购明星照片、足球专著和咨询服务等,并编有《球迷手册》。”[3]179重庆球迷协会在中国较有影响力,“在‘贺龙杯’等较有影响的国内邀请赛上,他们前往助阵,跟随中国队走南闯北,其酷爱足球程度不让欧洲球迷。”[3]180莫里斯还论及球迷领袖问题。“在全体粉丝中存在几个特殊的类别。有一些人承担着天生领袖的角色。有一些人是暴力行为领袖,会在爆发暴力事件时充当指挥。另些人是吟唱领袖,他们发明新的歌和短句然后负责领唱,确定新的旋律,或者发起有节奏的鼓掌。还有一些人是旅行组织者,负责安排大巴、集合地点和其他交通细节。”[1]285莫里斯显然看到了球迷组织工作的严肃性,其中不乏组织旅行之类的内容。
在类型多样的朝圣式远足的球迷当中,残疾人球迷的朝圣之路更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典范性。比如盲人萨利。“萨利‘看球’的瘾很大,除了‘看’多特蒙德市各个俱乐部之间的比赛,还奔波于杜塞尔多夫、拉德巴赫、波鸿等城市,欣赏各种高水平的足球赛。……萨利自豪地说:‘我只要一听观众的反应和球场上扩音设备发出的声音,就能判断出这是在哪个城市的哪个球场。’”[3]82萨利的观球行为中更多地充满了人类学意义的内蕴的感触感,而非常态化的观球感,他凭借声音记忆便可以分辨出各城市的差异,不只证明了他身体感知条件的特殊性,更说明他对异地观球的投入程度。与之类似的还有德里克·多尔顿。“德里克·多尔顿可算得是英国最忠心耿耿的足球迷了。1949年,在他2岁时,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尽管严重的残疾使他大半生的光阴只能病卧在床上,但他却始终不渝地支持罗瑟勒姆联队达30年之久。他乘坐一辆具有特殊装备的大篷车,跟随着他所崇拜的足球队,每个赛季都要周游8 000公里。”[3]58萨利和多尔顿的行为只能从信仰学或宗教学的角度来释读了,他们的惊人之举也恰恰证明了足球自身已具有宗教般的独立性。
3 朝圣式的异地观球必然伴随着超常行为和超常体验
体育的宗教特性早已为西方学者广泛认可。朝圣与体育的关系可追溯到古代奥运会。“体育也仅仅是奥运会的一部分。奥运会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世俗娱乐盛会。人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辞辛苦地赶赴圣地,感受众神与凡人交汇的慰藉,使之成为一次宗教的朝圣、体育的朝圣、文化的朝圣。奥运会的魅力磁石般地吸引着希腊人。”[12]朝圣元素存在于体育本体,正因如此,任何种类的球迷的朝圣心理都显得格外强大,参与此道的球迷做出一些令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1982年5月,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市,一位名叫彼尔·曼因斯的青年,因盗窃汽车而被当场抓获,送交法院审理后,法官邦克判了他三个月的监禁和罚款。当宣判完毕后,当事人曼因斯请求法官可否将监禁延期至两个月后执行。理由是他已花了1 500美元买了在西班牙举行的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联票,而一个月后比赛就要开始了。”[3]51-52曼因斯奔赴西班牙观球的意愿十分强烈,其所提出的要求虽属世俗层面的非常态,却有足球层面的常态性。
异地观球既然带有朝圣性质,也自然高于金钱和家庭。“第11届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阿根廷队与荷兰队比赛时,球票的黑市价高涨到500美元一张。一位叫汉斯的球迷苦于囊中钱币不足,他急中生智,毫不犹豫地竟用自己的小汽车换了一张球票入场观球赛。当比赛结束后,他只好乘出租车回家去。有人对他说这样做吃了大亏。而汉斯则斩钉截铁而又喜形于色地说:‘不!不吃亏!划得来。汽车没有了可以买得到,而这样世界高水平的足球赛不会再有了。’”[3]110由此可见,足球时而会缔造一种凌驾于自然生活之上的另类生活。
弗尔曾经讲述过一位苏格兰球迷的故事。“这位球迷认为他所钟爱的球队的价值高于工作、家庭和妻子。‘我热爱流浪者队。如果我不得不在工作和流浪者队之间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流浪者队。如果我不得不在我妻子与流浪者队之间选择的话,我还会选择流浪者队。’的确,一年中有16个周末,他选择了流浪者而不是他的妻子。他邀集了伙伴,喝上两大杯威士忌,然后开车上路,车里放着宗派主义色彩的曲子,一路遥遥北上。”[13]与之高度相似的还有格伦·邦内尔。“这位英国足球迷正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要老婆还是要他所支持的足球队。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关键时刻,邦内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邦内尔家住英国兰开夏郡的彭沃萨姆,可他却一天到晚魂不守舍地向往300公里以外的格拉斯哥,因为那里有一个他崇拜备至的凯尔特人足球队。每年的足球赛季,他总是要跋涉几百公里,花费数百英镑去看比赛,不然就没法活下去。……终于,在当了11年的‘足球寡妇’之后,邦内尔的妻子对邦内尔郑重其事地发出了最后通牒:要老婆还是要足球队?邦内尔选择了凯尔特人足球队并离家出走。”[3]78前者的开车上路和后者的离家出走都带有强烈的流浪生活性质,其与足球的纽带关系也尽显其中。由此可见,异地观球不仅会成为一种个体性的需求,还会催生出一种超强性的精神和身体的依赖性元素。
在一种热恋足球的强直情结的蛊惑下,很多球迷几乎须臾不可摆脱自己钟爱的球队。高强度的部落凝聚力迫使球迷急欲归队,成为球队的主体成员。这种现象让人想到这个星球上所有群居动物的天性。很多群居动物都有为同类牺牲自己的本能。球迷大体也属于这样的类型。当看到球迷们自虐性地奔赴异地观球之时,很多非球迷人士的心里多多少少还会困惑。但是,高度群居化的球迷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奔赴异地,借以成为一名真正的部落精神的信徒。
质言之,球迷奔赴异地观球带有强烈的求取内心满足的愿望,这种满足感蕴含有一种圆满之境,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团队精神、明星膜拜、实地观览、异地助战之类。从实际的情况中不难看出,球迷的异地观球行为带有明确的实用性动机。但须说明,球迷朝圣的实用性体现在一种精神价值的兑现层面,而非世俗利益的获取领域。在此层面上,球迷放弃工作、家庭也就不足为奇,甚至改变信仰,亦情有可原。1988年欧冠1/4决赛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流浪者队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斯泰亚乌亚队之间进行,赛场是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鉴于英国球迷有奔赴客场观球并闹事的传统,罗马尼亚方面不愿为这批球迷发放签证。“当格拉斯哥队的部分球迷听说罗马尼亚方面可能会对共产党党员提供优惠待遇后,不少球迷纷纷申请加入英国共产党。”[3]80球迷信仰的游走性并不明显,相反,球迷为了自己认定的观球大业,往往会爆发出无以抵挡的精神与行为能量。因为,在球迷眼中,足球高于其他信仰。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朝圣已然是球迷的一种生活常态,任何人都很难说清楚哪一种球迷的哪一次朝圣活动最具典型性。而鞍山球迷罗西的经历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球迷朝圣行为的典型。罗西是超级球迷,笃信足球中所有的理念及其衍生物。通常而言,球迷以看球为本色,但罗西则属于朝圣与演说兼善的球迷。“每逢足球大赛,他就是砸锅卖铁也不含糊,毫不犹豫地背上军号,南征北战,几年来在全国大中城市的球场洒下自己喜悦和悲伤的泪水。10年中他把自己拼命挣来的10多万元,全部用在了足球上。面对他这种疯狂的举动,妻子无法忍受了,流着泪让他选择,结果他挥泪选择了离婚,选择了足球。”[3]150罗西为了观球而奔赴异地的行为强直而简单。很多人将罗西看作是中国的第一位职业球迷,这也给他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乃至生命感受。罗西组织球迷参与的一次长途旅行观球活动值得言说。“1990年4月29日,辽宁队在沈阳主场迎战日本尼桑队争夺亚洲俱乐部杯。罗西在鞍山振臂一呼,呼啦啦500多球迷跟随他奔赴沈阳为辽宁队助威,球迷每人出5元钱,其余全由罗西付账。在鞍山通往沈阳的公路上,一列车队浩浩荡荡,坐着鞍山500多名热血壮士。此时的罗西激动得更加滔滔不绝,他可能没想到他因此首创了中国球迷规模最大的运动战。”[3]151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资深球迷,罗西的确创造过一些看似更为纯粹的朝圣镜像。“1992年夏,又一项伟大的计划在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罗西心中诞生:骑车周游全国的四万里长征。球迷发烧友应该在球场上,罗西周游全国为了啥?他说:‘中国足球屡战屡败,许多球迷的心渐渐凉了。我周游全国,为的是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火,让他们回到赛场上去,继续为中国足球的拼搏和腾飞摇旗呐喊,为中国足球献出自己的一颗心、一份爱。’”[3]152无以否认,罗西的骑车旅行完全是为了中国足球,其朝圣的意味十分明显,充满了鲜活的仪式性与强烈的画面冲击力。罗西获得球迷认可的缘由有很多,其中不乏其朝圣旅行距离远、朝圣时间长、心态坚定等元素。
处于部落思维状态中的球迷的确存在反社会的迹象,由球迷群体缔造出来的足球文化也充满了悲剧性。且不说罗西为了足球放弃固定工作与完整家庭,单说他的足球朝圣之旅。“罗西在穿越秦岭时,遇到几个路霸的威胁,他掏出匕首高呼:‘谁敢犯我,我必杀人!’使路霸未敢轻举妄动。他骑到山西榆次一小镇时,正逢亚洲杯中沙之战,这里的小旅店却收不到电视转播,他急得发疯似地向县城饭店跑去,冲进去后,罗西顾不上说话,拿出两百元让服务员开一个房间,并向站在旁边的副经理说:‘你有什么要问,等足球赛结束了再说。’”[3]15“罗西在‘长征’途中,几度因发高烧和犯心绞痛被送往医院急救……1994年3月,罗西克服重重困难由北向南,历时1年零6个月,跨越24个省、3个直辖市,行程23 000公里,完成了‘红拖球迷万里行’的壮举。”[3]152-153不难看出,罗西的朝圣之举富含游戏人生的元素,但也充满了浪漫主义和悲剧色彩。
很多人将球员的炫技性看作是男性游戏精神的象征,而经常遗忘球迷的炫技性游戏精神。从罗西的故事可以看出,足球激活了都市闲人的思维与行动活力,一种足球信徒的想象图景在这些人心中全然浮现,都市闲人由此演化为崇高的民众卫士,也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存在的合理性。其实,球迷和球员都是游戏人,前者更为放达,后者更为严谨。两者都是人类自然意志的扮演者,同时也是大自然本体意志的表演者。在此意义上看,罗西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典型的执着型、信仰型、迷恋型球迷的代表,其自然表演的意义压倒了世俗世界的内涵。
在精神纯洁度层面上考量,罗西称得上是中国球迷的一面镜子。时过境迁,罗西已然老去,其球迷领袖的地位已然烟消云散。但是,罗西的故事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球迷的信仰高度,罗西以朝圣始,又以朝圣终,他所完成的恰是他有关完满人生的一种求索程序。
如果将足球朝圣事件搁置到当下来衡量,肯定有人认为那里呈现着一种精神异化之态,也会让更多人联想到人类社会中的诸多集体迁徙的壮丽图式。人们可以想到麦加朝圣的集团庄严感,以及儒教文化体系中的大年三十归家大团圆式的集群性大迁徙。人类的集团大迁徙有两类,一类是物质性的,如美国的西部淘金热;一类是精神性的,如球迷的异地观球。质言之,足球朝圣之举在更高的层面上可以体现出足球的文化学、信仰性和宗教学的天然属性。
4 结语
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已然占据重要的一席,人类学是一种以他者眼光考察独特的封闭式文化的学术体系,而球迷的异地观球行为几乎就是球迷人类学的主导性内容。足球有许多值得人再度解读的地方。质言之,足球是一种由全方位的感官体系激发出来的文化或文明形态。足球中的异地观球传统映照出人类男性喜好远征、探险、旅行的天性,三者具有行为学的联动特性,其核心点在于一种迁徙或旅行过程中的朝圣心理。于是,球迷的观球朝圣主旨更像一种生活隐喻。足球激活了球迷的远征、探险、朝圣之欲望。足球之欲催生出球迷群体的生命之欲,球迷远足朝圣模式就此成立。它旨在演示一种源自远古信仰的迁徙仪式,并在适当的场域展示出一种关于人类生活中原生性、神话性与史前性的极端欲望。舍此以外,足球的朝圣之旅难获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