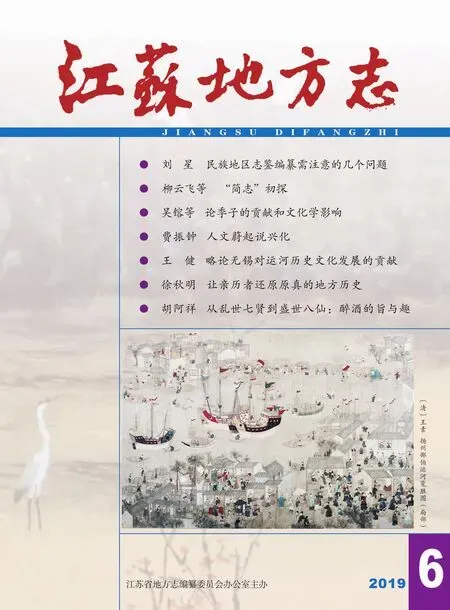人文蔚起说兴化*
——《兴化文化史稿》导言
◎ 费振钟
(江苏省作协 南京210019)
提 要:兴化是里下河区域的腹地。该文将兴化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即上古阶段的萌生期、春秋战国至两汉隋唐的显形期、北宋时的形成期、明清两代的丰盛期、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转型期。对兴化文化发生的自然与经济基础,近代以前兴化的社会生活形态,兴化的教育、学术与科技文化,兴化古典文学艺术的重要成就,兴化的民间风俗礼仪等作了概要揭示。指出兴化文化的高端与突出部分,是基于“水文”与“人文”融合,借助中国诗教传统所产生的社会美学精神。《兴化文化史稿》旨在通过小传统传承大传统,梳理兴化文化经脉在今天的意义所在,通过兴化有限区域范围,提升兴化人的生存高度,放大中国人对于诗意栖居的理想和经验。
一
兴化为古楚昭阳之地,虽然史说不明,但公元前323年,楚国通过战争,已将版图扩张到了兴化所在的海滨淮夷之地。那时候,兴化地区是否确认分封给楚国大将昭阳为领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兴化这块地方从此与楚国之间建立了政治、社会与文化关系。“昭阳”之说,就是这种政治、社会、文化关系的体现。附丽于历史情景之上的“昭阳采邑”,既是对来自楚国拓疆者和传说中领主昭阳的尊重,也是兴化进入人文之治的源头性标志。其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事实意义,于兴化地方价值的建立不可谓不重要。
“昭阳”以后,兴化地方行政情况漫漶不记。史料有载,到秦王朝结束分封制,设立郡县制,兴化地区属东阳县或广陵县。当时这里仍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海碱荒地,无论地产为盐、为渔、为农,社会尚未建成,政治亦未健全。
汉王朝初年,兴化地区在吴王刘濞封地。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吴王刘濞招纳流亡人员,到这里“煮海为盐”。今兴化一带始有以盐政为主的行政管理。汉武帝至东汉末年,兴化隶属海陵县。三国时期,废海陵县,兴化地区成为吴、魏双方对峙的军事缓冲地带,社会零落,几无治理可言。西晋统一南北,重置海陵县,东晋永嘉南渡时(390 年左右),大批北方士民涌入今兴化境内,在今兴化边城一带建立了侨置建陵县。又过近二百年,直至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撤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唐初改海陵县为吴陵县,不久又恢复原名,延至唐终,兴化地区都属海陵县。
“五代十国”是一个政治上分割的时代。也就在南北方重新统一之前的杨吴武义二年(920),由杨吴政权划出海陵县北乡,在盐政管理建制“招远场”的基础上设立兴化县,从此正式开始了兴化县治。设立兴化县的原因不能具知,但也不外乎人口、土地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需要。可以考量,在兴化地区设立县一级地方政权,应缘于经济变化。农业经济取代国家盐业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当本地区农耕为主体的社会业已定型,需要更加适当有效的地方管理。
县名“兴化”,其意为“兴盛教化”,是对地方未来发展预设的社会理想。后来《扬州府志》这样解释“兴化”:“兴化义无所考,旧志以杨行密‘觊兴其化’,疑或然也”。
所谓“觊兴其化”,大约要到北宋王朝时期才算真正展开。“兴化”成为地方历史中一个响亮的人文之邦,也从这时候起步。
自宋王朝至清王朝,兴化历属泰州、承州(州治设今高邮)、高邮(路、府、州)和扬州府。民国中,兴化县为地方职权自治单位。延至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兴化县转为扬州地区管辖。
二
兴化文明在大海的气息中从水中生长。
距今7000 至6000 年左右,一条地质史上叫做西冈的砂地,在大海与长江交汇处水下形成,为兴化地区成陆做好了准备。而后,经过大约1000 年,海水退去,西冈露出,再经过中冈、东冈,海岸线东移,这时候,陆地渐出,兴化一带进入潟湖湖时期。海水时涨时消,又经过2000 年左右,演变成湖泊沼泽。在潟湖到陆地湖泊时期,兴化开始有人群居住,先民肇基,文明始现。
第一批到达兴化生活的人类,大约在5000 至6000年前,他们在境内林湖乡影山头一带高地,留下了栖居的痕迹。当时为新石器时代,那些石斧一类的工具,以及稻禾残物,预示了日后这片土地农耕的可能。不仅如此,他们在渔猎和耕种之余,甚至还在陶罐上刻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笔画简洁,但难于破解。
蒋庄良渚文化遗址,则证明了4000 至5000 年前,兴化先民生活的继续。有一支良渚人乘桴泛海,来到这里建立了大型居住聚落。他们在平地上建房,在这里捕鱼、种植,可能还有自己的果园。他们中的能工巧匠制作出玉琮、玉璧、玉钺等许多精美的玉器。他们还会画画,那些陶器上的图像,显示了他们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他们有部落首领,有代表神权的巫师,这些高贵者的墓葬堂皇富丽,说明了社会的尊卑有序等级分明。
另外,南荡文化遗址则是兴化文明的另一个插曲。北方人类向这里迁徙而来,也许他们仅仅是路过。这些先民们在此生活时间不长,给兴化留置了一些绳纹陶器后,继续向江南迁徙而去。
这是否象征着兴化从海水生长的原始文明到此终结呢?无论怎么说,存在于兴化地区的三大遗址,为人们建构关于兴化的文化想象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空间。
三
在现代地理上,兴化地属里下河区域。
民国时期的地理史家,借用宋、明两代扬州运河以东地区称“下河”说法,重新厘定了一片区域,这片区域称“里下河”。里下河区域以“水”为范围,西至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南至运盐河(老通扬运河),北至淮河入海水道(苏北灌溉总渠)。
里下河这个特定的地域概念,既标明了里下河的地理空间,也体现了里下河的地形历史特性。简单地说,里下河地区是历经数千年海进海退,长期在波浪、潮汐和水流的作用下,于长江下游北侧冲积而成的海滩湖洼平原。
时间太过漫长,以至大海不知不觉向东移去,新的海岸线将海边以西地区,与外海完全隔开。留下的一大片海湾浅滩,起初呈形为潟湖地貌,随着长江与淮河的泥沙冲积,以及江水与河水的注入,水质逐渐淡化,形成陆地湖泊。于是离现在3000 千年左右,在这大片浅滩上,古射阳湖出现。
正是古射阳湖的万项碧水,孕育了里下河区域大块土地。
古射阳湖,汉代称射陂。其范围西起今宝应县射阳湖镇、安丰一线,北至今淮安泾口、左乡一线,东至阜宁县西喻口,南至兴化市得胜湖和白沙湖。《汉书》里所说“射陂”,当时实际面积多大,没有具数。800 多年后,唐元和年间修撰的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对唐代射阳湖有记录:“射阳湖——萦回三百里”。由东汉末到唐元和年间,这一时间段里的“三百里”射阳湖,肯定是已经缩减了很多面积的测算,或者只是古射阳湖南部中心湖区的面积了。原本汉代在射阳湖区域制盐垦土之列的兴化地区,大约这时已从古射阳湖分身,仅在它最南面留下白沙湖和得胜湖两片湖水作为小小的遗存。北宋时期的射阳湖,显然已在兴化身后。所以11 世纪初兴化知县范仲淹站在兴化土地上返身北望,写下这样的诗句:“渺渺指平湖,烟波入望初。纵横皆钓者,何处得嘉鱼?”
明王朝以后,黄河淮河交涨,由西而来的河水冲堤溃坝,注入射阳湖,“潮沙溢入,淤浅且过半”(《读史方舆纪要》)。到清朝乾隆中期 ,虽然疏浚,却不见成果,延至清王朝末年,射阳湖已淤积。
于是古射阳湖完全消失。
古射阳湖的消失,同时便是里下河平原土地和地域的完型与成就。围绕着古射阳湖的里下河地域,完整范围为1.3万多平方公里。到它地域成型时的清代末年,这1.3万多平方公里上分布着山阳(今淮安区)、宝应、高邮、甘泉(今扬州市区西北)、江都(今扬州市区东南)、泰州、兴化、东台、盐渎、阜宁10 个州县。现在则为高邮、江都、海陵、姜堰、海安、兴化、大丰、东台、盐城、建湖、宝应、阜宁、淮安13个县市。
里下河平原的腹地是宝应、建湖、兴化。兴化则是腹地中的腹地。按照本地区地形的一种形象化描述,里下河平原“形如侧釜”,兴化位置恰好在釜脐,俗称“锅底洼”。
四
在里下河平原上,处于最低洼位置的兴化,为真正的水乡泽国。
明嘉靖年间,主修《兴化县志》的本县知县胡顺华,如此描写兴化水乡风光:“沧海远环于东,珠湖迥挹于西,南望大江,北指长淮,地气毓灵之会。镜中水色,出没鱼龙。虽无山麓,实阻水为固。若襟六溪,带五湖,桥枕凤凰,沟盘龙虎,皆一邑之大观也。”五湖六溪,鱼龙世界,构成了兴化“一邑大观”,在一位外来的文人官员眼里,可能足以称羡于外,让他深感置身此中的得意与骄傲。
水,不仅是兴化文化的色调,也是兴化社会的主题。
自唐史所记在射阳湖“屯田”开始,兴化从延续千年的渔盐之利,转而跨入农业经济本位。当唐王朝委派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主持修筑常丰堰(捍海堰)在兴化以东阻挡海潮时,事实表明从8世纪开始,兴化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便进入漫长“治水”历史。
治水既是兴化的社会重任,也是兴化历代地方政治之要务。正是在治水的过程中,兴化社会文化进入了它重要的时代节点。
既是必然,也是偶遇,北宋天圣初年范仲淹由盐官调任兴化知县。他是兴化在史有载的第一位地方官,他来兴化的主要理由是为了治水。11 世纪前期的兴化,由于范仲淹的到来而成为后世所重的“名县”,而重修“捍海堰”的壮举,显然是兴化成为名县的前提。
经过五年的曲折反复,新的捍海堰修成,创基人范仲淹的名字和其他两位后续者名字,刻在三贤祠上。兴化因范仲淹而传名。
对于捍海堰的重建,历史评价多在农业社会的经济利益方面,事实上,范仲淹对兴化通过治水发生的影响与贡献,远远超过一篇《捍海堰记》的表扬。
就社会来说,由于此前多年水涝灾害造成的社会凋零,至范仲淹“知兴化事”后很快恢复生机。史传,“流民返回兴化者众”,不单是因为范仲淹倡导治水的成功,也是他的号召与吸引。一个社会重新回到安定的生活秩序之中,不仅意味着丰衣足食,而且意味着一种社会伦理的安稳。当时,突出的表现是,回到兴化的农户,由于感慕范仲淹,有不少改宗范姓。这件发生在兴化的社会伦理大事,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它说明范仲淹个人所造就的一种良善德性,深入人心与人性,而内在于社会教化,持久地促进了兴化文治。这是“兴化”,“觊兴其化”的开始和基础。
因此,就不能不惊异于范仲淹在兴化短短二年多时间里,兴学校、定礼俗、敦民风等各项举措,当时就能取得成效。如果离开他个人建立起来的道德影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以后,范仲淹的影响一直是兴化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要言之,以治水为契机,通过范仲淹在治水上的功德建树,兴化获得一种特殊的文化力量。或者说,范仲淹为兴化创造和凝聚了一种“水德”文化。中国传统中历来就有“水德”之说,但在兴化,这一文化具体化、时代化和现实化了。因水建功,因功传德。由于范仲淹,兴化的水赋予了一种新文化功能。洋洋至化,日见深柔,这对兴化是怎样的一种文化机运。
似乎是一种刻意说明,范仲淹在兴化任上,于城南旧三闾大夫庙旁的馆舍,建了两座亭阁。他为这两座亭阁取名“沧浪”与“濯缨”,并且赋诗其上,其一云:“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范仲淹创造性地通过诗教传统,成功地将屈原诗中关于“水”的德性之义,注入到了兴化,而兴化由此将自己的目光接通了更高的文化目标。毋宁说因有范仲淹的“素心爱云水”,这才凸显了作为“水德”的诗性崇拜。
楚水汩汩,将来也会流淌不息。
五
驾舟串场河上,贩运私盐的张士城,乘时而起,在兴化东北白驹场起义。这位在“斥卤之地”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他的成功,谱写了自“煮海为盐”开始的淮南盐场历史新篇,他的失败,则带来14世纪末兴化社会与文化的重建与更张。客观上,张士诚是范仲淹之后影响兴化社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张士诚从兴化戴窑起兵一直到苏州称王,历时14 年。最后几年中,对手朱元璋为了截断张士诚与“肘腋之地”的联系,以重兵包围张的家乡,并取得成功。经过这样的残酷战争,包括兴化在内的里下河地方社会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367年张士诚在平江被彻底打败,朱明王朝建立。战乱加上灾害,此时兴化仅剩8000 多人。从宋代以来,偌大兴化,陷入社会解体几近不毛的悲凉境地。
这是明洪武初年的情景。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兴化户口忽然急速增加,人口一下子达到63000 多。这种社会复苏的超常现象,似乎没有别的可能,只能是外来移民的加入。
这里就要说“洪武赶散”的故事了。
所谓“洪武赶散”,说的是朱明政权为了报复江南苏、松地区支持张士诚,将本地人民强行驱赶到苏北地区。这一说法颇见于苏北移民区域后代移民大族的家谱记录,后世一些相关的地方志不少也据以转载,如《续修盐城县志》说:“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又如《新安镇志》,在讲该地大姓来历时,直接使用了“洪武赶散”的说辞。地方志之外,还有一些文人笔记,又加以渲染。于是,经过口头与文字的传布,“洪武赶散”便成为对14 世纪末苏北移民的一种生动解说。
但在《明史》里,虽有洪武年间大规模进行社会移民的文件,却未见从苏松地区向苏北移民的官方记录,“洪武赶散”仅被看民间传言,此事本身的真信度,及与张士诚的关联,其确证性都有怀疑不决之处。
民间传言往往是对历史事实的改写。考据苏北淮、扬两地,当日确有大量移民进入,而且主要移民来自苏、松地区,那么“洪武赶散”就不会是凭空杜撰,它的真相可能被隐匿,也可能被借用。隐匿可能是有意无意的历史遗漏,而借用只是一种历史修辞,通过一种语法和叙事,把民间不能清楚辨析的,或因时间长久难于重返现场的事实,加以情境化和故事化。“洪武赶散”就是这种具有明显“借用”性质的移民故事。
分析当时的政治情势,“洪武赶散”最大可能是一个流亡者的故事。
朱元璋立朝伊始,立刻对昔日张士诚占据并统治了十多年的苏松等地区采取重赋方式,以示新王朝对该地区的缙绅不久前强力支持张士诚抵抗的惩罚。其中苏州府税赋最重,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升至全国田税平均水平的八倍。如此重赋,朱元璋不容许有任何反对,洪武十年,苏州知府不合建议减赋,竟被朱元璋诛杀。因此,以苏松等地区农民和地主们,在无法承受重赋、生活迅速贫穷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集体流亡。按有关史录中的户口统计,苏州府所属太仓,洪武二十四年在册8986 户,到宣德时仅存738户。如太仓所见,当时苏州地区不仅流亡规模大,而且是持续性的。
那么他们流亡到哪儿去?苏北淮扬里下河地区,显然是他们选择流亡的主要目的地。
这是一种被动而痛苦的移民。出于流亡者的心理,也是出于他们对新到陌生土地的情感认同,“洪武赶散”的移民故事,隐含了对朱明政权的憎恨,和对前吴王张士诚的怀念与忠诚。流亡者来到苏北里下河地区,这里是张士诚故乡,如今成为他们落脚的之地,无论怎么说,大家在这里同讲“洪武赶散”的集体故事,都是对背井离乡之痛的内心安慰。
在这个移民故事中,兴化无疑成为“洪武赶散”的中心叙事之一。兴化凋落的社会也按这个移民故事的结构(张士诚—苏州—兴化)重建和更张。
洪武二十四年的兴化6 万多人口中,占全部移民到淮扬地区的比例多大,其中又有多少来自苏州地区,没有必要核计。关键在于,一个以“苏州之梦”为凝聚力的移民社会在兴化建立,它重构了兴化,更新了兴化过去已有的楚文化背景,将吴文化推到了新时代幕前。
吴风吹过楚水,风生水起又一代。
六
14 世纪末15 世纪初,兴化作为移民社会,开始了它的另一个起点。
从明王朝嘉靖年间开始撰写的兴化地方志,记录的都是这个起点之后的兴化性状。自然环境没有改变,湖泊与河流依然环绕,水仍旧是兴化的风景、资源以及灾害主因。变化的是社会生活,从县城到乡村,大到社会格局,小到生活细节,都明显体现出新时代的特点。
第一座青砖筑成的高大城墙,代替了昔日的兴化土城,显示了新王朝的对于地方宣示“洪武”之威,同时也表明了社会进入安定。城墙使用的是本地戴窑烧制的大砖,昔日这个张士诚起事之地,现在被限令为官府专窑。陶匠以新的身份为王朝服务,一个外来韩姓家族,原来还是农民,现在却世代从事陶业。他们的后代中,居然出了一位叫韩贞的乡村哲学家和教育家。兴化美称他为“东海贤人”。
新移民们开始“修造”土地。他们首先在属于得胜湖区的低洼地,垒土为垛,建立家园,种植菜蔬瓜果。洪武二十四年出生、到景泰年间在朝中为官的高榖返乡时,时间不过五十年,他已经可以为这里的“两厢瓜果”写上一首范成大式的江南田园诗了。不仅菜蔬瓜果,垛上还大量种植大蓝、小蓝,制作蓝靛和青靛,人们用它们来染成蓝布青布和黑布,这样的衣着很容易又回到早先吴地的色彩。
沿着兴化东西几条河流,一批大型村庄聚落和市集出现。由市集而发展起来的大市镇,最早有四个:安丰、芙蓉、陵亭和长安。它们都在重要的水岸,承担着交通盐粮的任务,在这些市镇周边,乡村社会和经济也围绕着它们展开。市镇里有良好的建筑,青砖黛瓦,临水而起,人家枕河,街桥连通。市面一天天繁荣,店铺里出售农民需要的本地工具,商行经营米麦,以及从下江运来的货物。茶馆早晨散发着氤氲之气,而悬挂在桥堍边的酒旗,飘着米醪的浓香。人们似乎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生活之中。
当然,这些变化还属于表象,真正带来兴化社会变化与更张的是新家族的兴起。集体移民的意思主要指家族的群体迁徙。不少江南大户的到来,不单单是地主,而是宗族地主为首的大家族,在其率领下,合族移居。
到达兴化的大族大姓有多少,惜无具体数目。从后来分布在车路河和海沟河一南一北双轴线上的村镇大姓看,这个数目不下数十,其中不乏吴中顾、陆、朱、张四大姓氏。另有孙氏、吴氏、李氏、吴氏、解氏、魏氏、高氏、宗氏、徐氏、杨氏、袁氏等,也都是江南大姓。
他们合族而居,大多数形成一姓一村的同姓共同体,也形成了由一个或几个家族关系所结构的乡土小社会。与宋元以前兴化相对松散的乡土社会不同,新的移民家族不仅有着固有的家族伦理秩序,同时还有着文化身份的一致性,有着共同的社会认同,尤其是那个绵延不绝的“苏州梦”,更让家族之间彼此有着生存的关照和维系。因此,在兴化乡村,家族社会的聚合,不单单是以村庄为自然单位,同时还以一种“庄园”式的经济体出现,比如海沟河一带的李氏、宗氏庄园,白涂河北岸的袁氏东古庄园。这可以说是兴化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
明代以后,江南移民家族在兴化的存延,不仅仅表现为乡镇社会共同体的搭建,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形成和促进了兴化乡土社会的耕读传统。如果说宋代“兴学校”的影响,曾经为兴化乡土社会开辟文化基础,那么由于移民家族的到来,他们把江南悠久的“耕读传家”的价值观念深植到兴化的土壤当中,才使兴化真正达成了“觊兴其化”的理想。
这样的例子很多,戴窑东古村袁氏家族是其中典型。袁氏宗族从苏州渡江北上,迁居兴化,在草堰、戴窑一带建村定居。不久,他们买下了前朝陈氏私人园林,扩展为方圆达五里的家族经济核心庄园。就是在这里,袁氏一族通过耕读,很快成为兴化著名的士绅家族。从明王朝嘉靖到万历袁氏父子三人科第成名,不仅极大提高了袁氏家族的地方声望,也为乡土社会树立了楷范。袁氏后来自起堂号为“树德堂”,当然不是自夸。
七
另一位明代兴化知县欧阳东凤,他在万历年间主修《兴化县新志》时说,“兴化僻处东海,斥卤之地,赋重民罢,物力少诎,而人文蔚起,学问好修不减邹鲁。若乃省阁名公、朝廷元辅、谏垣台宪、秘书藩臬、心膂股肱之佐先后踵出乎其乡,诚缙绅之渊薮、人才之都会也。”欧阳东凤没有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清康熙年间,知县张可立在他的《重修兴化县志》里接着解释道:“兴化东濒海,北距淮,湖波浩荡,城郭居其中,一泽国也……其水势回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甲于江淮。贤相名铨、乌台梧掖之贤者后先接踵。”
张可立把兴化人文兴盛的原因归于水的滋润浸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突出了“水”对人的塑型力量。兴化人文因水而兴,这并非简单的环境决定论,而是一种“因水生文”的意象化说法,它与前述“水德”,相为表里。
如果说,范仲淹借助“水德”所作的文化价值导引,主要从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建构兴化的民间文化精神 ,而这里“因水生文”的意思,则集中反映为兴化精英文化(士大夫文化和文学与艺术文化)的生长。
15 至16 世纪的明王朝,仿佛集中了兴化的文章风流。短短百年间,接连产生了高榖、李春芳、吴甡三位重量级文人。他们都是从兴化城乡普通士子,经过层层考选,进入仕途,成为国家重要的文臣。李春芳甚至以文章第一,获得科考的最高头衔“状元”。作为兴化最优秀的士大夫文人代表,他们三人都有着良好的政治名声和清正的文化品格,这在明王朝的政治环境中,更加突出显示了兴化文化中那种“沧浪”与“濯缨”的传统。他们不仅是一般的士大夫,而且还是田园诗人、准小说家、书法家,文学艺术在他们身上不是装饰,而是一种灵秀的才能。
正如前面两位外来者所见所闻,兴化的这些“贤者”,接踵而至,不仅在明朝中期形成了兴化的士大夫文人群体,而且几乎在每个历史时段,都活跃着这个群体的后来者身影。即现代来临之前, 任大椿和刘熙载尚以清华之臣身份,或修国典,或入史馆,成为政教传统和经典学术中的杰出人物。
然而,所谓社会文化精英不仅在于此等人物一时出类拔萃,而且在于“缙绅之渊薮”中形成的一批士绅阶级,他们作为兴化的文化中坚,才是推进地方文治社会的键钮。因此,尽管兴化为水乡泽国,为“斥卤之地”,资源相对贫瘠,物力或有不足,水涝频仍,生存多艰,然而有一个持续稳固、根基性的士绅阶级存在,仍然是可以强健和可以保持其社会发展的。“人文蔚起”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丰硕表现,也是兴化之能够在历史长河中保持其兴盛丰华的原因。
八
文学与艺术是兴化文化河流上盛开的奇葩。这里略以小说绘画为例。
《水浒传》的出现,既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传奇,更是兴化的传奇。13世纪,兴化东北水荡中间的一座村庄施家桥,诞生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水浒传》对于兴化的意义,或许是第一次显示了“水”的文学草根性质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施耐庵的创造并不仅仅在他对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在于从“替天行道”中表现了他作为兴化文人的那种为生民立命的道德情怀。“水德”之思,再次经过文学化为“忠义”主题。在这个意义说,施耐庵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
由《水浒传》而《封神榜》而《明珠缘》,有明一代,兴化贡献了三部长篇小说。三部小说分别代表人、神、情三种观点。三位作者身份不同,一个据说为元朝末年进士,后来却加入张士诚的起义军;一个参加过九次乡试,九次落第,不得已做了道士,并成为道教东派一派之主;一个为明王朝最后的文臣,不久成为躲避满清政权的前朝遗民,在家乡著书立说。然后,作为“文学之士”,施 耐 庵与陆西星和李清,其写作几乎表现出一致的“神道设教”思路。施耐庵的天罡地煞、陆西星的阐教、截教不用说,连历史学者李清也把邪恶而人性的现实男女归之于天道孽缘。很难完全说清楚这样相同的思路出自哪里,但观之小说里的九天玄女、女娲娘娘及九尾狐仙、碧霞元君这些形象,不能不感到楚水中悄悄流淌着女巫的精灵。
18世纪,兴化画坛上同时出现了两位异人。一位是李鱓,一位是郑燮(郑板桥)。他们都走过仕进之路,都曾做过一、二任县令。但事功之路对他们似乎不合适,他们也都因正直敢当被罢免官职,重回年轻时的艺术道路。
他们在扬州卖画为生,却为兴化赢得当世艺术声誉。当时扬州有来自江浙等地众多画家,李鱓与郑板桥是其中的领军人物。李鱓创造了他的“破笔泼墨”,郑板桥则以“诗书画三绝”独步画坛,为清代中期的“文人画”注入了一股生气与活力。
李鱓与郑板桥的作品中显然包含着清晰的兴化元素。尤其郑板桥,他的书画笔法线条与构图表现出来的“杂垛戏水”,更是直接将兴化水土之风致移植到了艺术形式之中。在中国书画史上,这种得之于水土形态的启发与观想,以及将其提炼为线条与水墨语言的独创,实在难得一见。
这些艺术上的标新立异,并不在于笔墨,而在于精神上与那个时代拉开距离,甚至是为了反叛那个时代。对于李鱓与郑板桥来说,传统文人中有一种他们为之效法的精神,那就是狂狷之气。这一点,他们两人通过自己的书画作品,表现得淋漓尽致。李鱓的破笔泼墨书写,展现了人生的自由与狂放,郑板桥简洁的兰竹中,最大程度凸显出他的傲岸与孤独。这样的狂狷精神与人格,与其像郑板桥所言是出于明代画家徐渭的影响,不如说是兴化文化精神中宝贵遗产。板桥曾作道情十首,“道”个人之心志情怀,其中有“老渔翁”之一蓑笠一钓竿的遗世水边形象,正是屈原笔下不滞于物、清浊自得的渔父,亦如庄子笔下的楚狂接舆。
九
从时代节点看,兴化文化成于宋、兴于明,但文化在生长年轮上有着历史连续性,兴化文化其漫长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一、萌生期。这一时期时间最长,文化生长的速度最慢。大约从距现在6000 至7000 年,到称为淮夷的上古阶段。在萌生期,兴化文化的性状,主要通过地下遗存的发现加以辨识。影山头遗址、蒋家庄遗址和南荡遗址,现在所发现的地下物质存在,提供了关于兴化文化的想象。
二、显形期。时间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到两汉隋唐,这一时期,借助地缘和疆域的划分,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折射兴化文化形象。其显征有三:楚国拓地而兴化成为“昭阳采邑”,汉初吴王在淮南“煮海为盐”而兴化成为盐区,隋、唐在射阳湖地屯田而兴化始以向农业社会转化。但这一时期兴化乡土社会尚未完备,文化的自然性大于文化的社会性,形态单调,自身特征不明。
三、形成期。北宋王朝是兴化文化的形成期。文化形成之义是指这一时期兴化文化有了它的内核与结构,并且有了精神特点和内涵。由于历史的巧妙安排,范仲淹将儒学之德性与兴化水土之实际结合,而通过事功转化为一种文化精神样式,同时开源导流,以屈原的诗性赋予兴化之水,而构就了兴化文化“水德”内涵。一种士大夫文化观念进入到社会肌理之中,形成了以“崇文尊学”为中心风尚的兴化本土文化。
四、丰 盛期。进入明朝时期,由于兴化乡土社会的重构,给文化注入了新的成分,原有文化结构得以更张,由此兴化文化进入了它的丰盛期。这一时期,兴化文化从精英文化到草根文化,从宗教文化到世俗文化,从艺术文化到日常文化,都得以充分展开。其总体面貌是,士绅阶级兴起,一批贤良之才涌现,文学艺术成就斐然。乡土社会在家族伦理之下,建立起稳固的耕读传统,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稳定,而促成了文化的增进。由此,兴化文化在明、清两代,呈现了长达三百多年的繁富局面。这中间虽有改朝换代,但文化根深叶茂,一直延至清代中期,犹能保持文化的活力。
五、转型期。晚清以后至民国初年,社会进入现代,这一时期的兴化文化随之转型。体现在教育、医学、科技诸方面,兴化文化多受西方新学影响。社会革命,王朝结束,在“咸与维新”的时代潮流中,兴化文化传统的维系力,势将由新时代价值观念所取代。
十
循此历史分期,兴化文化之树年轮可见。但树干之上,兴化文化事象枝叶繁茂。因此,按类型本书所叙述兴化文化分为五章,简说如下:
第一章,兴化文化发生的自然与经济基础。这一章主要讲述兴化自然环境的形成及其变化,以及按自然需要,兴化的经济的生长与发展。水与土,盐与粮,一为自然之情状,一为经济之展开,四者相辅相成,为社会活动和文化的形成与兴起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近代以前兴化的社会生活形态。这一章裁取明清两代的社会图景,着重讲述始于元末明初移民后兴化社会的重组,以及在重组的历史过程中突出的文化认同现象。明代后得以重建的兴化社会,以其家族性的优势,推进了乡土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中乡镇的建立与稳定繁荣,则进一步促成了兴化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功能建构,从而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本地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点。
第三章,兴化的教育、学术与科技文化。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教育与科举,一是思想学术。从北宋初年设立学宫开始,按时间顺序,详细介绍兴化的教育与科举文化。其重点为明清两代“学校”在兴化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而科举制度之下所形成的士阶级群体,则是兴化教育显著的成果。思想学术亦因士阶级文人而产生,但其独立于教育之外的价值在于,它更深刻地体现了兴化精神文化的重要建树。
第四章,兴化古典文学艺术的重要成就。这一章集中分析兴化在文学艺术上的创造性表现及其历史源流。在古典文学艺术领域,明清两代兴化出现了以施耐庵、郑板桥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和优秀文学艺术家,他们构成了兴化文化中一道奇丽的文化风景线,他们的作品是兴化的文化瑰宝。
第五章,兴化的民间崇拜与风俗礼仪。这一章详细描述兴化古代民间崇拜与风俗礼仪形式。从贯穿千年历史的精神崇拜,到乡镇自发的各种大型民艺活动,从不同社会组织举行的会期,到一年四季的节令仪式,以及见于日常生活的种种习俗,进而在社会生活深处,梳理出民间兴化的肌理。
所有地方文化都具有它的独特性,兴化也不例外。但独特性并不表示独立,文化是在自然与社会、人类活动诸种关系中产生的,由这些关系决定文化的品质和精神特点,也由这些关系将文化的价值推向普遍性。兴化文化的高端与突出部分,其价值的普遍性建立,是基于“水文”与“人文”融合,借助中国诗教传统所产生的社会美学精神。这种社会美学精神 ,在兴化如此有限区域范围内,不但提升了兴化人的生存高度,而且放大了中国人对于诗意栖居的理想和经验。
通过小传统传承大传统,这就是梳理兴化文化经脉在今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