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中的伪诗与伪好诗
题目中的“伪好诗”是我生造的,前两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名为“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的特展。“伪好物”,就是说画是假的,但是伪造得很好。我想借这个意思讲一些伪诗中的好诗。在此之前,先和大家讲《全唐诗》是怎么成书的,为什么《全唐诗》里有大量的伪诗。
“《全唐诗》中的伪诗与伪好诗”,这个题目涉及学术研究和文学品鉴根本的不同。研究学问要求实辨伪,而文学品鉴讲究艺术精湛。这两者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各行其是,各有道理。如果一位学术名家讲解唐诗,所欣赏的恰是一首伪诗,不免留下笑柄。反过来看,宋人说到好诗,一下子想不起姓名,于是就称是唐诗,任何人都不怀疑。偏偏现代人发明了古籍全文检索,又偏偏遇到像我这样爱认死理的所谓考据学者,逐一查來,居然一半是宋诗。《全唐诗》编成那会儿,没有全文检索,编纂者又迫于皇命,学识也有些局限,采取凡前人有一书说是唐诗者,一律视作唐诗收入,问题自然不少,当然也给后人留下发现问题的机会。研究学问的基础是必须要求实辨伪,因为只有求实辨伪我们才能知道某一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无论研究李白或者杜甫,他们的传世作品中都有疑伪的,《全唐诗》里也包括了大量的伪诗,因此文学品鉴是普及性的工作,作品辨伪是专业性的工作,这两者都是有价值的。现代《全唐诗》学术研究的工作其实是把九百卷中的四万九千四百多首诗,每一首都解剖出来,仔细地分析,做文本的溯源和史实的探究,追求文献之真相,这样的一个工作虽然艰难,但是它可能也会有特殊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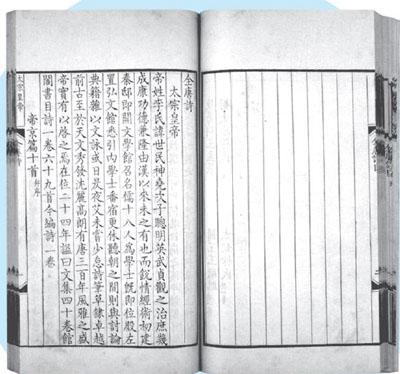
《全唐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扬州诗局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音统籤》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胡氏家族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季振宜画像
一、《全唐诗》是如何编成的
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皇帝第五次南巡,对接待他的江宁织造曹寅提出,希望能够以清宫收藏的两种与全唐诗有关的著作为参考,在扬州编修“全唐诗”。于是曹寅就延请十位在籍翰林—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纮、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在扬州开馆,进行这项工作。所谓在籍翰林就是其在翰林院的工作已经结束,回到南方的故里,养老或者赋闲。皇帝命令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去扬州编书。第二年十月,《全唐诗》编修完成,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编成的《全唐诗》全书九百卷,目录十二卷,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以及一千五百五十五句残句,涉及作者两千五百七十六人。
之所以这么快完成,是因为这本《全唐诗》是在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籤》和清初季振宜《唐诗》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胡震亨是浙江海盐人,《唐音统籤》是他个人一生的积累,共一千零三十三卷,按天干地支的方式来编制,当时因为个人财力有限,只刻了其中的“癸籤”(三十三卷)和“戊籤”。但是《唐音统籤》的稿本一直存在大内,即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直到将近二十年前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于是今天我们就能够知道胡震亨在唐诗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季振宜是江苏泰兴的盐商后代,年轻时爱读书,利用家里的财富收集了大量善本书籍,编成七百一十七卷《唐诗》。这本书现存三个文本,一个文本是保存在台湾的手稿粘贴本,即在初期工作中利用原始材料拼贴出来的一个长编,通过上面的涂画,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季振宜是根据什么材料来剪贴,贴了以后怎么删、怎么改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出版了影印版。另两个文本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呈进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个文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
将《唐音统籤》的稿本与《唐诗》的手稿粘贴本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是在这两部书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毕竟翰林院不是专门研究唐诗的机构,在康熙皇帝的命令下,《全唐诗》成书十分仓促,在文本的鉴别、史料的排编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但是由于是皇帝领衔,所以这本《全唐诗》一直沿用到今天。
《全唐诗》的体例,全书首列帝王后妃作品,其次为乐章、乐府,接着是历朝作者,略按时代先后编排,时代不明及事迹不详者殿后,再次为联句、逸句及名媛、僧人、道士、神仙、鬼怪、梦、谐谑、判、歌、谶记、谣、语、谚、谜、酒令、占辞、蒙求,而以补遗、词缀于末。它在当时条件下,网罗了唐五代的全部诗歌作品,不但包含了已结集的著名诗人的诗集,而且广泛收罗了一般作家及各类人物的作品,全面反映了唐诗繁荣的景象。可以说这套《全唐诗》的编撰,将明末到清初近两百年中,许多学者积累下来的成果,做了一个集大成的简单处理。虽然问题很多,但使用比较方便。
《全唐诗》编校者在《凡例》中,曾说明订正过一些所收材料的错误。《四库全书总目》据以概述云:“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如《册府元龟》所载唐高祖《赐秦王诗》,则考订其伪托。又旧以六朝人误作唐人者,如陈昭仪、沈氏、卫敬瑜妻之类;以六朝人讹其姓名误为唐人者,如杨慎即陈阳慎,沈烟即陈沈炯之类;以六朝诗误入唐诗者,如吴均《妾安所居》、刘孝胜《武陵深行》误作曹邺,薛道衡《昔昔盐》误作刘长卿之类。唐诗之误以诗题为姓名者,如上官仪《高密公主挽词》作高密诗,王维《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作慕容承诗之类,亦并厘正”,“至于字句之异同,篇章之互见,根据诸本,一一校注,尤为周密”。
也就是说这本《全唐诗》是以《唐音统籤》为稿本,增加了清宫所藏的一部分诗集。据今人根据已影印出版的胡震亨《唐音统籤》和季振宜《唐诗》所做的研究,以上所述颇多掩饰与夸耀。所谓“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即指季振宜《唐诗》。以《全唐诗》与胡、季二书比读,可以发现当时几乎全靠二书拼接成编。全书主体部分,大致以季书为基础,仅抽换了少数集子的底本,因季书不录残句,援据胡书补遗,小传则删繁就简,编次做了适当调整。因此,实际情况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叙述正相反。此外,《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孙儿乾隆皇帝评价爷爷康熙皇帝的工作,自然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只能说好话。譬如闺媛、僧道以下的部分,几乎全取《唐音统籤》,仅删去馆臣认为不是诗歌的章咒偈颂二十四卷。《全唐诗》里边没有收录王梵志的诗,正因为他的诗在《唐音统籤》里被编入了章咒偈颂部分。唐诗字句的异同和篇章归属的互见,胡、季二书多有说明文献依据的文字,《全唐诗》编校者将二书校记中一律改为“一作某”,并没有根据诸本去做周密的考订。《全唐诗》卷八八二至卷八八八补遗七卷,是编校者据新发现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唐百家诗选》《古今岁时杂咏》等书新补的诗篇。所以,这本《全唐诗》的编纂大体是草率的,由于编纂时间仓促,所据文献有限,以及大型官修书难免谬误的通病,此书漏收唐人作品,误收非唐五代人的诗篇,以及作者小传舛误,收诗重复互出,一首诗,既见于甲的名下,又见于乙的名下,还见于丙的名下,到底是谁作的,《全唐诗》不做鉴别。而作者张冠李戴,诗题、录诗和校注的错误,都所在多有。尽管如此,它毕竟实现了总汇唐诗于一书的工作,不失为一部资料丰富、比较完整的唐诗总集,使此后的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大获沾益。

《全唐诗》 中华书局196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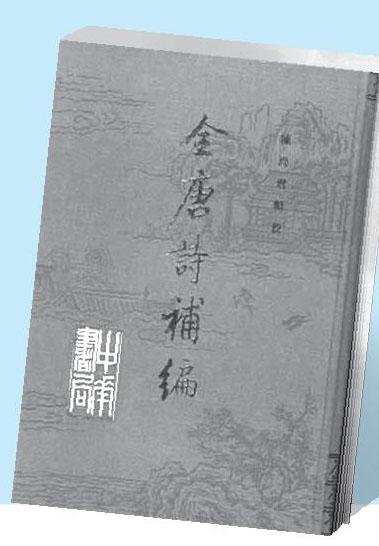
《全唐诗补编》陈尚君编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全唐诗》最早的刊本,是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扬州诗局本,分为十二函一百二十册,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归并成四函三十二册。中华书局于一九六○年出版点校本,以扬州诗局本为底本,除断句外,还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一九九九年又出横排简体字本,附收《全唐诗逸》和《全唐诗补编》。这本《全唐诗逸》,是最早为《全唐诗》所做的辑补,编者是日本人市河世宁(旧署上毛河世宁),全书共三卷,据日本所存《文镜秘府论》《千载佳句》《游仙窟》等书,补录一百二十八人诗六十六首又二百七十九句,中国的“知不足斋丛书”本、中华书局本《全唐诗》都附收了此书。中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希望重编《全唐诗》,六十年代中华书局点校本的点校者署名“王全”,其实是两位作者整理的。一位是王国维的第二个儿子王仲闻,一位是中华书局前总编傅璇琮。
此外,学者王重民利用敦煌遗书编成《补全唐诗》(收诗104首)和《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收诗62首);孙望利用石刻、《永乐大典》和新得善本编成《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诗八百三十首又八十六句;童养年利用四部群书和石刻方志,作《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得诗逾千首。三书合编为《全唐诗外编》,一九八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个人是在一九八一年研究生将毕业之际开始做《全唐诗》的补辑工作的,从存世典籍中得诗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又一千一百九十九句,作《全唐诗续拾》六十卷;并删订《全唐诗外编》,增加王重民的《补全唐诗拾遗》,重编为《全唐诗补编》,共存逸诗六千三百多首,一九九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中华书局2000年)中,尚有唐人逸诗数百首。
二、《全唐诗》中为何有大量伪诗?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什么是伪诗。这个概念对于个人和一代文献,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不是他本人所写的诗,就是伪诗。这些伪诗的出现,有的是因为传说,譬如李白的这首—出自《唐诗纪事》一八卷,引自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

《唐诗纪事》(全二册)〔宋〕计有功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北宋)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于此,窃从学士大夫求问逸事。闻唐李太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入令卧内。尝驱牛经堂下,令妻怒,将加诘责。……顷之,从令观涨,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复苦吟,太白辄应声继之。令诗云:“二八谁家女,漂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傍珠。”太白继云:“绿鬓随波散,红颜逐浪无。因何逢伍相,应是想秋胡。”令滋不悦。太白恐,弃去,隠居戴天大匡山。
杨天惠北宋末在彰明任县令时,在地方上采集的传说,说当时李白在县里做小吏,县令来考李白是不是会写诗,正好看到江水涨潮,有女子溺死江上,县令苦吟了一首诗,李白在旁边应声继之,写下了上面这首诗。问题在于,这样的诗水平真的是很卑下,而且选题糟糕至极。但这就是一个传说,真假无从分辨。
除了这类传说外,还有一些诗是可以考证清楚的。比方说李白名下有一首《傀儡诗》—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这首诗讲一具被雕刻成老人的牵线木偶,“鸡皮鹤发”,和真人一模一样。被牵动时,生龙活虎,但傀儡戏演完以后就被扔在一旁,像人生一梦。这首诗据说唐玄宗退居西内以后曾经吟诵过,并且记载创作者是李白。然而在《全唐诗》中这首诗同时出现在三个人名下—唐玄宗、李白以及梁锽。梁锽名下的这首诗的题目叫“咏木老人”。现在普遍认为,这首诗的作者只可能是梁锽,他是与李白、高适同时代的一位年轻诗人。因此,这首诗肯定是唐诗,但对李白来讲,它就是伪诗。
还有些情况,虽然存在很多怀疑,但没办法做很清楚的判断。比方说这一首李白的《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李白和杜甫曾经有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经常在一起,关系很密切,但分开以后,杜甫不断地怀念李白,李白却好像根本没这回事情一样,这是由两位诗人性格差异很大而造成的。李白是一个主观的诗人,眼中只有自己;而杜甫是一个入世的诗人,很注意其他人的情感的变化。就这首诗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饭颗山”。我们在中国找不到这么一座山,中国之大,这座山是不存在的。再一个问题是,在这首诗中,李白对杜甫到底怀有怎样的感情。如果这首诗是李白作的,显然李白在讥讽杜甫才情不够(郭沫若认为这样的口气表达出李白对杜甫很亲切的关心,这也是一种说法)。但由于诗中的“饭颗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题,所以尚没有人能够做出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解释。进一步说,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李白所作的,也就只能存疑了。
当然,在李白的名下也有许多纯属附会的诗歌。因此就李白个人来讲,名下存在许多伪诗,有疑问的诗大概超过一百首,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有证据或者是没有证据的怀疑的议论。对于这些议论,既没有办法推倒,也没有办法求得更可靠的证据,因此只能存疑。
而对于一代文献的研究,必须确定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即所谓的唐代诗歌,规定了《全唐诗》收诗之起讫时间,上限是唐开国即武德元年(618)五月,下限因十国之亡有先后,因地方之不同,有九六○年至九七九年之不同。如果所收诗歌的创作年代是在这段时间之前或之后的,就可以被认为是伪诗。第二个原则是,它必须是诗而不是文章。第三个原则是必须用汉语创作,而非日文或中亚文字。第四个原则,这些诗歌可以是中国人到日本、新罗等地写的诗,也可以是日本人、新罗人入唐以后,用汉语写的诗;但是如果外国人在国外所写的汉诗,就不能收入《全唐诗》。以上四条原则,确定了《全唐诗》应当收录的范围。
一九八三年,我曾经撰写《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1985年第24辑),其中罗列了《全唐诗》误收的十种情况。第一种,唐以前的作者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进来的。比如说《全唐诗》收入的一位诗人叫徐之才,不算很有名,但他是北齐时人,在《北齐书》中有传,最近几十年他的墓志铭也出土了。那为什么《全唐诗》会把徐之才收进去呢?因为在明代流传一本书,叫《玉台后集》,其收诗的范围实际上是从梁末到中唐前期,包括北齐、北周、隋等。在《全唐诗》编纂等过程中,人们看到了《玉台后集》中收了徐之才的诗,却不知道他的事迹,于是就一并作为唐诗收进来了。第二种情况,是唐以前作者的诗误归唐人名下而收入者。比如说《全唐诗》中李商隐名下有两句诗:“头上金雀钗,腰佩翠琅玕。”这两句诗出自曹植的《美女篇》。再比如,陆龟蒙名下有六首《子夜歌》,其实都是东晋时的民间作品。第三种情况,是隋唐之际作者在隋所作诗。以上三种情况说明了《全唐诗》误收唐以前诗歌的原因。
第四种情况,是宋及宋以后人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者。比如北宋诗人胡宿,《宋史》有传,并有文集《文恭集》存世。《全唐诗》之所以误收胡宿的诗,是因为金元之间的诗人元好问,在他的名下有一本唐诗选《唐诗鼓吹》,其中收入了二十首左右胡宿的诗,后来编纂《全唐诗》时就这样错误地延续了下来。第五种情况,宋人姓名与唐人相同而误收其诗为唐人诗。古今姓名相同是很常见的事情。比方说《全唐诗》里收入的郭震,唐代的郭震是武后到玄宗初年的一代名将,宋代初年成都的一个处士也叫郭震。两个人的字不同,唐人字元振,宋人字希声。再比如说周渭,唐中期有一个周渭,宋初也有一个周渭,《全唐诗》中周渭名下的诗,实际就包括了这两个人的诗歌。第六种情况,是宋初人误作唐末五代人收入者。也就是说宋代初年有些人事迹不是很显著,一直被认为是唐人,比方说李九龄、滕白、廖融、刘兼等,都是宋初时人。第七种情况,是由五代入宋者入宋后所作诗。譬如乾康,是湖南的一个和尚,从唐末一直活到了宋初。还有《全唐诗》中所收的何象,当作何蒙。《全唐诗》收入的何象诗,是投献给宋太宗的。何蒙另有一诗创作于南唐,《全唐诗》没有收入。因此,对于跨代的诗人来说,很难编得很完整,鉴别很困难,但这是一项有必要去做的工作。第八种情况,是宋及宋以后人诗误作唐五代人诗收入者,属于这种情况的诗人,过去我们知道有戴叔伦、殷尧藩、唐彦谦,现在又发现了张继、牟融、陈元光、田颖、吕从庆、莫宣卿等人。

《濠上漫與》陈尚君著中华书局2019年版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扬州诗局刻楝亭藏书本
第九种、第十种情况分别是,仙鬼之诗必出于宋及宋以后人之手者,以及宋及宋以后人托名唐五代人或神仙所作诗。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首是五代后蜀国主孟昶的《洞仙歌》。这首诗在北宋时很有名,苏轼说,他早年在蜀中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尼姑,自陈早年是后蜀宫中的宫女,记得当年孟昶和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游玩,写下《洞仙歌》,开头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于是,苏轼根据这两句,敷衍出一篇词《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问题在于,之后的人拿出这首所谓由孟昶所作的词,说是一首《木兰花》,即一首压仄韵的七律诗—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显然,这就是把苏轼的《洞仙歌》再改写为仄体的七律。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人在摩诃池上面施工,挖出了一个石刻,石刻里边刻了一首词,前面两句正是“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后面完全不同,因此后来认为被发掘出来的这首词才是孟昶的原作。但马上又有人反对,认为发掘出来的这首词风格太差,不符合孟昶的水平。因此至今尚无定论。
另外一个例子,现在成为学术史上重大的公案,即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首诗同样被收入《全唐诗》中。我在一九九三年提出《二十四诗品》为伪书的说法,认为现存的《二十四诗品》是明末人根据《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品》一段,托名司空图的伪作。试举一例—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纵。
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元宗。
这首诗中,“月出东斗”一句,有一种解释认为其中的“东斗”是道教名词,但释读下来,可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这句诗化用了苏轼《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将两句压缩成一句。因此,《二十四诗品》显然是在苏轼以后创作的。
这里的第三个例子是吕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吕洞宾。浦江清先生的《八仙考》认为,吕洞宾的传说是北宋中期庆历年间在岳阳一带兴起的。我后来做了一些考证,比浦江清先生的说法大概提前了五十年,在宋太宗初期吕洞宾的传说已经在陕北出现。过去我一直以为,吕洞宾传说为宋人编造,宋以前全无痕迹可寻,近日因一则记载而稍有改变。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吉州”载:“雪浪阁,在县北崇元观。吕洞宾有诗云:‘褰裳懒步寻真宿,清景一宵吟不足。月在碧潭风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参见拙文《吕洞宾的最早记录》,收入《濠上漫与》,中华书局2019年)这首诗,很可能真的是吕洞宾自己所作,而且创作时间可能是在五代的中后期。关于吕洞宾真实的家世与经历,已经不可考,只能确定他应该是从南唐入宋的一个道士,可能有一些仙迹,后来宋人凡是碰到不可解释的事情,就认为是吕洞宾来了。这样一来,围绕吕洞宾的传说越来越多。现存吕岩名下的诗歌,少说也有三千至五千首,真正的作者可能是宋人、金人、元人、明人甚至是清人。
因此,伪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造成《全唐诗》误收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传误,即诗歌在流传的过程之中,文本之残缺、讹误,以及其他非人力的原因所造成的过失。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依托,即托名于某个名家撰写的诗篇,一个是伪造,因为唐诗卖得好,而书肆里没有合适的、好的文本,就从各种途径找来诗歌,以唐诗为名刊印。据我所知道的,现存《全唐诗》中非唐人所作的,超过一千首,唐诗之间,互见、传误的作品大概在六千到七千首,也就是说,《全唐诗》四万九千多首诗中,有七八千首诗是有疑问的。但其实,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这些有疑问的诗是读不出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一般读者没有能力占有全部文献,很难做出判断。我个人近三四十年一直在做一件自己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对《全唐诗》的考订和编撰,已经接近完成,希望两三年之后能与读者见面。
三、唐诗中的伪好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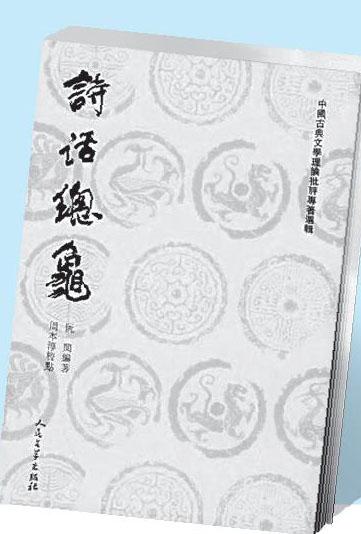
《詩话总龟》〔宋〕阮 阅编著周本淳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特别要说明的是,唐诗里确实有好作品,但其实唐诗未必都好,伪诗也未必都烂。我们一方面需要提倡科学的态度,另外一方面也要知道,好坏和真伪不是同等的概念。如果我们稍稍转变一下立场,不难发现伪诗中尽多好诗,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遇到一些与作者全无关联的意外状况而已。换句话说,一首诗要从宋代甚至明代,顺利地混到唐代,没有它自身的优势,能做到吗?当然,唐人有唐人的优势,唐代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一个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思考的时代,这一点和之后的时代有根本的不同。因此,我们有一个观念一定要改变,那就是诗不一定只有唐人才写得好,其实宋、元、明、清各代的诗都是越写越好的。
伪好诗里边最有名的是杜牧的《清明》,但是《全唐诗》中并没有这首诗,杜牧的文集里面也没有。这首诗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宋末的时候,被编入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成为宋元明清以后各代小学读本里边的诗歌。对于这首诗的流传历史,我来做个梳理。这首诗收录于南宋中期的两种类书,在谢维新的《合璧事类别集》里边是作古选诗,在《锦绣万花谷后集》里是作唐诗,但是都没有说是杜牧所作。最早将其作为杜牧的诗,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日本所藏的一个宋刻的善本。从宋末开始,《千家诗》以及其他一些诗集都收了这首诗。宋元之间的瓷州窑的题诗有这么两句:“禁烟山色雨昏昏,立马垂鞭看右贲。借问酒家何处好,牧童遥指杏花村。”我无法解释这首诗是比这首《清明》早还是晚。但这前面两句和后面两句是不搭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南宋何应龙的诗歌之中可以看到也是有关系的:“八十昂藏一老翁,得钱长是醉春风。杏花村酒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这首诗显然是在《清明》出现以后,根据后者改写的。
在此,且说说《全唐诗》中的伪好诗。
第一首,骊山游人《题故翠微宫》—
翠微寺本翠微宫,楼阁亭台几十重。
天子不来僧又去,樵夫时倒一株松。
诗见《全唐诗》卷七八四。诗的来源应该是《诗话总龟》卷二四引《谈苑》:“翠微寺在骊山绝顶,旧离宫也。唐太宗避暑于此,后寺亦废。有游人题云(诗略)。”《谈苑》即《杨文公谈苑》,是黄鉴根据著名文人杨亿晚年所谈写成的一部笔记,原书不存,宋人各书引录很多,今人李裕民有辑本。杨亿晚年约当宋真宗末期,时去五代入宋仅五六十年,后人即此怀疑这首歌咏唐代史事的诗出自唐人,也可以理解。
翠微宫,经考证可能在骊山华清宫附近,到唐末的变乱衰落以后,变成了翠微寺。《题故翠微宫》一诗诗意直白而简单。这里本来是一处皇家宫苑,规模宏伟,亭台楼阁层层迭迭,何等繁盛。后来,皇家不再来了,就施舍给寺院做功德,这样又维持了很长时间。然而现在,皇帝是早就不来了,寺院也不知何故,无法维持了,和尚也不见了。眼前一片荒凉,但还有一些人气,砍柴的樵夫正在砍伐松树,这松树可是皇家寺院的古松,也许有几百年了。通过这一场景,这首诗所表达的世事沧桑之感,与元稹诗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首诗到底是谁作的?宋元间,这首诗曾被传为唐代著名诗人所作者,如《竹庄诗话》卷一五引《瑶溪集》作武元衡诗,题作“山顶翠微寺”,《类编长安志》卷九作刘禹锡诗,题作“翠微寺有感”,但二家别集皆无此诗,应属误记。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南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二:“元微之有一绝句:‘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洪景卢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煇幼时亦得一诗云:‘翠微寺本翠微宫,楼阁亭台数十重。天子不来僧又死,樵夫时倒一株松。乃张俞所作也,思致不减前作。”洪景卢即洪迈,他在《容斋随笔》中称赏元稹《行宫》诗“语少意足”,回味无穷,周煇认为此诗足与相当,他得知此诗作者是张俞。张俞,又作张愈,字少愚,号白云,成都附近的郫縣人。他在科场屡举不第,宋仁宗时曾上书言边事,授校书郎,随即归隐以卒。因此,这首诗其实是北宋中期创作的。

罗稚川《古木寒鸦图》
第二首,太上隐者《答人》—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全唐诗》卷七八四收此诗,不云作者时代。其来源应该是《诗话总龟》卷一八引《古今诗话》云:“太上隐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从问其姓名,不答,留诗一绝云(诗略)。”我认为更可靠的记载是南宋书坊编《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四《赠梁道人》注引《池阳集》引滕宗谅《寄隐者诗序》:“历山有叟,无姓名,好为歌篇。近有人传《山居书事》诗云云。”滕宗谅即范仲淹《岳阳楼记》开始所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之滕子京,他生活在宋仁宗时,他的《寄隐者诗序》全篇不存,据此节引的片段,知道这位自称太上隐者的隐士,所住地历山在今安徽贵池附近,生活时代与滕相接,可能年长一些,但绝不会是唐人。诗的原题也应是“山居书事”。
但这首诗确实是一首好诗,原因在于他真正写出了隐士的情怀。唐代明瓒和尚《乐道歌》最后一节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涧长流。卧藤萝下,块石枕头。山云当幕,夜月为钩。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须何忧?水月无形,我常只宁。万法皆尔,本自无生。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写出隐者远离世嚣,亲近自然,不委屈于世务,不忧患于生死,完全超脱世事的感受。太上隐者的这首五绝,恰是对《乐道歌》最简明的概括。人生随意,不必有求,更不必关心世事的变化,一切尽可随心所欲。偶来树下,枕石而眠,只是适意,不需要理由,更没有时限。山中连历日都没有,当然更不关心天气冷暖,时光流逝,随顺自然,无忧无虑,这是真隐者的情怀。诗意很简单,但确是无欲无求的真隐者之态度。
第三首,杜常《华清宫》—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
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

《戴叔伦诗集校注》〔唐〕戴叔伦著蒋 寅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全唐诗》卷七三一收此诗,作者事迹无考,小传云“唐末人”,出于附会。南宋周弼编《三体唐诗》,以此首为全书第一篇,即认为是唐人最好的诗。再往前追,则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收入《唐人杂记》,且说明所据为《西清诗话》。再看《西清诗话》卷上,云“世间有才藻擅名而辞间不工者,有不以文艺称而语或惊人者”。下录“近传”之此诗及方泽《武昌阻风》。《西清诗话》作者蔡绦是权臣蔡京的儿子,书则作于南渡初,所谓“近传”,当是南北宋之间事。至胡仔认识稍有偏颇,周弼更推一程,就认定为唐诗。
其实此诗石刻在华清宫,明人还见到,明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二录诗共四首,署“权发遣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公事太常寺杜常”,更有杜诩跋,称是杜常“自河北移使秦凤,元丰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过华清”而作诗。《河上楮谈》录诗前二句作“东别家山十六程,晓来和月到华清”,应该是作者的原诗。杜常,《宋史》卷三三○有传,他字正甫,卫州人。登进士第后,历任使职。元符元年(1098)知青州,次年改知郓州。崇宁二年(1103)自徐州移知镇州。崇宁末,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军,卒年七十九。说这首诗是宋诗,应该没有疑问了。
杜常的家在卫州(今河南新乡)一带,因受命处理秦凤(今陕甘接界处一带)刑狱公事而入关。华清宫在临潼骊山下,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宫苑。大约作者行色匆忙,临晨方到临潼,且天气不好,风雨交加,在诗中写出来,则引起“多少楼台风雨中”的无限感伤。诗写得很流动,写景纪行的画面感很强,感伤借画面传出,不加议论而引人无限联想。诗的后两句写景引起议论,包含无限的感伤。
第四首,方泽《武昌阻风》—
江上春风留客舟,无穷归思满东流。
与君尽日闲临水,贪看飞花忘却愁。
这首诗的流传轨迹,与上引杜常一首一样,也被称为很有唐人风韵。只是方泽不像杜常那样有明人所见石刻与正史传记,可以确定无疑。方泽生平资料比较零散,据《莆阳比事》卷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嘉靖《邵武府志》卷四所载,可以大抵拼出他的生平:字公悦,莆田人;熙宁八年(1075)为大理寺丞,旋除江西路提举常平事;元祐五年(1090)知邵武;元符元年为吏部郎中;寻贬知万州;建中靖国间官鄂州,与黄庭坚多有唱和。这样看,与《西清诗话》所讲的“近传”是契合的。
诗是作者晚年之作,细节较难还原。较大可能是在知万州或官鄂州放归时所写。鄂州临近武昌,作者家在闽中,归乡首先是沿江东下。也许是久未还乡,也许是家有急事,他是赶急着希望尽快还乡。然而因为江上阻风,预定的行期难以成行,只能留下。诗人解释,这是春风多情,故意留客。后两句中的“君”,应指春风,大风不停,自己日日临水以卜行期,好像与风有约一样。虽然归心如箭,归思无端,但春风春花,又给自己以无穷慰藉,在迷人春色中忘却了愁思。诗写得很随意,但又风流蕴藉,给人以进留各有所得的感受,深得诗人温厚之旨趣。
第五首,唐彦谦《采桑女》—
春风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
侵晨探采谁家女?手挽长条泪如雨。
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
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
诗见《全唐诗》卷六七一,稍早则见明刊《鹿门诗集》卷下。社科院文学所本《唐诗选》收有此诗,上海辞书版《唐诗鉴赏辞典》各版均收此诗。艺术上比较直白,就写阶级剥削来说,确是少见的贴切之作。
就直观来说,此诗有一疑问,聂夷中《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是有名的诗篇,此诗末句似有依傍或抄袭之嫌疑。但就唐、聂二人生平来说,基本是同一时代之人,谁抄谁就难说了。
然而存世唐彦谦《鹿门诗集》,前人多有质疑。唐人郑贻、五代薛廷珪、宋初杨亿均曾輯唐集,没有保存下来。明刊《鹿门诗集》三卷,存本甚多,近人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卷五《剡源逸稿》云此集“多误收《剡源》之作,与三十卷诗同者六十二首”。今人郑骞《有关唐彦谦之札记六则》(《东吴文史学报》,1976年第1辑)、曹汛《唐彦谦诗中的所谓孟浩然父子》(《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王兆鹏《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辨伪》(《中华文史论丛》,1993年第12辑)先后揭出唐集中误收的元戴表元诗四十多首。朱绪曾所见《剡源逸稿》,今不存,以至今人所见戴诗未及朱氏之多。今人重新编定全部唐彦谦诗,唯一的办法是为他可靠的诗找到明初以前书证,今知约九十首,剔除误收戴诗四十多首,另不知真伪而只能存疑者尚有五十多首,这首《采桑女》恰在其中。
仔细读诗,可见作者对南方采桑女的生活观察得很仔细。春风初起,蚕宝从卵中孵化而出,细小如蚁,而桑条也才初绽幼叶。今年春寒,桑叶较往年迟开,如果在以往,最早的一批蚕已经长成吐丝了。官府哪管时令早晚,到了时间就逼迫蚕家缴纳新丝,已经到家家户户叩门催促了。蚕女无力反抗官家,只能更加地早起晚睡,即便如此也无可奈何,“手挽长条泪如雨”,进退失据,痛苦而绝望。放在宋元之际的诗坛来说,这首诗也是好诗,是很少见到的真实反映江南蚕桑女生活的作品。
第六首,戴叔伦《题稚川山水》—
松下茅亭五月凉,汀沙云树晚苍苍。
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似故乡。
初版《唐诗鉴赏辞典》收戴叔伦诗五首,仅《除夜宿石头驿》《三闾庙》确为戴作,另三首皆伪。其中—
兰溪棹歌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苏溪亭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一百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都收了戴叔伦的这两首诗。确实都是好诗,写景如画,非常生动。但是仔细地研究发现,这两首诗其实都是明代初年一个不知名的诗人—汪广洋的诗。汪广洋大约是明洪武时做了一个小官,有诗集《凤池吟稿》存世,以上这两首诗都出自汪广洋《凤池吟稿》卷十,而且《兰溪棹歌》实际是三首,通过比较另外两首《兰溪棹歌》,可以相信这三首诗是同一个人的作品。
而这首《题稚川山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稚川”是葛洪,但葛洪生活的时代有山水画吗?如说是写稚川的景色,偏偏稚川是道家传说中的仙都,要写也不该是这样的山村景色。今人熊飞《戴叔伦诗杂考》(《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认为是明初刘崧诗,见刘著《槎翁诗集》卷七。“稚川”为罗稚川,元明间画家,揭徯斯、乃贤、林弼等皆曾题其画。有这样的考证,对其真伪似乎已经可以不必多加讨论。
那么,为什么明初人的诗会进入《全唐诗》,归收到戴叔伦的名下呢?原因出在明中期以后在前七子“诗必盛唐”口号的倡导下,明人写诗普遍学唐,书坊也顺势而动,抢印可靠的唐集,也顺便伪造唐集以射利,《戴叔伦诗集》两卷就此出笼。《全唐诗》会聚真伪诗之大成,收戴诗约三百首,半数为伪。今人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2008年增订)广稽历代典籍,将戴集真伪基本理清了,读者可参看。但其实,明人伪造戴集,还是花了很大气力的,《唐诗鉴赏辞典》中周啸天为这首《题稚川山水》撰文云:“这里的写景,着墨不多,有味外味,颇似元人简笔写意山水,确有‘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意趣。”现在确定这就是一首元人题写元画的诗。
第七首,吕岩《梧桐影》—
落日斜,秋风冷。
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
诗见《全唐诗》卷九○○,作词收录,源自《花草粹编》卷一。其实《梧桐影》的词牌即源于此篇,原作应是诗而非词。较早记录见南宋初曾慥《集仙传》(《山谷内集诗注》卷一六《次韵高子勉十首》之一注引),题作“题汴都峨眉院法堂屋山”。吕岩就是吕洞宾,是宋以后最有名的唐末大神,今知挂在他名下的诗作约有数千首,有宋以后各代伪造者。今人认为几乎无一可靠,大致不错。
大梁就是北宋的东京。此诗包含一动人故事。峨眉道者持律严格,历二十年不下讲席,是一位有道高僧。某日一位高大伟岸的布衣,穿着青裘而来,与道者畅谈良久,约明年此日再相见。到明年此日,道者端坐而逝,伟人来而不见,叹息许久,留下这首诗。伟人没有留下姓名,因此传为吕洞宾现身而作。
这首诗的主题是等待,是忘形友人间契阔生死的等待。黄昏落日,秋风渐寒,相约见面,然而老僧已经远行。生死能够分隔彼此的友谊吗?约定的见面还是不能违背的。僧家喜欢讲因果轮回,道家自能返魂摄魄,都相信灵魂不远,今夜必会归来。诗很质朴,首两句点出时间氛围,第三句很直接,远行的故人,今晚你能回来吗?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教人立尽梧桐影”,你看到我了吗?我就在去年说定的梧桐树下等你。梧桐是一种高大的大叶乔木,月光在梧桐叶间泻下,移动的月光代表时间的推移。我为你彻夜守候,我相信你会来的,我看到了月升月落,我看到了月影在梧桐叶间起舞挪移,我还在等待,相信你的承诺。
宋元人遇到高道异人有不识或无名者,皆喜用吕洞宾现身来解释。这首短诗寥寥二十字,写尽友谊、等待、坚守和希望,能说不是好诗吗?至于是谁作的,关系倒不大了。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七十六期所作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