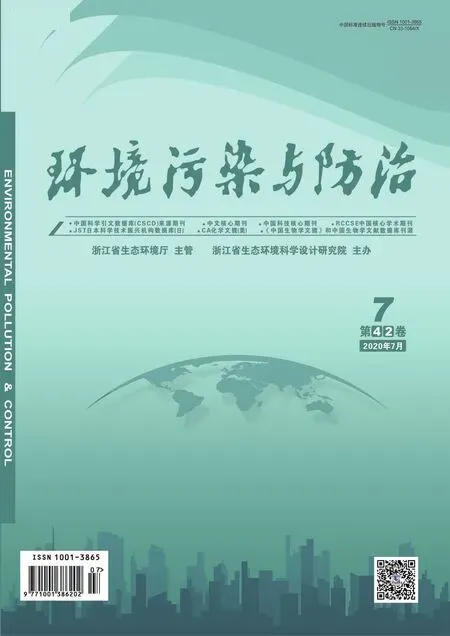药物与个人护理品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分布特征及其生态毒性与降解综述*
张 琪 杨 芳 王 峥 简宏先 王翠苹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育部环境污染过程与基准重点实验室, 天津市环境修复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50)
药物与个人护理品(PPCPs)的广泛使用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了潜在的威胁[1]。绝大多数PPCPs的半衰期较短且在环境介质中的浓度较低,处于ng/L至μg/L水平,但是由于不断输入,PPCPs在环境中呈现“伪持久”的状态[2-3],PPCPs长期暴露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不亚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目前,在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沉积物、污泥等环境介质中都有PPCPs被检出。中国对PPCPs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而其滥用率较高。研究PPCPs在中国的分布特征,可以为中国PPCPs的环境风险评价以及污染环境的治理提供基础数据。
研究表明,PPCPs对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存在着潜在危害[4]。SANDERSON等[5]的实验室研究表明,很多PPCPs对藻类、水蚤、鱼类等水生生物具有急性毒性(半数效应浓度(EC50)小于1 mg/L)。在实际环境中,PPCPs的浓度可能达不到产生急性毒性作用的水平,但其慢性毒性的影响不能排除,并可能会因其持续输入而造成生物体内的累积,从而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6-7]。同时,PPCPs还可能诱导微生物产生耐药性,使环境中抗性基因丰度增加,扰乱生态平衡并威胁人类安全。因此,应关注环境中PPCPs的生态毒性,有针对性地选择毒性大的PPCPs进行优先控制。
目前,环境介质中PPCPs的去除主要有光化学降解、水解、生物降解3种途径,需要根据PPCPs分布特征和生态毒性效应,选择合理的技术去除PPCPs,以降低环境中PPCPs的暴露风险,减少其对人类及生态系统的威胁。
近些年国内对PPCPs分布特征及其生态毒性与降解开展了较多研究,因此本研究综述PPCPs在中国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现状,探讨其潜在的生态毒性效应以及致毒机理等,深入剖析PPCPs在环境中的去除途径及其影响因素,为PPCPs的管理与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1 PPCPs在中国不同环境介质中的分布特征
近年,中国不同地区报道的PPCPs已有上百种,常见的包括8类,分别为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杀菌剂、抗癫痫类药物、抗心血管疾病药物、β受体阻滞剂、抗精神病类药物、人工合成麝香,主要分布于不同环境介质(饮用水、地表水、地下水、沉积物及污泥等)中。应光国[8]还绘制了中国58个流域的抗生素环境浓度分布图。
1.1 饮用水中PPCPs污染特征
PPCPs在饮用水源、供水管网和水龙头中均有检出。据报道,PPCPs在饮用水中的检出率较高,不同种类的化合物检出浓度差异很大[9]。天津市某自来水厂检出三氯卡班最高质量浓度为3.39 ng/L,双氯芬酸最高质量浓度为1.77 ng/L,达舒平最高质量浓度为6.07 ng/L[10]。东江水源检出舒必利最高质量浓度为13.4 ng/L[11]。
饮用水中的PPCPs种类及含量还与水源和季节等有关。PPCPs可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间接影响人体健康,而目前生活饮用水相关标准尚无PPCPs等项目,因此未来应对饮用水中的PPCPs进行相关标准制定,保证饮用水的安全性。
1.2 地表水中PPCPs污染特征
我国地表水(包括河流、湖泊、近海水域)中检出的PPCPs有144种,包含21种个人护理品(PCPs)和123种药物[12]4。珠江水系检出的PPCPs种类达95种,辽河水系检出48种[13]3143,[14-17]。大量PPCPs排放后进入地表水,造成地表水严重污染。黄浦江和苏州河中均检测到环丙沙星和红霉素等药物,两种化合物的最高质量浓度分别达到14.6、10.9 ng/L;巢湖中检测到氧氟沙星的最高质量浓度达182.7 ng/L;而磺胺甲噁唑在黄浦江、苏州河和巢湖均有检出,最高质量浓度为171.6 ng/L[18]2380,[19]。三氯生是地表水中检出率最高的PCPs,在汉江、黄浦江、苏州河、珠江等地均有检出,最高质量浓度达1 023 ng/L[18]2380,[20-22],[23]9。
地表水中的PPCPs来源十分广泛,外用护肤品可通过沐浴、游泳等途径进入地表水;制药、医疗和水产养殖废水中含有的大量PPCPs会通过排放进入地表水;污水处理厂的含PPCPs污水也可能进入地表水。因此,地表水是PPCPs分布最广、污染水平相对较高的环境介质,要高度重视地表水中PPCPs的污染治理。
1.3 地下水中PPCPs污染特征
地下水中的PPCPs通常是由于市政污水管道滴漏、污染地表水和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下渗而来,极性越大的化合物越易渗透至地下水[24]。我国地下水中已有不同种类的PPCPs检出。上海市地下水中检测到三氯生的质量浓度为50.10~185.80 ng/L[18]2380。常州市地下水中检测到布洛芬的质量浓度为31.00~118.74 ng/L,双酚A的质量浓度为7.51~84.37 ng/L[25]。上海市、珠三角等地区地下水中检出卡马西平最高质量浓度为563.00 ng/L,咖啡因最高质量浓度为10.80 ng/L[18]2380,[26],[27]4。
1.4 沉积物中PPCPs污染特征
在不同水系的沉积物中也检测到多种PPCPs。黄河沉积物中检测到环丙沙星的最高质量浓度为93.80 μg/kg[13]3143;太湖沉积物中检测到磺胺甲噁唑的最高质量浓度为47.40 μg/kg,林可霉素的最高质量浓度为47.70 μg/kg,咖啡因的最高质量浓度为482.00 μg/kg,卡马西平的最高质量浓度为31.85 μg/kg[28];台湾碘河沉积物中氯霉素的最高质量浓度为11 μg/kg[29]。人工合成麝香在太湖、梁滩河、苏州河、海河、松花江等地沉积物中均有检出,质量浓度为1.50~268.49 μg/kg[12]3,[13]3146,[27]5,[30]。LUO等[31]研究发现,海河流域中大部分PPCPs在沉积物中的含量高于地表水中的含量。一般而言,同一地点的沉积物中PPCPs含量高于地表水中的含量,这主要是因为PPCPs的辛醇-水分配系数较高,水溶性低,易被有机质含量较高的沉积物吸附[32]。
1.5 污泥中PPCPs污染特征
污水中的PPCPs会以母体化合物或者代谢产物的形式通过吸附或沉积作用而进入污泥中[33]。据报道,中国46个污水处理厂检测到环丙沙星的最高质量浓度为926 μg/kg,诺氟沙星的最高质量浓度为21 335 μg/kg,氧氟沙星的最高质量浓度为7 788 μg/kg,红霉素的最高质量浓度为55.8 μg/kg,磺胺嘧啶的最高质量浓度为67.4 μg/kg,磺胺甲噁唑的最高质量浓度为17.0 μg/kg[34]。三氯生在污泥中被检出的报道也较多,它在上海市、广州市、珠三角等地污泥中的质量浓度为200.1~1 187.5 μg/kg[23]9,[35-36],但卡马西平及雌激素酮在污泥中的检出质量浓度分别低于2.9、22.9 μg/kg[23]9,这与PPCPs在各地区的消费量有关。
2 环境中PPCPs的生态毒性
PPCPs是具有强光学和化学活性的极性物质,能干扰内分泌系统[37]。PPCPs通常具有亲脂性和生物活性[38]。壬基酚、卡马西平、萘普生、雌二醇等能通过干扰虹鳟鱼肝脏细胞脱乙基酶(EROD)与乳过氧化物酶(LPO)的活性而使虹鳟鱼产生氧化应激反应,影响其代谢过程,导致肝细胞损伤[39]。对25例肾功能衰竭秃鹫进行检测发现,肾中均有兽药双氯芬酸,质量浓度达0.051~0.643 μg/g[40]。研究发现,金霉素和土霉素的质量浓度为160 mg/L时,植物会枯萎死亡,即便是较低浓度也会导致根与芽的干重降低[41]。长期暴露于低剂量(1 ng/L)人工合成乙炔雌二醇中的鱼类内分泌系统会受到干扰,出现鱼类的雌性化现象[42]。
同种PPCPs对不同生物的毒性效应不同。1 mg/L的红霉素对浮萍和蓝藻的最大生长抑制率分别为20%、70%[43]。环境介质中的PPCPs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其毒性具有复合效应。蔡梦婷等[44]研究表明,诺氟沙星与铜复合暴露对小球藻的联合作用类型为协同作用;土霉素与铜复合暴露对斑马鱼的联合作用类型为拮抗作用。SCHNELL等[45]研究了麝香与另外11种PPCPs之间的复合毒性效应,发现大部分PPCPs和麝香对肝脏RTL-W1细胞的联合作用类型为协同作用。PPCPs还具有生物富集性,可通过食物链从环境介质迁移至动植物及人体中,从而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负面效应[46]。
药物类PPCPs的主要毒性作用机理为抑制核酸、蛋白质的合成,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与影响细胞壁的形成,干扰细菌的能量代谢等[47]。PCPs通常会扰乱生物体内分泌系统,特别是激素类物质会影响生物的生长和发育,导致生育能力降低、雄性雌性化或双性化等。据报道,激素类物质会使鲫鱼、鲑鱼、鲦鱼、海龟等水生动物产生性别畸变,雌性化趋势严重[48-50]。HENNIES等[51]对瑞士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调查发现,出水中高浓度的乙炔雌二醇是产生雌雄同体鱼的原因。三氯生是典型的抗菌剂,但对水生生物有内分泌干扰效应[52]。当三氯生质量浓度达到0.25 mg/L时,斑马鱼体内胆碱酯酶和乳酸脱氢酶等的活性增加;成年斑马鱼的96 h半数致死浓度为0.34 mg/L;三氯生质量浓度为0.17 mg/L时,鳉鱼胚胎发育和孵化率受到影响,甚至改变鳉鱼的正常游动速度[53]。抗生素在环境中长期存在会使微生物产生耐药性,使环境中耐药性基因增加。GAO等[54]对污水处理厂污水和污泥样品中磺胺类抗生素浓度水平及微生物耐药性和耐药性基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耐药微生物数量与抗生素浓度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出水中检测到较高浓度的耐药性基因和耐药微生物。THIELE BRUHN等[55]调查了磺胺嘧啶和土霉素对土壤中微生物活性及种类的影响,发现磺胺嘧啶抑制了微生物活性并导致土壤还原细菌对Fe3+的还原能力下降,此外还导致耐药微生物大量出现。
3 环境中PPCPs降解
PPCPs在环境中会发生光化学降解、水解和生物降解等一种或多种反应。PPCPs在不同介质中的降解方式不同。PPCPs在水溶液中大都发生光化学降解和水解反应,而在沉积物和土壤中主要发生生物降解反应。PPCPs的降解会受到PPCPs的结构和性质的影响。
3.1 PPCPs光化学降解
光化学降解是表层水体中各类污染物的主要降解方式[56]。光化学降解分为直接光解和间接光解两类。具有吸光基团的阿维菌素等PPCPs可直接光解[57]。但有些PPCPs在自然环境中发生光化学降解需要光敏剂的诱发[58-59]。喹诺酮类与呋喃类对光敏感,在光存在的水体中可直接光解[60-61];四环素类可通过1O2和O2·诱发进行间接光解[62-63]。水体中溶解性有机质(DOM)会作为活性氧自由基、羟基自由基猝灭剂而影响PPCPs的光化学降解过程[64-65]。
3.2 PPCPs水解
PPCPs的水解主要受PPCPs类型及水体pH的影响。据报道,β-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和磺胺类PPCPs在环境中较容易发生水解反应,但大环内酯类和磺胺类在中性条件下水解较慢,而β-内酰胺类水解速度不受pH影响[66]。
3.3 PPCPs生物降解
生物降解也是去除PPCPs的重要途径。大部分PPCPs可以被微生物直接降解,但有部分PPCPs不易被生物降解[67]。氨基糖苷类、β-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磺胺类和四环素类药物易发生生物降解[68-69]。PPCPs的生物降解主要途径有:(1)PPCPs不作为碳源,但微生物与PPCPs发生共代谢作用而导致部分降解;(2)微生物利用PPCPs作为碳源和能源,将其完全矿化。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PPCPs在中国水体、沉积物、污泥等环境介质中的污染问题已十分严峻,PPCPs具有生物富集性和生态毒性,在环境中很难被完全去除。环境中的PPCPs主要因光化学降解、水解和生物降解作用而被去除。笔者认为今后PPCPs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 开展PPCPs间的复合效应或PPCPs与重金属间的复合效应研究。目前的研究几乎都是针对单一PPCPs或少数几种PPCPs,而在实际环境中,PPCPs通常是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共存的,因此需要加强多种PPCPs化合物污染行为的复合效应研究。
(2) 开展PPCPs的降解代谢产物检测及毒性效应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针对PPCPs母体化合物进行毒性效应检测,事实上,有些PPCPs的代谢产物毒性仍然很大,甚至比母体化合物还大,所以应开展PPCPs降解代谢产物的检测及毒性效应研究,建立完整的数据库。
- 环境污染与防治的其它文章
- 中国省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实践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