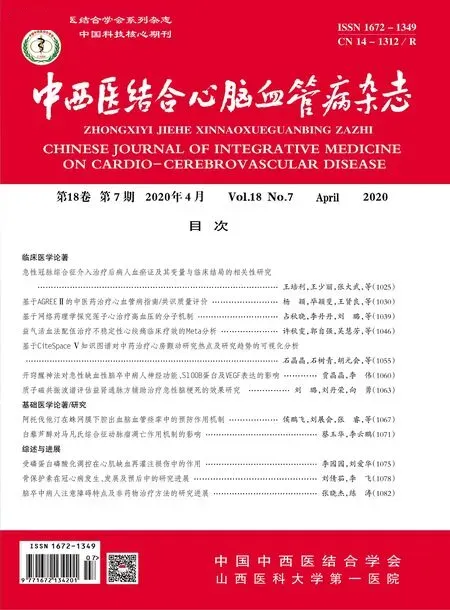徐浩教授分阶段论治血脂异常经验浅析
徐 璇,王心意,徐 浩
徐浩教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青年名中医,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师从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院士,在继承名老中医诊疗经验的同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加以创新发展,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方面取得较好的疗效。笔者有幸师从徐浩教授,跟随门诊学习期间获益匪浅,现将徐浩教授治疗血脂异常的经验介绍如下,以飨同道。
1 血脂异常病因病机认识
血脂异常是指由于遗传和(或)环境因素的影响,血浆脂蛋白的结构和代谢发生异常时,血液中某种或几种脂质成分的升高或降低[1]。血脂异常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中风、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病等一系列疾病[2-3]。目前,西医治疗本病主要有他汀类、贝特类药物,虽然治疗有效,但部分病人有一定副作用,可引发肝功异常等不良反应[4],因此,高脂血症病人常常寻求中医药的治疗方法。
血脂异常属于中医学“脂浊”的范畴[5]。清代张志聪《黄帝内经灵枢集注》云:“中焦之气,蒸津液化,其精微……溢于外则皮肉膏肥,余于内则膏脂丰满。”西医学的“血脂”可比同于中医学之“膏脂”。张景岳在《类经》中对“膏脂”的理解:“膏,脂膏也。精液和合为膏,以填补于骨空之中,则为脑为髓,为精为血,故上至巅顶,得以充实,下流阴股,得以交通也。”膏脂由水谷所化生,呈气化状态随津液的流行而敷布全身,有注骨空、补脑髓、润泽肌肤的作用,是人体生化阳气的基本物质之一。徐浩教授认为膏脂与津液同源,其正常的生理与脾的运化,肺的敷布,肝的疏泄,肾的主宰开合密切相关。若因嗜食膏粱厚味,劳倦内伤,或年老体衰使脏腑功能失调,水谷精微不归正化,津液生成输布障碍,多余的膏脂滞留积聚血脉而化为脂浊。若浊邪持续性增高,可生痰生瘀。故本病可从湿、痰、瘀不同病理产物分阶段论治。
2 不同阶段病理产物的演变过程
徐浩教授认为膏脂是“痰”“瘀”的致病源头。血中的膏脂属于精微物质的范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如果因为脏腑功能失调,使得体内的膏脂异常形成早期病理产物为“湿浊”。湿为黏腻之邪,重浊之质,病延日久,气虚不复,积湿不化,聚湿成痰。血中痰浊是痰与血的混合物,痰借血体,血借痰凝,着于血脉,凝滞愈坚使脉管本身受损,局部气血的运行和温煦受阻,导致脉络壅滞不畅,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管壁损害。受累动脉病变从内膜开始,一般先有脂质和复合糖类积聚、出血及血栓形成,纤维组织增生及钙质沉着,并有动脉中层的逐渐蜕变和钙化[6]。湿浊、痰凝均为阴霾之邪,留而不去,阻塞气机,日渐浸淫血脉,滞塞脉络,日久营血瘀滞。随着病情的进展,痰瘀互结沉积于血脉,形成血脉之痰瘀结块,壅塞脉道,即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旦发展到足以阻塞动脉腔,则该动脉所供应的组织或器官将缺血或坏死。而血瘀证的出现亦是动脉粥样硬化进一步发展,病情加重的标志,是演变为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必然转归。
3 分阶段论治
3.1 健脾祛湿利湿浊 此阶段病人病程常较短,多仅有实验室生化指标轻度升高,尚未表现出明显的痰浊及瘀血之象。病人形体超重或肥胖,平素嗜食肥甘厚味,饮食不节,久坐少动。饮食不节,嗜食肥甘厚腻,脾化失司,使水谷精微不能输布全身,多余的精微物质在血中聚积;虚弱的脾胃因运转乏力,使膏脂不能及时的转化,留滞不去,反而阻碍了脾运的功能,进而滋生脂浊。如果因肝气不足或情志不畅,而致肝失疏泄,气机横逆,则进一步影响脾的运化功能。如此,互相影响,愈增愈多,升清降浊功能失调,清浊不分,精微物质堆积于血脉之中而成脂浊之患。首次就诊多以体困乏力、头重如裹为主诉,舌体胖大有齿痕,舌苔白腻,脉弦细或濡缓。徐浩教授治疗此阶段病人以健脾祛湿,升清降浊为法,自拟健脾消脂方(由黄精、苍术、荷叶、泽泻组成),或用升阳益胃汤健脾除湿,益气升阳,清热和中,多获良效。若见胁肋胀痛,心烦易怒或情志抑郁,口苦脉弦等肝木克脾土之证者,可加入柴胡、郁金、决明子或合用逍遥散加减;若见脘腹胀满,口苦口黏,苔黄腻等湿郁化热之证者,加入黄连、枳实等以清热利湿。
3.2 祛痰化浊除痰凝 痰浊之为病,因其具有黏滞、凝涩之特点,流注全身而产生困遏沉重之感。痰浊阻遏阳气,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浊气在上则见头晕头重;痰浊阻遏胸阳,胸阳不振,可见胸闷,甚或出现胸痛;痰浊中阻,胃失和降,则见脘痞、恶心欲吐;痰浊盛于内,故咳嗽有痰;苔厚腻,脉弦滑。由于痰浊内聚,注入血脉,滞塞脉络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管壁损害。如颈部血管彩超提示颈动脉内中膜增厚或小斑块、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CTA)可见轻度狭窄。徐师认为此阶段病人应以祛痰化浊为主,方用温胆汤、瓜蒌薤白半夏汤等。根据病人体质,偏寒者治以温化,方选枳实薤白桂枝汤、五苓散加减;偏热者则治以清化,方选小陷胸汤、清气化痰丸加减。
3.3 痰瘀互结重在化瘀通络 “痰瘀同源”,血液的高黏及痰湿的重浊,共同作用致痰浊致瘀。而“痰瘀互结”是“脂浊”发展的必然结果。痰瘀互结沉积于脉道,附着于脉壁,发为胸痹心痛、中风偏枯等病证。故在此阶段,病人除有血脂异常以外,多伴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临床辅助检查可见有动脉中重度狭窄及闭塞等,症见胸闷如窒且痛,气短喘促,肢体沉重或麻木,形体肥胖,痰多,口唇紫暗,面部瘀斑,舌下脉青紫、紫黑或曲张、粗胀,苔厚腻,脉弦滑。治疗上则以祛瘀通络为主,正如唐容川所言“但去瘀血则痰水自消”。徐浩教授自拟化瘀降脂方(柴胡、郁金、生蒲黄、红花),或用血府逐瘀汤,或补阳还五汤加生山楂、红曲、虎杖、酒大黄等,久病及血瘀明显者可加水蛭以加强活血通络之功,降低血液黏稠度。根据陈可冀院士经验,大黄、南星、菖蒲、郁金、香附、蒲黄、水蛭、泽兰、薤白等为兼治痰瘀的药物,临证可酌情选用。
此外,血脂异常在中老年发病率明显增加。徐浩教授认为中老年人脏腑生理功能逐渐衰退,代谢失调,胸阳不振,津液不能蒸化,膏脂不能宣泄于内外,聚积于血脉之中,血行缓慢瘀滞。临床症状以腰膝酸软、动则气短、耳鸣健忘,或畏寒肢冷,夜尿频多,或五心烦热,夜间盗汗等一派肾虚之象为主。此时病多本虚标实,治疗尚应兼以补肾益气,常合用自拟补肾降脂方(枸杞子、女贞子、制首乌、桑寄生),根据肾阴阳虚损偏重酌用左归丸或右归丸加减调治。
4 验案举隅
病人,女,67岁,主因头晕3年,加重1个月,于2018年5月15日初诊。病人3年前因头晕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高脂血症”,查生化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4.0 mmol/L,服用辛伐他汀2个月,因肝功异常遂停药。病人自觉头晕时轻时重,每于情绪激动及季节交替时头晕明显。2017年复查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3.40 mmol/L,未系统治疗。近1个月无明显诱因头晕反复发作,为求中药治疗遂来我院门诊就诊。刻下:头晕、头昏沉感,晨起明显,乏力,腹胀,心烦易怒,焦虑状态,食欲差,口干欲饮,无口苦,大便2 d或3 d行一次,大便干,小便频。平素怕冷明显,腰部为甚。舌暗苔薄黄稍腻,舌下络脉紫黯,脉弦细。体格检查:血压125/70 mmHg(1 mmHg=0.133 kPa)。辅助检查:总胆固醇(TC) 5.81 mmol/L,LDL-C 3.71 mmol/L。颈动脉彩超提示:双侧颈动脉内-中膜不均增厚伴斑块形成,左侧颈动脉球部狭窄50%。西医诊断:①高脂血症,②颈内动脉狭窄。中医辨证:痰瘀互结,兼肝郁气滞。处方:柴胡10 g,枳壳10 g,白芍10 g,郁金15 g,生蒲黄10 g,红花15 g,荷叶10 g,泽泻30 g,生山楂15 g,水蛭10 g,决明子30 g。二诊:2018年7月3日复诊,自诉头晕明显缓解,近一周夜间耳鸣,舌下络脉瘀紫有所减轻,脉弦。上方加磁石30 g,继服。2018年11月电话随诊,病人无明显不适,复查血脂结果显示:TC 4.26 mmol/L,三酰甘油(TG)1.78 mmol/L,LDL-C 2.13 mmol/L。
按: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果,辨证为痰瘀互结。肝藏血主疏泄,脾统血主思,病人心烦易怒,造成肝失条达之性,疏泄升发无力,从而导致全身气机升降失常,水液代谢障碍,痰湿内生,清浊不分,血中痰浊壅遏留而为瘀,痰瘀互结积存血脉故见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方中生山楂、红花、生蒲黄、水蛭活血化瘀通络,促进体内膏脂的转运和排泄;荷叶、泽泻祛湿利水,升清降浊;柴胡、郁金、枳壳、疏肝理气;决明子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白芍柔肝养血。服药60剂后,病人血脂明显降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病人未再就诊,后期出现耳鸣,肾虚之象渐显,如兼以补肾益气继续调治,可望进一步巩固调脂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