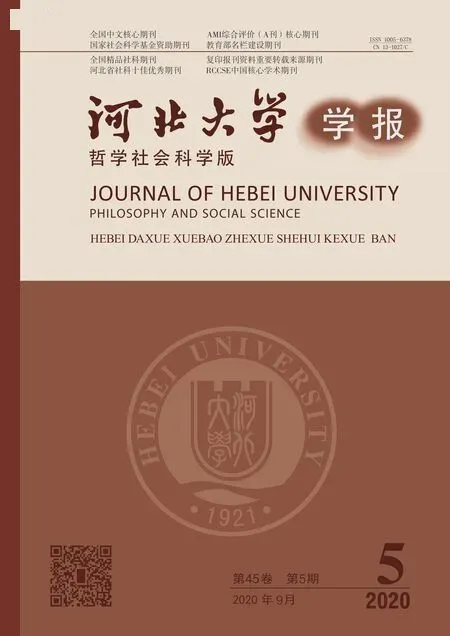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
——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路鹏飞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一、引 言
目前学界主要是以两种“道统”说进行阐释的,其中又以理学“不得其传”说的道统说占主流,即宋明理学直承孔孟的理学谱系。而近年来道统“不绝其传”说的谱系也渐渐有学者注意到。如周炽成论述了韩愈两种不同的道统版本在唐宋不同时期的反映[1],叶平梳理了唐末时期以韩愈为主的道统,即包括孔孟至韩愈的道统谱系[2],赵瑞军探讨了宋初的道统含义及其谱系[3]。他们都论述了道统说的另一个谱系,即孔孟之后包括汉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在内的道统说。然而两种道统说的含义背后实际上是和韩愈对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有关。其分歧同样是对这两种阐释的分析和接受,理学官学化后,最后“不得其传”说占据统治地位,获得了学术和官方的统一认可。
一般来讲,道统说主要的理论渊源是韩愈,其影响也最大,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后改为“不得其传”。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原道》为吾国文化史中最有关系之文字。”[4]他特别肯定了韩愈建立道统证明传授渊源的功绩。冯友兰先生在《论道统》中则指出:“所谓道统是指一个社会的人在思想方面的中心哲学。”[5]553他指出“统”包括两层含义:统一、传统。就传统来说,这个道统必须要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传承的方法包括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两个方面,如尧舜相传为见知,周孔相传为闻知。他提出:“就中国历史说,统一的中国的治统及道统的形成都是在秦汉的时候。秦汉以后,我们才有整个的中国这一个大社会。”[5]554理学确立的道统忽视汉唐而重视先秦,这和韩愈对道统的阐释变化不无关系。刘成国道:“自中唐至宋初,韩愈《原道》的影响有限。北宋仁宗朝的前三十年,是《原道》走向经典化的关键时期。它被士人精英尊为文以明道的典范,排佛卫道的一面旗帜。”[6]42
韩愈仿照佛教法统尊孟子为儒家道统的载道者,与佛教相抗衡。他以孟子为道统载道者,区分了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的不同,后之学者言儒家之道则常言孟子。韩愈最初指出道统之说“不绝其传”,即道统并非一定要上接孟子,荀子、扬雄包括韩愈皆为道统的接续者;变为“不得其传”后,则必须上接孟子,甚至韩愈自身也被略过。由此也造成了理学确立的道统谱系自秦汉至宋朝的连续性中断,发生了由重经学到重理学的唐宋思想转型,其积极的一面在于先秦儒学复兴和理学的产生,消极一面则在于汉唐思想不受重视。因此有必要探究韩愈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以及儒家道统由“不绝其传”向“不得其传”转变的过程和原因。
二、“不绝其传”“不得其传”辨析
韩愈对于孟子、扬雄、荀子、杨墨都曾发表过看法,由于传承以及版本等原因,其字词在过往的传抄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改变。朱熹在《韩文考异》序言中提出,韩愈的文本从宋代开始就已有许多改动和怀疑之处,“然如欧阳公之言,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7]。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当属《原道》篇中的道统观:“尧以是传之舜……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8]4原句本为“不绝其传”,这在《昌黎文录》中有记载,《昌黎文录》是和韩愈同时代的赵德所编选,也是最早的一部韩愈选集,赵德本人也受到过韩愈教诲。然而其书早已失传,目前有刘真伦先生根据两宋文献勾稽出的资料集《昌黎文录辑校》。韩愈文集现存最早的底本——北宋监本系统的潮本,其中保留有注解:“得,赵作‘绝’。”[9]71这个版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昌黎先生集》。《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曾考辨,“此本为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刻本,在传世韩集中,这是刊刻年代最早的一个刻本。它的祖本是北宋徽宗大观年间潮州刻本,在传世韩集中,这是唯一的一个属于北宋监本系统的传本”[10]。此注另外在南宋版本祝充本、魏仲举本中也均有保留。可见在宋代流传的版本已经是“不得其传”了,至于何时何地改为“不得其传”则无从考证。由于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州后,赵德问学于韩愈方做此注,甚至可能更晚,五年后(824)韩愈去世,因此一般认为是韩愈晚年改“绝”为“得”,但并无实据。这也解释了韩愈思想中某些矛盾的方面,然而“不绝其传”和“不得其传”的不同,一字之差所包含的意蕴和所造成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若为“不绝其传”,文武周公、孔孟荀之道统谱系传承则绵绵不绝,传承道统并非一定要上接孟子,如荀子、扬雄以及韩愈等人均可为道统的接续者。赵德在《昌黎文录》序言中曰:“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9]25可见赵德评价韩愈是把自己以及扬雄等人作为道统的接续者的。据《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韩愈二十九岁时(贞元十三年)作《重答张籍书》,文中同样提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杨雄所传之道也。”[8]562此时韩愈仍然赞成扬雄等人同样为道统的接续者,否则的话则与“不得其传”相背离。韩愈三十六岁时(贞元十九年)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言:“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册,中国之人世守之。”[11]5618文武周孔之道“世守之”,其中意蕴和“不绝其传”是相符合的,以上语句总体上也是表达道统之“不绝其传”。
韩愈在《读荀子》中提出“晚得杨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8]111,他当时同样把扬雄作为圣人之徒看待,荀子则“在轲雄之间”。“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杨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8]111。并且进而提出孟子“醇乎醇”,荀子、扬雄则“大醇而小疵”。对于儒家典籍文本,除《孟子》外,韩愈同样评价《诗》《书》《春秋》“无疵”,对于《墨子》他同样推崇备至,《读墨子》篇中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8]127以上思想与“不绝其传”说观念一致。
若为“不得其传”,荀子、扬雄等在道统上的影响便自然降低,这也间接造成了宋儒不把韩愈等列入理学道统谱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可以说是韩愈本人造成的。韩愈对荀子、扬雄并非持完全否定态度,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可荀扬的“圣人之徒”身份的,也就是说他们同样在道统谱系。鉴于目前《原道》最终定稿时间难以敲定,虽有相关研究,但实际却难以令人信服,综合韩愈前后文章,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在传承演变过程中,《原道》的最终版本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8]4这在现存最早的宋版里已是定论。童第德先生评价“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便表明了前面应该是“不得其传”[12],失之于武断。刘真伦先生则推断韩愈晚年后将“不绝其传”改为“不得其传”,并提出在《与孟尚书书》时荀、扬的地位已开始发生变化[8]15。韩愈五十二岁时(元和十五年)作《与孟尚书书》:“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 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11]5602此篇内容和说法同样不足以证明“不得其传”。因为韩愈一向尊孟,也向来对荀子、扬雄有微词,然而类似“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大醇而小疵”等并不表示他们便不能继承道统,关键还是在于“绝”和“得”的取舍。
总体来说,“不绝其传”的内容在韩愈文集中占的比重很大,或者说是绝大部分,甚至只有“不得其传”这一孤证。这也反映在唐末至宋初,直至二程以前学者主要以“不绝其传”阐释的,也就是儒家道德传承有序这个脉络。因此,认为韩愈晚年改为“不得其传”的说法并不必然成立,如果成立,韩愈为何不修改其他相关内容则值得深思。在李翱为韩愈写的行状中提道:“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13]27韩愈曾经在为文方面以扬雄自任。刘昫在《韩愈传》中提出在唐代大历、贞元期间,古学盛行,士大夫阶层独孤及、梁肃等纷纷学习董仲舒、扬雄等人述作,而韩愈从之游。这也是韩愈逝世后直到宋初很多人都是依照“不绝其传”来诠释道统的重要原因。
三、唐末宋初对“不绝其传”说的倡导
和韩愈同时代的唐代儒士,主要也是站在道统“不绝其传”的立场上。他们不单独把孟轲作为道统的接续人,同样也把荀子、扬雄,以及韩愈纳入其中。张籍曾和韩愈书信往来,贞元十四年他在《上韩昌黎书》中推崇扬雄:“扬雄作《法言》而辩之,圣人之道犹明。”[13]8张籍还把孟轲、扬雄并列,共同作为圣人之道的传承者,这也是韩愈当时的观点。林简言在《上韩吏部书》中同样是把韩愈作为孟轲、扬雄的传人来看待,“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睎阁下之门,孟轲、扬雄之门也”[13]39。柳宗元和韩愈往来的书信中认为,韩愈之才和司马迁不相上下,而超过扬雄,可见时人的普遍观点应是“不绝其传”。
五代到宋朝韩愈的地位发生过转折,主要体现在《旧唐书》《新唐书》中,《旧唐书》由五代时后晋的刘昫、赵莹等编写,《新唐书》则由北宋欧阳修、宋祈等编撰。《旧唐书》对韩愈贬过于褒,如称韩愈“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等,至宋代《新唐书》而发生转折,称韩愈“其道盖自比孟轲”,并评价韩愈功绩比孟子要“齐而力倍之”,可以说是推崇备至:“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14]从中可见宋代后韩愈地位的上升。王鸣盛指出正式对韩愈的推崇正是始于欧阳修,而非宋祈:“韩子在唐虽名高,及唐末已少问津者,直至欧阳公方表章推重。”[15]他所指的应当是指对韩愈在政治地位和古文运动中的推崇,此前唐末皮日休也曾上书要求尊韩愈配享太学。皮锡瑞曾提出:“唐韩愈始推尊孟子,皮日休尊孟并尊韩,开宋学之先声。北宋李觏、司马光犹疑《孟子》,南宋朱子始以《孟子》配《论语》《学》《庸》,后为《四书》,而孟子益尊。”[16]宋代除了道统之说外,古文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当时的古文运动皆推崇韩愈、柳宗元。
宋初柳开效法韩愈,在《应责》中提出:“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13]72这基本是站在道统“不绝其传”立场上说的。袁辉在叙述宋初道统复建时指出其背后原因以及理解的不同:“以柳开、穆修以及田锡等为代表的士人在救弊心态的影响下,开始自觉突破五代以来儒风陵夷的局面,他们皆以道统重建为己任,以古文复兴相号召,开启了北宋儒学发展最初的历史进程,但其间对于道统的理解与取径又有所差异。”[17]此外还有欧阳修、孙复、石介、王安石等人,其中孙复、石介是把孟、荀、扬以及王通、韩愈作为孔子之后传承儒学之道地接续者,石介有《尊韩》一文。苏轼专门写有《韩愈优于扬雄》的文章,评价扬雄与韩愈相去甚远,但他的理解又不相同。直至辛弃疾词中仍有“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之意,表明当时时代对韩愈的推崇。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曾提道:“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徂来列之于道统。”[18]其中欧阳修对韩愈的推崇主要是在史学地位上,古人往往重视盖棺论定,欧阳修对韩愈的定位,从历史、政治上抬高了其地位。而当时宋代其他诸儒,对韩愈及其提出的道统谱系推崇又从学术上进行了表彰。孙复肯定韩愈为知道者,不杂于异端,推崇韩愈提出的儒家传道谱系,但是他同样是以“不绝其传”的立场论述的,“孔子而下,称大儒者,曰孟轲、荀卿、扬雄。至于董仲舒,则忽而不举,何哉? 仲舒对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斯可谓尽心于圣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19]98-99。孙复强调道的作用,如他提出文者道之用,道者教之本,他推崇孔子、孟子、荀子,并且将韩愈与董仲舒、扬雄、王通并称:“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19]99石介作为孙复弟子,对韩愈的道统说推崇并不亚于孙复。石介作有《尊韩》一篇,他认为“道”始于伏羲,成于孔子,道成之后不生圣人,所以孔子后没有圣人,孟轲、扬雄、王通、韩愈为贤人,因为韩愈使道大明,所以韩愈后不生贤人。他推举了孔子以及孔子之前十四个圣人,韩愈以及韩愈之前五个贤人,孔子为圣人之至,韩愈为贤人之卓。石介推崇韩愈功绩自诸子以来未有:“孔子为圣人之至,吏部为贤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19]109但他仍然是以道统“不绝其传”说为依据的,并且他同样倡导古文运动,反对佛老。
除欧阳修外,王安石对韩愈也多有推崇,并因此推崇孟子。詹大和等所做的《王安石年谱》称“公少有大志,其学以孟轲自许,荀况、韩愈不道也”[20]。不知是特意美化王安石或是其他原因,书中内容同时又表现了王安石对于韩愈的推崇,显示了自相矛盾的一面,而且此论断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王安石对韩愈的尊崇表现在他尊韩愈为韩子,并且真实的承接了韩愈的道统说,可以说王安石正是因为尊韩愈而尊孟子。如欧阳修曾以韩愈许王安石,在《赠王介甫》中言:“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21]王安石在回赠欧阳修的《奉酬永叔见赠》中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22]264这也是时人以孟子许王安石的原因。他在《庙议札子》《送孙正之序》等都曾引用韩愈的观点,并作有《韩子》《孟子》《扬子》等诗,《韩子》中“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一句表明了王安石高扬韩愈所提出的儒家之道说。《孟子》中“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一句也表现出王安石将孟子作为人生榜样,以接续道统为己任的担当与情怀。《扬子》则表现了王安石对扬雄弘扬儒道的肯定,如“儒者凌夷此道穷,千秋只有一扬雄……道真沉溺九流浑,独泝颓波讨得源”等句,可见他是真的承接了韩愈的观点。在《送孙正之序》中王安石有孟、韩连用之语,“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22]885。可见他同样认可韩愈的道统说,并且是站在“不绝其传”的立场上的,否则王安石对扬雄、韩愈的推崇则无法自圆其说。但是他并不完全追随韩愈,如《性说》中,他提出:“吾是以与孔子也。韩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22]727
四、“不绝其传”向“不得其传”的转变
如果说道统“不绝其传”说在唐代和宋初时期还占主流的话,那么自以程颐为代表的程朱学派开始则主要转向道统“不得其传”说。宋代尊韩思潮受到佛教契嵩等批判后也有所改变,如李觏由尊孟转向了非孟,王安石、司马光在对韩愈肯定外也有所批评。这可能间接也导致程颐对韩愈的辩证对待。因为倡导孟子后道统“不得其传”说最有力的为理学宗师程颐,程颐曾提出:“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然韩子责人甚恕。”[13]140程颐一方面反驳了韩愈对荀、扬的看法,否定了荀子、扬雄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截取了韩愈孟子后道统“不得其传”的说法,但是又把韩愈排斥在外。《程氏遗书》载:“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23]最后经过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裁定而广为流传。
《宋史》载宁宗时期朱熹去世后,朝野讨论其谥文,最后认为:“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为韩文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与。请以韩子之谥谥公。从之,乃谥曰文。”[24]若真如其所言,孟子后道统“不得其传”的说法实际上是从程颐开始流传,至朱熹而成为定论,以至于天下纷纷从之。费密曾在《道脉谱论》中叙述宋代“道统”说的最终奠定过程,指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的奠定实际源于朱熹和陆九渊的门户之争。“独言孟轲之传,开于唐儒韩愈,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轲,程颐又以程颢为孟轲后一人,而尚无道统接传之论也。南渡后,朱熹与陆九渊争胜门户,熹传洛学,乃倡立道统,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轲,而程颢、程颐接之”[25]8056-8057。换言之,宋代最初蔡京以王安石类比孟子,程颐盛赞程颢为孟子后第一人,至朱陆之辨、门户之争后,朱熹方把理学道统真正确立起来。相关内容李承贵先生在《陆九渊》一书“道统之争”中有详细辨析,不再赘述。
程颐除没有把韩愈列入理学道统谱系外,对韩愈的看法可以说毁誉参半,如“唐人善论文莫如韩愈”,推崇韩愈为近世豪杰之士。同时肯定了韩愈对《春秋》等经学的看法,推崇他深得其旨、名理皆善。其中尤其强调韩愈《原道》中孟子后道统“不得其传”说,“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26]5。然而他认为老子不识道,扬雄不见道,对韩愈推崇的荀子、扬雄等人则贬斥甚多。可以说,程颐继承和光大了“不得其传”说,在《刘元承手编》《畅潜道录》中多次强调,推崇孟子而对荀子、扬雄、韩愈等则多有贬斥,如程颐评价王安石之学“极有害”,评价佛家印证之说“极好笑”,荀子“极驳”,葬埋昏嫁之书“极有害”,论说守节之说则曰:“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26]301
程颐之所以强调道统“不得其传”,一方面是为了以孟子道统接续者自任,树立自己的理学思想,一方面是为了与佛道抗衡,确立儒家的道统心性之学。如他曾表彰程颢为孟子后第一人,“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27]。契嵩曾批评韩愈:“韩子徒守人伦之近事,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岂暗内而循外欤?”[28]批评韩愈不重性命之学。因此程颐强调道统“不得其传”说,其中重要一点便是要重视性命之学。例如他在人性论上确立性善说,否定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说,以及韩愈的性三品说。他完全从孟子后“不得其传”的立场出发,主张人性本善,以孔孟所说为是,否定扬雄、韩愈的人性论。他认可韩愈对孟子“醇乎醇”的推崇,肯定此言极好,但是对“荀、杨大醇小疵”的说法则强烈批判。“荀子极偏驳”,程颐指责荀子性恶论大本已失,扬雄则不识性,质疑更何谈儒家之道。程颐辨析扬雄、韩愈所说之性实际是才,而才出于气。他们区分了性、气的不同:“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26]252程颐提出能够顺四端之情则为善,不能顺四端之情而悖天理则为恶,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至清之气为圣人,禀至浊之气则为愚人等。
在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上,程颐否定了荀子、扬雄以及王安石的理解。他批评王安石分道为二——“尽人道谓之仁,尽天道谓之圣”,强调道必然尽人尽天而合为一。评价王安石是从人主心术处用功,对于这种正君而国定的做法表达了批评观点:“此学极有害。……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其如之何!”[26]50用语不可谓不重。他把儒家之道进一步追溯到个体、内圣的一面,由内圣而外王,尤其是落实到了心性论方面。如程颢所说:“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26]1“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更无别处”[26]3。程颐有专门的《论道篇》,理谓道,率性谓之道,克己复礼为道,等等,其内容主要侧重于内圣、学统方面,对于外王方面则有所忽视。
此后朱熹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他在《中庸集解序》言“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孟子序说》中言“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再次强调孟子后道统“不得其传”的观点,以此树立理学上接孔孟的渊源。对于韩愈确立的道统谱系,他也曾提到这点:“盖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8]890批评韩愈在本体论、心性修养方面学识不够。他在《近思录》中论述圣贤气象时引用了二程对韩愈的评价,南宋叶采在其序言中提道:“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断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于是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29]再次强调了理学的道统谱系,并没有把韩愈等人列入其中。
理学后来被立为官学和科举取士的标准,尤其是在明、清两朝,实现了其道统、治统的统一,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尽管清代有汉学兴起,虽有汉宋之争,但是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理学,尤其是官学的指导作用。两者的统一性要远大于其斗争性,“从统一性来看,明代整理了宋元以来文献典籍,将程朱理学设为官学,同时作为科举考试和价值导向,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上,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儒家文化,形成了延续到现在的儒家文化共同体”[30]。当然由于理学本身是从内圣方面入手,因此也导致强内圣而弱外王,重学统而轻治统,至明末而有空谈心性之弊。
五、道统“不得其传”说影响及其他理解
对于道统,韩愈所指主要是指儒家的道统传承,因为他本身是为了从政教上反对佛老之教而提出来的。然而最初提出之时,其含义并不被接受,如柳宗元与佛教亲近,他甚至把佛教也列为孔子之道的相近者,虽然他同样反对佛教“无夫妇父子”之伦理,但他更欣赏佛教“不爱官,不争能”的做法,并主张前者为外而后者为内,“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31]。刘禹锡同样好浮屠之学,同样不赞成韩愈儒家道统说。直至宋代柳开、欧阳修、宋祈、王安石等对韩愈的推崇,以及孙复、石介、程颐等继续辟佛老倡道统,韩愈儒家道统说的内涵方被接受。然而道统“不绝其传”说还是“不得其传”说在道统说确立后又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欧阳修、孙复、石介等人是以“不绝其传”为代表的话,程颐等理学家则主要是以“不得其传”说为立场。因此可以说这又是一个改变,主要体现在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
此外,并非所有宋儒都接受韩愈的道统说,如苏轼虽然写有《韩愈论》《韩愈优于扬雄》等文章,对韩愈多有推崇,并且受到了韩愈古文运动等的影响,但他对韩愈提出的道统主张没有全盘接受,甚至对韩愈道统说有所批评,而且他对佛、老均有所吸收。在《韩愈论》中,苏轼认为对于圣人之道的理解有两种人:趋名而好之者和安实而乐之者。他认为韩愈对于圣人之道,属于安其名而未能乐其实。苏轼批评韩愈持论太高,对孔孟太尊而拒杨墨、佛老太苛,以致理而不精、支离荡佚而自叛其说。在《韩愈优于扬雄》一文中,苏轼指出扬雄与韩愈相去甚远,认可韩愈为近世豪杰,“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自亦难得”[32]。司马光对韩愈道统说的观点同样持有怀疑,并著有《疑孟》一篇,他主要推崇孔子观点,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看法。他在《资治通鉴》中对韩愈在儒佛之争中的作用有所褒奖,但也指出了韩愈矫枉过激的情况。“独愈恶其蠧财惑众,力排之,其言多矫激太过”[33]。
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在道统“不得其传”说基础上更激进,如李觏、叶适是在“不得其传”观点的基础上直承孔子之道。李觏指出孔子后道统即不得其传。然而,李觏也有对孟子观点赞成的一面。郭畑梳理了李觏由尊孟到非孟的心理变化历程,他指出李觏在作《常语》前对孟子是持推崇态度的,而他态度的转变,“应是受到阻遏古文运动排佛攻势的僧人释契嵩援引孟子以攻击韩愈、甚至进而消解孔子和儒经神圣性的刺激”[34]。叶适和李觏的做法很相似,他同样是在韩愈道统“不得其传”说基础上更进一步,主张直承孔子,他认为孔子之后道统便断了。对于叶适的非孟思想,徐洪兴指出,叶适承认韩愈所树立的儒家道统说,但他不承认韩愈所说的道统传承顺序,他反对接续孔子的曾参、子思、孟子的道统传承说[35]。叶适不认为曾参、子思、孟子所传承的便完全是孔子的道统,他通过反对这种道统传承顺序,把自己作为道统接续人而直承孔子。对于曾参,叶适引用“参也鲁”的说法,以及曾参不列孔门十哲,进而认为其“未可为至”,他反对曾参把孔子的“一贯之道”理解为“忠恕”。对于子思,叶适怀疑他和《中庸》的关系,同时对《中庸》也提出了质疑。对于孟子,叶适指出了孟子的几方面问题,“后世以孟子能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36],并一一分析,最终否定孟子为孔子的道统接续者,可以说叶适的做法,比韩愈所的道统“不得其传”说犹有过之,他通过对韩愈的道统传承说法一一分析与批驳,进而认为孔子之后道统便“不得其传”了。
宋儒之所以对韩愈儒家道统说极力推崇,主要是宋朝仍然延续着三教在政治教化上的争斗,由此产生了儒道复兴——即“要用儒家之道取代佛老等‘异端’”[37]。为了反对佛道二教,辟除异端邪说,必然要高扬儒家的道统,无论是“不绝其传”说还是“不得其传”说,这一点是一致的。如孙复、石介强调儒家的仁义礼乐之教化,反对佛老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作为政治教化之本。“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得不鸣鼓而攻之乎?”[19]100程颐强调孟子后道统“不得其传”的说法后广为流播,如黄庭坚、晁说之、陈傅良、胡安国、朱熹、胡宏等人都接续其说。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进行了强调,此后几乎成为定论。
其间并非没有反对意见,宋高宗绍兴六年左司谏陈公辅曾上疏禁二程之学:“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诚恐士习从此大坏,乞禁止之!”[38]刘屏山也曾提出道统“不得其传”说“孤圣人之道,绝学者之志”,然而未曾引起重视,而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认为道统“不绝其传”的说法更是少有人提起。清代黄家岱在《读韩子原道》中指出,“后学窃谓程、刘两说似皆失韩子意,韩子盖曰自孟子殁后,传道统者皆具体而微,未有若孟子能得其全也。故下云‘荀与扬择焉不精,语焉不详’,非孟子后绝无人也”[25]6002。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多见,理学普遍所倾向的还是“不得其传”说。
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及道统由“不绝其传”到“不得其传”变化,也显示了唐宋鼎革之际对于道统理解的转变。然而一字之变,可以说是相差甚远。道统“不绝其传”说表明道统绵绵不绝,千年思想传承有序,韩愈自然也包括在内;而“不得其传”说则表明儒家之道自孟子后已经隔断,若想接续儒道只能重返先秦,虽然韩愈同样以孟子传道者自任,但是理学还是没有把韩愈列入理学正统,只是在清代被熊赐履等列入道统之翼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吊诡的说法,不知韩愈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后果。因为两种说法都是基于儒者的传道抱负,以与佛老相颃颉,“不绝其传”说只是把自身纳入道统,以后继者自任,这种说法实际并无新意,与秦汉儒者无所区分。与之相比,“不得其传”说气魄雄浑,以舍我其谁的孟子“传道者”自任,甚至表现为李觏、叶适等人直承孔子的做法。而且此说法在宋代的传播也迎合了当时道学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抱负,如邵雍的数学、张载的气学、王安石的新学等,为此《宋史》专门列“道学”篇。然而这种舍我其谁的道统说在清代却逐渐走入偏狭,除统治因素影响外,清代儒道之辨、汉宋之争等儒学内部正统性的论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儒家门户道统说的闭塞性。
另一方面,“不得其传”说确立后,理学思想追溯至孟子,自然不必焚膏继晷、皓首穷经,而从经学的经传注疏中脱身出来,专注于先秦儒学。因为孟子后道统“不得其传”,所以理学方有许多“自得”之说。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流播甚广,甚至影响了当时及其后朝鲜、日本等国家的理学发展。其积极的一面在于,它是理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唐宋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反而能够深造自得,最终在经学体系外成功确立了四书体系。使得理学成为延续千年的官学和科举取士的标准,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受理学影响,“四书五经”之说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此外,道统“不得其传”说同样有负面影响,即秦汉至宋朝千年期间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过于强调道统也导致了理学思想后继发展的偏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