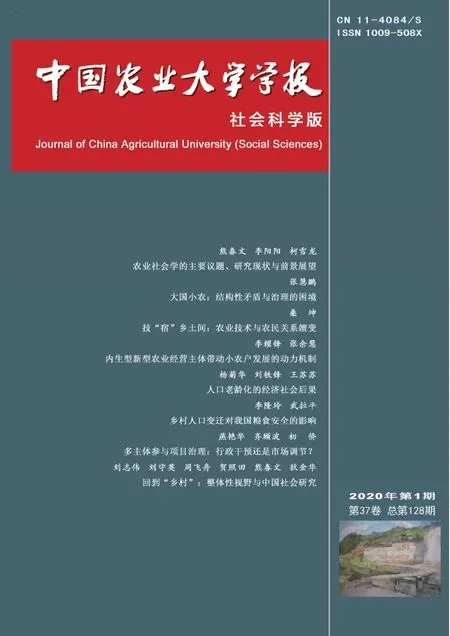人口流动、治理规则与乡村社会治理
狄金华
我先从刘守英老师讲的乡村问题研究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说起,每一次从政策层面关注农村问题时,可能往往都不是农村自身出了问题。我们从最近两次的乡村建设政策为例来讲,新世纪之初进行新农村建设,是因为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城市里面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以新农村建设为政策目标的工作,它事实上是在特定宏观背景下一些工业产业与产品向农村的转移;最近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推进,大的背景则是2008 年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和延续着的城市工业过剩。我们看到政策层面对乡村的关注往往是因为乡村之外的东西出了问题,政府试图通过调整乡村或城乡关系来应对这些问题。
在这种格局之下,我们如何回到乡村中间去,如何以乡村为本位来看乡村?当我们进入乡村时,我们首先要破除原来对乡村理解的误区。第一误区是关于人口的流动。通常人们认为,人口的流动是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度流动,是线性的流动,但事实上农村人口的流出并不是线性的。刚刚几位老师都讲到,这种流动并不一定是线性的状态,不是说出去了就一定不回来,或者我直接地、顺利地出去。在我的调研经验中,人口作为一种要素的流动具有多种可能性。飞舟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一些本地人陆陆续续地回来,间断性地回来。另外一方面,以我的老家——一个江汉平原的村庄为例,我们既看到了本村的人陆陆续续离开村庄进城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但同时也发现它并不是完全空心化,期间充斥着相当数量的外地人。我的老家是江汉平原的一个农村,去县城还很远,它完全没有所谓的区位优势,如果非要罗列它的优势,可能就是靠近省道,但这个优势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已经不算优势了,很多地方在交通上面远远超过它。迁移到我们村的外地人都是从四川、重庆来的移民,也有从宜昌、恩施等山里面慢慢搬迁出来。他们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买这个地方的地,形成了一种人口流动的独特路径——不是从乡村向城市移民,而是从山区乡村向平原乡村的移动。这说明在今天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乡村人口的流动具有多种谱系。这些移民移入到平原乡村的村庄之中,就会改变他们原来在山上耕地面积少、交通不方便等诸种状况。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新的样态就是这些年有很多在城里的创业者开始往乡村去。上述的这些人陆陆续续返回或进入到乡村,这对我们原有的认知形成了挑战:我们一方面强调许多的人和资源从乡村流出去了,但我们又看到很多的人和资源又进入到乡村来,进来的这些人和资源是否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以及如何能够起到好的效果,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人上面,人并不是完全都走了,有一些人是留下来了,还有一些人是进来了,这些留下来和进来的人是否都可以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呢?先从留下来的那一波人讲起,就像刘守英所老师看到的,你让他去养头牛,他看你两眼;他家里有地,但你发现他几乎不种或者他基本只种可以满足口粮的地,其他的也不种了。你问他为什么不种,他说我去城里面打两天工的钱比种一年地的收入还多,但你发现他也没去城里挣钱,他在那里听音乐。这个时候,他其实是用这种城市对劳动的定价来预期他的收益,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闲暇——他宁可在这儿闲着,也不会干点农活。这与我们之前对乡村社会中农民行为的认知是不完全一样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人留下来未必能像我们所预期的留下来就能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
其次,进来的人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还要仔细讨论。从移民来看,如果他们想在这儿扎根,则一定要建立起跟现在村组内村民之间的关系。在乡村社会之中,建立关系最典型的方式就是随礼,所以移民一定要随村组内所有人的礼。在村子里面谁家的红白喜事,他们比所有本地人都更加积极地投入进去;相反,本地人则未必,因为他们可能预期着自己要离开村庄进城,有了这个预期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会随所有人的礼。这样,我们看到本地人和外地来的移民在村庄社会中的行为就存在了一定的差异,这对地方社会发展和地方社会治理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这里我举一个小例子。我在江汉平原做博士论文调查的时候就发现,本地人和外地移民之间围绕房屋的屋界和地界往往出现纠纷,相反本地人之间现在几乎是没有任何矛盾。我当时很奇怪,外地人既然想在这里站住脚,为什么还要同自己的邻居发生矛盾呢?调查之后我们发现,作为纠纷一方的本地人其实并不看重“地界”本身,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外地人竟然敢跟他闹。负责调解的村干部给我讲,在1980 年代刚刚分田到户的时候,本地人之间也像今天外来户一样经常发生纠纷,当时村民们想,田地分到各家各户,这是要祖祖辈辈传下去的,今天他要是让出了这一寸地,以后他子子孙孙就再也要不回来了,所以他们分寸必争。1990 年代之后,本地人就不再为地界田界闹纠纷了,大家都“想通了”——我们一定会出去(城里),即使我这一代出不去,我儿子也会出去,何必为了这个地界田界来争呢。我们进城卖掉老家房子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少这一寸的地而少卖钱;既然如此,为了今天的地界田界而使邻居两家之间关系闹别扭了不划算。在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在1990 年代之后村落内部的关联变得极为松散。为什么2000 年之后,外地人过来这里要过“安生”日子却又一定要闹呢?事实上他们扮演的是当地人1980 年代的角色,他们从山里面出来,认为这个地方好——田既大又成块,交通也方便,所以我的子孙在这个地方驻扎下去。他们的逻辑跟1980 年代本地人的逻辑一样,要为子孙守得每一寸土地。从这个争夺的逻辑背后,可以看到个体跟村庄的认同其实是极其重要的,外地人的行为只是从一个反向的逻辑证明地方认同观念对地方社会发展和地方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
外来资本进入到乡村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资本下乡做农业一般都要雇工,这些雇佣人员的构成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是否能挣到钱。如果老板是完全按照制度化的方式来进行管理,那他一定没有办法融入乡村;如果他要融入乡村,他一定要跟乡村比较重要的人建立某种特殊的关系,结拜兄弟,或者结拜其他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构建,就会将农场整体打包给当地人来委托其管理。他的经营是否成功,雇佣什么样的人也是非常的重要,否则就会出现当你种的玉米快要成熟的时候,全村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去偷你的玉米,大家好像不偷你的都觉得自己亏了。本地人自己种玉米,本地人绝对不会偷的,充其量说家里没玉米吃,随手掰两根玉米回去煮着吃,绝对不会拎着蛇皮袋一袋又一袋往家里拎。
刚刚举的例子和分析事实上说明进入乡村中间的人和各种资源主体是否跟村落之间发生有效关联对于乡村的发展和治理说来极其重要。当然,这背后也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需要反思。我们总认为现在乡村的各要素都在外流,但我们忽视了更多的要素在回流。刚才讲的是人,其实还有资源——这些年通过转移支付、精准扶贫、各种项目资金进去的以及通过资本下乡方式进去的都已经不少了。这些要素大量回流之后能否自然地形成乡村的复兴?不尽然,它还取决于这些要素是否能够重新完成乡村社会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一点极其关键,也是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最难的工作。这些要素进入乡村之后如果不能促进既有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甚至反过来破坏这些关系,那它们的进入只能导致乡村社会各种问题的激化。
第二点结合我自己做的基层治理谈一下这些年乡村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当乡村没有办法完成社会意义再生产时可能为乡村治理带来的危机。
关于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前几年有一个争论,讨论“皇权是否下县”,关注的焦点是在基层治理中是否有国家的官员和权力的触角,分析的切入点主要还是在乡村的基层治理中是否有国家的代理人在场。这是一种研究视角,在我看来,这种关注治理主体的视角可能会遮蔽治理中的一些关键性要素。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运用的治理规则的视角来展开分析。在这种视角下,什么人在治理不关键,关键的是用什么样的规则来进行治理,究竟是用地方性的规则还是用外来的公共规则来治理,这比治理者本身是否拥有正式的体制身份可能更为关键。因为我们在经验层面总是能够看到,治理者身份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那么清晰的,他可能既有体制内的身份,也有其他的关系,有些时候他体制内的身份恰恰是因为他非制度的、非正式的关系所带来的。
从治理规则的角度来看,朝廷在乡村基层治理时并没有将超地方性的规范强行在地方推行,这在法律史的研究中业已有较多的研究。他们发现,县官一般是不介入地方纠纷的处理,而是由地方社会依据地方的规则自行调节。依据情理法则而形成的规范成为地方社会秩序的主导,同时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制同乡村社会中人们的日常行为中的差序格局特征具有同构性,这种基层的治理被黄宗智和李怀印称之为“简约治理”和“实体治理”。这种治理形态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当代的治理实践就是“民不告官不究”,最典型的表征就是国家对村庄内部土地调整的治理。如果村民们一致同意调地,村庄是可以进行调地的;甚至有一小部分人不同意调地,只要他们不诉讼,不上访,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村庄自行进行处理,哪怕有些措施执行得并不符合政策。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治理形态就开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国家开始比较强行地推动公共规则进入乡村。这一转变与1990 年代中期乡村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直接的关系。面对干群关系的紧张,国家自上而下推动依法治国,法律这种外来的公共规则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基层的官员,基层官员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行为。这一改变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当这个公共规则进来之后,原有地方规则内在的等级性被打破了。
我们都知道,所有人在互动的时候背后都会建构一个行为的合法性,前不久刘世定教授在他的一次讲座中就指出,每一个人都是携带着自己的规则来与他人互动的。我所要强调的是,规则与规则之间是具有等级性的。乡村中的人们都知道,道理之间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规则之间的等级性是由地方性的权力和权威来维系,当公共规则进入乡村之后,它建立的是普遍性秩序,强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这与地方社会的公平正义观是不一定相契合的。刘志伟教授在研究明朝税赋的时候就强调,朝廷在税赋的分担上特别强调针对家庭人丁的多寡、产业的厚薄来进行差异化对待,明代税赋中的“纳粮当差”就呈现了这种差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支配行动发生的公平观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公平,而是一个与身份甚至情景相对应的正义。
今天做基层治理的学者都知道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核心其实是“有问题不轻易上交,而是在地化解”。既然是在地化解,则一定不能完全按照条条框框和制度来一板一眼地执行。枫桥经验背后所呈现的是上层与基层(地方)治理的双轨制。在这种治理结构中,地方性的规范能够执行一定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比如基层干部中有一定相当比例的从村干部中选拔上来的干部,这一批人谙熟地方事务的处理之道。在很多地方,这些人构成了乡镇管区干部队伍的核心。这种治理的双轨特征在当下逐渐变成了单轨,即政府开始用公共规则替代地方性的规范。当适用于城市的、普遍性的公共规则往下延伸到乡村时,公共规则的善果往往未先得,而恶果却先得。这种双轨变单轨,首先导致的恶果是乡村社会内生的具有等级性的社会规则体系发生坍塌。当内生的等级性秩序坍塌时,每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将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拿出来,由此低成本地达成有效一致变得不可能,农民的机会主义被不断放大,“为了自己多得一块钱,哪怕由此带来其他人多付一万块钱的代价”也可能发生。为了应对这种治理规则等级性坍塌带来的治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很多时候基层引入灰色势力来参与治理。灰色势力参与地方治理,事实上是当没有体现合法性力量可以维系不同规则之间的等级与有序时,灰色势力客观上依据其拥有的恶与黑的势力来重塑规则内部的等级性和秩序,当然这种重塑未必与地方社会的正义观相契合,这也恰恰构成了当前扫黑除恶的背景与前提。
规则内部等级性的坍塌也构成我们去理解今天诸多农村制度变迁的关键。比如,这两年关于农村土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农田按户连片耕作,这是湖北荆门的经验。我们去荆门农村调研后发现,按户连片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乡村规则内部等级体系坍塌后,农民围绕农地经营进行的制度创新。在荆门,我去一个小组长家调研,他说按户连片让他的地块少了很多,我们到他的地里一看就明白了,按户连片解决的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规模化问题。他家的一片地集中后仍然有十多块,每块只有1~2 分。我站在地头,问他哪些是他的地,他说地里正在放水,水能流到的地方都是他的。看到这里我就明白,按户连片核心解决的问题不是分散地块难以机械化的问题,而是解决相互性的问题,他放水、播种和收割都不用从其他人的田里过,也不依赖其他地块农户的农时安排。为什么相互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变得很关键,因为以前有小组长和村干部,这些村组干部可以也能够进行有效协调,人们也知道什么是大道理什么是小道理,小道理是说不过大道理的;现在你会发现规则之间没有等级性了,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样治理与协调变得成本极高。按户连片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通过调整土地的空间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要解决规则等级性坍塌带来的治理困境问题。
当我们重新回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去处理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问题和农户生计问题,而且也是跟这一套乡村规则体系、社会价值有诸多关联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所勾连出来就不再仅仅是产业、区域和个体的问题。